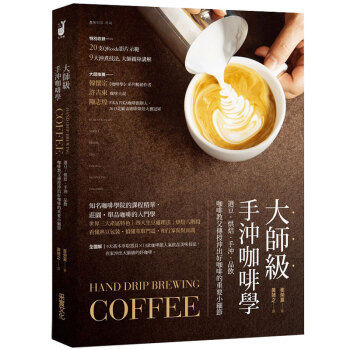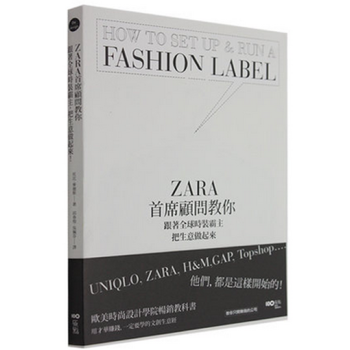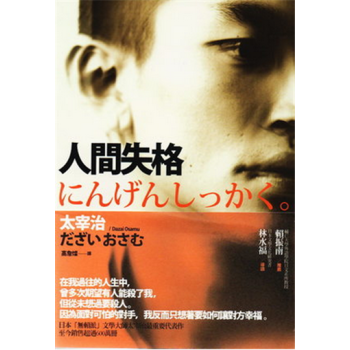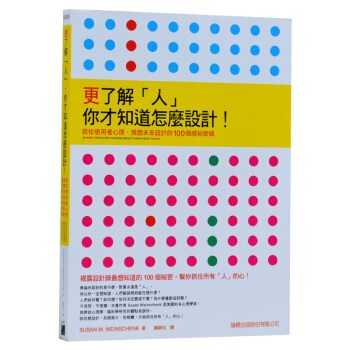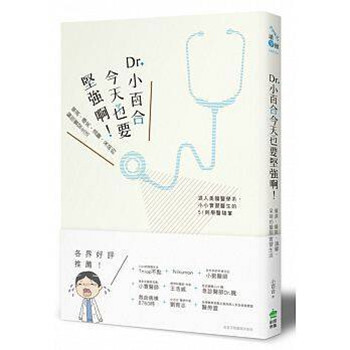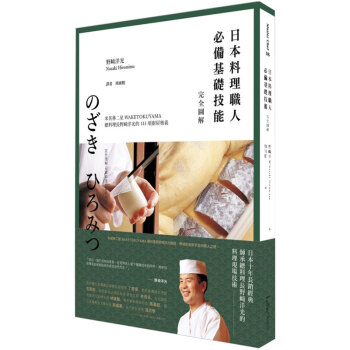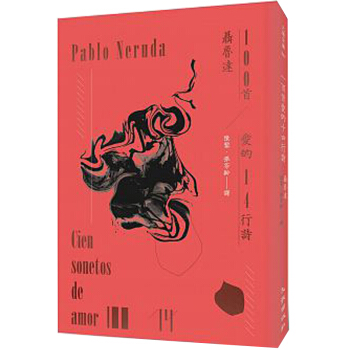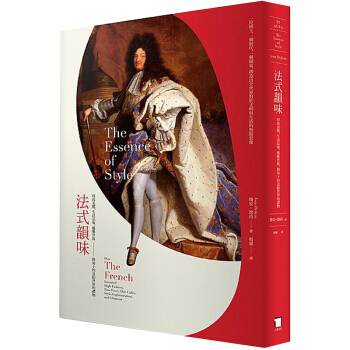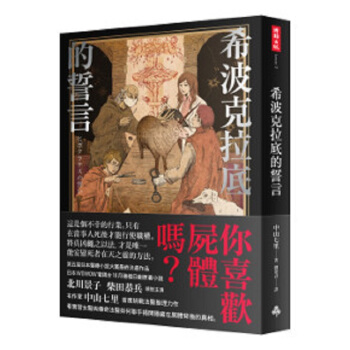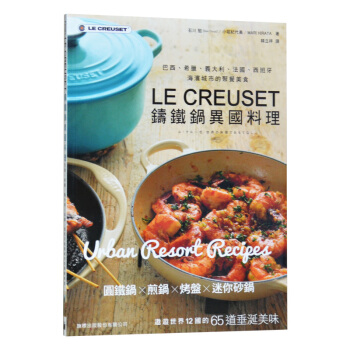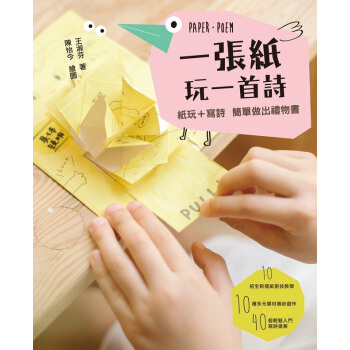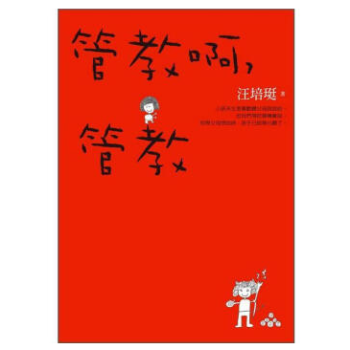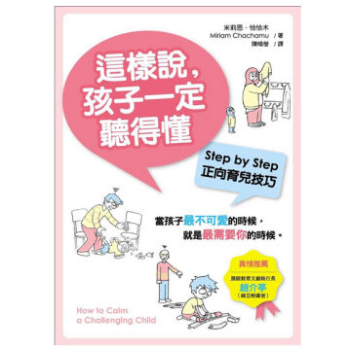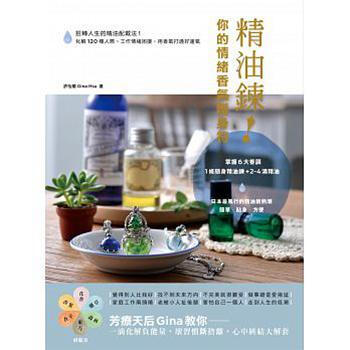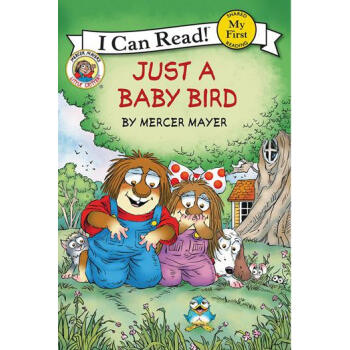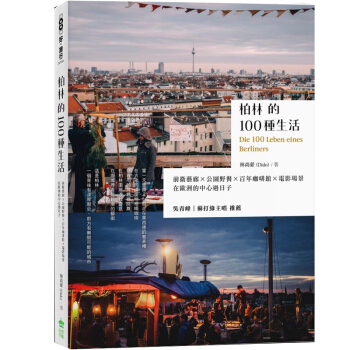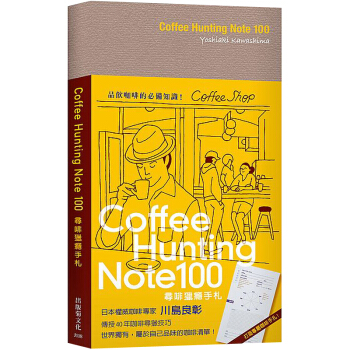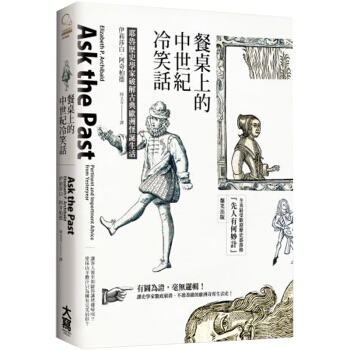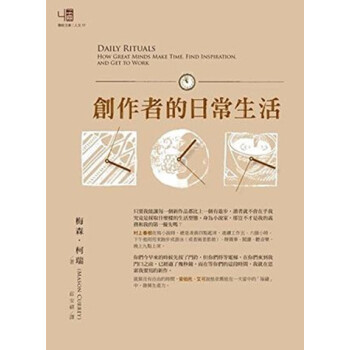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书名: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作者:梅森·柯瑞 (Mason Currey)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4年4月4日
ISBN:9789570843743
页数:288
尺寸: 18.6 x 12.8 x 2.4 cm
装帧:平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容簡介
完全透視偉大創作者的日常生活與時間分配!
村上春樹的小說是怎麼寫出來的?
畢卡索、梵谷的名畫是怎麼畫出來的?
莫札特、貝多芬的交響樂是怎麼譜出來的?
偉大的心靈究竟如何規劃時間,創作不懈?
他們真的是天才嗎?還是具有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
161位古往今來偉大的哲學家、作家、作曲家、建築師和藝術家……
在《創作者的日常生活》裡,作者柯瑞一一敘述他們的日常工作習慣,
激勵你建立自己的創作儀式!
柯瑞書寫過去四百年來161位偉大創作者每天怎麼分配時間,運用自己的能力,如何安排他們的作息,發揮創意和生產力。藉著撰寫這些人物日常生活平凡的細節,提供新鮮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個性和生涯,描繪出這些藝術家在習慣驅使之下有趣而細微的肖像。
創作者怎麼才能一邊在賺錢餬口之餘,又能創作出意義深遠的作品?舒適和創造力是否互不相容,抑或正好相反:日常生活的基本舒適是持久創意工作的先決條件?本書提供各種例子,說明形形色色各種聰穎而成功的人物如何面對這許多現實的挑戰,說明了許多宏大的創作憧憬如何轉譯為每日的工作;人的工作習慣如何影響工作本身,反之亦然。
知名創作者的工作習慣
例如:
只要我能讓每一個新作品都比上一個有進步,讀者就不會在乎我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生活型態。身為小說家,那豈不才是我的義務優先嗎?
村上春樹在寫小說時,總是凌晨四點起床,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下午他則用來跑步或游泳(或者兩者都做)、辦雜事、閱讀、聽音樂,晚上九點上床。
你們今早來的時候先按了門鈴,但你們得等電梯,在你們來到我門口之前,已經過了幾秒鐘。而在等你們的這段時間,我就在思索我要寫的新作。
就算沒有自由的時間,安伯托艾可說他依舊能在一天當中的「隙縫」中,發揮生產力。
當我在寫書或故事時,總是一見黎明就立刻振筆疾書。那時沒有任何人會打擾你,天氣可能或涼或冷,而你開始工作,邊寫就邊暖和起來。
海明威成年之後,天天都很早起,早上五點半或六點,曙光一現就醒來,即使前一晚爛醉如泥依舊如此。
時間很短,我的精力有限,辦公室是一團混亂,公寓則喧鬧不休。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
1908年,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勞工意外保險局找到一份差事,……但卡夫卡依舊覺得自己受到束縛。當時他和家人住在一間狹窄的公寓裡,唯有在深夜大家都熟睡之後,才能專心寫作。
規範熱情可靠的方法,就是規範時間。
詩人奧登認為像軍事行動般精準的生活,對他的創造力有其必要,是馴服他自己時間表靈感繆思的方法。
我先喝茶,然後大約十點時開始工作,一直到下午一點。接著我拜訪朋友。等到下午五點,我再回頭工作,直到九點。接續上午的工作對我毫無困難。
波娃在工作上很少有困難,恰巧相反──每當她休年假,要消磨兩三個月的假期時,卻常在放下工作幾週後,覺得無聊而不自在。
……我不用電,自己燒火開爐。到晚上,我點起舊油燈。這裡沒有自來水,我從井裡打水來用,自己砍木頭,煮食物。這些簡單的動作讓人簡單;而要簡單是多麼困難!
在整個1930年代,榮格以波林根塔樓為遠離都市塵囂的隱居之所,他在那裡過著工作狂的生活。
我一定很像咬著骨頭的狗,牠們偷偷摸摸的溜走,接著大概有半個小時,你看不到牠們的身影,然後牠們鼻子上沾著泥回來,一副不自在的模樣。
阿嘉莎克莉絲蒂在自傳中坦承,即使在她寫了十本書之後,依然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
我會吃巧克力奶昔和四、五、六、七杯咖啡──加很多糖,巧克力奶昔裡也有很多糖,是很濃的奶昔,裝在銀色的高腳杯裡。我會因為攝取這麼多糖而興奮莫名,腦中一下湧上許多點子!
大衛林區另一個想點子的方法是他自1973年以來天天都做的超覺靜坐。
隨著你的身心習慣每天晚上固定的睡眠──六個小時、七個小時,甚至睡滿醫師推薦的八個小時,你也同樣能訓練清醒的心智充滿創意地睡眠,並且創作出充滿想像力的清醒的夢,而那就是成功的小說作品。
史蒂芬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寫作,包括他的生日和假日,而且他從不讓自己在達到每天兩千字的字數限額之前停筆。
媒體推薦
本書值得推薦之處在於,它以精薄短小的傳記綱要彰顯了創意人日常作息的無限多樣、難以捉摸的愚蠢瘋狂和不變永恆。
──《華爾街日報》
一頁接著一頁,我們可以由數十甚至數百年把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創意人工作習慣中,得到不少啟示……要是你對古往今來知名的作曲家、作家,和畫家的工作習慣感到好奇,或者想要尋找方法提升你的創作習慣,那麼本書就能給你莫大的啟發。
──《今日美國報》
《創作者的日常生活》對創意人來說,是令人鼓舞的讀物,而我們其他人,則能夠藉此一探那奧妙的創作世界。
──羅娜布林利(Rona Brinlee),書籤書店(The BookMark),為全美公共廣播電台(NPR)作評
導言
一年半以來,幾乎每週一到週五的早上,我都五點半就起床,刷牙洗臉,泡杯咖啡之後,就坐下來寫過去四百年來一些偉大的心靈如何面對這時間的要務──也就是他們每天怎麼分配時間,運用自己的能力,如何安排他們的作息,發揮創意和生產力。藉著撰寫這些人物日常生活平凡的細節──他們什時候睡覺、吃飯、工作、憂慮,我希望能夠提供新鮮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個性和生涯,描繪出這些藝術家在習慣驅使之下有趣而細微的肖像。「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能說出你是什麼樣的人。」這是法國美食大師布里亞薩瓦航(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的名言,而我要說,告訴我你什麼時候吃,還有接下來睡不睡午覺。
就這方面而言,這是本看似蜻蜓點水的書,談的是創作活動的背景,而非其產品;內容是製造,而非意義。
但難以避免的是,這也是一本相當私人的書(小說家約翰契佛認為,即使寫一封商業書信,也不可能不流露出一點你的自我,可不是嗎?)在本書背後,我所關懷的主題正是我在自己生活中所奮鬥的問題:怎麼才能一邊在賺錢餬口之餘,又能創作出意義深遠的作品?是該完全把自己奉獻給某個計劃,還是每天撥出一小部分時間?要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做你想要完成的每一件事,那麼你是否非得放棄一些事物(睡眠、收入、整潔的房屋),還是可以濃縮你的活動,以更少的時間完成更多的事物,像我爹經常訓我的「要工作得聰明一點,而不是辛苦一點」?更廣義的說,舒適和創造力是否互不相容,抑或正好相反:日常生活的基本舒適是持久創意工作的先決條件?
在下面的篇章裡,我不假裝能解答這些問題,其中有些或許根本不能回答,或者只能依不可靠的個人狀況作個別的回答。但我努力提供各種例子,說明形形色色各種聰穎而成功的人物如何面對這許多同樣的挑戰。我希望能說明許多宏大的創作憧憬如何轉譯為每日少量的工作;人的工作習慣如何影響工作本身,反之亦然。
本書的書名雖然是《創作者的日常生活》,但我寫作的重點其實卻在於人們工作的規矩、習慣。這樣的詞彙雖然聽來平凡,甚至缺乏思考,遵循日常的作息,就像自動駕駛一樣。但日常作息其實也是一種選擇,或者是一整體系列的選擇。如果做得對,就可以當作精確測定的機制,得以運用許多有限的資源:時間(有限的資源)以及意志力、自我紀律、樂觀的態度。固定而實在的作息就能為人的心力刻劃出可靠的溝槽,阻擋起 伏不定的情緒。這是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喜爱的主題。他認為人刻意讓部分人生成為自動駕駛模式。他說,養成好習慣就能讓我們「解放心智,達到真正有趣的行動領域。」諷刺的是,詹姆斯本人卻有拖延的毛病,永遠不能堅持規律的作息。
巧的是,正是因為一番拖延,反倒使我創作出本 書。那是2007年7月一個週日下午,我正獨自坐在我 所工作的那家小建築雜誌灰撲撲的辦公室裡,想要趕出次日截稿的稿件。只是我非但沒有全力以赴,趕緊努力,反而卻瀏覽《紐約時報》網路報,清掃我的辦公空間,在小廚房裡泡咖啡,總之就是在浪費時間。這是再熟悉不過的困境,我本是「早起型」的人,在早上可以十分專注,但一過午餐時間就發揮不了什麼作用。那天下午,為了要讓我對自己這種頗為不方便的偏好(誰會想每天大清早五點半就起床?)釋懷,我就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其他作家的工作習性,這種資料並不難找,而且非常有意思。我不禁想到該有人把這些軼事收集起來──因此當天下午我就成立了「日常作息」(Daily Routines)部落格(我那篇雜誌稿到次日早上趕在後一分鐘驚險交卷),如今就成為這本書。
這部落格原是無心插柳;我只是把我由傳記、雜誌側寫、報紙訃聞等等文章上看來名人的作息貼在部落格上。至於本書,我搜羅了更廣泛、資料也更深入的作品,同時也儘量維持文章的簡短和多樣,以保持其吸引力。
我儘可能讓我的人物自己發言,用引述自他們的信件、日記,和訪問中的言語。我也由二手資料搜羅了他們作息的摘要,如果有別的作家精彩的說明了主題人物的習慣,那麼我就引述其大作,而不再重寫。我要在此說明的是,若非採用數百位傳記作家、新聞記者,和學者的研究與作品,本書根本無法成書。 在匯整本書的各個條目時,我也一直謹記V. S. 普瑞契特(V. S. Pritchett)在1941年寫的一段話。普瑞契特在寫到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時,提到這位偉大 史學家極其勤勉,即使在服兵役時,吉朋依舊找出時間來作學術研究,他行軍時還隨身帶著羅馬抒情詩人賀拉 斯(Horace)的作品,在帳篷裡則讀異教徒和基督教神學書籍。普瑞契特寫道:「這些偉大的人物遲早都會變成一個模樣,他們從不停止工作,絕不浪費一分鐘,這真教人沮喪。」
哪一個有抱負的作家或藝術家會沒有這樣的感慨呢?看到過往偉人的成就一方面具有啟發性,一方面卻又教人洩氣。但是當然,普瑞契特還是錯了。因為在每一位孜孜不倦、從不停止工作,也絕不自我懷疑或出現信心危機,教我們這些凡人自嘆不如的吉朋身邊,同樣也會有一個威廉詹姆斯或者法蘭茲卡夫卡這種虛擲光陰的偉大心靈,他們徒然的等待靈感降臨,體驗到瓶頸和文思枯竭的折磨,因為懷疑和不安而焦慮痛苦。在現實中,本書描繪的大部分人物則都介於其中──他們全心投入日常的工作,但卻永遠對自己的進展沒有完全的信心;永遠小心翼翼,生怕有朝一日前功盡棄。所有的人都找出時間完成他們的工作,但究竟他們怎麼架構自己的生活,達到這樣的目標,則有無盡的變化。
本書談的就是這樣的變化,而我希望各位讀者能夠覺得受到鼓舞,而非沮喪打擊。在寫作期間,我常 想到卡夫卡在1912年寫給戀人菲利絲包爾(Felice Bauer)信中的一段話。他對自己狹隘的居住環境和呆板的日常工作感到洩氣,不由得抱怨:「時間很短,我的精力有限,辦公室是一團混亂,公寓則喧鬧不休。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可憐的卡夫卡!然而我們之中又有誰能期望過著輕鬆愉快的生活?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大半的時候都是寸步難行,而卡夫卡巧妙的迂迴前進與其說是破釜沉舟,不如說只是個理想。而接下來的篇章則告訴你該如何迂迴前進。
內文選摘
W. H. 奧登(W. H. Auden,1907–1973,英國詩人、劇作家、文評家,後歸化美國)
「智者的常軌,乃是雄心之明證。」奧登在1958年如是寫道。如果這話是真的,那麼奧登自己就是當年雄心勃勃的人。這位詩人講究準時到了強迫的地步,終其一生都以精準的分秒過活。他的一位客人曾說:「奧登一再的看表,不論是吃、喝、寫作、購物、玩填字遊戲,甚至等郵差按鈴,都分秒不差,並且還有相配的作息。」奧登認為像軍事行動般精準的生活,對他的創造力有其必要,是馴服靈感繆思按照他自己作息時間的方法。他曾說:「現代的禁欲主義者知道,規範熱情可靠的方法,就是規範時間:決定你這一天想要或者該要做什麼,接著天天在準確的同一時刻去執行,熱情就不會為你惹上麻煩。」
奧登每天早上六點一過就起床,沖好咖啡,或許玩一下填字遊戲,然後馬上就開始工作。他的頭腦由上午七點到十一點半清楚,而他很幾乎從不會辜負這一段時光。(他很不屑夜貓子:「惟有『世上的希特勒』才會開夜車,真誠的藝術家絕不會這樣做。」奧登通常在午飯之後又重新伏案工作,直到傍晚。晚上六點半,詩人準時開始餐前雞尾酒的輕鬆時光,他親自為自己和客人調製幾杯伏特加馬丁尼。接著上晚餐,提供大量的葡萄酒,然後再斟上更多的葡萄酒,大家也打開了話匣子。奧登很早就上床,從不會超過十一點,他年紀大了之後,上床時間更提前到九點半。
為了維持自己的活力和專注力,這位詩人服用安非他命,每天早上吃一劑苯丙胺(Benzedrine),就像許多人每天吃維他命丸一樣習以為常。晚上他則服用速可眠(Seconal,又稱西可巴比妥,中樞神經抑制劑)或其他鎮靜劑助眠。這樣的習慣──他所謂的「化學人生」,維持了二十年,直到後来藥力失靈為止。奧登認為除了酒精、咖啡,和香菸之外,安非他命也是「心靈廚房」中的「省力工具」,儘管他明知「這些裝置非常粗糙,很容易傷害廚師,而且老是會出差錯。」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創始人)
「我總是匆匆忙忙開始工作,雖然大體說來,我並不喜歡開始一天。」1965年,波娃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時這麼說:「我先喝茶,然後大約十點時開始工作,一直到下午一點。接著我拜訪朋友。等到下午五點,我再回頭工作,直到九點。接續上午的工作對我毫無困難。」的確,波娃在工作上很少有困難,恰巧相反──每當她休年假,要消磨兩三個月的假期時,卻常在放下工作幾週後,覺得無聊而不自在。
雖然波娃以工作為優先,但她的日常作息也以她和沙特(Jean-Paul Sartre)的關係為重心。這段關係由1929年一直延續到他1980年去世為止。(他們的關係是知性的夥伴,又帶著一點詭異的性成分。根據沙特在關係之初所提出的條約,雙方都能擁有其他的愛人,但必須把一切坦白告知對方。)一般說來,波娃上午都獨自工作,接著和沙特共進午餐。兩人下午在沙特的公寓裡沉默的一起工作。晚上,他們一起去參加沙特預定參加的政治或社交活動,要不然就一起去看電影,或者在波娃的公寓裡喝威士忌,收聽廣播。
法國製片人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1952至59年是波娃的戀人,他曾親自體驗過這樣的安排。他描述兩人在波娃巴黎公寓同居之始的情況如下:
一天早上,我想賴床,但她已經起身漱洗,坐到工作桌前。「你在那邊工作,」她指著床說。所以我起身坐在床沿吸菸,假裝在工作。我不記得她有向我說任何一個字,直到午飯的時間來到。接著她去找沙特,他們共進午餐,有時我也加入。然後到下午,她去他家,兩人工作三、四小時。接著是開會和約會。稍後我們見面,共進晚餐,而她和沙特幾乎總會單獨坐在一起,由她評論他當天所寫的作品。接著她和我回到公寓睡覺。沒有宴會、沒有招待會,沒有布爾喬亞所著重的價值。我們完全避免這一切,只在乎基本的事物。這是一種整潔乾淨的生活,是刻意創造的簡單,讓她能做她的工作。
卡爾榮格(Carl Jung,1875–1961)
1922年,榮格在瑞士小村莊波林根(Bollingen)買了一小塊地,在蘇黎世湖畔興建了兩層樓的石造房屋,接下來數十年,他修改擴建了這幢世人稱為波林根塔樓(Bollingen Tower)的屋子,增建了兩座較小的附樓,並用牆砌了庭院,戶外有很大的火坑。不過即使有這些增建,房屋本身還是原始的居處,凹凸不平的石板地面上,既沒有地板,也沒有地毯,既沒有電力,也沒有電話。屋裡靠柴火取暖,烹飪則是用油爐,人造光源是油燈。水得由湖裡打來煮開飲用(後来才裝了手動抽水機)。容格寫道:「要是十六世紀的人住進這幢房子,那麼只有煤油燈和火柴對他是新鮮事。至於其他部分,他都很熟悉。」
在整個1930年代,榮格以波林根塔樓為遠離都市塵囂的隱居之所,他在那裡過著工作狂的生活,每天有八、九小時都在看病人,並且經常講課和主持研討會。也因此,幾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是在假日寫的。(儘管許多病人都依賴榮格,但他還是毫不避諱大大方方的去休假,他說:「我已經明白,如果累了,需要休息了,還依舊去工作的人是傻瓜。」)
在波林根塔樓,榮格上午七點起床,向他的鍋碗瓢盆道過早安,然後「花很長的時間準備早餐,通常都包括咖啡、義大利香腸、水果、麵包,和牛油,」傳記作家羅納德海曼(Ronald Hayman)記載道。他通常會在早上用兩個小時專心寫作,剩下一整天的時間則在私密的書房裡畫畫或沉思、到山上去散個長步、接待客人,以及回那每天源源不絕的來信。他在下午兩、三點時喝茶;晚上則喜歡為自己準備豐盛的一餐,往往先來一點開胃酒,他稱之為「晚酌」(sun-downer)。上床時間則為十點。「在波林根,我置身真實的生活,我是深沉的自我,」榮格寫道:「……我不用電,自己燒火開爐。到晚上,我點起舊油燈。這裡沒有自來水,我從井裡打水來用,自己砍木頭,煮食物。這些簡單的動作讓人簡單;而要簡單是多麼困難!」
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海明威成年之後,天天都很早起,早上五點半或六點,曙光一現就醒來,即使前一晚爛醉如泥依舊如此。他的兒子葛瑞格雷說他似乎不受宿醉的影響:「我父親總是神清氣爽,彷彿剛在防音室戴上眼罩睡了一個甜覺一樣。」1958年海明威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說明了他怎麼運用那些早起的時間:
當我在寫書或故事時,總是一見黎明就立刻振筆疾書。那時沒有任何人會打擾你,天氣可能或涼或冷,而你開始工作,邊寫就邊暖和起來。你讀讀自己寫了些什麼,而由於你在停筆時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因此你就由那裡接著寫,寫到你還有靈感,而且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之後停筆,然後去過你的日子,直到第二天你再拿起稿子來為止。你早上六點已經起身,可能一直寫到中午,或者更早就結束。等你停筆時,你一方面是空虛的,但另一方面卻又一點也不空虛,而是實在的,就彷彿你已經和你所愛的戀人行了魚水之歡一樣。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傷害你,沒有任何事會發生,沒有任何事有任何意義,直到第二天你再做一次。難以度過的是在來到第二天之前的等待。
海明威並不像流行的傳說那樣,每一次寫作都先削尖二十枝二號鉛筆──「我從沒有同時擁有二十枝鉛筆,」他說麼告訴《巴黎評論》──不過他的確還是有自己的寫作怪癖。他站著寫作,面對著及胸高的書架,上面放著一台打字機,打字機上面還有一塊木製的閱讀板。他的初稿是用鉛筆寫在斜放在板子上的葱皮紙(onionskin paper,薄的半透明紙)上,如果寫作順利,海明威就會抽掉板子,直接用打字機。他在圖表上追蹤自己每天的產量──「這樣才不會欺騙自己,」他說。如果寫作進行得不順利,他就會放下書稿,先去回信,這讓他能夠休息一下,暫時擺脫「可怕的寫作責任」──或者,如他有時候說的,「可怕作品的責任」。
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1949年生)
村上春樹在寫小說時,總是凌晨四點起床,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下午他則用來跑步或游泳(或者兩者都做)、辦雜事、閱讀、聽音樂,晚上九點上床。「我保持這樣的作息,天天如此,從不改變,」2004年他告訴《巴黎評論》說:「這樣的重複本身就很重要;它是一種催眠。我為自己催眠,以求更深入我的心靈。」
村上春樹曾說,為了在寫小說的這段時間維持這樣的重複,需要的不只是心理上的紀律:「身體的強健就如藝術的敏感一樣必要。」他先在東京經營一家小爵士樂咖啡館,幾年後打出專業作家的招牌,但他發現這種坐著不動的生活方式讓他體重增加很快,而且他還吸菸到一天六十支。他很快就下定決心要改變自己的習慣,帶著妻子遷往鄉下,戒了菸,減少喝酒,並且改變飲食,以蔬菜和魚為主。他還每天跑步,而且一直持續這個習慣,逾四分之一個世紀。
村上春樹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認這種自訂作息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它沒有留多少時間社交。他寫道:「你一再拒絕人們的邀請,結果冒犯了他們。」但他認為他和讀者的關係才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只要我能讓每一個新作品都比上一個有進步,讀者就不會在乎我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生活型態。身為小說家,那豈不才是我的義務優先嗎?」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1908年,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勞工意外保險局找到一份差事,他很幸運,這工作是眾人艷羨的「一班制」,意思是辦公時間由上午八、九點到下午兩、三點。雖然比起他先前在另一家保險公司工時長、而且常加班的情況,這已經改進很多,但卡夫卡依舊覺得自己受到束縛。當時他和家人住在一間狹窄的公寓裡,唯有在深夜大家都熟睡之後,才能專心寫作。他在1912年寫給戀人菲利絲包爾(Felice Bauer)的信中說:「時間很短,我的精力有限,辦公室是一團混亂,公寓則喧鬧不休。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他在同一封信中描述自己的作息:
由八點到兩點或兩點半在辦公室,午餐至三點或三點半,之後上床睡覺(通常只是設法入睡;一整週來我在睡夢中除了蒙特內哥羅人(Montenegrins,歐洲民族之一)之外什麼也沒有,他們的形象清楚得教人心悸,讓我頭痛,我可以看到他們複雜服飾上的有細節),直到晚上七點半,接著裸身在窗戶前面作十分鐘運動, 然後散步一小時──可能獨自一人,也可能和馬克斯(Max Brod),或者和其他朋友,接著和家人共進晚餐(我有三個姐姐,一個已婚,一個已經訂婚,而還保持單身的這一個,當然就成為我喜愛的姐姐,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對其他兩位姐姐的情感);到了十點半(但通常要一直等到十一點半 )我坐下來寫作,依我的力氣、意願,和運氣,一路寫到一、二、三點,有一次甚至寫到早上六點。接著再如前面一樣做運動,但當然會避開要費力的動作,盥洗,通常在心臟有點疼痛,胃部肌肉痙攣的情況下上床。接著我挖空心思努力想入睡,但──那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不可能一邊睡[K先生(卡夫卡小說中的人物)甚至還要求無夢的睡眠)],一邊又掛念著自己的工作,並且想要解決明明就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第二天究竟會不會收到你的信;如果有,又是什麼時候送來。因此夜晚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醒著的,另一部分則是無眠的。而如果我要長篇大論告訴你,而你又願意聆聽,那麼恐怕它永遠結束不了。因此如果第二天在辦公室,我只能以僅餘的丁點力氣開始工作,也就不足為奇。在我要走去找打字員的長廊上,有個像棺材一樣的手推車,用來搬動檔案和文件。每一次我走過它的旁邊,都覺得它是為我而設,正在等待著我。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
克莉絲蒂在自傳中坦承,即使在她寫了十本書之後,依然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在填表的職業欄時,她除了寫「家庭主婦」之外,也從沒想到要寫什麼別的。她還說:「有趣的是,一結了婚,我對自己寫的書都忘得一乾二淨。我想我可能是太享受普通的生活, 結果寫作成了偶一為之的工作。我從沒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作為書房,或者可以躲起來寫作。」
這為新聞記者帶來了無盡的麻煩,因為他們必然想要拍這位作家伏案工作的照片,但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所在。克莉絲蒂寫道:「我需要的只是穩固的桌面和打字機。主臥室大理石洗手台面就是個寫作的好地方,不是吃飯時間的飯桌也很適合。」
許多朋友都和我說:「我從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寫你的書,因為我從沒見過你當著我們的面寫作,甚至也沒看過你到別的地方去寫作。」我一定很像咬著骨頭的狗,牠們偷偷摸摸的溜走,接著大概有半個小時,你看不到牠們的身影,然後牠們鼻子上沾著泥回來,一副不自在的模樣。我也差不多,如果我打算要寫作,就會覺得有點尷尬。不過一旦我溜走了,關上門,不讓人打擾我,那麼我就可以全速前進,完全沉醉在我所做的事情裡。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年生)
這位義大利哲人和小說家四十八歲時發表的小說《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一鳴驚人。他表示自己沒有固定的寫作時間表。他在2008年說:「沒有規則。對我來說,要有作息表是不可能的。我可能在上午七點開始寫作,一直到凌晨三點方休,中間只停下來吃個三明治,但有時我卻一點都不覺得有寫作的必要。」不過在訪問者的追問之下,艾可還是承認他的寫作習慣並非始終是這樣兩極化。
要是我在鄉下的家,在蒙特費爾羅(Montefeltro)的山頂上,那麼我就有固定的作息。我打開電腦,接收電子郵件,開始讀東西,然後一直寫到下午。接著我到村子裡,在酒吧喝杯酒,看看報紙,然後回家,晚上看電視或DVD,到十一點,再工作一下,到凌晨一兩點。我在那裡能有固定的作息,是因為沒有干擾。如果我在米蘭或在大學裡,就不能掌控自己的時間──總有人會決定我該做什麼。
不過,就算沒有自由的時間,艾可說他依舊能在一天當中的「隙縫」中,發揮生產力。他告訴 《巴黎評論》的記者說:「你們今早來的時候先按了門鈴,但你們得等電梯,在你們來到我門前之前,已經過了幾秒鐘。而在等你們的這段時間,我就在思索我要寫的新作。我可以在洗手間、在火車上工作。游泳時我也能想出很多事物,尤其是在海中。在浴缸裡雖然比較少,但也一樣可以。」
大衛林區 (David Lynch,1946年生,美國電影、電視導演、編劇)
「我喜歡一切井井有條,」林區1990年對記者這麼說:
七年來我都在「鲍伯的大男孩」(Bob’s Big Boy)漢堡店吃飯。我都在下午兩點半,午餐時段已過才去。我會吃巧克力奶昔和四、五、六、七杯咖啡──加很多糖,巧克力奶昔裡也有很多糖,是很濃的奶昔,裝在銀色的高腳杯裡。我會因為攝取這麼多糖而興奮莫名,腦中一下湧上許多點子!我會把它們寫在餐巾紙上,就像我有紙在書桌上一樣。我只要記得帶著筆就好,但女服務生也會給我一枝筆,只要我記得走時要還。我在鮑伯的店裡想出了許多點子。
林區另一個想點子的方法是他自1973年以來天天都做的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他在2006年的出的書《大衛林區談創意》(Catching the Big Fish)中說:「三十三年來,我從沒有錯過一次靜坐,我上下午各靜坐一次,每次約二十分鐘,然後去忙我的事。」如果他正在拍攝電影,那麼有時他會在一日將盡時再靜坐一次。「我們浪費這麼多時間在別的事物上,」他寫道:「一旦你把這個也加進來,養成規律,它就會自然的融入其中。」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狄更斯是多產作家──他寫了十五本小說,其中有十本厚逾八百頁,另外他還寫過無數故事、散文、信件,和劇本。不過要是達不到某些先決條件,他是無法寫出成果來的。首先,他需要絕對的安靜;他家的書房需要多裝一扇門,以阻隔噪音。另外,他的書房必須精心安排,書桌要放在窗戶前,桌上則要備妥他寫作的用具──鵝毛筆和藍墨水,放在幾件裝飾品旁邊,一小瓶鮮花,一大把裁紙刀,一片鍍金葉片,上面有一隻兔子棲息,另外還有兩個銅製小塑像(其中一個是兩隻肥蟾蜍正在決鬥,另一個則是一名紳士和一堆小狗擠在一起)。
狄更斯的工作時間非常固定,他的長子說:「沒有任何公務員比他更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再怎麼平凡、單調、傳統的工作,都不如他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創作時那般規矩準確,充滿效率。」他早上七點起床,八點早餐,九點進書房,待在裡面工作至下午兩點,短暫的休息一下,和家人午餐,在午休這段時間他神思恍惚,食不知味,幾乎一言不發,急著回到書桌前。在平常日子裡,他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完成大約兩千字,但若想像力一發作,他有時甚至可以寫出兩倍的字數。不過也有時候,他幾乎什麼也寫不出來,但他依舊謹守工作時程,心不在焉的亂塗亂畫,或者盯著窗外打發時間。
兩點二十分,狄更斯準時離開書桌,在鄉間或倫敦街頭散步三小時,一邊思索他的故事,一邊如他所描述的:「搜尋我想要編織故事的畫面。」他的妹夫記得:「他神采奕奕回到家,全身充滿活力,彷彿來自某個看不見的蓄水池。」不過狄更斯的夜晚卻很輕鬆,他在六點吃晚餐,然後和家人朋友一起消磨到午夜時才上床。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1931年生)
1950年代,身為年輕母親的孟若在照料兩個幼兒之餘,只要在做家事和育兒之外,一有零碎的時間就趕緊寫作。她常在下午趁著大女兒上學,小女兒午睡時,躲進自己的房間寫作。(孟若說小女兒那些年「可以睡很長的午覺」。)然而想要保持這樣雙重生活的平衡並不容易。當鄰居或熟人來訪,打斷了孟若的寫作時,她總不好意思告訴他們她正在工作;除了家人和摯友之外,孟若一直把她寫小說的事保密。1960年代之初,兩個孩子都上學之後,孟若在一家藥店樓上租了間辦公室好寫小說,但四個月後就放棄了;因為即使在那裡,饒舌的房東依舊干擾她,她幾乎什麼都沒有寫出來。儘管這些年來孟若固定發表短篇故事,但之後還是花了她幾乎二十年的時間,才寫出足夠出選集的材料。這本《快樂陰影之舞》(The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在1968年她三十七歲時出版。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年生)
史蒂芬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寫作,包括他的生日和假日,而且他從不讓自己在達到每天兩千字的字數限額之前停筆。他早上大約八點或八點半開始寫作,有時在十一點半就已經寫完,但通常要到下午一點半才達到目標字數。接著整個下午和晚上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午睡、寫信、閱讀、和家人共度,並且在電視上看職棒紅襪隊的球賽。
在他的回憶錄《史蒂芬金談寫作》(On Writing)中,他把寫小說比喻為「創意的睡眠」,而他每天晚上準備上床的寫作習慣是:
就像臥室一樣,你寫作的房間也該隱密,是你可以作夢的地方。必須要有日程表──每天大約同一時間進去,把上千字寫在紙上或磁片上之後才出來,讓你能夠養成習慣,就像你每天晚上大約都在同樣的時間上床,依同樣的規矩準備就寢準備作夢一樣。不論是寫作還是睡眠,我們都學會要保持身體的靜止,而同時我們也鼓勵心智大腦由日常生活平凡庸碌的理性思維解放。隨著你的身心習慣每天晚上固定的睡眠──六個小時、七個小時,甚至睡滿醫師推薦的八個小時,你也同樣能訓練清醒的心智充滿創意地睡眠,並且創作出充滿想像力的清醒的夢,而那就是成功的小說作品。
用户评价
这本小说简直是把人拉进了另一个时空,那种代入感太强了,读起来完全停不下来。作者的笔触细腻得让人心惊,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描绘得入木三分。你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尘土味,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欢愉。尤其是一些日常琐碎的细节,被赋予了生命力,不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元素。读完后,我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的是那些画面,那种情绪,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他们的生活。那种对生活本质的探寻,那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让人在合上书本后陷入长久的沉思。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评分我向来对叙事结构比较挑剔,但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着实精妙。它像一个多面体,从不同的切面去折射主题,每一个角度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信息,环环相扣,却又浑然一体。作者在时间线的处理上也颇具匠心,时而跳跃,时而聚焦,将过去、现在和潜在的未来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让故事的张力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脑海中重构情节线索,享受这种跟随作者思维迷宫探索的乐趣。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游戏,需要读者全身心地投入才能领略其全貌,绝对是文学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氛围营造能力简直是顶级的,让人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中。作者对于环境的细致描摹,不仅仅是背景板的作用,它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发展和行为选择。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特有的时代气息和地域风情,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声音的捕捉,都做得极为到位。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暂时逃离了现实的喧嚣,完全沉浸在故事营造的世界里。读到最后,我甚至有点不舍,仿佛要告别一群熟悉的朋友。这种依依不舍的情绪,恰恰证明了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它成功地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一块无法磨灭的印记。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担心阅读体验,毕竟这类题材的作品有时候会显得过于晦涩或沉闷。但是这本书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它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高潮迭起却又张弛有度,绝不拖泥带水,但也绝不让人感到仓促。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简直是出神入化,那些看似平实的语句中,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和情感张力。很多地方,我需要停下来,细细咀嚼那些句子,才能完全体会到其中深藏的韵味和哲理。读完后,我忍不住会翻回去重温一些章节,总能从中发现新的理解,这绝对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每一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就像品尝一坛陈年的老酒,越品越有滋味。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一种久违的阅读震撼,它不是那种情节跌宕起伏的商业小说,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直击灵魂的体验。作者用近乎于诗意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完整且自洽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角色的命运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弦。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人性时的那种毫不留情却又充满悲悯的态度。他没有把任何角色塑造成完美的圣人或纯粹的恶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灰度,都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和坚持。这种真实感,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同理心被极大地拓宽了,看待周围的人和事,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港版]堅守信念:給社工學生的30封信 /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704541771/57e1e1a2Nf71063e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