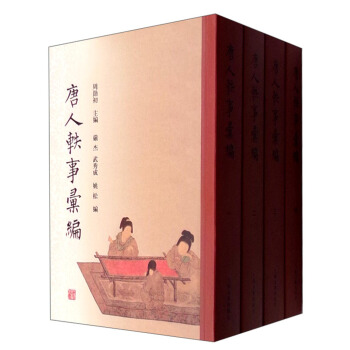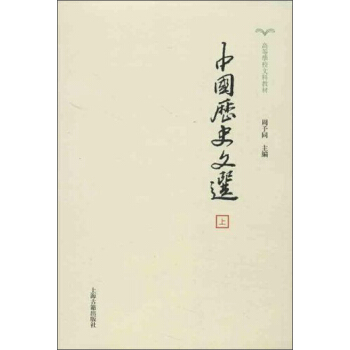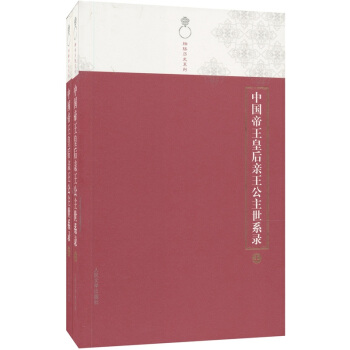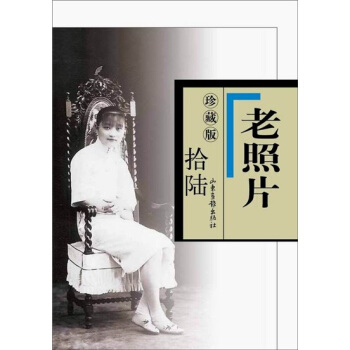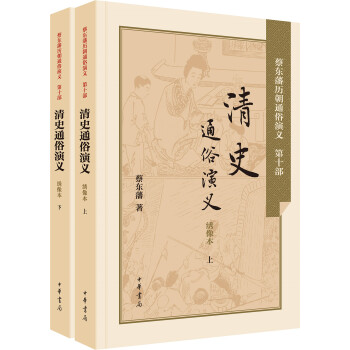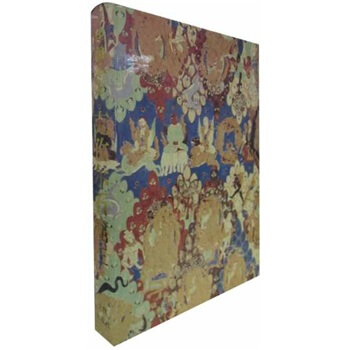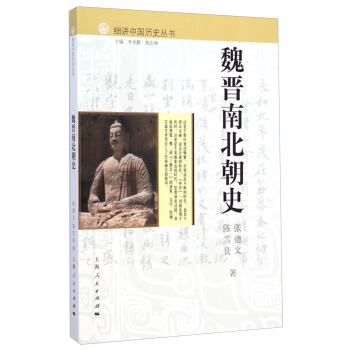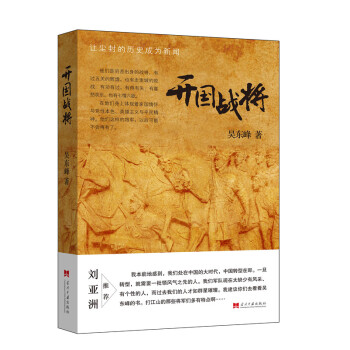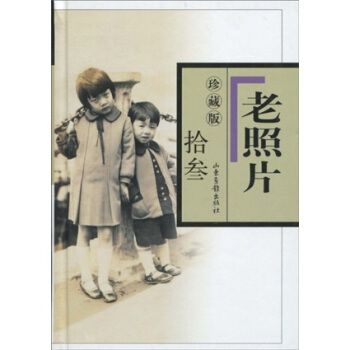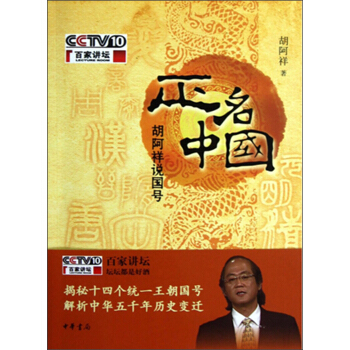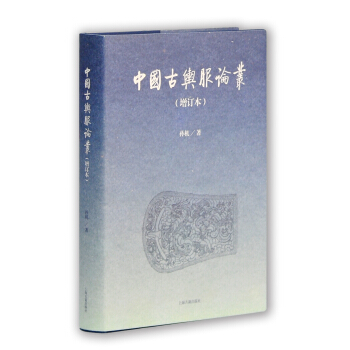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是对中国古代车舆、冕冠、服饰进行研究的论文集。书稿上编通过对实物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展开研究。通过对车舆各个细节、部位的探讨,作者孙机提出了中国古代车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这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各个时代冕冠、服饰的梳理,作者孙机透彻分析了中国服装史上的若干重大变革。书稿下编是对《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的校释,所引文献为第一手材料和好的版本,所引实物年代清楚、性质明确,为治舆服史者了解和利用古文献提供了方便。
作者简介
孙机,文物专家,考古学家。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山东青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79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1年,孙机开始随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进入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几十年来,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代车舆、冕冠、服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内页插图
目录
上编
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
中国古独辅马车的结构
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商周的“弓形器”
辂
“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周代的组玉佩
深衣与楚服
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
进贤冠与武弁大冠
汉代军服上的徽识
说“金紫”
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
从幞头到头巾
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中国古代的带具
霞帔坠子
明代的束发冠、(髟狄)髻与头面
下编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
凡例
卷一 总序、车舆
卷二 冕服、朝服、公服
卷三 常服、其他
图片目录
精彩书摘
“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
我国的独轮手推车发明于汉代,既有文献与图像可征,又为刘仙洲、史树青诸先生著文考证过,今日已成为定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前人也多认为是一种独轮车。然而“木牛、流马”是诸葛亮的一项重要创造。《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记》载晋·李兴祭诸葛亮文,其中说到他造的“木牛之奇,则非般模”。对之均推崇备至。晋·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在评价诸葛亮的成就时,有“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的话,也应是就他在连弩和“木牛、流马”等方面的创制而发。按《诸葛氏集》目录,其第一三篇为《传运》,可知诸葛亮在交通运输方面确有见地,所以他的独轮车应不同于汉代旧制。但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木牛、流马”的优越之处何在?尚无明确的答案。本文就此试加探讨。
汉代的独轮车名犖,又名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鹿车在敦煌卷子本句道兴《搜神记》引汉·刘向《孝子图》中作“辘车”。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说“鹿车”之“鹿”“当是鹿卢之谓,即辘轳也”。刘仙洲说: “因为这种独轮车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就把它叫作‘辘轳车’ 或‘鹿卢车’,并简称为‘辘车’ 或‘鹿车’。”其说固是。但所谓鹿车“裁容一鹿”,是否纯属望文生义的敷衍之词?却也并不见得。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之鹿车,只装载一件羊尊,可谓“裁容一羊”。羊尊常与鹿尊为类;如若此车改装鹿尊,就和《风俗通》之说相合了。
汉代画像砖、石上出现的鹿车,车型相当一致。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考察,可知它具有以下特点:
1.鹿车只用人力,不驾牲畜。不但《风俗通》说它“无牛马而能行”,图像中也未见过在鹿车上驾牲畜的。《后汉书·鲍宣妻传》说,西汉末年鲍宣的妻子“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如果所谓“共挽”,不意味着两人轮流推车,而是指两人合作,一推一拉的话,则鹿车除有人在后面推以外,还可有人在前面拉。
2.鹿车的车轮装于车子前部,无论山东武氏祠画像石、四川渠县蒲家湾汉阙雕刻,还是四川彭县和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所见者都是如此,因而车子的重心位于轮子的着地点(支点)与推车人把手处(力点)中间。从杠杆原理上说,这是一种费力的方式。
3.文献记载的鹿车,多用于载人。如前引《孝子传》说董永之父乘鹿车。《后汉书·赵熹传》说他将韩仲伯之妻“载以鹿车,身自推之”。同书《范冉传》说他“推鹿车以载妻、子”。《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说他“以鹿车推载母”。至晋代,《晋书》犹说刘伶常乘鹿车。可见鹿车在使用上和解放前的人力车相仿,都以载人为主。它一般只载一个人,也有载一成年人和一儿童的(如《范冉传》所记)。
4. 鹿车偶或也装载盛尸体的棺木等物。如《后汉书·杜林传》说他“身推鹿车,载致弟丧”。同书《任末传》说:“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 画像石中虽未发现过这种场面,但成都扬子山画像砖上的鹿车于车之后部横放一箱,估计用鹿车运棺木时也只能这样横着放,其费力之状,不难想见。
而关于诸葛亮制造的“木牛、流马”之记载却远较鹿车为少,更没有发现过图像材料。现在能据以立论的根据,主要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及《后主传》中的几条记事及刘宋·裴松之注中所引《诸葛氏集·作“木牛、流马” 法》。裴松之的时代去三国尚近,当时二十四篇的《诸葛氏集》完本尚应存世,裴氏可以直接引用。而且此文又见于《艺文类聚》卷九四、《太平御览》卷八九九,所以不能把《作“木牛、流马”法》一文看成伪作。但此文是用隐喻的形式写的,遣词造句相当晦涩,史称诸葛亮为文“丁宁周至”,这篇文字却适得其反。因此目前还难以据此对“木牛、流马” 之整体形制作出令人信服的复原方案,而只能按照文中之能够看得懂的字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来。并且,根据前人成说与刘仙洲先生的研究结论,“木牛、流马” 均是独轮小车,二者应为大同小异的一类运输工具。故本文亦统而言之,不再强作区分。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增订部分做得相当到位,并非简单的修补或注脚增加,而是真正融入了作者近年来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使全书的学术前沿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通过对比增订前后的章节,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方法和理解视角的迭代与深化。特别是对于一些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作者能够迅速地将其纳入到原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检验和修正,展现出极强的学术活力。对于资深研究者而言,这部分内容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而对于反复阅读的读者来说,它也像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总能从中发现新的解读角度。这种持续性的学术投入和对知识更新的执着,使得这部“增订本”的价值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再版,更像是一部不断完善中的知识体系。
评分初读此书,我立刻被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清晰的逻辑脉络所折服。作者在引述前人研究成果时,总能做到博采众长而不流于窠臼,对不同学派的观点都能进行客观而深入的评述,展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在对某些关键性服饰形制演变进行论证时,作者并未简单罗列史料,而是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推导路径,从出土文物、壁画图像到文字记载,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清晰地追踪其学术思路,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对于我这种非专业出身,但对古代服饰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种循序渐进的讲解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使得深奥的专业知识变得触手可及,可以说是学术普及与专业研究的完美结合。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中又不失古韵的风格,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仿佛就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历史积淀。封面用的纸张质感非常出色,纹理细腻,色彩搭配也显得十分考究,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内页的排版布局也十分合理,字体选择古朴典雅,行距字距把握得恰到好处,即便是大段的文字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吃力。更值得称赞的是,书中配图的质量极高,无论是拓片、线描还是彩绘复原图,都清晰锐利,细节丰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图版资料的价值不亚于文字本身。装帧上的这些用心,无疑提升了阅读的整体体验,让人在翻阅时就能感受到一种对传统的敬畏与珍视。这种内外兼修的质感,使得它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评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那种“存疑”精神。面对某些记载模糊不清、史料互相矛盾的关键节点,作者没有采取武断的结论,而是坦诚地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路径,邀请读者一同进行思考和辨析。这种坦率的态度,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历史真相的敬畏,而非急于求成的“盖棺定论”。书中对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服饰名称或形制考证,都做了详尽的辨析过程,不仅梳理了前人不同的观点,还加入了作者的独立判断和新见解,虽然有时读起来略显复杂,但正是这种审慎和求真的态度,才使得这部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是提供标准答案的教科书,而是激发进一步研究的“对话者”。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单纯的服饰形制考证,而是巧妙地将社会史、礼仪制度乃至当时的生产技术和审美风尚融入到服饰的分析之中。例如,在讨论某个朝代官服的色彩等级时,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染料的来源和工艺难度,还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等级观念,揭示了颜色背后所承载的权力符号意义。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古代服饰的认知边界,使“服饰”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图像符号,而是活生生地嵌入了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文化载体。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都有了更加立体和丰满的理解,仿佛能“看”到那些华服在特定场合下所发挥的作用。
评分好,不错
评分速度很快。
评分挺好的书,京东价格给力!
评分《书法约言》1卷7篇。即总论2篇:答客问书法1篇,论作字之始1篇,论楷书、行书、草书3篇。在这部著作中,宋曹集中阐述了他的书法理论。他认为书法的笔意贵淡雅,不贵艳丽;贵流畅,不贵紧结;贵含蓄,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做作。说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关于临写,他主张初写字不必多费纸墨临摹,应取古拓善本,仔细玩赏,对之加以熟悉,进而须背帖而求之;要边学边思,反复进行,成竹在胸,然后举笔为之。论草书,他说张旭喜肥,怀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认为写草书时用侧锋,则能产生神奇。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以灵转取致。说草书无定,须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悟生后能自我作古,也能产生自己的方法和面貌。
评分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孙机经典作品。
评分??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经典好书
评分非常喜欢书,每次京东有活动都会买买买,希望喜欢过的书都能在京东集齐,要是活动的力度更大就更令人开心了?????
评分儿子喜欢,是他想要的东西。
评分孙机先生是沈从文的弟子,当代名物研究首席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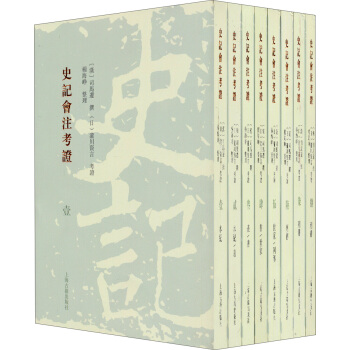
![军阀之国1911-1930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套装共2册) [Warlords of China 1911-1930]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41491/567a586eNc279b16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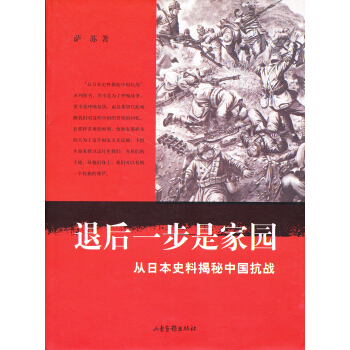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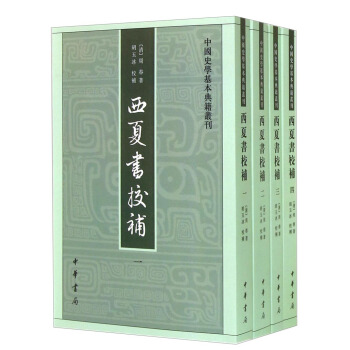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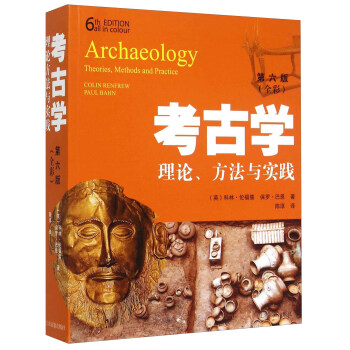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48213/rBEQWFNYfTMIAAAAAAKfK3-V3MIAAFX7gPCe4QAAp9D8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