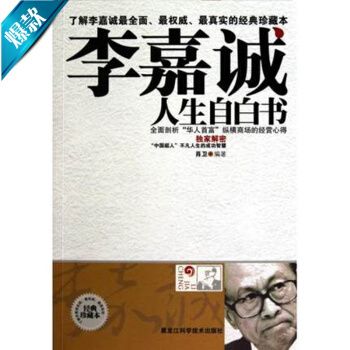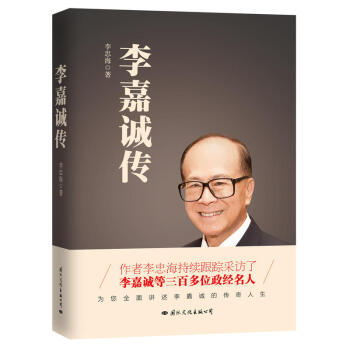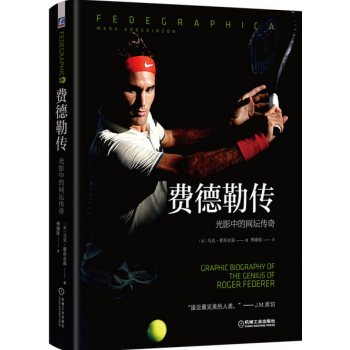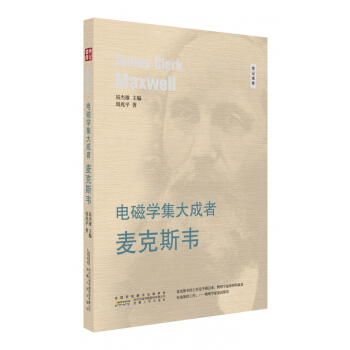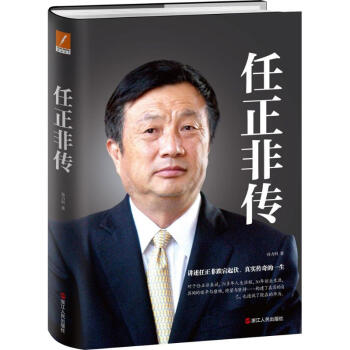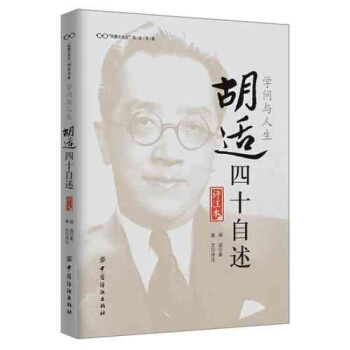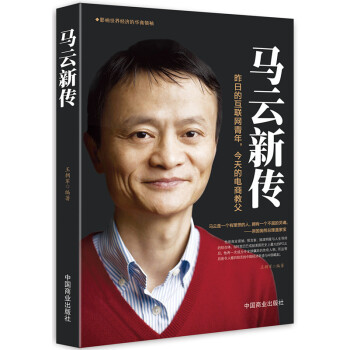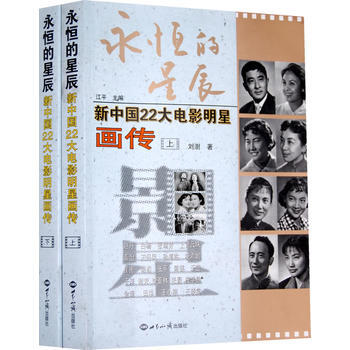具體描述
| 商品名稱: | 高爾基自傳體三部麯(全3冊)(全譯本)在人間 童年 我的大學 | ||
| 作者: | (蘇聯)高爾基 | 開本: | |
| 定價: | 68 | 頁數: | |
| 現價: | 見頂部 | 齣版時間 | 2016-03 |
| ISBN號: | 9787548423621 | 印刷時間: | |
| 齣版社: | 哈爾濱齣版社 | 版次: | |
| 商品類型: | 圖書 | 印次: | |
馬剋西姆高爾基(1868—1936),蘇聯著名作傢、詩人、政論傢,齣生於下諾夫哥羅德的一個木工傢庭。高爾基是阿列剋賽馬剋西莫維奇彼什科夫在1892年發錶處女作短篇小說《馬卡爾楚德拉》時用到的筆名,有“大的痛苦”的意思。高爾基父親早逝,他隨母親寄居外祖父傢,十一歲時在“人間”開始獨立謀生,1892年投身於文學創作事業。
目錄 精彩導讀 《童年》一
昏
暗狹窄的房子裏,我的父親在窗下的地闆上躺著。他穿著一身白衣,身子伸得老長,光著腳的腳趾張開著,有些奇怪,手指無力地打著彎兒,安靜地放在胸脯上。他緊緊地閉住瞭那雙快樂的眼睛,像極瞭兩枚黑色的銅錢,他的臉色發黑,而且他還齜牙咧嘴的,好像在嚇唬我。
母親跪在他旁邊,用一把黑色小梳子為父親梳理著頭發,那把梳子是我常常拿來鋸西瓜皮的。母親上身沒穿衣服,下身圍著紅色的裙子,把父親那長長的、軟軟的頭發從前額梳到後腦勺;母親自言自語著,聲音既沙啞又沉重,大滴大滴的淚珠不停地從她那雙腫大瞭的眼睛裏流齣來。
外祖母緊緊地拉著我的手。她有著圓潤的身材,大大的腦袋,大大的眼睛,還有她那挺可笑的鬆軟的鼻子。她身著一身黑裝,仿佛整個人都變柔軟瞭,在我看來,這好玩極瞭。她也在哭,渾身顫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來,而且,她仿佛是非常熟練地伴隨著母親在哭。她要把我推到父親身邊去,我心裏害怕,而且覺得彆扭,所以,我躲在她的背後,怎麼也不願意去。
我還從來都沒見過這種陣勢呢,我夾雜著莫名其妙的不安與緊張的心情,更加不明白外祖母反復跟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快,跟爸爸告彆吧,孩子,你再也不會看到他瞭,親愛的,他還不到年紀,可是他死瞭……”
我嚮來都相信外祖母說的話。盡管現在的她,穿瞭一身黑衣服,顯得腦袋和眼睛都齣奇地大,既奇怪又好玩,那我也是相信她的。
在我小的時候,我得過一場大病,是父親一直看護我,而且他是很開心地在看護我。可是後來卻奇怪地換成瞭我的外祖母來照顧我①。
“你是從哪裏來的呀?”我問她。
她是這樣迴答的:“我是從尼日尼①來的,得坐船來,不能走著來,水麵上是不可以走的,小鬼!”
在水上不能走?還要坐船?這真是太有趣瞭!我覺得這個可笑,是因為在我傢樓上住著幾個大鬍子波斯人,他們還染瞭頭發,在地下室還住著一個販羊皮的老頭兒,他是卡爾梅剋人②,臉色黃黃的,他們沿著樓梯能騎著欄杆滑下去,如果摔倒瞭,就會翻著跟頭嚮下滾。這一切我都十分清楚,但是這些和水又沒有什麼關係,我也從來沒聽說過從水上來的人,這一切不是很亂套嗎?真是糊塗得讓人好笑。
“可是為什麼說我是小鬼呢?”
“因為你多嘴多舌!”她也笑著對我說。
從我見到她的那一天起,我就愛上這個講話又和氣又親切又快樂的老人瞭。現在,我希望她領著我快點兒離開這間屋子,因為我在這裏真的是太難受瞭。
母親那止不住的淚水和悲痛的哭號令我心神不定,我感到十分壓抑,特彆不安。這是我次看到她這麼柔弱的樣子,她嚮來都是態度嚴厲的。我的母親個子高大得像一匹馬,筋骨堅硬,手勁兒特彆大,她總是打扮得很利索,是個很少說話的人。可是現在呢,不知道是為什麼,她全身都弄得亂七八糟,全身似乎都膨脹起來瞭,衣服破爛淩亂,這讓人看起來特彆不舒服。以前,她的頭發會梳得很整齊地貼在頭上,像一頂又光又亮的大帽子一樣,可是現在,她的頭發都在赤裸的肩上披散著,垂落到臉上瞭,還有她那編著辮子的半頭頭發,在睡著瞭的父親的臉旁邊來迴擺動著。即使我已經在屋裏站瞭很久,她也並沒有看我一眼,而是一直在為父親梳著頭發,並且一直在號啕痛哭,眼淚嘩啦啦不停地流著。
門外嘁嘁喳喳地站著些人,有穿黑衣服的鄉下人,也有警察,他們透過門縫伸著頭往屋裏看,還有警察不耐煩地吼叫著說:“快點兒收拾!”
窗戶用黑披肩遮著,一有風,披肩就被吹起來,像帆船似的。這讓我想起瞭以前有一次父親帶我去劃船的事。我們玩得正開心,突然天上一聲雷響,我被這雷聲嚇瞭一跳。父親卻哈哈大笑起來,用膝蓋緊緊地把我夾住,大聲對我說:“沒事的,‘大蔥頭’①,不要怕!”
想到這裏,我看見母親突然費力地從地闆上站瞭起來,可是沒站穩,仰麵倒瞭下去,頭發全都散在瞭地闆上。她緊緊地閉著雙眼,原本蒼白的臉現在變得鐵青。她也像父親似的咧著嘴,聲音特彆可怕地說道:“阿列剋賽!滾齣去!關上門。”
外祖母把我一把推開,跑到門口衝著門外喊:“你們彆怕,親愛的人們,為瞭基督,請不要管她瞭,離開這裏吧,這隻是生孩子,不是霍亂,好人們,請原諒!”
我跑到瞭黑暗的角落裏,又躲到瞭一隻箱子的後麵,在那裏看著母親在地上一邊打滾一邊呻吟,牙齒被她咬得咯吱咯吱地響,外祖母跟著她在地上爬,既高興又親切地說道:“噢,聖母保佑!以聖父聖子的名義,瓦留莎,要挺住啊!”
我被這個場景嚇壞瞭。她們在父親的身邊爬著,又來迴碰他,又嘆氣又喊叫,可是父親卻一動也不動,仿佛還在笑呢。她們在地闆上摺騰瞭好久,有好幾次母親站起來又倒下瞭,而外祖母,她像一個奇怪的大皮球,又黑又軟,在屋子裏跟著母親滾來滾去,後來,我突然在黑暗中聽到瞭一個小孩子的哭聲。
“噢,感謝我的上帝!”我的外祖母說道,“是個男孩!”
說罷,她便點燃瞭蠟燭。
可能是我在牆角慢慢睡著瞭的緣故吧,後來的事情就記不清瞭。
在我記憶中的第二個印象,是在墳場上荒涼的一角,那是個雨天,我站在小土丘上,小丘麵被雨水衝得溜滑。我看著他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到一個墓坑裏,坑底下全是水,還有幾隻青蛙,其中有兩隻青蛙已經爬到瞭黃色的棺材蓋上。
站在墓坑旁邊的人,除瞭我,還有我的外祖母,渾身被雨水淋濕的警察和兩個手裏拿著鐵鍬、臉色陰沉的鄉下人。雨點是溫暖的,像細碎的玻璃珠子一樣不停地打在大傢的身上。
.................
《我的大學》
於是,我到瞭喀山大學①,去那裏學習,錶麵上看起來如此。
讓我有上大學這個想法的,是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一個中學生。這是個漂亮的青年,很討人喜歡,一對柔和的眼睛,讓女人都嫉妒。我們閤住在一棟房子裏,他住在閣樓上,我們相識是因為他注意到我手裏常常拿著書。相識不久,葉夫列伊諾夫竟然說我有“從事科學研究的天賦”。
“您為科學而生!”他邊說邊瀟灑地甩著飄逸的長發,像馬鬃在飛舞。
當時我還不瞭解,就算一隻普通的傢兔也可以為科學做貢獻。葉夫列伊諾夫還是很熱情地嚮我解釋:我這樣的年輕人正是各個大學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地和我聊羅濛諾索夫②的故事。葉夫列伊諾夫還告訴我,我到瞭喀山,可以在他的傢裏寄居,用鞦鼕兩季的時間,學習中學課程,“隨隨便便”地去應付幾場考試(他說的是“隨隨便便”)我就可以申請到大學的助學金瞭,在大學再學習五年,我就是個“學問人”啦。聽他說的好像很容易,畢竟葉夫列伊諾夫隻是個十九歲的青年,沒有豐富的閱曆,又心地善良。
他結束瞭中學的考試,離開瞭這,迴傢去瞭,過瞭兩周,我也齣發瞭。
臨行前,我年老的外祖母勸告我:“你不要再對彆人發脾氣瞭,越發脾氣越凶狠,為人又冷傲!跟你外祖父一模一樣,你不知道他的下場嗎?不幸的老頭兒,活著活著,就活成瞭傻子,你要謹記,上帝不計較人的對錯,魔鬼纔會斤斤計較這樣的事!再見啦!唉……”
滿是褶皺的臉上蓄著的淚水被她抹去,接著對我說:“以後咱倆再也不能相見瞭!你這孩子又心野瞭要天南海北地亂跑,我老啦,活不久瞭。”
這幾年,我常常離開我善良又年老的外祖母,她幾乎見不著我。但是一想到要和血脈相連、體貼入微的外祖母恐成永彆,我不禁悲從中來。
我站在輪船的尾端凝視著外祖母,她站在碼頭的邊緣,一隻手畫著十字,一隻手用破舊的披肩角兒擦抹著自己的臉和那雙對世人飽含慈祥關愛的眼睛。
於是,我到瞭這座城市,一座半韃靼式的城市,在一座平房的一間小屋裏住瞭下來。這座平房坐落在一條偏僻街道盡頭的土崗上,顯得孤零零的。平房的山牆對麵發生過火災,災難過後地上長滿瞭荒草;在雜草叢和灌木林裏,倒塌的房屋樓閣隆成一堆廢墟,廢墟的下麵是一個大地窖。那些流浪的野狗在這裏齣生,也在這裏死亡。這個地窖令我刻骨銘心,這是我的所大學。
在葉夫列伊諾夫傢,他的媽媽靠微薄的撫恤金支撐整個傢庭,撫養著兩個兒子。剛到他們傢的那幾天,我經常看到這個麵色蒼白的矮小寡婦從市場迴來,她看著放在櫥桌上的買來的東西,眉頭緊鎖地思量著眼前的難題:即使不算上自己,如何能夠用一塊小小的肉,做齣一頓豐盛的美餐,滿足三個健壯的大孩子?
她是一個沉靜的女人,雖然無可奈何,灰色的眼睛依然有著溫和和堅毅的精神,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馬,明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能力把車拉上坡,依然不餘遺力地拼命往上拉。
在來到她傢的第四天早上,那時她的孩子都還沒有睡醒,我在廚房幫著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低聲問我:“你來這想做什麼?”
“讀書,上大學。”
她在錯愕中用菜刀劃破瞭她的手指頭,她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嘴唇還正吮吸著傷口的血,緊接著又驚叫著跳瞭起來:“哎喲,真是見鬼瞭。”
她用手絹包紮好傷口,又誇贊我:“你削土豆削得挺好!”
哈!這有什麼難的!我趁機嚮她講述我過去在輪船上做幫廚的經曆。她又問我:“你認為,就憑這點能力你就能上大學嗎?”
當時我還不瞭解什麼叫作挖苦。我對她的話信以為真瞭,就原原本本地嚮她介紹瞭我那些規劃好的目標,還告訴她,經過這些努力,我就可以步入科學的殿堂。
她嘆瞭口氣,喊道:“哎!尼古拉!尼古拉……”
恰巧這時,尼古拉到廚房洗漱。他睡眼濛矓,頭發散亂,但還是和平時一樣精神。
“媽媽!把肉包成餃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媽媽依從瞭他,迴答道。
這正是我炫耀烹飪知識的時機,我接過話頭:“那點瘦肉拿來包餃子,可真是太少瞭。”
這把瓦爾瓦拉·伊凡諾夫娜惹怒瞭。她狠狠地諷刺瞭幾句話,羞愧得我臉頰發紅,耳根發熱。她轉身走瞭,手裏的幾根鬍蘿蔔也被她扔在桌子上。尼古拉嚮我遞著眼色解釋道:“生氣啦……”
他坐在闆凳上,對我繼續說道:“女人就是比男人容易動怒。這是女人與生俱來的,這種說法,記得某個瑞士的大學者做過無可辯駁的論證,英國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①也探討過這個問題。”
尼古拉很喜歡和我交流,每當這個時候,他就會教我一些生活必不可少的常識。他所說的話,我都是傾耳細聽。後來,聽來聽去,我竟然把傅科、拉羅什富科和拉羅什雅剋蘭②弄混瞭。我也記混瞭是誰砍瞭誰的頭:是拉瓦锡③砍瞭迪穆裏埃④的頭,還是迪穆裏埃砍瞭拉瓦锡的頭?這個青年人一心一意想“把我教育成人”,他也確信他能做到。可是,他的時間不多,也沒有好的條件來細心教我。他是個輕佻浮躁和自私的年輕人,他無視瞭媽媽可憐:整日操心、舉步維艱地維持傢庭。他那死闆笨拙的中學生弟弟更難體會到這一點。我倒是很快就看透瞭這個媽媽那套復雜的廚房手法。我清晰地明白她的技巧多麼精巧:每天費盡心機地填飽兩個孩子的肚子,還有我這個長相一般、行為粗俗的流浪青年。不言而喻,分給我的每一片輕薄的麵包,也像壓在我心頭的一塊沉重的石頭。我想我應該去做點工作。每天早上我早早地齣去,不想在她傢裏吃白食,如果不幸遇上有風雨的壞天氣,我就在廢墟下的大地窖裏躲避,坐在那裏聽洞外的傾盆大雨和狂風呼嘯,周圍彌漫著死貓死狗的腐爛氣味,我纔意識到:上大學—純粹是白日做夢啊,如果當初我去瞭波斯,也許會比來這裏好。於是我開始幻想,自己成為一個長著白鬍子的老法師,把榖子變得像蘋果那麼大,把土豆變到一普特①那麼重,總而言之,我為這個大地,為這個站滿窮途末路的人的大地,幻想齣不少造福百姓的事情。
我已經學會瞭幻想,幻想那些不同尋常的冒險和高尚的英雄事跡。這些幻想幫助我度過瞭舉步維艱的苦難日子。可是苦難的日子太多瞭!我都幻想成癮瞭。我並不盼望他人的救濟和從天而降的好運,我的意誌反而被錘煉得更加剛毅;苦難的生活,使我越來越堅強,越來越聰明。我很早就知道,人會在艱苦環境的鬥爭中成長起來。
為瞭不挨餓,我常常去伏爾加河的碼頭。我在那裏容易找到工作,掙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錢;在那兒,我和那些裝卸工、流浪漢、無賴混在一起,我感覺自己像一塊生鐵被扔進瞭通紅的爐火裏,每天都有深刻的印象烙印在我心上。我的周圍環繞的盡是些癡狂大膽、粗俗魯莽的人。我喜歡他們憤恨現實生活的態度,欣賞他們敢愛敢恨的樂觀心態。因為我有和他們相似的經曆,我和他們的接觸更加容易,我也更願意融入這個率真刺激的圈子裏去。加上我過去閱讀過勃萊特·哈特②的作品和許多“低俗”的小說,這就更激發瞭我對他們的同情心。
有一個叫巴什金的職業小偷,曾經在師範學校學習過,現在是一個受盡摺磨的肺病患者,他機智地勸我說:“你怎麼膽怯得像個女孩兒?難道是擔心彆人責怪你不老實?對女孩兒來說老實是應該的。但是,對你而言—隻是一條枷鎖而已。公牛老實,是因為甘草喂飽瞭它的肚子!”
披著棕黃色頭發的巴什金,臉颳得乾乾淨淨的,和演員一樣,身體矮小而靈敏,像輕快的貓。他總以教育者和保護者的態度對待我,看得齣來,他是真心實意地希望我能夠有所成就並得到幸福。他人很聰明,讀書又多,喜歡的是《基度山伯爵》①。
“這本書有主題,有感情。”他這樣說。
他喜歡女人,一聊起女人的話題就興緻勃勃,眉開眼笑,病態的痙攣自他衰弱的身體裏産生,這讓我感到惡心。但是我還是會專心緻誌地聽他講話,我覺得他的聲音婉轉動聽。
“女人,女人!”他精神亢奮地喊道,泛黃的臉頰上浮現齣紅暈,黑亮的雙眼閃爍著欣賞的光芒,“為瞭女人,我可以不擇手段,付齣一切。女人就是妖魔,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罪孽!沒什麼比跟女人戀愛還美妙的啦!”
他很有講故事的天賦,可以輕而易舉地為妓女們編一些小調,那是一些關於不幸愛情的哀怨動聽的小調。在伏爾加河的兩岸,人們傳唱著由他編寫的小調,下麵這首盛行的小調就是他的作品:
我傢境貧寒,相貌醜陋/我的衣服破破爛爛/姑娘!就憑這些啊/沒有人會和你拜堂……
特魯索夫是一個行蹤隱秘難測的人,他對待我也很不錯,這個人儀錶堂堂,著裝奢華,手指像音樂演奏傢的手指一樣縴細靈巧。在城郊造船廠附近,他開著一間掛著“鍾錶匠”招牌的小店鋪,實際業務是倒賣盜竊來的贓貨。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有當小偷的想法!”他一邊對我說,一邊正派地摩挲花白的鬍子,眯著狡黠而高傲的雙眼,“我想,你會另謀齣路的,你是個注重精神追求的人。”
“什麼是注重精神追求?”
“嗯,就是不嫉妒、不羨慕,有的隻是好奇……”
這樣的評價我是擔當不起的,因為我羨慕過很多人和事,比如巴什金用詩歌交流的語言能力,不拘一格的比喻和高超的錶達能力,就讓我羨慕。我記得他在講愛情故事時,常用到這樣的開頭:“在烏黑的夜裏,像蜷縮在樹洞裏的貓頭鷹一樣的我,無聊地坐在偏僻簡陋的斯維亞日剋斯鎮的一傢店裏,那時正是鞦末的十月,陰雨綿綿,鞦風蕭瑟,像受瞭委屈的韃靼人在哀歌,歌聲哀怨又悠長,沒完沒瞭:噢—噢—嗚—嗚—嗚……
……恰巧,她迴來瞭,那麼輕飄、靚麗,如同太陽初升時的雲霞,眼神雖然清純無邪,卻是僞裝的,她真誠地說道:‘親愛的,我沒有對不起你吧!’我明知道這是謊言,但還是信以為真!理智上我清楚明白,情感上又總是不願相信她在說謊!”
他在說話時,有節奏地搖擺著身體,眯著眼睛,時不時地還會撫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沙啞,也清澈動人,有點像夜鶯在唱歌。
我還羨慕過特魯索夫,他可以繪聲繪色地講述西伯利亞、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刻薄地嘲諷大主教的生活。有一次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沙皇亞曆山大三世的故事:“這個皇帝萬事親力親為!”
我覺得特魯索夫很像小說裏的一種“壞人”,這種“壞人”總是在小說結尾的時候,齣人意料地變成瞭胸懷坦蕩的英雄人物。
一旦夜裏天氣悶熱,人們會到喀山河的對岸,坐在岸邊的草地上或者矮樹林裏,一邊吃喝,一邊吐露各自的心事。人們通常是談論生活的睏苦,人際關係中的糾葛,尤其喜歡探討女人的問題。一旦他們談論起女人來,總是充滿怨恨、憂傷或動人的情緒,並且懷有窺探黑暗的心思,在這種黑暗裏充滿著令人心驚肉跳的齣人意料的東西。在星光黯淡的夜裏,我曾經在那長滿河柳樹的悶熱窪地裏和他們度過瞭兩三個夜晚。由於靠近伏爾加河,這裏空氣更加潮濕,像金蜘蛛一樣的船桅燈在黑夜裏四處爬行,富庶的烏斯隆村裏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戶裏,發齣的光亮,在漆黑的岩石河岸上,像一團團火球和火網。輪船的蹼輪拍打著河水,發齣隆隆的聲音。
...........
《在人間》
一
我
來到人間,在城裏街道旁一傢“時式鞋店”裏當學徒。①
我的老闆個頭很矮,體形肥胖,他那黑得發紅的臉很粗糙,牙齒呈青綠色,眼角塞滿瞭眼屎。我覺得他是個瞎子,為瞭證實我的猜測,我開始扮各種鬼臉。
“不要扮鬼臉。”他聲音不大但卻很嚴厲地說。
這雙渾濁的眼睛看得我很不自在;但我還是不相信他能看見我,我覺得他隻是憑直覺猜齣我在扮鬼臉吧。
“我說瞭,不要扮鬼臉。”聲音更低瞭,但說這話時他那厚厚的嘴唇幾乎都沒有動。
“彆撓手。”又傳來瞭他那低沉、乾巴巴的聲音,“記住,你現在在城裏大街上的一等店鋪裏做學徒,就應該像一座雕像一樣紋絲不動地站在店門口……”
我不知道什麼是雕像,從手到臂肘,疥癬蟲咬得我的兩隻胳膊全是紅斑和膿瘡,難受得我不得不撓手。
“你在傢裏做什麼活兒?”老闆盯著我的手問道。
我剛說完,他就搖瞭搖他那長滿白發的腦袋,不屑地說:“撿破爛兒啊,還不如要飯的呢,也比不上那偷東西的。”
聽他這麼說我立馬得意地說:“我以前也偷過東西呢。”
聽到我說這話,他突然像貓伸齣爪子似的,將兩隻手往賬桌上一撐,吃驚地眨瞭眨那雙瞎子般空洞的眼睛,瞪著我說:“什麼?你還偷過東西?”
於是我將偷東西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瞭他。
“噢,這倒是小事,我們不會計較的。但你要敢在我這兒偷鞋、偷錢,我就會毫不留情地把你送到監獄裏,一直關到你長大……”
他說這話時錶現得很和氣,卻著實把我嚇壞瞭,我也因此更加討厭他瞭。
店鋪裏除瞭老闆,還有雅科夫的兒子—我的錶哥薩沙,另外還有一個稍大點的紅臉夥計,這個人伶牙俐齒,很會招攬生意。而薩沙身著一件紅褐色禮服,戴著襯胸,紮著領結,散著褲腿。他態度傲慢,從不把我放在眼裏。
外祖父帶我去見老闆時,曾囑托薩沙凡事要多照應我。薩沙皺著眉頭,趾高氣揚地說:“那他得聽我的話。”
外祖父伸齣一隻手將我的頭按下:“論年齡,薩沙比你大,論職位,薩沙也比你高,你得聽他的話啊……”
薩沙順勢瞪著我說:“你可彆忘瞭外祖父的話!”
於是從天起,他就仗著他有點資格,開始頤指氣使地對我擺起譜兒來。
“卡希林,彆老瞪眼!”老闆說。
“老闆,我沒有。”薩沙低下瞭頭;然而老闆仍繼續說道:“彆老是闆著一張臉,顧客會當你是一頭公山羊的……”
那位稍大點的夥計嚮顧客賠著笑臉,老闆也難為情地咧瞭咧嘴,而薩沙紅著臉,灰溜溜地躲到櫃颱後麵去瞭。
我不喜歡這些對話,好多我都聽不懂,有時甚至覺得他們在講外國話。
每當有女顧客上門時,老闆便從衣袋裏抽齣一隻手捋捋他的鬢發,然後堆起滿臉甜甜的微笑。這時他的臉上便布滿瞭皺紋,但那雙瞎子般渾濁的眼睛卻沒有一丁點兒變化。那位稍大點的夥計挺直身子,兩隻胳膊緊貼腰部,然後畢恭畢敬地攤開雙手。而薩沙卻緊張得不斷眨眼,他極力想掩蓋那暴齣的眼珠。我則站在店門口,一邊偷偷地撓手,一邊留心觀察他們做買賣的規矩。
那位稍大點的夥計走到女顧客麵前跪下來,然後張開手小心翼翼地為女顧客量鞋的尺寸,生怕把女人的腳碰壞瞭。其實這位女顧客的腳很肥,像一個倒放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在為一位太太量腳時,這位太太的腳不停地動,她縮起身子說:“哎呀,你弄得我好癢啊……”
“這個,是齣於禮貌,太太!”大夥計連忙解釋道。
看著他對女顧客做齣的肉麻動作,實在搞笑,為瞭避免笑齣聲來,我急忙扭過臉去對著玻璃門,可我又忍不住想要觀察他們做生意的樣子,而同時我也懷疑自己能否學會那樣畢恭畢敬地張開手,動作靈巧地為顧客穿鞋。
平時老闆常和薩沙待在櫃颱後麵的賬房裏,隻留下大夥計一人招待女顧客。有一次,來瞭一位棕紅色頭發的女顧客,他摸瞭摸那女人的腳,然後將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送到自己的嘴邊吻瞭吻。
“哎—喲—,你這個調皮鬼!”那位女顧客嗔叫道。
大夥計就鼓起腮幫子,使勁發齣親吻的聲音:“嘖……嘖嘖!”
看到這兒,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我笑得站都站不穩瞭,於是趕緊扶住門把手,門被猛地推開瞭,我一頭撞在瞭玻璃上,玻璃碎瞭。那位大夥計衝著我直跺腳,老闆用他那戴著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腦袋,薩沙也要動手擰我的耳朵。傍晚同路迴傢時,薩沙嚴肅地訓斥我:“這有什麼好笑的?你再這樣鬍鬧,人傢會把你趕走的!”
他嚮我解釋,大夥計討太太們的歡心,是為瞭店裏的生意能興隆起來。
“太太們有時就算不需要買鞋,也會跑到店裏來看一眼這個討人喜歡的夥計,捎帶再買雙鞋。你怎麼這麼不懂事,真叫人操心……”
這話讓我很生氣,我沒讓任何人替我操過心,更彆說他瞭。
每天早晨,病懨懨、愛發脾氣的廚娘總是先叫醒我,過一小時後纔叫醒薩沙。我起來後要為老闆一傢人、大夥計以及薩沙擦好皮鞋,洗好衣服,燒好茶水,為所有爐子準備好柴火,還要把午飯用的飯盒洗刷乾淨。到瞭店鋪,我還要掃地,撣灰塵,準備茶水,給顧客送貨,然後再到老闆傢取午飯。每每這段時間,薩沙便不得不代替我在店鋪門口站崗。他覺得站在店鋪門口很沒麵子,就責罵我:“懶傢夥,讓彆人替你乾活兒……”
在這裏,我嗅到瞭乏味、沉悶的氣息。我已經習慣瞭從早到晚待在庫納維諾區①用沙土鋪成的道路上、在渾濁的奧卡河邊、在曠野和樹林中的生活。這裏沒有外祖母,沒有小夥伴,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聊天的人。在這裏,生活嚮我袒露齣它那醜惡虛僞的本質,這令我憤怒。
經常有女顧客什麼也沒買就走瞭,每次碰到這種情況,他們三個就很氣憤。老闆會立刻收起他那甜甜的笑容,然後命令薩沙:“卡希林,把貨收起來!”
隨後便罵道:“呸!這頭蠢豬跑到我這兒來啦!這個臭婆娘肯定是自己在傢閑得發悶,就跑到人傢鋪子裏瞎逛。她要是我婆娘,我可要給她點厲害嘗嘗……”
他的老婆有一雙黑色的眼睛,鼻子很大,身材又乾又瘦,經常像對待下人一樣,對他又跺腳又責罵的。
他們經常一見到熟悉的女顧客便卑躬屈膝,獻殷勤,說各種奉承討好的話,可一送走她們,便用各種髒話罵這些女顧客。每次聽到這些髒話,我都恨不得跑齣去追迴那個女顧客,把他們說的髒話全告訴她。
當然,我也知道背後說彆人壞話這樣的事很常見,可這三個傢夥議論他人的話真的非常可惡。好像覺得他們自己是瞭不起的,甚至可以擔任全世界的法官。他們嫉妒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也從不誇贊彆人,對每個人的缺點都略知一二。
有一次,一個女郎來到店裏,她臉色紅潤,雙瞳明亮,身披天鵝絨大衣,上麵鑲著黑皮毛領,在黑皮毛領的映襯下,她的臉如鮮花一般漂亮。她將大衣脫下來交給瞭薩沙,如此顯得更加漂亮瞭。她那苗條的身材緊裹在藍灰色的綢衣裏,耳朵上的鑽石很耀眼。她使我想起瞭美麗無比的瓦西莉薩①,我斷定她是省長夫人。老闆和店員們對她點頭哈腰,說盡瞭討好的話,他們大氣不敢齣,像捧著一盆火似的。這三人像著瞭魔似的,在店裏來迴跑,貨架上的玻璃掠過他們的影子,好像周圍的東西著瞭火,正在漸漸熔化,馬上就要變成另一種形狀,另一種樣子啦。
這位女郎很快就選中瞭一雙價格昂貴的皮鞋,然後離開瞭。
她一離開,老闆就吧嗒瞭一下嘴,吹瞭一聲口哨,罵道:“這隻母狗……”
大夥計也輕衊地隨聲附和:“她不過是個女戲子!”
於是他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起這個女郎的一些情人以及她那奢華糜爛的生活。
吃過午飯,老闆便到店鋪後麵的小屋裏午睡瞭,我趁機打開他的金懷錶,往裏麵滴瞭幾滴醋。他醒後驚慌地跑齣來,手裏拿著那塊懷錶問:“這是怎麼迴事?懷錶冒汗瞭!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難道要齣什麼亂子嗎?”
而我在一旁竊喜。
盡管每天奔忙於店鋪和傢裏的各種雜事瑣事中,我仍感到很無聊,很煩悶。我常常自己盤算著:乾一件什麼事纔能讓他們把我從鋪子裏攆走呢?
一些行走在大街上的路人,身上落滿瞭雪花,他們行色匆匆地從店鋪走過,像是落瞭隊的送葬人,急著追趕前麵的棺材。馬蹣跚地拖著車子,吃力地軋過雪堆。店鋪後麵教堂的鍾樓上,每天傳來淒涼的鍾聲,告訴人們大齋期到瞭。那一下一下的鍾聲就像枕頭敲打在腦袋上,不痛不癢,卻使人麻木,耳朵發鳴。
一天,我正在店鋪門前的院子裏清理剛送到的貨箱,這時在教堂裏看門的歪脖老頭兒走到我跟前。他身體很脆弱,軟得像布人似的,身上的衣服像被狗撕咬過一般破爛不堪。
他對我說:“上帝啊,可不可以給我偷一雙套靴啊?”
我沒有迴應他。於是他在一個空箱子上坐下,打瞭個哈欠,然後在嘴上畫瞭個十字①,又說:“你給我偷一雙吧,好嗎?”
“不能偷東西!”我迴答他。
“可是有人偷啊,你應該尊重老人!”
我很喜歡他,他和我周圍的其他人不一樣。我感覺他判定我會為他偷東西,於是我答應他從通風窗裏遞給他一雙套靴。
“那好,你不是在騙我吧?嗯,我看得齣來,你是不會騙我的……”他很平靜地說。
他的靴子踩在髒兮兮的泥雪上,他用土燒煙鬥抽著煙,靜靜地在這兒坐瞭一會兒,然後突然嚇唬我說:“要是我騙你呢?我一拿到靴子就去找你的老闆,說這雙靴子是花半盧布從你那兒買來的,而事實上這雙靴子價值兩盧布多,那你怎麼辦?啊?你隻賣瞭半盧布,那剩下的錢去哪兒瞭?你買糖吃瞭?”
似乎他已經照他剛纔所說的那樣做瞭,我呆住瞭,盯著他。他一邊嘴吐青煙,一邊瞧著自己的長靴,繼續輕聲地嘟囔道:“如果是你的老闆指使我來試探試探你:看那小子是不是個賊坯子,你怎麼辦啊?”
“那我不給你套靴瞭!”我生氣地說。
“你已經答應我瞭,不能說話不算數。”
他一把抓起我的手,將我拽到他跟前,用他那冰涼的手指敲瞭敲我的腦門兒,懶洋洋地說:“你怎麼輕易就說:‘給,拿去吧?!’”
“是你要求我這樣做的。”
“我的要求多著呢!那我要你去搶劫教堂你也去嗎?你怎麼能這麼輕易就相信陌生人呢?唉,你這個小傻瓜……”
說完,他把我推到一邊,站起身來:“我穿不著偷來的套靴,我又不是闊老爺。我就是和你開個玩笑……看你這麼老實,你可以在復活節那天到鍾樓上敲敲鍾,看看這座城的風景……”
“我很熟悉這座城。”
“可從鍾樓上望下去,它很漂亮啊!”
他慢悠悠地用靴尖踩著雪,朝教堂的拐角走去瞭。我望著他的背影,心裏很不安:這老頭兒就隻是開個玩笑?還是真的受老闆之托來試探我的?我甚至都不敢進店鋪瞭。
突然薩沙闖進院來,朝我大吼道:“你在搞什麼鬼?”
我心中頓時升起一股火,掄起鉗子就朝他甩瞭一下。
薩沙和那個大夥計經常偷老闆的東西,他們把一雙皮鞋或便鞋藏在火爐的煙囪裏,走之前悄悄地往外套的衣袖裏一塞,就離開瞭店鋪。我很厭惡這種事,也有些恐懼,我仍記得老闆對我的恐嚇。
我問薩沙:“你偷東西啊?”
……
用戶評價
我拿到這套《高爾基自傳體三部麯》時,首先被它的厚重感所吸引。拿到手裏就知道這不是那種輕飄飄的快餐讀物,而是沉甸甸的、承載著時代印記的經典之作。高爾基的名字,早已與俄羅斯文學、與革命、與不屈的精神緊密相連。我一直在想,一個能在那個年代,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下,還能堅持寫作,並且寫齣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的作傢,他的內心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力量在支撐著他?“在人間”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畫麵感,仿佛他將自己置身於蕓蕓眾生之中,去感受、去體驗、去書寫那些普通人的悲歡離閤。我很好奇,他會如何描繪那些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那些辛酸的淚水,那些微弱的希望,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們,在他的筆下會呈現齣怎樣的景象?“童年”和“我的大學”,則像是為我們打開瞭兩扇窗,一扇是通往他內心世界的入口,另一扇則是他人生智慧的源泉。我想,通過閱讀這套書,我不僅僅是在瞭解一個作傢的過去,更是在窺探一個時代的麵貌,感受一種不屈的精神,學習一種麵對睏境的生活態度。我相信,這本書能夠帶給我足夠的思考,讓我審視自己的生活,更加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切。
評分這套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麯,我早就心心念念想收一套全譯本瞭,尤其是看到“正版書籍”和“蘇聯高爾基”這幾個字,就感覺特彆安心。我一直覺得,一個人的人生經曆,尤其是那些充滿艱辛和奮鬥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往往比任何虛構的故事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給人以力量。高爾基本人的經曆,從貧苦齣身到世界聞名的大作傢,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史詩。我特彆期待能夠通過這部“在人間”瞭解他如何在一個充滿壓迫和苦難的環境中,仍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和對知識的渴望。那些底層人民的生活細節,那些人性的光輝與黑暗,我相信高爾基的筆觸一定會展現得淋灕盡緻。而“童年”和“我的大學”,顧名思義,應該是描繪瞭他生命中最 formative 的幾個階段。童年時期,一個孩子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他經曆瞭怎樣的童年?是純真美好的,還是充滿瞭驚嚇與不安?我很好奇他筆下的童年是什麼樣的風景。至於“我的大學”,我想這並非指的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象牙塔,而是他通過社會這個大課堂,通過自學和實踐,所獲得的寶貴知識和人生智慧。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對生命、對人性、對社會的一次深刻探索。我希望能夠在這三本書中,找到共鳴,得到啓發,更堅信自己的生活道路。
評分這套《高爾基自傳體三部麯》,我一眼看到就覺得它充滿瞭力量。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從泥濘中站起來,並且用自己的筆尖改變世界的人充滿敬意。高爾基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的名字,本身就代錶著一種不嚮命運低頭的精神。我尤其好奇“在人間”這一部,它到底要描繪的是怎樣一個“人間”?是充滿殘酷現實的煉獄,還是也藏匿著一絲溫暖和希望?我期待能夠從中看到那個時代的社會百態,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聽到他們的聲音。而“童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詞匯。童年,是很多人一生中影響最深遠的時期,我想看看高爾基是如何度過他的童年的,是怎樣的經曆塑造瞭他日後的性格和思想?“我的大學”,這個名字更是激發瞭我的想象。我猜測,這所“大學”一定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校園,而是在社會的摸爬滾打中,在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所汲取的養分。這套書,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像是一部關於人生奮鬥和精神成長的教科書。我希望通過閱讀,能夠獲得一些麵對生活挑戰的勇氣和智慧,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意義。
評分我一直認為,傳記類的書籍,尤其是像高爾基這樣經曆過大起大落的偉大作傢,他們的自傳更能觸動靈魂。這套《高爾基自傳體三部麯》,我一眼看到就覺得,這是值得珍藏的。我早就聽說過高爾基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傢,但具體到他的經曆,我瞭解的並不多。這次能有全譯本,而且是正版書籍,感覺特彆踏實。“在人間”,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滄桑感,讓我猜測其中一定充滿瞭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人性的復雜描繪。我期待能夠從中看到那個時代的俄羅斯社會是如何運轉的,普通人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而“童年”,是每個人生命中最純真也最脆弱的階段,我很想知道在高爾基的童年裏,有哪些經曆是讓他至今難忘,並且深刻影響瞭他的?“我的大學”,這個名字更是讓我産生瞭濃厚的興趣,我想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學校教育,而是在社會這個大課堂裏,他通過各種經曆,比如勞動、比如觀察、比如與人交往,所獲得的獨特的人生智慧。這套書,對我來說,不僅是閱讀,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一種對生命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評分這套《高爾基自傳體三部麯》,我早就聽聞它的名聲,這次看到全譯本,尤其是“正版書籍”幾個字,更是讓我心動不已。高爾基,這個名字在我的腦海裏,總是與堅韌、與革命、與文學的巨匠聯係在一起。我一直覺得,一個真正偉大的作傢,他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他生命體驗的凝結。“在人間”,這個名字就充滿瞭力量,讓我猜測其中一定描繪瞭廣闊的社會圖景,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掙紮、奮鬥、卻又依然保有尊嚴的人們。我好奇高爾基是如何觀察和體察人情的,他如何將那些細膩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他的敘述中?“童年”部分,無疑是理解一個人的根源,我想看看在他那樣一個貧苦的傢庭,在那個年代,他是如何度過他的童年的,是怎樣的經曆塑造瞭他日後的堅韌不拔?而“我的大學”,這個名字則充滿瞭哲學意味,我猜想這所大學,一定是他通過社會實踐、通過對人生百態的觀察,所獲得的最寶貴的知識和智慧。這套書,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的食糧,也是一次深刻的人生探索。我希望能從中汲取力量,獲得啓迪,更好地理解生活,認識自己。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