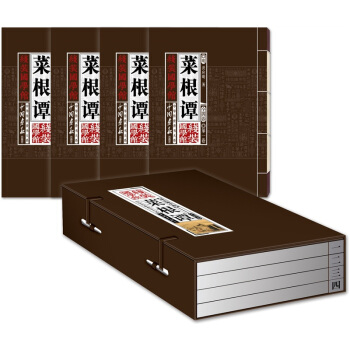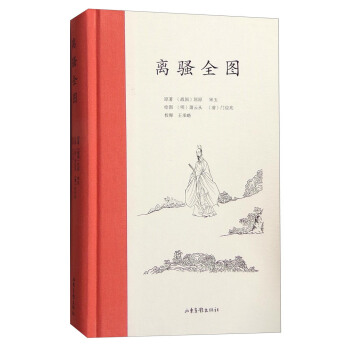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二十五史说略》是大家写小书。执笔的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作者们以自己丰富的学术积累、深切的研究经验,向读者介绍阅读经史的心得与方法。普及性强:一谈到十三经、二十五史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此书全无因传统文化经典的艰深、学术性强而造成阅读障碍。全书对每本书介绍的文字篇幅不长,文字平易,论证严谨,层次分明,可读性极强。作者们真正的做到了深入浅出,融深厚学识、思想于平实的论述中。
内容简介
《二十五史说略》全面、精练、准确地介绍二十五史中每部书的缘起、编纂始末、刊刻流布、内容特点、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研究状况等各个方面;每篇中都有推荐参考书目,以期指示门径。本书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必选入门读物,王钟翰、安平秋、黄永年、王天有等学术专家精心撰写的精准之作。李学勤赞誉到:“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目录
再版序言/李学勤《史记》说略 /安平秋 张玉春
《汉书》说略/周天游
《后汉书》说略/周天游
《三国志》说略/高敏 高凯
《晋书》说略/朱大渭
《宋书》说略/蒋福亚 李琼英
《南齐书》说略/蒋福亚 方高峰
《梁书》、《陈书》说略/蒋福亚 方高峰
《魏书》说略/高敏 高凯
《北齐书》说略/何德章
《周书》说略/何德章
《隋书》说略/黄永年
《南史》、《北史》说略/高敏 高凯
《旧唐书》说略/黄永年
《新唐书》说略/黄永年
《旧五代史》说略/郑学檬 毛章清
《新五代史》说略/郑学檬 毛章清
《宋史》说略/裴汝诚
《辽史》说略/李锡厚
《金史》说略/崔文印
《元史》说略/陈高华
《明史》说略/王天有 李新峰
《清史稿》说略/王钟翰
精彩书摘
史记其书——材料来源与整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就是用事实、靠材料体现自己的观点主张。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方法,将经过整理取舍的材料融会于《史记》之中,去实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宗旨,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进程的雄伟画卷。
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
《史记》凝聚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意念始,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记》取材丰富而具体,广博而典型。概括起来,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档。《太史公自序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西汉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国家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马迁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在汉初,朝廷就已对典籍文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提高了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马迁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备的优越的利用文献的条件。
司马迁运用西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具体篇章常常用“予观《春秋》”、“其发明《五帝德》”、“余以《颂》”、“采于《书》、《诗》”、“余读管氏商君《开塞》、《耕战》书”、“皆道《孙子》十三篇,”、“世之传郦生书”,或以“《礼》曰……”、“《周官》曰……”等方式说明所用材料出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具体篇章中还以种种方式,或是直录书名,或是采用某书之文等,显示出引用典籍的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西汉图书宝库的丰富收藏。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一百零六种之多。(张大可《史记研究·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划分,它包括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至今,这些典籍半数已经亡佚。而且,这并不能说司马迁著《史记》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所引典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汉以后就已亡佚,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难以知晓。仅从今天可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说:“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二是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虽没有成书,但它的史料价值并不低于典籍,或者可以说更重要、更宝贵。因为它们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灭亡后,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史记·萧相国世家》)这里的“图书”,是指地图和官方文书,应该包括郡县分布及各地形势图、户籍、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军事活动进程及朝议、巡游、封禅之纪录、各种制度的文本等。我们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史记》记述礼、乐、律、历、封禅、河渠、经济货币等制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赵高、蒙恬等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运用这些材料的痕迹。汉代档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汉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体、真实的材料,它大致包括: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纪录等。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这些具体的材料,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郦滕灌列传》所记樊哙的军功,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均是据计功档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记加封功臣,更是依据了计功档案。《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史记》引用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往往用“据……”、“天子曰……”、“诏曰……”、“有司言……”、“公卿言……”、“……上书”等形式表明所引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等档案资料。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在这方面,司马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正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选择地运用到《史记》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但“总不离古文近是”,《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幸运、背时,家族的兴旺、衰落,侯国的强盛、毁亡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后,“余视其母冢,良然”,引发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所以在《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再如“吾适齐”,体验到齐国百姓的天性“阔达多匿知”,是齐太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其他如亲身调查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古今地名变迁、各地物产习俗等,无不给他以熏陶、启示,对《史记》的撰写起了重大的作用。
(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当代人、当代事作《传》。这些人或作古未久,这些事或发生未远,均无书面材料可据。给他(它)们作《传》,就如同我们今天写“报告文学”,如果能参与其事,或是耳闻目睹,则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司马迁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因为《史记》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记》所记的亲闻亲见、亲身经历,他们父子皆在其中。同时,他们父子二人相继为太史令,其所经历的与作《史记》相关的人与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制度、事迹方面,如司马迁随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亲身参加了封禅大典,并且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史记·封禅书》)了解了当时“用事于鬼神者”的“表里”,所以在《封禅书》中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讥讽了武帝醉心于封禅之事的穷奢极欲行为;他随从武帝巡视黄河的瓠子决口,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的劳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为武帝当场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动“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灼龟问卜活动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频繁举行。传至西汉,具体过程已不甚了了。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卜为手段,或是牟利致富,或是构陷他人。司马迁为了揭开笼罩在龟策占卜行为上的神秘光环,“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仅得出食龟“有益助衰养老,岂不信哉!”的结论,(《史记·龟策列传》)于是作《龟策列传》(《龟策列传》原文已佚,仅存司马迁写的《序》,《传》文是褚少孙补写的)。在人物方面,如《史记》记叙战国史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记载了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始末,就是“吾闻冯王孙曰”得来的;《刺客列传》详尽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秦始皇侍医)游,具知其事,为余(指司马谈)道之如是”;《韩长孺列传》记叙了韩长孺的种种具有长者风范的事迹,他与壶遂都是梁人,而司马迁“与壶遂定律历”,亲身感受了“壶遂之深中隐厚”的性格,由他们二人的品德,印证了“世之言梁多长者”是“不虚”的。
司马迁把亲身所闻所见写进《史记》,使其内容更加准确、详尽、真切,为后世了解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可贵的资料。
2.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经过父子两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马迁掌握了丰富而又博杂的资料。司马迁根据《史记》的创作宗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确定了选择运用这些资料的原则,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厥协六经异传,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创作《史记》,是要效孔子作《春秋》,总结往古,彰明汉室,垂教后世。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一尊孔子整理过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以之为圭臬,也就是他所说的“折中于夫子”。但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传至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千万数”的经传“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抵牾”,(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何为孔子真谛,需下“协”的功夫。“协”就是综合。综合解说六经的各种异传,使之归于一致。一致的标准是符合孔子的原意。
《史记》中,上古史的绝大部分史料来自六经传记,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取材于《尚书》的《禹贡》和《甘誓》,另外补采了一些《世本》中的记载;《殷本纪》多据《尚书·商书》;《周本纪》多取材于《尚书·周书》,并分别补采了《诗经》、《国语》的一些记载。《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史料多来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传记部分取材于《礼记》。司马迁“协理”六经的重点在于“异传”,如果某种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记载没有异传,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说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了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悼,遭到子贡批评的事,鲁哀公在悼词中自称“余一人”,子贡对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抨击了鲁哀公的虚情假义行为和僭号言论。《公羊传》和《谷梁传》均未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全文录用了《左传》这段文字,以表明对鲁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评价。如果六经异传对同一件事记载不同,司马迁则“折中于夫子”,取一家之说,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例如《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公羊传》、《左传》在解经中都记叙了齐臣逢丑父为了让齐侯逃跑,自己冒名顶替齐侯欺骗晋军。可是,后果二传却记载得大相径庭。《公羊传》记叙为晋将郤克说逢丑父是“欺三军者”,按法当斩,“于是剒逢丑父”。《左传》则记叙为:“郤献子将戮之,(逢丑父)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采用了《左传》的说法,赞赏了逢丑父的忠君行为,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六经异传对同一事的评价相同,《史记》就同时采用各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说基本一致,《左传》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的话作解。《三传》均持这是“为天王讳也”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便无歧义:“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周本纪》和《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由以上诸例可以清楚看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折中于夫子”。
(2)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关于“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区别,虽然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概念还是很清楚的。“六经异传”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对它们进行解说的《传》。除此之外均是百家杂语,既包括战国、秦汉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也包括汉以前的史书,如《世本》、《国语》、《战国策》(当时尚未有统一书名)、《秦记》、《楚汉春秋》等,还有一些诗赋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著作,诸如《禹本纪》、《山海经》、《燕丹子》等。大体上说,司马迁写战国秦汉史的素材主要来自百家杂语。
“整齐百家杂语”的“整齐”,就是整理选择使之统一。自春秋起,学术下移,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私家著述层出不穷。而各家都有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体系,从他们各自的体系出发,常常产生一些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司马迁面对这种种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家杂语,就必须进行“选择整理”,使它们统一到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下。司马迁所作的“选择整理”,也有他的原则。总的原则是“考信于六艺”,就是说使之与“六艺”相印证。为贯彻“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又制定两条具体的标准:一是“总不离古文近是”;二是“择其言尤雅者”。所谓“古文”,其实并无深意,就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书,因为未经后人改窜,比较真实可信,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本”。学术界一些人根据这里的“古文”二字,便说司马迁是古文学派。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产生壁垒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术派别。所谓“言尤雅者”,一是指书的内容不荒诞,二是指言辞不轻浮。司马迁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史记》中有明显反映。如《五帝本纪》对上古帝王世系的确定,就是“整齐”掉百家杂说中“不近于古文”的说法。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诸子书有种种说法,《庄子·胠箧》、《六韬·大明》、《逸周书·史记解》、《战国策·赵策》、《山海经》、《左传·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吕氏春秋·古乐》均记有上古帝王世系。可是司马迁对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说法,因为其“不离古文近是”,同时结合《尚书·尧典》,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五帝。我们并不是说司马迁的确定是正确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系统。再如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咸不同”,就是离“古文”的记载差得太远了,所以“乖异”。他认为像谍记这一类的文献,列出黄帝以来的具体年数,是不可靠的。他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阈,不可录。”并由此肯定地说:“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孔子都没能论年次,这些谍记怎么会论得出来呢!至于百家杂语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了。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可是《山海经》却载黄帝与蚩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司马迁认为所记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记·刺客列传》论赞说:“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迁说它“太过”,就是太荒诞了。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们阅读先秦诸子的书,还会发现这些书里相当多的对上古事件、人物的记载与《史记》所载不同,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近“古文”而没有收入《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了“整齐”众多纷繁的百家杂语,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
——出自《史记说略》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一直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那些能够帮助我构建宏大历史框架的著作。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往往会被细节淹没,或者因为零散的知识点而感到迷茫,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脉络。《二十五史说略》这个名字,光是听着就有一种“纲举目张”的希望。我期望它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越浩瀚的史海,点明那些关键的时期、重要的人物和影响深远的事件,让我能够站在制高点上,俯瞰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我不是历史专业的学者,但我渴望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历史认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那些庞杂的历史信息进行提炼和梳理,让我这个历史“小白”也能轻松地理解其中的逻辑和发展。它应该是一本能够激发我对历史学习兴趣的书,而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教科书。我希望它能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如果它能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就更好了,毕竟这些都是构成历史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分这本书拿到手的时候,就被它厚重沉稳的质感深深吸引了。封面采用的是一种哑光处理的深蓝色,摸上去细腻但不滑腻,触感温润。书名“二十五史说略”几个字采用了烫金工艺,在光线下会泛出淡淡的金辉,显得格外大气和庄重,一看就知道是精心设计过的。打开书页,纸张的厚度适中,色泽是柔和的米黄色,对眼睛非常友好,即使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疲劳。字号大小也刚刚好,排版疏朗有致,没有那种拥挤感,让人读起来非常舒服。合上书页,它的重量也很实在,拿在手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学问感,光是摆在书架上,就已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书本的装帧工艺也非常考究,每一页都缝合得严丝合缝,用力翻开也不会有松散的迹象,可见其制作的精良。而且,它还有一块丝质的书签带,平时看书看到哪里,轻轻一夹,下次翻开就能准确找到,这种细节的周到,真是让人倍感贴心。总而言之,从外在的包装到内在的印刷,这本书都展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者的诚意,这本身就为我的阅读体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让我对即将开始的阅读充满了期待。
评分我一直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宝库。而《二十五史》,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其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原典浩瀚,并非所有人都有精力去研读。因此,一本优秀的“说略”类书籍,便显得尤为珍贵。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精炼而深刻的方式,解读二十五史的精髓。它应该能够帮助我理解每一部史书的时代背景、编撰特点,以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让我领略到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例如不同朝代的治国理念,以及对人性、权力、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历史的“读法”,教会我如何去分析和理解历史事件,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也许它会提供一些关于历史规律的思考,或者对某些历史人物做出一些有见地的评价。我渴望它能在我阅读时,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去探索更深层次的历史奥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表面的了解。
评分我对于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迷。而二十五史,无疑是承载和记录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历程最权威、最详实的文献。我希望这本《二十五史说略》能够成为我通往这片知识海洋的桥梁。我期待它能够以一种不失严谨又不失趣味的方式,带领我走进那些王朝的兴衰,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以及那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的重大变革。我希望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能够体会到古人的智慧,能够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它应该能够点亮我心中的历史地图,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比如,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在思想文化的传承上,在科技的进步上,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我都能有所感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立体的历史认知,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并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力量。
评分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但对阅读的热情从未减退,尤其是那些能够拓展视野、增长见识的书籍。这次注意到《二十五史说略》,是被它“说略”两个字吸引。我知道,要将“二十五史”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进行概括和解读,绝非易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的是,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至于太过晦涩,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精准地提炼出每一部史书的精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想要的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介绍,让我能够快速地掌握二十五史的全貌,了解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和历史价值。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史学框架,了解史书的编撰传统,以及如何去解读和运用这些历史资料。如果书中能够包含一些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或者如何避免历史误读的提示,那就更完美了。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在学习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捷径”,让我能够高效地获取关键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好评!质量很好,内容也不错,慢慢看。
评分国学经典,精品收藏,趁活动价拿下,值!
评分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也有不算新元史而计入《清史稿》的) 二十五部史书。二十五史之中,除第一部《史记》是通史之外,其余皆为断代史。
评分很好,非常满意,要再买一套
评分才看了一部分,感觉还行,看资治通鉴前先看看这个了解一下,印刷质量啥的都不错,就是有点大了。
评分崔永元亲笔题词,致敬普通口述者和口述史从业人员
评分京东正版,价格实惠,值得翻阅收藏。
评分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也有不算新元史而计入《清史稿》的) 二十五部史书。二十五史之中,除第一部《史记》是通史之外,其余皆为断代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