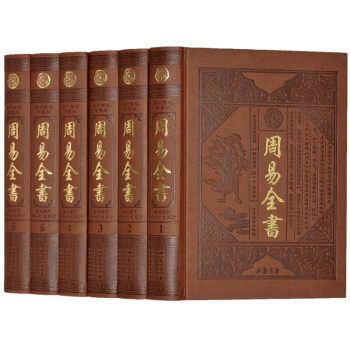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在20世纪中国遭遇了激烈批判;但常被忽略的是,此时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对人伦的反省,创造了三个“学术神话”: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其中di一个还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本书考察了这三个命题在西方古今形质论哲学传统中的根源,尝试探索在中国文质论传统中反思人伦问题的可能。本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比较极端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
吴飞,男,1973年出生于河北肃宁,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自杀问题、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奥古斯丁)、宗教人类学、中西文化比较、礼学、清代思想史等。吴飞学术的根本问题意识来自于混杂了古今中西各种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的现代中国。通过对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提出了西方思想作为“形质论”、中国思想作为“文质论”的结论。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使命:在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处境之下接续清代自戴震、程易畴至张锡恭、曹元弼以礼学(尤其是《仪礼·丧服》)为基础、以“人伦”为核心的、兼采汉宋的一套独特的、未完成的“清学”,并将之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进行重构并发扬光大。
主要著作有:《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SuicideandJustice:AChinesePerspective,Routledge,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书社,2001;宗教文化,2013)、《尘世的惶恐与安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北京三联书店,2013)、《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译著包括:《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海三联书店,2007-2009,三卷本)、《苏格拉底的申辩》(华夏出版社,2007;修订版,2017)。
主编有:《“思想与社会·第八辑”·洛克与自由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12)、《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目录
导论:重提人伦问题一、以仁黜礼:人伦批判的第一条线索
二、礼法之争:人伦批判的第二条线索
三、母系社会:人伦批判的第三条线索
四、对中国母系论的批驳
五、西方的人伦神话
上篇 知母不知父——“母权神话”探源
一、父母何算焉
二、婚姻史的辩证法
三、母权论的自然状态
四、男女与哲学
五、父母与文质
中篇 礼始于谨夫妇——“乱伦禁忌”与文明的起源
一、进化论与家庭伦理
二、达尔文的自然正当
三、神圣家庭与乱伦禁忌
四,作为人性的乱伦
五、从爱欲到力比多
下篇 资于事父以事君——“弑父情结”的政治意义
一、独眼巨人王朝
二、孝敬性背叛
三、弑君与弑神
四、家父与君主
结语: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人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人伦作为哲学问题为什么我们又感觉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人伦遭到了长期的忽略呢?这并不是因为人伦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无论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还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中,人伦都是西方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不是因为重要的思想家不谈人伦,虽然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家庭主义者很少,但在大多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对人伦的讨论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很难想象,人们在思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候,会完全抛弃掉家庭问题,涂尔干把家庭当作一切神圣制度的源头,更是将人伦问题上升到了最高位置。
真正原因在于,当西方思想家在回答更根本的哲学问题“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有什么关系”时,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人有没有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之上,追求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于是,现实物质世界与超验精神世界的二元分立,成为西方哲学思考“形质论”传统的一个重要品格,而人伦问题往往被掩盖了。
在这二者之间,人伦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存在很大讨论空间的问题。一方面,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如性需求、生儿育女、延续种族等等,好像属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血缘关系也只不过是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家庭中相互结合,家庭中的道德伦理,似乎又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在古今哲学家的诸多人伦争论中,问题的焦点就往往发生在这双重性之上。像《理想国》中所描画出来的智慧世界,就把尘世生活的诸种制度和道德拒斥在地上;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继承了这一思路,奥古斯丁同样将现实中的家庭当作魔鬼之城的一部分。但亚里士多德就看到了家庭生活与城邦的关联,对家庭中的道德伦理有更多肯定,托马斯·阿奎那也对家庭和国家都有更多肯定。至于巴霍芬将母权社会当作更接近自然,而父权社会是精神性的,涂尔干把家庭当作最初的神圣社会,都充分肯定了人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不过,巴霍芬和涂尔干又都将人伦关系拆解了,他们所肯定的只是一部分的人伦关系,却把其他类型人伦关系的地位大大降低了,这还是因为,人伦关系很难纳入他们对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圣俗二分框架。
这种二元分立在古典希腊哲学中已经很明显,灵智派将它推到极端;基督教虽然试图以万能的上帝和意志概念来沟通二者,但在实质上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分裂。[2]夹在二者之间的人伦问题,也会被卷入这种对立和断裂当中。所以,到了现代思想中,我们既会看到涂尔干这样对人伦关系的高度肯定,也会看到弗洛伊德那样对人伦问题的彻底化约;既可以看到对精神生活更高的追求,也可以看到自然世界的空前反抗。于是,人伦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
这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人类生活的一些方面却回到了混同于禽兽的状态。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遍追求平等的时代,但很多思想家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是深入骨髓的;时代的精神要求人们走向充满爱的世界,但文明的发展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商业关系。难道文明的进步都只是假象,这一切带来的都仅仅是道德的堕落与人伦的解体吗?平心而论,我们无法这样彻底地否定现代文明的成就,无论是它带给全世界的还是中国的,进步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这种进步是在文明与自然高度分裂的状态下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分裂,在精神性创造达到极其崇高的境界之时,那些固守尘世生活的人们似乎显得尤其粗鄙和庸俗。本来是为了纯化道德、敦厚人情的礼节,现在却显得极其虚伪、平庸、装腔作势、俗不可耐。这是一个崇高与鄙俗同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分裂时代,人伦的解体正是这种分裂的后果。但这种解体更多发生在意见中,我们毕竟仍然生活在人伦之网当中,没有一刻可以回避人伦的问题。如何为人伦生活重新找到妥当的安置,不仅是这个诡异时代的重要问题,而且牵涉到对宇宙观、世界观的全面调整。这要求我们在思考崇高生活的哲学框架中,给人伦问题一个新的定位,看有无可能使它不会随着精神追求而分裂和跌落。
在五四的大讨论之后,中国也被卷入到了现代世界的文明体系中,领略了政治生活的严厉与社会生活的美好。但无论我们对西方政法体系的接纳,还是对母系社会的思考,都处在相当被动的姿态,这种被动使我们在以西方的概念思考自己的人伦问题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不过,前辈学者毕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我们必须采取更大的主动,要看到,母权神话只是西方现代人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只是西方形质论与意志论哲学传统的一个环节,要看到形质论哲学背后真正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一体系的现代版本的问题所在。
如何超越于凡俗的自然生活之上,寻求更高的文明境界,这是中西圣贤同样关心的问题。但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圣贤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思路?这条思路有可能造成压抑人性的后果,这是五四学人已经看到的现实。但我们应该比五四时的学人看到更多的维度——因为我们有可能看到西方人伦思考中更多的层面,可以更全面地审视古今中西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比五四学人问得更复杂些:在自然生活与人类文明之间,有没有可能给人伦一个更好的安顿?在和西方形质论的对比中,中国圣贤的解决方式到底有何不同?中国的这种方式能否更好地处理自然和文明的关系?
面对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中国圣人确实没有采取形质论的思路,而是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高明的精神境界,并不是现实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生活,而要在人情的质地中,寻求人伦的纹理。缘情以制礼,是始终不能丢弃人情的本然状态的;但礼乐文明的内核,又是对质朴生活的一种提升与文饰。所以,要达到极高明之境,必本乎中庸之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贤,恰恰不是标新立异、素隐行怪之人,而是最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道理、比一般人还要正常的人。所以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在这样的一套思想体系之中,天地人之间不会出现那种无可化解的断裂。人伦,是这个体系中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说中国思想重视人伦,并不是说中国的家庭生活就比西方更重要,也不是说,中国的家庭就一定比西方的家庭更和谐美满,而是说,在中国思想中,人伦秩序是天地秩序的体现,也是家国秩序的基础。
《易》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人伦秩序与天地秩序是贯通的,夫妇关系与父子关系是贯通的,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又是贯通的。虽然古书中也有上古之世“知母不知父”的说法,但并没有出现以乱伦为自然,以人伦为文化的思路,没有出现夫妻关系与家庭关系相对立的假设,更没有出现弑父继承、弑君继承这样的理论。因而,忠孝一体,移孝可以作忠,圣王当以孝治天下。即使是通过篡位弑君夺得帝位,也一定要褒封前代之后,以示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即使在从清朝向中华民国的演化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份严肃的逊位诏书,而不是兄弟联合弑父的场景。[3]君臣之伦虽已不复存在,但对于我们仍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理解这套贯通的道理,当为理解人伦秩序的中心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种思路会导致对人性的压抑呢?任何一套思想体系,都会有着内在的张力。西方形质论的思路中,形与质之间的张力有可能演化为精神与自然的分离与断裂。同样,文质论的人伦架构也经常会出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情况。文、质之间任何一方的偏胜,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问题。本来应该缘情而来的礼文若是变得过于繁琐,失去了人情的基础,就会成为压抑与束缚人性的桎梏;反过来,若是任由人情泛滥,冲破了任何节制与礼文,就会造成人伦解纽的混乱局面。在这个框架之中,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之所以和魏晋玄学的论调非常相似,就是因为这两个时代都在激烈反对文胜质则史的状况;但现在之所以陷入到人伦混乱的状态,又是因为批判太过导致了质胜文则野。文与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维护文质彬彬状态的关键。这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有诸多可以呼应的地方。
回到本书最开始谈的问题:五四时期的主流论调虽然与魏晋时期非常像,但批判之后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人伦批判对于去除僵化礼教的禁锢,确实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所以正如贺麟先生所言,这种批判其实是儒家思想新一轮建设的开始。不过,这次批判是在彻底否定了君权和宗法制度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而且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变得越来越复杂。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中的言论虽然与孔融有些相似,但其背后却是康德的逻辑。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成为既有的事实,政治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也已经成为我们同样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否从人伦出发,重建自然与文明之间“文质彬彬”的关系呢?
只有在与西方思想更加深入的对话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好地消化近代以来的批判,才可能开出一个新的局面。但对话的对象不能仅限于母系论,而必须向前、向后,并向纵深展开,以中西思想中最根本的观念来对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西圣贤所关心的实质问题是一致的,对辩证法的运用也可互通,对许多人伦问题的讨论都可以相互激发,只是由于思考方式的差别,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本书中,我们只是尝试对文质论文明中的“知母不知父”问题略作分析。我们希望以后能够以更中国的方式来更好地理解人伦问题。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色彩的运用大胆而富有张力,仿佛预示着故事本身的跌宕起伏。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起它的时候,那种厚重的质感和散发出来的独特油墨香气,就让我立刻沉浸在一种期待之中。书页的装帧也极其考究,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制作者对这本书的珍视。故事的开篇并没有急于抛出核心冲突,而是用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触,缓缓铺陈出一个小镇的日常生活场景。那里的空气似乎都带着一种湿润的泥土气息,人物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和未言明的潜流。作者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令人惊叹,比如一个老妇人整理窗台上花盆的动作,或是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林间的样子,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实则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深远的伏笔,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回味和揣测。整体而言,阅读体验是极其流畅和享受的,它成功地将读者引入了一个既熟悉又充满异质感的叙事空间。
评分情节的推进速度掌握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拖沓,却也绝不让人感到信息过载。作者显然对叙事节奏有着极强的把控力,高潮部分的爆发力十足,而在紧张的间隙又能适时地插入一些哲思性的停顿,让读者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间。我尤其欣赏作者处理多线叙事的方式,几条看似无关的故事线,在巧妙的时机点汇集,那种“原来如此”的顿悟感是阅读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之一。某些角色的命运转折,设计得极为精巧,完全出乎意料,但回溯去看,又觉得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书中对特定场景的氛围营造,更是达到了教科书级别的水平,比如那场发生在暴雨之夜的秘密会面,文字仿佛变成了三维的声光电,让人仿佛亲历了现场的压抑与惊悚。这种代入感,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
评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在结构、人物和语言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作品。它没有提供任何廉价的答案,反而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迫使读者跳出舒适区,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和既有的观念。读完后,我感到一种智力上的充实和情感上的震撼,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富有意义的旅程。它的后劲很大,很多场景和哲思会时不时地在日常生活中闪现,提醒我曾经在那里留下的印记。我强烈推荐给那些不仅寻求故事,更渴望被文字触动灵魂、寻求思想共鸣的读者。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次与一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深度对话,让人在合上书页后,依然久久不愿离去。
评分语言风格的灵活性令人赞叹。在描述宏大场面时,文字气势磅礴,如同史诗般庄严;而在刻画亲密场景或私密情感时,笔调又变得极其细腻婉转,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这种在不同语域之间自如切换的能力,极大地丰富了阅读的层次感。书中不乏一些极具张力的对话,它们往往言简意赅,却饱含深意,每一次交锋都像是思想的激烈碰撞,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同时,作者似乎非常善于运用象征和隐喻,许多看似寻常的物件或自然景象,都被赋予了超越其实质的含义,为文本增添了无穷的解读空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揣摩其中几段关于时间流逝的描写,其措辞之精妙,结构之严谨,让人忍不住想要抄录下来,细细品味。这种对语言工具的极致运用,无疑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评分人物的塑造是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特质之一。这里的角色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他们都是在特定环境和压力下做出选择的复杂个体。主角的内心挣扎尤其真实可触,他的每一次犹豫、每一次妥协,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弦。我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看”故事,更像是“活”在了这些人物的生命体验之中。特别是几位配角,虽然戏份不多,但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他们就像散落在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移动之间,全局的格局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者没有简单地用标签去定义他们,而是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展现了他们性格的层次和矛盾性。这种对人性的精微剖析,使得故事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具有了探讨人际关系本质的深度。读完后,你很难立刻抽离,仿佛还能感觉到那些人物的呼吸和温度。
评分非常不错的一本社会学著作,值得购买,更值得阅读!
评分活动价格比较划算,屯着
评分这次京东活动非常给力,许多想买的书都入手搞到了。快递小哥也给力。谢谢?!
评分伦理学的本质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科学,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或者说,伦理学是以人类的道德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伦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复杂,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决定谁,以及道德对经济有无反作用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评判标准和取向。
评分内容很丰富,制作也不错!喜欢这种书刊!
评分此书不错,教授推荐购买
评分活动买 合适。
评分书不错,服务也不错,满意
评分北大吴飞教授的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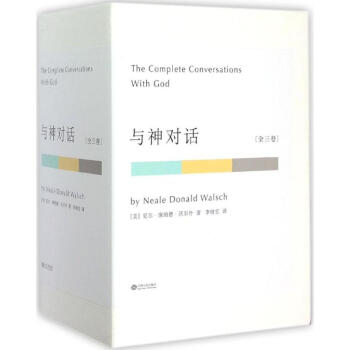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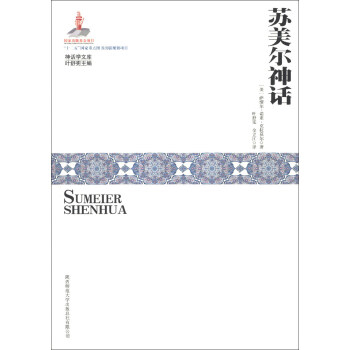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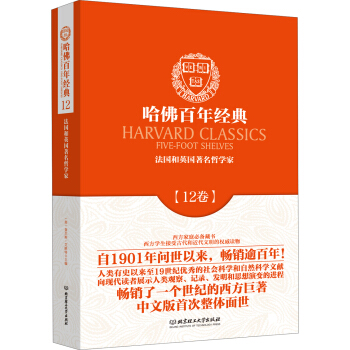


![体验宗教:传统、挑战与嬗变 [Experiencing the World’s Religions: Tradition, C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45713/5a167679Nf8cafd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