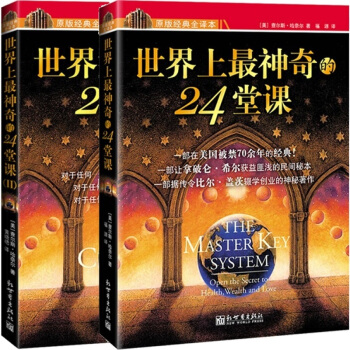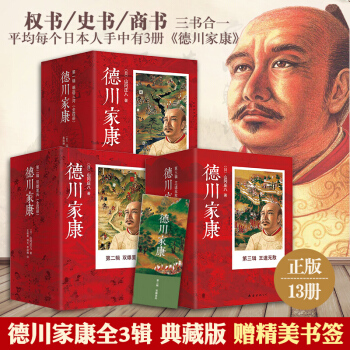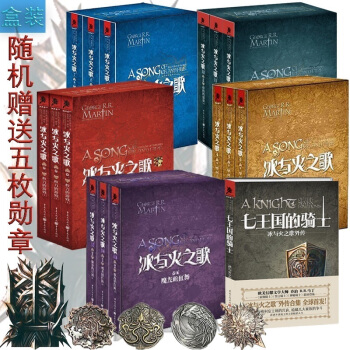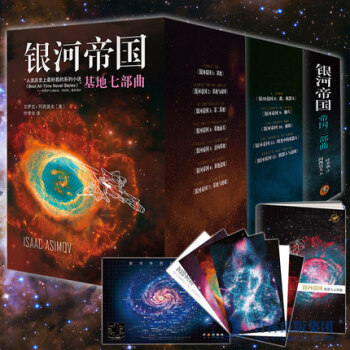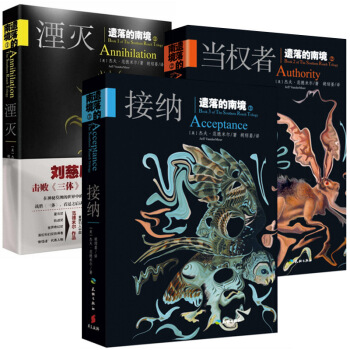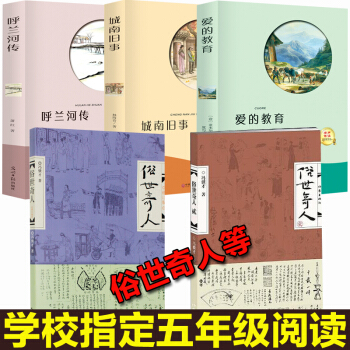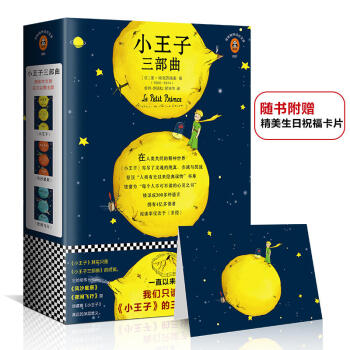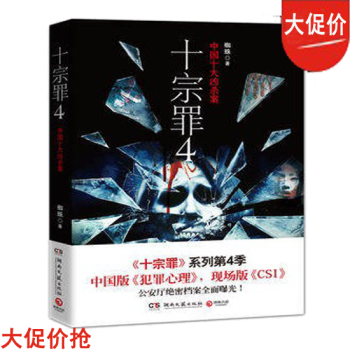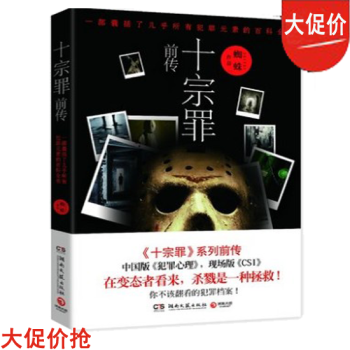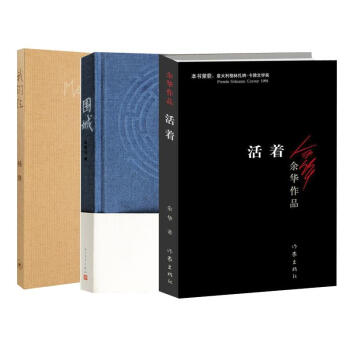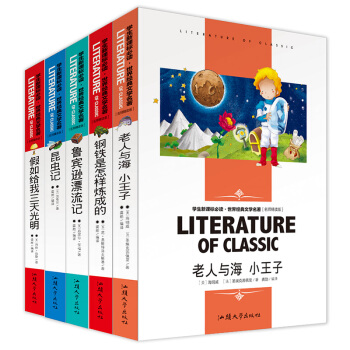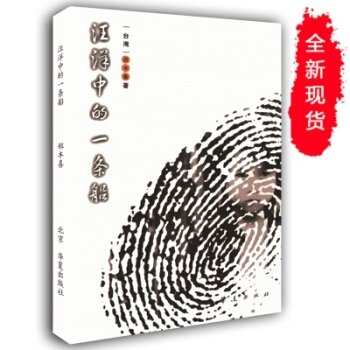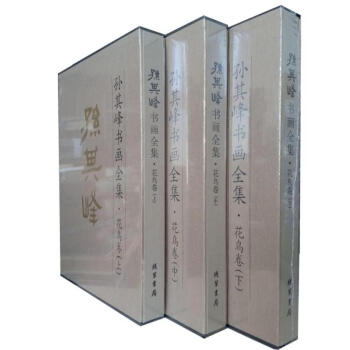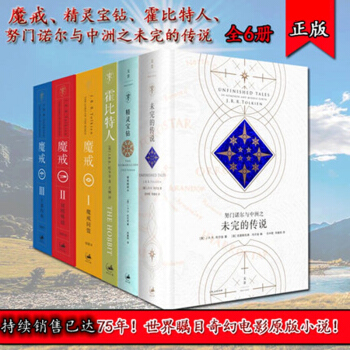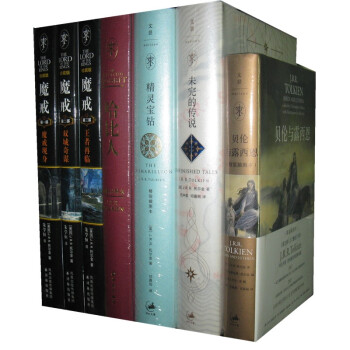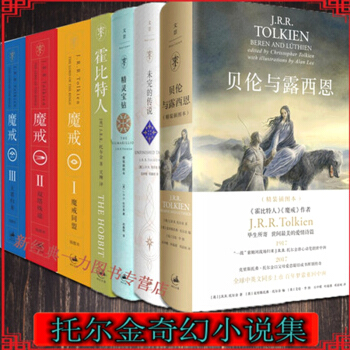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他来自农村,生性怯懦,在人才辈出的钢七连显得如此不着调。但就是这种笨拙,让他心无旁骛,让他心思简单,无往而不胜。
从不抱怨,相信别人就像相信自己,承担所有误解,接受一切现实而永不改变内心的信仰。他是当代中国军人*真实的士兵形象,他叫许三多,一名二级士官……
作者简介兰晓龙:
生于湖南邵阳。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成为职业编剧。现居北京。
话剧《爱尔纳·突击》获得2002年全军新剧目展演编剧一等奖。2005年2月《爱尔纳·突击》获得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奖。
代表作:《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好家伙》
前 言楔子
一只蚂蚁攒行于它这一系侦察蚁用腹腺分泌物标志的蚁路上,这东西对它的重要就如铁轨对火车头的重要。世界对它像对我们一样是个大得没谱的地方,它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靠那些不可复制的碳氛分泌物确定前边是不是它该去的地方,我们则只能靠蜘蛛网一样延伸的交通网络和航班表,自然,我们、我类或者说我辈族群中间也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去同类未有涉足的地方,或者是丛林莽荒或者是心灵的纵深,但那类家伙叫作冒险家,就如那类的蚂蚁叫作侦察蚁一样。博苑图书
但我们这只蚂蚁是只兵蚁,褐色族群。无论颜色,兵蚁就如我臆想中“一战”时的士兵,终其一生装在不见天日的闷罐车里,运行于据说安全实则杀机四伏的轨道之上,直到车门打开看见天日的时候……
作战。
终其一生。
好吧,我们的褐色兵蚁不听我们的唠叨,它不安地竖起了触须,今天的空气不大对劲,前边出现了十二只兵蚁的身影——幸好那支小分队和它属于同一蚁城。
它跑上前,立刻和领队者开始了永恒不变的互哺和交流。授予者从自己的公共嗉囊吐出流质食物,搓成球状喂给饥肠辘辘的伙伴。我们的兵蚁很想报答以同样的行为,但它力不从心,它要把消息送回去,路还长得很。
蚂蚁触角上的十一个节能释放出它独有的费尔蒙,这是它的十一张嘴。十一张嘴同时又是十一只耳朵。
提供食物的领队者从兵蚁的第一节触角上知道它的年龄:一岁。从第二节触角上知道了它的军阶:无生殖力狩猎兵蚁。第三节触角指出它的种类和所属蚁域。第四节触角显示了编号和称呼。第五节显示出兵蚁的精神状态:疲劳而激动。第六节用于一般交流。第七节专用于较复杂的对话。第八节只用于和蚁后交谈。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在战斗时可作为大头棍使用——类似我辈族群中的*甩棍。
……
您确定您买对书了吗?是《士兵突击》不是《蚂蚁突击》?
我坦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士兵突击”四个字后写上了一只蚂蚁,然后就此敲响了新换的键盘——也许只是觉得声音很爽——然后无耻地抄袭着法国佬贝尔纳·韦尔贝尔《蚂蚁联邦》的片段。贝尔纳·韦尔贝尔试着用蚂蚁的触角来观察、评论甚至改变世界,但是世界让蚂蚁茫然就像让我们茫然一样——蚂蚁的世界是方的,世界的尽头寸草不生,像地狱一样冒着焦化的沥青味……真是不幸,某位侦察蚁的伟大冒险遇上了我辈族群的蚁路:沥青浇的公路,并且就此终结。世界的尽头有毁灭和魔鬼,魔鬼的形态是巨大而柔软的粉红色柱子,有时一个单挑,有时五个一起出现,无论五个还是一个,那只侦察蚁的下场只有一个,成为沥青上肝脑涂地的一个剪影。实际上我不知道这只让哥伦布也要汗颜的侦察蚁如何发出*后的信息,也许只是在粉身碎骨的痉挛中用全部的触角,第一节至第八节,甚至包括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全力地嘶吼出它的信息: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世界到了尽头,到了世界的尽头……
五个或者单个出现的粉红色柱形魔鬼……和我辈族群恐怖的东西不大一样……是某个小孩恶作剧的手指头,他抬起他的手指头,上边还黏着那只仍在发送信号的侦察蚁尸体:我又碾死了一只。他心里模糊地说,并且有模糊的快乐。坦白讲,我小时候常干这样的勾当,长大后就像《中山狼》里的东郭先生一样小心脚下,唯恐断送了麦哲伦、伽利略和哥伦布,直到有一天自己也烦了,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心里说,死便死吧,这是命运。
书归正传,我们的褐色兵蚁和那支步兵班告别,迅速前往它的蚁城,它第五节触角上激动不安的信息我可以翻译如下:
不对劲。有异味。世界要坍塌,世界在震动。
蚁群的遗传记忆告诉它,那是那只永逝的侦察蚁前辈用全部触角描述过的气味,地狱的味道。兵蚁不知道那是沥青、汽油、钢铁、火药和硝烟的味道,和它不同族类中同一职业的人类的味道。
它所属的蚁城物产丰富,幅员广阔,九百六十万……——#¥%我在说什么?无边无际的方底穹形宇宙向无边无际的两端无尽延伸。它们的蚁后依照此格局构筑了辉煌的蚁城,并且竭尽心力想要模仿出方底穹形的内部结构——徒劳无功,混凝土抹出,非自然形态的方底穹形对还未发现火的蚂蚁们不可模仿,蚂蚁们的精神导师们于是把这种形状作为神之存在的铁证如山。
兵蚁回到了让它觉得安稳踏实的四方体宇宙。然后……
一个巨大的粉红色柱形魔鬼向它压了下来,另一个稍短但更粗的魔鬼加入……
兵蚁被拈了起来,而不是被碾死。
它用全部的触角——包括不具备发送功能的第九节至第十一节触角——竭尽全力地发送信号,并且力图这信号能强烈到加入它这一族群的遗传记忆:
世界在坍塌,世界在震动。别走了,到了尽头……
钢铁味、硝烟味、汽油味,非自然的纤维织物的味道。
魔鬼和末日的味道。
兵蚁在哭泣……不,兵蚁不会哭泣。《我的团长我的团》内容节选:
在长江之南的某个小平原上,我抖抖索索地划拉着一盒火柴,但总是因无力而过度用力,结果不仅弄断了火柴梗子,还让满盒的火柴撒了一地。我只好又从脚下去捡那一地的火柴梗。
我无力又猛力地划着火柴,这次我让整个空火柴盒从手上弹出去了。于是我再用抢命般的速度抢回地上那个火柴盒。
“烦啦你个驴日的!连根火柴也日不着啊?!”
我想起了我屡被冒犯的官威。我一手火柴,一手火柴盒,愠怒地盯着那个发话的对象——二排四班的马驴儿,河北乡下佬,怒目金刚,倒抡着他那条离腰折已经差不远的汉阳造,我现在不想说他要砸谁。
“我是你们的连长!”我维护我随着火柴梗子掉了一地的官威。这种抗议有点儿文不对题,并且立刻被反驳回来——“副的!正的正烧着呢!”
我是文化人,我认为这种辩论有点儿无聊。我经常认为别人很无聊,而我自己更无聊——我又开始跟火柴较劲儿。
马驴儿在不管我之前又嚷嚷了一句:“你不会跟连长借个火啊?——哇呀呀,驴日的!”
后边那一句是对他要砸的对象喊的,很京剧腔。喊过去之后,马驴儿就抡圆了他那条打光子弹当锹抡的汉阳造扑过去了,现在我可以说他要砸什么啦,哈哈——一辆日本九七式中型坦克,辗转着,原地转向着,咆哮着,炮塔转动着,与主炮同轴的同步机枪轰鸣着,像是冲进蚂蚁群中的庞大甲虫。与其说它是困兽犹斗不如说是在玩耍,因为像蚂蚁一样附着在它身上的中国兵实在是太不得要领,拿铲子砍的、拿锹棍撬的、拿手榴弹敲打舱盖以为里边会打开的、对着装甲开枪崩到自己的、跳脚大骂的都有。我跪在火海和坦克之间,脚下放着一个土造的燃烧瓶。连长在我身边燃烧。因为我连马虎潦草的抵挡,阵地已经被日军炮兵化为一片焦土,几乎所有死人都在燃烧着。我拿着火柴和火柴盒,似乎要划火柴,又似乎是在思考,而实际上只是 简单的三个字:吓傻了。
马驴儿成功地用枪托在装甲车车体上制造出一声巨大的响动,代价是枪托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这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他发现车头有个缝隙,就猫了腰低了头去看,其情状酷似从门缝里窥视。
那是航向机枪的射击孔。在突发的轰鸣声中他安静而飘逸地飞出去了。
这实在是让我看得发怔,但我身上有这种素质——即使在上吊的时候也不忘打击一下别人,我扯嗓子为他送行:“白痴! 后一次!”但我还记得马驴儿的提示,我看着手上的火柴盒,扔了它,看着手上的火柴,扔了它,我抓起燃烧瓶,爬向离我*近也烧得*炽烈的那个——实际上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团火焰。真是的,我为什么要跟一盒发了潮的火柴较劲儿?
“连长,借个火。”
连长没发表意见,我借了火,借火的时候肚子里发出饥肠辘辘的轰鸣。我吸了吸鼻子,因我在焦香中所起的生理反应而觉得罪过。此时我听见来自身后的机枪连射,夹着主炮发射的轰鸣,这与方才日军坦克的点射迥异。我拿着已经点燃的燃烧瓶回身。
坦克上已经没有附着的人类了,它在尸骸中进行一个小半径的转向,刚发射过的主炮炮塔对着我。不知属于谁的半截枪杆自半空落下,砸掉了我的茫然。三八式的子弹自侧后方射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好容易被我们和坦克分隔开的日军小队正拉了个散兵线,慢慢往这边走来。
我拉开了架势,扬起燃烧瓶,开始冲刺。那辆近在咫尺的九七式坦克现在看起来真是庞大无比,它的炮口正对着我,像只毒眼。三八式步枪又响了一次,是个排枪,燃烧瓶从我手上落下,我摔倒。
坦克以一种人散步时的速度漫不经心地离开,日军小队虽仍拉着散兵线,却也和散步一样漫不经心,其中一个日本兵经过我身边时,用刺刀捅进我的大腿,绞动了一下。
我死了,我就不动。
他们走了,消失于焦炽的地平线上,既然焦土上已经没有站立的中国人了。
整个阵地都在烧着。白磷和汽油在燃烧,武器和弹药在燃烧,尸体在燃烧,连泥土和弹坑都在燃烧,而我睁开眼时,只看见在我身边燃烧的那个燃烧瓶。它已经碎了,燃液在土地上流淌,流过我身边,把我没能划燃的火柴一根根点燃。我呆呆地看着那些在火海中依次蓬然亮起的小小火光,它们不属于我,从来就没属于过。
永远是这样。一群你看不上,也看不上你的粗人一再挫折你的希望,*后他们和你的希望一起成为泡影流沙。在经历四年败战和几千公里的溃退之后,我的连队终于全军覆没。
我叫孟烦了,二十四岁,今国军某支所谓新编师之一员,中尉副连长。家父大概是烦恼很多的样子,以致要用我的名字把烦恼了却。烦恼从不了却,倒连累我从小心事重,心事多,而且像刚才死的那些大老粗们,总是“烦啦,烦啦”地叫着,有的是不认字,有的是图省事。
现在他们都死啦,人要往好处看,我想我终于摆脱了“烦啦”这该死的名字。
一个多月后,我走在滇边一个叫禅达的小镇上,忽然听得一个山西佬在我身后鬼叫:“——烦啦!——烦啦!”
我站住,因为没能摆脱“烦啦”这个该死的名字而受惊、失望到狰狞。为了表示抗议我缓慢地顾盼,其实我知道叫我的人是谁。我现在给人一种迟钝和呆滞的假象,其实我是这时代为数不多的反应奇快甚至过快的人类之一。
我站在巷口,禅达的这整条巷子现在已被划为军事区,吓人名目下其实就是个溃兵集中地。溃散的各路诸侯被集中于此以免对地方上造成困扰。巷口草率筑就的沙袋工事和工事后的几个哨兵形同虚设, 多表示我们仍算是军人。我仍穿着装死时穿的那身衣服,这也是我唯 的衣服,它更加脏污和残破;我手上玩着一盒火柴,但已经不是我扔在逃生之地的那盒。
叫我的人自身后重拍我的肩膀。山西佬康丫的军装扣子已经全部掉光了,以致始终得腾出一只手掩着衣衫下摆,这是为了身份而非风化——一个兵敞着也就算啦,但康丫是准尉,他是官儿。
康丫,有着还算清晰的外表和*粗糙的心灵,生活对他来说是理应心不在焉对待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里他的甘为弱智是一种自保。他*的特点是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在问任何人要任何东西,要不到无所谓,要到了便当喜财。他甚至上茅坑都不带厕纸,宁可蹲在那儿找人要,他总是厚颜无耻地在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模糊地明白:生活不会让他这样的人占到更大便宜。
康丫说什么,是我睡着了也能猜到的:“有吃的没?”
我白眼向人,望了一望,慢慢把康丫的肘子抬到嘴边张口,康丫败不馁地拿开:“有烟的没?”
我开始摸身上,在康丫的期待中掏给了他一根火柴。康丫毫不在意地接过来开始掏耳朵:“有扣子的没?”
这是康丫的绝活儿,他会一直要下去,要到你不得不用什么来打发他。我只好看了下我衣服上所剩无几的扣子,康丫明白这算是默许,伸手拽走了一颗。同时,他发现沙袋后的哨兵扔下了一个烟头,足足半根!他在那烟头刚落地时就打算捡起来了,但扔烟头的很不给面子,在他手指碰到前就一脚踩灭了。
我不吸烟,没有康丫的那种欲求,所以我看着。一个军装工整补给齐全的编制内士兵和一个无兵无枪无弹只有一颗扣子的溃兵排长,像雕像一样一挺一躬地对峙着,相当有趣。康丫很快觉得不那么有趣了,因为哨兵拉了下枪栓,我们清晰地听到子弹上膛,于是雕像们活了,康丫不屈不挠地捡起了烟头,并且聪明地转向了我:“有火的没?”
我手上就捏着一盒火柴,我犹豫了一下,康丫立刻拿走了它,可那玩意儿的磷面都快被我玩儿没了,也快被我的汗手浸透了,根本划不燃。康丫徒劳地划几次后放弃了,扔掉了我的火柴:“你的火柴从来划不着。——有针线的没?”
我立刻捡起了火柴,有点儿像瘸子捡回自己的拐杖。我们早已不会为不被理解而愤怒了,所以我平实地回答他:“郝兽医有。”
“兽医死哪儿啦?”
我悻悻地打击他:“在问有吃的没。”
康丫对这种打击基本是免疫的,他提议:“一起去?”
反正今晨的逡巡除了个并无兴趣的烟头之外,并无其他发现,那就一起去。
......
李晨:如果这样一部诚意之作无法与观众见面,那我就解甲归田。
《好家伙》剧组筹备之初只有两个人:一个编剧,兰晓龙本人;一个演员,他的朋友张译。在朋友住宅的大堂里,两人各自不停翻着手机通讯录,一个接一个给熟人打电话。他记得自己靠着窗,视线里始终有一片湖,张译坐在沙发上,而电话那头的回复是意料之中的拒绝:“你要约我拍戏,居然只提前一个月?”
2012年,小马奔腾的李明找到兰晓龙,问他手头有没有可以做的项目。朋友的影视公司次年的项目运营量不够,而如果要赶在2013年的时间节点播出,筹备时间仓促得只剩一个月。
有一个非常早的剧本,曾在2004年拍成电视剧《零号特工》。“人家那边正愁着没项目,那就做吧。”兰晓龙说。
他答应得多少有点冲动,项目上马后才愈发意识到时间紧迫得不像话。他也觉得是在为难对方。这个时候会联系的演员多半已有过不错的交流,人家想来,可是合同定了,人正在剧组。整件事透着荒谬,找完演员,他们还要找导演。“连导演都没有,你说这剧组有多乱?”理论上说,提前三个月联系演员已经算仓促,而导演需要的时间更久,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来运作会需要半年筹备期。连放弃的时间也没有了:李晨加入了,三人剧组发动各自的资源,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这样了,干吧。”他咬牙切齿。
码齐人马,心思放回剧本,这位编剧才开始想到*要命的问题:《零号特工》版本的剧本里,张译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阴郁的人,李晨的角色则非常暴戾。“张译完全是跟阴郁对着干的啊。再一看,我靠,李晨也不是那个角色。”他们是敬业的演员,一个敬业的演员不会想角色跟自己有多贴近,而是拼命去贴近角色。但在兰晓龙看来,剧本不合适,这么演会把演员*有价值的、甚至不属于表演技巧范畴的东西丢失了。
他决定把两个主角的戏全改了。
每逢一部戏开拍,编剧对兰晓龙来说是*快活的环节。“谁都不好跟你急,制片人不好跟你急,演员不好跟你急,导演不好跟你急,没人跟你急。”他得意地说,“我就可以扮演我闺女的角色,所有人不说宠着你,至少得惯着你啊。然后坚决不干活,希望我改剧本?没门,我就是来捣蛋的。”
但是这一回,一边拍戏一边改剧本,他变成了一个眼冒绿光、精神非常充沛而外表非常消瘦的家伙。
每天一睁眼,焦虑就摆在那里。“明天就要拍这场戏了!”
《好家伙》是一个双线的故事,这意味着几乎每场戏至少有一位主角在场。为了节省时间,导演拿着没改的剧本先去做统筹、制景、定场地、做道具,兰晓龙则保证改剧本时不动场次、不动大场景、不动大道具。“原来那个场景发生在哪个房间,我都不会挪到另一个。但整个戏全部要改掉。”他说,惟一能改动的是人物基点。实际上,整个剧本全部重写。*后除了一个上海犹太人的名字叶尔孤白,他想不起有什么角色是没改过的了。
“这戏我花的力气,客气地说,至少够我做三个戏的了。”重提那段经历,兰晓龙还心有余悸。写剧本的日子里,他住在剧组,有时到导演屋里去喝点茶、吃点零食。俩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导演简川訸也累,他也累,累得谁也不想谈这个戏的事情,宁可明天现场发挥。
他们赶着时间拍完了电视剧,却没有料到等在前方的是接连的坏消息。2013年,电视剧的发行计划搁浅;2014年初,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去世。
《好家伙》播出时,已经是2016年9月底。阴差阳错,一切都缓了下来。
由于《好家伙》的播出,接受采访时他被频问及收视率相关的问题,比如:影视潮流变化非常快,这部作品已经隔了四年,是否担心跟不上观众审美?兰晓龙感到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对方在谈市场,他答非所问:这几年观众审美在倒退,对一个正在倒退的东西如何谈得上跟不上?
“我听说现在我们演戏都已经可以到现场不用记台词了?”聊到演员,他幽幽地扔过来一句。“摆个嘴形,随便说点什么。这跟表演还有什么相关?”
他不打算跟上所谓的潮流了,而且决定不再被这些东西影响。“有一拨人逐利,有一拨人踏踏实实该干吗干吗。后一拨活得舒服得多,我觉得应该做后一拨,就这样吧。”
用户评价
《士兵突击》这部作品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成功地将“励志”这个略显老套的主题,用一种极其接地气、毫不矫揉造作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许三多这个角色,从一个在家里被忽视的懦弱小孩,到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他的成长路径并非一帆风顺的开挂升级,而是充满了笨拙、坚持和一点点运气。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非常细腻地描绘了这种“笨拙的坚持”如何在一个集体中产生涟漪效应。他不需要成为最聪明或最能言善辩的人,他只需要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这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最终汇聚成了强大的力量。书中对“七连”这个战斗集体内部关系的刻画也相当到位,那种战友情谊,不是靠喊口号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起扛过最艰难的时刻,在彼此的缺点面前互相支撑而自然形成的。这种由内而外的凝聚力,让人看了非常热血,也让人重新思考,真正的强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评分要说起对人性深处的挖掘,我必须提一下《生死线》这部作品。它和《团长》那种直接面对历史创伤的厚重感不同,《生死线》似乎更偏向于探讨个体在极端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与“代价”。开篇的几章,那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简直要把人憋死。兰晓龙在这里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群像,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难以启齿的秘密和不得不履行的“契约”。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界限”的描绘,生与死、敌与我、忠诚与背叛,这些界限在故事的推进中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互相渗透。书中那些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场景描写,比如那片荒芜的土地,或者某个关键时刻的暴雨,都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宿命感。读完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梳理其中几位核心人物的动机,你会发现,最极端的行为往往源于最朴素的愿望——活下去,或者保护某件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部作品的节奏把握得极好,张弛有度,高潮迭起,读起来简直就像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博弈,后劲非常足,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最近一口气读完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上下两册,那种震撼感久久不能平复。兰晓龙的笔触实在是太有力量了,他没有过多渲染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将镜头紧紧对准了那群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人物。孟烦了,这个自诩为“一个人在逃跑”的兵,他的视角充满了世俗的、甚至是有些犬儒的清醒,却也正是这种清醒,让我们看到了战争最残酷的底色。他和其他“炮灰”们,比如那个看似莽撞实则心思缜密的迷龙,那个沉默寡言却无比可靠的克虏伯,他们的性格冲突与最终的相互依偎,构成了一幅无比真实又令人心碎的画面。更让我动容的是他对“家”和“身份”的探讨。他们没有明确的归属,只能在战场上互相成为彼此的“团”——一个临时的、脆弱的,却又无比坚固的依靠。那种“我们都是没有祖国的孤儿,所以我们自己造一个祖国”的悲壮感,读到酣畅淋漓的同时,眼眶也湿润了。这本书的对话设计尤其精彩,充满了市井的狡黠和底层人物的智慧,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反而让人拍案叫绝。它不仅仅是关于战争,更是关于人在绝境中如何保有尊严和人性的史诗。
评分不得不提的是,这套书的叙事节奏和结构安排,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不同篇章之间,虽然主题都围绕着军旅和奋斗,但切入的角度却大相径庭。《好家伙》那种带着点黑色幽默和江湖气的故事,与《团长》那种宿命般的悲壮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跨度的掌控力让人赞叹。特别是当你读到那些关于“兄弟情”的描写时,你会发现,真正的兄弟,不是你选择了谁,而是谁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你挡子弹,愿意为你扛下所有的后果。故事中的角色们,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军人的责任,更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和愧疚。兰晓龙似乎有一种魔力,他能让那些在历史中几乎被忽略的底层士兵,拥有了极其饱满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我甚至觉得,透过这些故事,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呼吸声,那种粗粝的、充满汗水和尘土的味道,真实得让人心疼。
评分我最近翻阅的这本小说集,特别是其中涉及到战争和人性挣扎的部分,给我的感觉是极其沉重的,但沉重中又透着一种近乎于原始的生命力。它不是那种粉饰太平的英雄史诗,而是用一种近乎于残酷的写实手法,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处境。我注意到作者在构建人物对话时,有着一种独特的腔调,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深度,仿佛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带着伤痕的哲学家。例如,在描述他们如何面对死亡和分离时,那种对“意义”的追问,非常耐人寻味。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没有硝烟,但每个人不也在日常的琐碎和压力中,不断地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吗?所以,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其时代背景,它触及了人类共通的困境: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如何在绝望中保有希望。读罢,仿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洗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