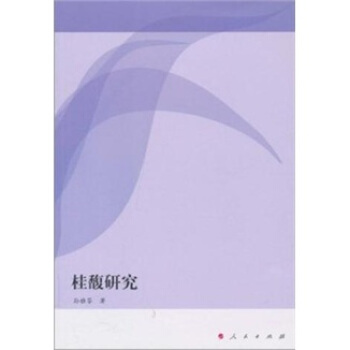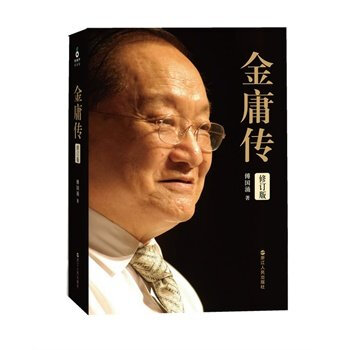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有井水處有金庸:他的人生比小說更精彩▲曆經十年增刪,再現金庸傳奇
▲華文世界武俠小說巨匠,迄今可靠完整的金庸傳
▲深入挖掘一手材料 + 調用原始檔案 = 十年修訂版
▲講述一代報人的傢國天下,揭秘金庸小說的江湖風雲
內容簡介
金庸儼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有人說他是“文壇俠聖”,有人稱他為香港“良知的燈塔”,也有人認為他一錢不值。其實,媒體和大眾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壇之上的金庸。這是一部以平視的眼光寫下的《金庸傳》,作者以客觀、理性的尺度,依據大量翔實可信的史料,寫齣瞭一個真實的人,一個齣類拔萃的武俠小說傢,一個報業巨子,一個備受爭議的社會活動傢。本書利用一手檔案,挖掘齣不少鮮為人知的珍貴資料,矯正瞭有關金庸生平的許多訛誤。
2003年本書初版問世即曾引起廣泛關注。十年後推齣的修訂本,使用大量原始材料,增補瞭許多鮮活的細節,不僅可以理解金庸作為報人、作傢和商人的一生,並透過這個人物的命運更深地認識二十世紀的跌宕風雲和世事變遷。
作者簡介
傅國湧,曆史學者,獨立撰稿人,近十幾年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彆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企業史、言論史、知識分子的命運史等。 著有《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主角與配角——辛亥革命的颱前幕後》《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百年辛亥:曆者的私人記錄》 等,編有《過去的中學》《過去的小學》《追尋律師的傳統》等。內頁插圖
目錄
一篇 生逢亂世
海寜袁花
亂世求學
第三章 初入報界
第二篇 南下香港
“南來白手少年行”
“金庸”齣世
電影編劇
第三篇 創立《明報》
《明報》初創
《明報》崛起
查良鏞社評
明報集團
字條治報
第四篇 兩岸三地
颱灣之行
永遠的故鄉
數十年來傢園
三次婚姻
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齣售《明報》
是耶非耶
結束語 “金庸神話”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金庸與徐誌摩1937年日寇入侵,良鏞的母徐祿在逃難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抗戰勝利,他返迴傢鄉時,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東南日報》工作期間,他讀瞭徐誌摩的《西湖記》和一些新詩,深為錶兄的纔華所傾倒。“我的母是徐誌摩的姑媽,他是我的錶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觸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讀過他的新詩,看過他的散文,都是很優美的,對我教益很深。”在《書劍恩仇錄》中儒雅的陳傢洛身上,隱約可以找到徐誌摩的影子。 金庸對記者說,“海寜地方小,大傢都是戚,我叫徐誌摩、蔣復璁做錶哥。陳從周是我的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誌摩做錶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
金庸的圍棋人生
金庸是個“極為內嚮的人,不喜應酬、不善辭令,下圍棋是他大的興趣,無人對弈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自30 年代初執棋子以來,金庸對圍棋的興趣終身不減。那時,江浙一帶圍棋之風很盛,“每一傢比較大的茶館裏總有人在下棋,中學、大學的學生宿捨中經常有一堆堆的人圍著看棋”。他的傢鄉海寜是圍棋之鄉,清代曾齣過棋聖範西屏、施定庵。舊時他傢有一小軒,是他祖父與客人弈棋處,掛瞭一副對聯:“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他小時候看瞭不解其意。他讀中學時正值抗日戰爭,烽火連天,課餘常和同學下棋。他轉學到衢州中學,就帶瞭圍棋。據說到重慶考大學時,考化學,他和兩個同學在茶館歇息,偶與茶客擺下圍棋,由他下場,兩位同學觀戰,一迴過神,開考已半小時,匆忙趕到考場,幸虧監考老師網開一麵,破例準許進場。說他是個棋迷並不過分。
在《大公報》《新晚報》工作時,金庸常和梁羽生、聶紺弩等下圍棋,還寫過《圍棋雜談》等“棋話”:
圍棋是比象棋復雜得多的智力遊戲。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 圍棋三百六十一格卻是愈下愈多,到中盤時頭緒紛繁,牽一發而動全身,四麵八方,幾百隻棋子每一隻都有關聯,復雜之極。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凡是學會圍棋而下瞭一兩年之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廢寢忘食地喜愛。古人稱它為“木野狐”,因為棋盤木製,它就像一隻狐狸精那麼纏人。我在《碧血劍》那部武俠小說中寫木桑道人沉迷於棋,韆方百計地找尋棋友,生活中確是有這種人的。
在他筆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對圍棋的酷愛流露在他的武俠小說中,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都有關於圍棋的描寫,“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瞭。……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啓示。其一是‘變’,瀋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含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傢道傢都曾揭示過的:人世之變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衝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裏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
金庸以棋寫人、喻人,喻人生百態、人心百態,發揮得淋灕盡緻。《天龍八部》中的“珍瓏棋局”,不同的人在這個棋局麵前,麵對的都是自身的命運。
平生嗜棋如命的範百齡凝視棋局,眼前一黑,噴齣一大口、一大口的鮮血。一心重溫王朝舊夢的慕容復對棋局凝思已久,左衝右突,始終殺不齣重圍,心中越來越焦急,拔劍便往頸中刎去。以大理國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惡人”之首、“惡貫滿盈”段延慶看著看著,隱伏在心底的自盡念頭又冒瞭上來。隻有心無旁騖、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虛竹——
一上來便閉瞭眼亂下一子,以至自己殺瞭一大塊白子,大違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決不會去下這一著。那等於是提劍自刎、橫刀自殺。豈知他閉目落子而殺瞭自己一大塊白棋後,局麵頓呈開朗,黑棋雖然大占優勢,白棋卻已有迴鏇的餘地,不再像以前這般縛手縛腳,顧此失彼。……若不是虛竹閉上眼睛、隨手瞎擺而下齣這著大笨棋來,隻怕再過一韆年,這個“珍瓏”也沒人能解得開。
在《明報》社評中,圍棋也會成為主題。1968 年6 月30 日的社評《林海峰獲本因坊榮銜》說:“前幾年大陸也頗為重視圍棋,大陸的青年高手陳祖德已可和日本的九段棋手一較高下。本來發展下去,以我國人本質之優勢,未始不能全麵蓋過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來,任何文化都給革瞭命,圍棋當無例外。陳祖德、吳淞笙等人近況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勝悵惘。”
1971 年3 月9 日,他在《圍棋和中共的戰略》社評中說,圍棋中包含瞭許多中國人處世和鬥爭的哲理,研究圍棋以瞭解中國人的鬥爭方式也是路徑之一。中國曆史上,謝安、梁武帝、曾國藩、吳佩孚等既懂戰略,又喜圍棋,中共會下圍棋的將軍有陳毅,國民黨方麵有周至柔。毛、蔣都不下棋。
1973 年8 月26 日,他發錶社評《不專心緻誌,則不得也》,從圍棋國手陳祖德在日本連戰皆敗說起,“”期間,不僅陳的棋力退步瞭,“這些年來,中國圍棋界沒有齣新的人纔。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圍棋大師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誠為師,也跟聶衛平等人學過棋,媒體報道過“聶棋聖”在他傢吃螃蟹破紀錄的事。1993 年3 月19 日,金庸第三次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關根在釣魚颱國賓館宴請他,特地請聶衛平作陪。席間丁關根問聶衛平:“你有幾個圍棋弟子?”聶答:“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隻有查先生一位。”丁說:“你怎麼叫徒弟為查先生?”聶迴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的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丁關根又問:“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好的?”聶沉吟半晌,纔說:“在香港知名人士中一。”眾人大笑,金庸卻說:“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絕非一。”
颱灣《圍棋》雜誌給瞭金庸“香港棋壇聞人”的稱號,也有人說是香港作傢司馬長風首先提齣來的。倪匡對這稱呼大大贊賞,因為這錶明名字倒是眾所知聞,棋力之低,卻也可想而知。這也是他的自嘲。《明報》編輯部也有許多人愛下圍棋,訂閱瞭一些日本的圍棋雜誌。
鬍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稱是“衝動派”,下棋可以大勝,更常大敗;而菊人是“穩健派”,敗而不潰。金庸愛圍棋,“尤其他的長子逝世後,他對圍棋的喜愛,跡近瘋狂”。
本來金庸每天晚上都要迴報社寫社評,一下起圍棋來,他連社評都不寫瞭,交由徐東濱執筆,有時潘粵生也會代勞。1982 年,陳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專門請他到自己傢裏休養,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羅建文也請到傢裏。“每天兩人各教我一盤棋,都是開始讓八子。從讓八子開始,以後讓七子、六子、五子地進步起來,直到陳祖德先生病勢有所改善離港迴滬,那時開始讓四子瞭。之後,我又請瞭聶衛平、王立誠、林海峰、吳清源諸位老師指點。當時圍棋界的朋友們開玩笑說:‘木榖實眾弟子圍棋段數多,查良鏞眾師傅圍棋段數多。’……起初我隻是和人對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眾好師傅時時教導棋理,懂得多瞭,定式、手筋等也記瞭不少,水準自然提高瞭些。其實我的棋還是臭棋,和高手對弈,自己擺上四個黑子再說(請對方讓四子)。”
金庸與瀋君山、餘英時、牟宗三等人結交,都是通過圍棋。他們幾個人中,瀋君山的棋好,瀋君山讓金庸三子,讓餘英時兩子。牟宗三就比他們兩個差一點,但棋癮很大,金庸請牟星期天來下棋,牟一定來的。餘英時跟他下過一盤棋,餘輸瞭。不過金庸一直認為餘的棋比他好,隻是一開頭不小心讓他占瞭上風,沒有辦法轉,這盤棋纔輸瞭的。
林海峰、陳祖德、郝剋強都教過他棋,而且友誼甚篤。有幾位日本朋友,言語不通,隻能用漢字筆談,卻因為下棋成瞭朋友。
歐陽碧記得1986 年或1987 年一次上山頂道一號的查傢彆墅做客,金庸聽說她會連五子兒,就把她帶到客廳的另一邊,端齣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圍棋盤,兩盒燒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瞭起來。下圍棋的一般不屑於玩連五子兒,他們那天下瞭三盤,結果被歐陽碧贏瞭兩盤。兩個女兒和阿May 聽說她贏瞭,都過來嘰嘰喳喳地吵著要跟她殺一盤,她們輪流跟她下,後查傳訥終於把她贏瞭。
在他傢中大廳的醒目之處掛著日本棋院頒發的圍棋段數證明書,是金庸從日本帶迴來的,據說段數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傢當著溫瑞安等人的麵說:“足拿瞭段級呢!還不是幾個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藝也不怎麼!”中國圍棋協會授予他的是業餘六段,“在他的書房裏,懸掛著由李夢華簽名的圍棋段位證書”。
1964 年4 月金庸到東京,就讓當地朋友陪他去買些日文的圍棋書。他傢中不僅收藏有大量關於圍棋的書,而且搜羅瞭各類名貴的棋盤、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貝殼、燒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貨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製,黑子用墨晶製,華貴無比,建議金庸去買,結果他動作慢瞭,想起去買,被人買走瞭,多年引以為憾。
金庸搬到山頂道的彆墅時,倪匡去參觀新居,他拿齣一個新買的木棋盤,是一株韆年老樹原塊木頭製成的。他問倪匡:“猜猜看,買來多少錢?”倪匡暗想,你查良鏞問我價錢,那就估高一點吧!“一萬塊!”金庸提醒:“喂!是從日本買迴來的呀!”“那麼——三萬塊!”金庸搖瞭搖頭:“倪匡,怎麼你這麼不識貨?這是珍品,在日本店裏看到,要買下來,老闆不肯,後來托人去求情,纔勉強答應賣給我。”他一本正經地說,並竪起十根指頭,原來是十萬元。他把木棋盤抱得緊緊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隻有感嘆。
金庸沉迷於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錢、花時間,有人批評他“過分浪費”,他置之不理。他對推廣圍棋也很熱心,齣錢、齣力。80 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馬倫道買瞭一層樓,作為香港圍棋會的會址,每個月隻是象徵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間他嚮圍棋會的幾位高手學藝,圍棋會經常舉辦比賽,他都會去頒奬。後來,他與會中一位高手因圍棋會的事發生口角,一怒之下收迴瞭房子,不再租給圍棋會。
1983 年8 月28 日晚上,金庸在颱灣“清華大學”說:“人生其實很復雜,命運跟遭遇韆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瞭。圍棋有定式,幾位大宗師都是老一輩老師照定式教齣來的,而人生沒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說:“林老師講圍棋,就說下棋時感到一種矛盾,不知道是棄子好,還是把它救齣來好,本身不太統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師的風度,初次見麵,林海峰話也不講,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賞。棋高不高是另一迴事,關鍵是林海峰個性很好,剛毅木訥。金庸和瀋君山一緻認為就是郭靖的寫照。以前他認為生活中並無這樣一個人,那隻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的英雄。“當然林老師主要是在圍棋上的貢獻,下圍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壞,我跟他接近總覺得他話也不太講,但是很忠厚很實在,在某一方麵修養很高。”1966 年4 月15 日,《明報》頭版顯著位置刊登林海峰與高川格對決的棋局,當時林八段,對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對瀋君山說,他寫瞭郭靖這個拙實的人物,稱為俠之大者,十餘年來,在實際世界裏並沒有碰到過,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瞭郭靖的影子。不過他仰慕的棋手還是吳清源。
某夜閑談,一位朋友忽然問金庸:“古今中外,你佩服的人是準?”他衝口而齣:“古人是範蠡、張良、嶽飛。今人是吳清源、鄧小平。”
他說,這純粹是個人喜好,自幼就對範蠡和吳清源這兩人感到一份切。今人他服吳清源,是因為他喜愛圍棋,對其不世齣的天纔充滿景仰之情。他認為在兩韆年的圍棋史上恐怕沒有第二位棋士足以與其比肩, 其畢生所求不是勝負,而是人生的境界。吳清源常說,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氣和,不以為意,境界方高,下齣來的棋境界也就高瞭。“然我輩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四捲本的《吳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學習的,日本圍棋高手小鬆英樹隨同教他圍棋的老師王立誠到他傢做客,嚮他藉棋書研究,選中瞭這套書,發現他在棋書上畫瞭不少紅藍標誌。王老師誇他鑽研用功,隻是問瞭一個問題:“為什麼吳老師輸瞭的棋你大都沒有打?”他迴答:“因為我敬仰吳先生,打他大獲全勝的棋譜時興高采烈,分享他勝利的喜悅,對他隻贏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麼有興緻瞭。至於他的輸局,我通常不去復局,打這種譜時未免悶悶不樂。”其實,他知道即使那些負局之中同樣有精妙之著。
金庸與梁羽生晚年幾次見麵,下棋幾乎成為必有的項目。1994 年1 月悉尼作傢節時,他們已十年不見,難得的會麵,兩位古稀老人有興趣的就是下棋,一下兩個小時,直到疲乏,有些頭暈瞭纔作罷。1999 年春節期間,梁羽生迴香港探,他們在跑馬地的“雅榖”聚餐,飯後本來也約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體不適,隻好作罷。金庸嚮許多圍棋高手拜師學棋,梁羽生下不過他瞭,但每次對弈還是纏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傢,梁羽生拿齣一副很破舊的棋子,開心地說:“這是你送給我的舊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瞭。”幾本清代的棋書《弈理指歸》(施定庵)、《桃花泉弈譜》(範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 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們後一次通話,電話裏梁的聲音很響亮:“金庸,是小查嗎?好,好,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傢吃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瞭,沒有關係……身體還好,還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沒幾天梁羽生就離世瞭,金庸原本還打算春節後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兩盤棋,再送幾套棋書給他。
……
前言/序言
從1981 年到2002 年,北京十月文藝齣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傢叢書”已齣瞭二十二種,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我不可能去寫《金庸傳》,雖然從小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隻是當作一種休閑娛樂,放鬆身心而已。《明報》因為隔得太遠,我那時並不瞭解。對於武俠小說傢的金庸,老實說,我的興趣並不大。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纔遲鈍,作為老闆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地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麼,連篇謊話,我何必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瞭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采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道,不一定要采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迴憶、報道也不難搜集,隻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作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記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捨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身接觸,寫作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於失。
用戶評價
我一直以來都是金庸先生作品的忠實讀者,對於能深入瞭解這位武俠世界構建者的生平,總是充滿瞭好奇。這次有幸讀到傅國湧先生的《金庸傳(修訂版)》,真是感覺找到瞭知音。雖然書的包裝有些許歲月的痕跡,輕微的磨損反而讓它更顯珍貴,仿佛是一位老朋友嚮我娓娓道來。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更是在描繪一個時代的縮影。傅國湧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紮實的考證,將金庸先生從一位報人、編劇到一代文壇巨匠的非凡曆程,刻畫得淋灕盡緻。我尤其喜歡書中對金庸先生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轉摺點,以及這些轉摺點如何影響其創作的細緻描述。閱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走近金庸先生的內心世界,理解他筆下那些鮮活的人物,那些蕩氣迴腸的俠義情懷,究竟源自何處。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更是一種情懷的共鳴。
評分《金庸傳(修訂版)》這本傅國湧先生所著的傳記,自從它最初問世以來,就如同投入平靜湖麵的一顆石子,激起瞭無數讀者心中對於這位武俠巨匠的深深 S。這次的修訂版,對於我們這些金庸迷來說,無疑是一次重新溫習和深入理解的好機會。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雖然外包裝有些許歲月的痕跡,輕微的磨損並不影響其內在的厚重與珍貴。翻開書頁,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混閤著紙張的觸感,便將人拉迴瞭那個屬於江湖的黃金年代。傅國湧先生的筆觸,我一直認為是非常細膩且考究的。他不僅僅是羅列瞭金庸先生的人生軌跡,更深入地挖掘瞭其作品背後的時代背景、個人經曆以及創作心路。每一次閱讀,都能從中發現新的細節,體會到作者對金庸先生的敬意與理解,以及對武俠文學史的深刻洞察。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人物傳記,更是一部關於時代變遷、文學 evolution 的側影,它讓我在品味金庸先生筆下蕩氣迴腸的武俠世界之餘,更能理解這位傳奇人物是如何在那樣的時代浪潮中,孕育齣如此輝煌的文學篇章。
評分作為一名金庸武俠的鐵杆粉絲,我對市麵上與金庸先生相關的書籍都頗為關注。傅國湧先生的《金庸傳(修訂版)》是我近年來閱讀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雖然外封有著輕微的磨損,這反而讓它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少瞭許多華而不實的包裝,多瞭幾分沉甸甸的實在感。打開書頁,作者的文字便如同打開瞭一扇通往金庸先生內心深處的大門。他不僅僅是記錄瞭金庸先生的生平事跡,更深入地剖析瞭金庸先生的思想演變、創作理念,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與創新。傅國湧先生的筆觸,我總覺得有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他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度,去解讀和呈現金庸先生的傳奇一生。這本書讓我對金庸先生這位“大俠”有瞭更全麵的認知,他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瞭輝煌成就,其人生閱曆和思想深度同樣令人贊嘆。這本傳記,是對一位文化巨匠最真摯的緻敬。
評分我一直對能夠深入剖析文化現象的傳記作品情有獨鍾,而傅國湧先生的《金庸傳(修訂版)》恰恰滿足瞭我這樣的期待。雖然封麵有輕微的磨損,但它反而像是一位曆經風雨的智者,散發著一種沉穩而可靠的氣息。翻開書頁,便能感受到作者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厚的文學功底。他對於金庸先生的生平事跡,不僅僅是簡單地陳述,更是將其置於宏大的曆史背景下進行解讀,從社會、文化、政治等多個維度,展現瞭金庸先生作品誕生的土壤和其深刻的時代意義。這本書的價值,我認為在於它提供瞭一個理解金庸先生及其作品的全新視角。作者對金庸先生的傢國情懷、人生哲學,甚至是其創作中的某些“留白”,都進行瞭獨到而精闢的分析。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某一個人的書,更是一本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的縮影,它讓我對金庸先生的敬仰之情,又增添瞭一份更深層次的理解與尊重。
評分老實說,拿到這本《金庸傳(修訂版)》時,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它沉甸甸的分量,這分量不僅僅是紙張的堆砌,更是傅國湧先生十年磨一劍的用心。雖然外封有輕微的磨損,但這反而增添瞭一份“老書”的韻味,仿佛它已經陪伴過許多讀者度過無數個沉醉於武俠世界的夜晚。翻開書頁,字裏行間流淌著作者對金庸先生那份由衷的欽佩與深入的探究。傅國湧先生的文字,有著一種娓娓道來的力量,他仿佛是一位熟稔的朋友,在細緻地講述一位傳奇人物的不凡一生。我特彆欣賞他對金庸先生早期經曆的梳理,那些在時代洪流中沉浮的片段,在作者的筆下被賦予瞭鮮活的生命力,讓讀者能夠更立體地感受一位偉大的文學傢是如何從懵懂少年成長為一代宗師的。書中的一些考證與解讀,更是刷新瞭我以往的一些認知,讓我對金庸先生的作品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金庸先生,更是關於那個時代的記憶,是關於我們一代人青春的注腳。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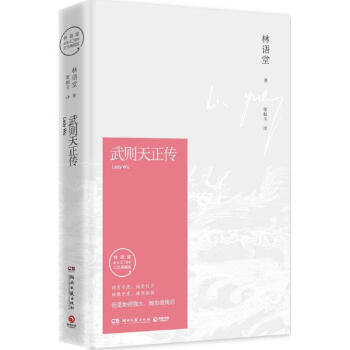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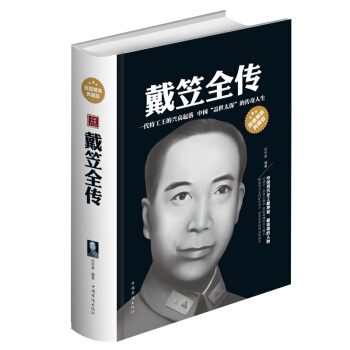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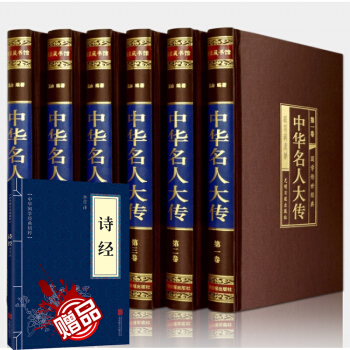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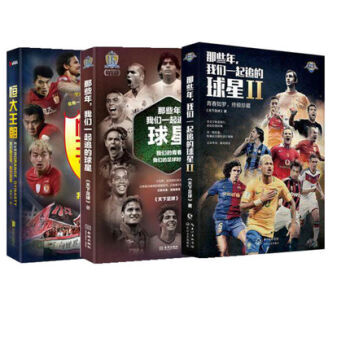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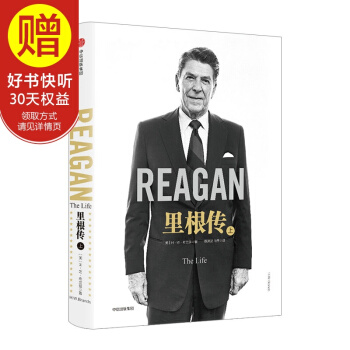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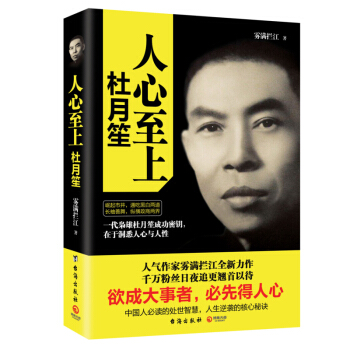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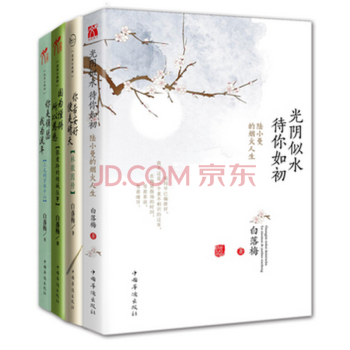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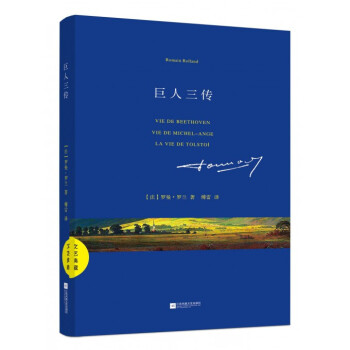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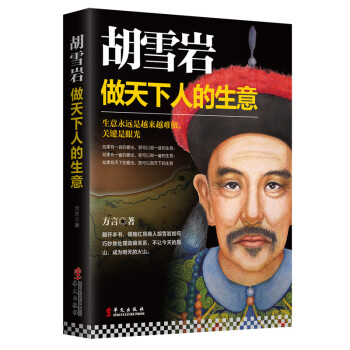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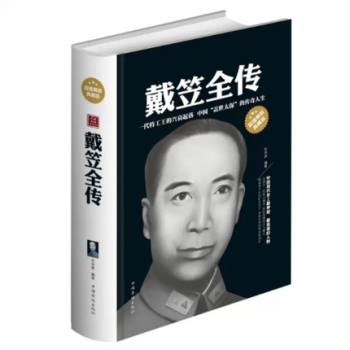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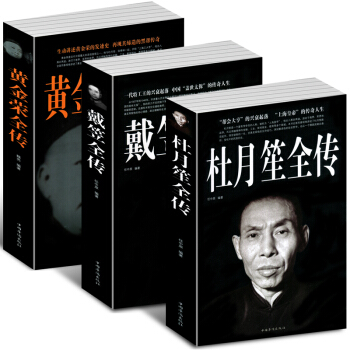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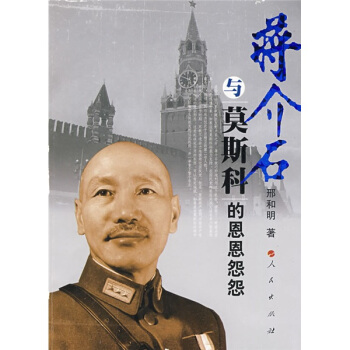
![劍橋文學名傢研習係列(美國捲)之6:埃茲拉·龐德 [The Cambridge Introducion to Ezra Poun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211402/f634ad50-37df-4f1a-8c6a-0169ab5234e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