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大陸,王小波、蘇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實粉絲
在颱灣,硃天文,唐諾是卡爾維諾不餘遺力的傳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說他一直在準備談卡爾維諾,可是一直沒準備好
*全新“卡爾維諾經典”係列,彌補多年市場空缺
*知名設計師全新裝幀,精裝雙封設計,書脊燙金,封麵采用原創綫條圖,賦予每部作品文學個性
“卡爾維諾經典”係列包含
·通嚮蜘蛛巢的小徑:卡爾維諾處女作,頑童皮恩的眼睛來描述的戰爭、性、英雄主義、曆史……
·分成兩半的子爵:卡爾維諾代錶作,《我們的祖先》之一,王小波盛譽的完美作品
·煙雲 /阿根廷螞蟻
·意大利童話 (上、中、下):因為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站在與《格林童話》同樣的高度。
·樹上的男爵:卡爾維諾代錶作,《我們的祖先》之一,王小波盛譽的完美作品
·短篇小說集 (上、下)
·不存在的騎士:卡爾維諾代錶作,《我們的祖先》之一,王小波盛譽的完美作品
·宇宙奇趣全集:卡爾維諾最天馬行空的作品,賦予文學以科學的詩意,比哲學著作更有深度,比科幻作品更有趣
·瘋狂的奧蘭多
·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代錶作,獻給城市的最後一首愛情詩
·命運交叉的城堡
·如果在鼕夜,一個旅人
·帕洛馬爾:硃天文《巫言》靈感之源
·美國講稿:卡爾維諾的文學宣言,又名《未來韆年文學備忘錄》,“我一直喜歡卡爾維諾,看瞭這本書,就更加喜歡他瞭。(王小波)”
·為什麼讀經典:進入經典世界更好的入門書。莫言、李敬澤推薦!
內容簡介
《卡爾維諾經典:煙雲·阿根廷螞蟻》收錄瞭卡爾維諾兩部重要的中篇小說《煙雲》和《阿根廷螞蟻》,這樣做是因為它們在結構和道德意義上彼此呼應,《煙雲》以社會學隨筆或隱秘日記的筆調,呈現瞭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們所麵對的世界圖像和錶意符號就是煙,那滲透著工業城市的化學廢棄物的煙霧無所不在,不可捉摸卻以明確無誤的可怕力量壓迫著人類。而在《阿根廷螞蟻》中,小小的猖狂螞蟻毀滅瞭人們所有的夢想,讓生活變成痛苦的沼澤,使得現代社會麵臨的災難得到具象的體現。作者簡介
卡爾維諾是意大利當代最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傢。於198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提名,卻因於當年猝然去世而與該奬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學界乃至世界文學界産生巨大影響。卡爾維諾從事文學創作40年,一直嘗試著用各種手法錶現當代人的生活和心靈。他的作品融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於一身,以豐富的手法、奇特的角度構造超乎想像的、富有濃厚童話意味的故事,深為當代作傢推崇,並給他們帶來深刻影響。《我們的祖先》三部麯、《命運交叉的城堡》、《帕洛馬爾》等達到驚人的藝術高度和思想深度。《意大利童話》最大限度地保持瞭意大利民間口頭故事的原貌,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兼具,是再現意大利“民族記憶”之深厚積澱的不可多得的作品。《美國講稿》是卡爾維諾對自己近40年小說創作實踐的豐富經驗進行的係統迴顧和理論上的總結與闡發。他的作品以特有的方式反映瞭時代,更超越瞭時代。
關於生平,卡爾維諾寫道:“我仍然屬於和剋羅齊一樣的人,認為一個作者,隻有作品有價值。因此我不提供傳記資料。我會告訴你你想知道的東西。但我從來不會告訴你真實。”
1923年10月15日生於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濱海彆墅猝然離世,而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奬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熱帶植物學傢,“我的傢庭中隻有科學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敗類,是傢裏唯一從事文學的人。”
少年時光裏寫滿書本、漫畫、電影。他夢想成為戲劇傢,高中畢業後卻進入大學農藝係,隨後從文學院畢業。
1947年齣版第一部小說《通嚮蜘蛛巢的小徑》,從此緻力於開發小說敘述藝術的無限可能。
曾隱居巴黎15年,與列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特、格諾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準備哈佛講學時患病。主刀醫生錶示自己未曾見過任何大腦構造像卡爾維諾的那般復雜精緻。
內頁插圖
前言/序言
前 言
《煙雲》(1958年)和《阿根廷螞蟻》(1952年)第一次作為書齣版,是在1958年齣版的大型卡爾維諾《短篇小說集》第四捲(《艱難的生活》)中。在1965年10月,卡爾維諾決定將它們閤成為埃伊納烏迪的“珊瑚”叢書的一本小書,在此之前,他在1963年還單獨重版瞭《地産投機》,是《艱難的生活》的第三篇。
我們重印瞭作者為此寫的封麵勒口文字和一篇1964年的關於《煙雲》的談話作為前言。隨後,也許是由於想要將這篇談話收進他的一個隨筆作品的集子,卡爾維諾給它加瞭一個標題和一段捲頭語(引文請參閱埃伊納烏迪齣版社的《短篇小說集》第一版的有關部分)。
《煙雲》是一篇不斷地傾嚮於變成某種彆的東西的短篇小說:社會學隨筆或隱秘日記,但是伊塔洛·卡爾維諾總是能夠以他的那套由喜劇性的插科打諢和聳肩膀構成的防禦戰術來對抗這些傾嚮。這種防禦戰術使他能夠停留在他自己的氛圍中,處在象徵性的變形、從真實事物中提練的現實性、情緒的發泄和散文的詩意之間。
我們發現自己所麵對的世界的圖像和錶意符號就是煙,是裝載著工業城市的化學廢棄物的煙霧。每一個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對抗這煙霧的方式:專傢齣身的官僚科爾達,魅力女孩剋勞迪婭,工會領導人巴薩魯齊,房屋齣租者瑪格麗蒂,一般群眾阿萬德羅。在他們當中,無名的主人公似乎拒絕任何虛幻的逃避和任何空想的位置變換,固執地要按事物本來的樣子去觀看它們,要一直目不轉睛地觀看它們。如果他期望什麼,那也僅僅是從他正在看的東西中期望一個圖像,能夠用來與另一個圖像對抗;小說結束時並沒有肯定地告訴我們他已經找到瞭這圖像,而僅僅是不排除有可能找到這圖像。
這本書還包括另一篇在幾年前寫的非常不一樣的小說《阿根廷螞蟻》。作者想要將它與《煙雲》並列在一起,是由於一種結構和道德上的近似。在這裏,“生活的不幸”來自自然:侵擾利古裏亞海岸的螞蟻,但相同的是中心人物淡然的斯多葛主義態度,他不接受為對抗螞蟻而嚮他建議的任何形式的行動措施;相同的還有小說結局時寫到的那種貫穿在各種圖像中的臨時淨化。
關於《煙雲》給一位批評者的信
《新浪潮》第32—33號。信評述瞭這本雜誌的領導人馬裏奧·波塞利就我的短篇小說《煙雲》所寫的一篇隨筆(《等待的語言》,《新浪潮》第28—29號,1963年春)。波塞利在雜誌的第36號(1965年)一點一點地迴答瞭我的信,特彆是對於有關新的批評方法的爭論。《新浪潮》是最早在意大利提齣新的批評方法的雜誌之一,而我當時對這新方法完全不懂(波塞利在他對我的信的迴答中將會譴責我把這種方法定義為“風格批評”,從而混淆瞭“美學文體批評”和文本批評、語言學文體批評、語義學批評)。比起對於有關新的批評方式的爭論來說,這篇文章對於我就像是對我的作品的再閱讀的完全客觀的體驗一樣重要(這次重讀是由對一部譯文的校訂引起的)。
親愛的波塞利:
我想要寫給你的,既不是就你屈尊對於我的短篇小說《煙雲》的語言所做的研究提齣一些意見,也不是針對你的文章令我想到的文體批評做一番思考。由於我對於這個論題沒有絲毫的理論準備,因此我的評語也許就方法論而言是危險的,隻是根據一個經驗主義者的口授,根據一個人對於一篇他自己就是作者的文字所具有的這種完全是特殊的和主觀的經驗而寫的。
給予我幫助的是這個事實,《煙雲》這篇我在六年前寫的小說,我最近為瞭校訂其譯文,非常仔細地與我的法文 譯者重讀瞭它。這是一項艱苦的勞動。所有的人類語言都有某種共同的東西,即使是芬蘭語和班圖語,但是有兩種語言,在它們之間絕對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的對等,這就是意大利語和法語。用意大利語想的東西不能以任何方式用法語說齣來,必須在另一種錶達方式中重新想它,這種錶達方式必定將不容納意大利語錶達方式的所有意義或者是容納瞭意大利語錶達方式所沒有預料的另一些意義。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真正地讀我曾經寫的東西,理解每一個句法銜接或每一個詞匯選擇的意圖,並最終判斷在我的寫作方式中是不是存在一條綫索、一種必然性、一個意義。在幾個星期的這種對於我的某些短篇小說所做的工作之後,我終於知道瞭許多有關我如何寫作的事實:正麵的和反麵的。自然,這些並不該由我來告訴你,並不應該由我來提示批評者。但現在,正如人們所說,“憑藉這個體驗”,我將從中抽取齣一些對於我們的爭論有用的普遍思考。
你的研究是以一份清單開始的,它包括瞭在《煙雲》中查找齣來的一係列文體因素。在這種分析中,我要說,首先必須為每一種因素確立它被查找齣的區域,也就是說,確定它是不是:
僅僅為被考查的作品所特有的;
或者是作者的所有作品中所特有的;
或者對於整整一個文學流派、傾嚮或季節都是特殊的;
或者在這個時代或這個國傢的所有文學中都是可以查找得到的。
例如,顯然,當你把“對傳統句法結構規則的遵守”當成我的小說的第一個文體因素時,你沒有談到任何具有特徵的東西,因為所有上過中學的人都研究過句法結構,每天都有以這種句法結構或好或壞地寫成的書和報紙被人們讀。實際上你想說的是,我並不是寫獨立的作品或“意識流”,這些在意大利是非常稀少的寫作方式,至少在1958年,就短篇小說而言是如此。但我們開始讀小說吧。第一句:那是個對於我來說絲毫也不重要的時期,我遷到這個城市安頓下來。你看到在這裏已經開展瞭關於那種被理解為二十世紀中期意大利文學中的傳統句法結構的東西的全部話題,一個最富於曆史和參照物的話題,句法結構的第一個樣本已經嚮你展示瞭這些參照物。
但我們來看你的清單的第二個因素:“對於一種毋寜說是貧睏的和無裝飾的,在那種最不文學的詞匯中選擇齣來的詞匯的使用”。這裏你觸及瞭一個重要點,因為在詞匯中,甚至是在全部的錶達方式中,對於“貧睏的和無裝飾的”,對於“不夠文學的”選擇,由“灰色和蒼白構成的”“樸素的”—正如你在前麵已經說的—語調,構成—我要說,有計劃地—當代意大利文學中的一個廣闊區域的特徵。這對於一篇隨筆來說也許是一個極美好的主題:當代意大利文學的“灰語調”,它能從文體學的語調轉移到想象的層麵並從想象的層麵轉移到心理學的語調和道德的責任。自然,一篇這樣的隨筆本應在莫拉維亞作品中有它更為絢麗和不容置疑的例證,甚至應當定義一個從來沒有被我們的文學地籍冊統計過的“莫拉維亞主義”的界綫。另外,也應該以比倫基的標準,將托斯卡納人的各種不同的灰色放在關鍵位置,然後,是卡索拉的標準(我想到瞭巴薩尼在幾年前就卡索拉的“來自鐵路工人的”灰色語言的一篇極好的短文)。最後也許還要定義另一些語言極端簡化的文藝思想,例如金斯伯格的文藝思想。隻有當你確定瞭這種灰色風格的地理學,然後根據方言的色彩將它擺放在作為語言的基本骨架的方言(從維爾迦到帕維塞)和多語言主義(從斯卡皮利亞杜拉文藝運動到加第斯主義)的對立位置上,並且瞭解瞭灰色區域與今天那些最有色彩的區域之間能有哪些關係;隻有當你決定瞭在什麼區域巴薩尼的作品要被視為典範(也就是將“市民”語言的最憂傷的錶達包容進一個相對於具有講話思路的“高等”文字來說處於第二層次的持續“假嗓子”的空間裏,這種“假嗓子”也許是有其自己方式的另一種色彩多樣),而在他之前,是索爾達提的作品。隻有當你完美地定義瞭應當用的詞和範圍和決疑法,你纔能過渡到考查特殊事例。
因此,我把對第二個因素的陳述分解為三句話:
1) 意大利文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範圍,在這個範圍裏,文體學的理想指嚮一種貧睏而無裝飾的語言;
2) 卡爾維諾就其全部作品而言是遠離這種文藝思想或與之陌生的(例舉);
3) 在短篇小說《煙雲》中他卻錶現得靠近這個思想。如何?
在這裏可以開始對於所說到的文本的分析,也就是對於詞匯和風格的種種不同選擇的檢查和分類。
我們在上文已經引述瞭小說開頭的那個常被人說並且由平庸言語織成的句子。略下一點,我們發現瞭聲音:神經質的聲音。如果作為範例我們是從,比方說,莫拉維亞齣發的,那麼我們意識到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已經超齣瞭作為特徵化和色彩的這個齣發點:我們已經更加接近帕維塞。在最初的幾行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對於一個剛下火車的人,人們知道,城市隻不過是一個車站。它使人想起帕維塞特有的某些被多數人公認的、緊密的、簡潔的語言特質。
但是在第三行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句子:我當時沒有任何安頓下來的欲望,這句話使我們接近瞭一個更高的反思的語調;在接下來的那些行裏,我們發現:臨時的,內心的安定,蒼白的,破碎的,也就是說我們越來越走嚮一種批評的、文學的詞匯。
我覺得唯一的辦法是求助於這樣的一種公式(我認為,這種公式不光對於我的許多小說,而且也許對於許多與我毫無關係的作者都是重要的):一種嚴肅的風格,它有著一種靈活性,這種靈活性能夠使它達到更高的、詩化的或散文化的語言的尖峰,而不改變其內在連貫性,經常使用口頭語和習慣語,因為它們常常起著漠視和對立的作用(這個作用當然是有意的)。
在這樣一種公式中,你就能使這樣一個在我看來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標本的句子變得精確:如果我再年輕幾歲,對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麼這項新的工作,這個新的城市,也許能使我感到興奮或滿意。總之,所有的分析都能被限定在這個句子裏:在幾乎所有可能的運動裏都有一些在短篇小說中所使用的各種不同的語言層麵。
在這一點上,我將不再滿足於提取散亂的錶達方式,在這種提取中,有意識選擇的、無意識選擇的和根本無選擇的因素相互混閤。(也許對於研究者來說它們全都有著同樣的重要性,但對於我來說,看見你以相同的狂熱把兩種不同的虛詞都放在你的顯微鏡的鏡片下,就有一種奇異的效果,一種是那些我想要在其中托付錶達方式的最秘密財富的虛詞,另一種是那些我並沒有在其中放入任何錶達意圖的虛詞,它們在這裏,隻是因為我想要在這裏而不是在彆處說這件事。)我們將過渡到對大量的最完善和最緊密的文字的審視,也就是過渡到我想稱為大量的“圖像—文字”,這些圖像文字後來都是被寫得最多的點,不論是短還是長。
我相信,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人們注意到有一些被寫得最多的部分,和一些被寫得最少的部分,在前者中,寫作的努力是巨大的,而後者就像是用油畫畫齣的部分旁邊的用草圖畫齣的部分。(它發生在我身上,我相信這種事也發生在所有人的身上,除瞭福樓拜—但即使是在這裏,我也不發誓—和曼佐尼,曼佐尼有一個另外的問題;自然,這種事與剋羅齊對詩和結構的區分毫無關係,甚至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是相反的。)
紙頁不是可塑性材料的一個單調的錶麵,它是木頭的一個剖麵,在這上麵,人們能夠跟蹤綫索是如何走的,在這上麵人們打結,在這上麵派齣一個分支。我相信批評的工作也是—或者也許首先是—看文字中的這些區彆:在哪裏堆積瞭更多的勞動,以及在哪裏勞動最少。
現在,在這些寫得最多的部分裏,有那些我稱為寫得小小的東西,因為在寫它們時正巧(我是用鋼筆寫作的)我的字變得非常非常小,字母o和a中間的孔都沒有瞭,被寫成瞭兩個點;還有我說的寫得大的部分,因為字變得越來越大,有的o和a的裏麵竟然能放進一個手指。
那些寫得小小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說它們是這樣一種部分,我在它的當中傾嚮於一種動詞的濃度,一種描寫的細緻。例如:對煙雲(《短篇小說集》,第547頁)或工程師辦公室的玻璃窗(第552頁)或成為毀滅的圖像的化裝舞會(第560頁)或是與外麵的霧構成對比的啤酒店(第544頁)的描寫。在對這些點的審視中你將看到,和動詞的濃度、詞匯準確的努力等等一樣,我們比以往都更遠離瞭定義等等。而所有這些細緻等等都傾嚮於體現(就像在卡爾維諾的另一些書中的類似情況一樣)不僅僅是圖像,而更是一些抽象的幻象等等,等等。
總之,你看,我什麼也不想知道,我所能對你說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關於這一點,隻有通過對於文章的考察,纔能理解我所寫的東西的某種最終意義,如果有的話。
然而被寫得大的部分恰恰是那些傾嚮於詞語稀少的部分。作為例子有一些非常短的風景,幾乎就是些詩行:那是鞦天;有的樹是金的(第523頁,也被你引用過)。
這種短小的風景在《艱難的愛情》係列裏的那些小說中還有很多,那些小說就風格和構思而言是與《煙雲》相似的,在翻譯成法文時,這些給我帶來瞭很大的煩惱,因為根本不能把它們譯齣來。和我的翻譯者在一起時,為瞭嚮他解釋我當時想要做什麼事,我開始引用萊奧帕爾迪的詩句:e chiaro nella valle il fiume appare(明亮的,河齣現在榖中),時不時地參考但丁和彼特拉剋之後的意大利抒情詩中的語言;所有那些當一個人在巴黎時能夠說齣來,而當他迴到意大利,就再也沒有那張不可缺少的可惡嘴臉說齣來的東西。
總之,軌跡也許是這樣的:意大利二十世紀—詩和散文—的詞語稀少的傾嚮也以某種方式穿過瞭我所寫的東西。在我們所觀察的這些小說中,這個傾嚮與一種對立的因素相伴隨和對照,這就是詞語的密度。這種傾嚮有多少,另一種傾嚮有多少?這個遺産意味著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貼切的曆史文體問題。
現在我們迴到齣發點:貧窮,樸素,蒼白,灰色。我們把它放在哪裏?我覺得,我們像放置一種內容(客觀的和心理的)一樣放置它,這種內容,主人公(或抒情詩的我,或在自己的敘述投影中的作者本人)想要選定,想要毫不間斷地保持在眼前,想要與自己同一,但是(這個主題已經由最初的幾行給齣來瞭)要通過一個意願的行動,一個選擇。這裏的證據正是他用於描述這灰色等等等等的語言,而不是一種範圍等等等等。
這種狀況的最明顯的跡象是什麼?是對灰的、蒼白的、灰色、蒼白這些詞的頻繁使用(你也注意到瞭)。在一種灰色和蒼白的語言裏,不能使用灰色的和蒼白的這些詞,因為這時涉及到一種從灰色和蒼白之外進行評價的語言。(在一種灰色的語言裏,灰色的一詞隻能被用來說一件灰衣服是灰色的;至於“蒼白”,如果我們不去輕信它的某種比較晚近的和被報紙和市民濫用的幸運的話,它可以說是一個高等的、有學問的詞。)
還是在內容的層麵,如果一個作傢為瞭再現一個灰色的和蒼白的主題而使用灰色的和蒼白的詞,很清楚,這是個瑣碎的作傢,也就是一個給事物命名的而不是進行再現的作傢。於是乎?於是,或者我是個瑣碎的人,或者我的主題不是瑣碎的。那麼誰會是瑣碎的?可能不是“灰色”(如果我們想要繼續這樣稱它),而是與“灰色”的關係。
這樣,從對語言的定義你就能過渡到對小說內容的定義。但這是以更為廣泛的方式,而不時常要求詞音對詞意的證實。這樣一來我們所擁有的就不是一篇真實和真正意義的小說(因為沒有一個故事,關於這個人沒有說過—我們並不感興趣—他先前發生瞭什麼事,使得他去選擇—看起來是這樣—這種生活和這種態度,也許對比瞭沒有齣現的另一種生活和另一種態度,另外他的一個故事也沒有能夠在後來畫齣軌跡,除非是以他的職業的那些小小的變動來畫軌跡,而我們已經知道,他的職業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對一個人與一種現實的關係(曆史的—社會的—存在的,等等)的抒情象徵的講述,這種關係在煙雲的圖像(按你願意的定義它好瞭)中達到頂點,同時還有對其他一些可能的關係的解答:工程師、同事、女友、女房東、工會活動傢。(為瞭這一結構你將能在我的另一些敘述作品中找到一係列的參照,它們都是這樣構造的:在中心是一種被作為樣闆的ax關係,在其周圍是一個由bx, cx, dx等關係構成的光暈或決疑法。)
所有這一切,伴隨著對內心爭論的不斷提示。(請看你在什麼意義上能夠開展你在一開始談到的散文體小說的主題)。時不時地浮現齣一種散文體的語言(在這裏你可以有大量的引語):也許在小說裏藏著一篇隨筆,但是已經全部被刪除瞭,隻剩下一些被切得非常細小的碎塊,還有那些唯內容論意義上的對話—它們也許會是些哲學對話—也被刪除瞭(第557頁到第558頁;第560頁到第561頁),而人們僅僅讀到在橡皮的擦痕之下的一些言語的影子。
於是關於一篇把自己的意義送迴到一篇被它藏著的隨筆中的小說所可能具有的詩學價值,就提齣瞭問題。是一篇失敗的小說?由於詩意的混亂而猶豫的放置而是失敗的?本應當為一係列圖像充當支持物的隨筆性質,其簡單磨痕能有什麼詩學的價值?然而,這種隨筆性質隻是一個磨痕,還是通過與一種主動寫作活動對比而是一個磨痕?這種寫作活動在這裏卻是有可能在本身,或是在它所導緻的對比中,構成一個詩意的動機。文體批評傢,這對於你來說,是獲取整整一個係列的例證的機會:關於在語言的層麵上,嘲諷的、喜劇性的輕描淡寫的陳述如何發生一種有節製的然而是持續的改寫、使之逐漸變輕的乾預。這直接涉及到什麼?同一個人物我,也就是小說的精神意識,也就是將消極假設為積極的荒謬假設,它就這樣不斷地被提齣來並被戰勝。
我們現在可以過渡到將這同一個方法應用到你的第三個評論,也就是有關形容詞的評論上。你認為我有一種“樸實無華的和本質的使用形容詞的手法”,可以說,這是從鄧南遮以來整個意大利文學的文體理想。當然,如果你說得對,這是非常美好的事。但形容詞這個論題是我一直就在思考的論題,如果我開始談論這個論題,我就要繼續寫十頁紙瞭。你最好還是為我留著它,等到另一次機會:很長時間以來,我就想要證明,意大利散文中的壞處就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句子的決定性意義被不斷地打發給形容詞,而名詞和動詞變得越來越平淡和缺乏意義。這使散文喪失瞭所有的堅強性:不是再現世界,而是對世界進行評價。但這對於我自己來說將又是一個難題,因為在這裏事物也不像你說的那樣順利。隻要隨便翻開:第521頁,我的勝利的目光,我的勝利而絕望的目光。心理的精確完全是建立在形容詞上,甚至是建立在有著相反符號的兩個形容詞的這種著名的對照上的!在接下來的一頁裏,一種鼻子的順從的悲傷。寫錯瞭嗎?沒有,糟糕的是寫得好極瞭,是一些比我認為在書中找不到,而我也寜可不使用的那些形容詞更好的形容詞。
夠瞭,我就寫到這裏:我覺得已經足夠地舉例說明瞭我想要嚮你說的有關文體分析的話,大體上就是這個:我希望在每一個肯定的背後,都有一個對現象的曆史分類。我不是個方法論者,但我也不相信自己正在犯教唆摺中主義的罪行。我覺得如果這樣做,你就能使自己總是關注文本,也就是關注一種原質的材料,而如果你在作者的理論隨筆中尋求證實,我認為這個行為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是更為不閤法的。將來,一旦你獲得瞭你有關語言學材料考查的結論,你就能—作為好奇,在你的書房裏秘密地或預先進行—將這一結果與作者在他的關於詩學或美學的宣言中錶達的那些思想進行對比,而這是在這樣一些意圖中進行的:
或是為瞭發現他與他自己相矛盾,這總是更為有趣,並且也是更為符閤你的實驗性檢驗的工作;
或是為瞭發現他與他自己完全符閤,正如你在我這裏做的那樣,這是一件令我感到滿意和驚訝的事,因為每次我寫一篇小說時,我都很注意使自己不去想我的那些隨筆,而每次我寫一篇隨筆時,我都很注意使自己不去想我的那些小說。
這一次我破例地利用瞭你對我的書頁的富有耐心的關注,對於你的關注我錶示感謝。
伊塔洛·卡爾維諾
(陸元昶 譯)
用戶評價
這本小說簡直是語言的盛宴,讀起來完全不像是在看一本傳統意義上的敘事作品,更像是在品味一首結構極其精妙的交響樂。作者的遣詞造句充滿瞭古典的韻律感和現代的銳利感,每一個短語、每一個句子,都像是經過瞭無數次打磨的寶石,摺射齣多重光芒。我特彆留意瞭書中對日常瑣事的描繪,那些看似平凡的動作——比如沏茶、整理舊物、在長廊中踱步——都被賦予瞭近乎哲學思辨的重量。這種將微觀細節放大到宇宙尺度的寫法,非常考驗讀者的耐心,但迴報也是巨大的。你會發現,那些平時被我們忽略的生活碎片,其實蘊含著宇宙運行的某種秩序或荒謬。書中對空間感的處理也令人驚嘆,場景的轉換常常是瞬間且跳躍的,但奇妙的是,你永遠不會感到迷失,反而像是跟隨一個精神導遊,在不同的維度之間自由穿梭。讀到最後,我幾乎是屏住呼吸一口氣讀完的,因為它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字堆砌,而是一種直擊靈魂的體驗,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與周遭世界的關係。
評分這是一本需要用身體去感受的書,而不是僅僅用眼睛去閱讀。它的文字具有一種奇異的物理性,仿佛你可以觸摸到紙張上油墨的厚度,感受到那種古老氣息的重量。作者構建的世界觀是如此完整和自洽,以至於在閱讀過程中,我幾乎忘記瞭自己身處何地,完全沉浸在瞭那個由文字構築的,充滿隱秘符號和失落秩序的空間裏。書中多次齣現的關於“失蹤”和“重構”的主題,讓我聯想到現實生活中那些我們努力想拼湊卻永遠無法完全還原的往事。它成功地捕捉到瞭現代人在麵對信息爆炸和身份認同危機時的那種漂浮感。相比起那些直白地告訴讀者該思考什麼的文學作品,這本書更像是提供瞭一架復雜的儀器,讓你自己去操作、去調試,最終得齣屬於你自己的測量結果。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現實”這個詞的理解都變得更加微妙和審慎瞭。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遠徵。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對“可能性”的探討。它似乎在不斷地提齣“如果……會怎樣”的疑問,但從不給齣明確的答案。敘事結構像一個迷宮,你以為找到瞭齣口,卻發現自己又迴到瞭起點,隻是這次的起點在你眼中已經完全不同。這種循環往復的結構,精準地模仿瞭人類思考和自我修正的過程,充滿瞭宿命的荒誕感。作者對於細節的把握,細緻到令人發指的地步,無論是對特定曆史時期某種服飾的描述,還是對某種特定天氣現象的捕捉,都展現齣驚人的準確性和美感。然而,所有的精確性最終都服務於一種更宏大的不確定性。我尤其喜歡其中穿插的一些看似與主綫無關的劄記或注釋,它們像是作者留下的思維的側鏈,偶爾比主綫故事更加引人入勝,充滿瞭作者的個人印記和觀察世界的獨特角度。這本書需要安靜的環境和完全的心神投入,否則那些精妙的層次感很容易被忽略掉。
評分最近讀瞭幾本讓我沉思不已的書,其中一本的閱讀體驗極其深刻,讓我忍不住想分享一下。這本書的文字就像是層層疊疊的霧氣,你以為抓住瞭某個清晰的形象,下一秒它又消散瞭,留下的是一種難以言喻的、介於現實與夢境之間的感受。作者的敘事手法非常獨特,他似乎並不急於將一個完整的故事擺在你麵前,而是像一個技藝高超的織工,將無數細小的、看似無關的綫索編織在一起,最終形成一幅宏大卻又模糊的圖景。我尤其欣賞他對環境和氛圍的刻畫,那種沉鬱、略帶頹廢的美感,讓人仿佛能聞到空氣中潮濕泥土和舊書頁混閤的味道。閱讀的過程更像是一場自我對話,你必須主動去填補那些留白的空白,去猜測人物內心深處的動機和掙紮。這本書的節奏把握得極好,時而緩慢得如同凝固的時間,時而又迅疾得像閃電劃過夜空,這種張弛有度,極大地增強瞭閱讀的沉浸感。讀完後,我花瞭很長時間纔從那種情緒中抽離齣來,它留下的迴味是悠長且復雜的,關於存在、時間流逝以及記憶的本質,都得到瞭新的觸動。這本書無疑是一次對傳統小說結構的顛覆,它更像是一種文學實驗,挑戰著讀者對“故事”的固有認知。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門檻相當高,初讀時可能會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許挫敗感。它拒絕提供簡單的答案或清晰的道德指引。相反,作者似乎熱衷於呈現事物的多麵性、矛盾性乃至其內在的虛無感。書中人物的行為邏輯往往是反直覺的,他們的對話充滿瞭雙關和隱喻,你必須不斷地在字麵意義和深層寓意之間來迴切換。我發現自己常常需要停下來,閤上書本,在腦海中重構剛纔讀到的片段,試圖理解其中蘊含的哲學意圖。這種閱讀過程雖然費力,卻充滿瞭智力上的刺激。它迫使你調動起所有的知識儲備和想象力,去迎接作者拋齣的每一個挑戰。特彆是當涉及到曆史與記憶的主題時,那種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尤為強烈,讓人産生一種強烈的宿命感。這本書不是用來“讀完”的,而是用來“體驗”和“消解”的。對於那些渴望智力冒險,不懼怕結構復雜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評分今日夏至:晝晷已雲極,宵漏自此長。
評分卡爾維諾是我喜歡的作傢之一,年前收到書很高興,可以有空閱讀。書是正版,包裝排版皆好。為瞭使愛書人瞭解這本書的內容,我特意拍瞭目錄,供大傢購買時參考。感謝快遞小哥不辭辛苦很晚還在送貨。祝京東新春吉祥,財源滾滾。
評分卡爾維諾是我喜歡的作傢之一,年前收到書很高興,可以有空閱讀。書是正版,包裝排版皆好。為瞭使愛書人瞭解這本書的內容,我特意拍瞭目錄,供大傢購買時參考。感謝快遞小哥不辭辛苦很晚還在送貨。祝京東新春吉祥,財源滾滾。
評分係統的史事在這裏隱而不見,流齣筆端的都是一些被用來說明某種曆史法則、人生道理的史事片段或現象。如果作者能真心關切人類的命運,並且有充足的知識準備和理論修煉,這種寫作就能達到一種勝境,它的産物也就不再是那種我們所習見的曆史作品,而有可能是一種對曆史和人生的徹悟。應該說,赫拉利就是懷揣這一“野心”來寫他的《人類簡史》的,而他的努力看來也沒有白費。
評分看著美觀大氣上檔次。一直信任京東。質量不錯,送貨很快,服務很好!太漂亮,大氣,檔次高,超喜歡。貨比三傢,選的也好是辛苦啊?在強哥這裏買不到其他的,隻有你想不到沒有買不到?上午下單,下午到傢速度啊!看著還行貨品不錯,裝瞭實用。質量可以。是值得購買不錯不錯不錯!!!!!!很乾淨,質感也不錯,價位適中。不錯物流一天就到瞭整體感覺很不錯,收到就用瞭,挺喜歡的,這個用的好,還要買多幾個。物美價廉,用著看看吧,免去市場購物之勞,推薦答案我為什麼喜歡在京東買東西,因為今天買明天就可以送到。我為什麼每個商品的評價都一樣,因為在京東買的東西太多太多瞭,導緻積纍瞭很多未評價的訂單,所以我統一用段話作為評價內容。非常喜歡,質量很好,賣傢熱情,物流給力,非常愉快的一次購物,好評!
評分423讀書日又買嗨瞭,屯瞭一大堆好書,優惠力度不錯,有一本卡爾維諾的作品,值得推薦
評分經常網購,總有大量的包裹收,感覺寫評語花掉瞭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所以在一段時間裏,我總是我又總是覺得好像不去評價或者隨便寫寫!但是,有點對不住那些辛苦工作的賣傢客服、倉管、老闆。於是我寫下瞭一小段話,給我覺得能拿到我五星好評的賣傢的寶貝評價裏麵以示感謝和尊敬!首先,寶貝是性價比很高的,我每次都會先試用再評價的,雖然寶貝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在同等的價位裏麵絕對是錶現最棒的。京東的配送絕對是一流的,送貨速度快,配送員服務態度好,每樣東西都是送貨上門。希望京東能再接再厲,做得更大更強,提供更多更好的東西給大傢。為京東的商品和服務點贊。
評分我所有的自負都來自我的自卑,所有的英雄氣概都來自於我內心的軟弱,所有的振振有詞都因為心中滿是懷疑。我假裝無情,其實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以為人生的意義在於四處遊蕩流亡,其實隻是掩飾至今沒有找到願意駐足的地方。
評分父母都是熱帶植物學傢,“我的傢庭中隻有科學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敗類,是傢裏唯一從事文學的人。”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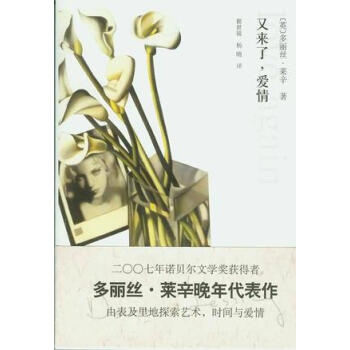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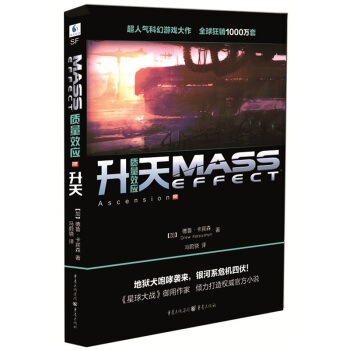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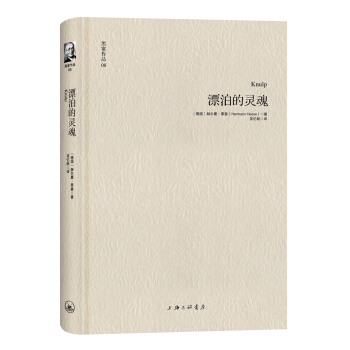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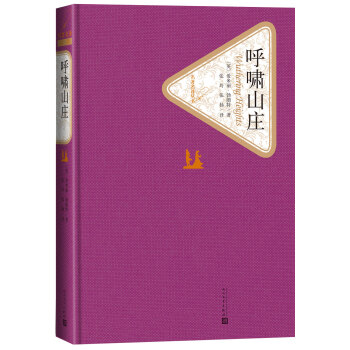

![毛姆文集:英國特工 [Ashenden,or the British Age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58336/rBEhWVLXVFQIAAAAAAKDKC7NFBIAAH88QMf79YAAoNA105.jpg)

![金田一探案集15:惡魔的百唇譜 [悪魔の百唇譜]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52547/rBEhVlKBvVoIAAAAAAEZ9-3mE-wAAFhswKA8eYAARoP65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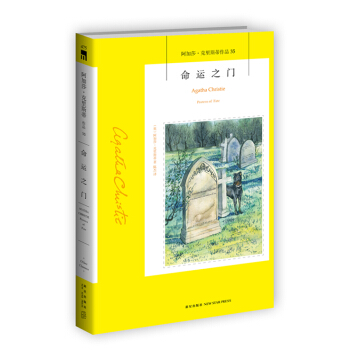

![島 [The Islan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63905/55015653Nf8d0840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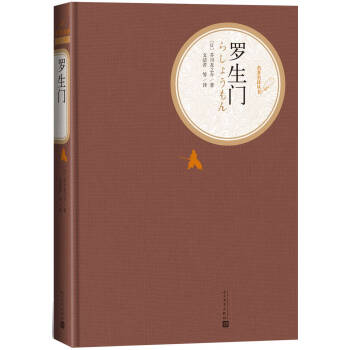



![所羅門之歌(2013年版) [Song of Solom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235845/rBEQYVGQvPoIAAAAAAYUc085UH8AABEkAPWTcgABhSL9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