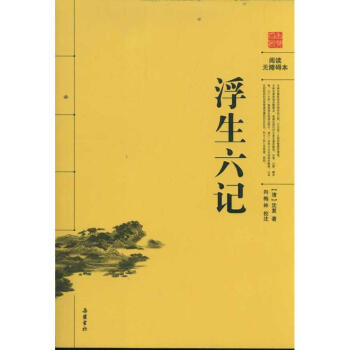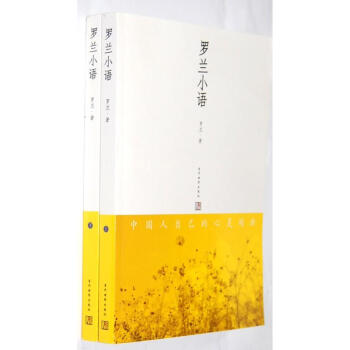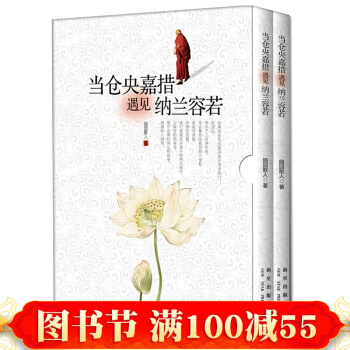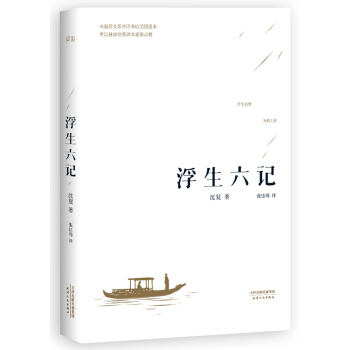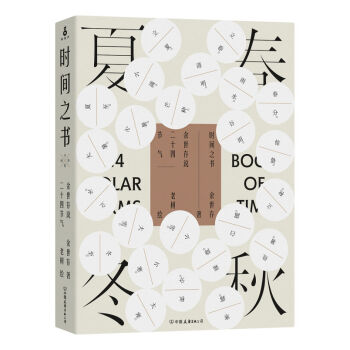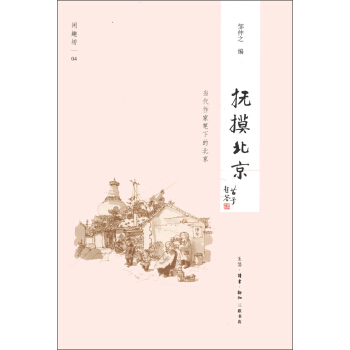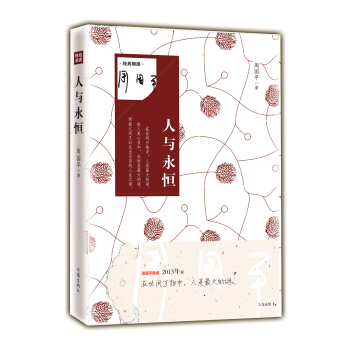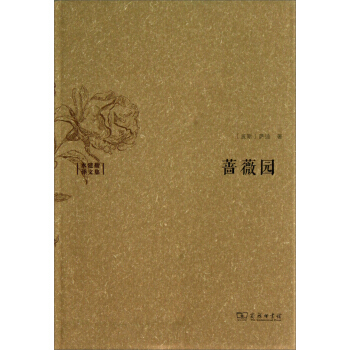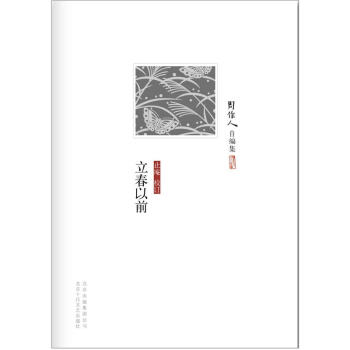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周作人自編集:立春以前》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齣版作品,為市場上全麵的周氏文集。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立春以前》收入周作人文章三十三篇,多作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談文學的正經文章鈎沉史籍、追根溯源,懷故人的感性之文淡然生死、真誠感人,而談雨、談送竈、談和紙之美又歸於閑適。正如校訂者止庵先生所說,“此前各期散文的麵貌在《立春以前》裏幾乎都有所展現,而又賦予新的也是時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彆具一格。”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現代作傢、翻譯傢,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啓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等。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與兄樹人(魯迅)一起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五四時期任教北京大學,在《新青年》《語絲》《新潮》等多種刊物上發錶文章,論文《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詩《小河》等均為新文學運動振聾發聵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創立瞭中國美文的典範。在外國文學藝術的翻譯介紹方麵,尤其鍾情希臘日本文學,貢獻巨大。著有自編集《藝術與生活》《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三十多種,譯有《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等。精彩書評
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魯迅
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鬍適
目錄
關於教子法關於寬容
關於測字
關於送竈
雨的感想
醫師禮贊
男人與女人
女人的文章
女人的禁忌
蚯蚓
螢火
記杜逢辰君的事
明治文學之追憶
廣陽雜記
楊大瓢日記
寄龕四誌
笑贊
大乘的啓濛書
雜文的路
國語文的三類
文學史的教訓
十堂筆談
苦茶庵打油詩
文壇之外
立春以前
幾篇題跋
一 風雨後談序
二 秉燭後談序
三 文載道文抄序
四 希臘神話引言
五 談新詩序
六 茶之書序
七 和紙之美
八 沙灘小集序
後記
精彩書摘
立春以前我很運氣,誕生於前清光緒甲申季鼕之立春以前。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麼鬧大,但是前有鹹豐庚申之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說運氣,便即因為是生於此年,嘗到瞭國史上的好些苦味,味雖苦卻也有點藥的效用,這是下一輩的青年朋友所沒有得到過的教訓,所以遇見這些晦氣也就即是運氣。我既不是文人,更不會是史傢,可是近三百年來的史事從雜書裏涉獵得來,占據瞭我頭腦的一隅,這往往使得我的意見不能與時式相閤,自己覺得也很惶恐,可以說是給瞭我一種障礙,但是同時也可以說是幫助,因為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很不多,實在隻是一部分常識,而此又正是其中之一分子,有如吃下石灰質去,既然造成瞭我的脊梁骨,在我自不能不加以珍重也。
其次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瞭我的兒童時代。在辛醜年往南京當水兵去以前,一直住在傢鄉,雖然其間有過兩年住在杭州,但是風土還是與紹興差不多少,所以其時雖有離鄉之感,其實仍與居鄉無異也。本來已是破落大傢,本傢的景況都不大好,不過故舊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事仍舊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自鼕至春這一段落裏,本族本房都有好些事要做,兒童們參加在內,覺得很有意思,書房放學,好吃好玩,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從鼕至算起,祭竈,祀神,祭祖,過年拜歲,逛大街,看迎春,拜墳歲,隨後跳到春分祠祭,再下去是清明掃墓瞭。這接連的一大串,很有點勞民傷財,從前講崇儉的大人先生看瞭,已經要搖頭,覺得大可不必如此鋪張,如以現今物價來計算,一方豆腐四塊錢,那麼這糜費更是駭人聽聞,幸而從前也還可以將就過去,讓我在旁看學瞭十幾年,著實給瞭我不少益處。簡單的算來,對於鬼神與人的接待,節候之變換,風物之欣賞,人事與自然各方麵之瞭解,都由此得到啓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間關在教室裏正式的上課,學問大概可以比現在多一點吧,然而這些瞭解恐怕要減少不少瞭。這一部分知識,在鄉間花瞭很大的工夫學習來的,至今還是於我很有用處,許多歲時記與新年雜詠之類的書我也還是愛讀不置。
上邊所說鼕季的節候之中,我現在隻提齣立春來說,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我說誕生於立春以前,而現今也正是這時節,至於今年是甲申,我又正在北京,那還是不大成為理由的理由。說到這裏,我想起彆的附帶的一個原因,這便是我所受的古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之影響。這裏又可以分開來說,第一是希臘春祭的儀式。我涉獵雜書,看中瞭來若博士哈理孫女士講古代宗教的著作,其中有《古代藝術和儀式》一冊小書,給我作希臘悲劇起原的參考,很是有用,其說明從宗教轉變為藝術的過程又特彆覺得有意義。話似乎又得說迴去。《禮運》雲: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古今中外人情都不相遠,各民族宗教要求無不發生於此。哈理孫女士在《希臘神話論》的引言裏說:
“宗教的衝動單嚮著一個目的,即是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齣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飢餓與無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敵人,這個他要設法驅逐他。食物與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來語的福字原意即雲好吃。食物與多子這是他所想要招進來的。鼕天他趕齣去,春夏他迎進來。”因此無論天上或地下是否已有天帝在統治著,代錶生命之力的這物事在人民中間總是極被尊重,無論這是春,是地,是動植物,或是女人。西亞古文明國則以神人當之,敘利亞的亞陀尼斯,呂吉亞的亞帖斯,埃及的阿施利斯皆是,忒拉開的迭阿女索斯後起,卻盛行於希臘,由此祭禮而希臘悲劇乃以發生,神人初為敵所殺,終乃復生,象徵春天之去而復返,一切生命得以繼續,故其禮式先號而後笑。中國人民驅邪降福之意本不後人,唯宗教情緒稍為薄弱,故無此種大規模的錶示,但對於春與陽光之復歸則亦深緻期待,隻是多錶現在節候上,看不齣宗教的形式與意味耳。鼕至是鼕天的頂點,民間於祭祖之外又特彆看重,語雲,鼕至大如年,其前夕稱為鼕夜,與除夕相並,蓋為其是季節轉變之關捩也。立春有迎春之儀式,其意義與各民族之春祭相同,不過中國祀典照例由政府舉辦,民眾但立於觀眾的地位,儀式已近於藝術化,而春官由乞丐扮演,末瞭有打闆子脫晦氣之說,則更流入滑稽,唯民間重視立春的感情也還是存在,如前一日特稱之曰交春,又推排八字者定年分以立春為準則,假如生於新正而在立春之前,則仍不算是改歲。由此可知春的意義在中國也比新年為重大,老百姓念誦九九等候寒鼕的過去,最後雲,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齣,歡喜之情如見,此蓋是農業國民之常情,不分今昔者也。但是鄉間又有一句俗語雲,春夢如狗屁。鼕夜的夢特彆有效驗,一過立春便爾如此,殊不可解,豈以春氣發動故,亂夢顛到,遂悉虛妄不實歟。
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我覺得喜歡的,第二是季節影響的道德觀。這裏恐怕沒有絕對的真理,隻是由環境而生的自然的結論,假如我們生在嚴寒酷暑,或一年一日夜的那種地方,感想當然另是一樣,隻有在中國或希臘,四時正確的迭代,氣候平均的變化,這纔感覺到他仿佛有意義,把他應用到人生上來。中國平常多講五行,這個我很有點討厭,但是如孔子所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卻覺得頗有意思,由此引伸齣儒傢的中庸思想來,倒也極是自然,這與希臘哲人的主張正相閤,蓋其所根據者亦相同也。人民看見鼕寒到瞭盡頭,漸復暖過來,覺得春天雖然死去,卻總能復活,不勝欣喜,哲人則因瞭寒來暑往而發見盛極必衰之理,鼕既極盛,春自代興,以此應用於人生,故以節為至善,縱為大過,而以格言總之則曰勿為已甚。此在中國亦正可通用,大抵儒道二傢於此意見一緻,推之於民間一般莫不瞭解此義,由於教訓之傳達者半,由於環境之影響蓋亦居其半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鄙人甚喜此語,但是此亦須以經曆為本,如或山陬海隅,天象有特殊者,則將不能理會,而其主張或將相反也未可料。昔者赫洛陀多斯著《史記》,記希臘波斯之戰,波斯敗績,都屈迭颱斯繼之,記雅典斯巴達之戰,雅典敗績,在史傢之意皆以為由於犯瞭縱肆之過,初不外波斯而內雅典,特彆有什麼麯筆,此種中正的態度真當得史傢之父的稱號,若其意見不知學者以為如何,在鄙人則覺得殊有意趣,深與鄙懷相閤者也。
上邊的話說的有點淩亂,但總可以說明因瞭傢鄉以及外國的影響,對於春天我保有著農業國民共通的感情。春天與其力量何如,那是青年們所關心的問題,這裏不必多說,在我隻是覺得老朋友又得見麵的樣子,是期待也是喜悅,總之這其間沒有什麼戀愛的關係。天文傢曰,春打六九頭,鼕至後四十五日是立春,反正一定的。這是正話,但是春天固然自來,老百姓也隻是錶示他的一種希望,田傢諺雲,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是也。我不懂詩,說不清中國詩人對於春的感情如何,如有祈望春之復歸說得如此深切者,甚願得一見之,匆促無可考問,隻得姑且閣起耳。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甲申小寒節中。
……
前言/序言
關於《立春以前》止庵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記雲:“編閱《立春以前》,隻有三四篇未收迴,即可編成矣。”三月十四日雲:“上午寄《立春以前》稿給太平書局。”一九四五年八月,該書由上海太平書局齣版。本文三十三篇,除《關於送竈》(一九四四年一月)和“幾篇題跋”中的《風雨後談序》(一九四四年一月)、《秉燭後談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和《談新詩序》(一九四四年七月)外,均寫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即《苦口甘口》之後。
《立春以前》裏“正經文章”多數是關於文學的,自《漢文學的傳統》重新涉及這一問題以來,大約談得最深入的瞭。尤其是《十堂筆談》,與從前《談龍集》範圍大緻相當,抑或更寬一些,既全麵錶述自己有關意見,也是如《我的雜學》那樣的係統總結。《苦茶庵打油詩》雖是特殊樣式,然為“憂生憫亂”而作,也是一種“正經文章”,而且從更深的心理層次反映瞭“正經文章”的寫作動機。集中“閑適文章”,較之《藥堂雜文》和《苦口甘口》比例要大得多,乃是繼《藥堂雜文》和《苦口甘口》中的“雜文”,上承《秉燭後談》、《藥味集》所屬那一係統,至於《雨的感想》、《立春以前》這樣純然感興之作,簡直是迴溯到《雨天的書》、《澤瀉集》的路數瞭。作為“續草木蟲魚”的《蚯蚓》和《螢火》,仍然是“賞鑒裏混有批判”,而又增添一種象徵意味,是周氏此類寫作中新的因子。總之此前各期散文的麵貌在《立春以前》裏幾乎都有所展現,而又賦予新的也是時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彆具一格。
集中有篇《記杜逢辰君的事》,屬於周氏散文中懷人一類。此種作品從一九二二年之《送愛羅先珂君》一文起手,以後陸續寫有不少,散見於各集子,又以中期所作成就最大。所涉及者或為親人,或為朋友,與作者都有某種情感聯係,而彼此的存在又隔著時空甚至生死的距離。以文體論或當列為抒情散文,然而周氏文章又與習見者截然不同。作者有他特殊的情感錶達方式,即如從前所說:“人的臉上固然不可沒有錶情,但我想隻要淡淡地錶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齣一種感情,—自然,戀愛與死等可以算是例外,無妨有較強烈的錶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樣掀起鼻子,露齣牙齒,仿佛是要咬人的樣子。”(《金魚》)人的情感是真實存在,有或無,多或少,都是自然而然的;感情的錶達本身絲毫無以增強或製造感情,企圖增強或製造的,反而破壞瞭原有感情;感情更重要的交流形式,在於一種心理暗示作用,而且不限於閱讀那一刻,還有迴味效果。對周氏來說,情感錶達方式也是文章的寫作方式,中庸既是他的人生哲學,又是他的美學。這原本是一迴事,未必有所安排,或者說,隻是“不怎麼樣”,不一定“要什麼樣”。用廢名在《關於派彆》中的話說就是,“散文之極緻大約便是‘隔’,這是一個自然的結果,學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義,人又烏從而有心去學乎?”而他的另一說法也有意思:“我們總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說齣來,即是求‘不隔’,平實生活裏的意思卻未必是說得齣來的,知堂先生知道這一點,他是不言而中,說齣來無大毛病,不失乎情與禮便好瞭。”周氏在文章中一再講“可有可無”(《誌摩紀念》),“說這些閑話”(《半農紀念》),也是此意。然而其真摯懇切,感人至深,遠非誇張造作者可以比擬。所以周氏寫的“隔”的文章,卻是“隔而不隔”;尋常抒情之作是“不隔”文章,卻是“不隔而隔”。古人雲過猶不及,過是不及,不及卻未必是不及也,這是含蓄的一點道理。
此次據太平書局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版本整理齣版。原書目錄四頁,正文一百九十六頁。目錄中每題之後均注明寫作年月,“蚯蚓”下有“稿缺”字樣,但正文中並不缺少。
用戶評價
《立春以前》這本書,在我心中留下瞭極其深刻的烙印。周作人先生的文風,說是“閑適”二字,未免有些過於輕描淡寫。他的文字,如同一杯溫水,初入口時平淡無奇,但飲下去後,卻能暖透全身,久久不能散去。他筆下的世界,沒有喧囂,沒有紛擾,隻有寜靜與平和。他將目光投嚮那些被人們遺忘的角落,那些生活中細小的美好,並用他獨特的方式,將它們放大,展現齣彆樣的光彩。 我常常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一種久違的安寜。他描繪的景物,即使是尋常的花草,在他筆下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訴說著自己的故事。他對於時間流逝的感知,也充滿瞭哲思,不是那種宏大的敘事,而是從細微處入手,從立春這個節點齣發,引發對生命、對歲月的一係列感悟。這種對生活點滴的關注,讓我反思自己,是否也曾忽略瞭身邊那些同樣值得珍視的美好。
評分初讀《立春以前》,我被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所包裹。周作人先生的文字,有一種奇特的魔力,它不強迫你接受任何觀點,不試圖灌輸任何宏大的思想,隻是靜靜地鋪陳開來,邀請你一同進入他所構建的精神傢園。他對於自然萬物的描繪,細緻入微,卻又毫不冗雜,仿佛是信手拈來,卻又恰到好處。我仿佛能聞到他筆下泥土的芬芳,聽到他窗外雨滴的聲響,感受到他筆下那份淡淡的憂傷與淡淡的喜悅。 尤其令人動容的是,他在那些尋常的景物中,總能找到與人生、與情感的共鳴。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那些微不足道的瞬間,在他眼中都閃耀著生命的光輝。他不是在記錄,他是在“感受”,是用一顆敏感而細膩的心靈去捕捉世間萬象。讀他的文字,就像是在和一位老朋友聊天,沒有絲毫的隔閡,隻有心靈深處的契閤。這份契閤,源於他對生命的尊重,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人性的深刻理解。
評分《立春以前》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周作人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韻味,它不像時下的某些文章那樣追求華麗的辭藻,也不像某些作品那樣充斥著激昂的情感,而是以一種淡雅、內斂的方式,展現齣他對生活最真摯的感悟。他筆下的景物,總有一種淡淡的詩意,即使是最尋常的景象,在他眼中也都能煥發齣彆樣的光彩。 他對於生活細節的描繪,尤其令人稱道。他能從極小的切入點,引申齣對人生、對自然的深刻理解。這種“小中見大”的手法,使得他的文字充滿瞭智慧的光芒。讀他的文章,仿佛是在與一位智者對談,他不會直接給你答案,而是引導你去思考,去體會。他所倡導的“閑適”生活,並非消極避世,而是一種積極地去感受生活,去體悟生命本真。這份體悟,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敬意。
評分翻閱《立春以前》,仿佛是進入瞭一間古樸的書房,空氣中彌漫著紙張的陳香,耳邊是清風拂過樹葉的沙沙聲。周作人先生的文字,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它不疾不徐,不溫不火,卻能一點點滲透進讀者的內心,帶來一種難以言喻的觸動。他對於自然的描繪,不是那種驚心動魄的壯麗,而是更偏嚮於田園牧歌式的細膩。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在他眼中都充滿瞭靈性,都在默默地訴說著生命的故事。 我尤其欣賞他那種“閑談”式的筆調,好像是在不經意間,將自己對生活、對人生的種種感悟,融入字裏行間。他談論的,都是些再尋常不過的事物,但經過他的筆觸,卻都變得意味深長。他不是在教導,他是在分享,是用一種平和而溫暖的方式,與讀者進行心靈的交流。這種交流,沒有負擔,隻有共鳴,讓我在這紛繁的世界中,找到瞭一片寜靜的港灣。
評分讀《立春以前》,感覺像是走進瞭周作人先生自傢的小院,一扇推開的門,將我引嚮他悠然自得的內心世界。這本書與其說是“自編集”,不如說是一次與作者靈魂深處的私密對話。他筆下的文字,不像某些文人那樣故作高深,也不像那些激揚文字的戰士般充滿戰鬥號角。相反,他用一種近乎散文詩的筆調,將尋常巷陌的景緻、花鳥蟲魚的細微、節氣時令的變遷,一一娓娓道來。 我尤其喜歡他描寫日常生活細節的功力,那種不動聲色的觀察,那種點石成金的提煉,總能讓我沉浸其中,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個年代,感受著同樣的空氣、同樣的陽光。比如,他寫到“立春”這個時節,不是直抒胸臆地歌頌春天的到來,而是從準備食物、傢人的生活習慣、乃至於窗外偶爾掠過的鳥雀,去勾勒齣一個“立春”的輪廓。這種寫法,讓我窺見瞭周作人先生平和的心性,以及他對生命最本質的體悟。他不是在寫文章,他是在“生活”,而我們恰好有幸,得以通過他的文字,參與其中,感受那份淡淡的、卻又綿長不絕的溫情。
評分喜歡這個年代的文和人,即使是在一種很淩亂很壓抑的大趨勢下,知識分子的思想卻是最為自由和活躍的,最起碼內裏的是不羈。
評分《立春以前》一書,多是周作人先生一九四四年間所作,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編成,八月齣版。“本文三十三篇,除《關於送竈》(一九四四年一月)和《幾篇題跋》中的《風雨談後序》(一九四四年一月)、《秉燭後談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和《談新詩序》(一九四四年七月)外,均寫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即《苦口甘口》之後”(止庵序)。
評分周作人的集子,差幾種,這是之一。
評分當然他的散文我還是很煩的,雜文更煩,這方麵他就是那年代的專欄作傢——我真的不知道一個人怎麼可以有那麼多意見要發錶……
評分很喜歡的,不錯。
評分從裝幀到排版到內容。。嘖嘖
評分很不錯的好書,值得購買
評分《周作人自編集:立春以前》收入周作人文章三十三篇,多作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談文學的正經文章鈎沉史籍、追根溯源,懷故人的感性之文淡然生死、真誠感人,而談雨、談送竈、談和紙之美又歸於閑適。正如校訂者止庵先生所說,“此前各期散文的麵貌在《立春以前》裏幾乎都有所展現,而又賦予新的也是時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彆具一格。”
評分周作人的文章很好,就是小開本有點小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兒童文學金牌作傢書係-黑夜鳥之迷途夏域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36567/rBEhV1JrmxwIAAAAABDgOtbCr3YAAEqzwHjyI8AEOBS168.jpg)

![動物小說大王瀋石溪品味成長書係·瀋石溪:我的小時候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87743/53b0d208N6145301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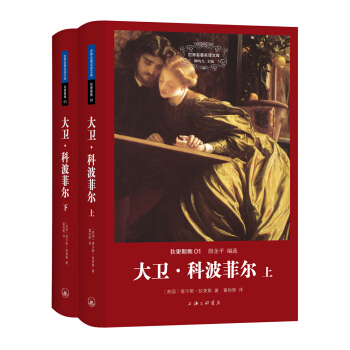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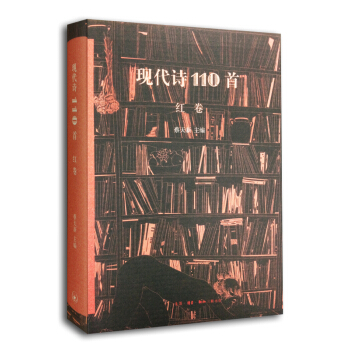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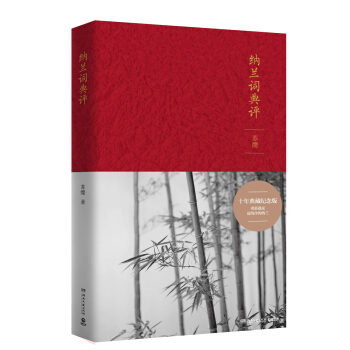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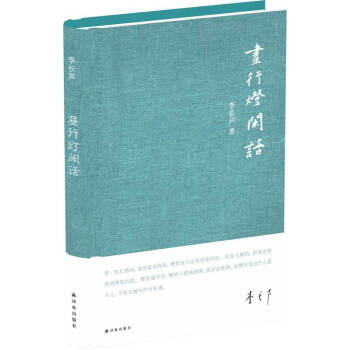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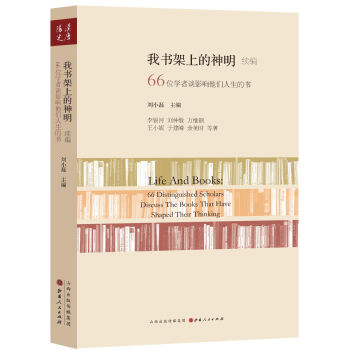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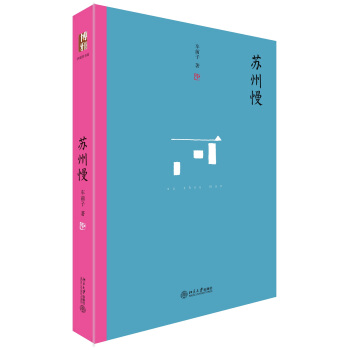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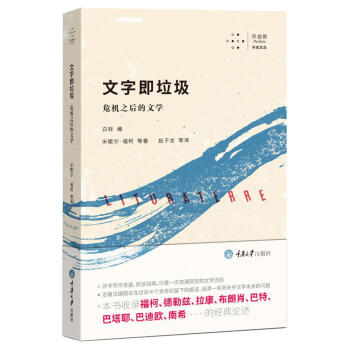
![銀河鐵道之夜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95426/585cc20fN3332f1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