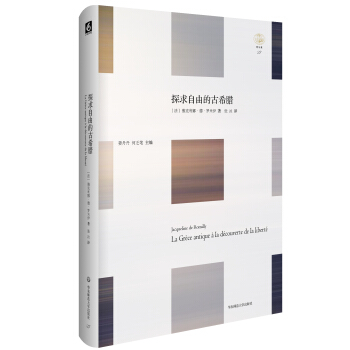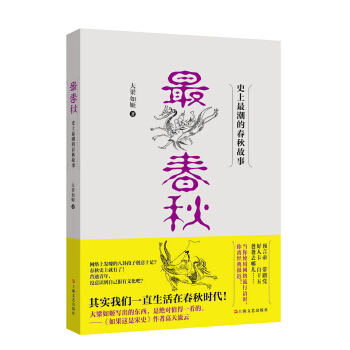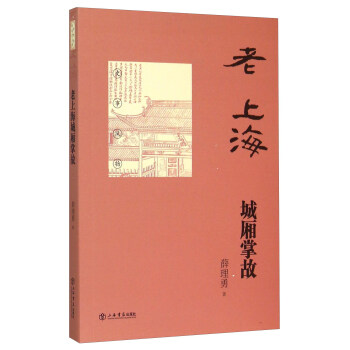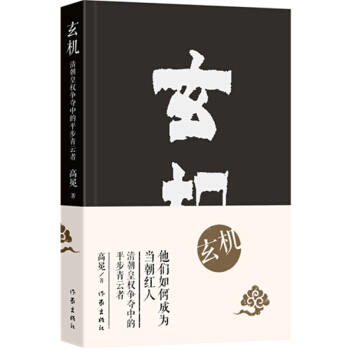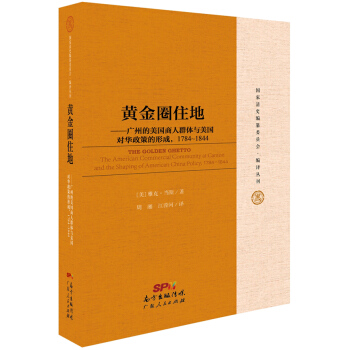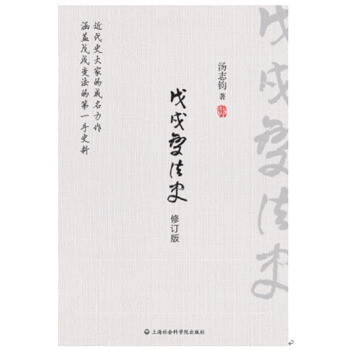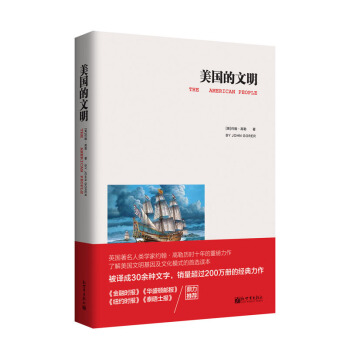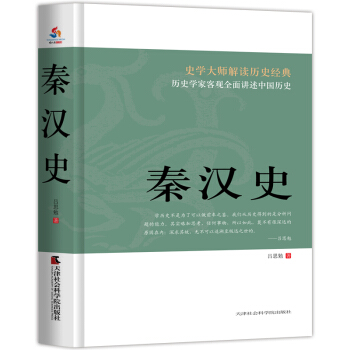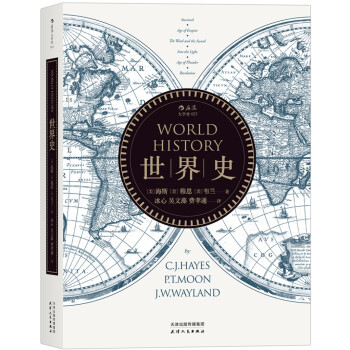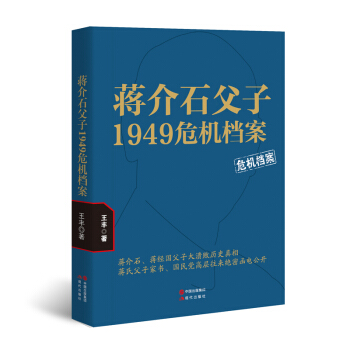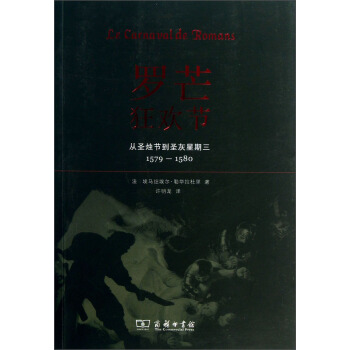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罗芒狂欢节: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讲述的是在1580年2月份的两周时间中,罗芒城(当年属于多菲内省,现今属于德龙省)的居民妆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乃至动物,欢快地跳舞、游戏、赛跑、联欢……在狂欢节期间每天上演的节目中,罗芒人的游行队伍行进在手艺人和显贵之间。全城到处都有自发的民间演出,街道与街道,行会与行会,各显其能,一比高下。黑社会人物法官盖兰设下陷阱,致使罗芒人互相厮杀。这是一件包含有多种意义的事件,一位史学大家对此做了破译。
目录
前言第一章 城乡概况
第二章 税收:平民向贵族抗争
第三章 1576年:让·德布尔格的陈情书
第四章 1578年:雅克·科拉审慎的造反
第五章 1579年:球王塞尔弗的首届狂欢节
第六章 1579年:抗税和债务
第七章 1580年:罗芒的民俗大师安托万‘盖兰
第八章 1580年:丰盛星期二或上帝与我们同在
第九章 虐杀农民的屠戳场
第十章 “喜鹊和乌鸦啄去了我们的眼珠子……”
第十一章 范型、会社、“王国”
第十二章 冬天的节日
第十三章 再说农民
第十四章 追求平等的先民
鸣谢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手稿与抄本
精彩书摘
火药的第二个要素(准确地说是第二种成分.也就是说,有了木炭还需要硝石,就在这里。硝石就蕴藏在16世纪从罗讷河到北阿尔卑斯民众的抗税行动中。我在这里要谈一谈两个特权等级所享有的特殊免税权。免税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完全不是虚幻的想象。据说,时间是在安贝尔二世1341年发布那项极为重要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免税令20多年之后,最晚不迟于在罗芒举行多菲内三级会议的1370年7月。从此以后,直至黎胥留时代,免税始终是一条得到切实执行的规定;不过也有若干例外,例如贵族和教会在某些时候也会被要求缴纳这个税或那个税,但是,这种例外情况不被看作此后可以照此办理的先例。1370年多菲内三级会议颁布的那个法令,完全符合法国贵族的行事原则,所以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具有不言而喻的法律效力,尽管当时颁布这项法令仅仅出于一时之需。当时(1370年)之所以颁布这项法令,完60全是为了争取多菲内地区的特权等级对法国国王的支持。(贵族免税在整个法国始终是中央君主政权的一个副产品。)国王狡诈地故意混淆多菲内三级会议同意的“自愿奉献”和国王庄园的正常收益。①国王因而需要在多菲内省的上层人物中找到一批同谋,于是乎,贵族得以享受免税,以便进一步在普通百姓身上榨油。
长期存在于多菲内地区的因抗税而产生的社会悲剧,从此埋下了日后将要发芽生根的种子。第三等级在16世纪展开了远比15世纪更为波澜壮阔的斗争,他们要求如同其他人一样享受免税。其余两个等级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免税的优惠待遇,第气等级理所当然地拒不承认这种免税优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依据1341年法令的精神,平民们明确地坚持认为,任何人都无需纳税。否则,包括贵族和教会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无一例外地按照各自应当承担的份额向国王缴纳“自愿奉献”,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或许更大。
从14世纪最后30余年以来,多菲内每年举行一次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与另外两个等级最严重的冲突就在多菲内三级会议上上演。这里有必要对多菲内三级会议这个庄严的机构说上几句,这肯定对于我们理解罗芒狂欢节何以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大有裨益。
多菲内三级会议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16世纪是如何组成的?肯定地说,三级会议的结构远非稳定和固定,由于受1560—1580年间的宗教之争和内乱的影响,这个机构时而被推向正确方向,时而被推向错误方向。
迪塞尔在他的著述中指出,①多菲内三级会议的名册上有:教会代表36人,贵族代表270人(这些人大多是拥有大庄园并享有司法权的乡绅),第三等级代表115人。第三等级代表包括各个城市的市议会议员、某些集镇的议会议员,甚至还有若干村庄的村民会议成员。这些地方中的大部分都位于国王和王储的直辖庄园中,有些地方则位于某些乡61绅的私人土地上。
由于遴选代表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某些乡村教区尽管直接隶属于领主乃至国王,在三级会议中却没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在1579—1680年间却也参与了起义,罗芒北面的伐鲁瓦便是其中之一。
从总体上看,三级会议无论采用何种投票方式,贵族始终在全省三级会议中占有等级优势,在人数上也压倒其他等级。②贵族不但享有权威。
……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人着迷的历史著作,它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了文艺复兴晚期法国宗教冲突背景下,民间狂欢文化与宗教礼仪之间的复杂张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仿佛带领读者亲身走进了十六世纪末的街道,感受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与狂热。书中对“罗芒狂欢节”这一特定时间段的社会心理描摹尤其精彩,那种由盛大的庆祝活动突然转向禁欲和忏悔的巨大落差,被阐释得淋漓尽致。我特别欣赏作者如何通过对地方志、私人信件以及少量幸存下来的仪式记录的交叉印证,构建出一个立体可感的历史场景。它并非仅仅是事件的罗列,而是在探讨在社会秩序摇摇欲坠之时,人们如何通过这些周期性的集体仪式来处理内心的焦虑和对权威的潜在反抗。阅读过程如同解谜,每一次对文献的解读都揭示出更深层的文化密码。
评分读完后,我感到仿佛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尽管这本质上是一部历史研究。作者对于中世纪晚期狂欢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国家权力构建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理解框架。那些关于游行队伍、假面、食物禁忌和性别角色的描述,细致入微,却又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学术距离,避免了过度浪漫化或猎奇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对“时间”概念的探讨——从放纵的“狂欢节时间”到神圣的“四旬斋时间”的转换,如何被统治阶级和教会用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点极具启发性。这种对仪式性时间序列的结构性分析,远超出了对单一事件的描述,它揭示了一种深植于欧洲社会肌理中的内在节奏和权力运作逻辑。
评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严谨态度和创新性。很多时候,历史书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但在这本书里,作者成功地将那些看似碎片化的教会法令、地方官员的报告以及教会法庭记录,编织成一张有机的网。他没有回避史料的模糊性,而是坦然地展现了在特定年份(1579-1580)所能捕捉到的历史残影,并基于此推导出当时社会氛围的微妙变化。这使得全书的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它让我们看到,历史并非是清晰的线条,而是充满了噪音和断裂的复杂文本。特别是关于狂欢节期间对社会等级的短暂颠覆与随后的权力回归的分析,深入剖析了社会张力的释放机制。
评分这本书提供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它挑战了许多传统上将“宗教”与“世俗”简单二元对立的解读。作者巧妙地证明了,在那个特定时期,狂欢的激情与信仰的虔诚并非完全对立,它们在复杂的文化互动中相互渗透、相互界定。它描绘的不是一个僵硬的、被教条完全控制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矛盾、正在努力寻找自身平衡点的复杂共同体。阅读时,我不断地思考,我们今天的节日和仪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承载着类似的社会功能和心理释放作用?这本书成功地跨越了时间鸿沟,使得古代的狂欢节具有了当代的回响。它迫使读者重新审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动力学。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相当典雅,但绝非故作高深。它以一种近乎散文诗的笔调,勾勒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我个人尤其喜欢作者在描述具体风俗时所采用的对比手法,比如对世俗享乐的描绘是如此的生动热烈,以至于与随后严格的禁食和祈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复述,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作者是高明的导演。尽管涉及大量的历史背景知识,但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总能在关键时刻插入富有个人见解的评论,使读者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对于那些对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心理和民间宗教实践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富矿。
评分应该选择破坏它,再重建一个新世界'还是应该继续努力地恢复它本来的样子.
评分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歌德
评分相比之下,影片就显得肤浅了些吧.不过有好听的音乐和漂亮的画面也多少弥补了一些
评分从总体上看,三级会议无论采用何种投票方式,贵族始终在全省三级会议中占有等级优势,在人数上也压倒其他等级。②贵族不但享有权威。
评分建议先看电影,再看漫画,不然会有很大的落差感.因为漫画的思想层次比电影要高出许多,而且电影把许多人物都给省去或是简化了,显得没有漫画中那么丰满.
评分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终于在京东买的书送到了。很满意。 《学记》曰:“是固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也。”对于我们教师而言,要学的东西太多,而我知道的东西又太少了。有人说,教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这话固然有道理,但一桶水如不再添,也有用尽的时候。愚以为,教师不仅要有一桶水,而且要有“自来水”、“长流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固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也”。因此,在教学中,书本是无言的老师,读书是我教学中最大的乐趣。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有方法才有成功的路径。教师今天的学习主要不是记忆大量的知识,而是掌握学习的方法——知道为何学习?从哪里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即使他教的门门功课都很优异,他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学习者。因为这对于处在终身学习时代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学习型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充裕的学习资源。学习化社会中的个体学习,犹如一个人走进了自助餐厅,你想吃什么,完全请便。个体完全可以针对自身的切实需求,选择和决定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学习的进度等等。 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向。在知识经济大潮中,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应该认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找准自己的价值空间。教书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一本好书会使我爱不释手,一首好诗会使我如痴如醉,一篇美文会使我百读不厌。我深深地知道,只有乐学的教师,才能成为乐教的教师;只有教者乐学,才能变成为教者乐教,学者乐学,才能会让学生在欢乐中生活,在愉快中学习,这就是我终身从教的最大追求。 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毅力。“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天爱读书容易,一辈子爱读书不易。任何人都可以使梦想成为现实,但首先你必须拥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信念。有信念自有毅力,有毅力才能成功。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的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一旦今日停止成长,明日你就将停止教学。身为教师,必须成为学习者。“做一辈子教师”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师只有再度成为学生,才能与时俱进,不断以全新的眼光来观察和指导整个教育过程。使广大教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创造性地开展教书育人工作。 常读书使我明白了许多新道理: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人——环境”系统。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教师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教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
评分好书,值得一读!
评分在官方叙事的版本中,正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小学课文《参观刘家峡水电站》里的描写:“碧绿的湖水映着蓝天白云,更显得清澈。……湖水从大坝的进水口直冲下来,流入电机房底部,推动水轮机。水轮机不断运转,发电机就产生了强大的电流。电流通过高压输电线,输送各地去。”个体被一种更大的叙事淹没,这种无始无终的静态画面,遮蔽了宛在水中央的大川。的确,如课文中色彩鲜明的画面中,“电机房里灯火辉煌,五台绿色的大型发电机组,整齐地排列着。……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区广大城乡用的电,都是从这儿输送去的。”由技术成就组成的现代性,构成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涂尔干式的“集体记忆”,而消失的个体则“失去”了自己表述另一种记忆的机会。
评分这“中心”,不仅是地域的中心,(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不存在地域上辐射其他城市的中心),更是每个美国人心目的价值观,就是一种强烈的独立自治精神,它使得美洲最终走上脱离母国的道路并取得胜利。至于美国人喜欢迁移的性格,当也能在早期美国历史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殖民地时代的美洲缺乏劳力和技艺,与稀缺而高价的人力资源相比,土地却是一样丰富而便宜的东西。“在任何东西,包括古老的宅基地都可出售的地方,人们便不那么衣恋于任何特定的土地。一旦某块土地不再能供养他们,他们便向别处迁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 [A Survey on Sexual Life in Europ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8652/rBEhVFKds5gIAAAAABQMQAITD7QAAGTdAILdTsAFAxY5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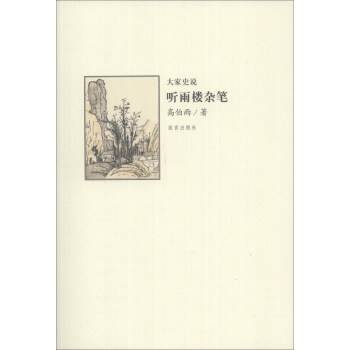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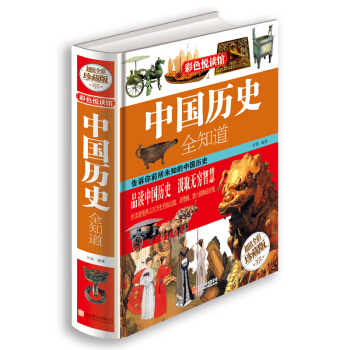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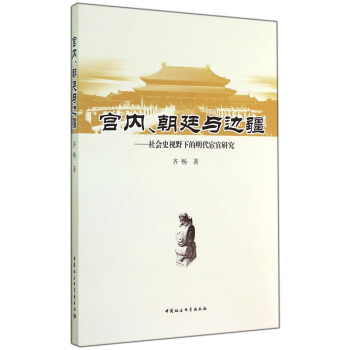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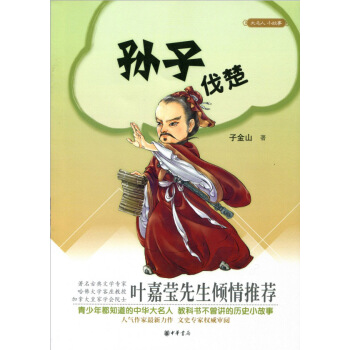
![第三帝国:非洲军团(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Afrikakorp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18/54d48a8cN01e9180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