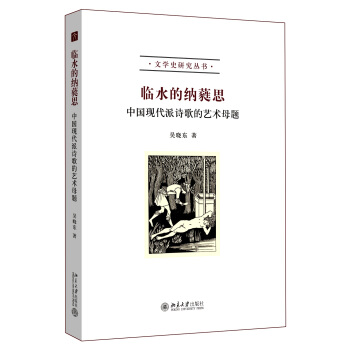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选择一系列母题意象作为研究现代派诗歌的微观化视角,通过对现代派诗歌派的文本细读,深入探讨现代派诗人的主体心灵世界和审美化的艺术形式。作者试图从理论建树和文本分析层面建立现代派诗歌研究的意象—母题诗学,表现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创性思维;而且对文学性和诗性分析颇有心得,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对文学文本的悟性。内容简介
《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探讨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截止到抗战之前崛起于诗坛的一个青年群体——现代派诗人群,作者认为,临水自鉴的纳蕤思形象历史性地构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的一个象征性原型。现代派诗人的笔下由此也集中出现了临水与对镜的姿态,甚至直接把自我拟想为纳蕤思的形象。本书选择了一系列母题意象作为研究现代派诗歌的微观化视角,通过对现代派诗歌派的文本细读,深入探讨了现代派诗人的主体心灵世界和审美化的艺术形式。作者简介
吴晓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年至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社会科学“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代表作品:《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漫读经典》《文学的诗性之灯》、《废名·桥》《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等。
目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导论 心灵与艺术的双重母题
纳蕤思的神话:诗的自传
临水的沉思者
母题:一种观察形式
一 辽远的国土
远景的形象
在异乡
“失乐园”
二 扇
中介的意义
“只有青团扇子知”
扇上的“烟云”
齐谐志怪的境界
三 楼
“泛滥”的“古意”
记忆的法则
规定的情境
“楼乃如船”
四 居室与窗
室内生活
落寞的古宅
临窗的怅望者
五 姿态:独语与问询
心灵的形式
自我指涉的语境
个体生命的境遇
“写不完的问号”
六 乡土与都市
荒废的园子
古城
老人
陌生的都市
两种时间
七 有意味的形式
梦
幻象的逻辑
表象的世界
拟喻性的语言
八 镜
“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
“我”与“你”
主体的真理
结语 关于生命的艺术
附录一 尺八的故事
附录二 西部边疆史地想象中的“异托邦”世界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八 镜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
莫掀帏望远吧,如不想自鉴。
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
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
——卞之琳的《旧元夜遐思》
每日清晨醒来
照着镜
颜色憔悴的人
那长夜的疲倦,像旅愁
需要点凭藉了
——朱英诞《镜晓》
与纳蕤思临水的姿态具有内在同构性的,是现代派诗人笔下更习见的“临镜”的意象。这种同构性在纳蕤思神话中仍可以找到原型。在梁宗岱所复述的纳蕤思的本事中即曾着意强调当纳蕤思诞生时,“神人尝预告其父母曰:‘毋使自鉴,违则不寿也。’因尽藏家中镜,使弗能自照”,但镜子可以藏匿,却无法把水面也藏起来,而纳蕤思正是从水中发现了自己的面影。因此,纳蕤思的临水自鉴透露出水面与镜子所具有的相似的映鉴功能 。而从自我认同的镜像机制上看,“临镜”与“临水”则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拉康所发明的镜像阶段的心理分析理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纳蕤思的临水自鉴。早在1914年,弗洛伊德就发表了《论那喀索斯主义》,把纳蕤思的自恋情结推衍为人类普泛的心理机制。这无疑对拉康后来的镜像理论具有启迪的意义,只不过临鉴的对象从水面置换为拉康的镜子而已。 当然,如果更细致分辨,镜子与水面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镜子——‘象征的母体’(matrice de symbolique),随着人类对于认同的需求而产生” ,它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史中发明的器物,而人们提到“水面”往往更强调的是其“自然” 属性。两者背后的人类学内涵、文化史语义以及隐含的美学效果尚需另文仔细分疏 。
“镜”的意象,也同样引我们进入现代派诗人具体化的艺术世界以及心理世界。我们试图探讨的,正是以“镜”为代表的,具现在个体诗人身上同时又具有普泛性特征的艺术母题内容。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临镜”的形象,可以看成是纳蕤思临水的原型形象的延伸。这使得一代诗人的“对镜”姿态也获得了一种艺术母题的意义。这同样是一种颇具形式感的姿态,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诗人们在频频对镜的过程中获得的是一种自反式的观照形式,在对镜的自我与其镜像之间互为循环的结构关系中体现着一种自我指涉的封闭性审美心态。镜中的镜像,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是“对镜者”自我的如实或者变形化的投射。
“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
隐含在对镜的姿态背后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哲学。徐迟在《我 及其他》一诗中,借助这倒置的“我”的形象传达了“‘我’一字的哲学”:
这“我”一字的哲学啊。
桃色的灯下是桃色的我。
向了镜中瞟瞟了时,
奇异的我 ,
忠实地爬上了琉璃别墅的窗子。
镜中出现的这倒置的以及反转过来的“我”的字形,乍看上去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实际上诗中试图表达的是“我”的哲学。反转的“我”是诗人的“我”在镜中的投射,它再形象不过地营造了一个自我与镜像之间的自反式的观照情境。无论是“我”的倒置,还是“我”的反转,都不过是“我”的变形化的反映。“‘我’一字的哲学”,实际上是自我指涉的哲学,言说的是自我与镜像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言说的是自我对象化和他者化的过程。而自我正是在这种对象化和他者化中获得了个体生命的确证。正如有的研究者所阐释的那样:“在镜中看见自己,发现自己,需要一种主体将自己客体化、能够分辨什么是外、什么是内的心理操作。如果主体能认出镜像与自己相似,还能说:‘我是对方的对方。’这种操作过程就算成功。自我和自我的关系,以及熟悉自我,是无法直接建立的,它仍旧受限于看与被看的相互作用。”
Sabine Melchior�睟onnet:《镜子》,余淑娟译,第23页,台北:蓝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在这个意义上,对自我的影像的着迷与执着,与镜子中的自己的映像的对峙与对望,都隐含着主体化过程中的某些无意识心理动机。
废名的《点灯》思索的也是自我与影像的关系:
病中我起来点灯,
仿佛起来挂镜子,
像挂画似的。
我想我画一枝一叶之何花?
我看见墙上我的影子。
“灯”是废名酷爱的意象,它使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佳构《十二月十九夜》中的诗句:“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灯”隐喻着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心理慰藉。而《点灯》中的灯也同样暗示着一种温暖的慰藉感,对于病中的“我”就更其如此。与灯相类的则是在废名诗中更加频繁出现的“镜子”的意象,《点灯》中的“点灯”与挂镜子由此形成了一种同构的情形,诗人的联想脉络也由“点灯”转喻到“挂镜子”。我们可以想象到诗人在这面虚拟的镜子中鉴照他病中的倦容。尽管这个鉴照的过程不过是一种虚拟,我们仍然在诗的最后一句领略了“我”与镜像的指涉关系——“我看见墙上我的影子”,一种形影相吊的凄清感透过看似平白如话的文字表层滋生了出来,诗人所获得的最终仍旧不过是孤独的慰藉。
对于大多数深深濡染着一种时代病的忧郁症和孤独感的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来说,“对镜”的自反式观照姿态印证的是一种孤独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封闭性的审美形式是与孤独的心灵状态合而为一的,因此,这种对镜的鉴照不唯带给诗人一种自足的审美体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强化了孤独与寂寞的情怀。卞之琳的《旧元夜遐思》就传达了一种对镜子的逃避心理:
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
莫掀帏望远吧,如不想自鉴。
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
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
诗人并不想自鉴于窗玻璃,然而远窗却是更深的镜子,它映现的是诗人内心更深的孤独。这种临鉴正是一种自反式的观照,镜子中反馈回来的形象是诗人自己。在这种情形中,诗人的主体形象便以内敛性的方式重新回归自身,能够确定诗人的自我存在的,只是他自己的镜像。从镜像中,自我所获得的,不如说是对寂寞感本身的确证,正如牧丁在一首《无题》中写的那样:“有人想澄明自鉴,把自己交给了/寂寞。”陈敬容1936年的一首诗也传达了同样的寂寞感:
幻想里涌起
一片大海如镜,
在透明的清波里
谛听自己寂寞的足音。
因此,有诗人甚至害怕临镜自鉴便可以理解了,如石民的《影》:“心是一池塘,/尘缘溷浊,/模糊了我的影。/但我怕认识我自己,如纳西塞斯(Narcissus),将憔悴而死。” 这首诗反用纳蕤思的形象,体现的是对自我认知的逃避。
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们营造的这种“镜式”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拉康的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尤其是想象界(l�餴maginaire)的理论。拉康根据他对幼儿心理成长历程的研究指出,刚出世的婴儿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存在。这一非主体的存在对自我的最初的认识,是通过照镜子实现的。当婴儿首次从镜子中认出自己时,便进入了主体自我认知的镜像阶段。婴儿最初对自我存在的确证是借助于镜像完成的。婴儿一旦对镜像开始迷恋,在镜子面前流连忘返,便进入了拉康所谓的想象界(l�餴maginaire),从而建立起一个虚幻的自我,但此时的自我并未形成真正的主体,它带有一种想象和幻象的特征,婴儿所认同的不过是自己镜中的影像。尽管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镜像,但仍是一个幻觉中的主体。
想象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临镜的自我与其镜像的一种自恋性关系。未成形的主体所关怀的只是他镜中的形象,并在这种镜像的迷恋中体验到一种自我的整一性。但这种整一性毕竟是幻象的存在,是一种镜花水月般的真实。一旦自我触摸到镜像发现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幻想性的同一便被打碎了。作为幻影的镜像并不能真正构成主体的确证和支持。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们在临镜的想象中最终体验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对现实的规避使他们耽于自我的镜像,迷恋于自己的影子,就像临水的纳蕤思终日沉迷于自己水中的倒影一样。这种自我指涉性的观照方式隐喻的是一个孤芳自赏型的孤独的个体。如果说具有原型性特征的文本模式往往意味着某种普泛性的秩序,而在现代派诗人营造的“镜式”文本中,自反性的观照形式则意味着自我与镜像间的封闭的循环,意味着一种个体生命的孤独秩序,意味着自我与影像的自恋性的关系中其实缺乏一个使自我获得支撑和确证的更强有力的真实主体。
朱英诞的《镜晓》正反映了这种诗人的“自我”匮乏依凭和附着的心理状态:
每日清晨醒来
照着镜
颜色憔悴的人
那长夜的疲倦,像旅愁
需要点凭藉了
谁想着天末
一个不可知而又熟悉的地方
是谁来点缀呢
山中白云沉默得可怕啊
小鸟是岩石的眼睛
青松是巢住着春风
清晨醒来对着镜子的“颜色憔悴”的人,自然而然使人想到憔悴的水仙之神。而“每日”这一时间性的修饰,则表明了对镜行为的惯常性特征,几成一种日常的功课。诗中“憔悴”的,不仅是对镜者的容色,更是一种心理和情绪。这是一种低回与无所附着的心态,“沉默得可怕”的,与其说是“山中白云”,不如说是对镜者的心境和主观体验,因而,诗人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凭借和点缀了,正像小鸟是岩石的点缀,春风是青松的寄托一样。这种凭借和点缀是对镜者与镜像的互为指涉之外对于诗中抒情主体的更高的支撑,是使诗人憔悴而疲惫的对镜生涯获得生动与活力的更为超越的因素。但由谁来点缀呢?是天末那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么?是对一个辽远的国土的向往么?似乎诗人也无法确定。“小鸟是岩石的眼睛/青松是巢住着春风”,这两句收束愈发反衬出对镜者主体的匮乏感。这种感受在朱英诞另一首诗《海》中获得了更直接的具现:
多年的水银黯了
自叹不是鲛人
海水于我如镜子
没有了主人。
这首诗套用了鲛人泣珠的神异故事。诗人自叹不是鲛人,而传说中鲛人遗下的珠泪已经像水银般黯淡了。面对海水这面镜子,诗人领悟到的,是一种人去楼空般的感受。“没有了主人”在文字表层正暗示着一个鲛人式的临镜者的匮乏,而更深层的含义则象征着一个更高的真正的主体的缺失。
“镜像”的隐喻意义正在这里。它给临镜者一种虚假的主体的确证感,而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影子。因此废名的这首费解的诗《亚当》便大体可以理解了:
亚当惊见人的影子,
于是他悲哀了。
人之母道:
“这还不是人类,
是你自己的影子。”
亚当之所以“悲哀”,在于他误把自己的影子看成了他的传人,亦即“人类”,而亚当的“惊见”也多少有些像鲁迅小说《补天》中的女娲诧异地发现她所创造的人类变成了她两腿之间“古衣冠的小丈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中“人之母”的解释当会构成亚当的些许安慰:他所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影像,尚不是“人类”本身。如果把“人之母”的解释加以引申,或许可以说,影像的存在是无法确立作为人类的实存的,而确证“人”的主体存在的,只能是他自己。
对于沉溺镜像本身的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来说,主体的匮乏更具体的含义在于他们面对世界所体验到的一种失落感。这是一批无法进入社会的权力体制以及话语结构的中心,也无法彻底融入社会的边缘人边缘心态的如实反映。但诗中体现出的主体的失落感并不意味着诗人们无法构建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恰恰相反,自我与镜像互为指涉的世界本身就有一种艺术的自足性和完美性。“这种完美的对应和等同正表明了幻想的思维方式—— 一种无穷往复的自我指涉和主体与对象间的循环。” 这个完美对应而又封闭循环的艺术世界满足的是临镜者自恋性的心态以及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并使诗人们在自我指涉的对镜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封闭性的安全感和慰藉感。正如阿弗叶利斯所说:“这种封闭式的表现手段说明了诗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封闭式的表现手段都出自这种心态”。在中国现代派诗人这里,这种“自我天地”便是他们构建的镜式文本,文本世界依据的是自我与镜像间互为指涉的想象逻辑。它超离现实人生与世界,最终收获的是一个语言和幻想的乌托邦。正像卞之琳在一首《无题》中写的那样:“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支撑这一批诗人的,正是一种镜花水月般幻美的艺术图式。
何其芳的《扇》即有一种烟云般的幻美:
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
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
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
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
叹华年流过绢面,
迷途的仙源不可往寻,
如寒冷的月里有了生物,
每夜凝望这苹果形的地球,
猜在它的山谷的浓淡阴影下,
居住着的是多么幸福……
“镜子”在妆台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首诗却假设了一个匮缺“镜子”的情境,少女的自恋与自怜则无从凭依。镜子恰恰在匮缺中昭示了它的重要性,因此它堪称一个“缺席的在场” 。在诗中,“宫扇”是作为“镜子”的一个替代物而出现的,也的确表现出了与镜子类似的某些属性,“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一方面透露出少女的泪水人生,另一方面也凸现了宫扇迷离虚幻的特征,有一种水中倒影般的朦胧与缥缈,汇入了现代派诗人的镜像美学和幻美诗艺。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氛围感”。它不是那种直抒胸臆、情感外露的表达,而更像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通过光影和回声来感知存在。阅读时,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参与一场发生在某个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集体潜意识活动。作者对于空间感的描绘尤其出色,无论是对城市边缘的冷峻刻画,还是对内心深处幽暗角落的探索,都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代入感。你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湿度,感觉到墙壁的粗糙,听到远处的喧嚣。这种强烈的环境烘托,使得抽象的情感和概念被赋予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大大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可以说,这本书成功地为读者搭建了一个可以暂时栖居的精神场域,让人在喧嚣的现实之外,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深度冥想的避风港。
评分这本书的内容带给我一种强烈的“陌生化”体验,它不是在重复我们日常的感知,而是在解构和重塑我们对世界的固有认知。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因为被某个词语的组合方式所震撼——它把一些本该并置的事物强行拉到一起,却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如同电流通过神经末梢的那一瞬间。这种对传统审美的挑战,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刺激和乐趣。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抛出无数个问号,促使读者主动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迷宫,虽然偶尔会迷失方向,但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这本书成功地打破了线性思维的束缚,鼓励我们用多维度的视角去审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现象,这对于一个习惯了被动接受信息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及时的精神按摩。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本身就很有品味,从封面到内页的排版,都透着一股沉静而深邃的气质。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是那种纸张特有的、带着微微油墨香气的味道,让人立刻就能沉浸到文字的世界里去。我特别喜欢那种留白的设计,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地将那些充满力量的诗句衬托出来,仿佛每一首诗词都有了呼吸的空间。装帧的质感也非常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一种厚重感,让人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珍藏之作。尤其是一些特殊字体的使用,处理得非常巧妙,既保持了现代诗歌的张力,又不会显得过于生硬。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从视觉到触觉,都在向读者发出一种无声的邀请,去探索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在如今的出版市场中,实属难得。每一次拿起它,都像是在进行一次仪式性的阅读准备,让人对接下来的文字内容充满期待。
评分从结构上来看,这本书的编排极其考究,它不像那种随意堆砌的篇章集合,而更像是一个精心规划的音乐会曲目单。不同主题、不同情绪的诗歌被巧妙地安排在相邻的位置,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和递进关系。比如,在几首相对压抑或内敛的作品之后,往往会插入一两篇情绪高昂、充满生命力的篇章作为缓冲或高潮,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感,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连贯性和沉浸感。我注意到作者似乎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空隙”,这些空白处并非虚无,而是用于承载前一篇的余韵和后一篇的序曲,使得整部作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这种对整体构架的宏观把控能力,让我想起那些优秀的电影导演,知道何时需要慢镜头特写,何时需要全景快速推进,阅读体验因此而变得层次分明,非常流畅。
评分我最近在阅读的这本诗集,其行文风格的跳跃性和丰富性,着实让我感到惊喜。它不是那种单一叙事或情感宣泄的作品,而是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建筑师,用不同的砖石结构搭建起一座座精神的殿堂。有些篇章的语言如同清晨的薄雾,朦胧而富有哲思,需要你慢下来,逐字逐句地去揣摩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而另一些段落,则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节奏感极强,仿佛是某种古典乐章的现代变奏,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意象时的那种老道和克制,他从不滥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精准地捕捉到事物最本质的“骨架”,然后用最简洁的词语进行勾勒,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给读者自己去填补色彩。这种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展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让人不得不感叹文字锤炼的功力。
评分很专业的诗歌理论著述,需要下点功夫才能读懂。
评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精彩分析。
评分满意!
评分诗歌文艺批评。行文也很诗意哦,很不错的。
评分质量不错,喜欢京东的送货速度!
评分北大教授名作,学术思想精神,文笔雅致优美,值得收藏。
评分不错的书,内容好,用纸也很好,就是运输差,挤压皱痕明显,懒得换了。
评分不错的书,内容好,用纸也很好,就是运输差,挤压皱痕明显,懒得换了。
评分不错,期待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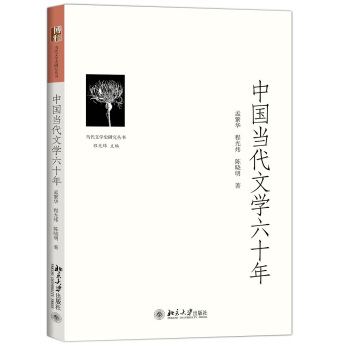
![沙与沫·先知——打动孩子心灵的世界经典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15626/57340f31N1a8e5e4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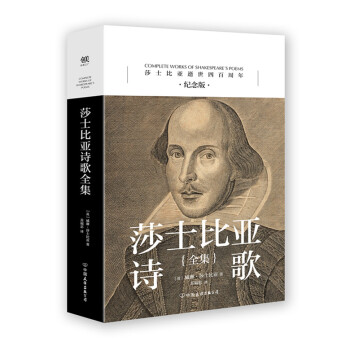
![我爱阅读丛书:会飞的鞋子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60514/576a40abN2a8ac02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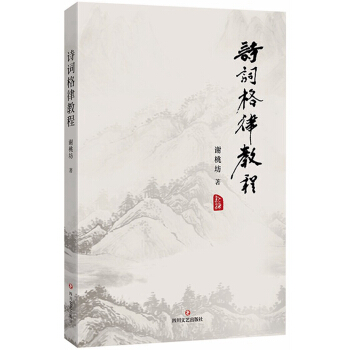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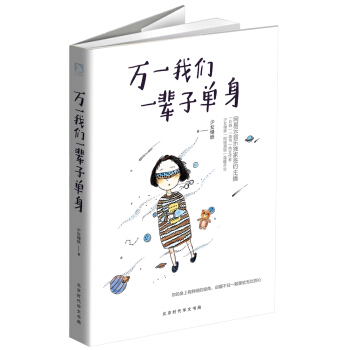
![小红豆系列(套装1-3卷 作者签名版) [8-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73684/58492867Nb324fcf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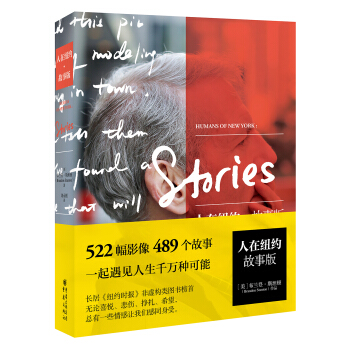
![幻想大王杨鹏获奖作品选(套装共5册)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32778/58c20faaN5b54fcc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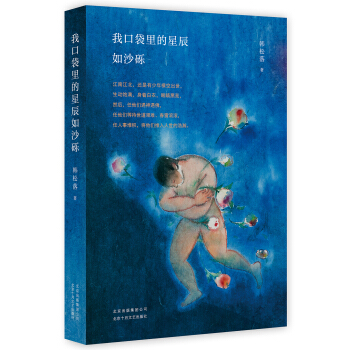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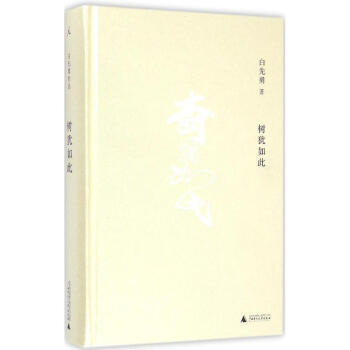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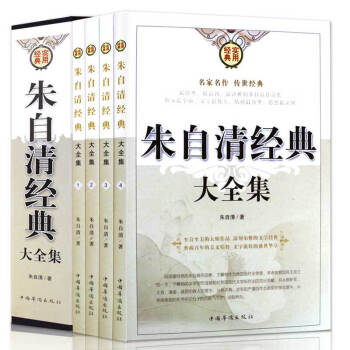


![中华经典故事:衣食住行故事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26430/rBEQYFGKKyMIAAAAAApgX-T_zUEAAAqaAMS_HkACmB342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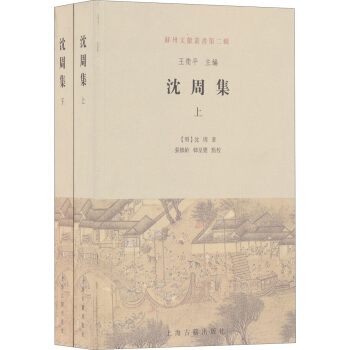
![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中华成语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4967/59f0614aN21dc6c79.jpg)
![摆渡船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金奖书系:奇妙的意外 [11-14岁] [The Great Unexpecte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75384/557e43c9N9a448be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