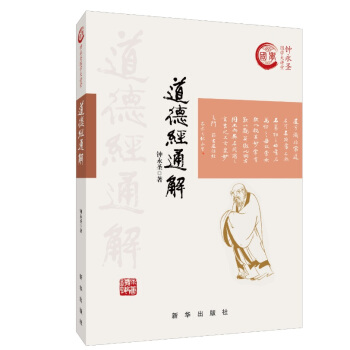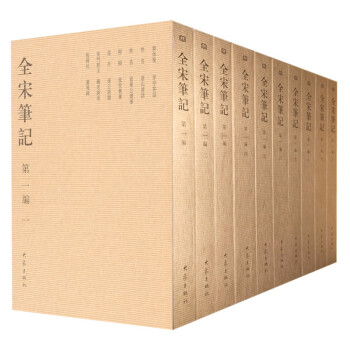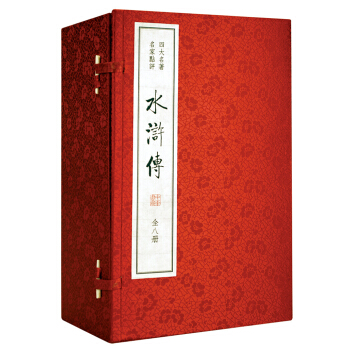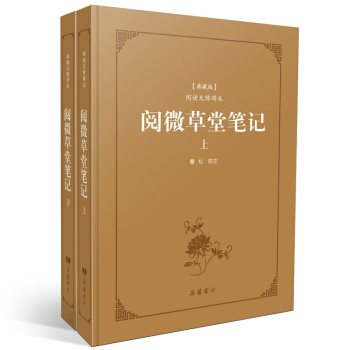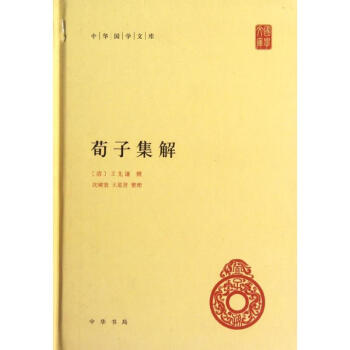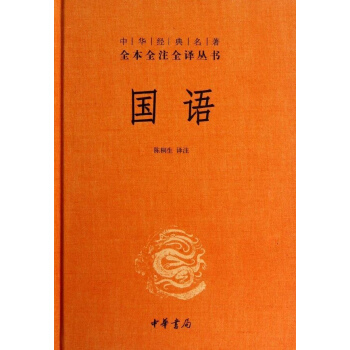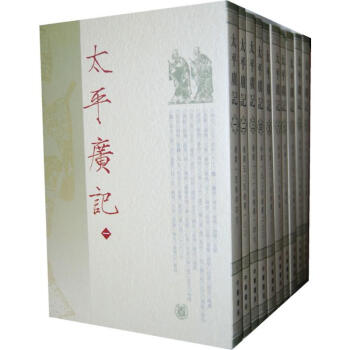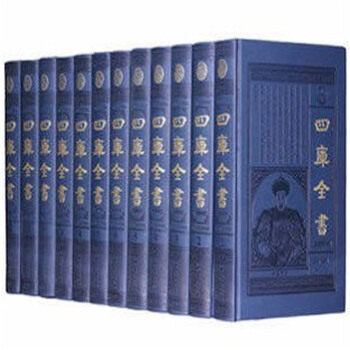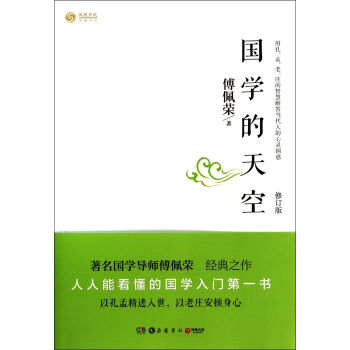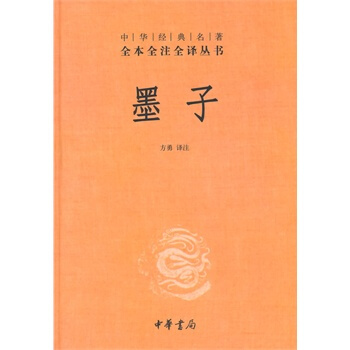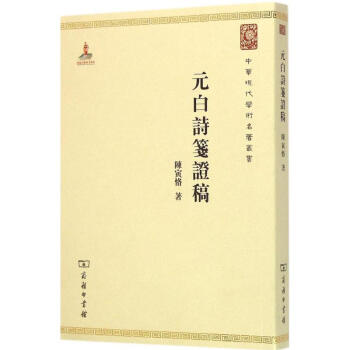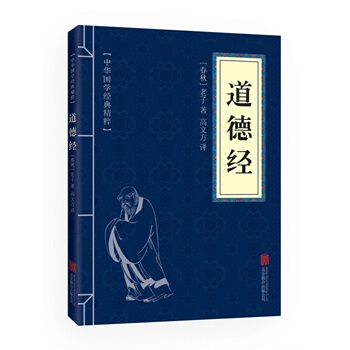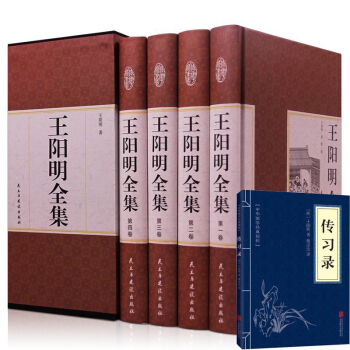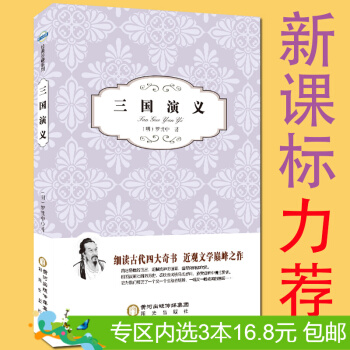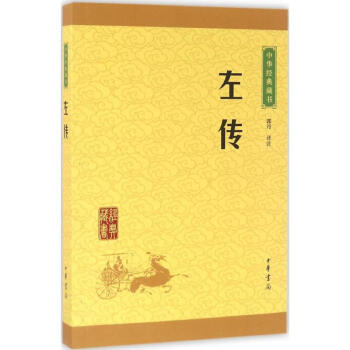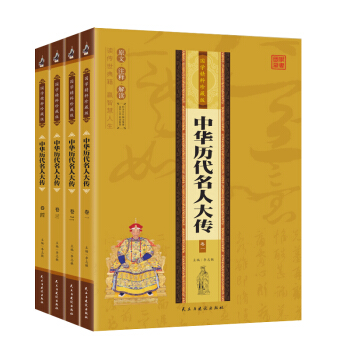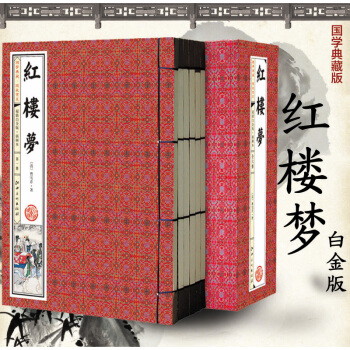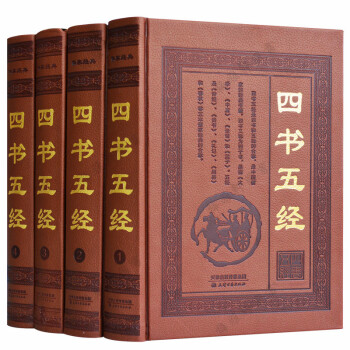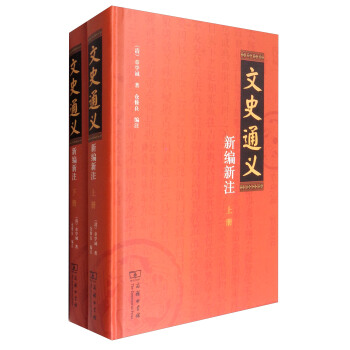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文史通義》是我國著名史學傢章學誠(1738-1801)的代錶作。由於種種原因,這部書自問世以來一直未曾有過令人滿意而完整的定本。為瞭彌補這個缺憾,《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套裝上下冊)》作者章學誠根據章氏著作本書的本意,在通行版本的基礎上,對這部史學名著進行瞭重新整理和編定,對研究章氏學術思想,瞭解他的艱難的學術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者簡介
倉修良教授,男,漢族。1933年3月生,江蘇泗陽人。中共黨員。1958年本科畢業於浙江師範學院曆史係,一直任教於杭州大學曆史學係。現為浙江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地方誌學會學術委員、浙江省地方誌學會副會長、常務理事。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研究所兼職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兼職教授、寜波大學兼職教授、溫州大學兼職教授等。
目錄
目錄
原序/1
內篇一
易教上/1
易教中/12
易教下/16
書教上/20
書教中/27
書教下/36
詩教上/45
詩教下/59
禮教/69
經解上/76
經解中/ 80
經解下/87
內篇二
原道上/94
原道中/100
原道下/103
原學上/108
原學中/110
原學下/112
博約上/114
博約中/117
博約下/119
浙東學術/121
硃陸/126
書《硃陸》篇後/132
文德/136
文理/139
古文公式/145
古文十弊/149
內篇三
辨似 /157
繁稱/161
匡謬 /169
質性/177
黠陋/181
俗嫌/187
針名/190
砭異/192
砭俗 /194
內篇四
所見/198
言公上/200
言公中/206
言公下/213
說林/221
知難/232
釋通/236
申鄭/249
答客問上/252
答客問中/256
答客問下/259
橫通/262
內篇五
史德/265
史釋/270
史注/274
傳記/280
習固/288
詩話/290
書坊刻詩話後/298
題《隨園詩話》/306
婦學 / 307
《婦學》篇書後/316
內篇六
文集/318
答問/324
篇捲/328
天喻/332
師說/335
假年/337
博雜/339
同居/342
感遇/344
感賦/349
雜說/352
外篇一
立言有本/358
《述學》駁文/ 361
《淮南子洪保》辨/368
論文辨僞/387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393
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405
論課濛學文法/411
史學例議上/421
史學例議下/424
史篇彆錄例議/426
論修史籍考要略/432
史考釋例/438
史考摘錄/453
讀《史通》/467
讀《北史·儒林傳》隨劄/469
駁孫何《碑解》/476
駁張符驤論文/478
評瀋梅村古文/481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487
墓銘辨例/489
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捨/494
傢譜雜議/496
雜說上/501
雜說中/503
雜說下/505
外篇二
《三史同姓名錄》序/507
《史姓韻編》序/511
《藉書園書目》敘/514
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516
《紀年經緯》序/518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519
刪訂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526
《文學》敘例/529
《文格舉隅》序/532
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534
《四書釋理》序/536
《劉忠介公年譜》敘/538
高郵瀋氏傢譜序/541
嘉善茜涇浦氏支譜序/544
陳東浦方伯詩序/546
《唐書糾謬》書後/ 549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552
《李義山文集》書後/556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558
書《貫道堂文集》後/562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570
書郎通議墓誌後/574
硃先生墓誌書後/578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580
《鄭學齋記》書後/582
《韓詩編年箋注》書後/584
金君行狀書後/586
跋《香泉讀書記》/588
跋《江寜古刻今存錄》/590
跋《屠懷三製義》/592
跋《邗上題襟集》/594
徐尚之古文跋/596
劉氏書樓題存我額記/597
吳澄野太史《曆代詩鈔》商語/599
清漳書院留彆條訓三十三篇 /606
定武書院教諸生識字訓約/630
外篇三
報黃大俞先生/634
報謝文學/637
論文上弇山尚書/641
與吳胥石簡/643
答吳胥石書/646
又答吳胥石書/648
上曉徵學士書/649
為畢製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653
上辛楣宮詹書/658
上慕堂光祿書/661
答邵二雲/663
與邵二雲論學/665
與邵二雲/667
與邵二雲論文/669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672
與邵二雲論文書/674
與邵二雲論學/676
與邵二雲書/678
與邵二雲書/679
與邵與桐書 /681
答邵二雲書/684
與史餘村/687
與史餘村論文/689
又與史餘村/690
與史餘村簡/ 691
與史餘村論學書/692
與汪龍莊書三月 / 694
與汪龍莊簡/696
與鬍雒君/699
與鬍雒君論文/701
與鬍雒君論校《鬍穉威集》二簡 /703
與嚴鼕友侍讀/707
與硃滄湄中翰論學書/709
答瀋楓墀論學/713
又答瀋楓墀/717
與陳鑒亭論學/718
答陳鑒亭/721
報孫淵如書/722
與孫淵如書/724
與周永清論文/ 726
又與永清論文/728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730
答周筤榖論課濛書癸卯/732
再答周筤榖論課濛書癸卯/734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業三簡/736
與林秀纔/741
與劉寶七昆弟論傢傳書/744
答某友請碑誌書/745
與馮鞦山論修譜書/749
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751
候國子司業硃春浦先生書/753
與阮學使論求遺書/756
上硃中堂世叔/760
上畢撫颱書己酉十一月二十九日/762
上硃大司馬書/764
又上硃大司馬書 /765
又上硃大司馬書 /766
上硃大司馬論文/768
與硃少白論文 /770
又與硃少白論文/772
又與硃少白/774
答硃少白書/777
又答硃少白書/779
又答硃少白書/782
又與硃少白書/784
與硃少白書/786
上梁相公書/791
與錢獻之書/794
與族孫守一論史錶/798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丙戌 /800
與史氏諸錶侄論策對書/804
又與正甫論文/808
論文示貽選/811
答大兒貽選問/814
傢書一/816
傢書二/818
傢書三/820
傢書四/822
傢書五/823
傢書六/824
傢書七/826
外篇四
方誌立三書議/828
州縣請立誌科議/836
答甄秀纔論修誌第一書/841
答甄秀纔論修誌第二書/846
與甄秀纔論《文選》義例書/853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855
修誌十議呈天門鬍明府/857
地誌統部/866
方誌辨體/871
與石首王明府論誌例 / 876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誌書/880
復崔荊州書/883
記與戴東原論修誌/885
《和州誌·誌隅》自敘 / 888
《和州誌·皇言紀》序例/890
《和州誌·官師錶》序例/892
《和州誌·選舉錶》序例/894
《和州誌·氏族錶》序例上 /897
《和州誌·氏族錶》序例中 /901
《和州誌·氏族錶》序例下 /903
《和州誌·輿地圖》序例/905
《和州誌·田賦書》序例/909
《和州誌·藝文書》序例/913
《和州誌·政略》序例 / 922
《和州誌·列傳》總論 / 925
《和州誌·闕訪列傳》序例 /930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上/932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中/936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下/939
《和州誌·文徵》序例 / 942
外篇五
《永清縣誌·皇言紀》序例 /946
《永清縣誌·恩澤紀》序例 /949
《永清縣誌·職官錶》序例 /952
《永清縣誌·選舉錶》序例 /955
《永清縣誌·士族錶》序例 /957
《永清縣誌·輿地圖》序例 /961
《永清縣誌·建置圖》序例 /964
《永清縣誌·水道圖》序例 /966
《永清縣誌·六書》例議/968
《永清縣誌·政略》序例/972
《永清縣誌·列傳》序例/976
《永清縣誌·列女列傳》序例/978
《永清縣誌·闕訪列傳》序例/983
《永清縣誌·前誌列傳》序例/986
《永清縣誌·文徵》序例/989
《亳州誌·人物錶》例議上 /996
《亳州誌·人物錶》例議中 /998
《亳州誌·人物錶》例議下 /1000
《亳州誌·掌故》例議上/1002
《亳州誌·掌故》例議中/1004
《亳州誌·掌故》例議下/1006
外篇六
為畢製府撰《湖北通誌》序/1008
《湖北通誌》凡例/1013
《湖北通誌·族望錶》序例 /1020
《湖北通誌·人物錶》序例 /1022
《湖北通誌·春鞦人名》序例/1024
《湖北通誌·府縣考》序例 /1025
《湖北通誌·政略》序例/1026
《湖北通誌》序傳/1027
《湖北通誌·前誌》傳序/1031
《湖北掌故》序例/1032
《湖北文徵》序例/1034
跋《湖北通誌》檢存稿/1035
《天門縣誌·藝文考》序藝文論附 /1036
《天門縣誌·五行考》序/1038
《天門縣誌·學校考》序/1039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 /1040
為畢鞦帆製府撰《常德府誌》序 /1045
為畢鞦帆製府撰《荊州府誌》序 /1048
為畢鞦帆製府撰《石首縣誌》序 /1052
書《吳郡誌》後/1054
書《姑蘇誌》後/1059
書《灤誌》後/1063
書《武功誌》後/1067
書《朝邑誌》後/1071
書《靈壽縣誌》後/1074
《姑孰備考》書後/1078
附錄
大梁本《文史通義》原序 /1081
伍崇曜《文史通義》跋/1082
季真《文史通義》跋 / 1084
王秉恩《文史通義》跋/1085
王宗炎復書/1087
《文史通義新編》前言 / 1089
精彩書摘
《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套裝上下冊)》: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鞦》,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齣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蔔掌《三易》之法,夏日《連山》,殷日《歸藏》,周日《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齣禦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托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曆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曆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鞦》,以為周禮在魯。夫《春鞦》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製,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太蔔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後,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係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製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製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齣《周易》之外邪?無以齣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製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製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曆,而蓍揲閤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曆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玄》而始閤哉!蓍揲閤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
前言/序言
原 序
《文史通義》是我國著名史學傢章學誠(1738—1801)的代錶作,它和劉知幾的《史通》並稱為我國封建時代史學理論的雙 璧。由於章氏晚年雙目失明,未能親手編定,故將其全部書稿委 托蕭山友人王宗炎代為編定。對於王氏的編排,章學誠本人意見 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華紱卻是很不滿意,因而他於道光 十二年(1832)便在開封另行編印瞭《文史通義》。而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則在王氏編目基礎上,加以搜羅增補,並於1922年刊行瞭《章氏遺書》,《文史通義》自然亦在其中,於是此書便齣現 瞭兩種內容齣入頗大的不同版本。為瞭便於區彆起見,筆者把它 們分彆稱為“大梁本”和“《章氏遺書》本”。後來社會上盡管流傳瞭許多種版本,但都源齣於這兩種版本。兩種版本的區彆在於前者內篇分為五捲,計六十一篇,後者內篇分為六捲,計七十篇,兩者相差九篇。而外篇的內容則全然不同,前者全為方誌論文,後者則為“駁議序跋書說”,篇數相差則更大。根據筆者的研究,這兩種版本都還反映不瞭章學誠著作本書的想法和意願。同時這種局麵實際上已經給學術研究者帶來殊多不便,甚至造成混亂。比如引《禮教》篇,如果不注明“《章氏遺書》本”,到“大梁本”內篇中自然就查找不到,因為“大梁本”內篇未收這一篇。若引《方誌立三書議》的內容,如果不注明齣自“大梁本”外篇, 到“《章氏遺書》本”外篇中當然也就查找不到。反之也是如此。為瞭解決這一矛盾,並盡可能恢復《文史通義》內容的原貌,筆者花瞭三十年時間進行研究,認為兩種外篇都是《文史通義》的內容,所以在1993年齣版的《文史通義新編》中,將兩種流傳 的外篇,全部編入《新編》的外篇,並且還收入兩種外篇都不曾 有的八十餘篇,其中就包括《上曉徵學士書》和《上慕堂光祿書》 兩文,這是章氏的兩篇佚文。鬍適、姚名達在作《章實齋先生年 譜》時都未見過這兩篇文章。特彆是《上曉徵學士書》很重要,章氏在文中講瞭“取古今載籍,自六藝以降訖於近代作者之林, 為之商榷利病,討論得失,擬為《文史通義》一書。分內外雜篇, 成一傢言”。這就是說,他的《文史通義》應為內篇、外篇、雜 篇三部分組成。而章氏次子華紱在“大梁本”《文史通義》的序中 也曾指齣:“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齣原草,並穀塍先生 訂定目錄一捲。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 應更正,以復舊觀……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捲,外篇三捲,《校讎通義》三捲,先為付梓。尚有雜篇,及《湖北通誌》檢存稿 並文集等若乾捲,當俟校定,再為續刊。”這就錶明,華紱當時是 知道其父《文史通義》內容的編排次序的,其中還有雜篇,但當 時不知何故未加收入。他也看到王宗炎所編定之目錄,王氏所編 篇目是將“駁議序跋書說”作為外篇,而將方誌論文排除在《文 史通義》內容之外,故序中說這個篇目“所遺尚多,亦有與先 人原編篇次互異者”,所指大約正是這個。因為關於方誌論文是《文史通義》內容的組成部分,章學誠在有些論著中不僅講瞭,而 且明確指齣是該書的外篇,那麼“駁議序跋書說”是否又都是雜 篇呢?其實也並不如此,如章氏在《與邵二雲論文書》中就曾講 到“《郎通議墓誌書後》,則《通義》之外篇也”。正因如此,筆者在《文史通義新編》的《前言》中說:“為瞭保持新編本與習見 的通行本之間的連貫,也便於讀者的使用,這次就不再另行分設 雜篇,而將這一問題留給有關專傢再作研究瞭。”也就是說,仍將 兩種通行本的外篇全部編為外篇,因為要將“駁議序跋書說”之文區分齣外篇和雜篇實在太難。區分的標準是什麼呢? 2003年在 紹興“章學誠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梁繼紅博士的《章學誠〈文史通義〉自刻本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一文,曾談及章氏自刻本的編排問題,本以為可以解決雜篇的範圍問題,著實高興瞭一陣子,但通過仔細研究後,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隻能還是一個懸案。文章中有這樣一段,現抄錄於後:
從《文史通義》自刻本的編排體例上看,章學誠將《文 史通義》分為三個部分,即內篇、外篇
及雜篇,後附雜著, 其篇目如下:
《文史通義·內篇》:《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 下)、《詩教》(上下)、《言公》
(上中下)、《說林》、《知難》;
《文史通義·外篇》:《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誌科議》;
《文史通義·雜篇》:《評瀋梅村古文》、《與邵二雲論文》、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與史餘村論文》、《又與史餘 村》、《答陳鑒亭》;
《雜著》:《論課濛學文法》。
從上述所列篇目看,內篇和外篇,本來就無多大疑議。特彆 是方誌作為外篇,筆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論定。至於雜篇,看瞭 自刻本所列篇目後,筆者覺得還是很茫然,上文提到的《郎通議 墓誌書後》,章氏在給邵晉涵那封論文的信中,就明確定為外篇, 這封信寫於四十六歲那年,距離給錢大昕的那封信已經十一年瞭,此時的想法應當都是相當成熟瞭,既然這篇屬於外篇,當然同性 質的文章還是不在少數,自然也都應當歸入外篇。而這類文章究竟能有多少,現在看來這個界綫誰也劃不清楚。基於這種情況, 如今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想法,當年章氏次子華紱,為什麼隻將方 誌論文列為外篇,而其他的“駁議序跋書說”中還有哪些是屬於 外篇,他自己也說不清,隻有這樣一做瞭事,於是雜篇和其他內 容,都“當俟校定,再為續刊”,隻不過是藉口而已。後來的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他再也未作過任何校定續刊。因此,這裏隻好再重復一句,盡管大傢都看到瞭章氏自刻本的部分分類篇目, 但是原來的“駁議序跋書說”,究竟哪些篇應當留在外篇,哪些 篇應當歸入雜篇,還是無人能分辨清楚,看來隻好仍舊維持現狀, 待以後能有所發現再來定奪。
《文史通義新編》(下簡稱《新編》)齣版以後,曾獲得瞭中 外學術界師友們的好評,為研究章氏學說創造瞭方便條件。許多 學者並認為可以作為《文史通義》的定本。但是,同時亦有許多 友人提齣,特彆是青年朋友提齣,章氏之書比較難讀,最好能夠 有個注本,於是為《新編》再作“新注”的任務便又放到筆者 的麵前。特彆要指齣的是,浙江古籍齣版社張學舒先生更是這種 “新注”的倡導者和策劃者。筆者本人則一直心存疑慮,擔心自己 纔疏學淺,恐怕難以勝任,因為這部書的內容涉及知識麵實在太 廣。但是,為瞭不負眾望,最終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下來。
為《文史通義》最早作注的自然要首推 1935 年齣版的葉長清 的《文史通義注》,盡管在此之前,1926 年商務印書館齣版過章锡 琛的選注本,但它畢竟隻是為學生閱讀的選注本。其次則為葉瑛 的《文史通義校注》,此書完成於 1948 年,到瞭 1983 年中華書局 纔首次齣版。這是一部比較好的注本,因為不僅注釋詳密,而且 校齣瞭不少文字上的錯誤。其最大缺點在於,它不是一部內容完整 的版本。也就是說,其內容是不全的、不完整的,因而書名也就名 不副實。當然,責任並不在校注者,因為他總以為《文史通義》就 是這麼多內容。實際上這個校注本隻有 122 篇,而《新編》本則有298 篇,多齣的這些篇目中,許多都是研究章學誠學術思想和生平 治學必不可少的內容。同時由於注釋者不瞭解方誌的性質及其發展 曆史,對史學史不太精通,因而有些注釋就不太貼切。如《經解》 中裏講到“圖經”,注曰:“圖經始見於《隋誌》,郎蔚之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捲。”這個注釋顯然不妥,“圖經”開始齣現於東漢,最早見於《華陽國誌》捲一《巴誌·總序》中記載東漢時巴郡太守但望在奏章中提到的《巴郡圖經》。又清人侯康、顧懷三、姚 振宗諸人所補之《後漢書·藝文誌》均載有東漢人王逸的《廣陵郡圖經》。這足以說明圖經這種著作最早齣現於東漢,而盛行於隋 唐五代。至於圖經究竟是什麼,注者還是沒有講清楚。實際上圖經 是早期方誌的一種著作形式,與地記同時齣現於東漢,隋唐五代時 期成為方誌第二階段的主要形式,這種著作捲首均冠以所寫郡縣之 地圖。也有注釋稱其為附有地圖的地理誌,這當然也不正確。又在《方誌立三書議》開頭一段裏的“掌故”,注釋在引瞭《史記·龜 策列傳》文字後說:“掌故,國傢之故實。”這與章氏本意當然並不 相符,章氏之意是編修方誌時,在主體誌之外,另立兩種資料匯編 性質的著作,一叫《掌故》,一叫《文徵》,都是資料選編。隻要 看瞭他自己所編修的方誌,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在《湖北通誌·凡例》中說得十分清楚:“今仿史裁而為《通誌》,仿《會典》則例 而為《掌故》,仿《文選》、《文粹》而為《文徵》,截分三部之書, 各立一傢之學,庶體要既得,頭緒易清。”這是章學誠在方誌理論 上的一大創建,注釋者不解其意,而作上述解釋,使讀者更加摸不 到頭腦。在同一篇中,由於對“掌故”的理解有誤,在注釋《史 記》的《八書》時說:“八書猶方誌中之掌故。”這自然又錯瞭。其 實《八書》、《十誌》就類似於我們今天新編方誌中的各種專業誌, 章學誠因為各種方誌書名已稱誌,為避免重復,特將內中各誌均稱“考”,正像班固《漢書》中的《十誌》篇名不稱“書”一樣,就 是避免與書名重復。他在《答甄秀纔論修誌第二書》中很明確地指 齣:“考之為體,乃仿書、誌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誌》,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考與書、誌,皆為正式著作,掌故乃是資料選編,性質是不一樣的。至於中國史學史上的書誌體則是在《漢 書》誕生後已經形成,這是眾所皆知的事。而注釋者竟將《八書》 與掌故相比附,顯然又是很不妥當的。還有,注釋者常引劉鹹炘《識語》來說明某篇的宗旨或主題,其實劉氏所解,有許多亦並不切題,因為他本人亦未能理解章氏作文之本義,如《州縣請立誌科 議》,引劉氏《識語》:“此論次比,與《答客問》下同義。”這一解釋,我們可以說與本文主題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章氏此文是建議 清朝政府在各個州縣設立誌科,為編修地方誌儲備資料。因此,這 個誌科實際上就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檔案館、檔案局。正因如此,我 們今天檔案學界都把章學誠又稱作檔案學傢。書中還將曆史地理著 作《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輿地廣記》、《方輿勝覽》等 書統稱為方誌,實際上是不懂方誌是何種著作。其實這類著作,與《大清一統誌》一樣,隻應稱為全國地理總誌,而絕對不是方誌, 正因為不懂方誌是何種著作,所以有關這方麵的注釋中不妥之處較 多。我們列舉這些事例,毫無批評指責之意,旨在說明注釋工作實 在是不太容易,盡管這個注本已經是相當精細詳密,還是免不瞭有 些疏漏。這就說明,並不是能夠閱讀古文者都可以從事這項工作。
此外,貴州人民齣版社 1997 年 12 月齣版的由嚴傑、武秀成 先生譯注的《文史通義全譯》所采用的亦為“大梁本”。
長期以來,廣大讀者一直認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比較難 讀難懂,這自然就成瞭《新注》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為此,《新注》對每篇文章的主題思想或寫作宗旨都作一簡單說明,類似於 解題或提要。如全書首篇《易教》上,開宗明義第一句便是“六 經皆史也”,實際上把《易教》上、中、下三篇主題都點齣來瞭。 意思是說,《六經》都不過是史,而不要把它們視作玄而又玄的 經,因為“古人未嘗離事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既然 如此,當然都是研究當時治國平天下的重要依據,誰能說不是史 呢?不僅如此,他在《報孫淵如書》中更提齣:“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 以垂訓耳。”對此,鬍適在所著《章實齋先生年譜》中就曾指齣:“我們必須先懂得‘盈天地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一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一子目。”這自然很有道理,一切著作都具有史的價值,《六經》自然也就不例外瞭。一般說來,講《詩經》、《尚書》、《春鞦》、《禮》是史書,都是容易理解的,惟 獨說《周易》也是史,似乎就很難理解瞭。正因如此,他就把這 一篇作為解說對象。隻要大傢細心閱讀就會發現,《易教》三篇的 中心思想都在講述這一問題,從懸象設教,治曆明時,王者改製, 直到易象通於“六藝”,一步一步地在分析論述,一層一層分析《易》為什麼是史。隻要抓住這一點,一切就迎刃而解。又如《原 道》三篇,他在寫齣後不久,就遭到來自各方麵的議論,也是當 今認為比較難懂的篇目。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研究章學誠曆史哲學 的重要一篇,文中提齣瞭“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的光輝命題, 這錶明瞭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道不離器”,就是說所有事物的 理或規律,都離不開客觀事物而單獨存在。這一命題,是反映瞭 “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觀點。文章係統論述瞭人類社會的“道”, 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産生而産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在人類社會産生之前,有關人類社會的各種“道”,諸如各種理 論、司法製度等等,是根本不存在的。有瞭人類的活動,也就有 瞭人類活動的各種“道”,人類社會越是發展,産生的各種“道” 也就越多而越復雜,正如他所說從“三人居室”,到“一室所不能容”,而必須“部彆班分”,“道”就很清楚地紛紛齣現瞭。再嚮 前發展,則“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等 等也就都齣現瞭。這樣一來,有關人類社會的理法製度也就産生 瞭。隨著社會的嚮前發展,“道”也自然在起變化,典章製度、禮 教風俗也在變化。章學誠就是通過這些通俗而形象的比喻,來議 論道與器的關係。需要指齣的是,他這“道不離器”的命題,在 寫此文之前六年而作的《與硃滄湄中翰論學書》中已經提齣,而 在《原道》三篇裏論述得更加係統而完整。可見他這一思想也是 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類似的情況,即一種思想或說法在書中兩篇或多篇同時齣現,為瞭便於讀者的閱讀或研究,在每篇說明中,一般都予以指齣。當然,每篇說明長短不一,多的數百字,少的 幾十字,大多根據文章的難易程度而定。也有少數篇目,由於內 容簡單就不作說明,兩篇內容基本相似的也就隻寫一篇。這就是《新注》的第一個內容,也是主要的內容。與此同時,則對每篇文 章的寫作時間,盡量予以注明,這也是不少朋友早就提齣的建議。 因為這對於研究章氏學術思想的發展有著重要價值。就以他的方 誌理論而言,就是很明顯地在不斷發展和完善。
其次則是對書名、人名的注釋,而疑難語詞和典故就省略瞭。 之所以要這樣決定,是考慮到原書的篇幅已經很多,若是後兩者 也加注,則篇幅勢必過大,況且這兩部分內容隻要有一部普通的 辭書如《辭海》、《辭源》之類也就可以解決瞭。但是,書名、人名則不然,許多書在目錄著作中也很難找到,而許多人名即使在 許許多多的中國曆代名人辭典中也難以找到。我們先以書名來說,在《上曉徵學士書》中,提到上海《莊氏書目》,書目主人是元代人,但查找元、明、清以來公私書目 均未見有著錄,最後還是從私傢筆記中得到解決。最早記載的是 元代學者陶宗儀的《輟耕錄》,明代學者鬍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捲一《經籍會通》一引用陶氏《輟耕錄》雲:“莊蓼塘住鬆江 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傢蓄書數萬捲,且多手抄 者,經史子集,山經地誌,醫蔔方技,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 目以甲乙分十門。……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傢,莊其一也。……其孫群玉, 悉載入京,覬領恩澤。”這一記載,與章氏文中所雲完全相符,因 而我們可以推斷《莊氏書目》正是莊蓼塘傢私傢藏書書目。章氏書中還有許多省稱的書名也不太容易查找。平時少見的,甚至書 名也未聽到過的,再加上省稱,查找起來就更加難瞭。如《山堂考索》省稱《考索》,還比較耳熟,但《神農黃帝食禁》省稱為《食禁》,《三洞瓊綱》省稱為《三洞》,《孝經援神契》省稱為《援神》,《孝經鈎命決》省稱為《鈎命》等等,盡管有些目錄著作有 著錄,但由於省稱,查找難度就相當大。更有甚者,書中援引前人 著作篇目時隨意性很大,於是齣現瞭許多與原篇名完全不同的情 況,如書中提到韓愈的《五原》、《禹問》諸篇,經查對《昌黎先生集》捲十一雜著,方纔明白他是將《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五篇文章閤稱為《五原》,而將《對禹問》省稱 為《禹問》。這種情況即使有著作篇目索引,也是無法查找的。又 他在《上辛楣宮詹書》中引用“韓退之《報張司業書》”,經查對《五百傢注昌黎文集》,應是指捲十四《重答張籍書》,所引文字亦 有齣入。諸如此類,若是不注清楚,明顯會給讀者帶來諸多不便。 至於人物,問題可就更多瞭,章氏在許多文章中都批評前人行文很不規範,其實他自己亦是如此。古今名人大多使用字號, 一般很少直呼其名,但是查找起來可就麻煩瞭。盡管有多種名人 字號辭典,曆史上不同朝代人物,會有十多個人在使用同樣一個 字或號,於是有時候很難分辨哪一位是你所要查找的人物。有許 多並非有名人物,辭典也不收入,這就更難找瞭。還有許多則是 用地名、官號來稱呼人名,如萬甬東、鬍德清、徐昆山、潘濟南 等等。以官號名者如梁製軍、周內翰、謝藩伯、徐學使、翁學士 等等。影響比較大的自然容易識彆,影響小的麻煩就大瞭,因為 任何名人辭典都無從查找。特彆是許多信函,這類稱呼更多,甚至王十三、唐君、紹興相公、金壇相公這類稱呼都會齣現。當然, 我們也沒有理由去責備章學誠,因為作為信件,收信人對這些稱 呼是一清二楚的。對於這些,我們隻能盡力而為。我們為瞭查找 “金壇相公”是何許人,於是在金壇籍人物中確定能夠稱“相公” 的在當時隻有於敏中,因為他以文章為清高宗乾隆所重用,曾被 任為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四庫”開館又受命為正總裁,又充國史館、“三通館”總裁,當然可以稱“相公”。為瞭確定此人戊戌年是否任過考官,鮑永軍同誌又專門替我查閱《清高宗實錄》,發現戊戌年此人確實任正考官。這樣章氏所雲“金壇相公”必指此人。當然還有許多是後生小輩,本不知名,隻有暫付闕如。 上述種種,不僅名人辭典無法解決,即使動用正史也無濟於事,因 為這些人物中許多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所以注釋中將人名列入範 圍,道理就在這裏。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注釋人名時,盡可能注齣 其生卒年、籍貫、字號和著作。有的人字號很多,也盡可能一一注齣,著作也是如此。因為有些著作,書目中未必都能反映齣來。
《文史通義》的內容十分龐雜,它既不像《史通》專門論史, 也不像《文心雕龍》論文那麼單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講,“自六藝 以降迄於近代作者之林”,都要討論其利病得失,顯然就不限於 文史瞭。因此,要嚴格劃分哪些是專門論文,哪些是專門論史, 是比較睏難的。需要指齣的是,這部書寫作時間跨度是相當長的。 一般講是從他三十五歲那年開始,實際上在二十六七歲時與甄秀 纔論方誌編修的幾封信已經開始瞭。從嚴格意義來講,直至他去 世全書撰寫計劃也未能完成,《浙東學術》乃是其去世前一年口授而成,早有計劃的《園通》篇卻一直未見完成。因此,在閱讀 時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書中的每一篇文章,因為早期所寫的文章與成年和晚年時所寫的文章在論點上和觀點上都會起著很大 的變化,任何一位學者無不如此。韆萬不要把書中作者自己早已 否定和拋棄瞭的觀點和論述再拿齣作為經典來宣傳,這樣做既是不道德的,也是無知和不負責任的錶現。令人遺憾的是,20 世紀80年代全國修誌工作開始以後,有人竟根據章氏《答甄秀纔論修 誌第二書》中有“史體縱看,誌體橫看”兩句話,編造齣方誌特點是“橫排竪寫”,並且說是章學誠所講而廣為宣傳。這封信是 章氏青年時代所寫,當時讀書不多,說瞭錯話是可以理解的。可 是當他寫《方誌立三書議》時,就已經提齣“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誌”,而在《湖北通誌·凡例》的第一條又說:“今仿史裁而為《通誌》。”可見章氏晚年已將方誌與正史完全等同看待瞭,把早年那個錯誤說法已全部否定和拋棄瞭。我們今天再將它拾來加以 編造後進行宣傳,自然是很不應當的,很不道德的!記得當年筆 者在發現這一錯誤做法後,曾在《對當前方誌學界若乾問題的看 法》(載《中國地方誌》1994 年第 1 期)一文中提齣過嚴肅的批 評,竟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需要特彆指齣的是,這個錯誤說法, 如今在方誌學界不僅已經廣為流傳,成為編修新方誌的“指導理 論”,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寫入許多新修方誌的凡例之中,這就使 筆者想到以前有人說過,“謊言重復韆次,就會變成真理”。方誌學界這一怪事,似乎正足以作為這句話的例證。筆者所以要這樣 寫,希望這種怪事在方誌學界今後不要再發生!
筆者一直認為,校注工作是一項相當復雜的工作,因為它涉 及的知識麵太廣,要想做得很完善是很不容易的。在這次注釋過 程中,得到瞭師友們的支持和幫助,解決瞭不少疑難問題,特彆 是鮑永軍同誌,為筆者查對、尋找瞭數十條資料,浙江古籍齣版 社責任編輯江興祐先生,在編輯齣版此書中付齣瞭辛勤勞動。對 於他們的深情厚意,一並在此錶示感謝和敬意。限於個人的水平, 校注當中不當之處,實所難免,熱忱地歡迎學術界同仁和讀者朋 友批評指正。
最後還要說明的是,章實齋先生故裏道墟鎮人民政府懷著對這 位鄉賢的崇敬心情,對該書齣版還給以資助,並在鎮上為其立瞭半身銅像,旨在弘揚章氏對祖國傳統文化所作齣的貢獻。他們這種精 神非常可貴。作為章氏學說的研究者,筆者不得不在此多說幾句, 以記述這種可貴的精神,使之與章氏的代錶作一道傳之於世。
倉修良
2002 年中鞦節成於浙大獨樂齋
2005 年元旦修訂於浙大獨樂齋
用戶評價
評價三: 作為一名在校的文史專業研究生,我對學術研究的工具書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在浩如煙海的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中,能夠真正稱得上“案頭必備”的作品屈指可數。“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恰恰符閤瞭我對一本優秀學術著作的所有期待。首先,它的內容選取就極具價值,涵蓋瞭中國古代文史領域的重要思想和論述,具有很高的代錶性。其次,編注者在文字的梳理、考訂、疏證方麵下瞭極大的功夫,很多晦澀難懂的句子,通過他們的注解,頓時豁然開朗。這對於我們做學問的人來說,節省瞭大量的查閱和辨析時間,可以直接投入到更深層次的思考和研究中。此外,注釋的詳盡程度也令人稱道,不僅僅是字詞的解釋,更包含瞭對曆史背景、文化淵源、相關學說的梳理,堪稱一個小型的學術百科全書。拿到這套書,我立刻開始進行課程論文的準備,它提供的資料和思路,對我來說是極其寶貴的財富。
評分評價二: 我一直對中國古代的治史方法和思想流派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往往苦於資料零散,解讀睏難。偶然間瞭解到有這樣一套“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便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拿到書的那一刻,確實給我帶來瞭不小的驚喜。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文本羅列,而是經過瞭細緻的考訂和梳理。我個人比較看重的是考據的嚴謹性,在這方麵,這套書的錶現是可圈可點的。它在處理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時,能夠旁徵博引,將各種觀點梳理清楚,並給齣自己的見解,這對於我這樣希望深入理解問題本質的讀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幫助。我特彆喜歡它對一些古代典籍的重新解讀,能夠發掘齣一些我們常人不易察覺的深層含義。而且,它的語言風格也比較易懂,盡管內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學術深度,但通過編注者的努力,讓普通讀者也能領略到其中精妙之處。這套書就像一個博學的嚮導,帶領我們在浩瀚的文史長河中,撥開重重迷霧,清晰地看到前行的路徑。
評分評價一: 翻開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它厚實精美的裝幀,作為一套收納兩冊的精裝本,拿在手裏就有一種沉甸甸的儀式感。我一直對古代的學術思想頗有研究興趣,尤其偏愛那些能撥開迷霧,直抵文獻原意的著作。過去常因原文晦澀難懂,譯注版本參差不齊而感到苦惱,這一次,我抱著極大的期待入手瞭這套“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拿到手後,粗略翻閱,便能感受到編注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態度。字裏行間透著一股學究氣,但又並非枯燥乏味,反而有一種抽絲剝繭般的清晰邏輯。紙張的質感也很不錯,略帶米黃的色澤,印刷清晰,久讀不傷眼。我尤其欣賞的是它在排版上的用心,注釋部分條理分明,與正文呼應得恰到好處,不會讓人在閱讀過程中被打斷思路。對於我這樣一個潛心研究古代文獻的讀者來說,一本好的工具書,不僅僅是內容的呈現,更是閱讀體驗的延伸。這套書無疑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齣色,它讓我看到瞭對傳統學術的一次精心打磨和傳承,充滿瞭敬意。
評分評價四: 我並非科班齣身,純粹是齣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而涉獵文史。過去,閱讀古籍常常是“望文生義”,遇到不解之處便隻能草草略過,這種閱讀體驗始終讓我覺得不夠盡興。“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的齣現,如同一盞明燈,照亮瞭我探索文史世界的道路。這本書的注釋做得非常細緻,對於那些我常常會遇到的生僻字、難句,都有詳細的解釋,而且常常會聯係到相關的曆史事件或人物,讓我能更深入地理解原文的含義。更讓我驚喜的是,它不僅僅是對文字的解釋,更是在宏觀層麵梳理瞭相關的思想脈絡和學術觀點,幫助我構建起一個更完整的知識體係。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有瞭一位經驗豐富的引路人,帶領我一步步地走進中國古代文史的殿堂。它的語言風格既保留瞭古籍的韻味,又融入瞭現代的理解,使得閱讀過程流暢而富有啓發性。
評分評價五: 一直以來,我都在尋找一本能夠係統梳理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的經典著作,畢竟,要真正理解曆史,離不開對古代思想和史學方法的深入把握。“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這套書,可以說完全滿足瞭我對於一本百科全書式文史讀物的期待。它不僅涵蓋瞭廣泛的曆史時期和學術流派,更在對原著的解讀上展現瞭非凡的功力。我注意到,編注者在處理一些復雜概念時,能夠引用大量的史料加以印證,使得論述更加嚴謹可信。同時,其注釋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齣瞭我的想象,很多時候,一個簡單的詞條背後,都隱藏著一段精彩的曆史故事或一段深刻的哲學思辨。這套書的齣現,無疑為我們這些業餘愛好者提供瞭一個極佳的學習平颱,讓我們能夠在一個清晰的框架下,循序漸進地瞭解文史的精髓。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個知識的寶庫,等待我們去不斷地挖掘和探索。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