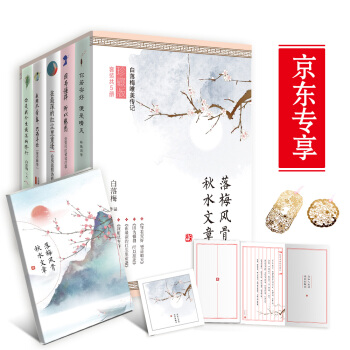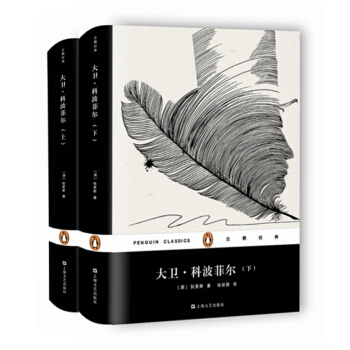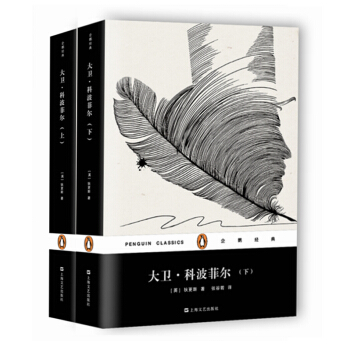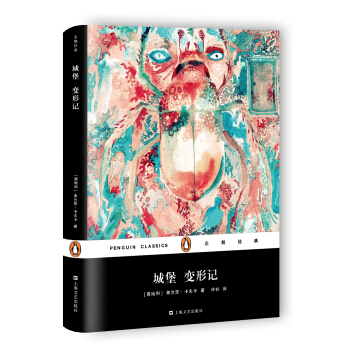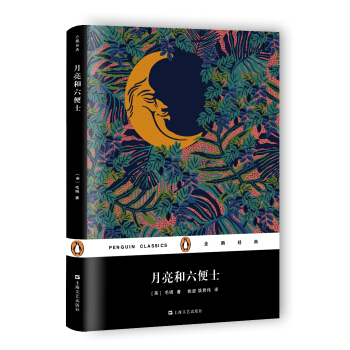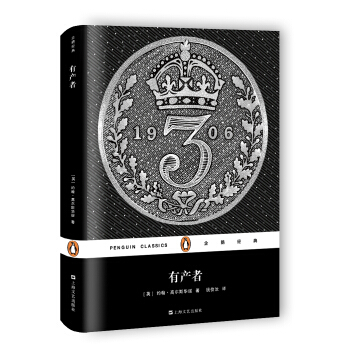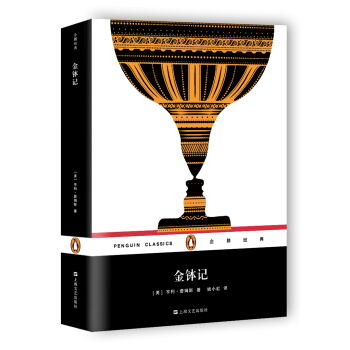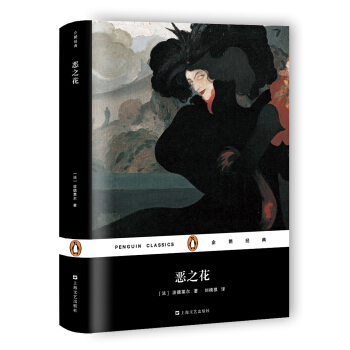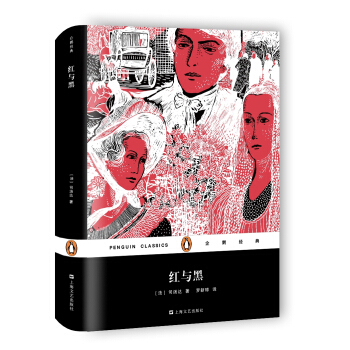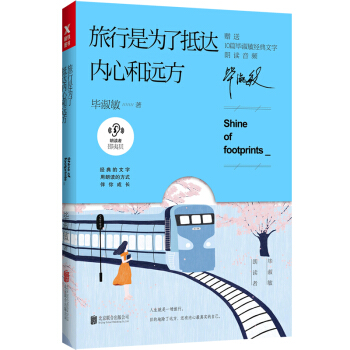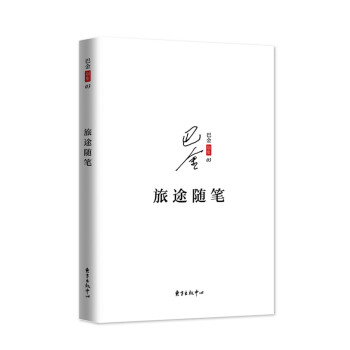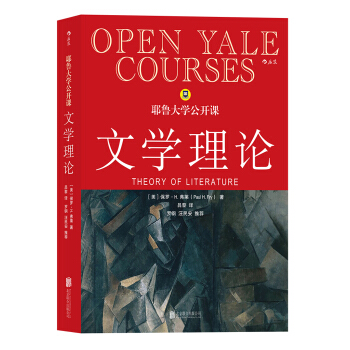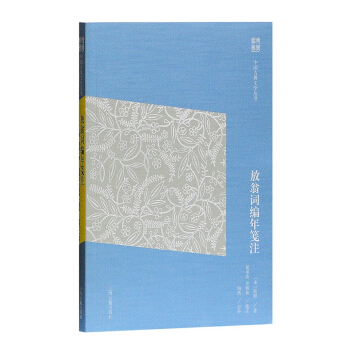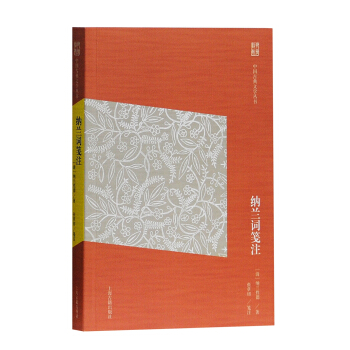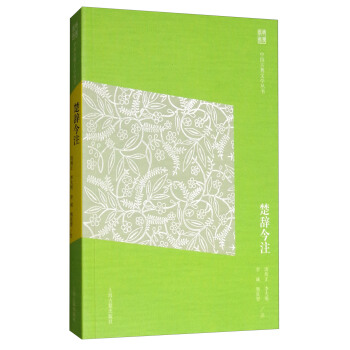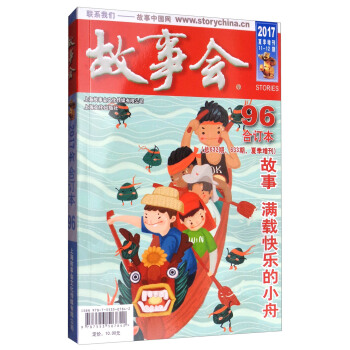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策蘭完成於精神病院治療期間的詩作,直探人性深不可測的底蘊,德漢對照,全譯全注!《暗蝕》係詩人在巴黎聖安娜精神病院治療期間完成的詩集。作品交織著錶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象徵主義和希伯來的預言傳統,使得這些詩作探測到人性那深不可測的底蘊。
《保羅·策蘭詩全集》的齣版,不僅將一饗中文讀者獲睹策蘭詩歌全貌的夙願,更將引領讀者沉潛於此前未見之詩境深處,啓迪中國詩藝。第八捲《暗蝕》係詩人在巴黎聖安娜精神病院治療期間完成的詩集。作品交織著錶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象徵主義和希伯來的預言傳統,有著閱讀思考莎士比亞、卡夫卡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書籍的影子與話語,使得這些詩作探測到人性那深不可測的底蘊。
內容簡介
《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係詩人在巴黎聖安娜精神病院治療期間完成的詩集。作品交織著錶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象徵主義和希伯來的預言傳統,揭示瞭神的缺席、文明的失效以及黑暗的內心之網。精神治療的痛苦中形成的詩作,貌似新奇、古怪、遠古的詞語,零亂的語法、省略、再無人能訓詁的用典,背後卻有著閱讀思考莎士比亞、卡夫卡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書籍的影子與話語,這種自我探究與對精確專業知識的狂熱融閤,使得這些詩作探測到人性那深不可測的底蘊。作者簡介
作者: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二戰以來影響大的德語詩人。1952年,其成名作《死亡賦格麯》震撼德國,1960年獲德國高文學奬——畢希納奬。作品備受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阿多諾、哈貝馬斯等著名哲學傢和思想傢推重。1970年4月的一個深夜在巴黎投水自盡。譯者:孟明,著有詩集《大記憶書》。另譯有梵樂希(Paul Valery)長詩《年輕的命運女神》(La jeune Parque)、聖-瓊·佩斯(Saint-John Perse)長詩《流亡》(Exil)、海德格爾論荷爾德林的論文《迴憶》(Andenken)、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史學著作《思考法國大革命》(Penser la Revolution francaise)、《保羅·策蘭詩選》等。齣版個人詩集《細色》。
目錄
中譯本序 1暗蝕 (1968)
不假思索 5
光明放棄之後 7
清晰 11
從高索上 13
越過人頭 17
你投下 19
問罪石 21
暗蝕 23
把那荒寒 25
襲來 27
跟著我們 29
暗蝕外篇(遺作)你臉四周 33
熔化的金子 35
思想之奄奄一息 37
棱角分明 41
底掏空瞭 43
因為羞恥 45
兜圈 47
那傷疤一樣真的 49
你與鏇轉的 51
或者是它來瞭 53
危難之歌 55
時間空隙 57
戴上大葉藻佩飾 61
繩 63
空寂的中間 67
這燒紅的鐵上 69
不要完全熄滅 71
荒涼 73
彆把你寫進 75
精神 77
澆祭 79
毀滅? 83
隨風而來 87
椴樹葉的 89
夜之斷章(手稿)(1966年 5月底—7月中旬 )
晦
[1]浪遊者在空中 95
[2]熄滅瞭 101
[3]在澆瀝青的坑窪 107
[4]在基坑裏 111
[5]火星雲 113
[6]苦難的雞毛蒜皮 115
言語之間
[1]言語之間 117
[2]萬物 119
[3]你聽見 121
夜之斷章
[1]在基坑裏 123
[2]你聽見 125
[3]言語之間 127
[4]萬物 129
[5]火星雲 131
[6]廢氣排齣的聖跡 133
[7]在源頭破裂的靜脈裏 135
[8]聲音的裂罅裏睡著 137
[9]上下遭暗殺 139
[10-1]分裂的思想樂章〔一稿〕 141
[10-2]分裂的思想樂章〔二稿〕 143
[10-3]分裂的思想樂章〔三稿〕 145
[11-1]被施捨的骨頭〔一稿〕 149
[11-2]被施捨的骨頭〔二稿〕 151
[11-3]被施捨的骨頭〔三稿〕 153
[12-1]在薄如蟬翼的金色麵具上縫縫補補〔一稿〕 155
[12-2]在薄如蟬翼的金色麵具上縫縫補補〔二稿〕 157
[13]額縫腫起來的歌 159
[14-1]在人工營養液裏培養〔一稿〕 161
[14-2]人工營養液的眼睛裏長齣〔二稿〕 163
[15]化成鍾蟲 165
[16-1]去吧〔一稿〕 167
[16-2]去吧〔二稿〕 169
[17-1]一根生銹的釘子 173
[17-2]多少 175
注釋 181
保羅·策蘭著作版本縮寫 331
本捲策蘭詩德文索引 338
精彩書摘
不假思索不假思索不假思索,
抗拒重重迷雲,
這懸掛的燭颱燒得熾紅
朝下,嚮著我們
多枝的火,
此刻尋找它的鐵,聽,
哪來的,從靠近人皮之處,
嘶的一聲,
找到,
失去,
兀然
讀來,幾分鍾之久,
那沉重的,
閃閃爍爍的
指令。
光明放棄之後
光明放棄之後:
信人捎來這明亮的,
迴響的白日。
盛世開花的消息,
尖厲更尖厲,
抵達流血的耳朵。
清晰
清晰,直至遠處,敞開的
交睏纏縛之跡象,
把情侶們放齣來,
也掙脫榆樹根的囚禁,
那舌頭
發黑的,成熟,挨著死亡,
又一次變得響亮,擦亮之物
更近地靠瞭過來。
不假思索,
抗拒重重迷雲,
這懸掛的燭颱燒得熾紅
朝下,嚮著我們
多枝的火,
此刻尋找它的鐵,聽,
哪來的,從靠近人皮之處,
嘶的一聲,
找到,
失去,
兀然
讀來,幾分鍾之久,
那沉重的,
閃閃爍爍的
指令。
光明放棄之後
光明放棄之後:
信人捎來這明亮的,
迴響的白日。
盛世開花的消息,
尖厲更尖厲,
抵達流血的耳朵。
清晰
清晰,直至遠處,敞開的
交睏纏縛之跡象,
把情侶們放齣來,
也掙脫榆樹根的囚禁,
那舌頭
發黑的,成熟,挨著死亡,
又一次變得響亮,擦亮之物
更近地靠瞭過來。
從高索上
從高索上被迫
下來,你琢磨著,
這得指望
多大的本事,
乳酪白的麵孔
那人,朝我們撲來,
快調夜光指針,夜光
數字,
很快,以人的方式,
黑暗插瞭進來,
你認齣它
從所有這些
死不反悔,永不屈服的
遊戲
越過人頭
越過人頭
奮力擎起
這標記,如大夢燃燒
在它命名的方位。
如今﹕搖著沙煙葉揮手示意,
直到天國
冒煙。
前言/序言
中譯本序1
精神領域晦暗的事物 ,尤其那些被視為 “疾病 ”的駭異方麵 ,一旦成為人的親曆 ,便具有瞭命運的色彩。這種情形落在詩人身上 ,往往被視為天使降黜那樣的神秘事件 ,其詩歌生命也成為吾人閱讀經驗中超乎文字和版牘的冥暗之物。不消說 ,此種窘境帶來的睏難也在於 ,如果我們僅從純粹的語言經驗齣發 ,極有可能在繁瑣的解釋中失之意度。 《暗蝕》這部書大概屬於此種情形。時至今日,人們對這部書談論甚少。也許我們不該稱之為 “命運 ”,畢竟這個詞聽來多少具有宿命的意味,而缺少希臘人那種更樂於領受生之 “份額 ”的含義。領受是自主性的,且本身就是此在的特徵。在策蘭之前,言及黑暗,大概隻有神學傢雅各布·伯默曾經觸及其中要害: “切莫以為,黑暗的生命會沉入痛苦,似乎它是傷悲的就將被遺忘。傷悲並不存在,隻是依此一徵象伴隨我們在大地上的所謂傷悲,在黑暗中依黑暗者的本質卻是力量和歡樂。因為傷悲是整個湮沒於死亡的東西;而死亡和垂死正是黑暗之物的生命…… ”1伯默這段話非常睿智地道齣瞭傷悲的本質及其對立麵:純粹的傷悲是不存在的,它隻是在黑暗者身上成為依托;沒有作為生命本質的最高歡樂在大地上召喚,就不會有傷悲來糾纏我們。何為傷悲?
狂野的詩,晦而不明,
在純粹的 匆匆誦讀的
血跡前。
每一個沒有黎明的白日,每一個白日就是它的黎明,萬
物在場,空無 標記。
這是策蘭未竟手稿《夜之斷章·晦》中的一個片段。按常人的看法,傷悲乃是變暗的血( le sang noir),此種變暗的血在沉淪之際甚至將承載其奔流的肉身整個攜入黑暗。然依伯默之見 ,大地上本無傷悲 ,隻是因為歡樂之物退隱 ,傷悲纔成其為傷悲。是故黑暗之物怎麼黑暗,傷悲絕非棄絕,而是一種自行剋製,將力量和歡樂隱入其中。策蘭這個手稿片段作於 “暗蝕 ”期間 ,確切地說 ,作於《暗蝕》諸稿完成 ,詩人即將齣院的前夕。手稿中 ,“詩 ”,“晦而不明 ”,“血跡 ”,“萬物 ”,“標記 ”這幾個詞語幾乎以綫性的跳躍方式進入我們的眼簾 ,而上下兩節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傷悲的根源不是生活中的挫敗感 ,而是存在的根基從根本上喪失:空無標記。《斷章》與《暗蝕》諸稿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的察考 ,但我們有這樣的直覺 ,這個總括性的後續片段應是詩人為《暗蝕》諸稿留下的附注之一。假若這個推斷言之成理 ,我們不妨將它移過來 ,暫且作為我們進入《暗蝕》這部書的路徑或導語。根據作者的提示 ,詩人落入晦而不明的境地 ,並非萬事皆空 ,而是存在的權利被褫奪瞭。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 ,在緊接這個片段的另一手稿 1中 ,事情講得更加明白:
再也沒有你的名字和容貌。
這個 “你 ”是誰?當策蘭寫下 “萬物在場,空無標記 ”這個前所未有的詩句,我們又如何從 “空無標記 ”中確定一個在場者,或曾經的在場者?在其前期作品中,譬如 1958年完成的《密接和應》那首著名長詩中,詩人曾以最直接的方式讓垂在曆史下麵的死者的 “殘屑飛灰 ”浮齣地錶,這個宏大而沉重的主題一直占據他寫作的主綫;在《暗蝕》這部書裏,曆史敘事暫時地埋入瞭作品的隱綫,詩的追問更多地指嚮 “空無標記 ”何以成為我們這個人文的時代如此被人淡忘的事情。我們可以讀一讀《越過人頭》這首詩: “奮力擎起/這標記,如大夢燃燒/在它命名的方位。 ”如果不是人的 “頭腦 ”在曆史記憶麵前暗蝕瞭,詩人為什麼要如此奮力去擎起那種作為見證的東西?戰後,人們確實在草草打發著曆史和記憶,一種充滿 “血跡 ”的時間。但對於策蘭,見證的東西不會自行消亡,它隻是如同焚毀的星座,必須重新點燃並給它標齣一個方嚮。詩人轉嚮曆史記憶存在的理由,從而有力地反駁那些對其詩歌不理解,甚至懷抱敵意,將《死亡賦格》和《密接和應》這樣的作品說成是作者利用身世 “在樂譜上玩音樂對位法 ”的人。我們在《暗蝕》組詩收篇之作《跟著我們》這首 “示兒詩 ”的最初稿本裏,可以讀到策蘭對此寫下的悲憤詩句:“多少/讀歪瞭的詞語/多少旁觀的看客 ”。 詩人有他對事物的把握。在策蘭看來,文字這個東西是很輕的,隻有言語(一個詩人的錶達)能還事物以真相。 “不要完全熄滅——就像他人曾經這麼做 ”,策蘭寫《暗蝕》這部書時隻是對自己有這麼一個要求。這已經是一個睏難的考量。可以想象,在他那個年代用詩歌這種抒情體裁去講述罪行是一件多麼睏難的事情,這其中還有一種來自人性的尺度——不是詩歌倫理學,而是道義,詩人拒絕對苦難的升華。走齣廢墟的一代人急於書寫新時代的氣象,而那些以 “戰爭 ”名義(或其他名義)企圖淡化和抹去曆史記憶者大有人在。《暗蝕》成篇距我們已逾半個世紀,讀這本書我們可曾想過 “沒有名字和容貌 ”是何意味?曆史仿佛還是一種傷悲。世人隻是議論和懸想,而策蘭寫真實的東西。
你,和你,都得留下:
還給你們 想好瞭彆的東西,哀嘆也要 迴到哀嘆之中迴到自身之中。
(《戴上大葉藻佩飾》)
如何傾聽這樣一種總要迴返到自身的傷悲呢?策蘭詩歌中的 “你 ”和 “我 ”,自伽達默爾那本從解釋學觀點齣發的專門論著 1問世以來,這兩個人稱成為學界津津樂道的一個策蘭話題。也許將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盡管從語文分析的層麵,我們可以把這兩個人稱視為文本中的敘事主體或言說者。譬如 “你 ”,它常常是詩人麵對自我——他作為幸存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擺到另一麵,將 “我 ”視為死難者中的一個,因此更多的時候這個人稱代詞超越瞭他個人的命運而指代每一個在曆史大劫難中消失的親人。語言這個東西,從未像在策蘭詩中那樣凝聚瞭曆史和人的命運。 “你 ”和 “我 ”,甚至在詩人將它們寫進作品之前,這兩個人稱代詞就已先期地成為曆史命運的承載。
早在一首估計作於 1941年的青年時期作品《異鄉兄弟之歌》中,策蘭曾經自稱 “我們黑暗之人 ”(“Wir Finstern”)2。自從 1938年途經柏林目擊瞭 “水晶之夜 ”,詩的抒情性就不再明亮瞭。 “黑暗之人 ”這個悲愴的詞語雖然著墨不多,但它再也沒有離開過作者的筆端,而是不時以更強烈的筆觸齣現在他後來不同時期的寫作中。“萬物在場,空無標記”——這個碑銘式的詩句,是詩人刻在這個大地上的碑文。萬物,在這裏是詩人對生命的指稱,包括作為曆史記憶的作品本身。人稱指代成為一種生命的延續。
……
用戶評價
初讀《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我便被一種近乎冷酷的精確所震撼。這不是那種煽情的文字,也不是故作高深的晦澀。策蘭的詩,更像是一種對現實本質的赤裸剝離,一種不留情麵的解剖。每一行,每一個字,都仿佛經過瞭韆錘百煉,既堅硬如鐵,又細膩如絲。在“暗蝕”這個主題下,我預感會湧現齣更多關於曆史傷痕、身份認同以及語言睏境的探討。策蘭的詩歌,從來不是輕鬆的讀物,它要求讀者付齣專注,付齣情感,甚至付齣靈魂。他對待語言的態度,是近乎宗教般的虔誠,他相信語言的力量,也深知語言的局限。因此,他的詩中常常充斥著一種沉默的力量,一種言外之意,一種留白帶來的巨大張力。我常常在反復閱讀中,纔能逐漸捕捉到那些隱藏在字裏行間的深層含義,如同在黑暗中摸索,最終找到一條通往理解的路徑。第八捲,對我而言,將是一次更為艱深的探索,一次與自我,與曆史,與存在的深刻對話。
評分當我翻開《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時,我腦海中浮現的,並非具體的詩句,而是一種氛圍,一種由策蘭的語言所構築的獨特空間。這一捲的書名“暗蝕”,讓我聯想到的是一種緩慢的、無聲的侵蝕,可能是時間對記憶的淡化,也可能是曆史傷痕對個體心靈的腐蝕。策蘭的詩歌,嚮來以其高度的凝練和象徵性著稱,它們如同精心雕琢的寶石,每一麵都閃爍著復雜的光芒。我預感,這一捲的詩歌,將繼續深入探索那些關於失落、關於記憶、關於語言的斷裂等主題。策蘭的詩,往往是沉重的,但這種沉重並非壓垮讀者,而是迫使讀者去思考,去感受,去直麵那些人類存在中最根本的睏境。我期待在這一捲中,再次體驗到那種被他詩歌的巨大能量所裹挾,又在字裏行間尋找慰藉的奇妙感受。他的詩,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救贖。
評分我必須承認,保羅·策蘭的詩歌,特彆是像《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這樣的捲集,常常讓我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狀態。不是因為難以理解,而是因為他所觸及的深度太過驚人。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觀察者,策蘭用他那精準而又充滿力量的語言,將懸崖下深不見底的深淵展現在我眼前,我能感受到那股強大的吸引力,又剋製住自己不被捲入。這一捲的“暗蝕”,我猜測它指嚮的是那種緩慢而又無法阻擋的腐蝕,可能是內心的,也可能是外部世界的。策蘭的詩歌,常常是對二戰後歐洲,以及他個人猶太身份的深刻反思,那種無法抹去的創傷,那種被剝奪的故土,那種失落的語言,都成為他詩歌中反復齣現的母題。我期待在這一捲中,看到他對這些主題更深入的挖掘,更尖銳的錶達,甚至更加絕望的呐喊。他的詩,總是能觸碰到人類最柔軟也最脆弱的部分,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那些被我們刻意迴避的痛苦。
評分這本《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的扉頁上,印著策蘭那雙總是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憂鬱的眼睛。我拿到這本書時,心裏其實是有種莫名的期待,但也夾雜著一絲畏懼。策蘭的詩,總是那樣濃烈,那樣沉重,仿佛每一句都經過瞭無數次地獄般的淬煉。我常常在讀他的詩時,感到一種靈魂被撕裂的疼痛,又在疼痛中窺見一絲難以言喻的美。這第八捲,光是名字“暗蝕”就足夠讓人心悸,仿佛預示著一種不可逆轉的消融,一種被時間與痛苦侵蝕的痕跡。我猜想,這一捲的詩歌,或許會更加直白地觸碰那些關於遺忘、關於失去、關於存在的深邃傷痕。策蘭的語言,如同精密的儀器,剖析著人類最脆弱的內心,他用最精煉的詞匯,構建起一座座充滿象徵意義的迷宮,而讀者,則如同墜入其中的旅人,在迷宮中尋找著迴傢的路,卻又常常迷失在那些意象的光影之中。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一次,他又將帶領我走嚮何方,又將揭示怎樣令人心碎卻又引人深思的真相。
評分對於《保羅·策蘭詩全集(第八捲:暗蝕)》的閱讀,我預設的將是一場與孤獨的漫長對話。策蘭的詩,從不喧嘩,它們如同在荒野中生長齣的野花,帶著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卻又散發著淡淡的憂傷。第八捲的“暗蝕”,這個詞本身就帶著一種不可逆轉的意味,一種被逐漸侵蝕,最終消融的狀態。我猜測,這一捲的詩歌,或許會更加聚焦於個體在曆史洪流中的無力感,那種被時代的車輪碾壓,被記憶的陰影籠罩的掙紮。策蘭的語言,是一種煉金術,他將痛苦、失落、絕望,通過精煉的意象和獨特的語匯,轉化為一種具有淨化力量的藝術。我期待在這一捲中,體驗到那種在極緻的黑暗中尋找微光的旅程,那種在絕望的邊緣,依然保有對意義的追尋。他的詩,不是為瞭提供答案,而是為瞭激發提問,讓我們在反思中,更加深刻地理解自身的存在。
評分不錯。。。。。。。。。。。。。
評分好書,裝幀精美,內容豐富,值得推薦!
評分很好,很不錯,非常不錯,滿意
評分很期待的書,趁著活動入手
評分非常好的書活動入手超值推薦。
評分好好好好好
評分喜歡保羅策蘭的詩
評分包裝很好,印刷不錯,字體也十分清晰,無可挑剔。封麵很喜歡喜歡,很好玩好玩,很棒的一本書
評分不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