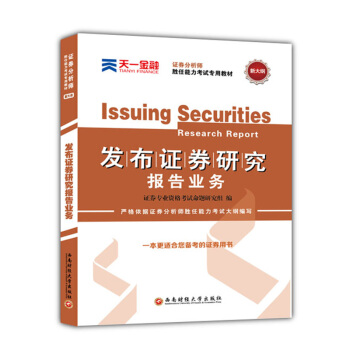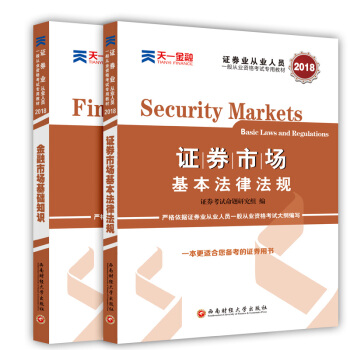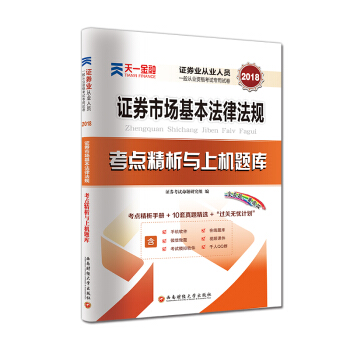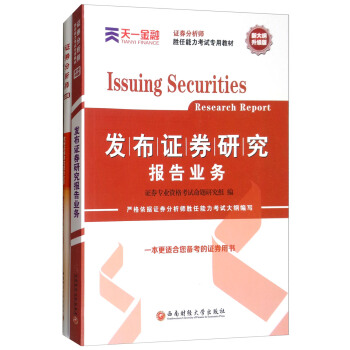![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The Big Questions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https://pic.tinynews.org/12379122/5b2c96e7Ne3b72b59.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昆,《魔鬼经济学》作者 史蒂芬·列维特推荐
2.本书推翻我们常见的思维错误,培养经济学思维,洞悉事件动机与本质,过更聪明的生活
3.《魔鬼经济学》系列*早成名就得益于本书作者的推荐。
4.逃出认知囚笼,以经济学方式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世界,打破惯性思维,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用完美的数学、经济学、物理学和哲学知识,**我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且充满刺激性和愉悦感的生活真相探秘之旅。
书中,兰兹伯格将自己幽默风趣、笔锋犀利和逻辑严密的写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一剖析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用浅显易懂的案例和直观生动的图示为我们讲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彩虹究竟有几种颜色? UFO是否存在?世界上*大的数字是多少?谷歌的名字从何而来?奥运会运动员与马戏团小丑的社会贡献度,孰大孰小?收入上的大赢家往往是幸福上的小赢家吗?为什么孩子的世界比成人的世界更公平?是否应该提倡环保和征收碳排放税?慈善捐款的数额多少为宜?我们应该为后代留下些什么?
常识有可能是错误的,公理往往不证自明;很多看似荒诞的行为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答,而许多我们自以为深信不疑的却完全站不住脚。这就是兰兹伯格眼中的真实世界和生活。
作者简介
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现任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兰兹伯格在《石板书》(Slate)网络杂志撰写的“每日经济学”专栏深受欢迎,他也应邀在《财富》《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价格理论与应用》《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列维特是这样评价兰兹伯格的:“他大胆、前卫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洞悉经济学常识,会改变我们看待日常生活的视角。”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写作此类经济学读物需要褪去其高深莫测的面纱,仅仅留下犀利的逻辑分析,当然或许还要加上点幽默和文采。
幸运的是,兰兹伯格的文章三者兼具。
目录
简介:旅程的开端 // V
为何要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涉及的内容
第一部分?现实与非现实
一?论万物 // 004
世间为何存在万物而不是空无一物?我给出的最好答案是:数学的存在是必然的,万物皆存在,因其皆由数学组成。这一部分会对人工智能有所涉猎。
二?经济模型的本质和目的 // 025
三?理查德·道金斯弄错了否认上帝的案例 // 033
为什么说道金斯反对智慧设计论的论点不可能是正确的——关于对上帝存在与否的论证另附有一部分数学分析。
第二部分?信念
四?白日梦信徒 // 048
人类大多数的信念都是欠考虑的,这是因为坚持错误的信念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会探讨一下我的这一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一话题:我们的信念和知识来自哪里。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病狂 / 054
色觉是如何运行的、声波和水波以及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之疯狂。
六?信徒信的是什么? // 067
人们对于宗教不加考虑的信念。为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是从内心深处信仰宗教的。
七?论显而易见的事物 // 083
人类关于自由意志、超感官知觉和来世的一些欠考虑的信念。
八?第欧根尼的噩梦 // 093
合理的分歧可能存在吗?如果你正与一个和你智商、见识不相上下的人争论,难道你不应该对对方的论点给予如同自己的论点那样同等程度的考量吗?我们一直对这件事情争执不下就表明我们实际上并不在乎到底什么是真的。
第三部分?知识
九?了解数学 // 110
我们的数学知识来自哪里,为什么逻辑和证据不足以说明问题。
十?未完的事情赫拉克勒斯和九头怪蛇(Hercules and the Hydra) // 122
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怪的寓言故事以及对大数字的探索。
十一?不完备的人类思维 // 133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以及该理论对人类知识的界限并未涉及的部分。
十二?逻辑规则和一头肥猪的故事 // 140
逻辑思维的力量,以及对数学理论中最违反直觉的定理进行探索。
十三?证据的规则 // 155
我们从证据中能学到的和不能学到的东西,另有对学前教育的价值以及网络色情对强奸犯的遏制作用进行探析。
十四?知识的界限 // 171
物理学告知或没有告知我们的那些可知或不可知的东西,另有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十五?未完成部分量子纠缠 // 179
量子世界的奇妙,以及它对博弈理论家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对与错
十六章?辨别是非 // 193
一些事关生死、对错的难题。
十七章?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 // 208
养成好行为的经验之谈
十八?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经济学家黄金准则的使用指南 // 217
把经验法则付诸实践
十九?不要做一个无良的人 // 233
以古福斯和嘉伦特探讨移民政策
二十?操场上的经济学家 // 244
我们关于市场和投票公平方面那些欠考虑的信念,以及于此形成对照的我们在操场上经过缜密思考的关于公平的信念。
二十一?未完成部分——让犹太法师来切分这块大饼 // 260
古老的犹太法师如何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学理论
第五部分?理性地生活
二十二?如何思考 // 275
让思路清晰的一些基本原则,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但也涉及算术、神经生物学、原罪以及如何避免胡说八道。
二十三?学什么给大学生的一些建议 // 300
给大学生的建议:远离英语系,选择哲学要慎重。顺道岔开讲了一下弗兰克·拉姆齐辉煌的一生。
附录 // 301
致谢 //315
精彩书摘
操场上的经济学家
我需要学到的东西早在幼儿园时就都学到了。
——罗伯特·弗尔杰姆(Robert Fulghum)
如同道德一样,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公平这个话题。于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哪些属于公平的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
每次当孩子哭喊着嚷嚷“这不公平”时,做父母的就得面对一个有关经济公正的问题。比如孩子会走过来问我们下棋的过程中改变游戏规则可不可以,或者有个孩子躺在沙盒里声称1/4的地盘都是他的,这时候该怎么办。作为父母,我们有很大一块内容是教育孩子做事要讲究公平公正。一旦谈到操场上怎么区分好行为和恶劣行为这个问题,每一位父母都成了专家。
虽说这种专长不可能被硬生生套用到市场或投票站,你的孩子指着你给他指导,而国会议员对你的期待则只是选票。因此,在思考对孩子行为的容忍程度时,你自然会想的更多更清楚些,而对于国会议员则不会如此。
我认为想要成为公平领域的专家,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切观察操场上那些你已经知道的有关公平的东西。就此精神,我列了几条每一位父母都应该明了的原则,我还会说下这些原则用在成年人世界中的一些看法。
1.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每当政治家提议要改革税法、使其更完善时,我们总能听到有关富人拥有的太多、穷人拥有的太少,让财富平均分配才是唯一公平的做法等此类说辞。在我看来,这套说辞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人会信这一套。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确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带女儿去操场玩耍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个父母会跟孩子说,如果谁的玩具比你的多,你就可以从他那拿走一些。我也从未听说哪个父母跟孩子说,如果你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的玩具多,你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政府,然后投票决定从多的那个人那儿拿走一些玩具。
父母当然鼓励孩子们相互分享,而且当他们表现的非常自私时,父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羞愧自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跟他们讲,如果碰到有的小孩比较自私,处理此类问题时要用某种合理的方式,断不可采用强制的办法获取。小孩子可以用甜言蜜语讨好下对方,或者讨价还价商量下,甚至孤立那个自私的孩子,但是绝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去抢或偷。同样,对于任何一个合法正当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帮你从他人那里窃取财富的权力。
对孩子来说这一点很简单,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就复杂多了。成人要面对的问题并不会出现在操场上。政府提供服务,而我们要为此交税。这样一来,关于“哪些人为哪些事情应该花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就会有颇多争议,需要商榷的空间不小,而从操场上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无法来指导我们。是不是富人在国防上就应该比穷人多交点钱呢?或许吧。那么多出多少呢?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征税仅仅是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话,这就和我们在操场上一直训导孩子不应该有的那些行为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孩子做出那样的行为,我怀疑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国会议员们这样做。把更重的税收负担转移给富人,或许理由充足,也可能毫无道理可言(在第22章中我会提到一些)。但是公平并不能成为这一行为的理由之一。
2. 做出什么选择,就怎样生活。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吃饭。他们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现在吃一份冰激凌或者饭后拿一份泡泡糖。艾利克斯选择吃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
艾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离开座位去拿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拿到了自己的泡泡糖,而艾利克斯手里什么都没有。这时候艾利克斯就开始不讲理地哭闹起来。对于任何一个局外的成年人来说,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艾利克斯没有理由这样;因为当时她和凯莱有同样的选择权,而且她还先拿到了自己选择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在成人的世界里也会发生。早年的时候,彼得和保罗都面临相同的机遇。彼得选择了一份工资有保障、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保罗选择了创业,日夜辛劳,而且回报不确定。30年后,彼得穷困潦倒,而保罗变得富有起来,彼得就谴责是社会体制造成了这种不平等。
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对泡泡糖的喜爱比对冰激凌的喜爱更令人羡慕,同样地,我也不想讨论保罗的选择是否在本质上比彼得的选择更加令人向往。关于彼得抱怨的那个造成最终结果的理由,我确实想要讨论一下。一个好的测验方法就是去找几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问问我们是否应该严肃对待这一争论。测试结果是,彼得的理由均被否定。
3. 不要心怀嫉妒。如果你有过同时给几个小孩分蛋糕的经历,你肯定会不断听到有人嚷嚷“这不公平!我这块蛋糕比较小!”如果你当时足够有耐心的话,你可能会向他们解释说那些心无旁骛、不在乎别人盘里蛋糕大小的孩子,会比那些常常分心、一心要和别人比较的孩子在生活中要过得更幸福。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开心,于是我们会告诉他们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那么这就值得开心。而如果别的孩子分到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得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比你得到的更少。下次如果你觉得某个同事不该提拔却被提拔时,不妨想想这句话。
4. 错错不会得对。如果你居住在美国的普通阶层社区里,那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每年要从你的腰包里拿走5块钱来资助像美国公共国家电台这样的节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辩护者们,都是成年人,他们习惯性地为这项收费辩解的理由就是其他项目会索取更多的钱;据他们的某些估计,政府在企业福利上索取的费用几乎是这个数目的两百多倍。也许这些辩护者的诉求目标是那些没有小孩的选民吧,要不然有哪个父母会接受小孩这样的说辞,例如“是的,我偷了曲奇饼,但是我知道别的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5. 不要多管闲事。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类在进行交易、易货贸易或兑换物品方面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8岁左右的儿童身上就能完全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在学校的跳蚤市场上交换贴画、卡片和瓶盖。
某个时候,有个孩子——我们叫她露西安——她想和班上的同学利兹进行交易,但是她发现利兹更愿意和三年级的艾米丽进行交易。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们希望露西安能够认识到她并不能强迫利兹和她进行交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强迫利兹和她交易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那种对他人及其苛求的孩子才会想要老师进行干涉,阻止利兹和“外人”进行交易。
对那些持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就是把国会当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层面的老师,要其来维持校园秩序,通过使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老师的特殊喜好或者某些特别行业的要求来行动——以此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此的话,任何一个八岁的小孩都会告诉你,这个做法糟透了。
6. 勇敢地对抗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近期估计,大约会有3000万—40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低工资竞争者的出现而失去工作。而换句话来说,这3000万—4000万的外来劳工所带来的低物价确是所有美国人要面临的一个前景。这样的话结果很好,尽管那6000万—8000万人本应该有更好的工资待遇。
包括布林德教授本人在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的工作机会被外包时,美国人整体上是最后的赢家——低物价带来的好处远远可以抵消低工资造成的损失。换句话来说,赢家可以多负担一些来补偿失利的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这样做呢?比如,为失业人士开一门再培训课程,是否就是一种道德要求,要由纳税人来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几乎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最终失利的人。[这一观察应该要归功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如果可以和邻居自由交易,我怀疑世上居然还有人没有从中获益。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交易,你还得自己种植食物、自己缝制衣服、靠奶奶的家庭食疗法治病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找到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也许你就不用那么依赖奶奶的鸡汤了,但是——尤其是考虑到她的高龄,你还得为此心存感激。
即便你因为自由贸易丢了工作,满心抱怨这种现象实在是有点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你才能从出生那天起就过上一种高水准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在自由贸易中遭受了负面影响,世界应该对你有所补偿,那么之前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时,你又为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呢?
不过,让我们暂且把这一观察结果放到一边,现在我们把一次新的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影响孤立起来看,我们姑且假定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我们的某些同胞会因为这些协定而受损,至少从狭义上讲,在贸易更加蓬勃发展的世界,他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不过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确实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亏欠这些同胞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扪心自问:如果有类似的情景,你的道德直觉会做出什么判断?假设多年以来你一直在当地的药店买洗发水,而有一天你发现在网上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洗发水。你选择从网上买洗发水是否就意味着你有义务向药店的药剂师做出补偿呢?如果你搬到了租金较低的公寓,你是否应该向原来的房东做出补偿呢?如果你选择了在麦当劳吃饭,你是否应该向隔壁餐馆的老板做出补偿呢?
或许会有些神秘莫测的道德哲学理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应该做出补偿,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理论。公共政策总不会为了推广那些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的道德观而制定吧?
那么,从道义上讲,失业的工人和被消费者抛弃的药剂师或者租客放弃的房东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你也许会说药剂师和房东一直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知道将要面对的状况,然而,举个例子来说,几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政策使得制造业的工人们看到被保护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工人们会学习一些别的技能,现在如果抽走政府层面的保护,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这次还是一样,我们还得问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景,他们的这种直觉和我们日常产生的直觉如何关联起来?几十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成为一种谋利的方式而风靡整个美国,而这些恶霸们积累了一些技能使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从中获得好处。如果我们严加治理,使得校园欺凌不再有利可图,那么我们还必须向恶霸们作出补偿吗?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使用了强制的手段(不管是直接使用还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方作出非自愿的牺牲而另一方得到财富。比如说,你本来可以从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人那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却强迫你花超过三倍的价钱从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这样你是被敲诈了。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让你自由地决定去哪里买东西,你应该为这种自由感到庆幸。而补偿之前那些剥削你的人就跟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无异。
7. 对不宽容回馈以宽容。我相信每个小孩都经历过被排斥的痛苦,而他们最终会明白这样的痛苦正是获得自由所要付出代价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生日聚会都会对你发出邀请。如果有人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不邀请你,那么你有权利去为此伤心,但是你没有权利擅自闯入会场捣乱。
大人们总是试图牢记这一原则,却又总是忘记。举一个程式化的例子:玛丽有一间空置的公寓,而乔正好在找住的地方。如果乔因为看不惯玛丽的种族、宗教或生活方式——甚至完全是出于恶意——他都可以自由地另寻他处。但是如果玛丽看不惯乔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是生活方式,法律要求她必须忍下这些疑虑把房子出租给乔。
或者:伯特想要雇一名办公室经理,而厄尼正好想要管理一间办公室。法律赋予了厄尼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一份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就可以选择不给其打工。法律对伯特的要求标准要更高一点:如果他公开表示这个职位不招阿尔巴尼亚人的话,那么他最好请个超厉害的律师。
这些不对等的要求违背了公平的最基本准则——即人人都应该被公平地对待,不能因为不相干的外界因素而改变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玛丽和乔——或者是伯特和厄尼——都有意成为一段商业关系的其中一方。那么为何在以反对歧视为宗旨的法律下却要承担不对等的责任呢?
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可以来阐释下这种伪善的情况。一个是原则性的:不对等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另一个是经验性的:一个体制今天可以限制你邻居的自由,明天它的权限就有可能扩展到你身上。今天政府要求玛丽去怎样选择租户,明日就可能要求乔去怎样选择出租公寓。今天他们要求伯特怎么去选一个办公室经理,明天就可能会要求厄尼怎样去选一份工作。如果厄尼拒绝了一个厄尔巴尼亚雇主的工作邀请,那么他是不是还得出具证明,说明他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地域歧视呢?
然而为什么就此打住了呢?如果反优先雇佣行动的原则一贯执行下去的话,它们最终会把控制的触角伸到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或者甚至于婚姻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那样一种超现实的未来世界里,如果你在选择爱人的时候还考虑种族因素的话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司法部的统计人员会详细检查你的约会模式,以确保你正在社会的各阶层进行合理的抽样选择。当你要定下终身大事的时候,你还得要证明你所选择的配偶客观上比其他任何候选项更有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一旦这种系统进入应用,它就会被扩展(就如同反优先雇佣行动那样)到性别和种族方面。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玛丽可能会被传唤到法庭受审,原因只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男人,而此时有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女性更适合做配偶。
如果说这个设想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的话,你别忘了今日的反优先雇佣行动在几年前也是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这听起来就像一场噩梦,那么请记住玛丽和伯特的噩梦已经成了现实。
对白人男性求职者来说,反优先雇佣行动已经被认为不公平,对那些无辜的被认定为犯了种族歧视罪的企业老板们不公平,甚至对他的目标收益人群来说也不公平。这一行动的部分或全部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是这些内容都和我正讨论的议题不相干。我认为反优先雇佣行动对偏执的人不公平,就算是偏执狂也有权受到公平对待。就算一个孩子纯粹是出于恶意排斥你,他也有权拒绝你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你我都不赞成偏执的行为。但是主张宽容的个人美德和多元化的公众美德要求我们支持那些我们并不赞成的东西。让人们对不宽容的行为报以宽容的想法有点自相矛盾,但其他有些不错的想法也都是这样,比如那些支持政府审查制度的人享有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和宽容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对于我们拍手称快的事情和那些打心底里冒犯我们的事情不能一视同仁的话,那么他们就毫无意义。
8. 不要惩罚无辜的人。种族性的规定和反优先雇佣行动自有人为其辩护,部分原因是:这是对奴隶制遗留问题的一种公平的补偿。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的成本费用大部分是由白人子孙来承担,而他们的祖先是在奴隶制被废除很久之后才来到了美国。种族优先权并不是消除奴隶制残余影响的办法;它只是简单地把影响从一群无辜者身上转移到了另一群无辜者的身上。
当我在杜克大学那间挤满了本科生的屋子里发表这样的论点时,一个学生经过沉思,提出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他认为即使是一个二十世纪才来美国的移民家庭也有可能受益(以牺牲黑人为代价),因为后来有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规《吉姆克劳法》。
但是话说回来,《吉姆克劳法》(和其他种隔离措施一样)是种族间进行贸易的障碍,而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障碍从总体上来说对双方都不利。白人被劝阻不要去服务黑人顾客、光顾黑人商店、雇用黑人员工或者为黑人老板打工,这些白人也都是《吉姆克劳法》的受害者,就和黑人是一样的。
换一种方式来讨论可能是一种糟糕的经济学理论,也可能被认为是种族歧视。《吉姆克劳法》阻止黑人去和白人做生意,同样也阻止白人去和黑人做生意。剥夺和白人做生意的权利就是一种压迫,而剥夺和黑人做生意的权利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吗,有谁会这样想?
诚然,《吉姆克劳法》是白人选民制定的,因此人们会倾向于得出结论认为该法律总体上是对白人有利。但是这种逻辑需要建立在这样一种民主理论上,它与所有的经验都不一致。白糖补贴、烟草补贴和石油补贴是由所有的美国选民制定的,而且理智的人们没有一个会认为这些法案对所有的美国人有利。相反,这些法案只对一小部分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有利,他们利用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去利用大众来获利。
《吉姆克劳法》造成了贸易壁垒,的确如此。不过这一法规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它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侮辱性的规定,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饮用水隔离到不平等的公立学校的隔离等。因此,这套法规给黑人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给白人造成的伤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事实远不致于说白人就是这一法规的受益人,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就该承担起赔偿黑人因《吉姆克劳法》而过上悲惨生活的责任。
这里似乎要引发一场政治争议,但是如果我们把操场上的那一套标准用到这里的话,争议点会迎刃而解。在那里,如果约翰尼偷走了玛丽的沙桶,没有人会想到强制无辜的博比向玛丽做出赔偿。
9. 对自愿者不要得寸进尺。当食品杂货店里的莴苣价格卖得高时,顾客就会咒骂杂货店老板,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咒骂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因为朋友和邻居根本不会卖莴苣给他们。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些满腹牢骚的顾客去自己开个杂货店,然后出售低价食品。那些一步路都不愿意多走的家伙却要求杂货店老板再多走一英里去给他们采购更便宜的食品。
同样地,工人们对于付给他们低工资的老板总是怨声载道,却不会去诅咒其他那些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工资的老板(或者不是老板的人)。这一点不仅在道义上毫无意义,在经济学上也不划算。一个老板要雇用工人——而且是低薪雇用——从市场上带走了几个工人,这就会迫使其他雇主之间相互竞争去抢夺剩下的那些工人——由此工资就会涨上去,而不是下降。如果你要找一份高薪的工作,那么开出低工资的老板是提供了解决办法,而不是制造了麻烦。
我们再来考虑下房东玛丽,她不愿意把房子租给那些她不喜欢的人。也许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然而,当玛丽修建了一栋公寓楼而不愿意出租给你时,她仍给你带来了一点点好处:通过招揽租客,从而别的公寓楼会产生闲置的房间,这样住房市场的压力会减少那么一点点。拿这点和我可能给你带来的好处进行对比。我并没有计划要进入房地产市场。就像玛丽不会把房子出租给你一样,我也不会把房间出租给你;我甚至都没有可供出租给你的房产。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玛丽拒绝租房给你,这已经给你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我却是完全无辜的。这样听起来实在令人抓狂。
一方面怨恨杂货店老板、雇主老板或是房东,然而另一方面却无视世界上其他那些不能给你提供更便宜的莴苣、一份高薪工作的人,这其实至少可以说是一种相对没什么害处、但却有多重道德标准的做法。但是,人们道德矛盾的倾向在别处也有体现,而且有时候还会很激烈。每6个月左右,在自然灾害导致受灾区常用资源匮乏时,你就会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抨击那些把一加仑水卖到7美元或者肆意哄抬某些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无良商家。通常,对于此类事件,新闻主播和政治家们总是义正言辞,非常愤慨,但是我从来没见他们去运水到灾区来,以每加仑7美元或者其他任何价格提供给灾民。如果那些不道德的奸商有责任把水价降到每加仑7美元以下,那么新闻主播为什么不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同样地,小企业的老板被要求必须给残障人士工作机会。如果这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的话——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一种必须聘请残障人士的道义责任——那么其他人也应该被要求去开办小企业来招聘残障人士。毕竟,当道德责任存在时,它一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要么它对所有人都有要求,要么不对任何人有要求。
有时候——也不会过于频繁,只是偶尔——操场上会有孩子自愿去清扫垃圾。我们通常的回应是不会要求这个孩子去清理整个操场。杂货店老板卖给你莴苣,只是价格略高;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只是租客不是你;一个公司的老板没有直接聘用你而是雇了你的邻居,但是却改善了你的就业前景——所有这些人都给你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益处,就像那个在操场上捡起几张糖果包装纸的小孩。你可以希望他们为你做的更多,但是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却是极其无礼取闹。
前言/序言
旅程的开端
我非常喜欢人们向我讲述他们的童年时光,但是他们得说快点儿,要不然我就耐不住向他们讲我的童年了。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入幼儿园的第一天,罗森伯格太太就跟我们交代了一天的日程安排:午休时间、游戏时间和点心时间,并且每天下午两点,要集体“穿过大厅”。
她并没有说我们要到哪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也不记得我对此产生过好奇。事实上,不会对事物产生好奇这一点在我的整个小学时代一直困扰着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关于纺织业一切能够了解到的知识,而我却从来没问过纺织到底是什么,而且也从来没有想过纺织必须得是点什么。如果有人非得让我猜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说纺织就是一种类似油毡的东西,但我还从来没有猜过这个地步,或者想都没想过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猜想。
反正一到下午两点,我们就会绕着教室外面排好队跟着罗森伯格太太穿过大厅。一开始我还高高兴兴地让自己跟上大家的步伐,直到我们转了个弯,我见到了我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五年中最不祥的东西:墙上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很闪亮,你绝对不会怀疑它的重要性——上面有一排字:安全出口(FIRE EXIT),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箭头指向我们正在走的那个方向。
那会儿我还完全不知道“出口”(EXIT)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确定知道火(FIRE)是什么,要想让我跟着罗森伯格太太或者任何人再往前走,门儿都没有。我掉头回了教室,坐在教室里安静地等待大批焚烧人体消息的到来。
我不认为我曾向他人提出过警告。大概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来幼儿园之前没有学会认字是他们自己的错。或许我那时候想最好还是不要引起他人对我的注意,以免那股控制住罗森伯格太太的力量会来找我,把我也扔到大火里。我不记得当时我有多焦虑不安。我只是平静地坐在教室里,即便他们都安全返回时,我也不认为我当时感到特别惊诧或好奇,我并不好奇他们是如何躲过了这场灾难。
从那一天起,两点钟,其他人照旧排队穿过大厅,而我则安静地坐在课桌旁等待。罗森伯格太太对此从来没说过什么。她和班上的其他同学照例穿过那个大厅,一会又回到教室。我一直坚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被烧成灰烬。从那时起,我确实开始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
这是我在幼儿园的大谜团之一。第二个大谜团是: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罗森伯格太太就会派一个同学带我去上厕所。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单独挑出来带着上厕所;可以肯定的是,班上的其他孩子都和我一样家境贫寒。也许他们都是金属制造的机器人,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能穿过火海还能活着回来。
有一天,罗森伯格太太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跟我们一起穿过那个大厅呢?”如果跟她说是因为我害怕火,我会觉得非常难为情,于是我就说“只是不喜欢而已”。就像其他伟大的幼儿园老师惯常的做法那样,她用饱含温柔和坚定的语气跟我说:“那么,以后你必须得去。”然后我回答:“好的。”
那晚我并没有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没有感到惊慌,也没有计划逃跑。带着一种禅意的宁静,我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将和班上的同学一起穿过那个大厅,然后彼此就再也杳无音信;其他人已经成功地来来回回走了十几遭这件事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意识,不能作为相关的数据说明什么。明天我们将一同穿过那个大厅,然后我们再也不会回来。我准备顺其自然了。
但是第二天快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我内心的平静开始消散。我得提起勇气站进队列里,因为罗森伯格太太说了我必须得这样做,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我们穿过了大厅,走过了那个清晰的标志,它直指我们的死亡之路。但是——你应该预料到了——旅程结束时,并没有出现大火。那里有个卫生间!
就是在那个卫生间里,我得到了一生中最为惊人的知识上的启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谜团:同学们每天排队去的是哪里?还有为什么是我,而且只有我每天被护送去上厕所?最后证明两个谜团有着恰好一模一样的答案。就在那一刻,我了解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复杂交织的地方,每一个事物都会触动其他事物,复杂中透露着美丽,我还知道了真正的了解得靠亲眼看见万物是怎么整合为一体的才行。
当我跟罗森伯格太太说“我只是不喜欢”穿过那个大厅时,我相信她感觉到了我的尴尬,而且我还相信她以为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卫生间本身。可怜的罗森伯格太太不会像我一样,她绝对了解不到真理。
那天之后,我再也不为那个出口标志担忧了。生命太过丰富精彩,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上面,比如为什么有人把这个误导人的标志贴到墙上,或者纺织是什么。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下定决心要把注意力放在整体上面,着眼大局,但十岁的时候我就非常肯定将会投身于哲学研究。对我来说,其他道路仿佛都是险境丛生。是的,你可以选择去建造桥梁、写诗或治疗癌症救死扶伤,但是如果不把生命浸润在哲学的海洋中,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桥梁、诗作或者医学突破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呢?
几年后,有两个令我惊诧的发现使我偏离了既定的生涯:其一,所有的道路其实都是险境丛生,充满风险。要是你把一生都投入到哲学研究,而在九十二岁高龄时突然发现你本应该去上医学院怎么办?其二,为什么要穷尽五十多年深入研究,就为了看看某个癌症疗法是否可行?
受着这两个发现的影响,我之前立下的志向受到了不小的冲撞,之后我混沌了几年,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小书,名字叫作《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Space and Time in Special Relativity),作者是康奈尔大学的大卫·默民教授(N. David Mermin),然后我发现我有可能进行思考。我指的是真正的思考。默民教授的阐述非常清晰,而且行文出彩,正是他向我展示了如何以一两个简单清晰的假设开始,然后梳理出它们对应的逻辑结论,进而建立起关于时空本质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都非常壮观,出人意料。物理学专业的大一新生上课都会用到这本教材,但是对于一个准大学生来说,这些内容还是相当令我惊奇的。
许多年后,我开始思考人口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思考“对整个世界来说,拥有‘适量数目’的人口意味着什么?”,例如,“居住着十亿非常幸福的人的世界”和“承载着一百亿不那么幸福的人类的世界”哪一个更好,我们是否应该力求幸福总数的最大化(暂且不论这个幸福意味着什么),或者幸福平均值最大化,又或者某个别的值的最大化。
我先找了几个简单清晰的假设作为开端,这几个假设我猜想每个人应该都没有异议,然后我梳理出它们的逻辑结论。尽管这个问题我只解决了一小部分,但是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我推理出的那套方程式恰好和默民教授在他另一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中推导出的方程式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和他研究的问题在结构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我把我的论文复印了一份给默民教授送去,还附上了一封说明信,感谢他一直以来给我的启发,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他那封亲切的回复。
尽管默民教授的书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研究物理学;我一直怀疑,我不是那种能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前坐得住的人。因此我上了大学,在几个专业(英语、历史、政治学)间来回踌躇,直到有一天,一个在数学方面极有天赋的朋友鲍勃·海曼(Bob Hyman)来找我,他说无穷集有无限种形式,规模各有不同,有一些比另一些要大得多。这话听起来特别奇怪也特别有趣,于是我还得去了解好多相关知识。在鲍勃的推荐下,我修了一门集合论的课,并因此爱上了数学。
我热爱数学和热爱那本相对论的书的理由是一样的——结构优美,逻辑清晰,包含的真理深奥而又无可争议。从那时候起,我修了好多数学课程,以至于最后疏忽了大学对于课程分布的要求,最后没能拿到学位。
所幸的是,当我认清我不可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时,我已经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同样幸运的是,在芝加哥大学没有人曾问起我是否真的读完了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数学期间,我偶然结识了一帮活力满满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每日的午餐自由知识竞赛。这不免让人想起了阿尔冈昆圆桌午餐会,不仅有智慧的火花,还有令人醍醐灌顶的观点。我了解到,经济学家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从简单的假设开始,然后通过逻辑手段步步推进,最后得到出人意料的结论。我也想要学一下这些手段,这些朋友就很有耐心地教我,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令我又高兴又吃惊的是,那些一起午餐的同伴不仅精力充沛,大脑聪明,风趣幽默,而且都对真理有一股强烈的热情,所有这些特点和我刚来到研究生院时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这30年来,我一直把这些同伴看作我幸福生活中最大的福分。
后来我继续从事数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偶尔也会涉猎一点点物理学,即便如此,我从来没有忽略过对于那些大的哲学问题的痴迷:宇宙从何而来?世上为何存在万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知识如何能被人类触及?用什么可以来证明人的信念?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和善恶?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关于这些问题,哲学家有一套很有用的思维方法,但是即便不是哲学家,人们也自有办法。物理学家也能知道一些关于宇宙起源的东西;数学家能够了解到一些现实中运行着的模式;经济学家能够知晓我们的选择如何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和辨别是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些学科为研究那些哲学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当一个拿着锤子的人跟你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的时候,你应该怀疑他的客观性。当一个对数学和经济学都有涉猎的人跟你说哲学问题可以通过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时,你就可以和他做出一模一样的反应。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我被数学和经济学吸引到是因为它们可以阐明那些大问题。我看到了钉子,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锤子。
在这本书中,我将会和大家分享下我关于现实本质的看法,知识的基础以及伦理学的根基。我不敢说我所有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是我会一一解释下为什么我认为它们是合理的——或者为什么它们比其他看法更有可能是对的。(尽管最后我有可能会被其他新的观点说服。)
在讲述这些话题的过程中,我也会岔开去阐述一点点科学、数学以及经济学的东西——有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好玩。因此我们将会学习到一点关于大数字的知识、色觉的运行机制、海森堡不确定原理的真正含义、犹太教法典《塔木德》中对破产财产如何分割的指示等其他很多内容。
如同我们对儿时光景的记忆那样,我对哲学的漫谈也是没个头尾,没有顺序。有时候岔开话题后会再回到主题;有时候我会继续去讲点新的东西。
独到的见解乃为世间罕见之物,而我的书中也委实不多。书中提到的那些思想,其他人已早有涉猎,或许还有驳斥,但是我希望我的讲述方式能够激起你的兴趣,对你形成一定的挑战,如此我们在这本书中就能得到极大享受。
用户评价
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又能深入人心的作者充满敬意。这本书的书名,尤其是“为什么常识会撒谎”这个副标题,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生活中无数个“照着做却失败了”的场景,让我不禁怀疑,那些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金玉良言”,真的适合每一个情境吗?我深信,经济学并非象牙塔里的高深学问,它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塑造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浅显的“常识”层面,这让我觉得,我们可能错过了很多更深层次的洞察。这本书承诺要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这让我眼前一亮。我期待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更是对这些理论背后哲学思考的挖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希望作者能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引导我们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常识”,揭示它们在特定情境下的局限性,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源。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正是当下社会所稀缺的,也是我渴望从中学习和汲取的。
评分我拿到这本书,第一眼就被它的书名所吸引:《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这几个字瞬间击中了我内心深处一直以来存在的疑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总是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看似“理所当然”的经济现象,但深入思考后,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比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量入为出”,但现代金融体系却鼓励消费和信贷,这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矛盾?再比如,我们都知道“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但为什么有时候市场上的某些商品价格却显得如此“不讲道理”?这本书所承诺的“The Big Questions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让我看到了它不仅仅是一本纯粹的经济学著作,更是一次对我们认知世界方式的深刻反思。我期待作者能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剖析那些根深蒂固的“常识”,揭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局限性,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位循循善诱的智者,引领我走出思维的误区,用更批判、更深入的眼光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充满魅力的经济世界,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就像是一声响亮的号角,吹散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笼罩的经济学迷雾。我一直觉得,经济学不应该只是枯燥的公式和晦涩的理论,它应该是解释我们生活,帮助我们做出更好决策的实用工具。然而,现实往往是,我们听信了无数“常识”,却在实际操作中碰壁。比如,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告知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有时候,那些后起之秀却能弯道超车?为什么我们认为“价高者得”是市场规律,但很多时候,低价策略反而能占领市场?这种“常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我感到困惑。这本书承诺的“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更是让我眼前一亮。我期待它能不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深入到经济行为背后的哲学思考,去探讨人类的动机、决策的本质,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我希望作者能够用生动有趣的例子,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经济学理论,转化成易于理解和应用的生活智慧,帮助我们识别那些“会撒谎的常识”,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判断和选择。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人,那种带着点玩味和挑衅意味的标题,立刻点燃了我对“反常识”这个概念的好奇心。作为一名对经济学并非专业出身,但却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充满疑问的普通读者,我常常觉得教科书里那些看似严谨的理论,在现实世界里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比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付出,结果却事倍功半?为什么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道理,在现实中却屡屡失效?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书,能以一种更接地气、更具洞察力的方式,来剖析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相。这本书的出现,仿佛是一盏明灯,预示着我将踏上一段颠覆固有认知、探索经济学深层逻辑的旅程。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挑战那些根深蒂固的“常识”,揭示它们为何会成为误导我们的陷阱。这种“反常识”的视角,让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一本经济学读物,更像是一次关于思维方式的重塑。它承诺了要探讨那些“大问题”,解决那些“哲学难题”,这听起来就充满了挑战性和启发性,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第一页,看看作者是如何一步步拆解这些看似复杂实则迷人的经济学悖论的。
评分拿到这本书,首先就被它的书名所吸引——《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作为一个对经济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常常被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弄得云里雾里的人来说,这个书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现象,在深入探究后,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逻辑?比如,为什么普遍认为勤俭节约是美德,但在某些宏观经济环境下,过度储蓄反而可能拖累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免费”是最好的,但很多时候,“免费”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代价?这本书承诺要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相信,经济学本质上是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究,而哲学则是对这些规律背后更深层意义的追问。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提供经济学上的洞见,更能引发我们对事物本质的思考。我希望作者能以一种颠覆性的视角,引导读者跳出思维定势,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审视我们周围的经济世界,去发现那些被“常识”所掩盖的真相。
评分物流超快,书本质量很好,下次再来,发票服务也很到位,就喜欢在京东买东西
评分大小宝都喜欢,送货快,价格优,忍不住买买买,在京东买食品、饮料、日用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给家里人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非常感谢京东优惠的购物政策、快速的送件速度、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我们买起物品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评分一直看好这套书,618优惠购入,买书就喜欢京东,正版优惠物流快。
评分这两套书的经济学知识,通俗易懂,老少咸宜。
评分618真开森,又是活动又是券的,书确定是正版,就是侧页,切得有点不齐,看在六折的份上,算了吧。运输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磕碰,书的四角都很好,没有褶皱什么的。
评分书挺好看的,单位很多人喜欢
评分一直在京东买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书看得晚了,过了售后时间…我是不是得怀疑是否正品…………
评分还算不错吧 挺好 还没看呢 棒棒的
评分很久没有看纸质书了,一直都是用手机看小说的,太伤眼睛了,所以想买点纸质书看看。正好看到京东图书有活动,果断入手。这次买的书偏经济类,也是自己一直想买的,书的质量很好,印刷也很清晰,也没有什么难闻的味道,很喜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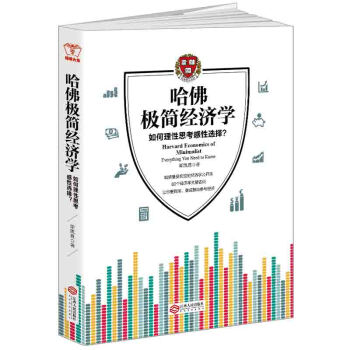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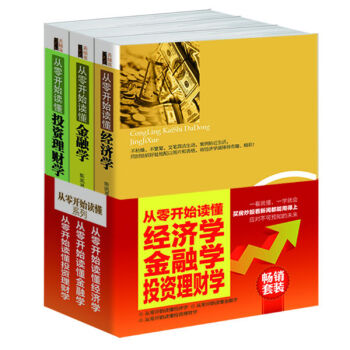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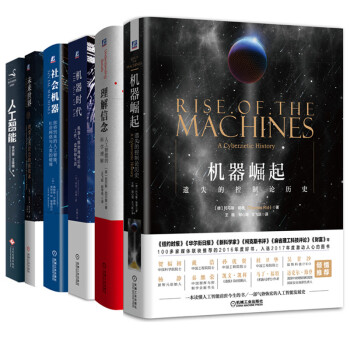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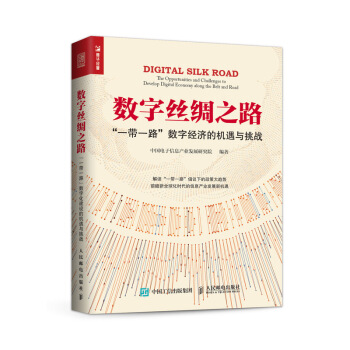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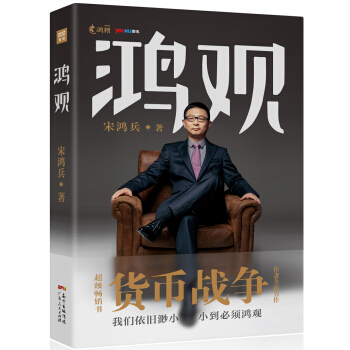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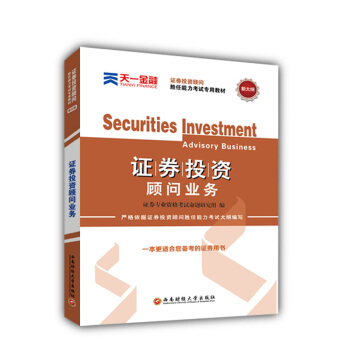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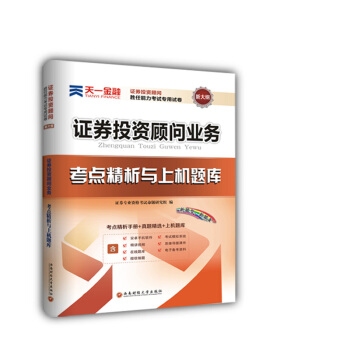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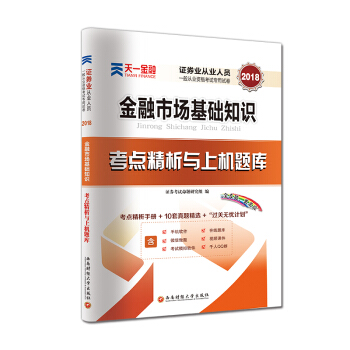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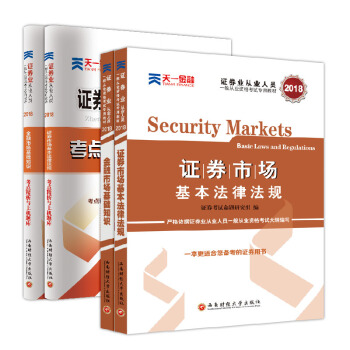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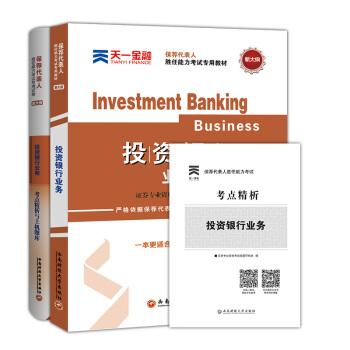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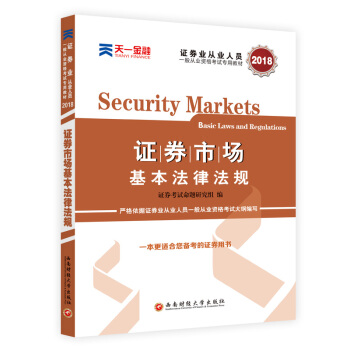
![证券从业资格证考试2018天一官方教材+真题试卷题库:证券投资顾问胜任能力(投资顾问业务 套装共2册) [Securities Investment Advisory Busines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57209/5b239edbN998b88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