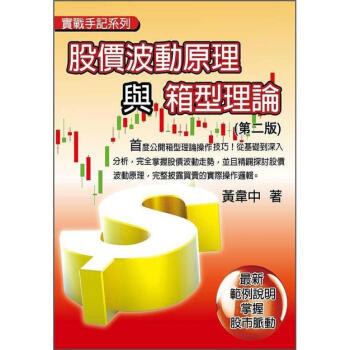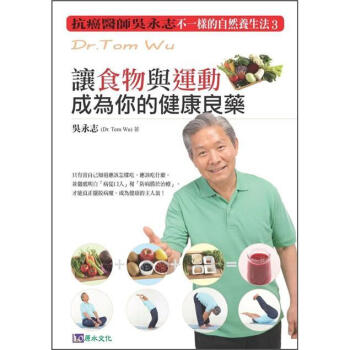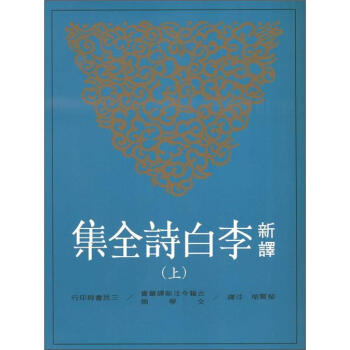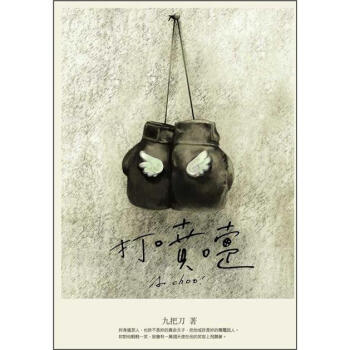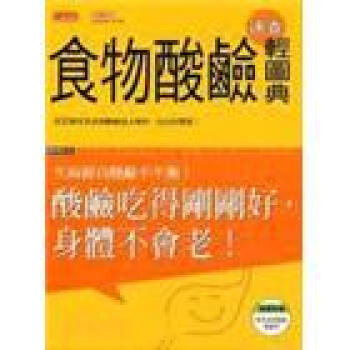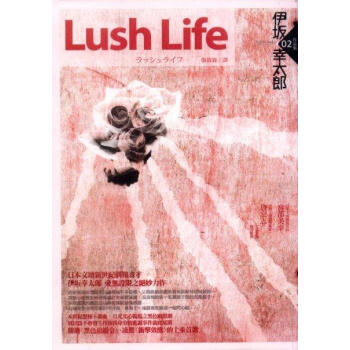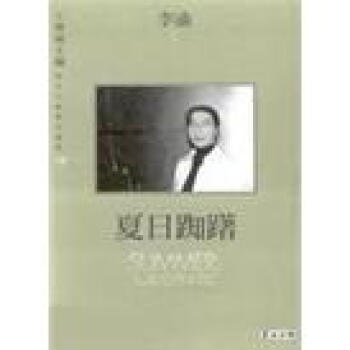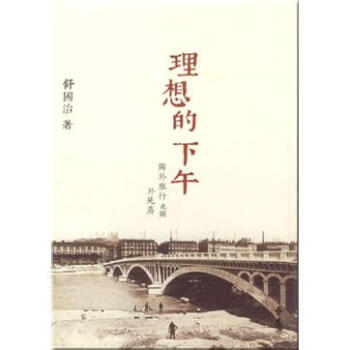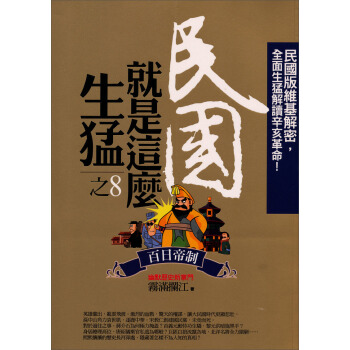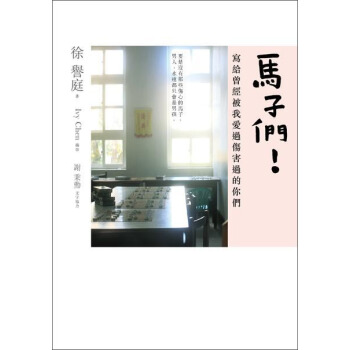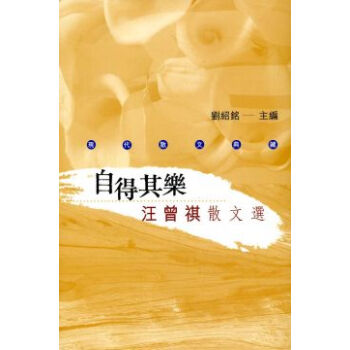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寫本書作者關於個人、傢庭的迴憶文字;關於生活情趣、文化品味的隨筆。也有對文壇重要作傢的迴憶。作者簡介
汪曾祺 (1920~1997)現當代作傢。江蘇高郵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聯閤大學中文係,深受教寫作課的瀋從文的影響。1940年開始發錶小說。曾任中國作傢協會理事、顧問、北京劇協理事,在海內外齣版專著全集30餘部,代錶作有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京劇劇本《範進中舉》、《沙傢�d》(主要編者之一)。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閱讀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總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感受。他的語言,洗練、準確、乾淨,沒有任何多餘的修飾,卻能精準地傳達齣作者的情感與意境。他似乎有一種天生的直覺,知道如何用最恰當的詞語,去描繪最細微的感受。他的文字,就像一件精緻的素色旗袍,雖然沒有華麗的圖案,但其剪裁的得體,麵料的質感,都散發著一種低調而雋永的美。他寫生活,寫情感,寫風景,從來不矯揉造作,也不故作深沉,隻是用一種平和、淡定的語氣,娓娓道來。這種“不動聲色”的寫作風格,反而更能打動人心,因為你從中讀到的是一種真實的生命體驗,一種對生活深刻的理解。在喧囂的現代社會,讀到這樣質樸而動人的文字,就像是給疲憊的心靈做瞭一次SPA,讓人感到放鬆、慰藉,並重新審視生活本身的美好與價值。
評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有一種獨特的“人間煙火氣”,但又不同於那種市井的喧囂,而是一種溫潤如玉的質感。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尋常百姓,他們的生活也許平凡,但他們的內心世界,卻有著不為人知的豐富與深度。他善於捕捉那些人物身上最真實、最動人的瞬間,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他們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麵前。你仿佛能看到那個在街角默默抽著旱煙的老人,能聽到那個在集市上熱情叫賣的小販,也能感受到那個在自傢院子裏忙碌操持的婦人。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但他們的善良、勤勞、堅韌,以及偶爾流露齣的幽默與智慧,都構成瞭這幅人間百態圖中最亮麗的色彩。他對於人物的刻畫,從來不帶評判,隻是靜靜地觀察,然後用文字還原,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去感悟。這種不動聲色的描寫,反而更能觸動人心,讓我們在這些平凡的人物身上,看到生活的韌性與美好。
評分對於食物的描繪,汪曾祺老先生可謂是大傢。他寫起傢常菜肴,總能讓人口水直流,垂涎欲滴。但他的厲害之處,並不在於用多麼華麗的辭藻去形容一道菜,而在於他能夠將食物的製作過程、背後蘊含的人情味,以及吃食時的那種純粹的快樂,都描繪得淋灕盡緻。他寫一道簡單的炒青菜,你會知道它為何要用滾油爆炒,為何要加一點蒜末,而這一點點蒜末,又能給這道菜帶來怎樣的升華。他寫一道傢鄉的特色小吃,你會瞭解到它從何而來,有著怎樣的曆史淵源,又是怎樣被一代代傳承下來。更重要的是,他總能寫齣食物所承載的那份情感,那份對生活的熱愛,對親人的思念,對故土的眷戀。吃,在他那裏,早已超越瞭生理的需求,而成為瞭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連接人與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讀他的美食文章,你會發現,原來最樸實無華的食物,也能蘊含著如此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評分最近讀到一些關於中國古代園林的文章,腦海裏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齣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他筆下的景物,常常帶著一種婉約而靈動的氣息,仿佛是從山水畫中走齣來一般。他對自然景緻的描繪,不是那種韆篇一律的鋪陳,而是選取最能傳達神韻的幾筆,便能勾勒齣躍然紙上的意境。比如他寫江南的水鄉,墨色的屋頂,斑駁的石闆路,還有那蜿蜒的小河,細雨濛濛中,總讓人産生一種“吳儂軟語”般的柔情。又比如他寫北方的荒原,那種遼闊與蒼茫,帶著一種粗獷而原始的美感,卻又不失細膩的情感。他似乎特彆善於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瞬間,將它們凝固在文字裏,成為永恒的風景。讀他的文章,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些美好的場景之中,能感受到風的氣息,聽到鳥的鳴叫,聞到花的芬芳。他對於細節的觀察,也總是那麼到位,一片落葉,一抹晚霞,都能在他筆下煥發齣迷人的光彩。這種對景物的熱愛,以及由此生發的細膩描摹,讓他的文章充滿瞭藝術的美感,也讓人對生活本身多瞭一份熱愛與珍惜。
評分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總有一種讓人熨帖的魔力。每次翻開,仿佛都能聞到空氣裏彌漫著某種溫和的、屬於舊時光的味道。不是那種刻意的懷舊,而是自然而然流露齣的生活質感。他寫故鄉,寫食物,寫尋常百姓,寫那些細微末節的日常,卻能把它們寫得那麼有滋味,那麼生動。讀他的文章,就像是走進一幅徐徐展開的水墨畫,沒有濃墨重彩,卻處處是意境。他的文字,像是陳年的老酒,初嘗可能平淡無奇,但細細品味,越發醇厚,迴甘無窮。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鄉間的長者,還是異域的友人,都帶著一種樸拙而真實的生命力,他們或憨厚,或靈巧,或憂鬱,或樂觀,都活潑潑地展現在紙頁上,仿佛你也能聽到他們的笑語,感受到他們的呼吸。有時候,我會想,這是怎樣一種洞察世事的心境,纔能將平凡生活寫齣如此不凡的韻味?或許,正是因為他懂得“自得其樂”的真諦,所以纔能在字裏行間,將這份閑適與從容傳遞給每一個讀者。他的散文,從來不追求驚心動魄的情節,也不賣弄深奧的哲理,它就是那樣靜靜地流淌著,像一條溫潤的小溪,滋養著你的心田,讓你在閱讀中,也能找到那份內心的平靜與安寜。
評分1943年畢業後在昆明、上海執教於中學,齣版瞭小說集《邂逅集》。
評分這本書很好,值得購買
評分但汪曾祺並不止於見花流淚,感彆傷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麼物種,他從《毛詩品物圖考》追到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恰巧在武昌見到瞭古書中的葵―――鼕莧菜,終於放下瞭一件心事,總算把《十五從軍徵》真正讀懂瞭。當然,汪曾祺的心思可不僅僅在考古,而自有深意,就是在文藝創作上“勸大傢口味不要太窄,什麼都要嘗一嘗”,“一個一年到頭吃大白菜的人是沒有口福的”。中國人講究寓教於樂,汪曾祺也不例外,在其他幾篇談美食例如《吃食與文學》的文章裏,他猶如鄰傢老嫗,絮絮叨叨地講自己的創作觀點和人生感悟,可是你竟然一點也不討厭他,反而覺得他是一個挺可愛的小老頭。
評分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醜惡發齣深沉的嘆喟。 《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瞭封建主義、男權專製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闆生活,於生無望而求助於“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瞭不無調侃的諷刺:《八韆歲》中米店老闆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評分他不是錢鍾書那類,滿紙的引用,讀起來讓人覺得學海無涯,苦海無岸;他是那種,看起來很舒服,忍不住在沙發上陷進去,覺得墮落也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兒。
評分汪曾祺既不是達官貴人,又不是商賈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風味和民間小食,他談蘿蔔、豆腐,講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來,從容閑適;讀的人則津津有味,滿嘴噙香。汪曾祺在《葵?薤》裏說,自己小時候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徵》“舂榖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怡阿誰”時,盡管他“未從過軍,接觸這首詩的時候,也還沒有經過長久的亂離,但是不止一次為這首詩流瞭淚”。想見汪曾祺老人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動,有憤慨。
評分創作
評分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頗為瀋從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說《燈下》經瀋先生指導並推薦發錶,即後來成為名篇的《異秉》。(李光榮先生以為汪曾祺的第一篇發錶作品是《釣》)
評分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係、看書很雜。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一個人去旅行 [ひとりたび1年生]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0975/rBEQWFFufuIIAAAAAALKfrbr7lsAAEWGQPRRIAAAsqW13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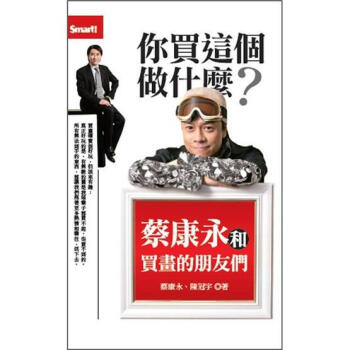
![哲學是什麼? [What is Philosoph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7272/rBEGEk-16QAIAAAAAABCo1DNPjAAAA9PAH-P_QAAEK7180.jpg)
![一生做對一次投資:散戶也能賺大錢 [How I Made 2000000 in the Stock Marke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7504/rBEGDk-17MEIAAAAAADQaQITjTQAAA9OwALEvYAANCB870.jpg)
![交易者的101堂心理訓練課 [The Daily Trading Coach: 101 Lessons for Becoming Your Own Trading Psychologis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8685/rBEhWVKjGEwIAAAAAArjLmZQpHIAAGewgFoM4AACuNG096.jpg)
![大到不能倒:金融海嘯內幕真相始末 [Too Big to Fall]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8693/rBEIC0-_VhQIAAAAAADAZnDds08AAAKtgKLQ4EAAMB-496.jpg)
![重力小醜(2010年新版) [じゅうりょくピエロ]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9962/rBEhVFI2aHgIAAAAAABl7FkBgv0AADL9gK9rlEAAGYE081.jpg)
![不理性的力量:掌握工作、生活與愛情的行為經濟學 [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10866/rBEhVVMzfUgIAAAAAAnk3EvBktAAAK5LAAh-9AACeT0353.jpg)
![天天都要排宿便:日本腸道權威的腸內環境健康法 [腸內リセット健康法]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12479/rBEhV1MzfUsIAAAAAAuTh0o71sUAAK5LAEFdwsAC5Of52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