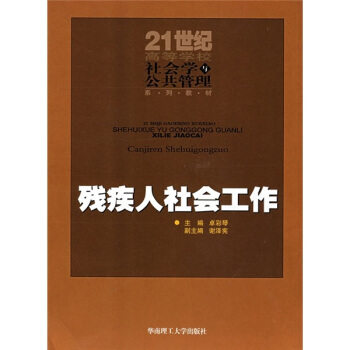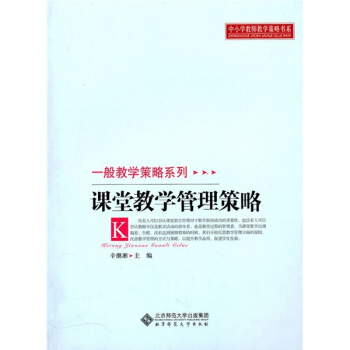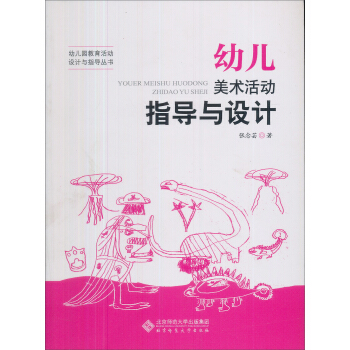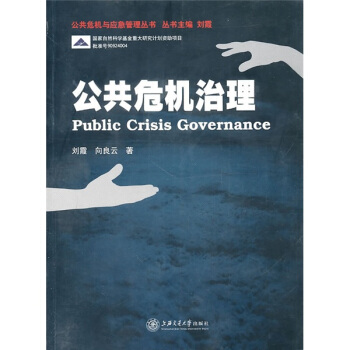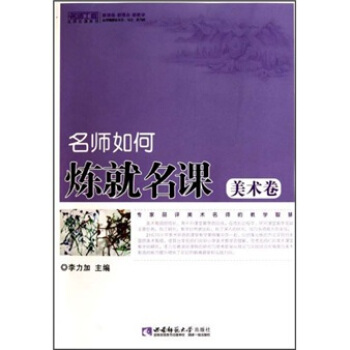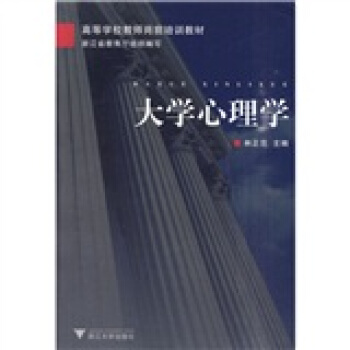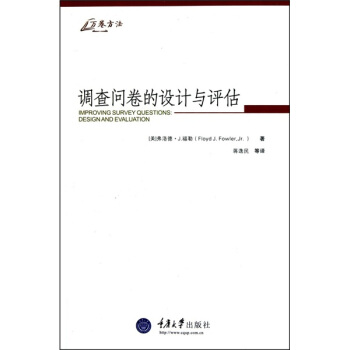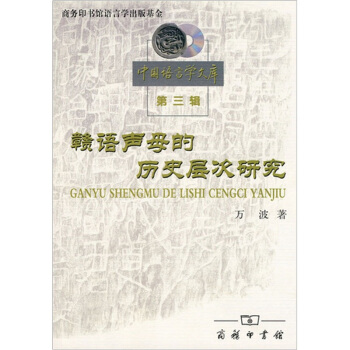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必须从共时的内外比较人手,归纳区内的各种类型,再和周边方言比较其异同,然后在汉语语音吏方面分析其历史层次。因此,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实际上就是方言语音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内容简介
《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是就一个大方言区进行这种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必须从共时的内外比较人手,归纳区内的各种类型,再和周边方言比较其异同,然后在汉语语音吏方面分析其历史层次。因此,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实际上就是方言语音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虽然讨论的只是声母的历史层次,其实在许多方面已涉及韵母和声调的特征。因为声母的分合和演变常常是以韵母、声调为制约条件的。不仅如此,讨论声母的历史层次势必还会牵连到词汇的特征,关系到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常用词和非常用词、方言固有词和通语用词、口语用字和书面语用字等等,也常常成了不同语音历史层次的取决条件,而方言历史背景对于理解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来说,有时,是不可缺少的。《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关于赣语声母历史层次的研究方法是遵循内外比较、历史分析、关照系统(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语音系统和语音、词汇的系统),并且联系了语言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外部关系,因此,所做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也可以使人们得到关于赣方言的整体特征的认识。可见,研究方法对头了,分析问题就会有新的突破,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升华。除了方法科学,《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的成功还在于作者下足了功力。在讨论每个声母现象的时候,《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都能尽量不遗漏地罗列已有的赣语调查材料,努力进行类型归纳,做到言之有据。同时也尽量不遗漏地查检历来学者们的有关分析结论,认真加以比较、权衡和评价。在材料方面,作者从1987年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就一点一点地调查赣方言,后来参加我们所主持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这个研究项目,赣方言点大多是他参与'或独力到实地调查的。从那时到本.书成书,真可谓是十年磨_剑,其中甘苦不言而喻。所以,《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这十几年的积累。在理论方面,作者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努力做到不论巨细,一一检验。对于初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忽略,对于大专家的结论也敢于提出质疑,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发掘材料和检验理论这两方面的功力,要寻求突破是艰难的。
《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对于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的研究上有哪些突破,当然还有待于各方面的专家们审核。无需在这一篇序文里一一提出。但是,由于我们始终都参与并关注这项研究,还是有不少感触的,希望专家和读者能仔细披阅,多加发掘。这里只就若干较为重要的课题提个头,供大家思考。
目录
序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2 研究方法
1.3 资料来源
1.4 标音说明
第二章 赣语的分布与历史形成
2.1 赣语的分布及其区分标准
2.2 邵武方言的归属
2.3 赣语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章 赣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历史层次
3.1 赣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今读类型
3.2 汉语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及性质
3.3 客赣方言“渠辫笨队赠叛站铡”今读的性质
3.4 赣语古全浊声母今读的历史层次
第四章 赣语端组声母的历史层次
4.1 赣语端组声母的今读类型
4.2 透定母读h型的历史层次
4.3 透定母读1型的历史层次
4.4 端透定母细音读ts、ts型的历史层次
第五章 赣语泥组声母的历史层次
5.1 赣语泥来母今读的分混类型
5.2 泥来半混型与泥来全混型的关系及历史层次
5.3 赣语来母的今读类型
5.4 来母塞音化现象的性质及历史层次
第六章 赣语见组声母的历史层次
6.1 赣语见组声母的今读类型
6.2 见组腭化现象的音韵分布及历史层次
6.3 见组今读ts ts、tf tf型的历史层次
6.4 见组今读ts、ts型的历史层次
6.5 见组今读t、t型的历史层次
6.6 溪群母今读h(x)、f、型的历史层次
6.7 溪群母今读零声母型的历史层次
第七章 赣语晓组声母的历史层次
7.1 赣语晓匣母的今读类型
7.2 晓组唇化现象的音韵分布及历史层次
7.3 匣母今读零声母的历史层次
7.4 匣母今读k、t型的历史层次
第八章 赣语知庄章 精组声母的历史层次
8.1 赣语知庄章 精组声母今读的分合类型及历史层次
8.2 赣语知二庄精组声母的今读类型及历史层次
8.3 赣语知三章 组声母的今读类型及历史层次
第九章 总结
9.1 各章 回顾
9.2 从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看赣语形成的多元性
9.3 从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看语音演变过程中各语言要素
之间的相互制约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
精彩书摘
禹征三苗后,史籍上“三苗”的名称不见了,在南方代之而起的是越族。从来源上看,越族可能是苗蛮的后裔。关于其活动范围,《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说得更具体一些:“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学界一般都同意林惠祥(1936:111)的观点:“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可见,自夏以后,江西地区的居民应为越族。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一般认为,至青铜时代,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文化,为古代百越族物质文化遗存。从江西境内180余处已发掘的商周文化遗址来看,基本上各处都有几何印纹陶出土。如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地区考古学重大成果之一的江西吴城商代文化遗址,共出土文物900余件淇中就包括大量几何印纹陶,纹饰特别丰富。根据彭适凡(1992:95)的研究,吴城遗址大量出土文物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说明它不可能是中原商民族的文化,“而应是与中原商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古越族的文化。”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说明,夏商西周时期,江西地区的居民为百越民族,所以,当时通行于江西地区的语言也应是非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古越语。……
用户评价
全书的阅读体验,可以概括为“在严谨中求证,在复杂中求简”。尽管主题是高度专业的声母研究,但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对语言生命力的敬畏感。某些章节对于声母在不同声调下的变异表现,分析得极为细致入微,甚至精确到语境对音值的影响。这让我意识到,语言的演化不是僵硬的规则集合,而是充满了细微差异的生命体。书中对某些“异读”现象的解释,提供了超越传统注疏学的新见解,它们不再是简单的“错误”或“例外”,而是不同历史音系在特定地域的“共存”表现。这本书无疑是赣语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挖掘遗迹般的热情和精确性,向世人展示了赣语声母那层层叠叠、蕴含着千年风云的历史肌理。
评分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令人惊叹的。它不仅仅是对赣语声母进行纯粹的音系描述,更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华夏语言交流史的侧窗。作者在论证某个声母的古音归属时,往往会巧妙地引入相邻方言区(如吴语、客家话)的对应材料进行参照,这种“参照系”的建立,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大增强。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及“次级分化”时的细腻笔触。很多声母并非一步到位地发生变化,而是经过了中间过渡阶段,书中对这些“过渡态”的捕捉和记录,体现了研究者对语音变化规律的深刻洞察。读到后半部分,我甚至开始思考,如果将这种研究方法论应用到其他方言族群的声母研究中,会得出怎样一番新的图景?这本书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单一语种的考察,它为汉语方言学提供了一套极具说服力的、可推广的研究范式。
评分作为一名对汉语方言史有长期关注的爱好者,我阅读此书时最大的感受是“颠覆认知”。我原以为赣语声母的某些特征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创新或变异,但通过这本书的系统梳理,我才意识到,很多现今听起来“新奇”的声母现象,其实是古代汉语某个时期语音系统残存下来的“活化石”。作者通过对不同历史层面的声母进行层级划分——比如被认为是上古残留的、中原雅言影响的、乃至近现代社会变迁导致的——清晰地勾勒出赣语声母的“年龄结构”。这种分层研究的方法,使得声母的演变不再是线性的、单向的过程,而是多股历史力量交织、碰撞、融合的复杂动态过程。书中的插图和表格设计也相当到位,虽然学术气息浓厚,但它们有效地将复杂的音位对应关系可视化,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难度,让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理论中的音变过程,仿佛可以被我们的耳朵捕捉到一般。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初读之下略显古朴,但细品之后,便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逻辑张力和深厚学养。它没有那种为了迎合大众而刻意简化的倾向,而是非常忠实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书中关于声母分化中“支流汇入”和“底层固化”的论述,构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框架。例如,在探讨某个特定声母的蜕变时,作者会引用大量罕见的古代韵书和方言志的记录,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编织成一张无懈可击的证据网,让人不得不信服。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那些音位对立模糊地带时的谨慎态度,没有急于下定论,而是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并进行优劣比较,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在当今许多快餐式的研究成果中是极为罕见的。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可能需要多次回溯前文以确保理解透彻,但只要愿意投入精力,这本书所给予的知识回报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关于赣语,更是一种关于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典范展示。
评分《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这本书的标题乍一看,就让人联想到深邃的语言学探讨,我本以为会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没想到读起来却有种拨开迷雾、重见天日的畅快感。作者在梳理赣语声母演变脉络时,展现了惊人的文献功底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书中对于中古汉语入声的归属分析尤其精彩,不同于许多沿用旧说、墨守成规的研究,作者引入了新的音韵学视角,比如对特定历史时期韵书中“破音字”的重新解读,这些都为我们理解赣语声母如何从一个大一统的音系逐步分化出今日的复杂面貌,提供了坚实的证据链。我特别欣赏的是,作者并非纯粹地罗列现象,而是将声母的变化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地理背景下考察,例如,赣语区不同方言在声母上的差异,往往能与古代的移民迁徙路线和文化交融点精确对应起来,这种跨学科的洞察力,让原本枯燥的音变过程充满了生动的历史叙事感,读完后,我对赣语的认识不再停留在“一种方言”的层面,而是将其视为一部活着的古代汉语变迁史。
评分家。史載幹越國在春秋時期為吳國所滅,其中心地帶可能位於今餘幹一帶,而艾國則位於今修水、武寧一帶,後其被楚國併吞。至春秋時代,江西地方經常被稱為“吳頭楚尾”,是因為江西曾迭為吳、楚、越國的爭雄之地。西元前473年越滅吳,西元前306年楚滅越。處於“吳頭楚尾”的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關係,而贛語中至今依舊保存著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吳語和古楚語詞的積澱,西漢揚雄在其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達85次,其中單言“南楚”、不並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則注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同時,《方言》中提及的吳越、吳楊越、吳楚等地亦被認為包括江西的部分地區,該時期的江西話是似吳類楚的一種獨具特色、有別于周畿雅言的語言。
评分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
评分家。史載幹越國在春秋時期為吳國所滅,其中心地帶可能位於今餘幹一帶,而艾國則位於今修水、武寧一帶,後其被楚國併吞。至春秋時代,江西地方經常被稱為“吳頭楚尾”,是因為江西曾迭為吳、楚、越國的爭雄之地。西元前473年越滅吳,西元前306年楚滅越。處於“吳頭楚尾”的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關係,而贛語中至今依舊保存著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吳語和古楚語詞的積澱,西漢揚雄在其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達85次,其中單言“南楚”、不並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則注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同時,《方言》中提及的吳越、吳楊越、吳楚等地亦被認為包括江西的部分地區,該時期的江西話是似吳類楚的一種獨具特色、有別于周畿雅言的語言。
评分配送速度比较迅速 感觉还好
评分此外,通行贛語的還有湖南省東界的13個縣:臨湘、平江、瀏陽、醴陵、攸縣、茶陵、酃縣、桂東、汝城、常寧、資興、安仁,有人認為岳陽、永興也屬贛方言區;福建省西北部的4個縣市:邵武、光澤、建甯、泰寧;湖北省東南部與江西省連界的 8個縣:通城、蒲圻、崇陽、通山、陽新、咸寧、嘉魚、大冶;安徽省西南部安慶地區的望江、東至、宿松、懷寧、太湖、潛山、嶽西、桐城等縣的方言,據初步瞭解,也和贛語相近,目前歸屬未定,可能也將劃歸贛方言;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區,也存在爭議,尚需進一步研究。
评分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
评分为了写论文买的,希望有用。
评分漢高帝初年(西元前202年),漢朝在江西設置豫章郡(贛江原稱豫章江,因此而得名),郡治南昌,下轄十八縣,管轄區域遍佈今江西四方。豫章郡人口由西元2年的將士35萬餘人猛增至西元140年的167萬餘人,淨增近132萬人。在當時中
评分赣方言研究之语音研究。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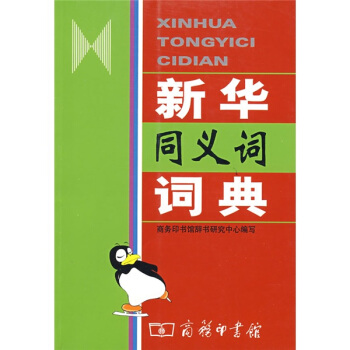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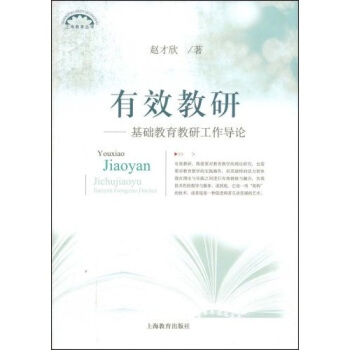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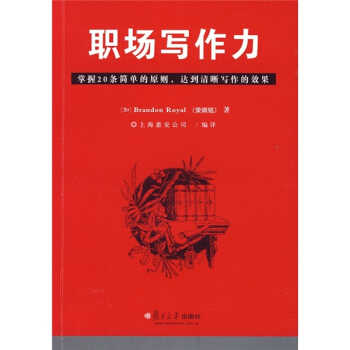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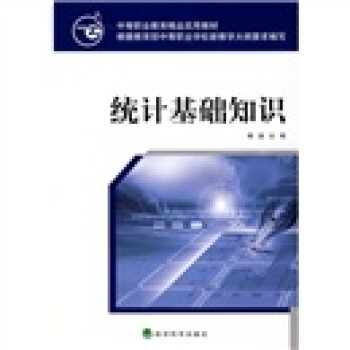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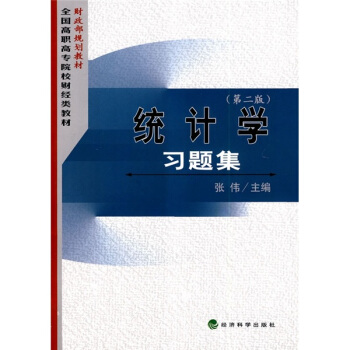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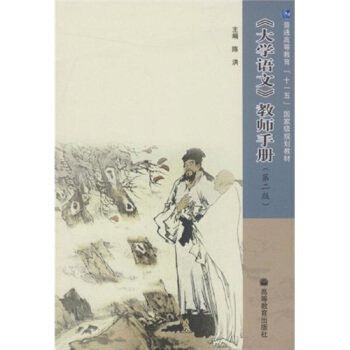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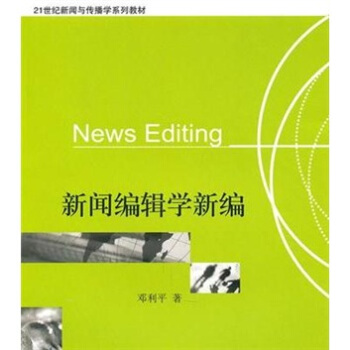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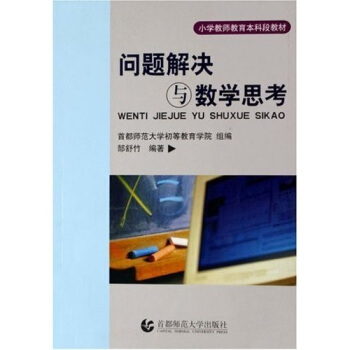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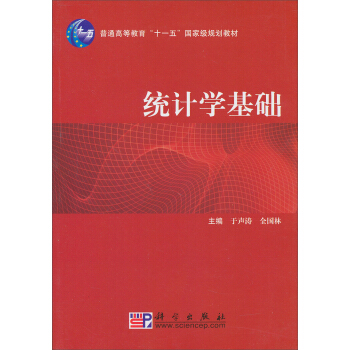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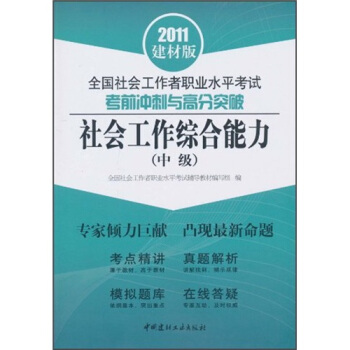
![社会问题:事件与解决方案(第5版) [Social Problems:Issues and Solutions Fif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366147/25c5b11c-2d09-449d-9bd2-225eb1b82ae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