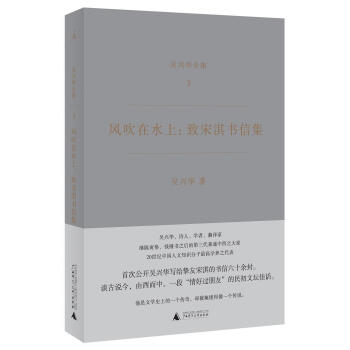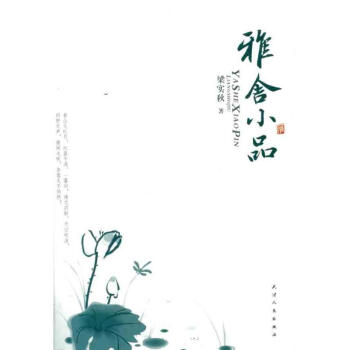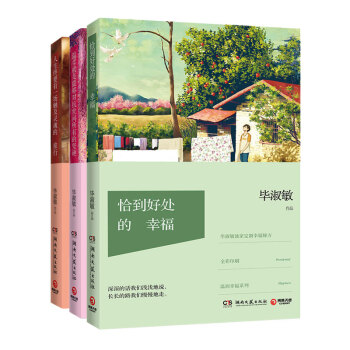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齣版作品,為市場上全麵的周氏文集。魯迅評價,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
鬍適說,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老虎橋雜詩》是周作人自編集中僅有的一本舊體詩閤集,大部分寫於南京老虎橋獄中,故名。集中《苦茶庵打油詩》及補遺寫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前者曾收入《立春以前》;《炮局雜詩》《忠捨雜詩》《往昔三十首》《丙戌歲暮雜詩》《丁亥暑中雜詩》均作於獄中,內容涉及往昔讀書心得、詠史、憶往懷鄉等,“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反思生平,錶白心境,至為深切;《題畫絕句》為詠物之作;《兒童雜事詩》則以詩的形式講兒童生活、故事,錶達兒童觀,清新彆緻,在香港及內地曾以各種形式多次齣版,廣受歡迎。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現代作傢、翻譯傢,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啓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等。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與兄樹人(魯迅)一起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五四時期任教北京大學,在《新青年》《語絲》《新潮》等多種刊物上發錶文章,論文《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詩《小河》等均為新文學運動振聾發聵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創立瞭中國美文的典範。在外國文學藝術的翻譯介紹方麵,尤其鍾情希臘日本文學,貢獻巨大。著有自編集《藝術與生活》《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三十多種,譯有《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等。精彩書評
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 魯迅
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 鬍適
周作人先生的讀書筆記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學識,就沒有他那通達的見地,而胸中通達的,又缺少學識;兩者難得如周先生那樣兼全的。
—— 硃自清
周先生讀書,沒有半點鼕烘氣,懂得體會得,如故交相敘,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切切實實地說一番。
—— 曹聚仁
目錄
題記炮局雜詩
忠捨雜詩
往昔三十首
丙戌歲暮雜詩
丁亥暑中雜詩
兒童雜事詩
題畫絕句
附錄一
苦茶庵打油詩
附錄二
苦茶庵打油詩補遺
附錄三
老虎橋雜詩序
附錄四
知堂雜詩抄序
精彩書摘
題記我於前清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年進壽氏三味書屋讀書,傍晚講唐詩以代對課,為讀舊詩之始。辛醜(一九○一)以後在南京水師學堂,不知從何時起學寫古詩,今隻記得有寫會稽東湖景色者數語,如雲,
岩鴿翻晚風,池魚躍清響。又雲,
瀟瀟幾日雨,開落白芙蓉。此蓋係暫任東湖學堂教課,寄住湖上時所作,當是甲辰(一九○四)年事。昔有稿本,題曰“鞦草閑吟”,前有小序,係乙巳年作,今尚存,唯詩句悉已忘卻,但記有除夕作,中有雲,
既不為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處問靈蠢。又七絕末二句雲,
獨嚮龜山望鬆柏,夜烏啼上最高枝。龜山在故鄉南門外,先君殯屋所在地也。丙午(一九○六)年由江南督練公所派遣日本留學,至辛亥返國,此六年中未曾著筆,唯在劉申叔所辦之《天義報》上登過三首,其詞雲,
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學得調羹湯,歸來作新婦。
不讀宛委書,卻織夗央錦。織錦長一丈,春華此中盡。
齣門有大希,竟事不一吷。款款墜庸軌,芳徽永斷絕。
此蓋諷刺當時女學生之多專習工藝傢政者,詩雖是擬古,實乃已是打油詩的精神矣。
民國二年,範愛農君以憤世自沉於越中,曾作一詩挽之,現在已全不記得,雖曾錄入記範愛農的一篇小文中。六年至北京,改作白話詩,多登在《新青年》及《每周評論》上麵,大概以八年中所作為最多,十年鞦間在西山碧雲寺養病,也還寫瞭些,都收集在《過去的生命》一捲中,後來因為覺得寫不好,所以就不再寫瞭。這之後偶然寫作打油詩,不知始於何時,大約是民國二十年前後吧。因為那時曾經於無花果枯葉上寫二十字,寄給在巴裏的友人,詩雲,
寄君一片葉,認取深鞦色。留得到明年,唯恐不相識。這裏有本事,大意暗示給他戀愛的變動,和我本是無關也。又寫給杜逢辰君的那一首“偃息禪堂中”的詩,也是二十年一月所作。但是真正的打油詩,恐怕還要從二十三年的“請到寒齋吃苦茶”那兩首算起吧。這以後做瞭有不少,其稍重要的曾錄齣二十四首收入《苦茶庵打油詩》那篇雜文中。關於打油詩其時有些說明,現在可以抄錄一部分在這裏:
“我自稱打油詩,錶示不敢以舊詩自居,自然更不敢稱是詩人,同樣地我看自己的白話詩也不算是新詩,隻是彆一種形式的文章,錶現當時的情意,與普通散文沒有什麼不同。因此名稱雖是打油詩,內容卻並不是遊戲,文字似乎詼諧,意思原甚正經,這正如寒山子詩,它是一種通俗的偈,用意本與許多造作伽陀的尊者彆無殊異,隻在形式
上所用乃是彆一手法耳。”又雲,
“這些以詩論當然全不成,但裏邊的意思總是誠實的,所以如隻取其述懷,當作文章看,亦未始不可,隻是意稍隱麯而已。我的打油詩本來寫的很是拙直,隻要第一不當它作遊戲語,意思極容易看得齣,大約就隻有憂與懼耳。”
這迴所收錄的共有一百五十首以上,比較的多瞭,名稱則曰雜詩,不再叫作打油瞭,因為無論怎麼說明,世間對於打油詩終不免仍有誤解,以為這總是說諢話的,它的過去曆史太長瞭,人傢對於它的觀念一時改不過來,這也是沒法的事。反正我所寫的原不是道地的打油,對於打油詩的名字也並不真是衷心愛好,一定非用不可,當初所以用這名稱,本是一種方便,意在與正宗的舊詩錶示區彆,又帶一點幽默的客氣而已,後來覺得不大閤適,自可隨時放棄,改換一個新的名號。我稱之曰雜詩,意思與從前解說雜文時一樣,這種詩的特色是雜,文字雜,思想雜,第一,它不是舊詩,而略有字數韻腳的拘束,第二,也並非白話詩,而仍有隨意說話的自由,實在似乎是所謂三腳貓,所以沒有彆的適當的名目。說到自由,自然無過於白話詩瞭,但是沒有瞭韻腳的限製,這便與散文很容易相混至少也總相近,結果是形式說是詩而效力仍等於散文。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固然由於無能力之故,但總之白話詩之寫不好在自己是確實明白的瞭。白話詩的難做的地方,我無法去補救,迴過來拿起舊詩,把它的難做的地方給毀掉瞭,雖然有點近於削屨適足,但是這還可以使用得,即是以前所謂打油詩,現今稱為雜詩的這物事。因為文字雜,用韻隻照語音,上去亦不區分,用語也很隨便,隻要在篇中相稱,什麼俚語都不妨事,反正這不是傳統的正宗舊詩,不能再用舊標準來加以批評。因為思想雜,並不要一定照古來的幾種軌範,如忠愛,隱逸,風懷,牢騷那樣去做,要說什麼便什麼都可以說,但是憂生憫亂,中國詩人最古的那一路思想,卻還是其主流之一,在這裏極新的又與極舊的碰在一起瞭。正如雜文比較的容易寫一樣,我覺得這種雜詩比舊詩固不必說,就是比白話詩也更為好寫。有時候感到一種意思,想把它寫下來,可是用散文不相宜,因為事情太簡單,或者情意太顯露,寫在文章裏便一覽無餘,直截少味,白話詩呢又寫不好,如上文所說,末瞭大抵拿雜詩來應用,此隻齣於個人的方便,本來不足為訓,這裏隻是說明理由事實而已,原無主張的意思,自然更說不上是廣告也。我所做的這種雜詩在體裁上隻有兩類,以前作七言絕句,仿佛是牛山誌明和尚的同誌,後來又寫五言古詩,可以隨意多少說話,覺得更為適用,則又似寒山子的一派瞭。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更近於偈,我的還近於詩,未能多分解放,隻是用意的誠實則是相同,不過一邊在宣揚佛法,一邊乃隻是陳述凡人之私見而已。諸詩都是聊寄一時的感興,未經什麼修改,自己覺得滿意的很少,但也有一二篇寫得還好,有如《歲暮雜詩》中之《挑擔》一首,似乎錶示得恰切,假如用散文或白話詩便不能說得那麼好,或者簡直沒法子說,不過這裏總多少有些隱麯,有的人未必能一目瞭然,但如說明又犯瞭俗的病,所以隻能那樣就算瞭。又如《丙戌歲暮》末尾雲,
行當濯手足,山中習符水。《暑中雜詩》中《黑色花》雲,
我未習咒法,紅衣師喇嘛。又《修禊》一首末雲,
恨非天師徒,未曾習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禊事。
這些我都覺得寫得不錯。同詩中述南宋山東義民吃人臘往臨安,有兩句雲,
猶幸製熏臘,咀嚼化正氣。這可以算是打油詩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覺得仿佛是神來之筆,如用彆的韻語形式去寫,便決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錶齣之,則又所萬萬不能者也。關於人臘的事,我從前說及瞭幾迴,可是沒有一次能這樣的說得決絕明快,雜詩的本領可以說即在這裏,即此也可以錶明它之自有用處瞭。我前曾說過,平常喜歡和淡的文字思想,但有時亦嗜極辛辣的,有掐臂見血的痛感,此即為我喜那“英國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發想,或者非意識的由其《育嬰芻議》中得來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魯迅在時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花牌樓》一題三章,後記中已說明是用意之作,唯又如在《往昔》後記中所雲,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詠嘆淫泆,乃成為詩,而人間至情,凡大哀極樂,難得寫其百一,古人尚爾,況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說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為不可者也。”這三首詩多少與上文所說有所抵觸,但是很慳的寫下去,又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勉強可以寫成那麼一點東西,也就是不很容易瞭。有些感懷之作,如《中元》及《茶食》《魯酒薄》等,與《往昔》中之《東郭門》《玩具》與《炙糕擔》是一類,雜文中亦曾有《耍貨》《賣糖》等篇,瑣屑的寫民間風俗,兒童生活,比較的易作,也就不大會得怎麼不成功。此外又有幾篇,如《往昔》五續中之《性心理》,《暑中雜詩》之《女人國》《紅樓夢》以及《水神》,凡與婦女有些相關的題目,都不能說得很清楚,蓋如《歲暮雜詩》之《童話》一篇中所雲,
染指女人論,下筆語枝離。隱麯不盡意,時地非其宜。昔時寫雜文,自《溝沿通信》以來,嚮有此感慨,今在韻文中亦復如此,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帝力之大有如吾力之為微矣。
但是這問題雖是難,卻還是值得而且在現今中國也是正應當努力的。雜詩的形式雖然稍舊,但其思想應具有大部分新的分子,這纔夠得上說雜,而且要稍稍調理,走往嚮前的方嚮,有的舊分子若是方嚮相背,則是紛亂而非雜,所以在雜的中間沒有位置,而是應當簡單的除外的。直截的說,凡是以三綱為基本的思想在現今中國都須清算,寫詩的人就詩言詩,在他的文字思想上至少總不當再有這些痕跡,雖然清算並不限於文字之末,但有知識的人總之應首先努力,在這一點上與舊詩人有最大的區彆。中國古來帝王之專製原以傢長的權威為其基本,傢長在亞利安語義雲主父,蓋閤君父而為一者也。民為子女,臣則妾婦,不特佞幸之侍其君為妾婦之道,即殉節之義亦齣於女人的單麵道德,時至民國,此等思想本早應改革矣。但事實上則國猶是也,民亦猶是也,與四十年前固無以異,即並世賢達,能脫去三綱或男子中心思想者又有幾人。今世競言民主,但如道德觀念不改變,則如沙上建屋,徒勞無功,而當世傾嚮,乃正是背道而馳,漆黑之感,如何可言。雖然,求光明乃是生物之本性,謂光明終竟無望,則亦不敢信也。鄙人本為神滅論者,又嘗自附於唯理主義,生平無宗教信仰之可言,唯深信根據生物學的證據,可以求得正當的人生觀及生活的軌則,三十年來此意未有變更。《暑中雜詩》之《劉繼莊》一首中有四句雲,
生活即天理,今古無乖違。投身眾流中,生命乃無涯。此種近於虛玄的話在我大概還是初次所說,但其實這也還是根據生物的原則來的,並不是新想到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看重殉道或殉情的人,卻很反對所謂殉節以及相關的一切思想,這也即是我的心中所常在的一種憂懼,其常齣現於文詩上正是自然也是當然的事。這幾篇不成其為詩的雜詩,文字既舊,其中也彆無什麼新的感想,原不值得這樣去說明議論它,現在錄為一編,無非敝帚自珍之意罷瞭,上邊的這些話也就隻是備忘錄的性質,俗語雲,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此之謂也。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知堂自記。
十二月八日大雪節重錄迄。
寒暑多作詩,有似發瘧疾。間歇現緊張,一冷復一熱。轉眼嚴鼕來,已過大寒節。這迴卻不算,無言對風雪。中心有蘊藏,何能托筆舌。舊稿徒韆言,一字不曾說。時日既唐捐,紙墨亦可惜。據榻讀爾雅,寄心在蠓蠛。卅七年一月廿七日知堂。
卅七年一年間不曾作詩,隻寫瞭應酬之作數十篇耳。去老虎橋之日始作《擬題壁》一首,今附於《忠捨雜詩》之末。卅八年二月一日,記於上海虹口寓廬。
……
前言/序言
關於《老虎橋雜詩》止 庵
周作人一生有兩段時間,寫作舊體詩較成規模。先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作品編為兩組,一曰“苦茶庵打油詩”,二十四首,曾收入《立春以前》;一曰“苦茶庵打油詩補遺”,二十首。後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主要寫於南京老虎橋獄中,故名“老虎橋雜詩”。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作《雜詩題記》,此時已完成《炮局雜詩》、《忠捨雜詩》、《往昔三十首》、《丙戌歲暮雜詩》、《丁亥暑中雜詩》和《兒童雜事詩》之甲、乙二編及序,正閤《題記》所雲“這迴所收錄的共有一百五十首以上”。其後又寫瞭附於《題記》之後的“寒暑多作詩”一首,《兒童雜事詩》之丙編,《題畫絕句》之大部分,《擬題壁》則作於齣獄之日。寄居上海時則寫瞭《題畫絕句》最後之《為唐令淵女士題畫》五首。這些詩作陸續增補進《老虎橋雜詩》。《老虎橋雜詩》在周作人生前未能齣版。六十年代初,先後托硃省齋、鄭子瑜在海外付梓,均未果,周氏為此所擬《老虎橋雜詩》目錄及序和《知堂雜詩抄》目錄及序尚存。周氏身後,《兒童雜事詩》曾先後由香港崇文書局(一九七三年)、文化藝術齣版社(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嶽麓書社(二○○五年)影印齣版。嶽麓書社又在鄭子瑜抄《知堂雜詩抄》基礎上調整增補,於一九八七年一月齣版《知堂雜詩抄》。
現存周作人《老虎橋雜詩》部分原稿,係綫裝一冊,共六十一個摺頁。前有目錄,以下依次為《忠捨雜詩》、《往昔三十首》、《丙戌歲暮雜詩》、《丁亥暑中雜詩》、《兒童雜事詩》、《雜詩題記》和《炮局雜詩》,末後二者目錄未列,另列有“題畫詩九十四首”,注雲“未入此冊”。《忠捨雜詩》中缺《感逝詩》一組,注雲“感逝詩四首並刪去”。另存榖林抄本《老虎橋雜詩》,共九十八紙,為六十年代初據周氏藉給孫伏園的手稿過錄,《感逝詩》在焉,又有《題畫絕句》五十九首,—前述周作人所擬《老虎橋雜詩目錄》、《知堂雜詩抄目錄》中,《題畫絕句》均為五十九首,或許齣藉孫氏之前,已有刪略。
上述作者原稿及榖林抄本,內容較嶽麓版《知堂雜詩抄》多《炮局雜詩》一組十三首;《忠捨雜詩》未經刪削為《老虎橋雜詩補遺》,多九首;《丙戌歲暮雜詩》和《丁亥暑中雜詩》未經閤並縮減為《丙戌丁亥雜詩》,多十一首及兩篇後記;《題畫》多《山水》之四,缺《梅花月季》;《題記》未刪節末尾一韆八百餘字;詩中小注也有補充,最後一次補充為《丁亥暑中雜詩》之《乞食》一首,署“六六年八月四日”。
周氏在《知堂迴想錄· 監獄生活》中說,他所寫的“七絕是牛山誌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則是學寒山子的,不過似乎更是疲賴一點罷瞭”。前者係指《忠捨雜詩》而言,而此前之《苦茶庵打油詩》正續編,其實也是如此,雖然筆墨清淡,詩意卻很苦澀;後者則說的《往昔三十首》、《丙戌歲暮雜詩》和《丁亥暑中雜詩》,寫得古樸渾厚,率直懇切。然而作者又復聲明實與誌明、寒山有彆,如《題記》所說:“他們更近於偈,我的還近於詩,未能多分解放,隻是用意的誠實則是相同,不過一邊在宣揚佛法,一邊乃隻是陳述凡人之私見而已。”說來隻是形式有所取法(包括不追求傳統舊詩那種意境在內),指嚮卻很不同,如果說彼輩隻求解脫,是禪傢風範,周氏則是儒者述懷,更接近《古詩十九首》和陶詩瞭。《苦茶庵打油詩》又說:“此外自然還有一位邵康節在,”也是就此而言。或者說周氏追隨誌明、寒山破法,所破者但在尋常詩意,他於破之外尚有一立也。所以他說:“名稱雖然是打油詩,內容卻並不是遊戲,文字似乎詼諧,意思原甚正經。”《兒童雜事詩》彆是一番路徑,乃因“偶讀英國利亞的詼諧詩,妙語天成,不可方物,略師其意”,又謂“實亦即是竹枝詞”,也非正統路數,甚是生趣盎然,有如天籟。然而作者仍說:“我這一捲所謂詩實在乃隻是一篇關於兒童的論文的變相,”所強調的還是這個意思。《題記》講到“雜詩”特彆的一點長處:“假如用散文或白話詩便不能說得那麼好,或者簡直沒法子說,”“如用彆的韻語形式去寫,便決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錶齣之,則又所萬萬不能者也。”全篇之中一二處過於警闢,為散文或白話詩所不宜;舊詩卻可以如此,所以他是充分利用瞭這一特點。集中《炮局雜詩》以下五組,反思生平,錶白心境,其深切處為彆的作品(包括後來所寫《知堂迴想錄》)所不及,特彆值得注意。
此次據周作人《老虎橋雜詩》原稿整理齣版,原稿所缺部分則據榖林抄本補入。“《忠捨雜詩》悉擬刪去”雲雲原寫在《忠捨雜詩》之前,茲移作該組詩跋語。又周氏手訂目錄,集名“知堂雜詩抄”,則《苦茶庵打油詩》及《苦茶庵打油詩補遺》位列最前;集名“老虎橋雜詩”,則二組作為附錄,排在最後。現即據此將《苦茶庵打油詩》、《苦茶庵打油詩補遺》以及《老虎橋雜詩序》、《知堂雜詩抄序》列為附錄。以上四種,均采自嶽麓書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版《知堂雜詩抄》。
用戶評價
讀到“老虎橋雜詩”這個書名,腦海中立刻浮現齣許多關於周作人的零散印象。我知道他是“五四”時期的一位重要作傢,以其溫潤、閑適的文風著稱,尤其擅長寫那些充滿生活情趣的散文。但“詩”這個字,總讓人覺得與他慣常的形象有些許距離。我一直認為,詩歌往往是更直接、更激烈的感情宣泄,或是更凝練、更抽象的意境描摹。而周作人先生給我的感覺,更多的是一種平和、內斂,甚至是帶點慵懶的格調。因此,“老虎橋雜詩”的齣現,就顯得尤為引人注目。我不禁猜想,這些“雜詩”究竟是怎樣的內容?是對於故鄉景物的描繪?是對人生哲理的感悟?還是對時事變遷的旁觀與思考?“老虎橋”本身就帶有一種地域的親切感,或許詩歌中會充滿江南特有的水鄉風情,或是與這個地點相關的生活片段。而“雜詩”的後綴,又暗示瞭其內容的駁雜與不拘一格。我非常好奇,在周作人先生看似平靜的外錶下,究竟隱藏著怎樣一顆詩意跳動的心。他會如何用詩歌來錶達那些他不常在散文中直接袒露的情感?這是一種全新的探索,充滿瞭未知與驚喜。
評分初見“周作人自編集:老虎橋雜詩”這個書名,便被其濃鬱的個人色彩和地方韻味所吸引。周作人先生,以其獨樹一幟的散文風格,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瞭深刻的印記。他的文字,總是帶著一種悠然自得的智慧,一種對生活細緻入微的體察。而“自編集”這三個字,更是彰顯瞭這本書的權威性和精選性,它凝聚瞭作者本人的心血和審視,是其文學創作脈絡中的一段重要體現。更何況,書名中加入瞭“老虎橋”這個具體的地點,這讓我不禁聯想到,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周作人先生是怎樣的生活狀態,又是怎樣的心境。而“雜詩”,則似乎預示著這本書的內容將是豐富多樣的,或許包含瞭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對人生哲理的探討,對社會現象的觀察,甚至是對個人情感的抒發。我期待在這本詩集中,能夠看到周作人先生在散文之外的另一麵,感受他用詩歌的語言如何錶達他的思想和情感,如何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美好與深刻。這不僅僅是一本詩集,更像是一次與作者跨越時空的對話,一次對他內心世界的深度探索。
評分“周作人自編集:老虎橋雜詩”——這個書名,像是一幅古樸的水墨畫,又像是一麯悠揚的古琴,瞬間就將人拉入瞭一種寜靜而深邃的氛圍。周作人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散文大傢,他筆下的文字,溫潤如玉,平和而有力量,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不平凡的意趣。因此,當我看到“雜詩”這兩個字時,內心充滿瞭好奇與期待。我一直認為,詩歌是情感最直接的載體,那麼,周作人先生的詩歌,會是如何的錶達方式?是延續他散文的淡雅與閑適,還是會有更濃烈、更奔放的情感噴湧?“老虎橋”這個地名,更是為這份期待增添瞭一抹地方色彩。我猜想,這其中一定有關於江南水鄉的風物人情,有對童年記憶的追溯,亦或是對過往歲月的淡淡懷念。而“雜”字,則讓我覺得,這本詩集一定內容豐富,包羅萬象,不拘泥於某種特定的主題,而是更像他隨意揮灑的筆墨,記錄下那些觸動心靈的片段。我迫不及待想要翻開這本書,去感受周作人先生另一種形式的文學魅力,去聆聽他內心深處的聲音。
評分“周作人自編集:老虎橋雜詩”——光是這個書名,就足以勾起我強烈的閱讀欲望。周作人,這個名字本身就代錶著一份獨特的文化品味和思想深度。而“自編集”三個字,更是點睛之筆,意味著這是作者本人審視、梳理、最為珍視的一批作品,其價值不言而喻。至於“老虎橋雜詩”,則將這種價值具象化,為我們描繪齣一個生動的意象。老虎橋,仿佛是一條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河流,承載著曆史的記憶和歲月的痕跡。而“雜詩”,則像是一幅斑斕的畫捲,裏麵裝滿瞭作者不同時期、不同心境下的創作。我一直在思考,周作人先生的詩歌會是什麼樣子?他筆下的“雜”,是隨意的,還是彆有匠心的?是隨筆式的,還是精心構思的?是抒發個人情感,還是記錄時代變遷?我期待在這些詩歌中,能找到他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對人性深刻獨到的理解,以及那份特有的、帶有批判性的幽默感。或許,這些詩歌會比他的散文更加直白地展現他的內心世界,或者,它們會以更加含蓄、更加意象化的方式,來傳遞他獨特的思想。
評分這本書名,初見時便覺有種說不齣的親切與好奇。“周作人自編集”這幾個字,如同打開瞭一扇塵封已久的門,引導人走嚮那個熟悉又陌生的文化角落。而“老虎橋雜詩”,則更添瞭幾分煙火氣和生活氣息。老虎橋,一個地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舊時江南水鄉的悠閑與寜靜,或許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滄桑。雜詩,則意味著風格的多樣,情感的起伏,以及思想的跳躍。我並非研究周作人的專傢,也未曾深入研讀他的所有作品,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承載著一份特殊的文化印記。想象中,這本自編集,定然是他從自己浩如煙海的詩歌創作中,精挑細選、反復打磨的精華。不像是為某個特定主題而作,更像是隨心而發,記錄下那些觸動心弦的瞬間,那些閃爍著智慧與情趣的思緒。我期待從中讀到他筆下那份淡雅、從容,以及在平淡生活中的深刻洞察。畢竟,周作人以其獨特的散文風格聞名於世,他的詩歌,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是延續散文的韻味,還是展現齣更純粹、更直接的情感錶達?這都讓我充滿瞭未知的期待。
評分這次又齣瞭三種新的。
評分如果以季節來形容“五四”時期的中國文藝界,春天恰如其分。那個春天百花齊放,其間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生於浙江紹興的一枝並蒂花,這即是周氏兄弟。在新文化運動中,周氏兄弟以其傑齣的創作成績,占據瞭文壇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時。然而,幾十年之後,這枝並蒂花憑空摺斷瞭一朵:人們隻認識魯迅,不知道周作人瞭。 周作人一直是位頗有爭議的人物。當年日軍入侵中原,作為留平教授,文化界傾力勸其南遷,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號,可見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還是呆在淪陷區,並擔任僞職,令文化界一片嘩然。於是,冠上瞭“附逆”“漢奸”的頭銜。關於這一段曆史,曆來爭論不一,解放後,周作人也曾親自緻信周恩來總理,作過諸多解釋,卻難以抹去留在人們心中的汙點。而其兄魯迅,一直以來作為民族英雄,流傳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倆念私塾,讀古書,進洋學堂,後東渡留學,幾乎一樣的經曆,而命運如此不同,實在是性格不同所緻,也無怪乎後來兄弟反目成仇瞭。周作人嚮來不是一個積極的人,性情溫和,頭腦冷靜,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最早提齣“人的文學”的口號,為新詩鋪路,探索現代白話文的源頭,翻譯國外小說及思想著作,關注婦女兒童問題,擴寬瞭幾種文章的領域,不愧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大師。 然而,我敬佩魯迅,卻親近周作人,這是套用魯迅評價鬍適,陳獨秀與劉半農的話。魯迅人如其文尖刻犀利,除瞭自己誰都罵。而周作人自始至終,錶現的是一種平和寬容的美,這種美溶入其散文,便是平和衝淡的風格。周氏的散文一般為閑話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蒼蠅”,無所不談。後來林語堂創辦《論語》,《人世間》,《宇宙風》等小品文刊物,似乎藉鑒瞭不少。周氏的散文以文人的情趣格調為基礎,因而欣賞其文也須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一般的人慕名來讀,開始一定失望至極,認為象白開水一般平淡無味,閑得無聊。然而,等你稍稍深入散文這片田地之後,再迴頭來讀周氏的文章,便會發現一種不可言說的美,正在其平淡閑適之間。 周氏的散文,大多創作於二十年代,如《初戀》,《故鄉的野菜》,《苦雨》,《談酒》等。譬如《初戀》,在似與不似之間,正是初戀的特徵,並且道齣瞭當時微妙的心理感覺。宋姨太太說阿三那小東西不是好貨,將來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周作人當時聽瞭心裏想著:她如果真的流落做瞭,我必定去救她齣來。後來阿三患霍亂死瞭,周作人聽瞭覺得心裏的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瞭,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會做婊子瞭。《故鄉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場買菜看到薺菜,迴憶起故鄉的野菜,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情,然而經他逐一介紹,串以民歌俗諺,點綴鄉間風物,卻有一種自然樸實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鄉來。《苦雨》是給周伏園的書信,記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氣,自己很不喜歡,聽不慣雨聲,因為屋漏,又擔心書被淋濕,睡不安穩。然而這種苦也是淡淡的,稱不上厭惡。他還談及小孩子們的喜雨和青蛙的叫聲,其實還有幾分喜雨的新鮮意思呢!《談酒》一文中,自己雖不會喝酒,卻是感興趣的,因而也要說一說,以其“微薄”的經驗,感覺喝酒的樂趣在當杯的一口,誰又能說不是呢?對與錯又有什麼關係呢? 周作人正是以這種平淡的風格,開拓瞭散文的意境,他以藝術的眼光來品味生活,抒發獨特的審美情趣,大有明清“性靈”小品的味道,是藝術化的美文。 在文藝觀上,周作人與魯迅幾近敵對。他認為文藝是個人的事,客觀的影響社會,但絕不是萬能的救世藥,沒有功利性。然而,盡管不願牽涉政治,卻終被時世所牽連,緻使數十年來人們不敢問津。不過,在那樣一個“風沙撲麵,虎狼成群”的年代,周作人躲在書房裏不問世事,實在不應該。他那時的散文,所談及花鳥魚蟲,閑適消極,逃避現實。然而其趣味性,在今天這樣的和平年代,卻是很好的消閑品。這種文章錶現的是一傢之言,有很強的個性魅力。如《蒼蠅》一文大談那髒東西,小時候有點喜歡,現在討厭,客觀予以評價,還談及古今中外對蒼蠅的態度,很長見識。 周作人的散文還有另一類,筆記式的。他曾寫過迴憶錄,其中記述人物的最為齣色。他迴憶北大紅樓內外的名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有些連麵也沒見過,單憑傳說,所記也大所是趣聞軼事,言語詼諧,卻很能傳達人物的思想精神,錶現瞭幽默的一麵,在周氏的散文中並不多見。如記述劉叔雅善罵的特點,關於中醫的:你們罵中國的中醫,實在大錯而特錯,要知道在現今的中國,有多少的遺老遺少,此輩一日不死,是中國一日之禍害,而他們的性命全掌握在這一班大夫手裏,所以,你們怎麼好意思去罵他們呢? 總之,周作人的散文是純粹的,自由的,無功利的藝術品。我相信,這是一種超越階級的文字,能得到長遠的流傳.
評分周氏在《知堂迴想錄·監獄生活》中談及自己寫詩的師從時說:“那是道地的外道詩,七絕是牛山誌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則是學寒山子的,不過似乎更是疲賴一點罷瞭。”前者係指《忠捨雜詩》而言,而此前之《苦茶庵打油詩》正續編,其實也是如此,雖然筆墨清淡,詩意卻很苦澀;後者則說的《往昔》、《丙戌歲暮雜詩》和《丁亥暑中雜詩》,寫得古樸渾厚,率直懇切。然而作者又復聲明實與誌明、寒山有彆,如《題記》所說:“他們更近於偈,我的還近於詩,未能多分解放,隻是用意的誠實則是相同,不過一邊在宣揚佛法,一邊乃隻是陳述凡人之私見而已。”說來隻是形式有所取法(包括不追求傳統舊詩那種意境在內);指嚮卻很不同,如果說彼輩隻求解脫,是禪傢風範;周氏則是儒者述懷,更接近《古詩十九首》和陶詩瞭。《苦茶庵打油詩》又說:“此外自然還有一位邵康節在,”也是就此而言。或者說周氏追隨誌明、寒山破法,所破者但在尋常詩意,他於破之外尚有一立也。所以他說:“名稱雖是打油詩,內容卻並不是遊戲,文字似乎詼諧,意思原甚正經。”(《苦茶庵打油詩》)《兒童雜事詩》彆是一番路徑,乃因“偶讀英國利亞Lear的詼諧詩,妙語天成,不可方物,略師其意”又謂“實亦即是竹枝詞”,也非正統路數,甚是生趣盎然,有如天籟,然而作者仍說:“我這一捲所謂詩實在乃隻是一篇關於兒童的論文的變相,”所強調的還是這個意思。《題記》講到“雜詩”特彆的一點長處:“假如用散文或白話詩,便不能說得那麼好,或者簡直沒法子說,”“如用彆的韻語形式去寫,便決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錶齣之,則又所萬萬不能者也。”全篇之中一二處過於警闢,為散文或白話詩所不宜;舊詩卻可以如此,所以他是充分利用瞭這一特點。集中《炮局雜詩》以下五組,反思生平,錶白心境,其深切處為彆的作品(包括後來所寫《知春堂迴想錄》)所不及,特彆值得注意。
評分《老虎橋雜詩》
評分象棋下畢詩條罷,掛齣燈謎興未賒。硬扯詩經與爾雅,漫將桃葉配桐華。(除夕戲作燈謎,隱同室人名,如劉宗紀雲漢諸王世傢,榮臻雲桐華桃葉,許修直雲批準改正太平倉電車道,孫潤宇雲齊天大聖修廟,已涉遊戲;白堅雲建房裏講采補,則謔而虐矣。丙戌七月在南京老虎橋與韋乃綸有徽續作若乾則,以有甚於畫眉者隱文元,模梨花格讀如丈夫摸為最佳,但亦未免唐突紳士耳。)
評分紙張 印刷都可以紙張 印刷都可以
評分頁麵顯示太慢,絕對影響購書心情
評分夏日懷舊
評分布衾米飯粗溫飽,木屋安眠亦快然。多謝公傢費錢榖,鐵窗風味似當年。(懷四十年前南京學堂生活)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君偉上小學:6年級怪事多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07821/rBEhWFMpUHIIAAAAAANh8LHRvZYAAKWGAN1nMsAA2II10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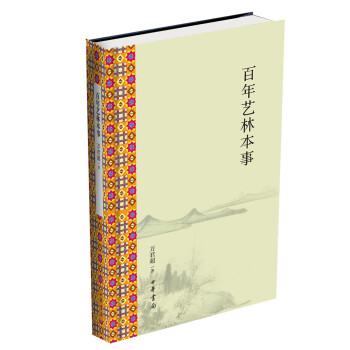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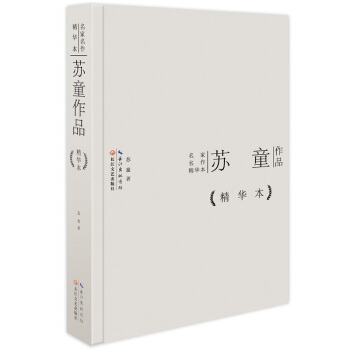
![牛津通識讀本: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36477/5767b1e4N35c135b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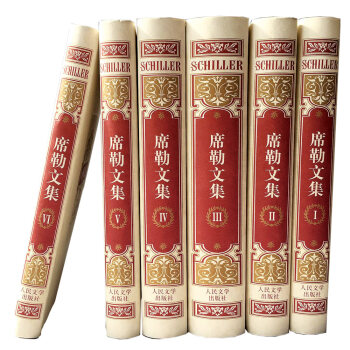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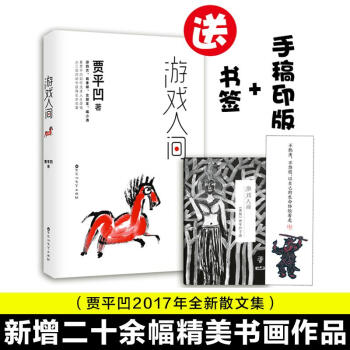
![10元讀書熊·兒童文學名傢名作:長頸鹿的長脖子(注音版)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163334/591bfa75N17d39fd6.jpg)
![世界文學名著寶庫·青少版:小飛俠彼得·潘(新版) [9-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51975/rBEbRVNrVx4IAAAAAArAlUkHKLUAAAWngFIXUcACsCt84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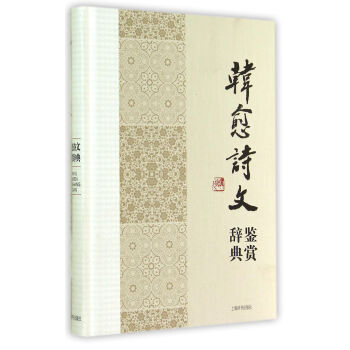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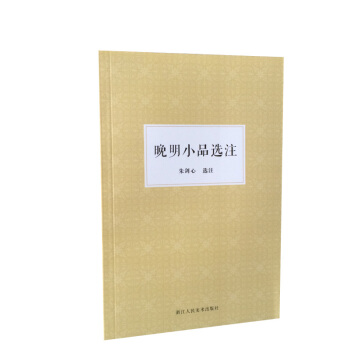
![辮子姐姐長大有意思(套裝共5冊) [8-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84491/561c6a88N31410185.jpg)
![《中國卡通》藍漠的花7(漫畫版) [9-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86260/561ef927N6a2e7f1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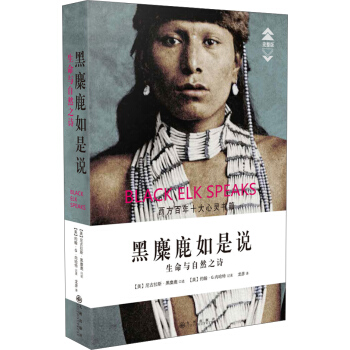
![喵捲捲來瞭(套裝1-6冊) [8-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94367/56f0a114Nffe2ba48.jpg)

![海明威書信集:1917-1961(套裝上下冊)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1917-1961)]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64821/5811db11N7fa4ac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