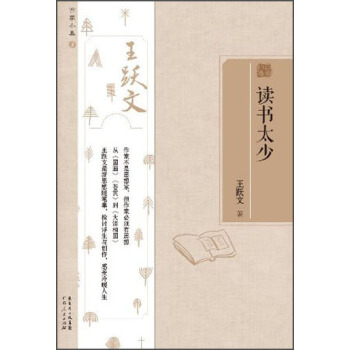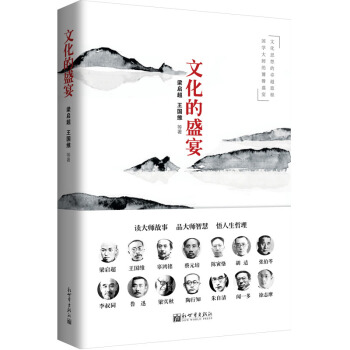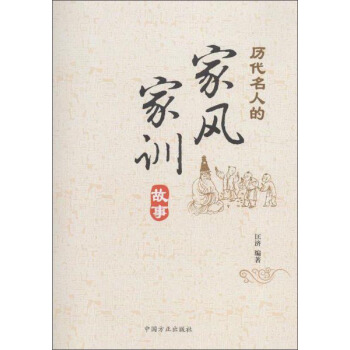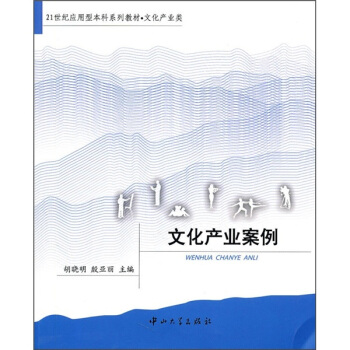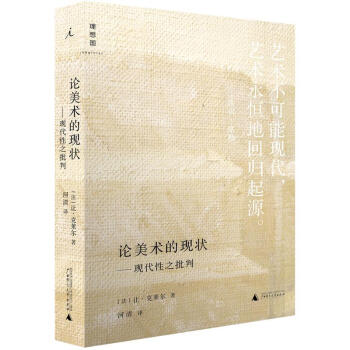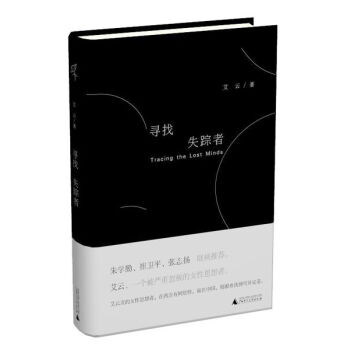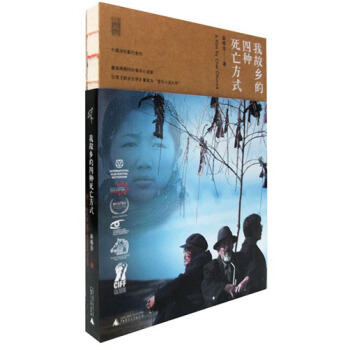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柴春芽被台湾文学《联合文学》誉为“青年小说大师”,是当代最值得期待的青年小说家。《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部电影是中国诗电影的代表作,该片获得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首作奖,入围第9届北京独立影展、第48届台北金马影展、第41届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和第30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初选入围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和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而《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部小说打破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界限,将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映照,以“电影小说”新文体的探索展示了柴春芽的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深沉内涵。书稿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现实与幻象交织,探讨了死亡的现象与本质。
在技巧上,《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打破了线性的叙事结构,魔幻与现实相结合,故事记录和灵魂拷问相衔接,多维地多元素呈现从而更自然地流露出作者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
内容简介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本书包含了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部分,在电影故事发展的线条中也融入了作者坎坷的拍摄经历,文字上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并且在书中作者以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宗教徒般的救赎情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诗意而荒凉的世界。同时,这部小说打破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界限,将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映照,以“电影小说”新文体的探索展示了柴春芽的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深沉内涵。书稿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现实与幻象交织,探讨了死亡的现象与本质。
作者简介
柴春芽,被台湾文坛称为“青年大师”的本土作家,被称为南周文字最好的摄影记者。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平面媒体任深度报导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任副刊编辑和图片编辑;2002年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任《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和《南方周末》驻京摄影师;曾有摄影专题《沿途的秘密》(Somethingin theway)参展2004年平遥国际摄影节。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执教,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在此之前,曾经多次游历卫藏、安多和康巴三大藏区;2010年驻台两月;著有小说《西藏红羊皮书》、《西藏流浪记》及《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其中《西藏流浪记》获台湾联合文学奖,简体版为《寂静玛尼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目录
Ⅰ为了一种电影小说。
东西方智力的鸿沟源自便于抽象思维的拼音文字
与适合事物表象之感官描述的象形文字的发明
Ⅱ
在十月。
小说是欧洲文明的产物。
皮影和电影的区别。
被剿杀在古堡里的三民主义者是谁
Ⅲ
我要拍摄一部具有哀歌或挽歌性质的独立电影
Ⅳ
电影主人公尕桂为什么选择自杀?
我初中的好朋友G被轮奸致死。
尕桂在沉溺的瞬间凝视了现实与超现实的多维空间
V
做一个行动主义者
而不是像怨妇一样沉浸于苦难的倾诉
VI
荒诞作为一种生存的境遇。
中国的红卫兵与法国“五月风暴”的少年。
一位友人想要成就我的电影的梦想。
VII
被神灵附体的史天生在回忆。
你相信一个神灵和鬼怪的世界与我们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吗?
VIII
汉语世界充满了被污染的言辞。
史天生仍在讲述记忆。
记忆像火焰一样。
1960年代的大饥荒。
IX
宇宙的真相:因陀罗之网。
X
寻找热卡亚。
古堡上的乡村诗人朗诵着具有警戒意味的诗歌。
乡村诗人和邻家男孩。
为了他那伤痕累累的自尊心。
XI
中国文学的野蛮状态持续千年。
我们从来不曾产生职业文化,我们只有发达的官僚文化。
地方官员粗暴地阻止我拍摄电影。
XII
七面大立镜中间盘腿坐着的史天生。
在棺材里生活了七年的愤世嫉俗者。
XIII
夭折的萨满舞蹈。
官方和民间始终横亘着一条巨大的裂谷。
XIV
电影拍摄陷入停滞。
想起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警察殴打。
我们不是感染,而是遗传了极权主义的恐惧症。
XV
梦。
在浑浊的激流中被淹没的梦。
关于鸟身狮头怪物的梦,它预示了什么?
XVI
死亡与地水火风。
尕桂在回乡路上遇见了热卡亚。
XVII
尕桂的饰演者是个篮球运动员。
腊梅。
会发出猫头鹰叫声的疯女人。
我怀疑热卡亚和腊梅患有梦游症。
XVIII
时间之马。
我们人类跟鸟的聪明一样愚蠢,所以我们习惯了在假象的天空中飞翔。
XIX
阿爸,你已经在棺材里生活了七年了。
XX
被暴力摧残的电影节。
现代艺术致力于解放心灵,而古代艺术则被用于祭祀。
你是否记得社火游行?
XXI
为什么一个愤世嫉俗者的死,竟与一只骆驼的死有关。
热爱库斯图里卡的电影。
太阳也会死吗?)
XXII
冬天的死寂映衬着尕桂的出走。
我是如此热爱马木尔的音乐,因其尊贵的品质。
XXIII
各民族都在弹拨那古老的口弦。
走进苏干尔湖的少女。
消逝于水,消逝于永恒的水。
XXIV
戈达尔越到后来,所用镜头越少,一个小时也就十个镜头。
尤利西斯的凝视。
三民主义者的鲜血渗入土地。
以一种理想谋杀另一种理想。
精彩书摘
我之所以敬仰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缘于他的多才多艺:农艺师、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和业余画家。当然,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那些论战性的文章──比如《为了一种新小说》──具有哲学性的深刻。罗伯-格里耶一贯反对把小说搬上银幕,因此,他给作为导演的自己及其助手还有技术人员制作了一份类似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一样的文本,比如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L’Annéedernière àMarienbad,1961)、《不朽的女人》(L’Immortelle,1963)和《格拉迪瓦在叫你》(C’est Gradivaqui vousappelle,2002)等,这些文本里有关于音轨的说明,有关于摄影机如何运用的说明,等等。他为这种文本发明了一个词:电影小说(ciné-roman)。在《不朽的女人》一书的导言中,阿兰·罗伯-格里耶给了电影小说一个这样的定义:人们即将读到的这本书,并不自诩为一部自成一体的作品。作品,是电影,如人们在电影院里看到和听到的那个样子。而在这里,人们只能找到对它的一种描绘:举个例子吧,这就好比对一部歌剧而言,它是剧本,配有音乐总谱,还有布景提示,表演说明……对没能去观看放映的人来说,电影小说还能够像一本乐谱那样被人阅读……
结合我编剧并导演第一部电影的经验,我愿意把对小说和电影的研究结合在同一个文本里。我愿意尝试一种新的文体写作,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既现实又超现实。也就是说,我想要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小说,也即电影与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彼此映照的新的小说。就我的理解(可能是浅薄的,甚至是谬误的)来说,电影小说(如果说真有这样一种小说的话),以打破小说和电影剧本在文体学上的差异,进而打破现实与非现实的铁幕。其实,早在1970年代我尚未出生之前,伟大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就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了。我只是在阿兰·罗伯-格里耶所定义的电影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叙事的成分,并且吸收了他那混合着自传与虚构故事的《重现的镜子》(或是《昂热丽克或迷醉》,或是《科兰特最后的日子》)的写作技巧,从而使电影小说在挖掘叙事之可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但是,每每想及自己受到阿兰·罗伯-格里耶如此深刻的影响,,我就痛感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Influence)之折磨,竟至于手指痉挛到有些不能敲打键盘以便写下自己贫弱的记忆和肤浅的思考以及畏葸的实验。在阿兰·罗伯-格里耶和我之间,间隔着两个遥远大陆的两个文明体系那至今不可跨越的智力的鸿沟(而且这智力的鸿沟日益扩大)。
智力的鸿沟可能源自便于抽象思维的拼音文字与适合事物表象之感官描述的象形文字的发明。也就是说,象形文字是感官的产物,而拼音文字是思维的产物。当我们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超绝万物的唯一而又绝对的“TheGod”和“All·h”译为“上帝”、“天主”或“真主”的时候,我们显然是降低了“TheGod”和“All·h”的神之属性,使其具有拟人的物化倾向从而不再超绝万物,不再绝对唯一。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书名,像一首低吟浅唱的民谣,又像一声饱含深情的呼唤。它没有直接点明故乡的美好,而是以一种更为深刻、更具冲击力的方式,将“故乡”与“四种死亡方式”联系起来。这让我不禁思考,作者所说的“死亡”,究竟是指什么?是故乡的地理环境的剧变,比如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或是自然灾害的侵蚀?还是文化层面的消亡,比如传统手艺的失传,古老歌谣的无人传唱,亦或是人与人之间淳朴情感的淡漠?“新民说”这个词,又仿佛是一种时代的召唤,一种在变革中对“新的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去感受那些隐藏在日常之下的、令人心痛的“死亡”景象。作者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悲伤的主题下,挖掘出四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去展现故乡的变迁与生命的顽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于自身故乡的深刻反思,也能够让我理解,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如何去守护那些珍贵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根。
评分这本《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书名,初读之下便在心头激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涟漪。它不像那些直白的讲述,而是用一种含蓄而富有诗意的方式,将一个核心议题——“死亡”——与“故乡”这个充满情感羁绊的地理坐标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抽象为“四种方式”。这本身就充满了引人探究的张力。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书页,看看作者究竟是如何描绘这四种死亡的,它们是具体到人的离世,还是更宏观的,关于故乡消失、文化断裂、记忆的消逝?抑或是,人与故乡之间那种看不见却深刻影响着灵魂的联系的终结?“新民说”这个词组,又似乎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在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传统、审视个体与集体命运的尝试。我的故乡,那个承载了我童年嬉闹、少年迷茫、成年后又时常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否也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死亡”?这让我开始反思,当我们谈论故乡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那些熟悉的街道、建筑,还是那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景象?是与我们一同成长、一同老去的人们,还是那些我们早已遗忘却依然深刻烙印在记忆深处的片段?作者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中,寻找出“四种”不同的维度,去剖析这种“死亡”的发生,去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是我最期待看到的。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挽歌,更是一种对当下普遍存在的“失落感”的深刻洞察,一种对我们在快速变迁的世界中如何寻找根源、如何安顿灵魂的思考。
评分当我看到《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时,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它既有一种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又有一种对时代变迁的深刻忧虑。“故乡”这个词,承载了太多我们生命中的最初记忆和情感联结,而“四种死亡方式”则赋予了这份眷恋一种迫切的审视。我迫切想知道,这四种“死亡”究竟是指什么?是物理空间上的消亡,比如老街的拆除,老宅的倒塌,还是非物质层面的流失,比如传统技艺的失传,风俗习惯的改变,亦或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挚的情感联系的淡漠?“新民说”这个词组,又暗示着一种变革与新生,一种在旧的模式终结之后,如何寻求新的生存之道。“故乡”在我们心中,既是出发的原点,也是心灵的港湾,当故乡本身面临“死亡”,我们又将何处安放我们的灵魂?我期待这本书能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方式,描绘出故乡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希望作者能够用冷静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展现出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死亡”,并引发我们对“根”与“身份”的深层思考。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它没有用那种过于煽情的语言,而是用一种冷静而富有力量的叙事,直接将“故乡”与“死亡”这两个沉甸甸的词语并列。但“四种方式”的引入,又让这个话题变得更加具体和有深度。我立刻开始想象,这四种“死亡”会是怎样的景象?是土地的沦丧,是生态的破坏,是文化的断裂,还是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熟悉的面貌,在时光的洪流中,无可挽回地消失?“新民说”这个词,又像是在为这种“死亡”注入一种新的生命力,一种在旧事物消逝后,新的事物将如何孕育和生长。我的故乡,那个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否也正以这四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悄然发生着改变?我期待这本书能够用细腻的笔触,将那些被忽视的、隐秘的“死亡”过程,真实而深刻地呈现出来。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这些故事,引发我们对于“故乡”更深层次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根基,是我们精神的归宿。
评分初见《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书名,一种复杂的情绪便在心头交织。它既有一种怀旧的温情,又带有一种警醒的锐利。“故乡”二字,承载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而“四种死亡方式”则为这份温情注入了一种迫切的审视。我很好奇,这四种“死亡”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它们是直接的物理消失,如旧时的村落被高楼取代,田野被钢筋水泥覆盖?还是更为隐晦的,文化的断层,传统的式微,甚至是我们与故乡之间那种原生的、难以言说的连接的消逝?“新民说”这个词组,又似乎指向一种在变革中寻求答案的可能性,一种在旧有模式消亡之际,孕育新生的希望。“故乡”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既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心灵的归宿,那么,当故乡本身面临“死亡”,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深入故乡的肌理,去感受那些在时代变迁中悄然发生的变化,去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却是深刻的“死亡”过程。我希望作者能够用一种真诚而富有力量的笔触,描绘出故乡的哀伤与坚韧,以及在这种“死亡”面前,我们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如同一个抛向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它不是那种浅显的怀旧,也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用一种更为成熟、更为沉重的视角,将“故乡”这样一个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主题,置于“四种死亡方式”的框架之下。这让我立刻开始好奇:这所谓的“四种死亡”,究竟会以何种形态出现?是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在时间的侵蚀下,一点点瓦解崩塌?是那些代代相传的乡土文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渐被遗忘,无人问津?是曾经淳朴、热情的乡邻,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疏远而冷漠?还是,是故乡与我之间,那种曾经紧密相连、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在距离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悄然发生的断裂?“新民说”这个词,又像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一种在旧有秩序消亡之际,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对“新的人”的期许。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故乡在时代的洪流中,所经历的种种“死亡”,并引发我对故乡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反思。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仿佛一道古老而又新颖的门扉,吸引着我想要一探究竟。它将“故乡”这个充满情感重量的词汇,与“四种死亡方式”这个充满解构意味的提法并置,瞬间便激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我想知道,这“四种死亡”究竟是指什么?是土地的流失,风貌的改变,还是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人,以及那些代代相传的习俗,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终结?“新民说”,又似乎暗示着一种对传统的反思与革新,一种在旧的模式消亡之后,如何寻找新的出路,如何重塑“新的人”与“新的故乡”的连接。我的故乡,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是否也正经历着书中描绘的这些“死亡”?作者是如何在一个如此宏大且深刻的主题下,构建出四个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叙事?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进入一个充满思辨的旅程,让我重新审视我对故乡的认知,理解那些正在发生的、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变化,并或许从中找到一些关于如何面对“失去”与“新生”的启示。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就像一封寄往遥远过去的信,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邀请。它不是直抒胸臆的告白,而是以一种含蓄而富有哲思的语言,将“故乡”这个承载了无数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的词语,置于“四种死亡方式”这样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框架之下。这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作者所描绘的“死亡”,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是那些老建筑在时光侵蚀下的坍塌?是那些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在信息洪流中的淹没?是淳朴的民风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异?还是,是故乡与我之间那种曾经紧密的、不言而喻的联系,在距离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悄然发生的裂变?“新民说”这三个字,又仿佛是一种宣言,一种在历史的长河中,试图为“故乡”寻觅新的生命力、新的意义的探索。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的故乡,也映照出无数个“故乡”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我渴望看到作者如何用细腻的笔触,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象的场景,如何将个体化的情感体验升华为对时代症候的深刻洞察。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更可能是一本关于我们与根源、与历史、与自我关系的思考。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个书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仿佛是一道带着一丝神秘色彩的邀请函。它没有直接歌颂故乡的美好,而是以一种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方式,将“故乡”与“四种死亡方式”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让我立刻开始思考,这“四种死亡”究竟是指什么?是故乡的自然风貌的改变,土地的荒芜,河流的干涸?还是故乡的文化传承的断裂,那些曾经熟悉的乡音、习俗、故事,在时代的洪流中渐渐消失?抑或是,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挚的情感联结的淡漠,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在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中,变得越来越罕见?“新民说”这个词,又暗示着一种变革与新生,一种在旧有模式消亡之后,如何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深入故乡的肌理,去感受那些在时代变迁中,不为人知却又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我希望作者能够用一种真诚而富有力量的笔触,描绘出故乡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从而引发我们对“根”的思考。
评分读到《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书名,一种浓厚的乡愁似乎瞬间涌上心头,但又被“四种死亡方式”这个颇具颠覆性的提法所打破。它不仅仅是关于故乡的怀念,更像是一种深刻的审视,一种对故乡正在发生的、不容忽视的改变的直面。我很好奇,这“四种死亡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它们是物理层面的消失,比如老房子的拆迁、土地的荒芜;还是精神层面的消亡,比如传统习俗的遗忘、人情味的淡漠、年轻人对故乡的疏离?又或许,作者将故乡比作一个生命体,它经历了不同的衰败过程?“新民说”这个词,更是让人浮想联翩,它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一种在变革中寻求新生、寻找身份认同的努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个人回忆录,而是能够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现实,能够用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故乡在我们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它在我们生命旅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变迁。我的故乡,那个承载了我最初的记忆和情感的地方,它是否也像书中描绘的那样,正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死亡”?作者是如何在这样的主题下,挖掘出“四种”不同的叙事角度,来呈现这种复杂而又普遍的现象?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自己故乡更深层次的思考,也能够让我理解,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我们如何看待和维系与故乡的情感联系。
评分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一点,一点,一点点地看完了朝花夕拾,连串的时间,连串的记忆,真想将鲁迅爷爷的记忆当做我的。整本文集用词语简洁柔和,正是鲁迅爷爷的平易近人的体现。书中的抨击,讽刺,嘲笑,正是鲁迅爷爷对当时社会的反感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安定,为孩子着想的鲁迅爷爷。柴春芽,园中淘气天真的小孩子,观菜畦、吃桑葚、听鸣蝉与油蛉和蟋蟀的音乐会,看黄蜂、玩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到在书屋读书习字,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课上偷偷画画,到书屋的小园玩耍。无一不体现出小孩子追求自由,热爱大自然的心态,也表现了社会对孩子们的束缚。柴春芽被台湾文学联合文学誉为青年小说大师,是当代最值得期待的青年小说家。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部电影是中国诗电影的代表作,该片获得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首作奖,入围第9届北京独立影展、第48届台北金马影展、第41届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和第30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初选入围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和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而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部小说打破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界限,将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映照,以电影小说新文体的探索展示了柴春芽的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深沉内涵。书稿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现实与幻象交织,探讨了死亡的现象与本质。在技巧上,新民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打破了线性的叙事结构,魔幻与现实相结合,故事记录和灵魂拷问相衔接,多维地多元素呈现从而更自然地流露出作者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这两个人物,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两个由当时社会造就的人物。一个下层的劳动者,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的阿长,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社会思想毒害的结果,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浑浊、昏暗。正直倔强的爱国者范爱农,对革命前的黑暗社会强烈的不满,追求革命,当时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体现了旧社会人民对束缚的反抗,向往自由、安乐的心。人民从囚禁中走向了反抗。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这本书包含了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部分,在电影故事发展的线条中也融入了作者坎坷的拍摄经历,文字上充满了诗意,哲学和宗教气息,并且在书中作者以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宗教徒般的救赎情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诗意而荒凉的世界。同时,这部小说打破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界限,将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映照,以电影小说新文体的探索展示了柴春芽的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深沉内涵。书稿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现实与幻象交织,探讨了死亡的现象与本质
评分记录了故乡的许多故事,文字还不错
评分对诗电影的一种解读,文字有看点
评分这是一本好书,非常值得买。
评分书中表露的原罪感很强。我的一些朋友读后都很赞同台湾联合文学对于柴的评价:“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但对中国人来说原罪是外来之物,太过强烈未免矫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原罪首先就应当承认自己没有原罪情结,不知救赎为何物。自卑者往往妄自尊大,能够保持正常心理状态的可说实在难得。说一句题外话,尽管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多已不屑李敖,譬如莫之许先生就曾对我提过李敖的投机,但当年杨照对李敖的评判放在前者(原罪感爆表的知识分子)身上恐怕未必不宜。杨照在《读<李敖快意恩仇录——绝对的意见、绝对的坚持>》一文中说:“李敖在一次次的反弹、报复与镇压中,近乎奇迹地没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是绝对不曾错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缩与虚伪的神色,更加感觉到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历经了勇气与义气的考验。他也就养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绝对的标准来武装自己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近乎我执的执信,也就直接导致了意见的僵固与无法变更。事实上,胡适之先生晚年一直坚持的“容忍远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从李敖到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皆难看到。芥川龙之介说:“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你所反对的却成了另一个你,日后的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评分书中表露的原罪感很强。我的一些朋友读后都很赞同台湾联合文学对于柴的评价:“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但对中国人来说原罪是外来之物,太过强烈未免矫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原罪首先就应当承认自己没有原罪情结,不知救赎为何物。自卑者往往妄自尊大,能够保持正常心理状态的可说实在难得。说一句题外话,尽管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多已不屑李敖,譬如莫之许先生就曾对我提过李敖的投机,但当年杨照对李敖的评判放在前者(原罪感爆表的知识分子)身上恐怕未必不宜。杨照在《读<李敖快意恩仇录——绝对的意见、绝对的坚持>》一文中说:“李敖在一次次的反弹、报复与镇压中,近乎奇迹地没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是绝对不曾错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缩与虚伪的神色,更加感觉到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历经了勇气与义气的考验。他也就养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绝对的标准来武装自己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近乎我执的执信,也就直接导致了意见的僵固与无法变更。事实上,胡适之先生晚年一直坚持的“容忍远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从李敖到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皆难看到。芥川龙之介说:“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你所反对的却成了另一个你,日后的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评分看了很受启发,好书!
评分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一遍了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 但是是自愿的没买 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评分我的这篇书评写得要算很慢了,本属可写可不写之间,但由于作者的一些意见我很赞同,而一些意见我很不赞同,所以坚持将这篇文字写完。且以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的一段话作结:“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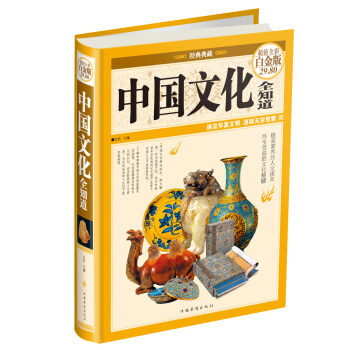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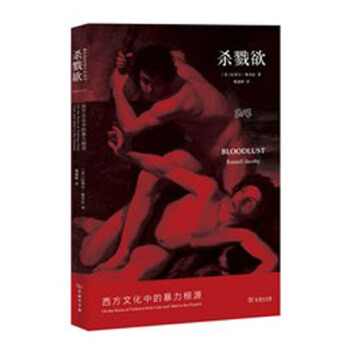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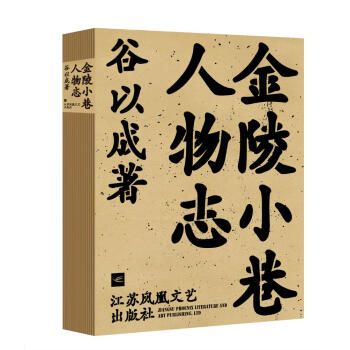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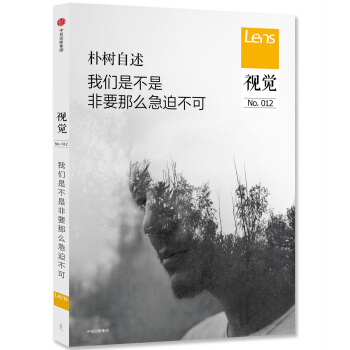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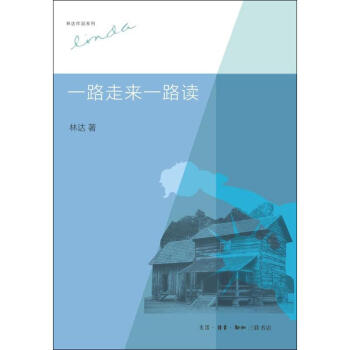

![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 [The Third Report on the Rural and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Study for the Capital Reg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4821/58ed9921N27c74ec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