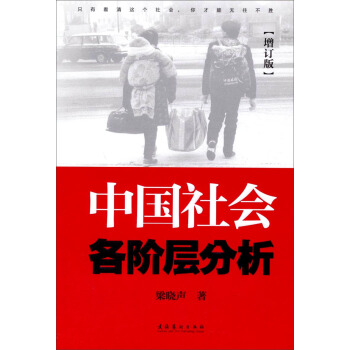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已经阶层化了。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咂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版)》中梁晓声对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老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中国农民工、中国当代“黑社会”以及中国“灰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作者简介
梁晓声,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至今作品逾千万字。作品曾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雪城》、《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民选》等。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引言
第一章 当代资产者阶层
附:俯瞰商业时代
关于资产者阶层
尴尬的现象
第二章 当代“买办”者阶层
第三章 当代中产者阶层
第四章 当代知识分子
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贫民
第六章 农民
第七章 中国农民工
第八章 中国当代“黑社会”
第九章 中国“灰社会”
附录:
关于土地的杂感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当务之急是教育谁?
精彩书摘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鳟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日“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
……
前言/序言
此书写于1996年,某些章节曾发表于报刊;1997年成书出版,至今十三年了。十三年中,未曾再版。
倒也不是遭遇过禁止,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肯于再版。事实上希望再版此书的出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却一次次拒绝了。
原因单纯,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看法越来越不怎么样。我对自己其他书的看法也有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说。小说家们十之八九都写过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小说,即使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由于成为自己某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证明,只要别人以为还有点儿再版的价值,自己们往往也就悉听尊便了。
然而我这一部书却非小说。究竟算是哪一类书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时评类的?沾那么一点儿意思吧。
我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比如冷静、客观、公允、详实的依据等等。当然,若有预见性,并且预见得较准,最好。总而言之,时评类的书,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为上。
而我这一本书,它的情绪色彩太浓了。
故当年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
小说家而写非小说类的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不务正业”的批评是不以为然的。
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本书呈现了显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当年不满也很忧虑的,其实不是富人们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种“体制”问题。
正因为不满很强烈,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又不愿被讥为“杞人忧天”,所以成心用了一种调侃的文笔来写。结果不但情绪色彩太浓,也同时缺少了一部好的时评书应有的理性庄重,那么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
现在我正做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的事情。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某一部书不怎么样,但希望通过修改,“改判”其“死刑”,尽量使之“重见天日”。
在修改过程中,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不满一次次使我停止下来--因为十三年后的今天看十三年前的自己的这一部书,荒唐印象每每产生。比如十三年前的富人与今天的富人们相比,富的概念是太不一样了;十三年前我这种人的工资才六七百元,普遍国人对工资的诉求与今天相比差距也太大了;十三年前“下岗”是中国城市剧烈的阵痛,而今天这种阵痛基本熬过去了;十三年前农民们的生存负担已快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而今天的农民们之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最主要的是--十三年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对于中国当年之现实是极其悲观的,而十三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主调,应该说已走出了悲观的阴影……
何况,我此书中片面的、偏激的、浅薄的文人之见比比皆是,改不胜改。最后也就只有不改,随它那么样了。
我还是决定让它“重见天日”的。起码,看了此书的人可以了解到,竟有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我们中国诸事,十三年前“不务正业”地想了那么多,自以为是地公开发表了那么多看法。
在有几章的后边,我加了些今天重新来看来想的补白。
在此前言中,我最想补的有以下两点:
一、对于从政的、从商的,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一个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章来进行评说的,即--知青群体。十三年前我没这样写,现在认为实在是大的遗憾?
我对“上山下乡”运动再没多少话可说。一言以蔽之,不论对于他还是对于中国,那都是没有另一种选择的事。
但“上山下乡”客观上却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其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总体上是那样)结合了十余年之久。这使他们对于“中国”二字具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于“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我的朋友秦晓鹰曾任《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主编;也是干部子弟,当年是山西插队知青。
十三年前我写这一部书时,我们曾一起开过一次什么座谈会。
会上,他讲过这样一件真事:返城开始后,有一名高干子弟终于可以返回北京了,十余年来他一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大爷和大娘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硬往他兜里塞鸡蛋,非让他带回北京一篮子大枣……夕阳西下时分,已走出了很远的他不禁地再一次回望,但见大爷和大娘的身影仍站在一处土崖边,之间隔着一道道沟堑。那一时刻,那一名高干子弟,不禁地双膝跪下,痛哭失声……
晓鹰对我讲的这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以至我又对别人讲过多次,并写入了我的电视剧新作品《知青》中。
那一名高干子弟,他返回北京又成为高干子弟后,会变吗?
又变回高干子弟“本色”的例子是不少的。
但,因为有着十年“上山下乡”那一碗粗饭垫底儿,以后无论身份怎么变,地位怎么变,对“人民”那一份儿深情厚谊非但没变,反而化作人性深处的“琥珀”;这样的“知青后”也是不少的。
那么,不管他们是从政了,是经商了,还是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了,都必然会是人文化了的从政者,人文化了的经商者,人文化了的知识分子。
进言之,他们将会使中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变得“有良心”。
倘无对人民的真感情,我不知所谓“人文”是什么“文”……
二、在我这一部书中,对于歌星们(当然也包括歌唱家们)多有不敬之词,这也是极使我忐忑不安的一点。
十三年后的今天我想说,作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汉族成员,我在此对他们和她们,郑重地表达我的大敬意。并且,因我书中当年写下的某些调侃的、戏谑的词句,郑重地表达我的真诚歉意。
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歌星们,尤其是汉族歌星们,正是他们和她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甚至可以说“改造”了汉民族。
我强调“尤其是汉族歌星们”,并非是要张扬一种“大汉民族”的狭隘意识,而仅仅是想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古代的汉民族,虽然不是一个善舞的民族,但也确曾是一个能歌的民族。
想想吧,连那时的樵夫和渔父、养蚕娘和采茶女都喜欢高歌低唱,证明汉民族也曾是一个多么爱唱的民族啊!但是越往近代过渡,爱唱的汉民族,分明的越不爱唱了。国难深重的近代,纵还
有些歌流行着,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愤激的歌。又往往的,是由一些人唱给众多的人来听的。1949年以后,汉族所唱的歌,渐渐变得极端政治化了。抒情的歌是极难产生的。以至于,汉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歌,要么是1949年以前的,要么是其他兄弟民族的,要么是外国的……
而今天,汉民族又变得空前能歌了!
尤其在城市里,到了春暖花开后的季节,街头歌者,公园里的歌声,往往的,真叫是此起彼伏。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居然是一个不爱唱歌的民族,那真叫是世界性的遗憾了!
现在好了,我们又恢复了爱唱的本能了。
而我认为,汉民族的这一种本能的恢复,与20世纪80年代后一代代汉族歌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大情怀也罢,小情调也罢,普遍情感也罢,人性私密情感也罢……总而言之,爱唱就比不唱好,唱出来就比压抑着好。
举凡一切与人情有关的情怀、情愫、情感、情调、情绪,三十年来,我们的汉族歌手们,几乎全都引领着我们汉民族唱遍了。
我们太有理由感激他们了。
而且,以我的眼看来,扫描中国大文艺状况,恰恰是通俗歌曲的品质反而优上一些。
因为,通俗歌曲中几乎什么都唱到了,就是没有一首通俗歌曲是唱权术计谋的。
也正因为如此,通俗歌曲反而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人性化”,而不是使人性狡猾和阴险……
2010年9月4日于北京
用户评价
从阅读的体验感上来说,这本书绝对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灵活,时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时而又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分享他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我尤其喜欢书中穿插的许多真实案例和访谈记录,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让冰冷的社会学理论变得有血有肉,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每当我合上书本,总会陷入沉思,思考书中提到的那些问题与我自身的生活,与我所处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上,而是深入剖析了每个阶层形成的原因,以及他们行为逻辑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我曾一直以为,某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只是个别现象,但读了这本书后才明白,很多时候,这些现象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深层矛盾的体现。作者的分析非常客观,也充满了同理心,他不会简单地去批判某个阶层,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去揭示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这种辩证的视角,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对社会和他人的固有认知,也促使我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评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版)》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理解中国”的教科书。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微观的个体体验出发,去窥探宏观的社会变迁。在阅读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我认识社会和理解他人的方式。这本书不光能让你了解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更能让你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挣扎、追求与无奈。对我而言,这本书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唤醒。
评分不得不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版)》在细节的捕捉上堪称一绝。作者仿佛拥有一双能够穿透表象的眼睛,他能够敏锐地发现那些隐藏在日常琐事中的社会密码。比如,书中对不同家庭在教育子女上的投入和期望差异的描写,就非常细腻,也极具代表性。我读到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部分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种深沉的无奈和对父母的期盼,让我深刻体会到阶层固化带来的情感隔阂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这种对个体命运与宏大社会背景之间关联的深刻洞察,是许多社会学著作难以企及的。
评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版)》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翻阅一本厚重的历史画卷,每一页都承载着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大学时代,当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还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概念层面,而这本书却以一种极其生动、贴近生活的方式,将那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了。作者的文字功底相当了得,他能用一种平实却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勾勒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心理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互动。我记得其中有一段关于城市白领的描写,将他们的焦虑、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我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觉作者仿佛就坐在我身边,分享着我内心的困惑。
评分东西不错,好评!
评分如图可以参考,好好看看。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活动的时候买的,很划算。京东送货就是快。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老师推荐的。 买了不少的书,一本一本的看吧。
评分对当前社会观察仔细深刻。
评分双11囤书,超优惠,放着慢慢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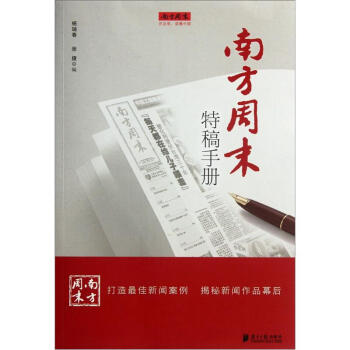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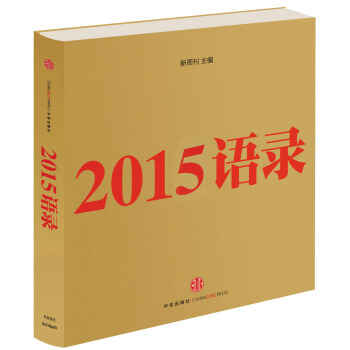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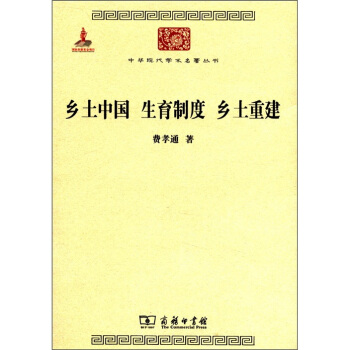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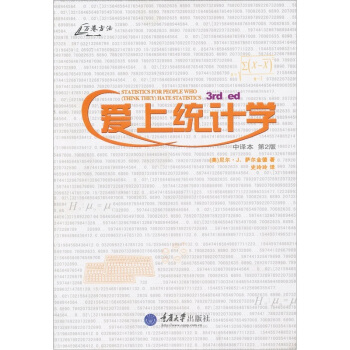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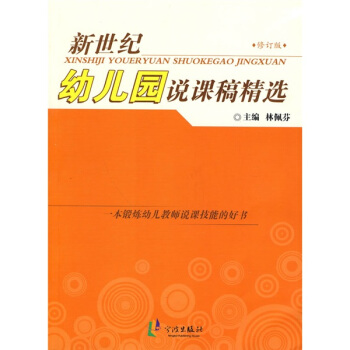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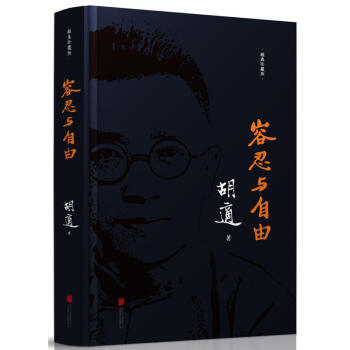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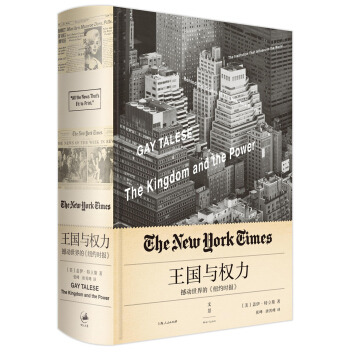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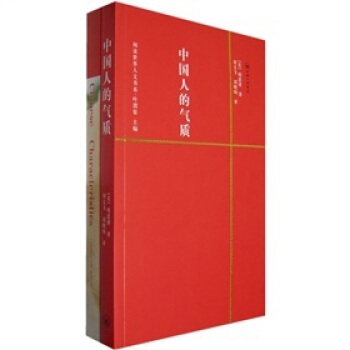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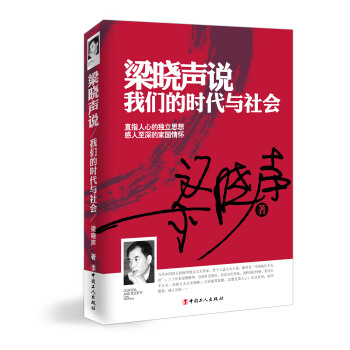

![金赛性学报告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60016/rBEhVFHBB14IAAAAAA2B06NWJtgAAAVcQFD4H8ADYHr32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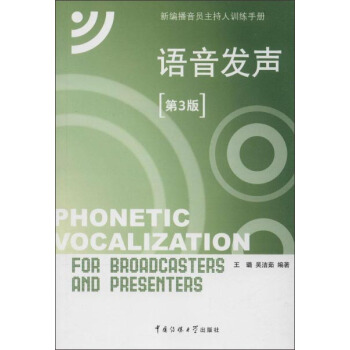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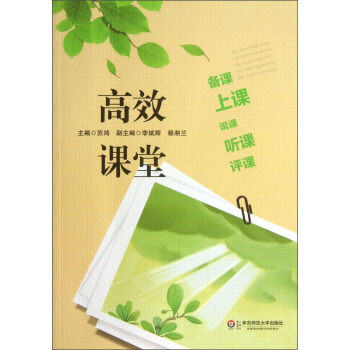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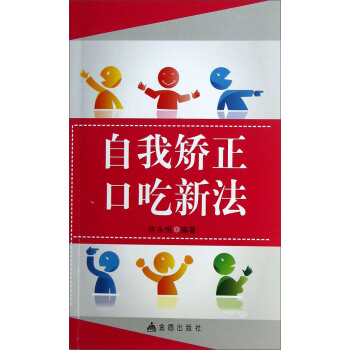

![理查德·桑内特作品集:匠人 [The Craftsm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5283/55c7fc7cN7353ee3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