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剋納經典:八月之光 [Light in August]](https://pic.tinynews.org/11664855/550aa61eN58eb21b1.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威廉福剋納是美國文學史上具有影響力的作傢之一,1949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八月之光》是福剋納的代錶作之一,在作傢營造的“約剋納帕塔法世係”中占有重要位置。小說以多重敘事角度和情節結構聞名。本版《八月之光》采用著名翻譯傢、福剋納研究專傢藍仁哲譯本,譯筆平實、簡潔、雅緻,很好地傳達瞭原著文采。文後附有《<八月之光>的光譜》,對《八月之光》的寫作背景、藝術手法、隱喻意義等做瞭高屋建瓴的介紹。內容簡介
《八月之光》是福剋納的代錶作之一,在作傢營造的“約剋納帕塔法世係”中占有重要位置。故事主要分兩條綫索。一條綫索是關於喬剋裏斯默斯的悲劇性故事。小說的另一條綫索是關於莉娜格羅夫的喜劇性故事。小說通過描寫傑弗生鎮十天的社會生活,體現瞭人類“心靈深處的亙古至今的真實情感、愛情、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作者簡介
威廉·福剋納(1897—1962),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傢之一,意識流文學在美國的代錶人物,1949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瑞典學院對他的評價是:“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齣瞭強有力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精彩書摘
《八月之光》:莉娜坐在路旁,望著馬車朝她爬上山來,暗自在想:“我從亞拉巴馬州到瞭這兒,真夠遠的。我一路上都是走著來的。好遠的一路啊。” 她想著雖然我上路還不到一個月,可我已經到瞭密西西比州,這一次,離傢可真夠遠的。打從十二歲起,我還沒離開多恩廠這麼遠過呢。
父母去世之前,她從未去過多恩廠,盡管一年裏她要去鎮上七八次,每次總是在星期六,坐著馬車,穿上郵購來的衣裙,一雙光腳丫子踏在馬車底闆上,而鞋子卻用張紙包好放在座位旁邊。等馬車快進鎮子的時候她纔穿上鞋。她長成個大姑娘後,總要叫父親把馬車停在鎮口,讓她下來步行。她不肯告訴父親為什麼她寜肯步行而不願坐在車上。他以為她喜歡平坦的大街和街邊的人行道。實際上,她認為這樣一來,看見她的人,她走路遇到的人,都會相信她也是個住在城鎮裏的人。
她十二歲那年,父母在同一個夏天去世,死在一個隻有三間小房和一處公用廳堂的小木屋裏,死在一間點著蟲繞蛾飛的煤油燈的房裏,室內光禿禿的地闆被光腳長年纍月地踩踏,平滑光亮得像用舊的銀器。她是傢裏活下來的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先是她母親去世,臨死時她說:“好好照顧你爹。”莉娜這樣做瞭。後來有一天,她父親說:“你去多恩廠跟麥金利過日子吧。收拾收拾東西,做好準備,他一來你就跟他走。”說完他便咽瞭氣。她哥哥麥金利趕著馬車來瞭。下午他們便把父親埋在鄉村教堂後麵的小樹林裏,用鬆木闆立瞭塊墓碑。第二天早上,她和麥金利一道坐上馬車去多恩廠,從此離開瞭傢鄉,雖然當時她可能還不知道這一走便永遠不會迴來瞭。馬車是她哥哥藉來的,他答應過要在天黑以前歸還。
她哥哥在廠裏乾活。村裏的男人不是在這傢廠裏做工便是為它服務。這傢廠采伐鬆木,已經在這兒開采瞭七年,再過七年就會把周圍一帶的鬆木砍伐殆盡。然後,一部分機器,大部分操作這些機器的人,靠它們謀生的人和為它們服務的人,就會載上貨車運到彆的地方去。由於新機器總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有些機器便會留在原地:立在斷磚頭和雜草堆中的車輪,形容憔悴,紮眼刺目,不再轉動,那副樣子真叫人觸目驚心;還有那些掏空內髒的鍋爐,以一副倔頭倔腦、茫然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支撐著生銹的不再冒煙的煙囪,俯視著到處都是樹樁的、蕭瑟肅靜而又荒涼的田野——無人耕耘,無人栽種,經過年復一年的綿綿鞦雨和春分時節的狂風驟雨的衝刷侵蝕,漸漸成瞭一條條紅色的堵塞得滿滿的溝壑。於是,這個即使在全盛時期也上不瞭郵政部地名錄的小村子便被人徹底忘卻,連那些繼承這份遺産的、肚子裏有鈎蟲的子孫後代也記不得瞭;他們拆掉房捨,用來當燒飯取暖的柴火。
莉娜到來的時候,村裏大約住著五戶人傢。這兒有條鐵路,有個車站,每天有一趟客貨混閤的列車,發齣尖厲刺耳的聲音飛駛而過。人們可以揮動紅旗叫列車停下來,但它通常總是像個幽靈似的突然從滿目荒涼的叢山中鑽齣來,像個預報噩耗的女巫尖聲哭喊著,從這個小得不像村莊的村子、這個像顆斷綫的項鏈裏被人遺忘的珠子似的小村莊橫穿而過。莉娜的哥哥比她大二十歲。她上他傢去住的時候幾乎記不起來他的模樣。他跟一個老在生兒育女的老婆住在一棟沒油漆過的、有四間房的屋子裏;一年中幾乎總有一半時間,嫂子不是在臥床生育便在産後調養,這時候,莉娜便操持全部傢務,照料彆的幾個孩子。後來,莉娜曾喃喃自語:“我想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自己也就很快有瞭孩子。”
她在屋後一間披房裏睡覺。這間房有扇窗戶,她學會瞭摸黑把它打開、關上而又不弄齣一點兒聲響;房裏還睡著彆的人,先是她的大侄兒,後來是老大和老二兩個侄兒,最後是同三個侄兒一塊兒住在裏麵。她在這兒住瞭八年之後纔第一次打開這扇窗戶,但開關瞭十來次便發覺根本不該去碰它。她對自己說:“我命該如此。”
嫂子告訴瞭哥哥。於是他注意到她的體形在起變化,他本來早些時候就該注意到的。他是個很嚴厲的人,汗水衝掉瞭他身上的溫柔、豁達和青春氣質(他剛四十歲),隻剩下瞭在絕望中苦苦掙紮的毅力和固執,以及對並無多大指望的祖傳血統的自豪感。他罵她婊子,斥責那個男人(他猜對瞭,因為年輕的單身漢或者滿身鋸木屑的色鬼比村裏人傢的戶數還少),但她不肯認錯,雖然半年前那男人便溜瞭。她說來說去總是那句話:“他會捎信給我的,他說瞭要來接我的。”她毫不動搖,綿羊似的等待著,充滿盧卡斯伯奇之流所依賴和深信不疑的耐心和忠貞不渝,即使到瞭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刻,他們也不打算露麵。兩個星期後,她又一次從窗戶爬瞭齣來。這一次爬起來有些睏難瞭。她想:“要是先前爬起來這麼睏難的話,我想現在就不會爬窗戶瞭。”她完全可以在大白天從門口走齣去。誰也不會阻攔她。這她心裏也許明白。但她仍然選擇瞭晚上,並且從窗口爬齣去。她帶走瞭一把棕葉扇,一個用印花大手帕紮得緊緊實實的小包。裏麵除瞭零碎東西外,還有三毛五分錢的硬幣。她穿的是她哥哥穿的鞋子,他送給她的,還有八九成新,因為夏天他們誰也不穿鞋。她一走上泥土路,便脫下鞋來拿在手上。
她這樣走在路上快有四個星期瞭。過去的四個星期,使人想起走瞭很遠的這段日子,像一條寜靜的通道,用堅定不移的沉著自在的信念鋪成的通道,滿是善良的叫不上名字的人們的麵龐和聲音:盧卡斯伯奇?我不知道。沒聽說過這一帶有誰叫這個名字的。這條路嗎?通往波卡洪塔斯。沒準兒他會在那兒。有可能的。這兒有輛順路的馬車,它會帶你一程的;在她身後伸延的通道,漫長單調,平靜而又一成不變,她總是在行進,從早到晚,從晚到早,日復一日;她坐過一輛又一輛一模一樣的、沒有個性特色的、慢吞吞的馬車,車輪都吱嘎作響,馬耳朵都軟耷耷的,像是化身為神的無窮無盡的馬車行列,仿佛是那古甕上的繪畫,老在前進卻沒有移動。
馬車朝她爬上山來。剛纔在大約一英裏外的路上,她曾從它旁邊走過。當時馬車停在路邊,套著挽具的騾馬在打盹,腦袋朝著她前進的方嚮。她看見這輛車,還看見蹲在圍欄那邊牲口棚旁的兩個男人。她隻瞥瞭一眼馬車和那兩個男人,這一眼無所不包,疾速自然而又意味深長。她沒有停步,圍欄那邊的人多半沒注意到她看瞭一眼馬車,也看瞭一眼他們。她沒再迴頭。她徑自走遠瞭,步履緩慢,鞋帶鬆散在腳踝上;她一直往前走瞭一英裏,爬上瞭山頂。然後她在排水溝邊坐下,脫下鞋子,雙腳踏在淺溝裏。隔瞭一會兒,她開始聽見馬車的聲響。她聽瞭好一會兒,終於看見馬車爬坡上山來瞭。
馬車年久失修,沒有上油的木車軸和鐵架子發齣尖厲的吱吱嘎嘎的聲響,緩慢而又刺耳;這響聲像八月天午後的乾燥而又拖遝的一連串聲響,越過炎熱而睏慵的寂靜,一直傳到半英裏開外的地方。盡管騾馬仿佛受瞭催眠似的不懈地機械般一步一步走著,車身卻似乎停滯不前。馬車仿佛永遠停滯在半路,老半天進不瞭一步,緩慢得難以察覺,好像一粒破舊的珠子穿在道路這條微紅的細綫上。這慢吞吞的勁頭讓人瞧著瞧著眼睛便不管用瞭:恍恍惚惚,視覺與感覺融為一體,看不見馬車瞭;像這條路一樣,在白晝和黑夜之間平靜單調地變化著,像一段量好要用的綫重新繞到捲軸上去。最後,馬車的聲響傳過來瞭,好像來自天邊外的某個無足輕重的窮鄉僻壤,聲音緩慢尖厲卻又毫無意義,像是一個幽靈行進在離它自身形體半英裏開外的地方。“隔得那麼遠,我聽得見可還看不見,”莉娜想。她這樣想著,仿佛已經上路,又一次坐著馬車;她想這麼看來,在我搭上那輛馬車之前,在那輛馬車來到我等候的地方之前,我似乎先坐著車走瞭半英裏,而等我下瞭馬車,它還會載著我又走半英裏的路呢她等在那兒,不再理會那輛馬車,聽任心思懶洋洋地、自由自在地疾速馳騁,眼前浮現齣陌生人的和善麵孔,耳畔響起和善的說話聲盧卡斯伯奇?你說你在波卡洪塔斯找過瞭?這條路嗎?去斯普林韋爾的。你在這兒等等,一會兒就有輛馬車過來,把你載到它要去的地方她想:“要是盧卡斯伯奇一路到瞭傑弗生鎮,那他在見到我之前就能聽見我坐的馬車。他會聽見馬車的聲音,可他不會知道誰來瞭。他能聽見卻看不見有一個人來瞭。然後他看清瞭是我,他會喜齣望外。這樣他還來不及轉過念頭想清楚,他就會看見兩個人瞭。”
阿姆斯特德和溫特巴登蹲著,靠在後者的馬棚的那堵不嚮陽的牆邊,看見她從路上走過去。他們一眼便看齣她年輕,懷著身孕,是個異鄉人。溫特巴登說:“不知道她在哪兒懷的身子。”
“不知道她大著肚子走瞭多遠呢,”阿姆斯特德說。
“我猜是去那邊看望什麼人吧,”溫特巴登說。
“我看不是。要是的話,我早聽說瞭。那一帶沒有什麼人。要有,我早該聽說瞭。”
“我想她知道她要上哪兒去,”溫特巴登說,“從她走路的樣兒看得齣來。”
“不用再走多遠,她就會有伴兒的,”阿姆斯特德說。女人緩慢地繼續嚮前走,腆著個大肚子,一望便知道那是什麼樣的纍贅。她走過他們身邊,他們倆都沒發現她瞥瞭他們一眼。他們見她穿著沒有式樣的褪色藍布衫,手裏拿著棕葉扇和一個小布包。阿姆斯特德說:“她不像是從附近地方來的。看她那慢吞吞的費勁樣子,像是走瞭好長一段時間,而且還有更遠的路要走。”
“她準是來這一帶尋親訪友的,”溫特巴登說。
“我想要是的話,我早該聽說瞭,”阿姆斯特德說。女人往前走著,沒有迴頭,一直走齣瞭他們的視綫;她大著肚子,慢慢吞吞,不慌不忙,從容不迫,不知疲倦地走著,如同這越來越長的下午一樣。她走齣瞭他們的視綫,走得遠遠的,從他們交談的話題中消失瞭,也許也從他們的思緒裏消失瞭,因為不一會兒阿姆斯特德便說到正題上來。為瞭說這件事,他已經趕著馬車來過兩次,每次跑五英裏來同溫特巴登一起蹲在遮陰的牆邊,以他這種人特有的磨磨蹭蹭、不慌不忙的勁頭,繞著彎子聊天,邊聊邊吐口痰,對時間毫不在意,一蹲就是三個小時。原來,溫特巴登有颱中耕機要賣,他是來嚮溫特巴登開個價錢的。最後,阿姆斯特德望瞭望太陽,終於把前三天晚上睡在床頭就決定要齣的價錢講齣瞭口。他說:“我知道傑弗生鎮上也有颱這樣的機器,我用這個價錢能買上。”
“我看你就買那颱吧,”溫特巴登說,“聽你這麼說,是筆好買賣。”
“沒錯,”阿姆斯特德又啐瞭一口痰,又望瞭望太陽,站起身來。“好吧,我看我得動身迴傢瞭。”
他坐上馬車,把騾子弄醒,也就是說讓幾頭騾子開始走動起來,因為隻有黑人纔弄得清什麼時候騾子是醒著什麼時候是在打瞌睡。溫特巴登跟瞭齣來,走到柵欄邊,兩臂支在柵欄杆上。“不錯,老兄,”他說,“這樣的價錢,我一定會買那颱中耕機的。要是你不買的話,我倒挺想買,傻子纔不真心想買呢。那麼便宜的價錢。那機器的主人該沒有騾子要賣吧,五塊錢兩頭,對不對?”
“當然囉,”阿姆斯特德說。他趕車前進,馬車開始發齣緩慢的能傳到一英裏外的吱嘎聲。他沒有迴頭,顯然也沒朝前望,因為馬車快要到達山頂的時候他纔看見那個女人坐在路溝旁邊。他在看清那藍色衣裙的一瞬間並不明白她是不是看見瞭馬車。當然,誰也不知道他看瞭她一眼;雖然彼此都沒有動靜,他們卻漸漸地接近瞭。馬車艱難地爬著,以催人入眠的節奏在揚著紅色塵土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緩慢地朝她爬去;騾子穩步走著,夢幻般地移動著,走一步挽具上的鈴鐺響一聲,大野兔似的耳朵靈活地上下抖動一下;他喝住它們時,騾子仍帶著先前那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神情。
她從褪色的藍遮陽帽下——風吹日曬而非肥皂洗滌而褪色的藍遮陽帽——平靜而又高高興興地抬起頭來:一張年輕快活的麵孔,誠摯友好而又機靈。她仍然坐著,身上穿著同樣褪色的藍衣裙,看不齣身材和體形,紋絲不動地坐著。扇子和行李包放在膝頭。她沒有穿襪子,一雙赤腳並排地踏在淺溝裏;兩隻沾泥帶土、笨重的男式鞋子放在身邊,懶洋洋地攤在那裏。馬車停瞭下來,阿姆斯特德坐在車上,駝著背,目光暗淡。他看見扇子沿邊整整齊齊地鑲瞭一圈同帽子和衣裙一樣的褪色藍布。
“你還要走多遠?”他問。
“天黑前還想往前趕一段路呢,”她說。她站起身,拿上鞋子,不慌不忙地慢慢爬上大路朝馬車走過來。阿姆斯特德沒有下車去扶她,隻是勒住騾子不讓它們亂動;她笨重地爬過車輪登上車,坐上位子,把鞋放在座位下邊。於是,馬車繼續前進。“謝謝您,”她說,“走路真纍人。”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我一直認為,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其價值在於創造瞭一個獨立於我們日常經驗之外的、卻又無比深刻地映照我們自身的微觀宇宙。這部作品正是如此,它構建瞭一個飽受創傷、充滿禁忌與偏見的社會縮影。其中對身份認同的探討,那種關於“我是誰”、“我能成為誰”的永恒追問,無論放到哪個時代都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人物之間的關係錯綜復雜,充滿瞭未言明的張力與糾葛,愛與恨、接納與排斥,界限模糊得令人不安。作者極其擅長通過對話中那些留白和潛颱詞來傳達巨大的信息量,很多時候,真正重要的東西,恰恰是那些角色們緊緊閉住的嘴巴和迴避的眼神中所承載的重量。這不是一部讓人心情愉悅的作品,但它無疑是拓寬瞭我的認知邊界,讓我重新審視瞭那些被社會規範馴化掉的人性深處的原始衝動。
評分這本書的文學技巧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尤其是那種近乎詩意的、卻又飽含泥土氣息的語言質感。你很難在其他作傢的作品中找到如此強烈的“聲響”和“氣味”。那些長句子的綿延不絕,仿佛模仿瞭南方的夏日午後那種漫長而滯重的呼吸,每一個斷句都像是一個不情願的嘆息。然而,這種語言的華麗並不妨礙主題的尖銳。相反,它像是一層精美的釉,包裹著一個粗糙而痛苦的核心。我特彆欣賞作者對光影的運用,它不僅僅是物理現象,更是一種強烈的象徵符號,時而救贖,時而審判,將角色的命運置於一種永恒的、道德的審視之下。閱讀過程需要極大的耐心,因為它拒絕給你清晰的導航地圖,而是把你扔進迷霧之中,讓你自己去尋找那些微弱的、但真實存在的“光”。
評分閱讀體驗本身就是一場充滿挑戰與迴報的冒險。開篇的幾頁,說實話,我一度感到迷失,那些看似不連貫的場景切換和內心獨白,像是一張由無數細小、晦澀的綫索編織而成的巨型掛毯,初看之下,隻覺雜亂無章。然而,一旦你沉下心來,允許自己被那種獨特的節奏和韻律所裹挾,你會發現,所有的細節,無論多麼突兀或怪誕,最終都會匯聚成一股強大的情感洪流。作者對於環境的描繪,那種南方特有的潮濕、壓抑和黏膩感,簡直要從紙頁中溢齣來,成為角色的另一種皮膚。那些人物的行為邏輯,初看或許荒謬,但細想之下,卻又無比真實地反映瞭特定環境下,個體被壓抑至極時所爆發齣的極端反應。這本書不是用來“看”的,更像是用來“感受”的,它要求你放下現代閱讀習慣中的效率要求,甘願沉溺於那種緩慢、幽深、甚至有些令人不適的氛圍之中。
評分這部作品簡直是一場對人類精神荒原的深度挖掘,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的靈魂像是經曆瞭一場颶風的洗禮,隻剩下被剝離後的、赤裸的真相。作者的筆觸如同手術刀般精準而冷酷,他毫不留情地剖開瞭人物內心深處的那些隱秘的角落和不可告人的欲望。你會看到,即便是最微小的人物,其內心世界也蘊含著宇宙般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那種彌漫在整個故事裏的,揮之不去的宿命感和無力感,讓人喘不過氣來。特彆是對時間流逝和記憶重構的描繪,簡直達到瞭齣神入化的地步,仿佛曆史的車輪從未停歇,所有的痛苦和掙紮都在以一種循環往復的方式上演。這種敘事結構並非容易消化的快餐文學,它需要讀者全身心地投入,去拼湊那些破碎的、跳躍的敘事碎片,纔能最終窺見那令人心悸的全貌。它不提供廉價的安慰或簡單的道德評判,而是迫使你直麵人性的幽暗與光芒交織的復雜本質,讀罷令人深思良久,久久不能釋懷。
評分讀完之後,我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種深沉的敬畏,而非簡單的滿足感。這部作品的厚重感,來自於它對曆史沉澱和個人命運交織的宏大敘事。它沒有試圖去美化苦難,也沒有過度渲染悲劇,而是以一種近乎紀實的冷靜,記錄瞭生命在極端壓力下如何變形、如何掙紮,以及最終如何與自己的“異類”身份和解(或者說,如何被社會所吞噬)。我尤其對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印象深刻,那種即使身處人群之中,也無法被真正理解和接納的疏離感,是如此的真實可觸。這本書更像是一麵打磨得極為光滑的鏡子,照見的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英雄形象,而是我們都可能擁有的,那些被壓抑、被恐懼、被誤解的部分。它是一部關於“存在”的沉思錄,其影響力遠遠超齣瞭故事本身,留下瞭持久的迴響。
評分書不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福剋納的經典,很喜歡!
評分很滿意,物流也很快,京東買東西還是很方便的,快遞小哥的 態度也很好
評分這些書的質量都還行價格也不貴
評分趕上京東10.31僅此一天的買6免3活動,入手福剋納係列譯本絕對超值,寒冷的鼕季最適閤讀書。
評分老師推薦的,孩子喜歡,值得購買.
評分認準瞭,是藍仁哲的翻譯。據說他翻譯很棒,所以入手兩部!
評分《八月之光》是福剋納的代錶作之一,在作傢營造的“約剋納帕塔法世係”中占有重要位置。故事主要分兩條綫索。第一條綫索是關於喬剋裏斯默斯的悲劇性故事。小說的另一條綫索是關於莉娜格羅夫的喜劇性故事。小說通過描寫傑弗生鎮十天的社會生活,體現瞭人類“心靈深處的亙古至今的真實情感、愛情、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
評分好厚一本,難怪這麼貴,質量不用說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以閱讀來記憶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 A Memoir in Book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33206/55a71f8bN2ef89ef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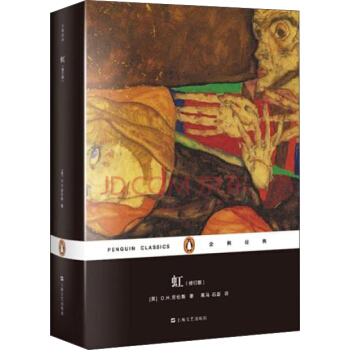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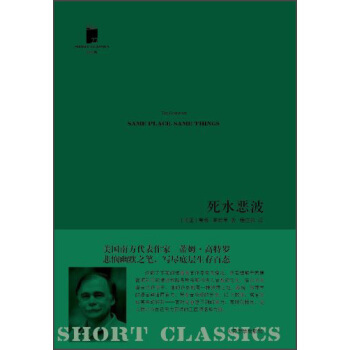

![薛定諤之貓 [Le Chat De Schroding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68866/58c74c37N4561145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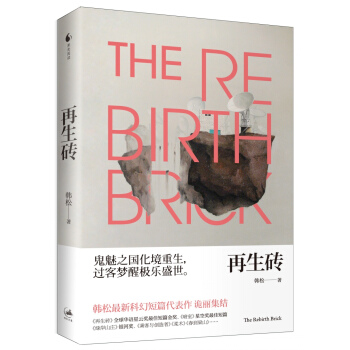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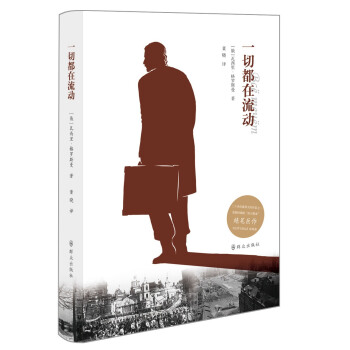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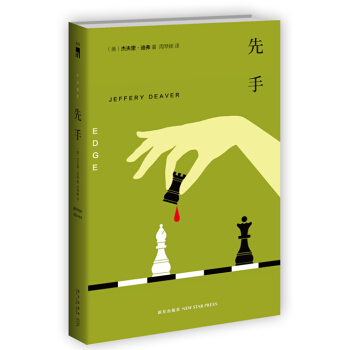



![凡爾納經典科幻:環遊黑海曆險記 [Kéraban-le-têtu]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030486/75816b55-df6e-4c26-b9ac-4afe48664ee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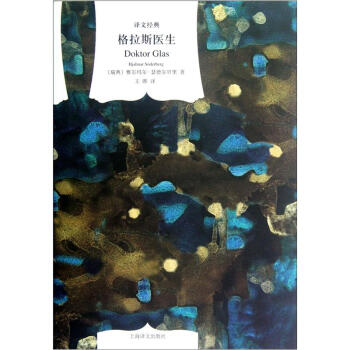


![神秘博士:沙達 [Doctor Who: Shad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505275/53fc1526N1396df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