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每一个人都想改变命运,但汪长尺却要“篡改”。别人篡改了他们,他们只能篡改自己。这是一部绝望之书,告诉我们在苦难面前如何寻找灵魂的出口?命运需要改变,但灵魂更需要清洗。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屌丝的故事。屌丝名叫汪长尺,高考超分不被录取。他父亲汪槐因为有过招工被人顶替的教训,所以怀疑有人动了汪长尺的奶酪,便进城抗争,意外摔成重伤。汪家重担压在汪长尺肩上。为还债,他进城打工,因领不到薪水替人蹲监,出来后继续讨薪,被捅两刀。可怜时,爱情出现,准文盲贺小文下嫁汪长尺。他们带着改变汪家的重托来到省城,却不想难题一道接着一道……他们一边坚守一边堕落,一边堕落还一边坚守。当汪家第三代出生后,汪长尺觉得他们的墨色必将染黑儿子汪大志的前途,于是,他做出惊人之举,让第三代不再成为屌丝。
这是作家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城市生活与乡土风俗同时呈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并肩使用。他的思考更为成熟,笔法更为老辣,文字生动,细节扎实,虚实恰当,语言幽默,可读性极强。
有人篡改历史,有人篡改年龄,有人篡改性别,但汪长尺篡改命。
作者简介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成法、韩、德、日、泰和希腊文出版或发表。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八桂学者。
精彩书评
读完《篡改的命》,我想寻找一个词汇来说明对其语言的感受,接着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说它是生活语言,又有不少书面语言的表述;说它是书面语言,又缺少书面语言的规矩。显然这不是一部语言优美的小说,那些坐在深夜酒吧里高谈阔论间吟诵艾略特或者辛波斯卡诗句的人不会想起这部小说里的某一句话;另一方面,也不能用粗俗这个词汇针对这部小说的语言,中超赛场上两队球迷互骂时基本上不会动用这部小说里的语句。我想寻找一个中性的词汇,想起20年前东莞电影院里满地瓜子壳被踩踏时发出的生机勃勃的声音。生机勃勃,就是这个。
东西选择了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之后,欺压和抵抗还有丑恶和美好都以生机勃勃的方式呈现出来……
——余 华(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
一位我很尊敬的编辑大家在概括这部长篇小说时如是说:“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投降,好人向坏人投降的过程。”这一投降过程,没有“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优待,而是被撞击,被粉碎到形容难识。农村包围城市,原本带着挑衅、对抗甚至颠覆的意识,结果被城市背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强大的力量吞噬。
农村城市化这一自然历史过程,首先吞噬的总是那些反抗者,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就是个“一生都想改变汪家命运的人”。反抗招致惩罚,一旦扛过惩罚并取得成就,城市会与之和解,收编他们成为新城市人。
东西的语言特色也很好地契合了这一吞噬的意象。基本上,东西的语言是简化的、写实的,与其人生经验相符,和现实不多偏离。和滋生背景为都市的精致学院派写作不同,东西的叙述节奏非常快速,小说框架简单,恰如人物进入城市后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对农村人而言的复杂,其实复杂不到哪里去,或者说,复杂不到精神维度层面。倒是城市的速度感对农村视角而言,流沙般快速流动,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可以说,东西把吞噬这一意象转化为语感,语言本身的速度形成惯性力,是一种语言的掠夺与吞噬。
——走 走(小说家,现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无还》、《房间之内欲望之外》、《我快要碎掉了》等。)
这个长篇很大的看点,不在故事,尽管故事已是如此惊心动魄,小人物的命运已推向极标致,无以复加。整个小说,处处充满两个方向的张力:语言上的张扬与凝炼;整体色调应是阴冷,却有扑面的暖意;人物个性鲜明,又有符号化的统一;故事波诡云谲,却又统摄于极为平静的叙述;文风写实气息浓郁,又处处存在四两拨千金的巧劲,写实和荒诞气质水乳交融。拿故事这一点说,汪长尺知道小文卖淫,从始至终从未说破,完全包容,行径与所有男人都不一样。甚至,谈论小文的职业(当妓女),竟成了他们交流的热门话题……当安都佬要验汪长尺的性无能,汪长尺也是不假思索,全力配合,所有的耻感,都在生存和“进城”的欲望中压缩到可有可无。如果从行为本身看,汪长尺已是不堪入目的失败者,但能将这一形象拗救回来的,正是汪长尺身上一种近乎天真的气质。他的包容和忍让,是出于临事时的利弊取舍,更是出于一种本性,一种在任何压力下都改变不了的天真。这种天真,是从东西的叙述腔调中生发而出,这种腔调,包含一种假痴不癫、大智若愚的通脱态度,几近达观。正是这种腔调,包容了文本中诸多相背而驰的张力,形成有奇观之效的文本。这个故事,故事中诸多突兀意外,让人乍一眼会发懵的细节,都被这腔调熨平,成为可能。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腔调,换一个讲述者,必将难以为继。由此,小说的腔调成为牵引阅读的核心动力。
——田 耳(1976年生,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代表作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长篇小说《天体悬浮》等。)
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现实,我也常常感到愤怒和想作为,而自小而来,跟着教育制度跑圈,又常常给我一种错觉,追求智性,勿论其他,似乎也是一条文人的出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创作卓越的虚构品,我书写真正的艺术,我把这当作一种保守的反驳(大意)。而我愈发发现,遁入艺术的细节,遁入书房的迷梦,是多么令人轻松和专注,以至于可以遗忘现实中正在进行的爆裂故事。而阅读《篡改的命》,似乎是一种令人警醒的体验,这不是一种保守的反驳,这是一声起立的呼喊,一次酣畅的迎击,一颗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也许我无法就此扭转自我的文学道路,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品令我激动,撩拨着我表达的欲望,怂恿我或多或少的作为。这样的作品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扔进文学史的废墟中,而是冒着扁平化和语义过于明确的风险,甘愿让自己扑向真相,溶于当下,献于隆隆而过的时代祭坛。
—— 双雪涛(1983年生,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目录
引子第一章:死磕第二章:弱爆第三章:屌丝第四章:抓狂第五章:篡改第六章:拼爹第七章:投胎后记精彩书摘
引 子 1 汪长尺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这辈子他从来没迟到过,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迟到”的名声。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理了头发,刮了胡须,本想买双崭新的皮鞋穿上,但想想五百块钱够他爹在农村装一扇玻璃窗,便咽了一口唾液,捏了捏手指,放弃。现在他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站在西江大桥正中的边栏旁。这个位置离水面的距离最高,估计摔下去时也会最响。人活一辈子,或默默地消失,或响响地离开,二者必选其一。天空出奇的蓝,云朵空前的洁白,上苍似乎故意给他一个好天气,抑或是送他最后一点念想。水面铺满阳光,由于风的原因,波光的强弱不停地改变,一会这儿刺眼,一会那儿刺眼。汽车的轰鸣没过去那么讨厌,似乎还有一点悦耳,就连车屁股喷出的尾气,也仿佛散发出清香。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他想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举着望远镜,正在监督我对我的执行…… 第一章 #死 磕# 2 汪长尺把消息捂臭了才告诉汪槐。汪槐正在自饮,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吃了一枚馊鸡蛋,恨不得马上呕吐。但消息就是消息,它是没法用来呕吐的。因此,汪槐只能憋着,几乎要憋成内伤,才放一口气,说你不是上线了吗,上线了为什么没被录取?汪长尺低下头:“他们说我的志愿填歪了。” “你怎么填的志愿?” “前面北大清华,后面服从调配。” “叭”的一声,汪槐摔烂了手里的酒杯,说你好大的胆,四九年到现在,全县没一个考上清华北大。 “只要填了服从,像我这样的分数,再烂的学校也应该捡到一所。” “不是每个人一低头就能看见钱,明明是一个烂学校的命,还做什么名校的春梦?” “我想幽他们一默。” “除了把自己的机会幽没了,还能幽谁的默?你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每步都像走钢索,竟敢拿命运来开玩笑。” 三无人员的头低了又低,就像颗粒饱满的稻穗那样低下去。整个晚上,他都没敢抬头,仿佛要用这种姿势证明自己和田野里的稻穗一样正在成熟。他看见汪槐的双腿摇摇晃晃,刘双菊的双腿战战兢兢,酒杯的碎片白光闪闪,黄狗在餐桌下窜来窜去。风肆意地扫进来,吹散闷热的空气。他感到后脖子一阵阵凉,好像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汪槐和刘双菊都不跟他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沉默是一种酷刑。他的脑海闪过自杀的念头,连地点和方式他都想到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很快就被橡皮擦抹掉。 夜越来越深,他听到洗澡声,关门声,却没听到床板声。那个平时“咿呀咿呀”的床板,今晚一声不吭,仿佛在为他节哀或者像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直到汪槐的鼾声传来,汪长尺才蹲下去捡酒杯的碎片。捡着捡着,他的右食指被划伤,血冒出来,却无痛感。 第二天早晨,汪槐的酒醒了。他要汪长尺跟他一起去找招生的理论。汪长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汪槐把门一脚踹开。这是他的脚最后一次精彩表演。汪长尺的肩膀一耸一耸,像个娘们似的抽泣,手里的毛巾都被泪水洗了。汪槐说哭能解决问题吗?汪长尺当然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但哭至少能让他减压。他试图停止,但越是想停越抽泣得厉害,就把毛巾捂到脸上,以为这样可以防洪,却不想“呜”的一声,决堤了,抽泣变成痛哭。汪槐站在门口看着,就像看着一出悲剧正上演。汪长尺“呜”了一阵,觉得怪丢脸的,慢慢减速,哭声渐渐变小,最后在自己的强迫下刹住。但平静后还心有余悸,身体会冷不丁地一抽,又一抽。 “可以走了吗?”汪槐问。 “我的手指被割破了。” “又不用手指走路。” “我一夜没睡。” “你妈生你的时候,我两天两夜都没合眼。” 汪长尺抹了一把眼眶:“自己没填好志愿,怪谁呢?” “怪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汪长尺申请先洗一把脸。汪槐到前门等待。汪长尺慢慢地洗,双手用力地从额头搓到下巴,又从下巴搓到额头,反反复复,就像女人做脸部按摩,恨不得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但是,很快就传来汪槐响亮的咳嗽,仿佛闹钟,提醒他忍耐是有限度的。汪长尺想与其跟他去丢人现眼,还不如逃跑。他朝后门走去,没想到汪槐就站在门外。一秒钟之前,他已经从前门转移到了后门。汪长尺想把迈出门槛的右脚收回,却怎么也收不回来,它被汪槐的目光死死地按住,像得了偏瘫。汪槐说是不是还要上趟厕所?汪长尺摇头。 他们朝公路的方向走去。汪槐在前,汪长尺在后。汪槐的身上背着软包,每走一步包里就传出“叮叮咚咚”的响。那是水声。他的包里装着军用水壶。满壶不响半壶响叮当。从他的包里还飘出玉米棒的清香。汪长尺走了一阵后全身冒汗。汪槐问热了?汪长尺说不热,出的全是冷汗。汪长尺想他又没回头,怎么知道我热?汪槐说渴吗?汪长尺说不渴。汪槐说饿不?汪长尺说不饿。其实汪长尺不吃不喝不睡已经八小时,他现在说的每一句都是假的,好像要故意跟汪槐对着干。 两人沉默。长长的路上响着“噗哒噗哒”的脚步。汪长尺看见澄碧的头顶划过一群鸟,它们像芝麻撒进树林,鱼苗扔进大海。汪槐越走越快,走出二十多米才发现汪长尺没跟上。他停住,掏出水壶来喝了一口。汪长尺远远就闻见一股酒气。原来壶里装的不是水。等汪长尺走近,汪槐递过水壶,问要不要来一口?汪长尺摇头。这时,汪长尺才注意汪槐又脏又乱的头发。他领子上的汗渍就像铁锈那么黑,他身上的软包打着巴掌那么大的补丁。汪长尺想难道我就跟着这么一个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的酒鬼去跟招生办的人讲道理? 看着汪槐渺小的背影,汪长尺越走越消极,越走越感到前途渺茫。路过茶林时,他忽然钻了进去,一阵狂奔,仿佛要跑出地球。树枝刷在他的脸上,像一记记耳光。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到一棵树上喘气。喘着喘着,天空中飘来汪槐的骂:“汪长尺,你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有理你不敢去讲,活该被人欺负……” 骂声在头顶盘旋,风一吹,声音就颤一下,听上去苍凉悲壮。汪长尺抱着树干,越抱越紧,像抱着母亲,最后抱得手臂生痛。他竟然抱着那棵树睡着了,醒来时手脚全麻。它们好像离开他的身体变成了木头。他坐在地上,慢慢地找知觉,直到找回自己的手,又找回自己的脚,才站起来往回走。 走到家门口,刘双菊问怎么回来啦?汪长尺说没带身份证。刘双菊朝路口望了一眼,说你就放心让他一个人去?他那脾气弄不好会跟人打架。汪长尺说自找的。刘双菊说你什么良心?他是为你去的。汪长尺说丢人。刘双菊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 第二天,汪长尺以为汪槐会回来。但是,天黑了路上没他的身影;夜深了,也无他的脚步。汪长尺竖起耳朵,直到天亮都没听到他想听到的。刘双菊急得跳进跳出,每天都催汪长尺去声援汪槐。汪长尺假装没听见。到了第五天,刘双菊说你再不去把他叫回来,稻谷都烂在田里了。汪长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看着遥远的山脉。刘双菊推了他一把,他像不倒的存钱罐,歪过去又弹回来。不管刘双菊从哪个角度推,使多大的劲,他的屁股像刷了万能胶,始终不离开椅子。刘双菊说也许你爹已经被人抓起来了,你怎么连屁股都不舍得抬抬,难道你是块石头吗?你可以不声援他,但你必须去接他,哪怕是一具尸体。刘双菊一边说一边抹眼睛。她的眼眶已经红了,马上就要哭了。汪长尺无动于衷。刘双菊背起书包,说你不去我去。 汪长尺终于动了。想想那么一大堆家务,他就害怕一个人留下。他双手扣住椅子站起来,好像椅子是他的器官。他扣住椅子走了几步,觉得别扭,就把椅子从屁股下移到肩上。他扛着椅子走去。刘双菊说为什么带椅子,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发呆?汪长尺说不懂就别装懂。刘双菊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扛着椅子挂着书包大步流星。 山路弯曲。树林越来越苍茫。他小得就像一只蚂蚁,路细得就像一丝白发。 3 从汽车站出来,汪长尺直奔教育局。他看见汪槐盘腿坐在操场上,手里举着一块纸牌。纸牌上写着:“上线不被录取,谁来还我公道?”除了汪槐的影子,操场上干干净净,明晃晃的阳光晒得他的脖子都勾了,整个人就像戳在旱地的半截禾苗,蔫头耷脑,又像树蔸一动不动。汪长尺放下椅子去扶他。他很重,比汪长尺想象的还要重几倍。第一次,汪长尺没把他扶起来。第二次,汪长尺加了一点力气,也没把他扶起来。汪长尺前几天才挨麻过,他知道汪槐那么重是因为汪槐的腿脚麻了,自己帮不上自己的忙。于是,他就帮汪槐揉腿脚。揉了半小时,汪槐的手在地上一撑,爬起来坐到椅子上。他说偌大一个县城,连张多余的板凳都没有。汪长尺把书包递给他。他从里面掏出一个玻璃瓶,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地喝掉三分之一。那是他自酿的米酒,一喝就来精神。汪长尺说稻谷黄了,妈叫你回去收割。 “谷子算什么?命运才是第一。”他用右拇指抹了一下沾满米酒的嘴角。 “就是把水泥地板坐穿,你也改变不了他们。” “改变不了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闲得没事干吗?告诉你,问题已引起领导重视,他们正在查。你跟我再坐几天,也许能坐出一个特批。” “我宁可回家做农民,也不在这里丢脸。” “你都上线了,凭什么做农民?你应该像他们那样坐在楼里办公。” 这是一幢四层高的办公楼,外走廊,每层有十二间办公室,门窗刷的都是绿色,因为有些年头了,绿色已不是当初的绿,而是斑驳的结壳的褪色的勾兑了日月和风雨的。墙根、走廊外侧以及顶层的一些角落或长着青苔或留下雨渍。楼前有一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汪槐对它指指点点,说局长在第三层第五间,两个副局长在第三第四间,招生办在四楼第一间。汪长尺看见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又飞快地缩回去。他说我到院子外面等你,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汪槐喊了一嗓子:“这事我没法想通,除非他们给你一个指标。” 许多窗口都探出头来,他们久久凝望,似乎是希望再看到一点不同凡响的动静。汪槐说知道他们为什么紧张吗?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每次我一吼,招生办的窗口总是最先伸出人头。你爹我什么时候这么威风过?只有在掌握真理的时候、伸张正义的时候。 那些人头还在,有的端着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看,有的敲响了杯子,有的举起相机。汪长尺小声地:“我给你磕头行不?” 汪槐大声地:“不行,要磕头也是他们给我们磕。” “我补习,明年再考行不?”汪长尺近乎哀求。 “今年他们都不给你上,明年照样把你当韭菜割掉。”汪槐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 楼上传来一阵哄笑,有人吹口哨,有人打响指。汪长尺感到腹背受敌。他想跑,又怕楼上的人笑他不团结。他只得硬着头皮迎接那些讽刺的鄙视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也许要半小时的沉默或者一动不动,他们才会失去围观的兴趣。汪长尺静静地立着,生怕一个喷嚏就会打破平衡。现在,操场上有了两条斜斜的影子,一条站,一条坐。阳光从西边晒过来,晒得他的头皮发麻。那些观察者先后缩了回去。汪长尺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开溜,忽然铃声就响了。那是下班的铃声。他们先后关了门窗,从楼道有说有笑地出来。眼看他们就要走到面前,但忽然一拐,全都绕行,好像遇到了礁石或瘟疫。汪槐站到椅子上,把纸牌高高地举起。汪长尺不忍直视,下巴紧紧贴着胸口,好像自己是一头乳猪,已被周围的目光烤焦。直到两旁稠密的脚步声消失,他才抬起头,转身跑去。汪槐跳下椅子,说等等我。 他们来到一座水泥桥底。汪槐爬上桥墩,从桥孔拖出一卷席子抛下。汪长尺接住。席子散开,一个塑料袋滚落。汪槐沿桥墩滑到地面,捡起塑料袋打开,掏出一个馒头递过来。汪长尺摇头。汪槐把馒头塞进嘴巴,一口含住。他的面颊顿时大了。从他咀嚼的时间和腮帮子运动的力度判断,那是一个硬馒头,它待在塑料袋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汪长尺的鼻子微酸,好像是同情汪槐又像是同情自己。他说你一直住在桥洞里吗?汪槐没法立即回答,他还在嚼那个馒头。汪长尺感觉嚼食声很响很持久,耳朵都被这个声音填满。汪槐嚼完,喝了一口米酒,说住在这里不花钱,还凉快。 “和乞丐差不多。” “当然,你来了,我就得搬家。” “搬去哪里?” “包你满意。” 汪槐在宾馆开了一个标间。他用双手压了压床铺,说这么软这么白,今晚早点睡吧。洗漱完毕,熄灯,各自睡在床上。汪长尺一闭上眼睛,脑海就像一台强力发动机,带着他无限困倦的身体四处飘游。身体和思绪似乎荡漾在失重的空间,怎么也落不了地。飘来荡去,他感觉大脑隐隐涨疼。五天前,他能抱住一棵树站着入睡,但今晚他每个地方都困却死活睡不着。半夜,他忍无可忍,爬起来打开灯,发现汪槐不见了。仔细一看,原来他躺在床那边的地板上。由于灯光太刺眼,他用手挡住眼睛,说睡了几十年的硬板床,遇到软的反而不适应。 “回家吧,何苦在这里受罪。”汪长尺一边说一边穿衣服,很快他就把衣服裤子鞋子全部穿好,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汪槐问现在几点?他说两点。 “两点,离天亮还差一大截,就是回家现在也没车。” 汪长尺拉开窗帘。远方漆黑如墨。他把椅子调过来,面朝东方一动不动,好像这么看着天就会亮得快点。汪槐爬起来,走进卫生间拉了一泡漫长的尿,然后回到床边坐下,说更何况,我不同意你现在撤退,好比打仗,有时胜败就看最后五分钟,我们到了吹冲锋号的关键时刻,千万别自己先软。汪长尺不相信什么冲锋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希望天空尽快变白,然后赶早班车回家。汪槐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说如果你上不了大学,一辈子就要待在农村,有必要急着回吗?二十多年前,我参加水泥厂招工,分数上线却没被录取,十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副乡长的侄仔顶替。你要是不抗议,他们就敢这么欺负你。更何况,一班的牙大山比你低二十分都被录取。……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我得说,完全超出了我对于一本“小说”的预期。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时间、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哲学思辨录,包裹在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外壳里。作者对叙事结构的掌控简直是大师级的,仿佛我们不是在阅读一个故事,而是在经历一场精心设计的迷宫探险。人物的内心挣扎被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些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情绪波动,都被捕捉得异常精准。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于“真实”定义的探讨,它不断地挑战读者的既有认知,让你在读完之后,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对过往经历的理解。情节的推进并非线性,而是如同多条河流最终汇入同一片海洋,看似独立却又环环相扣。当你以为已经掌握了故事的脉络时,作者总能抛出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你彻底推翻之前的判断。这种智力上的博弈,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紧张感和期待感。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阅读,更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和解构。那些关于选择与后果的探讨,深刻地触及了存在的本质,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
评分我通常是那种对文学作品的技巧性探讨不太感兴趣的读者,我更注重故事是否能打动我。但这本书的叙事技巧,却巧妙地成为了打动我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它没有冗余的描述,每一个句子都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分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支撑起故事的结构。最让我震撼的是它对“视角”的处理。作者似乎对“谁在讲述”这个问题有着近乎偏执的探索欲,通过不断地转换甚至扭曲讲述者的身份,使读者对信息的可靠性始终保持警惕。这种结构上的精妙设计,使得故事的悬疑性自然生成,不需要依赖传统意义上的阴谋或反转来吸引人。它更像是在引导你,去质疑你所相信的一切“既定事实”。读完后,我有一种被彻底“洗牌”的感觉,但这种洗牌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它开拓了我对叙事可能性的理解边界。
评分这本书的氛围营造简直是一绝,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略带潮湿的、旧照片般的怀旧感和疏离感交织在一起。作者对于场景和心境的描摹,具有极强的画面感,仿佛每翻开一页,我都能清晰地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某种特定的气味,或者感受到某种特定光线下特有的温度。它不像某些作品那样追求戏剧性的冲突,而是更偏向于对人物内在世界的细致描摹和缓慢渗透。角色的塑造非常立体,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只有在特定压力下做出不同选择的、充满矛盾的个体。我尤其喜欢作者处理时间流逝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刻度尺,而是一种可以被拉伸、压缩、甚至折叠的物质。这种处理方式,让那些关于失去和追寻的主题,获得了更深层次的重量。阅读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过往经历与之对照,引发了许多关于“如果当时……”的沉思。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些未竟的、被时间尘封的角落。
评分老实讲,一开始我对这类被誉为“烧脑”的作品是持保留态度的,总觉得有些故作高深,但这本书彻底扭转了我的看法。它的复杂性并非堆砌晦涩的词汇或故作玄虚的情节,而是源于其内在逻辑的精妙构建。想象一下,一个由无数个互相映射的镜子组成的房间,你看到的每一个反射都是一个“可能”的现实,而作者引导你穿越其中,却从不直接告诉你哪一面才是“真正的”镜子。语言的运用极其考究,充满了节奏感,时而如暴风雨般迅猛,将你卷入高潮;时而又像夏日午后的微风,留下悠长而意味深长的回味。我常常需要放慢速度,细细品味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因为其中往往隐藏着关键的线索或者对后续发展的深刻暗示。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要求读者付出相应的专注力,而作为回报,它给予的是一种近乎于顿悟的阅读体验。它绝不是那种可以让你边刷手机边看的读物,它要求你全身心地沉浸其中,才能感受到其构造的宏伟蓝图。
评分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克制美学。它有着宏大的主题,探讨的却是极度私人的经验和感受。作者似乎深谙“留白”的艺术,许多关键的情感爆发点和转折处,都没有被用尽全力地描绘出来,而是留给了读者去自行填补空白。正是这种不言自明、心领神会的空间,使得情感的共鸣达到了最大化。我发现自己在阅读时,经常会停下来,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需要时间去消化那种复杂的情绪冲击——那种混合着遗憾、释然、以及对未知未来的微微恐惧感。它不是那种读完后会让你大声叫好的作品,而更像是会潜入你潜意识深处,在你独处时,悄悄发酵、生根、直至开花的结果。它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性,触及了更深层次的、关于人性困境的永恒追问。
评分报纸上推荐的书,很不错
评分书很好,发货快,值得购买。
评分据说是年度最佳小说
评分商品不错!物流很给力!快递员服务很好!
评分好书 好速度
评分还在看之中,物流什么的都挺好的
评分点校本《新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柴德赓承担,1971年后转由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于1974年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酌了当时通行的明清诸本,并吸取了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纠订了部分错谬。
评分看了书,伤一点心,人生真的会那样吗
评分给朋友买的,说非常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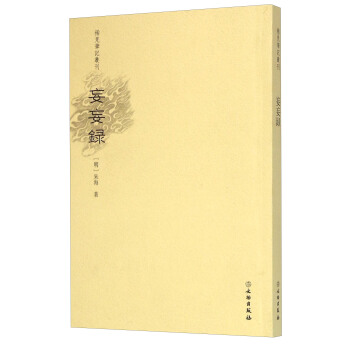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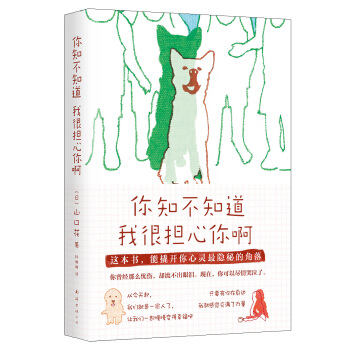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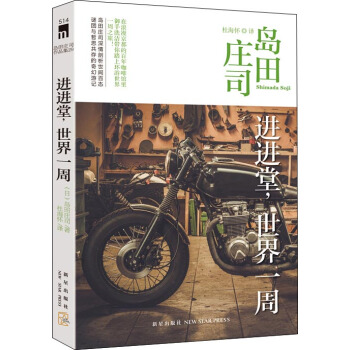
![E·M·福斯特文集:莫瑞斯 [Mauri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73048/57d21a9cN28d288e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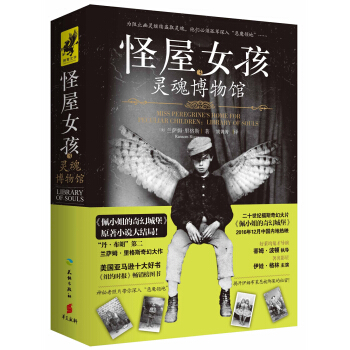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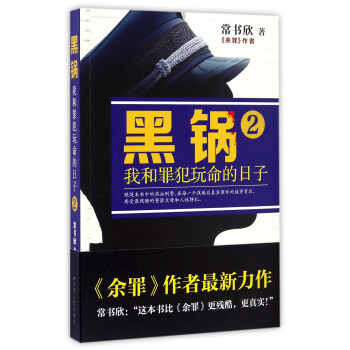




![俄亥俄,温斯堡 [Winesburg, Ohio]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36983/rBEIC0_2egkIAAAAAAE2j44SqTQAADvgQN7IGIAATan61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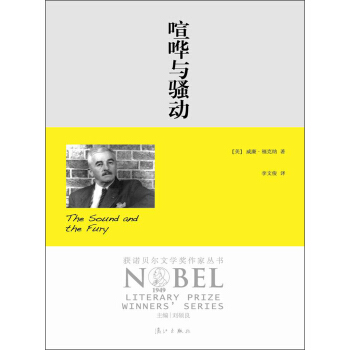
![横沟正史:抽泣的死美人 [喘ぎ泣く死美人]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93794/5487d8a5Nc43c129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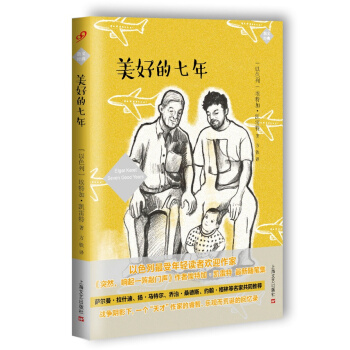

![E·M·福斯特文集:印度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73020/57d21a9bN251090e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