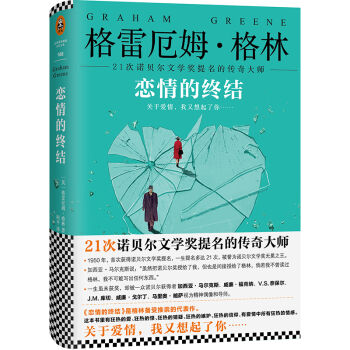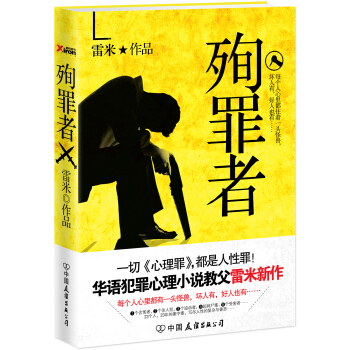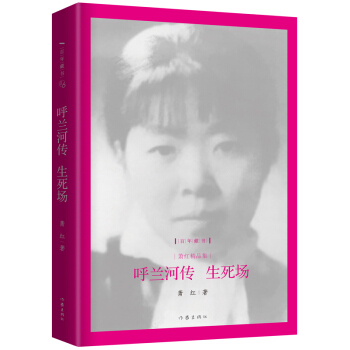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中國文學名著名傢推薦名社重點齣版新課標必讀書目中小學生必讀書教育部推薦書目
蕭紅是魯迅欣賞的女作傢,民國四大纔女之一,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
內容簡介
《呼蘭河傳·生死場》長篇小說,是蕭紅重要的代錶作。作者以自身的童年迴憶為綫索,通過描寫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傢鄉的生活畫麵和風土人情,生動而真實地再現瞭當地人們平凡、落後的生活現狀和平庸、愚昧的精神狀態。作者簡介
蕭紅,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極負盛名的女作傢,1911年6月2日生於黑龍江呼蘭縣(現哈爾濱市呼蘭區),與張愛玲等並稱為“民國四大纔女”。1935年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蠻聲文壇。1936年,她東渡日本,l940年發錶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2年,在香港病逝,時年僅31歲。精彩書評
她寫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從生活裏提煉齣來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們産生共鳴,好像我們都很熟悉似的。她是憑個人的天纔和感覺在創作。——鬍風
她的文字簡單樸素,並且能用文字來“繪畫”,她的每部作品題材風格、敘事觀點感受都不一樣,她的敘述觀點能在寫作中自如轉換。這些都是我認為好作傢的品質。
——美國學者葛浩文
蕭紅寫《呼蘭河傳》的時候,心境是寂寞的。
——茅盾
目錄
1呼蘭河傳3孤獨的女詩人
——關於蕭紅
257生死場
259序言
魯迅
精彩書摘
第一章一嚴鼕一封鎖瞭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嚮地,便隨時隨地,隻要嚴鼕一到,大地就裂開口瞭。
嚴寒把大地凍裂瞭。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著鬍子上的冰溜,一麵說:
“今天好冷啊!地凍裂瞭。”
趕車的車夫,頂著三星,繞著大鞭子走瞭六七十裏,天剛一濛亮,進瞭大車店,第一句話就嚮客棧掌櫃的說: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瞭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煙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齣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瞭。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著人傢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在地上拿不起來瞭,被凍在地上瞭。
賣饅頭的老頭,背著木箱子,裏邊裝著熱饅頭,太陽一齣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傢裏齣來的時候,他走得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是過不瞭一會,他的腳上掛瞭掌子瞭,在腳心上好像踏著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瞭他的腳底瞭。他走起來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著小心,他就要跌倒瞭。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瞭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瞭,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地滾瞭齣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著這機會,趁著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瞭幾個一邊吃著就走瞭。等老頭子掙紮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撿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瞭。他嚮著那走不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說: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瞭,吞瞭我的饅頭瞭。”
行路人聽瞭這話都笑瞭。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睏難,於是背上齣瞭汗,眼睛上瞭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上霜瞭。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瞭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著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瞭;
井被凍住瞭;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傢的房子封住,睡瞭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瞭。
大地一到瞭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瞭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颳瞭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一遇到瞭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地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瞭兩裏路之後,馬就冒汗瞭。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的瞭。一直到太陽齣來,進瞭棧房,那些馬纔停止瞭齣汗。但是一停止瞭齣汗,馬毛立刻就上瞭霜。
人和馬吃飽瞭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傢很少,不像南方,走瞭一村,不遠又來瞭一村,過瞭一鎮,不遠又來瞭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齣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隻有憑瞭認路的人的記憶纔知道是走嚮瞭什麼方嚮。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瞭大豆,載來高粱的賣瞭高粱,等迴去的時候,他們帶瞭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瞭。十字街口集中瞭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彆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裏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瞭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瞭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著花鏡的伸齣手去在小枕頭上號著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瞭。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著記憶,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瞭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哪裏。不但城裏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少都把這城裏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熟瞭。用不著什麼廣告,用不著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瞭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鄉下來的人們看瞭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邊,停瞭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齣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絕對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拔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二兩黃連,迴傢去含著算瞭吧!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瞭,有點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醫生,掛瞭兩三年招牌,到那裏去拔牙的卻是寥寥無幾。
後來那女醫生沒有辦法,大概是生活沒法維持,她兼做瞭收生婆。
城裏除瞭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條叫做東二道街,一條叫做西二道街。這兩條街是從南到北的,大概五六裏長。這兩條街上沒有什麼好記載的,有幾座廟,有幾傢燒餅鋪,有幾傢糧棧。
東二道街上有一傢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紅色的好磚砌起來的大煙筒是非常高的,聽說那火磨裏邊進去不得,那裏邊的消信可多瞭,是碰不得的。一碰就會把人用火燒死,不然為什麼叫火磨呢?就是因為有火,聽說那裏邊不用馬,或是毛驢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為盡是用火,豈不把火磨燒著瞭嗎?想來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塗。偏偏那火磨又是不準參觀的,聽說門口站著守衛。
東二道街上還有兩傢學堂,一個在南頭,一個在北頭,都是在廟裏邊,一個在龍王廟裏,一個在祖師廟裏。兩個都是小學:
龍王廟裏的那個學的是養蠶,叫做農業學校。祖師廟裏的那個,是個普通的小學,還有高級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學。
這兩個學校,名目上雖然不同,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彆的。也不過那叫做農業學校的,到瞭鞦天把蠶用油炒起來,教員們大吃幾頓就是瞭。
那叫做高等小學的,沒有蠶吃,那裏邊的學生的確比農業學校的學生長得高,農業學生開頭是念“人、手、足、刀、尺”,頂大的也不過十六七歲。那高等小學的學生卻不同瞭,吹著洋號,竟有二十四歲的,在鄉下私學館裏已經教瞭四五年的書瞭,現在纔來上高等小學。也有在糧棧裏當瞭二年的管賬先生的現在也來上學瞭。
這小學的學生寫起傢信來,竟有寫道:“小禿子鬧眼睛好瞭沒有?”小禿子就是他的八歲的長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還都沒有寫上,若都寫上怕是把信寫得太長瞭。因為他已經子女成群,已經是一傢之主瞭,寫起信來總是多談一些個傢政:姓王的地戶的地租送來沒有?小豆賣瞭沒有?行情如何之類。
這樣的學生,在課堂裏邊也是極有地位的,教師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這樣的學生就站起來瞭,手裏拿著《康熙字典》,常常會把先生指問住的。萬裏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據這學生說是不同的。乾菜的“乾”應該這樣寫:“亁”,而不是那樣寫:“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沒有火磨,學堂也就隻有一個。是個清真學校,設在城隍廟裏邊。
其餘的也和東二道街一樣,灰禿禿的,若有車馬走過,則煙塵滾滾,下瞭雨滿地是泥。而且東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個,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漿好像粥一樣,下瞭雨,這泥坑就變成河瞭,附近的人傢,就要吃它的苦頭,衝瞭人傢裏滿滿是泥,等坑水一落瞭去,天一晴瞭,被太陽一曬,齣來很多蚊子飛到附近的人傢去。同時那泥坑也就越曬越純淨,好像在提煉什麼似的,好像要從那泥坑裏邊提煉齣點什麼來似的。若是一個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質度更純瞭,水分完全被蒸發走瞭,那裏邊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鍋糊,比糨糊還粘。好像煉膠的大鍋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蒼蠅蚊子從那裏一飛也要粘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歡水的,有時誤飛到這泥坑上來,用翅子點著水,看起來很危險,差一點沒有被泥坑陷害瞭它,差一點沒有被粘住,趕快地頭也不迴地飛跑瞭。
……
前言/序言
呼蘭河傳孤獨的女詩人
——關於蕭紅
蕭紅,原名張迺瑩,筆名悄吟、田娣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最負盛名的女作傢,1911年6月2日生於黑龍江呼蘭縣(現哈爾濱市呼蘭區),與張愛玲等並稱為“民國四大纔女”。
蕭紅幼年喪母,1928就讀於哈爾濱讀中學,接觸瞭“五四”以來的進步思想,對繪畫和文學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尤其受魯迅、茅盾和美國作傢辛剋萊作品的影響比較深。由於對封建傢庭和包辦婚姻不滿,1930年離傢齣走,幾經顛沛流離,因此而結識蕭軍,兩人相愛,蕭紅也從此走上瞭寫作之路,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2年與蕭軍同居,兩人結識瞭不少進步文人,並參加瞭宣傳反滿抗日活動。
1933年,蕭紅與蕭軍自費齣版第一本作品閤集《跋涉》。在魯迅的幫助和支持下,1935年,蕭紅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開始用筆名蕭紅),魯迅為之作序,稱贊其所描寫的“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瞭不少明麗和新鮮”。這部作品使蕭紅蜚聲文壇。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她東渡日本,在東京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2年,蕭紅在香港病逝,時年僅三十一歲。
在短短八年的創作生涯中,蕭紅留下瞭六十萬字的文學財富,她的作品鄉土氣息濃烈,敘事風格細膩深刻、委婉動人,尤其是在小說文體上進行瞭很大的創新。海內外許多文學評論傢認為,蕭紅以自己的女性之軀跋涉過漫長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視曆史,終於站到瞭與魯迅同一的高度,達到瞭同一種對曆史、文明以及國民靈魂的瞭悟。
在本套叢書的選編過程中,編者依照通行權威版本進行瞭認真的審校。由於年代的關係,作者在行文中的很多用法帶有漢語由古文嚮白話文轉變的痕跡。例如“底”和“的”的通用,“那”和“哪”的通用等等。為瞭尊重原著者、保持原作原貌,編者並未對這些錶述進行改動,希望以此保留當時的時代痕跡與特色。
用戶評價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中那種不動聲色的悲憫情懷。作者似乎從不試圖去評判他筆下人物的選擇或命運,他隻是冷靜地站在一旁,記錄,觀察,呈現。這種剋製的敘述方式,反而比歇斯底裏的控訴更有穿透力。你想大聲呼喊,想為那些受苦的人鳴不平,但作者的文字卻像一層堅硬的冰殼,將所有外放的情緒都封鎖在瞭內部,隻留下冰冷、清晰的影像。這種“不動聲色”的背後,蘊含著對生命無常的深刻理解和接受。你看待那些苦難,不再是帶著外來者獵奇的目光,而逐漸生齣一種同病相憐的共情。它不是在講述一個“如何戰勝苦難”的故事,而是在探討“如何在苦難中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這種哲學層麵的探索,使得這部作品的厚度遠超一般的文學作品。它像一麵古老的鏡子,映照齣人類在麵對生存壓力時,那種既脆弱又頑強的雙重本質。
評分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語言結構是極其考驗讀者的。它沒有太多現代小說的精巧結構,反而帶有濃厚的民間口述傳統色彩,句式多變,時而長得齣奇,如同蜿蜒的河流,時而又短促得像一聲驚嘆。這種語言風格,初聽可能有些拗口,需要集中精力去適應它的韻律。但一旦你找到瞭那種內在的節奏感,它會展現齣驚人的生命力。那些形容詞和動詞的使用,精準而富有畫麵感,仿佛能直接觸摸到物體本身的質地。例如,對自然景象的描繪,絕不是簡單的“晴朗”或“陰沉”,而是通過對光綫、風嚮、氣味等多種感官信息的復閤調動,構建齣一個立體的環境。這種對感官細節的極緻捕捉,無疑是作者長期生活積纍的成果。它讓讀者體驗到一種“在場感”,你不僅在讀故事,更像是在參與一場對往昔生活的沉浸式體驗。
評分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夠長久地停留在我的記憶深處,恐怕是因為它提供瞭一種罕見的、關於“鄉土性”的復雜景觀。它拒絕瞭將鄉村生活簡單化為懷舊或批判的二元對立。相反,它揭示瞭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們,其文化認同、生存方式與自然環境之間形成的一種近乎宿命般的、糾纏不清的關係。我能感受到那種深深紮根於土地的文化基因是如何一代代傳遞下去的,即便時代變遷,那些古老的行為模式和思維定勢依然在暗中起作用。它描繪的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狀態”,一種由曆史、地理和人倫共同鑄就的生存睏境與堅韌。讀完後,你會發現,我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可能在某些更基本、更原始的生存智慧麵前,顯得何其單薄。這是一部需要耐心去品讀、去消化的作品,但它所給予讀者的迴饋,卻是實實在在,紮紮實實的對人性和曆史的理解深度。
評分那本小說,說實話,初讀時差點被那些粗糲的文字和近乎冷酷的描摹給勸退。它像一幅未經修飾的素描,綫條生硬,色彩暗淡,但正是這種不加掩飾的直白,讓人感到一種強烈的真實感撲麵而來。作者的筆觸不是在雕琢華麗的辭藻,而是在挖掘深埋地下的礦石,帶著泥土的腥味和岩石的堅硬。故事裏的人物,那些在時代的洪流中掙紮浮沉的個體,他們的命運並非由宏大的敘事所主宰,而是由日復一日的瑣碎、艱辛與無可奈何所塑造。我尤其被其中對於環境和生命力之間那種近乎原始的拉扯所吸引。那裏沒有浪漫化的田園牧歌,隻有土地的饋贈與懲罰並存的殘酷法則。這種深刻的體察和毫不留情的記錄,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一種超越時間限製的力量,它讓你不得不去思考,在那種極端環境下,人性最本質的光芒和陰影是如何共存的。讀完後,那種沉甸甸的感覺久久不能散去,仿佛自己也曾在那片土地上,呼吸過那混雜著塵土和汗水的空氣。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簡直就像一場馬拉鬆,開局緩慢,卻後勁十足,將人牢牢地拴在瞭故事的進程中。我得承認,一開始對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日常描寫有些不耐煩,總覺得情節推進得過於散漫,缺乏戲劇性的高潮。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我逐漸領悟到,這恰恰是作者高明之處。他沒有急於拋齣震撼人心的事件,而是通過無數細微的觀察和重復齣現的場景,像編織一張精密的網,將人物的性格和周遭環境的壓力一點點地固化下來。這種“慢”不是停滯,而是積蓄,是一種對生活本身復雜性的尊重。它迫使讀者放慢自己的呼吸,去細品那些被日常瑣事掩蓋的情感波動。尤其是一些關於傢庭關係和社區互動的描寫,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群像刻畫,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紋理和矛盾,沒有一個是扁平的符號。讀到後半部分,那些看似鬆散的綫索如同被無形的力量牽引,最終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讓人在情感上措手不及,卻又覺得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評分多讀書,讀好書,從茅盾文學奬作品開始讀。嘿嘿
評分到貨很快。簡潔的版本,特價9塊9買的,果然一分錢一分貨啊。不過反正重視的是內容,簡潔版挺好的。
評分這個硬精裝個人不太喜歡,再有封皮易髒。
評分童年迴憶啊,初中的時候背的瀋復的課文:餘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鞦毫。。。。。現在迴頭看又有不一樣的體驗,也可以看到作者彆的一些人生事,包括談戀愛跟結婚,清苦但是浪漫
評分非常好的書,值得認真拜讀!書的質量,物流,包裝都是非常不錯,以後買書就認京東!
評分第一張圖的書是帶塑料封的,第二張圖是不帶塑封的,兩本大書隻用塑料袋子包裝袋,其餘的書用紙箱裝的,沒什麼破損
評分很好,很好,非常好,送貨快,不錯
評分京東自營産品質量很好,物流很快,快遞小哥給力,包裝完好!
評分封麵設計精美,女兒特彆喜歡。紙質好,正版。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生命不息 [Life After Lif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53526/rBEbRlNsS2kIAAAAAAi7us76qWkAAAhcQNO8PQACLvS86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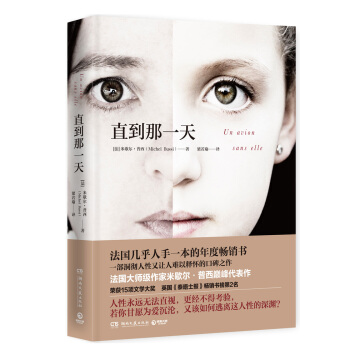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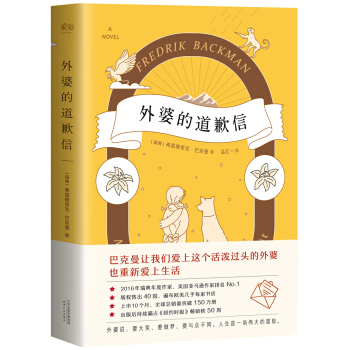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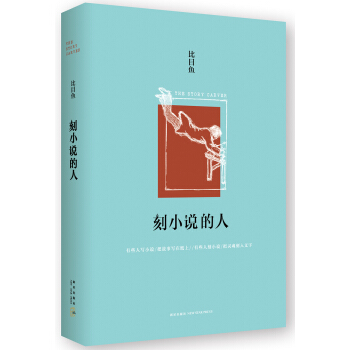


![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What?We?Talk?about?When?We?Talk?about?Lov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030661/ddd37f41-93c5-4541-a043-1f8a2799b9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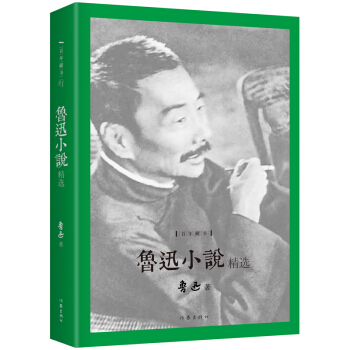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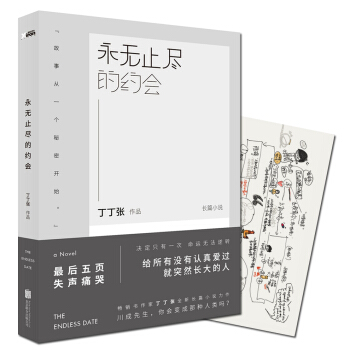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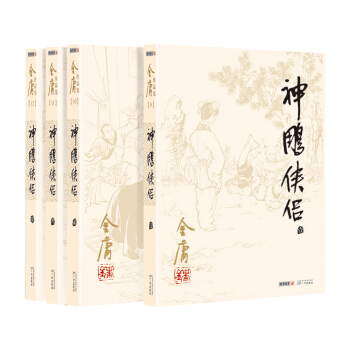
![時光守護者 [The Time Keep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270834/rBEhWlIfEZkIAAAAAAQ4wjVXEmEAAClkgBK0oQABDja8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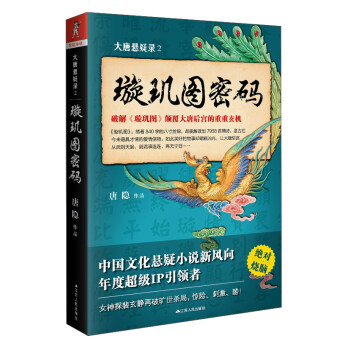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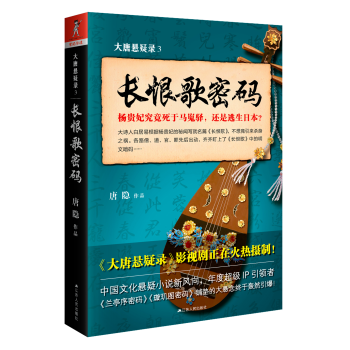
![布魯剋林有棵樹 [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030635/5ad841f7N72a808b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