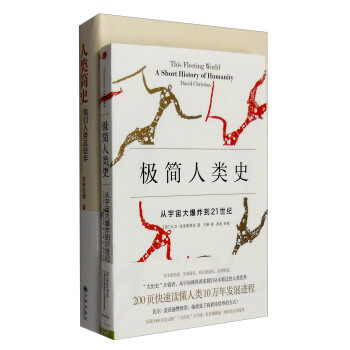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本书讲述现代智人近10万年的发展轨迹。它以宇宙大爆炸为起点,在138亿年宇宙演化的壮阔背景下,俯瞰人类历史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定位人类在宇宙长河中的历史坐标。
书中从宇宙大爆炸、星系演变,生命进化,讲到早期社会的诞生、农业文明的出现、现代社会与文明危机。
全书共4个篇章,在不到10万字的篇幅里,清晰地勾勒出每阶段的发展框架:
第1章,“前传:开端之前”,讲述在宇宙演化进程中,人类是如何诞生的,以及现代智人是如何出现的;
第2章,“开端:采集狩猎时代”,讲述现代智人如何从生物圈中脱颖而出,建立人类社会;
第3章,“加速:农耕时代”,讲述农业文明的扩散,以及分散在各地的社群如何建立起相似的生活方式;
第4章,“我们的世界:近现代”,讲述更高级的工业文明的诞生,及其如何一次次将我们推到文明危机的边缘。
通过这4个章节,《极简人类史》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壮阔的历史犬图景,帮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清,人类历史从哪里来,以及人类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
这本书用一个大比例尺看待历史,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接个了无生趣的事实”,而是富有逻辑、互动连接的人类共同的故事。
《人类简史:我们人类这些年》:
本书是作者潜心多年,精心写成的重磅力作,从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诞生到宗教的萌芽,从原始人部落之间的争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者将人类从无到有、从古至今的关键点和细节逐一讲述,风趣而幽默,犀利而深刻。翻开这本书,您将跟随作者感受三百万年人类发展史,六千年人类文明史。
为什么其他与人类同期诞生的物种逐渐毁灭,人类最终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为什么人类能适应群居生活?为什么人类需要宗教的寄托?为什么人类的社会欲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增长?在现代世界物质如此丰富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人们仍然相互争夺与伤害?人类的未来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否会消灭人类?……
梳理重大脉络,把握细节,披沙拣金,作者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带您领略人类发展的风云变幻和永恒魅力。
作者简介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历史学者,他开创了以“宇宙大爆炸”为开端的“大历史”(Big History)。他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演化的宏大背景之下,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俯瞰人类历史发展全貌。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将他的理论与牛顿、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克里斯蒂安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非凡成就,他的“大历史”观还改变了许多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比尔·盖茨在看到他所讲述的“大历史”课程后,斥资1000万美元打造“大历史”公开课,影响了美澳荷韩英等数十个国家的年轻读者。克里斯蒂安曾通过TED、达沃斯论坛等,向人们介绍大历史,他的TED演讲名为《18分钟人类史》(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in 18 Minutes)。
精彩书评
★我喜欢学习新事物,那是一种奇妙的旅程。但你还不知道我是怎样看待世界的全景的,也正是那一览众山小的视野才是振奋人心的。“大历史”正是一门这样的课程,它把所有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它使用时间线、系统的理解方式与历史视角,把所有相关的事物汇集在一个大框架之下。这正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门特有的课程,我鼓励你们不妨一试。——“微软之父” 比尔·盖茨
★《极简人类史》是一部视野宏大的人类简史,它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内,清晰地勾勒出现代智人10万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史的恢弘背景下,反思人类过去的生存法则,追问人类未来的发展之道。这本书为我们认清人类世界,提供了一种超凡的视野,书中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句,引领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
★恺撒一句名言,总结了征战高卢的10年峥嵘往事:我来、我见、我征服!现在,大卫·克里斯蒂安用同样卓绝的见识,在不到10万字的篇幅里,勾勒出人类25万年的发展进程。他比恺撒更能高谈阔论,告诉我们人类的集体学习能力如何促进技能的提升,并且促进人口、财富、实力的增长。要想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中认清自己,《极简人类史》就是一个快速、便捷、令人服膺的途径!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奠基人 威廉·麦克尼尔
目录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赞誉推荐
致中国读者
中文版推荐序
序言
1 前传:开端之前
2 开端:采集狩猎时代
研究采集狩猎时代
人类历史的开端
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采集狩猎时代的重大变革
世界历史中的采集狩猎时代
3 加速:农耕时代
农业的起源
总体特点和长期趋势
城市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公元前8000—前3000年
最早的城市和国家:公元前3000—前500年
农业、城市与帝国:公元前500—1000年
现代革命前夕的农业社会:1000—1750
世界史中的农耕时代
4 我们的世界:近现代
近现代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解释现代革命
工业革命:1750—1914
20世纪危机:1914—1945
现代历史:1945年至今
人类的结局
附录A 如何在课堂使用《极简人类史》
附录B 世界历史分期
附录C 参考文献
《人类简史:我们人类这些年》: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
古老的地球
生命的源头
达尔文与《进化论》
第二章 文明的诞生
最早的社会活动
文字的由来
第三章 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犹太文明与波斯文明
第四章 古埃及文明
古老的埃及文明
多神崇拜
宗教的改革
神秘的木乃伊
伟大的金字塔
第五章 古印度河文明
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早期城市生活缩影
印度河文明的衰落
第六章 爱琴文明
《荷马史诗》与特洛伊
克里特文明
迈锡尼文明
第七章 古希腊文明
城邦的历史
美的创造
第八章 罗马文明
共和国政体
罗马帝国
气势宏大的文化
第九章 人类的中世纪
中世纪的序幕
黑暗的中世纪
压抑的社会生活
第十章 拜占庭帝国
东罗马帝国
拜占庭文化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建立
斯拉夫传说
俄罗斯的统一
第十二章 宗教战争
伊斯兰世界
十字军东征
第十三章 文艺复兴
黑死病与中世纪的衰弱
文艺复兴揭开帷幕
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艺术成果
文艺复兴三杰
第十四章 古代亚非文明
古印度文明
古日本文明
古非洲文明
第十五章 古代美洲文明
美洲文明的起源
中部美洲文化圈
安第斯山文化圈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革命
尼德兰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大革命
欧洲1848年革命
俄国农奴制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
第十七章 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
欧美工业革命
第十八章 法国启蒙运动
用光明驱散黑暗
启蒙思想家
第十九章 殖民与侵略
开辟新航路
非洲黑人奴隶贸易
美国独立运动
亚洲的殖民、侵略与瓜分
第二十章 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联合国与世界和平
精彩书摘
前传:开端之前在人类历史以外,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范畴,即地球史甚至整个宇宙的历史。本章“前传”正是希望在这个更大的范畴之内,讲述人类过去的历史—这也正是“大历史”研究的范畴。正如我们需要用世界历史,来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区域的历史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历史在地球史乃至宇宙史中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进行超越人类自身历史的思考,我们就需要“大历史”。
20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没有历史,它始终存在着。但我们有理由对此假设持怀疑态度。20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Hubble)找出证据,发现大多数遥远的星系一直在离我们远去。这些证据表明宇宙可能一直在膨胀。如果宇宙在膨胀,则证明它过去一定小得多,而且在遥远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它可能被压缩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内—甚至比一个原子还要小。
20世纪中叶,大部分天文学家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猜测正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发现,人类并非唯一拥有历史的创造物。地球有自己的历史,整个宇宙也有自己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开始能够讲述这段历史,并将人类历史视为一部更宏大、更科学的“创世史”的一部分。本章人类史“前传”希望以21世纪的知识视野,向大家提供这部大历史的概览。(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宇宙出现在大约138亿年前,源于宇宙学家所说的“大爆炸”。这是所有历史日期的开端,我们对大爆炸之前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时间、空间甚至虚无,我们缺少任何与此有关的信息或是理论;这也正是创世故事开始的时候。但是其实,从宇宙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能够讲述一个符合现代科学基本理念的创世故事—这个故事建立在大量且仍在不断增加的证据之上。
当宇宙刚刚出现时,它极其微小,很可能比一个原子都小。然而,在其内部蕴含着组成宇宙所需的所有物质和能量。此时的宇宙温度极高,(几乎无法用数字衡量!)以至于物质、能量、粒子、空间和时间全都混杂在一起。随后,在巨大能量的作用下,宇宙发生急剧膨胀,其速度可能比光速还要快。在暴胀过程中,宇宙逐渐冷却。正如蒸汽最终会凝结成水一样,宇宙在冷却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变化”。从宇宙诞生的第一秒开始,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就出现了,包括引力(一种将万物拉拢聚合的力量)与电磁力(一种促使异性电荷相吸,同性电荷相斥的力量)。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夸克此时也出现了。然而诞生初始的宇宙变化剧烈,大部分粒子一出现就消失,转化成宇宙中的纯能量。
下一秒,宇宙暴胀的速度慢了下来。此时的宇宙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各种物质,包括质子和电子(组成原子的基本成分)以及至少四种基本形式的能量。这时的宇宙仍比太阳中心还要炽热,充斥着“等离子体”,这是一种由能量和带电粒子组成的杂乱的混合。大约38万年后,宇宙开始经历另一个“阶段变化”。此时的宇宙温度继续下降,使得带正电的质子能够捕获带负电的电子,形成最早的原子。原子呈电中性,于是突然之间,物质不再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在今天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中,我们仍可以探测到宇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释放的能量。宇宙背景辐射可以对老式电视机产生静电干扰,它的存在是上述故事真实可靠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在这个阶段,物质的存在形式都极其简单。大多数物质都由自由移动的氢原子和氦原子组成。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而氦原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组成。历经千百万年,早期宇宙就是由这种氢原子和氦原子构成的大片星云组成的。那时的宇宙没有星体,唯一将其点亮的是穿行其中的巨大能量。
·思想实验
人类试图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不一定能达成共识。参考一下作家马克·吐温的看法,他写道,人类总是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至少是整个历史的中心。1903年,在题为“世界是为人类而造的吗?”(“Wasthe World Made for Man?”)的文章中,马克·吐温写道,“如果埃菲尔铁塔代表宇宙的历史,那么它顶端的球形构造上,那层薄薄的油漆就代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人会认为那层薄薄的油漆是建造埃菲尔铁塔的目的。但我想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回应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我们人类是否应当一直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点重要吗?
……
前言/序言
我们迫切地需要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正是眼前这本《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 )的写作初衷。今天的世界联系空前紧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生活在地球村,我们不但要了解彼此的分歧,更应该清楚彼此共同的关切。如果我们想避免因战争或生态崩溃( 或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的全球性危机,“ 人性共通”和“ 全球公民”的意识就必须在未来几十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关切,我们必须清楚人类有一部属于自己的“ 大历史”,这是一部特定地区、国家、民族甚至不同世界的“ 大历史”。正如“ 一战”刚刚结束时,H·G·韦尔斯( H. G. Wells )在《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一书中写到的一样:“ 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没有和平与繁荣。倘若在合作中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仅凭狭隘、自私且彼此矛盾的所谓‘ 国家传统’行事,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就注定滑向冲突和毁灭。”就在韦尔斯写下上述文字前后,据称亨利·福特(HenryFord )也曾说过,历史仿佛是由“ 一个接一个了无生趣的事实”组成的。( 我们无从得知福特是否读过《世界史纲》一书,如果读过,他又该作何感想。)类似的历史并无太大意义。学生常常不知为何而学,而教师也常常不知为何而教。如果历史能够向读者讲述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周遭世界的趣事、要事,剖析前因后果,引人入胜而又催人奋进,那么历史是值得学、值得教的。要使细节产生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演变中,观察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或世界的历史演变。
但究竟是何种演变和哪些群体呢?历史学家在不同的维度进行历史叙事。有人书写特定的社群或历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阿兹特克帝国的兴起。有人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叙述,涵盖整个历史时期或区域,如古罗马史或美国史。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历史叙事,而且书写美国史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史其实都相对简单。此外还有第三维度,即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史。世界史学者们试图探寻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细节如何连接着更宏大的历史演变。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历史叙事自然比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叙事包含“ 更多的史实”,这也是为何讲述世界历史更加困难的原因。《极简人类史》一书正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而写。
当我们进一步涉足被称为“大历史”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时,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大历史演变过程将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融入宇宙演化史。典型的大历史叙事通常从多个维度审视历史。它往往从宇宙学家称之为“ 大爆炸”的宇宙开端落笔,在开头几页就进行描述;接下来,随着原始宇宙( 仅由氢原子、氦原子和大量能量组成)产生日益复杂的事物,大历史开始描述逐渐出现的更加复杂的实体。许多学生认为,大历史课程可以满足他们对生命、地球和宇宙等宏观问题的好奇心,而这些话题恰恰又是他们十分希望了解却被大部分学校课程忽略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希望讨论这个宏大故事的新走向,他们希望讨论未来。这自然而然将历史引入了环境研究领域,后者也是一个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领域。什么是“ 人类世”( Anthropocene epoch )?廉价能源是否会耗尽?新技术能够支撑人类的持续性发展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但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以及对人类世界以外更宏观领域的“ 大历史”的领悟,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议题的实质。
用户评价
阅读完这本书的初稿,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叙事功力非同一般。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原本枯燥、庞大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宏大历史叙事,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例如,在描述早期智人迁徙的章节里,他没有堆砌冰冷的考古数据,而是将视角聚焦到某个具体小群体在面对冰河期的挣扎与智慧上,那种画面感立刻就出来了,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风雪交加的时代,感受着生存的艰难与人类适应性的伟大。这种将“大历史”拉回到“小切口”的叙事手法,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即便是历史初学者也能轻松跟上节奏,并且能从中汲取到深刻的思考。叙述的节奏感把握得非常到位,有张有弛,该详尽处细致入微,该概括处则一笔带过,使得整本书读起来酣畅淋漓,毫不拖沓。
评分坦白说,我原本对这类“通史”读物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总担心内容会过于肤浅,蜻蜓点水,无法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然而,这套书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它在追求广度的同时,竟然没有牺牲深度的探讨。在涉及认知革命的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的前沿研究,即便有些概念读起来需要放慢速度反复咀嚼,但那种智力上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茅塞顿开”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它不是简单地告知你“是什么”,而是深入探讨“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种机制在今天如何依然有效”。这种对底层逻辑的挖掘和批判性思维的引导,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一般的大众科普读物,更像是一部引导我们重塑世界观的工具书。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有一种独特的、近乎哲学的魅力。它没有故作高深,但字里行间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一种淡淡的敬畏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争议性议题时所展现的克制与平衡。例如,在讨论基因编辑或人工智能的未来潜力时,作者并未简单地倾向于乐观或悲观,而是冷静地列举了各种可能性及其潜在的伦理风险,将最终的判断权交还给读者。这种成熟、不预设立场的态度,让人在阅读时感到非常信服。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氛围:我们都是这场漫长人类实验中的参与者,需要带着谦卑与警醒,去面对未来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读完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这个世界,乃至我们“何以为人”这个问题,都有了全新的、更具层次感的认识。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确实很有心思,拿到手时就被那种沉甸甸的质感吸引住了。封面的设计简约而不失深邃感,黑白灰的搭配很显高级,尤其是在书脊的处理上,那种磨砂的触感非常舒服,每次从书架上抽出来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我特别喜欢它那种低调的奢华感,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更容易沉浸到文字的世界里去,不会被过于花哨的元素分散注意力。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有考究,虽然是普及读物,但纸张厚实,油墨清晰,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出版方在制作这套书时所下的功夫,它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那种触感和视觉上的双重满足感,让我在翻开第一页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展开的旅程充满了期待,这套书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对阅读体验的尊重。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它对人类文明演进中那些关键“转折点”的洞察力。它不像传统的教科书那样线性叙述,而是像一个高空的观察者,不断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间进行切换和对比。比如,作者将农业革命的冲击与工业革命的爆发进行了跨越万年的平行对照,揭示了看似不同的社会结构背后,驱动人类行为的底层逻辑——对资源和生存的焦虑与渴望,其实从未改变。这种超越时间维度的宏观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二字的理解。它不再是帝王将相的更迭,而是关于生命形态、认知能力和集体组织效率的不断迭代。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次重新定位,让人不禁深思,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进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评分很好 价格很便宜用起来挺舒服
评分很好
评分不错,正品
评分搞活动 囤货慢慢看
评分?
评分挺好的,满意。
评分好!!!!!!!!!!!
评分很不错啊
评分很不错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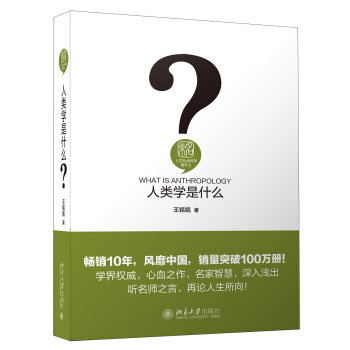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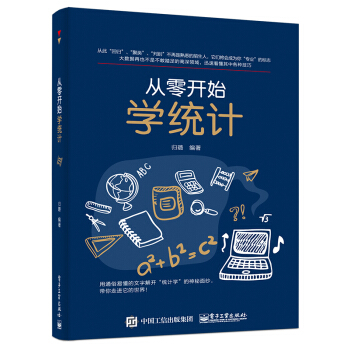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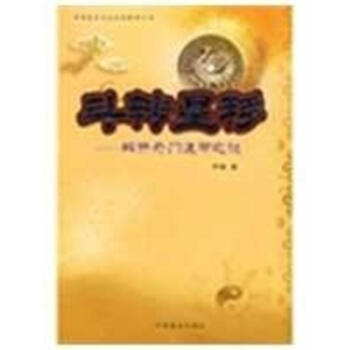
![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 [WORDS OF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19307/6e4f65cb-4362-41c2-a607-f8c3bc8ce1b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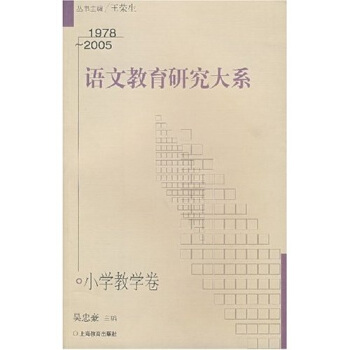
![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 [Teaching by Princip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33841/f7ccb882-12aa-4e14-8f5a-4e1f042db1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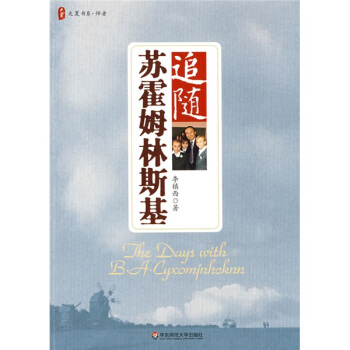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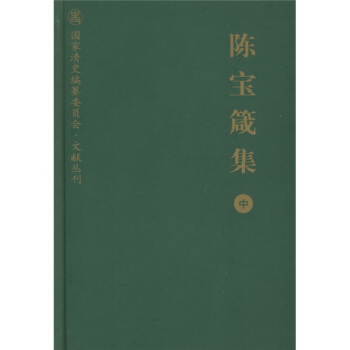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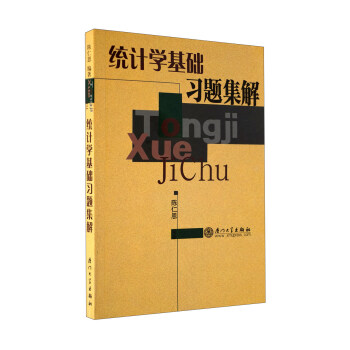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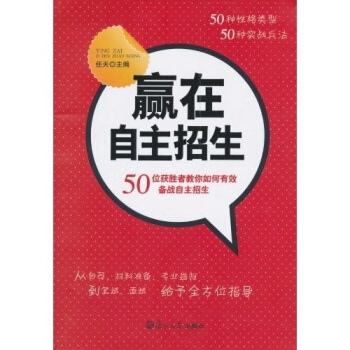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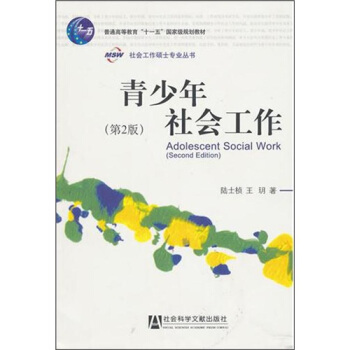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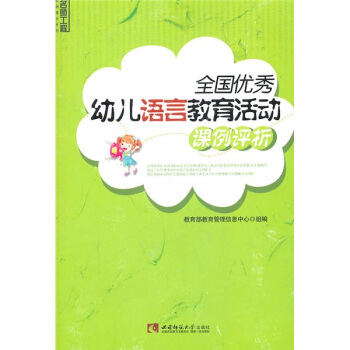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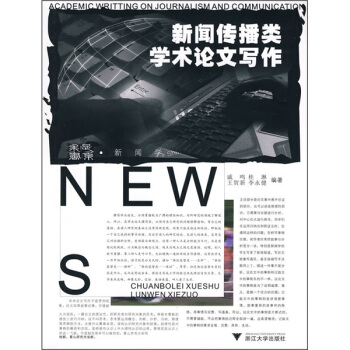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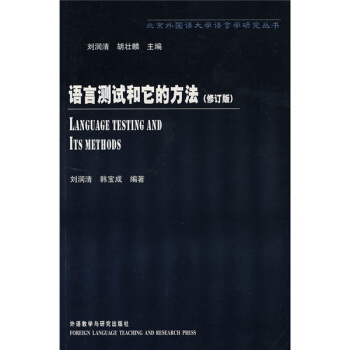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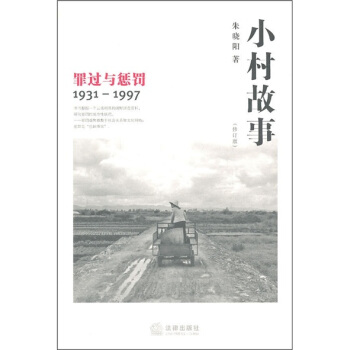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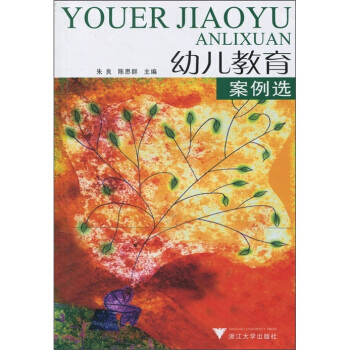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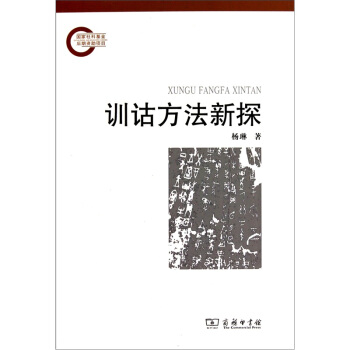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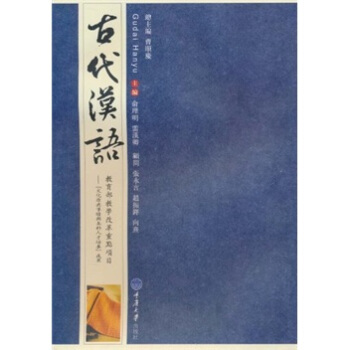
![社会理论研究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52506/16da1d2b-d347-472c-b4e5-be09ad179559.jpg)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61756/09fcb23d-7193-4fef-9b2e-c226c786623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