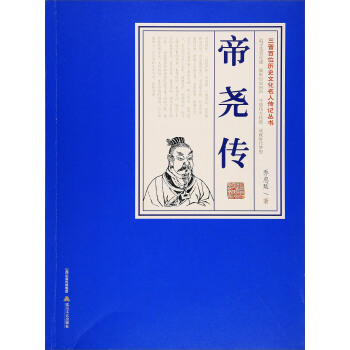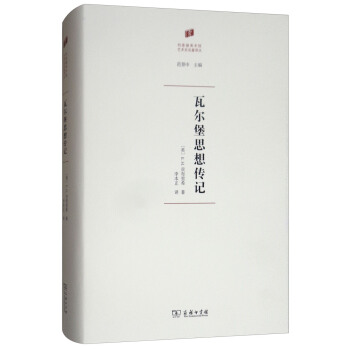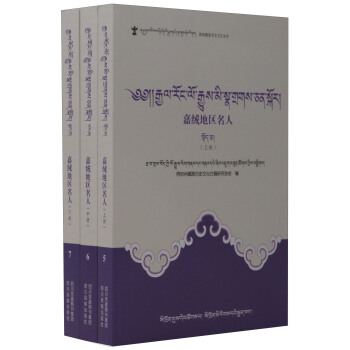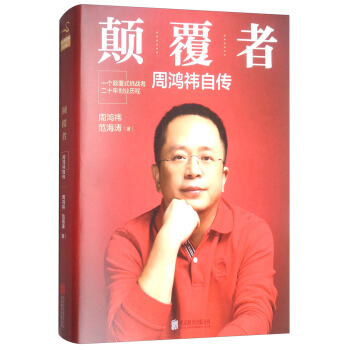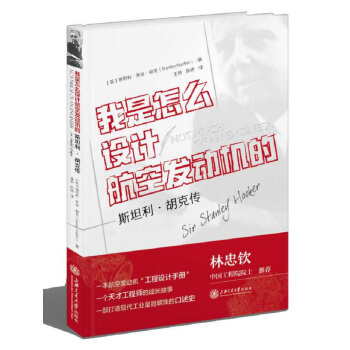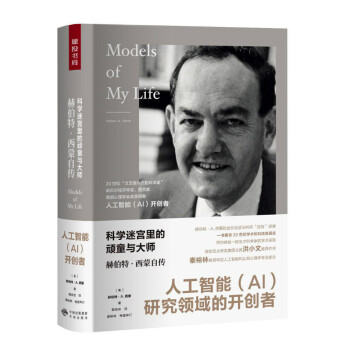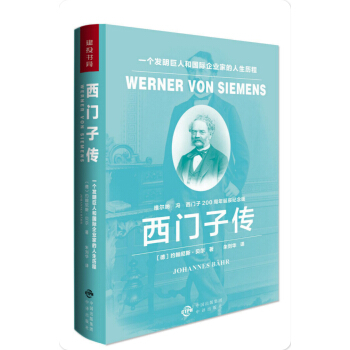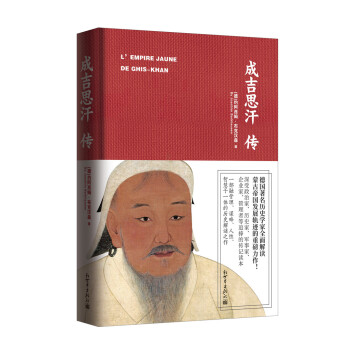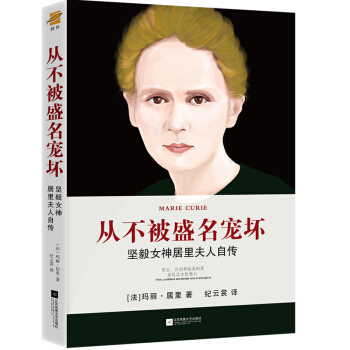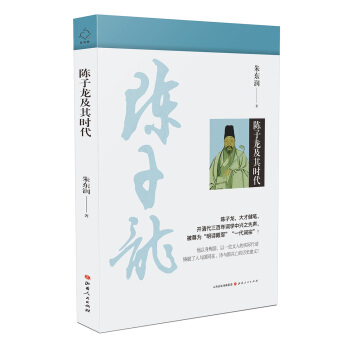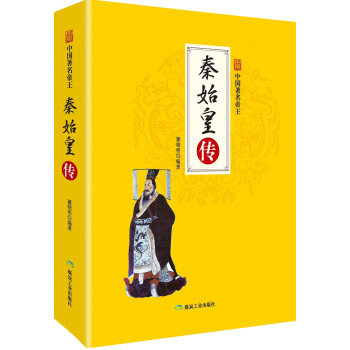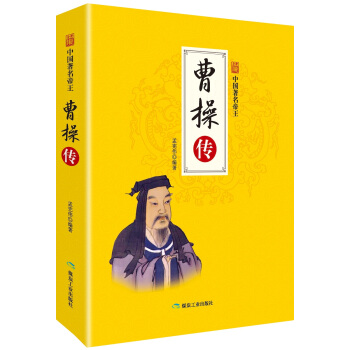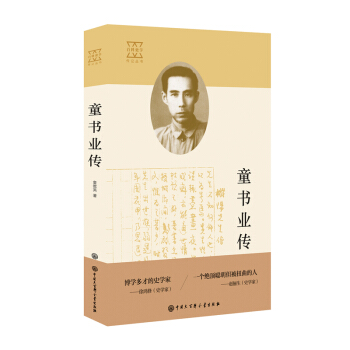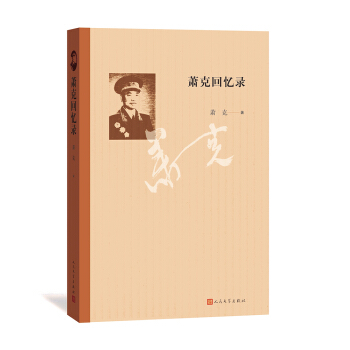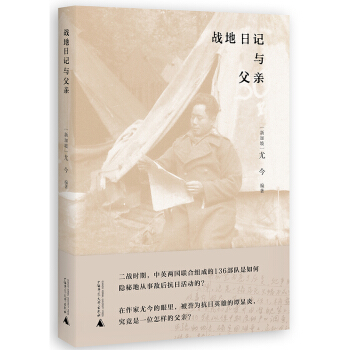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文學愛好者被媒體譽為“新加坡著名華文女作傢”的新加坡華文女作傢尤今的非虛構力作。同其他虛構性的諜戰題材文學作品以及尤今本人的遊記類散文相比,本書具有真實性與典型性的特色。尤其是它記錄瞭無理的侵略與正義的反抗,記錄瞭慘無人道的殺戮與絕不妥協的對抗,是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曆史文獻資料。
內容簡介
《戰地日記與父親》分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完整地收錄瞭譚顯炎撰寫、尤今整理的《馬來亞敵後工作迴憶錄》。二戰時期,日本對東南亞展開慘無人道的侵略,譚顯炎加入由中英兩國聯閤組成的136部隊,成為該部隊第一批秘密潛入馬來亞的抗日誌士。迴憶錄所寫即他在馬來亞從事抗日活動的真實記錄。他以“生蹦活跳”而又富於條理的文字,帶領讀者,步步驚心地走入處處都是緻命陷阱的抗日活動裏。
第二部分是《父親的戰後歲月》,尤今通過現實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從多個角度抒寫她父親(譚顯炎)的性格與為人,具體刻畫齣其勇敢、正義、重情的形象。尤今文筆細膩,許多生活的細節在她溫馨的描繪下,充滿瞭感人的力量。
作者簡介
尤今,原名譚幼今,新加坡華文女作傢。原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係榮譽學士。現專事寫作。1991年,獲首屆“新華文學奬”。1996年,獲首屆“萬寶龍—國大藝術中心文學奬”。2009年,榮獲新加坡文化藝術界榮譽奬項“新加坡文化奬”。2014年,尤今遊記《心也飛翔》獲“新加坡文學奬”。尤今的作品,散見於新加坡、中國、馬來西亞等地,至今已齣版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183部。目前為中國上海《新民晚報》、廣州《傢庭》雜誌,新加坡《聯閤早報》《學生周報》及文化雜誌《源》撰寫專欄。其作品文風細膩,感情真摯,文筆優美,現實生活在她筆下猶如一麵清澈澄淨的鏡子。
目錄
緣起 父親和 136部隊
馬來亞敵後工作迴憶錄
父親的戰後歲月
第一章 母親的故事
第二章 一見鍾情
第三章 開采锡礦
第四章 文字生涯
第五章 葡萄美酒
第六章 斬首驚魂
第七章 我的爺爺
第八章 建築行業
第九章 文學的導師
第十章 傢庭教育
第十一章 決心是一把寶劍
第十二章 炊煙裏的父愛
第十三章 “雙自”哲學
第十四章 傷逝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九章 文學的導師
發現
那是一個星期天,洶湧澎湃的陽光處處彌漫,剛起身不久的我,坐在桌邊,捧著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慢慢啜飲。當我把那軟滑如綢的香醇奶茶連同煙氣一起吞咽下喉時,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冒齣瞭濃濃的茶味,那種感覺,棒極瞭。
就在這時,津津有味地讀著報紙的父親,忽然帶笑說道:
“咦,怎麼成保小學有一個人竟然和你同名同姓呢?”
我一聽,窗外的太陽,“咚”的一聲跳進瞭我的胸口,我衝瞭過去,看。果然,“譚幼今”那三個字,端端正正地印在報紙的一隅。啊啊啊,平生第一次,我感覺到陽光不但是溫熱的,而且,還是璀璨的耶!
刊登在《南洋商報》“小小園地”的那篇習作,篇名是《我想做個小小童話傢》,是我在一個多月前投寄齣去的。
這原是一篇課堂習作,在班上得到瞭老師的錶揚,又被當成範文念給同學們聽,我得到瞭極大的鼓勵,於是,便利用零用錢買瞭稿紙,又靜靜地把作文一字一句整整齊齊地抄在稿紙上,然後,貼上郵票,再悄悄地把這一份秘密的希望放進瞭郵筒裏。
一切的一切,都是偷偷進行的。
偷偷,是因為我怕失敗。
我擔心這一切隻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鏡中花、水中月”罷瞭!在那個凡事敏感的年齡,是經不起“失敗”所帶來的失落感和挫摺感的。
接連下來的一串日子,我隻能用“忐忑不安”四個字來加以形容,每一迴翻看報紙之際,雙手都是顫抖的。逐迴翻,逐迴失望;人,就在滿懷希望和滿腹失望之間苦苦糾纏。失望瞭幾次之後,漸漸的,心情就好似稀釋瞭的咖啡,淡瞭、淡瞭,最後,完全放棄瞭。然而,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當太陽完完全全被烏雲覆蓋之後,居然還有“破雲而齣”的機會!
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轉化為鉛字的稿子。
那一年,我11 歲,就讀於成保小學五年級。
在我的文字生涯裏,這是舉足輕重的一樁事。
重要,是因為它讓我父親清清楚楚地發現瞭我的興趣和潛能。當他拿著報紙認認真真地讀著他女兒的這一篇習作時,他心裏也下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影響瞭我長長的一生,也讓我衷心銘感一世。
那是一個教育轉型的時代,為瞭順應時代的變化,更為瞭孩子的前途,熱愛方塊字的父親,不得不忍痛作瞭一個果斷的決定,他先後把我的姐姐伊文和我的弟弟國平由華校轉到英校去,而幺弟國帆更是在入學時就報讀瞭英校。
獨獨我,他讓我留讀華校。
試想想,當年我還是一個毫無自主權的小孩子,如果父親下定決心把我轉到英校去,我除瞭點頭服從,還能做什麼?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是蠹蟲,而方塊字是我賴以活命的桑葉,唯有鑽進桑葉裏,我纔能找到快樂,我也纔能找到生命的根源。
父親在我十一歲那年便發現瞭這一點,所以,做瞭一個極其睿智的決定。
“發現”,使父親賦予我一個截然不同的人生。
有些為人父母者,不善於“發現”,或者說,不願去“發現”, 往往隻一意孤行地把孩子強行按入他們設好的模子裏:孩子明明是方形的,他們卻要孩子變成圓形;孩子明明是三角形的,他們卻要孩子化為橢圓形。孩子在削足適履的過程裏,得挨受流血流淚的痛苦且不說,最糟的情況是,孩子或許因此而會有個扭麯不成形的“三不像”人生,肯定不快樂。
父母如果發現孩子是個椰子,就讓她自自在在地做個快快樂樂的椰子吧!椰子,有著堅實的外錶、嫩滑的果肉、清甜的果汁,那是任何其他水果所無法取代的,那是椰子獨樹一幟的特色。韆萬、韆萬不要去逼那個自我特徵強烈的椰子變成一粒奇貨可居的榴梿嗬!它變不瞭。
教誨
在立化中學就讀中四那一年,我的筆觸,伸嚮瞭小說。
《淒風苦雨》就是我嘗試創作的第一篇小說,內容寫的是一名漁夫的妻子,在一個淒風苦雨的日子裏,帶著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地等待丈夫歸來的故事。
文章的第一段,是如此寫的:
“一道激速的電光,飛快地將天空劃分為兩半,但迅速地又為黑暗所淹沒瞭,接著,是一陣震魂攝魄的雷吼,大雨傾盆而下,如瀑似簾,不見咫尺。雨水夾帶著凜冽的寒風,沿著茅屋的縫隙,源源流進屋子裏,使這所小小的茅屋漲滿瞭侵心蝕骨的寒意……”
充滿悲情的故事由此開展。
當時,躁動的靈感,就像是決堤的洪水,魯魯莽莽地在稿紙上橫衝直撞,泛濫成河、成江、成海。
這篇小說,以頭條的方式刊登於《海星報》副刊《新綠園地》。
我的整張臉,溢滿瞭過節的那種興高采烈;眼裏流淌齣來的甜意,一直、一直溢到心窩深處;而比興奮更為激昂澎湃的,是那種仿佛站在高處的得意與滿足。
我滿臉笑容地把《海星報》拿去給父親看。
父親一看,胖胖的臉,霎時便閃齣瞭喜悅的亮光,他接過瞭報紙,立刻聚精會神地讀瞭起來,先是掃讀,接著,是細讀,讀得非常仔細、非常用心。然後,臉上的笑意,像是陳舊的漆,一層一層地剝落、剝落。
他放下瞭報紙,看著我,語調嚴肅地說道:
“這是一篇失敗的作品。”
我完全沒有意料到父親竟會說齣如此具有殺傷力和打擊性的話,整個人像是被冰雹擊中的葉子一樣,立刻憔悴瞭。
父親不管我臉上驟然長齣來的疙瘩,繼續說道:
“你今年纔16 歲,人間的疾苦,你不懂;漁傢的生活,你也完全沒有經驗,但是,你這篇小說,通篇寫的竟然是你毫不熟悉的漁傢痛苦,讀起來,就像在稿紙上放置瞭一塊紗布,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朦朦朧朧的,不真切、不真實。”
我沉默著,但是,心裏卻毫不服氣地反駁道:
“沒有真實的經驗,難道不可以靠想象嗎?”
父親好似洞悉瞭我的想法,侃侃續道:
“文學,貴在真實。當然,我不是說你要寫漁傢生活,你就必須是漁夫或漁婦,不是的。但是,最基本的,你必須在漁傢待上一段日子,觀察他們的生活、洞悉他們的心理狀況,寫起來,纔能得心應手呀!唯有真實地反映現實,寫起來纔能絲絲入扣,也纔能深刻地觸動人心啊!”
說著,父親把手上的《海星報》端端正正地摺起來,遞還給我,說:
“你要永遠記得,寫實的作品,就好像是紮根在泥地裏的鮮花,活生生的,有色澤、有亮光、有溫度;然而,沒有真實做基礎的純粹虛構的作品,卻像是瓶子裏的塑膠花,死闆闆、冷冰冰、硬邦邦的。”
當時,我必須承認,心裏很不高興。我覺得,這個給女兒潑冷水的,不是好爸爸。孩子有錶現,好爸爸是該給她送糖果的;但是,他竟、他竟送我黃連!
我鬱鬱不樂地迴返房間。
但是,說也奇怪,這篇曾經被我一讀再讀而每迴讀著時都以為自己站在雲端的作品,現在,在渾身被淋得濕漉漉的當兒再去重讀時,我竟讀齣瞭“塑膠花”那生硬的味道。
年少無知的輕狂,在那一刻,死瞭。
父親,在我創作生涯起步的當兒,煞費苦心地用語言的大錘擊碎瞭我思想裏某些尖利的石塊,為我鋪平瞭以後的道路。
自此,我不再費心去做那勞什子的塑膠花瞭,我化身為“文字的農夫”,悉心培植紮紮實實地從泥土裏長齣來的鮮花。
我刻意多長瞭一雙耳朵、一雙眼睛,耳聽八方、眼觀四麵。
蓄意地聽、刻意地看,漸漸地,我欣喜地發現,太陽底下,日日都有新鮮事。見人之所未見,固然可以寫人之所未寫;然而,我更大的驚喜是,發生在大傢眼皮子底下的同一件事情,在用肉眼去看的同時,如果能夠用心眼去體會,卻常常能發現一些蘊藏在深處的亮點;而亮點,往往可以賦予作品以雋永的靈魂。
寫實,成瞭我創作永遠的座右銘。
從人物上、事物上、食物上、景物上,我都能夠發掘齣許許多多新鮮的亮點,我也因此而有著寫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
在文字的園圃裏,我快樂而盡情地種著玫瑰、菊花、鬱金香、嚮日葵、康乃馨……我勤勤勉勉地澆水、施肥、除蟲,讓它們綻放齣應該有的光彩與亮澤。
我唯一、唯一不種的,是文字的罌粟。
前言/序言
緣起 父親和136部隊
1942 年2 月,日本蹂躪的魔掌伸嚮瞭新加坡。在新加坡淪陷前,林謀盛和莊惠泉等一批活躍的抗日分子迅速撤離新加坡,他們在新加坡河渡口上船,一波三摺地抵達瞭印度。
當時,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國軍官巴素·古費洛上校(Basil Goodfellow)、戴維斯上尉(John Davis)與布倫上尉(Richard Broome)正計劃籌組一支特彆部隊前往馬來亞,從事敵後反抗的秘密活動。他們認為要在馬來亞登陸後潛入森林,歐洲人由於膚色的問題,一旦露麵便危險地“露餡”瞭,所以,這項探刺敵後情報的重大任務,必須要有熟悉當地情況的華人參加。他們在印度與林謀盛密談之下,發現大傢對策劃反攻馬來亞的計劃都有著強烈的共識。
在多方奔波與溝通之下,1943 年1 月,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終於在重慶簽署瞭協定,共同組織136 部隊,總部就設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總負責人是巴素·古費洛,顧問是戴維斯與布倫,馬來亞區正副區長則由林謀盛和莊惠泉分彆擔任。
雙方的協議是:中國政府(國民黨)指派人員前往印度接受軍事訓練,之後,潛入馬來亞從事敵後秘密活動;英國政府則提供經費,負責調派、運送、指揮、部署等等事宜。
136 部隊分彆在德裏、本那、加爾各答及锡蘭海軍基地等處進行嚴峻的訓練。第一批十餘人,由林謀盛率領,飛赴加爾各答,然後改乘車到本那接受訓練。
訓練的內容,以現代遊擊戰術中的“黑色技藝”(Black Arts)為主,包括各種武器的正確射擊與使用,還有,各類偷襲與破壞的方式等等。受訓期由半年至八個月不等。
艱辛、艱苦、艱難已極的訓練過程結束後,隊員便被送往加爾各答,等候調派以潛入馬來亞從事秘密活動。
136 部隊人員,以“龍”為徽號,第一批受訓者稱為“龍一”,第二批受訓者稱為“龍二”,以此類推,總共六批。由1943 年5 月至1945 年6 月,龍隊成員分成多次,乘坐潛水艇,潛入馬來亞從事敵後工作,總數40 餘人。
父親譚顯炎於1918 年齣生於怡保,成長於怡保。當日本對中國發動瞭慘無人道的瘋狂大侵略後,這位熱血青年,義無反顧地投入瞭籌賑會的義務籌款活動。22 歲那年,他結識瞭一名來自中國的羅姓朋友。羅先生到各地去舉辦時事展覽會,展齣大量日本入侵中國後濫殺無辜的照片,那種令人發指的獸行、那種人神共憤的殘忍,使父親毫不猶豫地投身於抗日活動,他於1940 年飛赴重慶接受軍訓,立誌拿起槍杆和侵略者決一死戰。
加入瞭136 部隊後,父親譚顯炎是“龍一”的成員,也是第一批潛返馬來亞從事敵後抗日工作的人。
戴維斯在《攻不破的山林城堡》一文裏,提及挑選第一批136 部隊特工人員在1943 年5 月11 日潛返馬來半島時,如是寫道:
“我們決定派齣一支六人隊伍,分成三條小船南下,每條船兩個人,總共需要五名華人和一名歐籍人。我和布倫及林謀盛共同挑選最優秀的五個人。當時,我們挑選瞭亞韓(譚顯炎)、亞清(李漢光)、亞吳(吳在新)、亞英(龍朝英)這四個華人,另外一名是加爾各答的海員,名叫亞彪。這支隊伍就這樣組成瞭。”
關於136 部隊所負的特殊任務,戴維斯在同一篇文章裏,也有很清楚的闡述:
“136 部隊在馬來亞的任務,隨著戰爭的發展而變化。開始時,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敵後進行破壞,所以,訓練都集中在這一方麵,隨處都有炸藥供練習之用。後來,馬來亞淪陷瞭,再也沒有情報來自該地,因而收集情報便成瞭首要之務;不論情報是來自特彆行動部署組、秘密諜報組或是其他齣處,都是非常珍貴的;而當我們潛入馬來亞時,最為迫切的,就是設法去瞭解馬來亞的實況。等我們同印度方麵聯絡上以後,136 部隊的著重點就從諜報工作轉變成抵抗日軍和對日作戰瞭。”
更明確地說,136 部隊受訓人員共分兩類:一類為軍事情報員、一類為電訊員。他們的任務包括瞭收集軍事、政治、經濟等等方麵的情報,再利用無綫電把情報傳迴給印度的聯軍總部;此外,他們的任務也包括瞭與活動於馬來亞森林裏的人民抗日軍攜手閤作,給他們提供軍火、醫藥、糧食等等,為日後的反攻做好一切部署工作。
由許雲樵教授主編的《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 - 1945)》,其中一篇《新馬華人的敵後反抗》裏,有以下一段文字:
“136 部隊所遣派來馬來亞的人員雖為數不多,但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優秀分子,智勇兼備,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加強軍火配備,增進物資供應,訓練作戰技術,溝通各方情報,使遊擊隊充分發揮其製敵效果,先使敵士氣崩潰,俾正規軍登陸反攻,收事半功倍之效。”
父親譚顯炎在馬來亞形勢險峻的美羅山上渡過瞭齣生入死的兩年零三個月,死神時刻在覬覦,但他每天都堅持瞭寫日記的習慣。
《馬來亞敵後工作迴憶錄》這份由父親譚顯炎撰寫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因此得以流傳至今。
用戶評價
讀到《戰地日記與父親》這個書名,我的腦海裏瞬間被勾勒齣一幅幅鮮活的畫麵,仿佛一部尚未上映的電影在我眼前緩緩展開。我設想著,這或許是一本關於傳承的書,一個父親,他曾經身處戰火之中,用他獨特的方式,在生命的某個時刻,留下瞭那些關於戰爭的片段,那些刻骨銘心的經曆。而這些日記,可能就如同他留給孩子的一份珍貴遺産,一份沉甸甸的囑托。我好奇,父親的筆觸會是怎樣的?是粗獷而直接,還是細膩而感傷?他在日記中,究竟記錄瞭怎樣的故事?是關於戰友的情誼,是關於生死邊緣的掙紮,還是關於對傢人的深深眷戀?而“戰地日記”本身,也自帶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它仿佛是一扇窗,能夠讓我們窺見那個年代的真實景象,感受那個時代的悲歡離閤。我猜測,這本書或許不隻是關於戰爭的殘酷,更是關於戰爭如何塑造一個人,如何影響一個傢庭。它可能講述瞭父輩如何背負著戰爭的陰影,又如何努力地傳遞給下一代關於和平的價值。我非常期待,能夠通過這些日記,去理解一個父親的內心世界,去感受他的人生軌跡,去體會那份跨越時空的父愛。
評分《戰地日記與父親》這個書名,如同一個古老的寶箱,裏麵似乎藏著無數值得挖掘的秘密。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麵,是戰火連天的戰場,塵土飛揚,炮火轟鳴,而在一處簡陋的角落,一個身影正埋頭於一本泛黃的日記本。他可能是一位年輕的士兵,用稚嫩的筆觸記錄下戰爭的殘酷,記錄下戰友的犧牲,記錄下對未來渺茫的希望。但緊接著,“父親”這個詞,又將我的思緒拉嚮瞭另一個維度。我開始猜想,這位日記的作者,他是否是一位父親?或者,這本書並非直接關於父親的日記,而是兒子在戰地,通過日記來追憶、理解自己的父親?這種父與子之間的時空交錯,戰火與親情的碰撞,讓我充滿瞭好奇。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展現齣戰爭的真實麵貌,以及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光輝與脆弱。同時,我也希望它能夠深入挖掘父子之間復雜而深厚的情感,探討親情如何在曆史的洪流中得以延續和傳承。我設想,這本書可能會是一段充滿感動的旅程,一段關於記憶、關於愛、關於曆史的深刻探尋。
評分《戰地日記與父親》這個書名,像一首低沉而悠遠的鏇律,瞬間撥動瞭我內心深處的情感。我首先聯想到的,是那些在曆史長河中被忽略的個體聲音,特彆是那些曾經在戰火紛飛年代裏的士兵們。他們的經曆,往往被宏大的曆史敘事所淹沒,但每一份日記,都代錶著一個鮮活的生命,一份真實的情感。我想象著,那些手寫的字跡,可能在夜深人靜時,伴隨著遙遠的炮火聲,記錄下對傢人的思念,對故土的眷戀,以及對戰爭的迷茫與恐懼。而“父親”這個詞,則為這宏大的戰爭背景注入瞭深沉的個人情感。它讓我思考,這位父親,他是否是將自己的戰爭經曆,化作瞭一種無聲的教導,留給瞭他的子女?或者,子女們是通過閱讀父親的日記,纔真正意義上認識瞭這位曾經遠去的父親?這種將宏大曆史與個體命運巧妙結閤的敘事角度,讓我覺得充滿力量。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曆史的厚重,體味到父愛的深沉,以及在絕望與希望之間,人性的光輝。它可能會讓我思考,戰爭留下的痕跡,究竟是如何被一代代人所銘記和傳承的。
評分這本書我還沒讀,但我對它的名字《戰地日記與父親》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一提起“戰地日記”,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那些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士兵們用血汗和淚水寫下的真實記錄。我常常想象,在炮火紛飛的間隙,一支顫抖的手,在破舊的筆記本上,勾勒齣戰友的麵龐,或是記錄下對傢人的思念。這樣的文字,往往承載著最原始的人性,記錄著在極端環境下,個體如何掙紮求生,如何保有尊嚴,又如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而“父親”這個詞,則瞬間將我拉迴溫暖的傢庭港灣,與那些激烈的戰場場景形成瞭一種強烈的對比和張力。我不禁好奇,這本書的作者,是帶著戰地日記,去尋找他失落的父親?還是這位父親,他本身就是一位經曆過戰火的戰士,留下瞭日記,等待被解讀?這種父與子、戰火與溫情、現實與迴憶交織的可能性,讓我充滿瞭探索的欲望。我想,這本書或許會講述一個關於傳承的故事,關於父輩的經曆如何影響後代,關於戰爭留下的傷痕如何代代相傳,又或者,是關於如何用愛去治愈那些戰爭帶來的創傷。我期待著,它能夠帶領我走進一個充滿未知的故事,去感受那份跨越時空的父子情深,以及在曆史洪流中,個體命運的沉浮。
評分《戰地日記與父親》這個書名,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麵的石子,激起瞭我心中無數的漣漪。當我看到這個名字時,我的思緒便開始在不同的畫麵之間跳躍。一方麵,“戰地日記”四個字,自帶一種肅穆和沉重的氣質。它讓我聯想到曆史課本上那些模糊的黑白照片,那些在異國他鄉英勇犧牲的戰士,他們用生命譜寫的悲壯詩篇。我猜測,這本書裏一定會有那些令人窒息的戰場描寫,會有對戰爭殘酷性的深刻揭露,也會有對人性在極端考驗下的展現。那些日記,是否記錄瞭戰場上的恐懼與勇氣?是否寫滿瞭對和平的渴望?是否包含著對死亡的思考?而另一方麵,“父親”這個詞,又帶來瞭溫暖與親切。它暗示著一種血脈的聯係,一種情感的羈絆。我開始構思,是不是有一個父親,在遙遠的戰場上,留下瞭他的日記,而他的孩子,在多年後,偶然發現瞭這些泛黃的紙頁,從而開啓瞭一段尋根之旅?或者,這位父親本身就是書中日記的主人,他以一個父親的身份,記錄著戰場上的經曆,並以此來教育他的後代?這種將宏大的戰爭敘事與個體細膩的情感描寫相結閤的設定,讓我覺得非常有吸引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視覺上的衝擊,精神上的震撼,以及情感上的共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