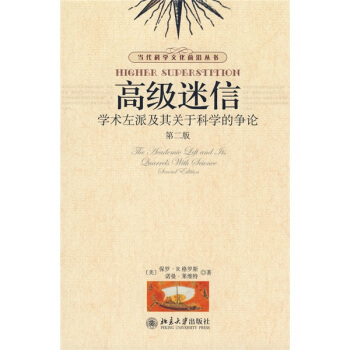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我们应对格罗斯与莱维特能给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深表感激。他们为那些在律师、记者和教师们耳边终日聒噪不休的思想家们所画的肖像,的确值得所有为科学之不景气现状而忧心忡忡的人们一阅。——《今日物理》
时至今日,终于有人挺身而出,把那些认为本世纪的每一重大科学进展都在腐蚀着西方思想传统根基的人们的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真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绩。
——《新政治家》
两位作者无情地撕开了众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大家们的荣誉面纱,这虽稍嫌有违与人为善之道,但其立论雄辩,时有振
内容简介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1994年初版以来,《高级迷信》一书一直是舆论界经久不衰且爱恨纠缠的焦点,引发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们广泛参与的“科学大战”。本书是首次将各种“科学批评”的视角与观点集结在_二起“示众”的宣传画廊。其中涉及许多严肃而又深刻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功能?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精髓是什么?科学专家的来源与合理性何在?……
作者简介
保罗·R.格罗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生物学家。诺曼·莱维特,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数学家。
目录
第一章 学术左派与科学学术左派
愤慨何由而来
褊狭性
必要的辨析
答辩状的设计
第二章 历史与政治因素考辨
——自然科学及其天敌
破迷与执迷
对美国左派历史的简要回顾
敌人的面目
第三章文化建构论的文化建构
弱形式的文化建构论
强形式的文化建构论——作为约定的科学
作为权力的科学
解释
作为权力斗争的科学
富豪统治者们
作为政治编码的文化建构论
第四章 瞎话王国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
文化批评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硬把科学当做隐喻
“理论”在政治上的诱惑性
哲学的复仇
文化研究:对理性的逃避
混沌理论简介
关于混沌的谬论1:史蒂文·贝斯特
关于混沌的谬论2:凯瑟琳·黑黎斯
第五章 应运而生的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的胜利
当今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代数学
单倍体的解释学
珍视卵细胞
关于性特征的舆论导向
整治物理学
科学与“科学研究”
“辩护”策略
论自然
无法逃避的语境
第六章 伊甸园之门
环境保护的现实方面
三种态度
理性的禁忌
“狼来了!”
公认的观点
瑞弗金的信条
一场未决胜负的战斗
第七章 控诉声何由而来
第八章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之事?
第九章 其干系何在?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学术左派与科学学术左派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所讨论的,是美国学术界一个庞大且极有影响的部分同自然科学之间那种令人异常困惑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这部分学界同仁在《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 》中被统称为“学术左派”(the academic left)。但这一称呼能否带来方便之利却颇值得怀疑。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学术左派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立场——这一“派”的分子毕竟是过于庞杂了,且内部纷争不断,因而很难达成统一的立场——但却有着明显一致的论调,这就是对科学毫不含糊的敌意。说得更坦率些,学术左派厌憎科学。自然,它不喜欢控制着我们社会的那些政治、经济势力强加给科学的某些功用,特别是在如下一些领域,如:军备,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监视,有害且导致环境恶化的工业加工,借助通俗文化技术对大众良知的操纵,等等。
这种对科学的厌憎情绪已广泛散布开来,就连科学家们自身的表现也和其他人一样,这样说估计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然而,在学术左派内部,对科学的敌意却无限扩展开来,矛头直接指向科学建制化得以维系的社会结构,指向职业科学家所赖以产生的教育系统,并且真真假假地指向科学家们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心理特征。最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人公然反对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反对那种被公认为所有受教育人士都会接受的普遍假设,即科学知识在理性上是可靠的,是建立在完善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正是这最后一种敌意,让意识到它的科学家们感到极为费解。因为这类论调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而目前包裹它的却是超现代语言(hypemodern language)。它似乎代表着一种对启蒙时代以来最强大的遗产的否定,似乎在嘲弄那种认为文明——就总体而言——能够从愚昧无知发展到富有洞见的进步观念,尽管学术左派的某些成员对科学的无知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每一次看到类似的观点,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非理性正在理直气壮地受到谄媚和宣扬。
前言/序言
《高级迷信》一书中译本要和读者见面了。作为译者,有三句关于本书的话要向其读者申明——首先,这是科学家阵营奋起对各种“科学批评”展开反批评的开山之作。
自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兴起后,尤其是随着国内学界所谓“广义STS研究”的发展及影响的深入,围绕科学事业而展开的各种研究进路逐渐向世人呈现出某种整体风貌,并汇聚成被国外学者称做“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统一战线”;其所给出的各色研究结论,在科学家看来,都属于“科学批评”(science-critique)之列。公允言之,科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呼应的正是人类欲全面理解科学事业的愿望与诉求:科学事业对人类发展及福祉的影响毕竟太重要了,只有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驾驭科学技术并使之为人类造福。所以,才会有众多学者挺身而出,从哲学角度解说科学何以可靠、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社会学角度解说科学事业应如何组织发展、如何评价激励,从心理学角度解说科学创新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从法学角度解说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应如何分配,从经济学角度解说应如何评价科技事业的投入与产出,从伦理学角度解说科技发展与价值观变迁间的关系,从文化角度解说两种文化之争、少数族群的权利、“科学霸权”的形成与影响……
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解说员”从身份上看大致都属于“非科学家”之列;即使偶有具备科学训练背景的学者,如卡尔纳普、库恩等,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主要是凭借其“科学批评”言论,而非通过其科学成就。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无疑是近年来政治思想领域里一股强劲的暗流,它以一种近乎考古学的严谨性,剖析了当代左翼思潮中那些常常被包装在光鲜理论外衣下的内核。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议题的细腻之处,那种不带预设的审视,如同透过老旧的显微镜观察细胞结构,将那些平时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微小裂痕一一展现出来。读完整本书,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被邀请进入了一个复杂的思想迷宫,而作者不仅提供了地图,还用火把照亮了那些故意被忽略的角落。他并不急于给出最终裁决,而是耐心地构建论证的脚手架,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些理论构建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尤其是关于知识产权和去中心化话语权的部分,作者的分析达到了惊人的深度,他没有停留在表面上的口号之争,而是深入挖掘了权力结构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中进行重组和伪装。这绝非一本轻松的读物,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理论准备和批判性思维的肌肉群,但回报是巨大的——你将获得一套全新的工具箱,用来拆解那些你以为已经完全理解的政治宣言。它挑战的不是具体政策,而是我们理解“真理”和“权威”的底层逻辑。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论证密度极高,读起来需要投入极大的心神,它就像一块结构复杂的矿石,需要用精确的锤子和凿子才能敲开其中最宝贵的部分。作者对于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剖析,达到了病理学的精确度,他似乎能精准地定位到那些“集体失忆”发生的关键节点。尤其在批判“进步主义的自我净化机制”这一章节中,作者的笔触锐利而冷静,他展示了当一个运动开始将内部的异议视为比外部的压迫更具威胁时,其内部结构会发生怎样不可逆转的僵化。这让我联想到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即便是最崇高的理想,也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异化为对异见的无情清算。这本书的深度不在于它提出了多么惊世骇俗的新口号,而在于它以一种几乎是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切开了当代政治话语的冗余脂肪,直抵其功能失调的器官。对于严肃的政治思考者而言,这是一次必要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清醒剂。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有一种奇特的、近乎催眠的魔力,它不是那种让你一口气读完的畅销小说,而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复研读的哲学论文集,但其散发出的洞察力却又具有散文般的美感。我尤其被其中对“进步主义的停滞感”的描绘所触动。作者似乎拥有某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视角,他能捕捉到一种集体性的焦虑——那种不断宣称自己在向前疾驰,却发现自己始终困在原地,或者更糟,在原地打转的无力感。语言的运用上,作者仿佛在雕刻微型雕塑,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承载了沉甸甸的重量,避免了任何浮夸的修辞,这使得核心论点得以穿透重重迷雾直达核心。我发现自己常常需要停下来,合上书本,去回味某一句措辞的精准性,思考它在更广阔的语境下可能产生的引申含义。对于那些长期关注社会运动演变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照组:我们所倡导的“解放”究竟是迈向自由,还是正在构建一套更隐蔽、更难以察觉的新型枷锁?这种内省的力度,是许多同类主题书籍所欠缺的。
评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祛魅”的体验,它将那些被神圣化、被奉为圭臬的社会理论,还原为一系列由特定历史和权力关系所塑造的行动方案。它没有采取那种粗暴的“全盘否定”姿态,而是以一种近乎仁慈的姿态去解剖这些思想体系的起源和演变路径。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处理“身份政治”与“阶级分析”的交汇点时所展现出的平衡感。他没有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试图揭示在当代语境下,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相互消耗,最终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标。这种精妙的辨析,让我对过去几年里许多热点事件的解读逻辑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感到一种认知上的“震颤”,那是旧有信念框架受到冲击时的必然反应。这本书的排版和引文处理也十分考究,体现了出版方对学术质量的尊重,让阅读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对知识严肃性的尊重。
评分整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合理性”的辩证体系,探讨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何种声音被赋予了“科学”的合法性标签,而何种声音则被迅速降格为“非理性”或“迷信”。作者的叙述风格中流淌着一种古典的人文主义关怀,他关心的不是谁对谁错的简单站队,而是人类心智在面对复杂现实时,如何倾向于构建那些既能提供慰藉又能限制视野的叙事框架。对我而言,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捍卫科学”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行为。它迫使读者去反思:当我们高举“理性”的大旗时,我们是否无意中竖立起了一道新的、同样难以逾越的墙?这种对自身立场进行持续反思的勇气和能力,是这本书给予读者的最大馈赠。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更高阶的提问方式,这种体验是任何肤浅的政治评论都无法比拟的。
评分人之所以会对某些事物昧于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许正是他所处其中的特定社会、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愚昧才会永存。(换言之,有些愚昧是故意的?)
评分这一派别主要由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组成,他们对文化问题表示热切的关注,尤其是根本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并认为实现这种变革的**过程只能植根于文化领域的全面革新。
评分先帝创建基业还不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三国之势,我们益州地区人力疲惫,民生凋敝,这的确是形势危急决定存亡的关键时刻啊。但是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稍有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地作战。这是因为追念先帝对大家的特殊恩遇,想要报答在陛下身上啊。陛下确实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发扬扩大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话不恰当,以至于堵塞了忠臣上谏的言路。 皇宫中的近臣和朝廷中的官吏,本来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因为在宫中或在府中而异。如果有做奸邪事情犯科条法令,或是尽忠心做善事的人,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不应该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啊。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志向思虑忠贞纯正的人,因此先帝才选拔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拿来问问他们,然后再去施行。一定能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增加成效。 将军向宠,性情德行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的时候,先帝称赞他说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如果都能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能力强的和能力弱的都能各得其所。 亲近贤良的忠臣,远离奸佞(nìng)的小人,这是汉朝前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汉朝后期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的做法,常常感觉到痛心和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评分科学卫士保卫科学力作
评分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印刷也很好
评分人之所以会对某些事物昧于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许正是他所处其中的特定社会、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愚昧才会永存。(换言之,有些愚昧是故意的?)
评分慢慢看………
评分写的是“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之间的争吵。
评分随着科学的发展,进军宗教的老巢不远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来吧,我们一起发现高山 [7-10岁] [Komm mit ,Wir entdecken die Berg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66705/c9737493-7b37-45bd-a8e3-3775b72242f2.jpg)
![什么是什么:鹦鹉王国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346818/0bf74575-d4bd-4168-b6f5-933db06ef0b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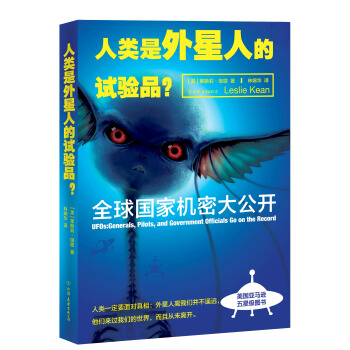
![第一次发现丛书·手电筒系列小百科:小动物有什么大本领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94083/53f297bcN228a6095.jpg)
![美国国家地理 它们是这样工作的系列 机械小常识 [4-7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59602/569890b7N5dac111c.jpg)
![拉鲁斯儿童立体百科全书:伟大发明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76332/56f0ea98N127e3792.jpg)
![我们去找小昆虫(全套共5册) [3-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96657/56f39c12N90656a79.jpg)
![洗澡水去哪儿了?/万万没想到·德国经典儿童科普翻翻书 [3-5岁] [Wohin flieβt das Badewass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29804/57d765acN1fab0ed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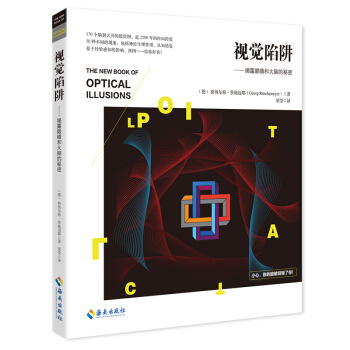
![无尽的追问(插图珍藏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19018/e552adf4-324e-49e4-8e6f-fdf11433111a.jpg)
![来吧,我们一起造房子 [7-10岁] [Komm mit,Wir bauen ein Hau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66704/97f26557-0c42-4927-98e2-71b69e994cb4.jpg)
![恐龙世界大百科(彩图版 套装共3册)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605029/53f5c938Nf52be0e3.jpg)
![青少年读图百科·古代兵器(我的第1套人文百科)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04540/rBEQWVFiHvkIAAAAAA7GGkVGhP4AADm_QIU-kwADsYy094.jpg)
![大嚼科学:人体卷·一个人的里子和面子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84570/547d2cddN5236fe01.jpg)
![少儿必读经典 成语接龙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2459/55b1e67eN3a2d2321.jpg)
![美绘注音版十万个为什么:动物植物+科技生活文化+人体饮食健康+天文地理环境(套装共4册) [6-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50346/55d13c72N5d8082cd.jpg)
![你绝对想不到(套装共8册) [3-6岁儿童] [First Fabulous Fac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72804/561f2331Ne50b67c5.jpg)
![美国国家地理 它们是这样工作的系列:汽车小常识 [4-7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59596/569859dfN32de792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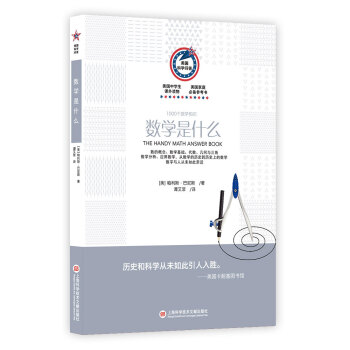
![看里面第六辑:揭秘名宫殿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96495/58be7523N95ccc6d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