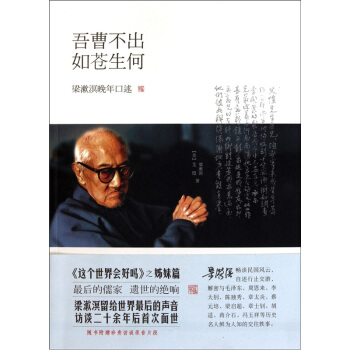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会好吗》之姐妹篇,梁漱溟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访谈二十余年后首次面世!梁漱溟先生畅谈民国风云,自述行止交游,解密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蒋介石、冯玉祥等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交往轶事。
内容简介
《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梁漱溟老先生晚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的对话实录,也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梁漱溟老先生畅叙平生,艾恺教授如实纪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作者简介
梁漱溟老先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東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这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粱老畅叙平生,艾兄如实记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谨此推荐,读者不可错过。”
——汪荣祖
“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实际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孔门之学,返躬修己之学也。”
——许章润
目录
“演戏也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事儿”我做司法总长机要秘书的时候
谈佛论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后后
总角之交:与张申府为友的七十余年
“延安欢迎我去”:跟毛主席正式见面
少年意气:参加同盟会地下工作
他不是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尽心尽力的人
我眼中的章士钊
与毛主席的阶级观辩论
亲历“五四”:“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
结识梁启超:“我们父子都崇拜梁任公”
“别忘了你是陶行知的学生”
李大钊是个看似温和实则激烈的人
同盟会往事:刺杀良弼、袁世凯
退居桂林:民主同盟成立前后
东北之行:高岗印象
心不离乎其身而有创造:卫西琴的教育实践
北游所见:与阎锡山的结识和交往
回忆毛主席的中医岳大夫
哲学家轶事:章太炎、贺麟、金岳霖琐忆
民主同盟对和平的贡献
毛主席建议我参观、比较新老解放区
骄兵必败:蒋介石逼人太甚
访日随感:日本的乡村工作和日本人的宗教观
乡村建设与县政实验
途经四川:主张改良征兵制
香港夹缝中:办《光明报》的曲折经历
从香港到桂林;战时杂忆
话邹平“朝话”
精彩书摘
艾(下略):您当时对京戏也很感兴趣吧?呵呵,我知道,您说北京人都喜欢。梁(下略):我那时候啊,我这个人哪,——北京话叫做“别扭”。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爱听戏。我就说你们爱听戏,我偏不听戏,呵呵。那年说这话的时候也都有20岁。后来到24岁那年,从前叫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的政局有个新局面。怎么说有个新局面呢?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成,之所以没做成的缘故是西南反对他。西南——在云南不是有一位将军叫蔡锷,有唐继尧,有广西的陆荣廷,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的部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原来国家的制度改了。国家的制度原来在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国务院有国务总理。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了,不要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个政事堂,他就是总揽大权在总统,不愿意另外要什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在袁世凯政府里头,他也不是国务总理,他是陆军总长,实际上军事大权由他掌着。所以旁人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却公开地反对。
公开反对反对不了,大伙儿还是都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就辞职——我不做官了——他不做陆军总长了,他退隐了,北京有西山,退隐到西山 上,闲住起来。他自己称病,辞职啊,辞那个陆军总长,就说我有病。袁世凯也无可奈何,他一定要辞职,要不干,也无可奈何。这样对他们北洋军人倒留下了一个生机,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是总统,副总统是黎元洪。按照宪法,应当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该是黎元洪出来了。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来了,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就把原来袁世凯的政事堂那套东西废除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恢复了国务院。这时候南方反袁的觉得他们这样做合法,合乎原来的民国宪法,就承认他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一方面有北方的,另一方面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统一内阁。这个时候按旧的说法叫民国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出人来参加北京的南北统一内阁,参加的人是云南的,西南方面的,是云南的张耀曾,他刚好是我母亲的一个弟弟,不是亲弟弟,一家的弟弟,我管他叫锫舅,他的号叫张镕西。他就出来担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他平素就喜欢我,叫我给他当秘书。
他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了吗?
他从云南来呀。
从云南来的,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凯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做法学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学法学的,反袁的时候就到云南去了。他本来是云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也是在您家……
是我们家的亲戚啊,我母亲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在去云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来往吗?
当然。
您当时对佛教是最感兴趣的,那张先生呢?
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跟他的亲戚关系,北京说法叫外甥。他岁数大过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岁。那年他做司法总长,我24,他33,也很年轻。
很年轻啊,做部长,当然年轻的。
他就让我给他当秘书。为什么要我给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代表西南反袁的势力来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面的主要人物通密电。他让我掌握密码电本儿。去电哪,来电哪,去信哪,来信哪,我都管这事儿。
所以他请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这种工作绝对不要别人知道的,您是他的亲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学问有关系,主要是您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沈钧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四个秘书中的一个。
哦,一共有四个秘书。
他是司法总长啊,有四个秘书。沈老师一个,我是一个,还有一位姓习,另一位姓杨,姓习的、姓杨的都是云南人,沈老是浙江人。四个秘书分担不同的任务,云南人姓习的、姓杨的管公事,他们管来往公文’,来的公文他们看,他们加意见,发出去的公文也归他们管。我专管机密的,呵呵,写点儿私人的来往信件。我把信写好,给镕舅看,末了他签个名,翻有密码的电报给他看。这年我24岁,沈老42岁,大我18岁。
这个时候的政局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必须要点明。过去主要是一左一右两党,左边就是以孙中山先生、黄兴、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是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是偏“左”一边的。偏右一边的叫进步党,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还有林长民等其他人。本来是这么一左一右两大党。前一段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后一段是他死了,大家反对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气死了。现在一切嘛都恢复,按照宪法啊,原来的宪法都恢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把段祺瑞找出来恢复国务院,请段做国务总理,这是民国六年(1917年)。
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的反袁势力参加了南北统一内阁。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四个秘书——我主要的给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沈老呢,是对外的事儿。所以对外——刚才不是提过了,一个国民党,一个进步党。大家都不讲这个,制定宪法的任务给耽误了,大家一定要抛除了党见,要制宪第一,把宪法搞住,因为是制宪第一。议员合起来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没有组织,各自组合起来,有的叫宪法研究会,有的叫宪法讨论会,有的叫宪法商榷会,都是研究宪法的。有名的是宪法研究会,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梁为首。后来口头上、报纸上常说谁谁是“研究系”,就是说他是宪法研究会那一派的人。
可是两院议员有八百多,有些没有收纳到这里面去,有的就叫“丙辰俱乐部”。为什么叫丙辰俱乐部呢?因为这一年是丙辰年。我们广东有个留学德国的,叫马君武,是丙辰俱乐部的头脑。还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褚辅成,他们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别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组织,这个时候,张耀曾跟他的云南同乡李根源,还有一位国民党老资格的叫钮永建、谷钟秀,他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政学会”。我们四个秘书中的沈钧儒代表张耀曾忙着招呼政学会的事儿,沈老人身体不高,头很大,留胡子。
……
前言/序言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访谈之后所作的第二次访问的内容。第一次的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这第二次的内容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且让我以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为例,来稍作解释。大体来说,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斯塔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人士,也是一位记者。凭着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rnerca,他在美国及世界的意识中留名(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狂销数百万册,同时也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Hard Times,该书与前书属同一类型,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由录音带所录制的对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在前一集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组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除了刺激他的记忆以及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以外,我无其他的想法。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所设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
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中国甚至全世界,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总被归类为“保守派”,无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贬为已被“扫人历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现今无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对于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准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得经过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较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访谈中,我无意将内容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人档收藏,这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一一仔细听过,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
从某一角度来讲,这些访谈代表着立传人和传主间一次偶然性的相会。说是偶然,实因背后许多因素在某一时间点上交会,促成了此一会面。第一项因素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与世界接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梁先生。第二项因素便是传记的出版及成功。当我和梁先生晤面时,该传记已赢得亚洲史主要奖励。由于该书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闻,并很快地间接联络我,告诉我欢迎我往访。第三项因素则是梁先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情况较佳。甚至在1984年,当时他已逾90高龄,我仍觉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于1980年访问梁漱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心里一直认为首次的访谈资料即为珍贵的历史文件。当我愈往这方面思考,愈觉得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读者若从梁漱溟似乎总是身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虚。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事实上,当年义和团人京时曾立即给梁漱溟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当时正在一所西式学校就学,该学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诒孙先生经营,彭先生也是梁漱溟与我的访谈内容里提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学校有西式课程(如英语和科学),义和团焚毁了学校,梁漱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为了不让漱溟有机会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将他的课本全数烧毁。就在此事发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义式的学生运动——抵制美国货。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内容包括从事一些“子弹和炸弹行动”。一年后,他担任记者,并在南京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又过了两年,他和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接触,直至他全心全意修习唯识宗佛学为止,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书,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军事人物有所接触,如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韩复榘等人。他甚至与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士结为好友,包括了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续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倾注关心,他结交了几乎所有的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如黄炎培和晏阳初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去了延安并且与毛泽东对谈。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即日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他于此过程中创办了《光明报》。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而来的国共和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串他认识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单以及他所亲身参与的事件可以一直写下去,但是我感觉这已足够证明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我因此决定于1984年继续访问他。
作为(在当时)梁漱溟唯一的传记作者,我很幸运能将访谈内容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呈现。我感觉有某种急迫的原因使我从这方面着手。当时梁老已逾90高龄,一身体状况就如同所谓“风中之烛”般,因此,我尽可能快地回去见梁老,以便展开第二次访谈的录音工作。如同首次,访谈地点在梁先生住处,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时间几小时,共进行一个多星期,访谈过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记忆极为清楚。
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所称,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甚至捏造回答。这些访谈录音有个小问题,当中有部分内容与1980年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重复。再说,由于我向梁老请教许多历史人物,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些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他大概以为我是外国人,故有必要作解说。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些历史背景解释确实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并支持梁先生个人的历史观点。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所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是惭愧)。
本次访谈的地点与首次访谈一样,在梁先生住处的小房间内进行,地址是木樨地22号宅。必须特别注明的是,这些录音的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至于我那时为何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颇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原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组成部分建立于1972年,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问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领域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将我们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不是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直接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整体而言,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我在此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以及吴浩先生的努力,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用户评价
我拿到《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最大的惊喜便是它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一直令人称道,而晚年口述,更能让我们窥见他思想脉络的晚期沉淀。书中的叙述,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审视和对历史的反思,他将自己置身于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革之中,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去审视那些他曾参与、曾为之奋斗的时代浪潮。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他不同人生阶段,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关系的阐述感到好奇。他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如何与现代思想碰撞融合?他晚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解读,是否有所突破?书中“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更是点睛之笔,它所隐含的对后辈的期许,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一种“责任在肩”的担当,都让我肃然起敬。这本书不仅仅是了解梁漱溟先生本人,更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的一把钥匙。
评分我听闻《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便心生向往。梁漱溟先生,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人生,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分量。晚年口述,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将一生的智慧与经验,以最直接、最坦诚的方式传递给后人。我非常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触摸到梁先生晚年的心境,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如何理解人生的终极意义。书名中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句简短的话语,却蕴含着无比的责任感和对“苍生”的深切关怀。我很好奇,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的?是带着一丝无奈,还是一种对后辈的鞭策?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梁先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关系的思考,以及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位智者留下的宝贵遗产,一份关于如何安顿自己、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爱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深邃教诲。
评分“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这本书,光是书名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对时代、对苍生的深切关怀。我最近刚好有幸接触到这本书,虽然尚未完全细读,但从零星翻阅和一些旁观者的分享中,我已经被深深吸引。梁漱溟先生,这位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晚年口述,无疑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深处,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窗口。我尤其期待那些关于他晚年心境的描绘,在经历了一生的跌宕起伏后,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如何评价那个他曾深情投身的中国,又怀揣着怎样的期盼去审视那些他认为“苍生”的未来。书中那个“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题目,本身就饱含了一种悲壮与责任感,仿佛是他在对后辈,对这个时代发出最后的叩问。我很好奇,他究竟是以怎样的口吻,带着怎样的情感,道出这些话语的?是慨然长叹,还是深沉的期许?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更可能是一份沉甸甸的临终嘱托,一份关于人生、关于中国未来的哲学思考。这本书的出现,填补了我对这位思想巨擘晚年生活与思想的空白,让我能从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角度去理解梁漱溟其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评分对于《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我能想象到的,是其中蕴含的磅礴大气与深沉情感。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思想,也如同滚滚长江,奔腾不息,最终汇入晚年的静水流深。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他如何回首往事,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选择,又如何看待那个他为之倾尽一生的中国。他早年的社会改造实践,他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周旋,他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历史素材。而晚年口述,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洗尽铅华后的坦诚与智慧。我尤其好奇,他对于“苍生”的理解,对于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怀,在晚年会以怎样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慈悲的姿态呈现出来。书名中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仿佛是一种对未来的告诫,一种对责任的提醒,又或许是一种对后继者的殷切期盼。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立体的梁漱溟,一个在历史洪流中,依然保持着清醒头脑和人文关怀的老人。
评分最近读完《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是那种被一位老人用一生智慧和悲悯所浸润的震撼。这本书的体量不小,但读起来却丝毫没有枯燥之感,仿佛梁先生就坐在你对面,娓娓道来,声音里带着岁月的沧桑,却又充满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我特别喜欢书里关于他晚年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梳理,那种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深刻体悟,以及对当下时代所面临挑战的独到见解,都让我耳目一新。他不是空泛地谈论哲学,而是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具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变迁之中,让那些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而鲜活。书中关于“人生问题”的探讨,更是直击人心,那种不回避痛苦、不逃避现实的勇气,以及在苦难中寻求解脱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晚年对“真”与“善”的反复追问,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梁先生身上那种“士”的风骨,那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以及那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即使在晚年,他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这种精神力量,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来得更为动人。
评分邓小平传(1904-1974)(套装上下册)
评分书写的不错,值得收藏
评分一个执着的倔老头,不过采访者过于考虑大众的口味了
评分大师的经典
评分最后的儒家,遗世的绝响。不错
评分《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梁漱溟老先生晚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的对话实录,也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梁漱溟老先生畅叙平生,艾恺教授如实纪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
评分速度快,收到非常满意非常喜欢
评分原来不太了解梁大师,先买了一本《这个世界会好吗》,看了以后觉得不错,就多买几本认真拜读。
评分经典书籍值得收藏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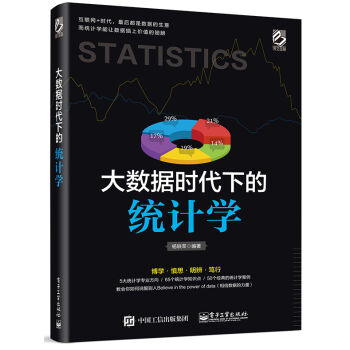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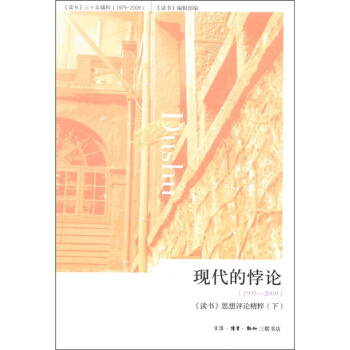

![邓云乡集:云乡丛稿 [邓云乡集]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3794/5577ec29N920b58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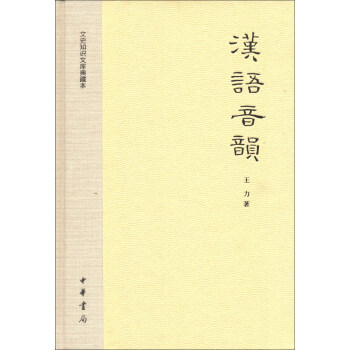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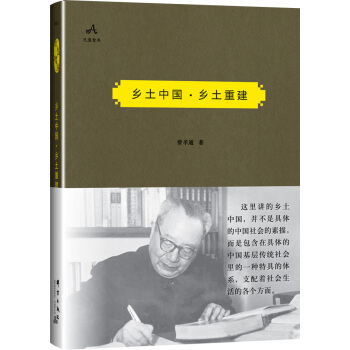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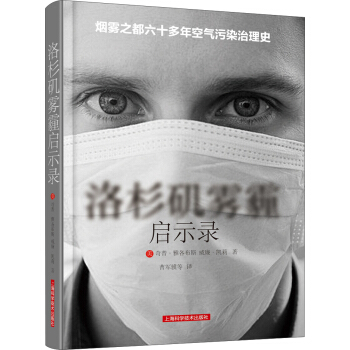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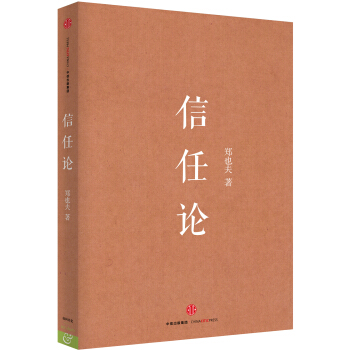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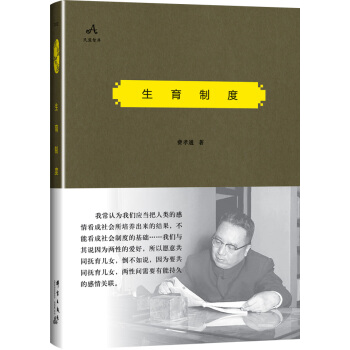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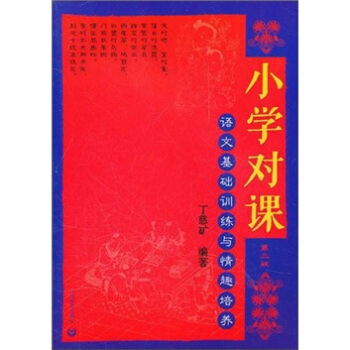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方法论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wleh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73991/b348b328-8fb2-49e8-a2f4-6cfc38f5e92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