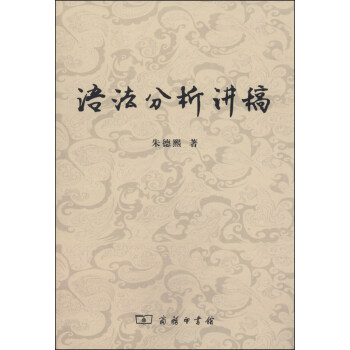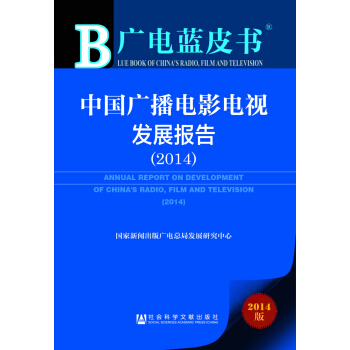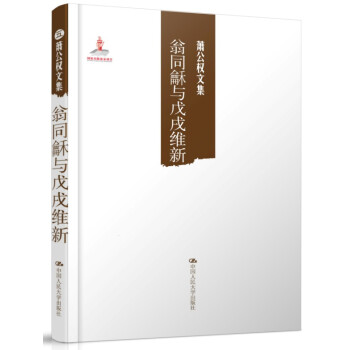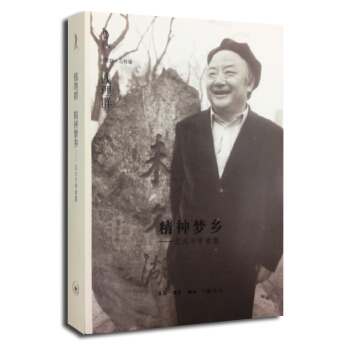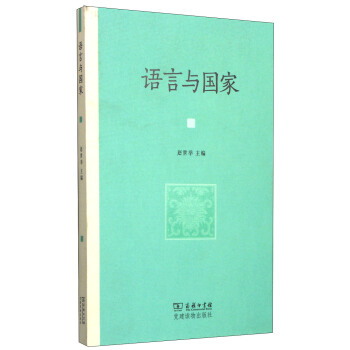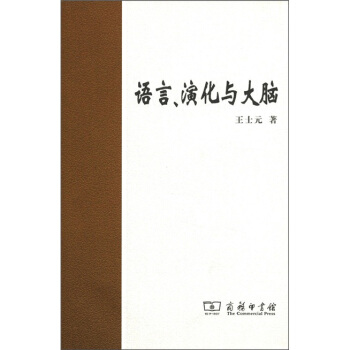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语言、演化与大脑》为《语言学论丛》的专辑。《语言、演化与大脑》是王士元教授在北京大学“语言与大脑”系列讲座整理而成。《语言、演化与大脑》从达尔文的演化论开始讲起,从灵长类到智人,从语言的演化到词汇的演化,从黑猩猩的语言到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从语言学的发展到儿童的语言习得,从研究大脑的几种方法到声调与大脑、类别、音乐的关系……王士元教授带您走入语言和大脑神秘关系之旅。目录
第一讲1.1 演化论的开端:达尔文与Wallace
1.2 从灵长类到智人
1.3 语言的演化:纵向及横向的传递
1.4 词汇的演化
1.5 大脑与语言:早期研究
1.6 两个失语症的例子
1.7 大脑与语言:Geschwind的综合理论
1.8 问答
第二讲
2.1 动物的分类、行为及沟通
2.2 黑猩猩与语言
2.3 教黑猩猩语言
2.4 鸟鸣与关键年龄
2.5 演化与遗传
2.6 人类起源于非洲
2.7 大脑与神经元
第三讲
3.1 语言学的宏观视野
3.2 语言学的发展
3.3 儿童的语言习得
3.4 母语、外语与关键年龄
3.5 Sapir、Whorf与语言相对论
第四讲
4.1 研究大脑的几种方法
4.2 MRI与语言习得
4.3 大脑与英语语法
4.4 构词的多样性
4.5 声调与大脑
4.6 声调与类别
4.7 声调与音乐
4.8 语言塑造大脑
参考文献
英汉词汇对照表
彩图
图片版权页
精彩书摘
最近的一二十年,很多实验室拿Y chromosome(染色体)来画人的树图,因为它是uniparental(单亲遗传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个细胞里面,有它的核,核的外头,还有一点DNA,很少。这个外头的DNA,叫做mtDNA,mitochondrial DNA(粒线体DNA)。mitochondrialDNA完全是母系的,是只由母亲传下来的,Y chromosome是父亲传给儿子的。所以有很多实验室专门研究母系的mitochondrial DNA,也画出一些树来,那么父系的树、母系的树基本是相同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有些图常把DNA画得很漂亮,但不是真的长那个样子的。一个基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所以一个基因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alleles(等位基因,对偶基因)。比方有基因是管头发颜色的,在这个基因里头,有的alleles会让人有黄头发,有的alleles会让人有红头发。同一个基因,有不同的基因表现(gene expression)。基因有一点像语言里面,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词。比方H2 0(水)这个概念,英语叫做water,俄语叫做voda,日语叫做mizu,我们叫“水”,西班牙语叫agua。当然英语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变化,本来水是akua,比方我们现在养鱼的那种缸叫aquarium,就有akua这个字根,就是“水”,到西班牙语里就变成了agua。有的语言从一开始是akua,有时候就变成agua;有的时候k跟g都不见了,就变成了awa;再有的时候整个东西都简化了,就变成o这个音。法语的“水”就是eau/o/,就是由akua来的。所以一个基因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言里,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论证过程极其审慎和严谨,它没有急于给出一个“万能钥匙”式的结论,而是耐心地展示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论辩和证据的局限性。对于那些习惯了简单答案的读者来说,初读可能会感到一丝挑战,因为它要求你对理论的细微差别保持高度的敏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对待“文化传输”与“生物预设”之间关系的平衡处理。他没有简单地偏向于任何一方,而是展示了两者如何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语言多样性。书中对一些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特别是关于“社会互动在语言形成中的作用”的论述,提供了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语言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社会粘合剂的观点,被大量生动的社会人类学案例所支撑。这种对复杂性的尊重和对证据的平衡引用,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证据中构建最合理的解释模型。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结构简直是一场智力的探险,作者仿佛带着我们穿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追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能力——语言的起源。开篇的几章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用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案例,比如对不同物种认知能力和交流方式的细致描摹,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背景。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什么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解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充满张力的动态系统。书中对早期人类社会结构和工具制造的讨论,虽然看似与语言本身有些距离,但却精准地揭示了环境压力如何塑造了交流的复杂性需求。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关于“窗口期”和“关键适应性”的论述,它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人类能发展出如此精密的符号系统,而其他物种却停留在更基础的信号传递层面。作者的文笔流畅,充满了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激情,让人感觉这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抽丝剥茧地揭示自然界中最深刻的谜题之一。那种读完后豁然开朗、对日常对话产生敬畏的感觉,是许多同类书籍难以给予的深度体验。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关于“人类独特性”的哲学思辨。作者的笔触中流露出的对人类心智的深切关怀,使得那些原本冰冷的科学论述充满了人文的光辉。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内在语言”与“外在表达”之间张力的探讨。它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用以思考的那个“无声的语言”,与我们用来交流的“有声的语言”,究竟是同一回事吗?作者巧妙地引入了音乐、视觉艺术等其他形式的符号系统进行类比,成功地拓宽了讨论的边界,让读者跳出语言学的狭隘视野。这种拓展性思维,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符号世界。它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说话”,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终极追问。每一次阅读,似乎都在揭示人类心智结构中那些不易察觉的精妙构造,让人对自身的存在感到既新奇又谦卑。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充满了迷人的节奏感和文学色彩,即便是处理最晦涩的理论,也能保持一种近乎诗意的叙述张力。它没有采用那种教科书式的僵硬结构,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着读者在不同的知识领域间游走,总能在恰当的时机引入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来巩固复杂的概念。我发现,这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亮点在于其对时间尺度的灵活切换,时而聚焦于百万年前的模糊回声,时而又立刻拉回到现代社会某个特定的语言现象分析,这种时空的跳跃处理得非常自然,有效地避免了单一时间线上叙事的枯燥。我个人觉得,最能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在于他如何将那些看似无关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对早期部落迁徙的影响、或者特定群体间的贸易往来——巧妙地编织进语言演化的叙事线索中,使得最终的图景异常的宏大和完整。读完之后,留下的不是一堆孤立的知识点,而是一个完整、相互关联的认知生态系统。
评分这本书对认知科学前沿的把握极其敏锐,简直像是一份精心策划的学术盛宴,每道“菜肴”都充满了令人回味的复杂风味。它没有满足于停留在宏观的演化理论层面,而是深入到了神经回路和基因调控的微观细节。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语法是如何在神经元层面编码”的章节,作者似乎掌握了最新的实验数据,将抽象的语法规则与大脑中特定皮层区域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跨学科的整合能力令人叹服。特别是对某些特定语言障碍患者案例的分析,简直是天才之举,它们如同自然界的“对照实验”,清晰地指出了哪些认知模块是语言能力不可或缺的基础。读到这些部分时,我感觉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前沿的脑科学实验,那些复杂的术语和模型,在作者的阐释下变得清晰而富有逻辑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敢于直面那些最难回答的问题,并且提供了基于实证的、虽然仍在发展中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让读者能够跟上科学探索最前沿的步伐。
评分就像梁漱溟,记忆中早就有这个名字,角角落落的八卦也知道的不少,但真正静下心来读他的东西,还是从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开始。
评分书的内容不多,但理论性十足。
评分对语言学、脑科学等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评分非常好的书,送货及时,好看
评分书品很好,值得一读。
评分讲座的讲稿,关于语言演化方面的书
评分书的定价有些高。但书的内容还不错。关注生物语言学的亲可以读一读。
评分对语言学、脑科学等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评分一直思慕前朝旧事。那段文韬武略怪人辈出的时空,名字太多,故事太多,总腾不出心境好好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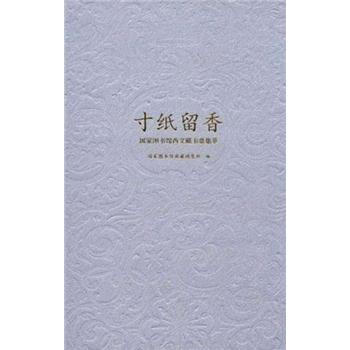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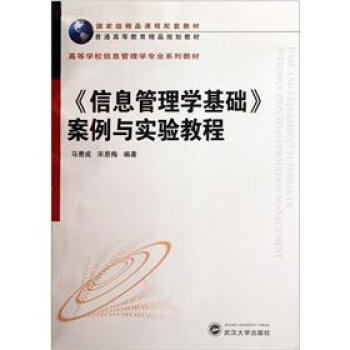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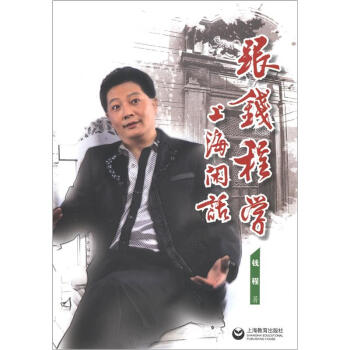
![应用统计学丛书·结构方程模型:Mplus与应用(英文版)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pplications Using Mplu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80754/565524ffN8a855c5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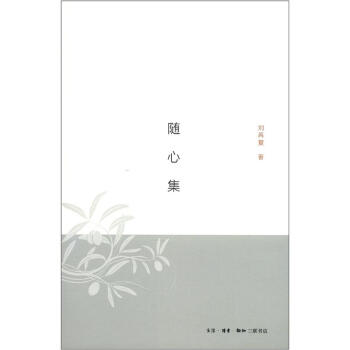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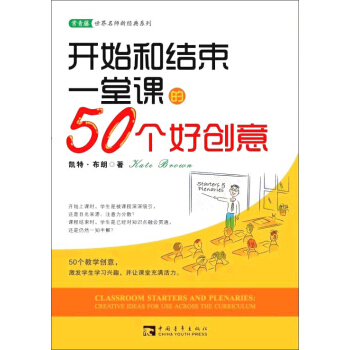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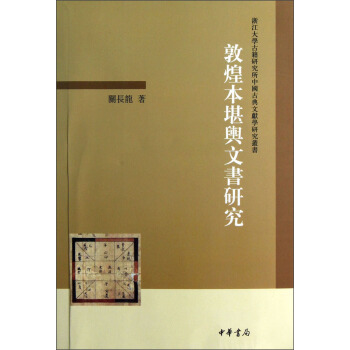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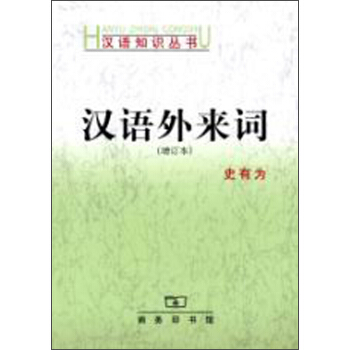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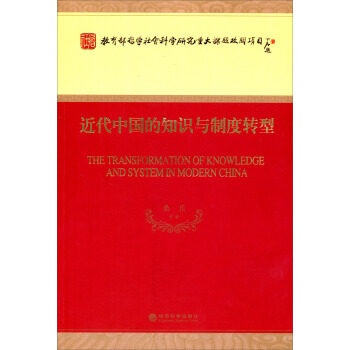
![电视新闻:摄像(第2版) [Television Journalistic Photograph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45275/rBEQYVGodFwIAAAAAAIcNG68QHIAACdjQHaF30AAhxM41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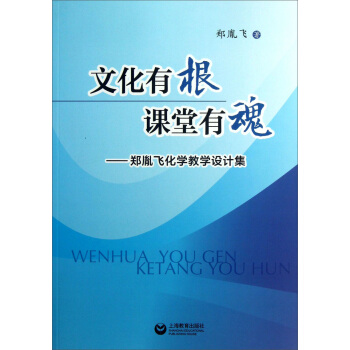
![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Third Media Age:Immersive Communic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27367/rBEhVFJWoJoIAAAAAAFVHiS45PAAAD_PQNiwUMAAVU2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