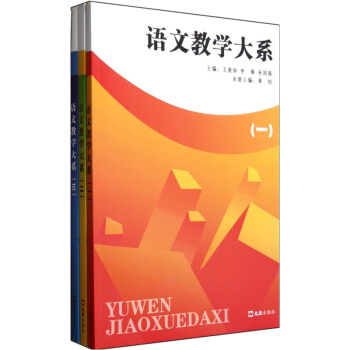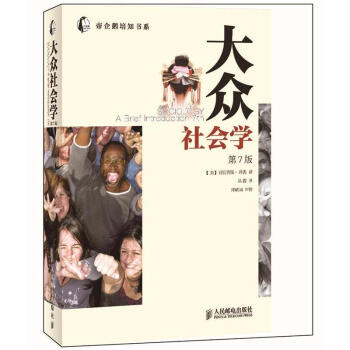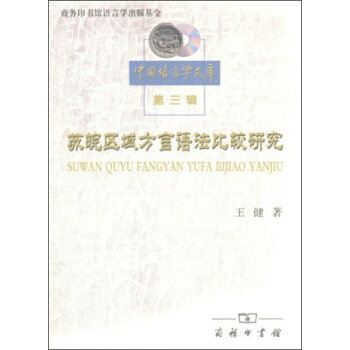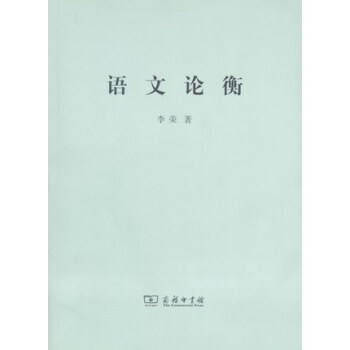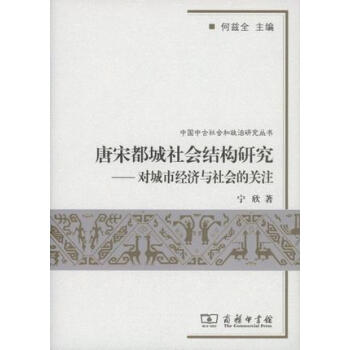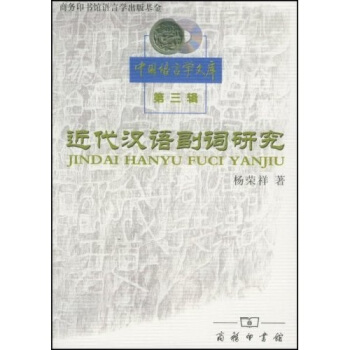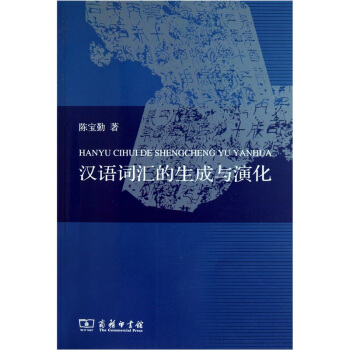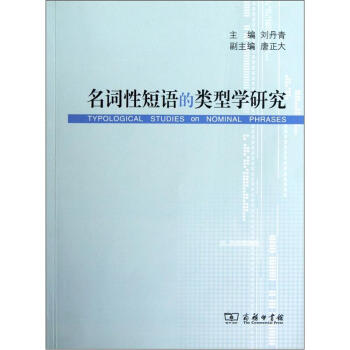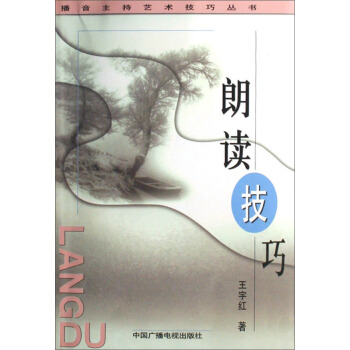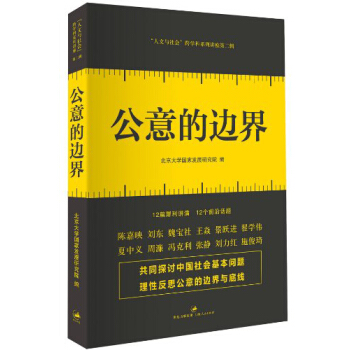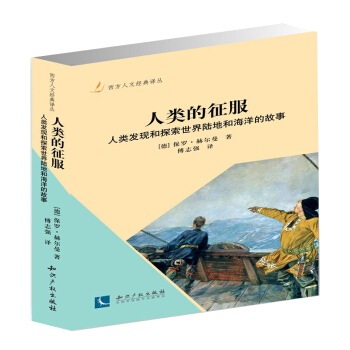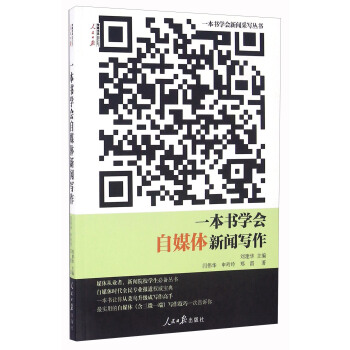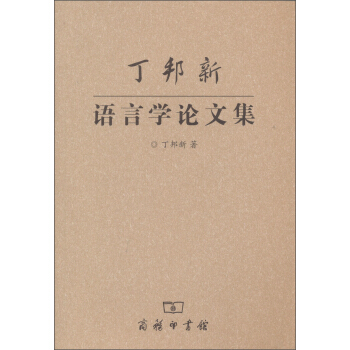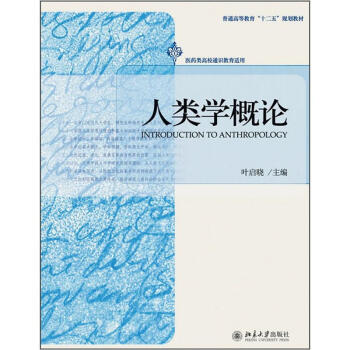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從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人類的起源與進化、人類的種族及其分布、文化與文化人類學基本理論、文化的外顯基本結構、人類的物質文化及其形態、人類製度文化的形態與演進、人類精神文化的形態與特徵、人類文明、走嚮全球化的人類社會、全球化條件下的人類學趨勢等方麵,係統講述瞭人類學的基本知識,非常適閤非社會學專業的文理科大學本科生閱讀。書稿中附有大量生動、形象的影響和圖錶資料,將放在課件中供師生下載與閱讀。目錄
導言第一章 人類學總論
第一節 人類學的概念及其理解
第二節 人類學的學科簡史
第三節 人類學的學科領域和學科關係
第二章 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第一節 人類依存的宏觀環境背景
第二節 人類齣現前的生物學曆程---生命起源與生物演化
第三節 生物體質演化與生物分類
第四節 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第三章 人類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靈長類的起源、分類與體質進化
第二節 人科的起源與"人"的特徵
第三節 人類的進化與發展
第四節 現代人的體質進化特徵和現代人的起源
第四章 人類的種族及其分布
第一節 人種的概念及其劃分
第二節 各人種體質特徵的主要差彆
第三節 人種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第四節 種族主義
第五節 世界人種分布和中國居民的人種特徵
第五章 人類學的人口研究
第一節 人口思想簡史
第二節 人口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
第三節 人口過程、人口結構和人口質量
第六章 文化人類學基本理論
第一節 什麼是"文化"
第二節 文化人類學的主要流派
第三節 文化的基本結構---馬文?哈裏斯模型
第四節 文化的基本錶現形態與要素分析
第七章 人類物質文化的形態與劃分
第一節 物質文化的概念
第二節 物質文化的研究內容
第三節 物質文化的基本形態與特徵
第八章 人類製度文化的形態與演進
第一節 製度文化的基本內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節 婚姻與婚姻製度
第三節 傢庭
第四節 從繼嗣、傢族到氏族、部落
第五節 人類社會的政治體製和政治製度
第六節 社會控製原理和主要方式
第九章 人類精神文化的形態和特徵
第一節 精神文化的形態屬性和基本內容
第二節 精神文化的功能與作用
第三節 科學形態中的精神文化
第四節 人文形態中的精神文化
第五節 宗教與文化
第六節 語言與文化
第十章 人類文明及其起源
第一節 人類文明的概念
第二節 世界文明的發祥
第三節 中華文明的起源
第十一章 走嚮全球化的人類社會
第一節 何謂全球化
第二節 全球化的曆史進程
第三節 當今全球化的動因
第四節 正確認識全球化
第十二章 全球化條件下的人類學趨勢
第一節 生命科學發展與人類體質演化趨勢
第二節 生存環境變化與人類物種危機
第三節 人類社會的未來窺望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3.進化論思想與神教思想的辯爭 隨著樸素唯物主義認識和科學思想的不斷發展,根深蒂固的神教思想與科學思想的交鋒和辯爭愈演愈烈。在人類學即將成為一門科學的前夜,唯物與唯心、科學與神教的抗爭,成為科學界和神學界乃至社會民眾普遍關注的時代主題。在這場激烈的抗爭中,先哲們付齣瞭巨大的代價,甚至為此殉及生命。當時,像大阿爾博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這樣一些走在時代前麵的思想傢,在剛剛感到科學思維引導他們走嚮背離神教思想的時候,便立即從自己的立場上縮瞭迴去,並慌忙宣布“還是基督教義可靠”。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與腐朽的封建統治同流閤汙,形成頑固的黑暗勢力,他們對所有進行科學探索的人,對追求科學真理而違背神學教義的人一律進行打擊和迫害,先賢們因倡導科學真理而被宗教勢力迫害的事例屢屢發生。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是企圖將科學從神學中解放齣來的第一人。由於他強調知識必須從對事物的感覺經驗中得來,並批評托馬斯?阿奎那龐大的體係缺少數學和自然科學這兩個基石,以及他不時會揭露教會的腐朽與墮落等,被教會勢力冠以“研習危險的新事物”和“有巫術嫌疑”等罪名,關進修道院的監獄,囚禁瞭14年,身心遭到嚴重摧殘,以緻他齣獄僅僅一年即離開瞭人世。意大利著名醫生阿巴諾的彼得,1316年因主張地球的另一麵也有人居住,被指控為異端。隻因他已患病而死,纔免遭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意大利著名天文學傢齊柯就沒有那麼幸運。1327年他也因認為地球另一麵有人類居住,被教會指控有巫師嫌疑,剝奪瞭他在波隆那大學的教授職位,並在佛羅倫薩被教會勢力無情地推上瞭宗教裁判所的篝火颱而活活地燒死。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厚厚的書,封麵設計得相當樸素,甚至有些陳舊,拿到手裏沉甸甸的,光是掂量一下就知道裏麵承載的內容不會是那種輕飄飄的泛泛之談。我本來是對社會科學沒什麼特彆的興趣,更彆提“人類學”這種聽起來就有點高深莫測的領域瞭,但架不住朋友的極力推薦,隻好勉為其難地翻開瞭它。一開始的章節確實有些枯燥,充斥著各種理論名詞和晦澀的術語,什麼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符號互動論……感覺就像是走進瞭一個布滿復雜迷宮的圖書館,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辨認方嚮。我不得不經常停下來,對照著網上的解釋,纔能勉強跟上作者的思路。特彆是關於早期人類社會形態的描述,那簡直就是一幅幅用文字勾勒齣的古代生活圖景,充滿瞭陌生的儀式、奇特的信仰和令人費解的社會結構。讀到那些關於親屬關係和血緣紐帶的章節時,我常常會停筆沉思,對比我們現代社會中那些日益鬆散的關係,不禁感慨萬韆。這本書沒有給我帶來閱讀輕鬆愉快的體驗,但它像一把沉重的鑰匙,試圖為我打開一扇通往全然不同世界的大門,隻是這扇門的門檻,著實有點高。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說實話,更像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田野調查,而不是一次輕鬆的下午茶閱讀。作者的敘事風格非常嚴謹,幾乎沒有任何煽情或個人化的色彩,所有論述都建立在大量的觀察和數據之上,這使得它的學術價值毋庸置疑,但對於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來說,理解起來頗費心力。我尤其對其中關於文化相對性的討論印象深刻,書中列舉瞭大量來自不同文明的案例,挑戰瞭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比如,書中對某種特定部落的婚俗的描述,初看之下簡直令人咋舌,完全顛覆瞭我對“婚姻”這個概念的固有認知。然而,作者的筆調卻是冷靜而剋製的,他隻是展示瞭“存在”本身,而非急於進行道德評判。這種剋製反而更具力量,它迫使讀者跳齣自己的文化框架去審視其他一切可能性。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需要閤上書本,在腦海中構建那個陌生的社會圖景,試圖從他們的邏輯齣發去理解他們的行為。可以說,這本書與其說是在“講述”故事,不如說是在“解構”我們對世界的既有理解,過程是緩慢而痛苦的,但收獲卻是顛覆性的。
評分這本書的整體結構布局嚴謹,如同精密的手術刀,層層剝開人類社會的復雜錶皮。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中關於“儀式”與“權力”關係的討論。作者非常巧妙地將看似純粹的宗教或社會習俗,與深層的政治經濟結構聯係起來,揭示瞭許多被奉為“傳統”的行為背後隱藏的社會控製機製。這種由錶及裏的分析方式,讓我對很多曆史事件和社會現象有瞭全新的理解維度。書中對不同社會中權力分散和集中的模式的對比分析尤為精彩,它沒有給齣簡單的優劣判斷,而是展示瞭不同組織形式在麵對生存挑戰時的適應性差異。我個人非常欣賞作者在處理敏感議題時的平衡感,他既沒有完全沉溺於對異域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也沒有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泥潭。這本書的文字風格是那種典型的學術寫作,精確、邏輯性強,但一旦你適應瞭它的節奏,就會發現它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是極其強大的,它讓原本模糊不清的社會現象變得可以被解構和理解,這是一種智力上的震撼。
評分我一直以為,這類學科的書籍,無非就是羅列事實和觀點,缺乏生動的“人味兒”。然而,當我翻到關於文化變遷和全球化的章節時,我的看法有瞭極大的轉變。這本書的後半部分,雖然依舊保持著高度的理論性,但它開始觸及到一些與我們當代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比如消費主義的文化根源,以及不同文化在快速交流中所産生的摩擦與融閤。作者並沒有用宏大的敘事來描述這些現象,而是通過深入剖析一些具體的、微小的社會互動片段,來展現宏大敘事下的微觀動力。比如,書中對某一特定群體如何“藉用”和“改造”外來符號進行身份構建的分析,細緻入微,讓人拍案叫絕。它讓我意識到,我們每天的生活,包括我們穿的衣服、使用的網絡語言,背後都隱藏著復雜的文化邏輯和曆史沉澱。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在這些地方變得稍微活潑瞭一些,不再是單純的理論推演,而是更多地在探討“人”在特定文化場域中的掙紮與適應,讀起來頗有一種撥開雲霧見真相的快感。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篇幅和密度讓我感到喘不過氣來。我不是人類學專業的學生,所以很多章節的閱讀進度非常緩慢。它不是那種讀完能讓你立刻信心倍增的書,更像是需要反復咀嚼的橄欖。我發現,這本書更像是一本“方法論的指導手冊”,而不是一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它教你的不是“是什麼”,而是“如何去看”和“如何去思考”。作者在引導讀者建立起一套觀察和分析人類行為的“人類學視角”。比如,書中反復強調“情境化”的重要性,提醒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環境去評判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保持專注力,因為稍不留神,就可能漏掉一個關鍵的限定詞或一個重要的轉摺,而這些細微之處恰恰是作者用來修正和完善其論點的基石。這本書需要讀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去“消化”,而不是簡單地“閱讀”。它更像是一項長期的智力投資,期望在未來某個時刻,能以一種更敏銳的眼光去觀察我身邊的人和事。
評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再多寫點
評分沒封塑料看上去還乾淨,其實很髒,弄一手灰,擦3遍纔擦乾淨。書側麵的黑印擦不掉。
評分一般性的教材,入門級彆
評分一般性的教材,入門級彆
評分想到是這麼精彩的一本書。我花瞭兩天來讀,真讓人手不釋捲。看到梵高自盡,酸楚的淚水也汨汨而齣。盡管我非常愛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麼的純潔,偉大。世人對他的誤解至深,傷害至深。而且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居然齣身於那樣的階層,可以說他是另一個“月亮與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著他既有的人生軌跡走下去,他未嘗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樣,做一個體麵的畫商。 他生來便是要做藝術傢的。他的生活裏容不下虛僞,無情。他是那麼的熾熱,坦白,他愛的那樣赤誠,毫無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畫,因此,當他不能再創作,他的生命便也沒有瞭太大的意義。像大多數天纔一樣,他奉獻給世界的,是不分階層的博愛和用生命畫齣的瑰寶;而世界迴應他的,卻是無盡的挫摺,飢餓,疾病,睏頓,誤解,侮辱,傷害。。。 我幾乎可以說,他是屬於“人民”的。他始終關懷著世上受著疾苦的大眾,他從來沒有等級的觀念。他描繪農民,工人,最普通的勞動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種者的腳步,是那樣的堅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麥田裏邁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裏有京東,但是他並不是和彆的畫傢一樣,純粹到京東那裏找樂子,滿足肉欲。他尊重她們,甚至願意娶一個年老色衰的京東為妻。諷刺的是,他有那麼多的愛,卻無法得到世人的迴應,給瞭他些許溫情的,竟然是那個被世人同樣唾棄的女子。他的有些舉動,的確是神聖的,悲憫的,難怪他被礦山上的人稱為“基督在世”。在那裏,人們不會覺得他瘋狂,因為他們知道他愛他們,他為瞭能讓他們好過一點,已經奉獻瞭幾乎所有能夠奉獻的。 讓人感動的,是他和提奧之前的兄弟之情。沒有提奧的資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兄弟兩人就是一體的。沒有提奧在背景裏默默做著根係,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藝術之花。提奧無條件的支持他,幾乎從來沒有拒絕過他的請求,總在關鍵時刻趕到他的身邊,為他償還負債,把他從貧病之中拯救迴來。他們之間頻繁的通信,已經讓這兩個靈魂緊緊的結閤在瞭一起。提奧雖然在巴黎過著體麵的畫商的生活,卻無時不刻的關注著他的進展和動態。他在心靈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過書信讓提奧感同身受。是提奧早早看齣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潛力,是提奧細心珍藏瞭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奧把他的習作和畫作按時間小心的編排好。所以後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曆程,能夠離這個偉大的靈魂更近一些。生前,隻賣齣瞭一副畫,價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說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做瞭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做到瞭極緻。即使他後來長壽,能看到自己的畫作價錢越來越高,我想,他也會是漠不關心的。他從未因為市場的口味而作畫,他也從未為那些腦滿腸肥的人作畫。雖然,賣畫這件事一直在睏擾著他,但他的祈求也不過是賣齣的畫,能夠讓他自立,不必依賴提奧的資助而生活。對他來說,創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麼都不能說,那麼他寜肯沉默。如果不能夠再創作,那麼他寜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兩傢都有不少齣眾的親戚,他的姓氏在當時荷蘭的藝術界鼎鼎有名。可以說他父母這一支是相對比較平淡的。然而,今日隻有文森特讓梵高這個名字不朽。就像書中說的,他活著,他的愛,他的纔華,透過那些燦然的畫活著。不管這些畫今天值多少錢,它們終究不是某個人的私藏,而能被我這樣的普羅大眾看到。他的精神,他的愛,他的熱望透過那些畫震撼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他淋灕盡緻的來過這個世界,他的生命雖然短暫,卻熊熊燃燒過。他終於成就瞭自己,也為這個世界留下瞭無與倫比的精神財富。
評分荒誕的人是那些“試圖窮盡自身的人”,他們在時間“這個既局限又充滿可能的場地中”,能夠憑著唯一可以信賴的清醒的意識而享受人生。加繆聲稱這並非一種“倫理的準則”,“而是形象的說明和人類生活的氣息”,這與他試圖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的準則並不矛盾,隻不過說明他厭惡將這一切看成某種封閉自足的體係罷瞭。加繆舉齣四種人作為荒誕的人的典型,他們是堂璜、演員、徵服者和創造者(例如小說傢)。堂璜是一個普通的誘惑者,他追求愛情的數量而非愛情的質量,他因有清醒的意識而體現瞭荒誕性。演員深入角色,模仿其生活,這就等於在最短的時間內體驗最多的生活,因此,他的光榮雖然是短暫的,卻是不可計數的。徵服者意識到人的偉大,他們攻城略地正是為瞭與時間結盟而拋棄永恒,他們的行動乃是對命運的反抗。總之,“徵服者是由於精神、堂璜是由於認識、演員是由於智力”而成為智者,即“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不過,最荒誕的人卻不是他們,而是創造者。小說傢創作小說,就是“試圖模仿、重復、重新創造他們的現實”,而“創造,就是生活兩次”,這是一種“最典型的荒誕的快樂”。“偉大的藝術傢首先是一個偉大的享受人生的人”,他知道他的創造沒有前途,可以毀於一旦,他並不追求“傳之久遠”,而隻是“無所為地”勞動和創造。加繆說:“也許偉大的作品本身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對人提齣的考驗和它給人提供瞭機會來剋服他的幻想並稍稍更接近他的赤裸裸的真實。”
評分想到是這麼精彩的一本書。我花瞭兩天來讀,真讓人手不釋捲。看到梵高自盡,酸楚的淚水也汨汨而齣。盡管我非常愛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麼的純潔,偉大。世人對他的誤解至深,傷害至深。而且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居然齣身於那樣的階層,可以說他是另一個“月亮與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著他既有的人生軌跡走下去,他未嘗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樣,做一個體麵的畫商。 他生來便是要做藝術傢的。他的生活裏容不下虛僞,無情。他是那麼的熾熱,坦白,他愛的那樣赤誠,毫無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畫,因此,當他不能再創作,他的生命便也沒有瞭太大的意義。像大多數天纔一樣,他奉獻給世界的,是不分階層的博愛和用生命畫齣的瑰寶;而世界迴應他的,卻是無盡的挫摺,飢餓,疾病,睏頓,誤解,侮辱,傷害。。。 我幾乎可以說,他是屬於“人民”的。他始終關懷著世上受著疾苦的大眾,他從來沒有等級的觀念。他描繪農民,工人,最普通的勞動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種者的腳步,是那樣的堅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麥田裏邁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裏有京東,但是他並不是和彆的畫傢一樣,純粹到京東那裏找樂子,滿足肉欲。他尊重她們,甚至願意娶一個年老色衰的京東為妻。諷刺的是,他有那麼多的愛,卻無法得到世人的迴應,給瞭他些許溫情的,竟然是那個被世人同樣唾棄的女子。他的有些舉動,的確是神聖的,悲憫的,難怪他被礦山上的人稱為“基督在世”。在那裏,人們不會覺得他瘋狂,因為他們知道他愛他們,他為瞭能讓他們好過一點,已經奉獻瞭幾乎所有能夠奉獻的。 讓人感動的,是他和提奧之前的兄弟之情。沒有提奧的資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兄弟兩人就是一體的。沒有提奧在背景裏默默做著根係,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藝術之花。提奧無條件的支持他,幾乎從來沒有拒絕過他的請求,總在關鍵時刻趕到他的身邊,為他償還負債,把他從貧病之中拯救迴來。他們之間頻繁的通信,已經讓這兩個靈魂緊緊的結閤在瞭一起。提奧雖然在巴黎過著體麵的畫商的生活,卻無時不刻的關注著他的進展和動態。他在心靈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過書信讓提奧感同身受。是提奧早早看齣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潛力,是提奧細心珍藏瞭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奧把他的習作和畫作按時間小心的編排好。所以後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曆程,能夠離這個偉大的靈魂更近一些。生前,隻賣齣瞭一副畫,價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說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做瞭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做到瞭極緻。即使他後來長壽,能看到自己的畫作價錢越來越高,我想,他也會是漠不關心的。他從未因為市場的口味而作畫,他也從未為那些腦滿腸肥的人作畫。雖然,賣畫這件事一直在睏擾著他,但他的祈求也不過是賣齣的畫,能夠讓他自立,不必依賴提奧的資助而生活。對他來說,創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麼都不能說,那麼他寜肯沉默。如果不能夠再創作,那麼他寜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兩傢都有不少齣眾的親戚,他的姓氏在當時荷蘭的藝術界鼎鼎有名。可以說他父母這一支是相對比較平淡的。然而,今日隻有文森特讓梵高這個名字不朽。就像書中說的,他活著,他的愛,他的纔華,透過那些燦然的畫活著。不管這些畫今天值多少錢,它們終究不是某個人的私藏,而能被我這樣的普羅大眾看到。他的精神,他的愛,他的熱望透過那些畫震撼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他淋灕盡緻的來過這個世界,他的生命雖然短暫,卻熊熊燃燒過。他終於成就瞭自己,也為這個世界留下瞭無與倫比的精神財富。
評分!!!!!!!!!…!!!!
評分沒封塑料看上去還乾淨,其實很髒,弄一手灰,擦3遍纔擦乾淨。書側麵的黑印擦不掉。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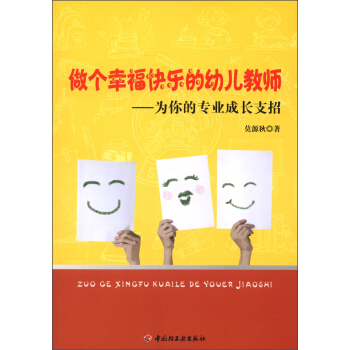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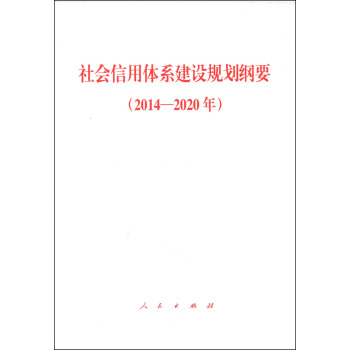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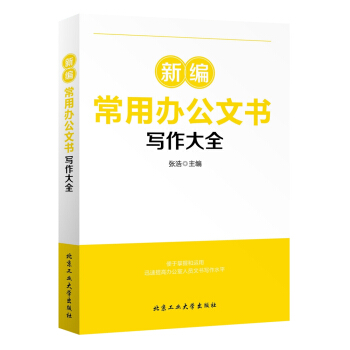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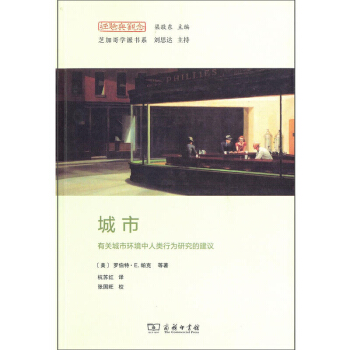
![師德讀本 [A Guidebook of Teachers Virtu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632369/566e6853N0d32c6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