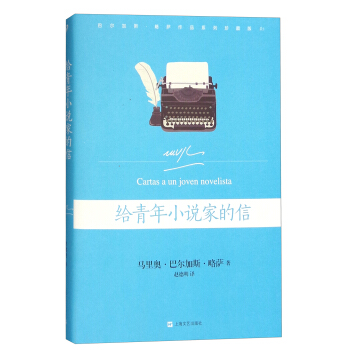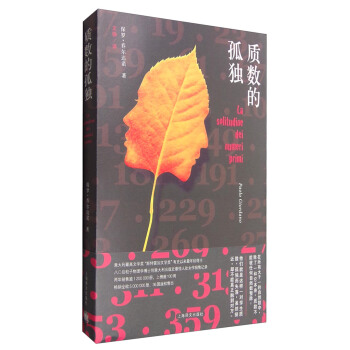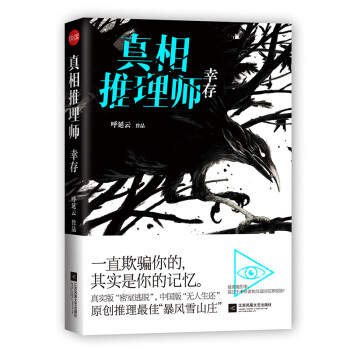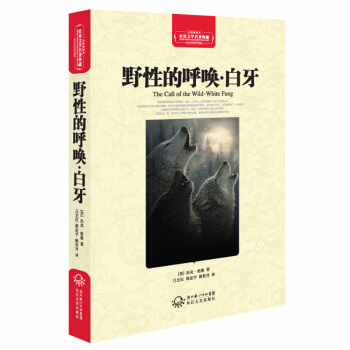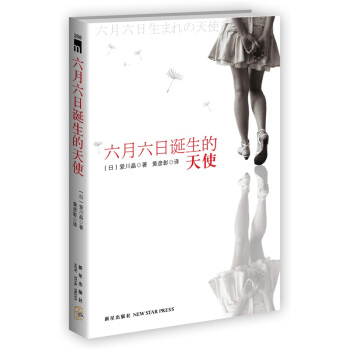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伊甸园里的罪恶乌托邦中的惨案
埃勒里·奎因匪夷所思的经历
侦探文学黄金时代高成就者
三度荣获埃德加·艾伦·坡大奖
希区柯克、斯蒂芬·金、博尔赫斯推崇的侦探小说作家
布洛克、康奈利、东野圭吾、岛田庄司的创作导师
全球销量超过两亿册
中文系列作品突破20万册
只有上帝和埃勒里·奎因才知道故事的最终结局
内容简介
二战时,埃勒里·奎因在荒野中迷失方向,误入与世隔绝的奎南山谷。虔诚的人们在这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不知道战争的存在。然而,随着奎因的到来,平静的山谷里发生了一件谋杀案。这是奎因的探案生涯中匪夷所思的案件,找出凶手绝不是故事的结尾……
作者简介
埃勒里·奎因(ElleryQueen),推理小说史上一个非凡的名字,实指弗雷德里克·丹奈(FredericDannay,1905—1982)和曼弗里德·李(ManfredLee,1905—1971)这对表兄弟作家。他们的创作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作品多达数十部,全球销量约计两亿册;他们曾五获埃德加·爱伦·坡奖;他们的四部“悲剧系列”和九部“国名系列”作品被公认为推理小说史上难以逾越的佳作;他们于1941年创办的《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成为劳伦斯·布洛克、迈克尔·康柰利等推理大家起飞的平台,迄今仍是最专业、最权威的推理文学杂志之一;他们出资设立“密室研讨小组”,定期与约翰·狄克森·卡尔、克雷顿·劳森等推理大师交流、切磋……他们成就的不仅仅是自己,更为成就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书写了浓墨重彩。目录
第一章 星期日 四月二日第二章 星期一 四月三日
第三章 星期二 四月四日
第四章 星期三 四月五日
第五章 星期四 四月六日
第六章 星期五 四月七日
第七章 星期六 四月八日
第八章 星期日 四月九日
精彩书摘
星期日 四月二日某个地方似乎有蒿草在燃烧,但向公路两侧望去,埃勒里并没有发现烟雾。先前以为看到的是火,原来只是墨西哥刺木火焰状鲜红的花簇。这里鲜花怒放,若不是由于早降的春雨,就是因为荒漠高原一年中罕见的阵雨刚刚滋润过大地。
他断定那是营火,或许只是出于希望。除了这条公路之外,他已经连续几个小时没有见到任何人类的踪迹了,
一阵模糊的突发奇想引得他拐上了这条哈姆林迤东的州际公路(从烈日烤炙的一块路牌上得知,哈姆林这个地名是以林肯的第一任副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这条路已经驶过的部分路况倒还可以,问题在于,平整的路面不够长。离开哈姆林五十英里之后,道路忽然变得曲曲弯弯,糟乱不堪。显然,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利福尼亚州公路部门的筑路工们使整修工程半途而废了。
埃勒里没有沿原路朝哈姆林方向折回,而是碰运气绕路而行。他早已对这一冒险的选择后悔不已,这条辙沟累累、破败不堪的土路并没有通到州际公路。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埃勒里开始相信,这根本不是什么支路,而是早先的拓荒者驾着马车行过的路迹,而且,它也不通向任何地方。
他开始为能否找到水而感到不安。
看不到任何路牌和标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仍在加利福尼亚州界内,还是已经进入了内华达州。
像是蒿草燃烧的芳香气息消失了。当前方高处的一幢木屋出现在视野中时,他早已把那股气息抛到了脑后。
埃勒里本可以早一些动身去好莱坞的。只不过,想到要挤在圣诞节前繁忙拥堵的交通中出行,还可能在不知何处的某个汽车旅馆里独自度过圣诞节,他便决定还是等一等再出发。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那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的官员对他说的话:“情况是这样的,奎因先生,我们可以给你的车多配些汽油,这要比在飞机或者火车上给你弄个座位容易得多,长途巴士也一样。”
一九四三年的那个十二月,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的候乘室里,人们都要受到这样的盘问:“你必须要做这趟旅行吗?”这些地方都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对那个问题想好了一个清楚无疑的回答:是的。有比画着手势申明确有急务在身、要求优先待遇的商人;有要回家度过参军前最后一个平民假期的学生;有嘈杂喧嚷、正在出发的新兵;有身着漂亮的定做制服、佩着绶带的高级军官;有沉默不言的战斗老兵;还有随处可见的恋人、已有身孕的新婚女子和拉扯着孩子的妻子们,小孩子们都是要“去看我爸爸——他是陆军士兵”,或者是水兵、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海岸警卫队员——总之都是无法在圣诞节休假的军人。而且,每个人都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欢快的:“他一定高兴极啦。他还没见过这孩子呢!”有哭诉的:“那我就站着。我不要座位,行吗?”还有没说出口、不能说出口的话:“可是我必须去那儿,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开车去吧。”埃勒里说。
于是,他留在纽约家中,与父亲和收音机做伴度过了圣诞节前夜。圣诞节那天,他们去教堂做了礼拜,吃了一顿还没有被归入配给制的火鸡,去中央公园散了步。而后,奎因警官便安闲自在地躺下来,又开始了他近来的一项休闲活动:重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①——那部书里充满了对拜占庭宫廷中奸诈之徒的阴谋恶行津津乐道的描述。埃勒里则给久拖未复的来信写回信。
二十六日,他已经收拾完行李,做好了旅行前的休整,但丝毫没有对这次旅行感到高兴或期待。一向工作得太过辛苦,他的身体都缺乏活力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把手提箱塞进老旧的杜森博格车,拥别了父亲,便上路了。
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当埃勒里出发不久、体力还不错的时候,沿途捎上的几位搭便车的军人还能跟他换换手开车;而跨过了密西西比河之后,他开始感到疲倦了,再碰到的搭车客当中竟没有一个会开车或者有驾驶执照的。当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黄昏时分抵达好莱坞时,那里已经沸腾着新年除夕的欢乐喧闹,他却从里到外每个细胞都疲倦难耐,只渴望马上洗个热水澡,再躺到一张舒适的床垫上。
“我知道,奎因先生,”旅馆的前台服务员长着一对贝塞猎狗②似的眼睛,解释说,“我知道我们确认过你预订的房间。不过……”看来,埃勒里预订的房间已经被两位刚刚从南太平洋回来的海军少尉占领了。
①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述了罗马帝国自二世纪起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
②贝塞猎狗(Basset),法国种猎狗,短腿,长耳,动作缓慢。
“那么,按照海军最优良的传统,”埃勒里叹道,“他们是不会弃船的。好吧,我认输了。最近的电话在哪儿?”
卢·沃尔什在电话里大声喊着:“埃勒里!你当然可以住在我们家,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快过来吧,派对正热闹着呢。”
派对的确很热闹,他也无法拒绝邀请。就这样,直到将近黎明的时候,他才洗了那个渴望已久的热水澡,躺上那张向往多时的舒适的床。然而这一觉却睡得辗转不安。模糊不清的号叫声在他耳内回荡着,他仿佛在一条无尽的公路上沿着一根永无终点的白线飞速猛冲。由于整夜紧紧抓着被单,他的手指都抓疼了。
现实中的感觉不时与梦中的世界重合,产生了幻觉。忽而,他看见一片闪烁的阳光,闻到刚刚浇灌过的土地上玫瑰花的香气;接着,当眼睛重新闭上时,却又挣扎着进入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之中,那是个幽暗阴沉的黄昏,皑皑白雪上染着玫瑰花般的斑斑血迹。还有一回,他听到一个像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满含激情地叫了一声:海伦①!转瞬之间,他被轮番抛入了两片大海:一会儿是荷马史诗中被冷兵器的撞击之声搅扰得波涛汹涌的大海,一会儿又是当代战争中被舰船爆炸时地狱般的火光耀亮的大洋,铿锵声不停震响、回荡,不得宁静的大海痛苦地咆哮着。
①海伦(Helen),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女,为了争夺她,希腊与特洛伊之间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荷马史诗中对此有记载。
他一觉睡到了天黑,醒来时依然觉得疲惫不已,热水浴也只是在他的疲倦边缘轻拂而过,并没有带走什么。伊夫琳·沃尔什急匆匆地朝他冲过来。“我们还以为你睡死过去了呢,埃勒里!”接着便端来一堆东西塞给他吃,橙汁、鸡蛋、烤面包片、薄煎饼,还有泛着黄铜色的茶(“我们没有培根和咖啡了,真是讨厌。”看来沃尔什一家的食物配给卡用得很费)。埃勒里只轻轻呷了一小口茶,他本指望能有大杯的咖啡呢。
卢·沃尔什让他选择:跟他们去朋友家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新年夜聚会,或者“就待在家里聊聊天”。那位朋友是个电影明星,住在比弗利山①。埃勒里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这种所谓非正式的好莱坞新年夜聚会了,因此他毫不客气地选择了后者。他们谈论这场战争,谈到了演员们时下的处境——卢是一家演员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关于纳粹集中营的一些传闻。埃勒里听到的谈话声变得越来越远。后来,他听见伊夫琳说:“够啦!”便猛地抬起头来,眼睛也一下子睁开了。
①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位于美国加州好莱坞附近,著名的高级住宅区,许多电影明星有豪宅坐落此地。
“你要马上回到床上去,埃勒里·奎因,要不然我就得亲自替你脱衣服了。”
“好吧……那么你跟卢还要去参加聚会吗?”
“是的。来吧,走吧。”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星期天下午了。疲倦没有消失,并且还添了新的不适——浑身像得了疟疾似的发冷。
“你怎么啦?”女主人问,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点儿咖啡。他尽力握稳杯子,大口地喝着。
“你看上去很糟糕。”
“看来我没办法摆脱这种疲惫的感觉了,伊夫琳。”
卢·沃尔什摇摇头,说:“如果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埃勒里,怎么能应付得了紧张劳累的工作呢?大都会电影公司里那个指挥你工作的家伙是陆军情报局的,听说他正想凭一己之力赢得这场战争呢。”
埃勒里闭上眼睛,说:“再来点儿咖啡,好吗?”
第二天早上,他毅然在九点钟赶到了大都会电影公司——以好莱坞作家们的作息标准,此刻相当于午夜。唐纳森上校面带冷淡的微笑,在那儿等着他。
“新年过得太长了吧,奎因?”上校的眼睛像少年一样明澈,“有句话我最好现在就讲明白:早起的鸟儿不会慌张出错。我指挥的是一个紧张工作的骨干小组。认识查利·戴尔斯吗?”
“嗨,查利。”埃勒里打了个招呼。新年,又是周末之后的星期一早晨九点钟,查利·戴尔斯已经在工作了,这样看来,唐纳森上校的确是在驱赶着一个神经紧张的小干部①。自从有人大胆地创造出特写镜头这种拍摄手法以来,戴尔斯就一直在做胡乱删改电影剧本的工作。
①此处埃勒里故意对上校的话做双关引用,因为英文“run a tight little cadre”,既可理解为“指挥一个紧张工作的骨干小组”,也可理解为“驱赶一个神经紧张的小干部”。
“嗨,年轻人。”那位老前辈说,他顺着自己酒红色的鼻子往下瞟了一眼雪茄上一英寸多长的烟灰,“欢迎加入团队。”
“是的。那么,”唐纳森上校说,“奎因,你对我们要做的事情熟悉吗?”
“前几天晚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些电影剧本都是关于‘防止苍蝇飞进食堂的重要性’,或者,‘如果不当心你就会染上性病’这类主题的。”
上校原本冷漠的表情此刻简直凝结成了冰。“那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性病的题目完全是归另一个小组处理的。”
埃勒里瞥了一眼查利·戴尔斯,他正一脸天真地朝上校房间的观景窗外凝望着,一股剥了皮的桉树似的药味从窗口飘了进来。依旧是这个好莱坞。唯一不同的是,往日戴米尔①们安坐的大桌子后面,如今换了穿军装的人。
“好啦,”唐纳森上校精神奕奕地说,“我们要在三个月、最多四个月之内,准备好二十部电影的剧本,其中十部是给军人看的,其余的给平民看。那么,先生们,要是按一句中国谚语说的:一画抵千言,你们自己也算得出我们需要准备多少句话,才能拍成这些电影。而且,没有时间犯错。”他严厉地补充道,“犯错是人性,宽恕是神性②。但是,在战争中,你们必须像神一样工作。自从一八六五年以来,这个国家再没有人听见过愤怒的枪炮声③,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我们有可能输掉眼下这场小小不言的战争。”当埃勒里还在琢磨上校最后这句话中令人费解的对比时,上校已经又发起了攻势。“那么,在我的影院里,战争是不会输的,”——声音像裸露的钢铁一般坚硬——“要齐心协力,奎因!要记住:我代表军队,戴尔斯代表电影公司,而你……”上校一时似乎不知该如何措辞。“而你,”他重整斗志,“你要跟我们一起工作,奎因,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我说的工作指的是……就是工作!”
①戴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1959),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兼导演,所拍影片以场面豪华壮观著称,名作有《十诫》等。
②出自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长诗《批评论》。
③南北战争一八六五年结束,其后美国没有发生过战争。
埃勒里确实开始工作了,跟那位总是骂骂咧咧的查利·戴尔斯面对面地挤在一处,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常常还会更久。他在抵达好莱坞时已经疲惫不堪,没过多久,便进入了衰竭状态,只是还没有卧床不起罢了。
不知怎么回事,陆军情报局曾许诺过的食宿条件在一片混乱当中不了了之。尽管有点儿不情愿,他仍住在沃尔什家,享受着热心款待。伊夫琳·沃尔什母亲似的细心关爱和卢毫无侵扰的殷勤照顾并没能让他的状态变好一些。甚至周末也是如此,上校关于早起的严明纪律使埃勒里形成了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到了星期天,他想睡懒觉也睡不着了。于是,即使在休息日,他也没有停止工作、养精蓄锐的感觉,似乎仍在继续着一周的工作。并且,一想到星期一还要早起就心生畏惧。
唐纳森上校说话时总会冲着他耳边喷出薄荷味儿的热气,比这更难以忍受的则是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埃勒里和戴尔斯常常是还没能安下心来做下一个新本子,而前一个或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做完的本子就已经打了回来,要他们修改、重写或删除其中的某些段落,不然就是添加一些穿插和过渡的段落,再对整个剧本加以修改校订。至少有两次,埃勒里恍然发现,自己正在写的这个剧本中的一段戏应该是发生在另一个剧中的事情。
他和戴尔斯早就不怎么交谈了,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跟对方说上一句。他们像被投入了炼狱一般辛苦地劳作。灰暗脏污的脸孔,白化病人般布满血丝的红眼,他们成了这场战争的囚徒,内心充满着永恒而绝望的仇恨。
完工领薪的日子到了,那是个星期天,四月一日。愚人节。
这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埃勒里已经到了电影公司。他一直在打字机上拼命敲打着键盘,完全没意识到时间已经过了多久。忽然,他觉得有一双冰凉的手按在了他的手上,他抬起头来,发现唐纳森上校正俯身站在他旁边。
……
前言/序言
在线试读
《然后在第八天》相关资料某个地方似乎有蒿草在燃烧,但向公路两侧望去,埃勒里并没有发现烟雾。先前以为看到的是火,原来只是墨西哥刺木火焰状鲜红的花簇。这里鲜花怒放,若不是由于早降的春雨,就是因为荒漠高原一年中罕见的阵雨刚刚滋润过大地。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氛围营造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高度,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世界,让你一旦进入就很难抽身。作者对环境的描写,简直就是大师级别的“环境叙事”,场景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载体,一种无声的压力。无论是阴沉的雨天,还是寂静无人的街道,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和目的,与角色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我甚至能闻到文字中描绘的那些气味,感受到那种潮湿的寒意。这种强烈的沉浸感,使得阅读体验远超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体验活动。而且,这种氛围的控制是极其精妙的,它不是一味的压抑,而是像在紧绷的弦上跳舞,时而有一丝微弱的光亮闪现,却又很快被更深沉的阴影吞噬,这种希望与绝望的反复拉扯,让我的心跳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频率上。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更多是哲学层面的反思。它没有提供任何现成的道德准则,而是将一系列道德困境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逼迫着我们自己去做出判断。那些情节的推进,与其说是推动故事发展,不如说是推动了角色(以及读者)的自我审视。我特别欣赏作者对“选择的代价”这一主题的探讨,他毫不留情地展示了每一个决定背后隐藏的牺牲与得失。读完之后,我久久无法平静,脑海中一直在回响着书中的那些对话和场景,它们像幽灵一样萦绕不去,不断提醒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岔路口都意味着一次放弃。它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些决定,那些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书中的逻辑下,似乎都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灰色。这本书的格局很大,它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讲述,进入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叩问,读完后,感觉自己的思维边界被拓宽了不少,同时也带走了一份沉甸甸的思考负担。
评分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位作者的笔力之老辣,绝对是新生代中罕见的。他对于语言的运用达到了近乎雕琢的程度,每一个词的选择都精准到位,没有一个多余的赘述。不同章节之间的语调转换,处理得极其自然流畅,时而沉郁如老酒,时而轻快如溪流,这种张弛有度,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比如他对“失落感”的描述,不是空洞的形容,而是通过一系列精确的感官细节勾勒出来,让人瞬间就能理解那种深入骨髓的空虚。阅读过程中,我数次停下来,仅仅是为了回味某一段文字的绝妙结构,那简直就是一场文字的盛宴。这不是那种快餐式的消遣读物,它需要你慢下来,去品味、去咀嚼,去感受文字背后的深意。它挑战了读者对于传统叙事模式的预期,用一种近乎诗意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又迷人的思想空间。
评分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作者那种打破常规的叙事结构。他似乎对线性时间不屑一顾,而是采用了一种碎片化的、多重视角的拼接方式来呈现故事的全貌。一开始,这种跳跃感会让人感到些许困惑,仿佛手里拿着一块块零散的拼图,无从下手。但正是这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反而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悬念和真实感——毕竟,真实的生活本身就是由无数个不连贯的瞬间构成的。随着阅读的深入,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开始奇妙地相互呼应,彼此印证,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情感洪流。这种“后知后觉”的阅读体验非常罕见,直到最后几章,我才恍然大悟之前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原来埋下了如此精妙的伏笔。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解谜游戏,它尊重读者的智商,鼓励我们主动参与到意义的构建过程中来。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真是出神入化,起初还略显平淡的开篇,像是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积蓄力量。随着故事的深入,作者不动声色地抛出各种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它们像散落在地上的碎片,你得紧盯着,才能在脑海中拼凑出完整的图景。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人物内心挣扎的刻画,那种细腻到近乎残忍的剖析,让人仿佛能穿透纸面,直接触碰到角色的灵魂深处。那些犹豫、那些自我怀疑、那些在关键时刻迸发出的勇气,都写得真实可信,没有丝毫矫揉造作。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急于告诉你答案,而是引导你去思考,去体验角色在不同境遇下的心路历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在面对困境时可能有的种种反应。那种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下涌动的暗流,被作者捕捉得淋漓尽致,读起来让人既沉醉又感到一丝不安,正因如此,我完全沉浸在了这个世界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直到合上书本,才猛然惊觉夜已深。
评分从后期开始,奎因的多部作品开始设计道宗教与神学的领域,比方《十日惊奇》,比方《另一方玩家》,从作者的创作中看出,重头并不在逻辑推演与诡计设计的游戏感,而是一种肃穆与痛苦挣扎的心情,这种痛苦与挣扎直接反映在这一时期作品艾勒里的心理描写中,从莱特镇以后,艾勒里虽然还是那个高智商的神奇侦探,但是读者也许会发现到后期的艾勒里一定不像前期那样潇洒不羁(中期是受剧本与感情拖累显得有点窘迫),在后期的奎因给我的印像一定不是偏偏绅士,而是一个愁眉不展的家伙。
评分正版图书 印刷的字迹很清晰 非常好
评分因为难以看到另一个推理小说作家创作了各种各样的经典模板作,并且还话题多多,数量可观。
评分好好好好价
评分作者是埃勒里·奎恩由一对来自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表兄弟:佛德列克·丹奈与曼佛雷德·李。其实,他们的本名分别是丹尼尔·内森以及曼福德·勒波夫斯基,他们在年轻时自行改了名字,并同时求学于布鲁克林高中。丹奈与李为了参与《麦克鲁杂志》与利普平科特出版社合办的推理征文比赛;由于比赛规定报名者必须以笔名参赛,他们就想出埃勒里·奎恩此一笔名,并以此作为小说中侦探的名字。 身为一个成功的系列推理小说作家,埃勒里·奎恩不只是一个笔名,他已然成为推理小说中的英雄。埃勒里·奎恩的作品含跨了电影、广播节目、电视节目。作者之一的丹奈甚至创办并担任《埃勒里·奎恩推理杂志》的主编,这部杂志被认为过去6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系推理小说杂志。作者也是卓越的推理小说历史学者,并编辑数本短篇故事选集,如《福尔摩斯的恶运》。他们在《现代图书馆丛书》里994页的选集里所作的《101年的娱乐,优秀的推理故事,1841-1941》,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许多年来被不断重复印制。这对表兄弟对推理小说的贡戏也借由他们共有的笔名,在1961年得到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大师奖殊荣
评分有活动的时候买了好多本
评分二战时,埃勒里·奎因在荒野中迷失方向,误入与世隔绝的奎南山谷。虔诚的人们在这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不知道战争的存在。然而,随着奎因的到来,平静的山谷里发生了第一件谋杀案。
评分非常喜欢,一如即往的好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书有封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阿莱夫 [ALEP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26958/rBEhVlJCP_AIAAAAAAMwHs0qJYoAADhbwJmCkEAAzA288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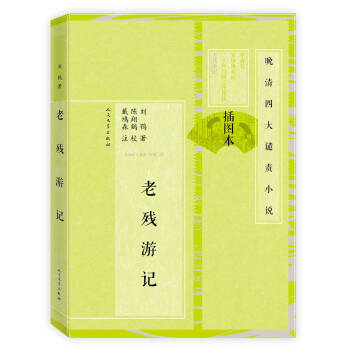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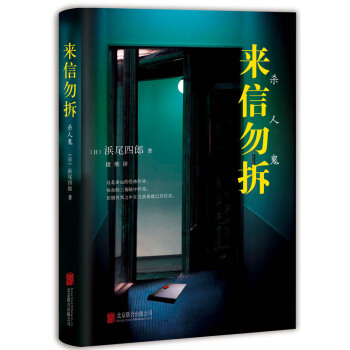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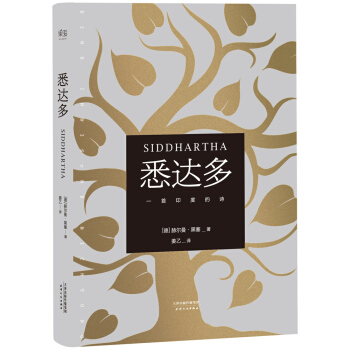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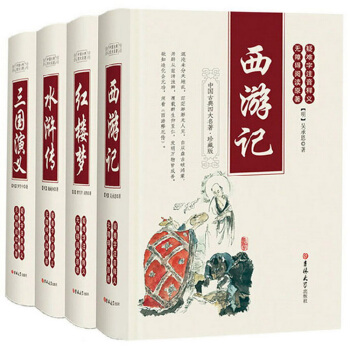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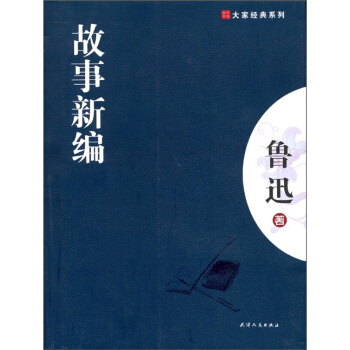
![盐之书 [The Book of Sal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12359/rBEIC0_2doEIAAAAAAAxL_O9HPQAADveAPOMYkAADFH28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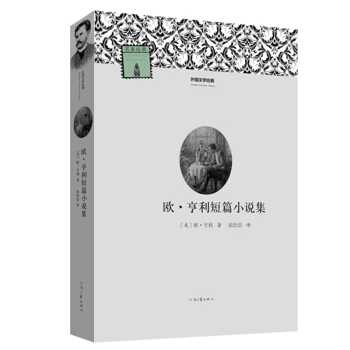
![皇家酒店 [ホテルローヤル]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54526/55d2f23eN406279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