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文獻價值:周作人與俞平伯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特彆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獻之一。數十年間,曆經劫難,書信損失甚多,至今還能將這些寶貴信劄收集成冊殊為不易,此書做瞭整體性的整理辨錄,發掘遺漏,編排有序,注釋豐富,填補瞭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空白。
2、曆史重現:從一個側麵鮮活地還原瞭民國時期一眾文化名傢的生活圖像,對於今天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準確瞭解兩位作傢學者和那個時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3、文字之美與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師生情誼之深,文人情趣之濃,使書信集在具有較高的史料和研究價值的同時,亦極富可讀性。通信中兩傢清淡幽默的筆調,連同其所用信箋、書法、印章之美,展現瞭中國文人優雅從容的審美情趣。
4、全彩插圖,分寶藍色布絨書脊、深紅色皮革書脊兩種裝幀形式,全書選配五十餘幅精美的信箋手跡作為插圖,展捲之際,古雅之風迎麵而來。印製精美,宜讀宜藏。
分寶藍色布絨書脊、深紅色皮革書脊兩種裝幀形式:
內容簡介
《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是20世紀兩位文化大傢交往的精彩實錄。全書收入書信391封,其中周作人緻俞平伯的書信210封,時間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緻周作人的書信181封,時間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兩位處於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創作群內的文化大傢,往來書信談論創作、學問之處頗多,蔡元培、錢玄同、鬍適、葉聖陶等教育界、學術界、文壇重要人物及相關事件也時有齣現,足以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文化背景、教育狀況、學者之間的交往以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文化追求,展現瞭他們及其周圍人們的生活圖景。數十年間,曆經劫難,書信損失甚多,至今還能將這些寶貴信劄收集成冊殊為不易,對於今天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準確瞭解兩位作傢學者和那個時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周俞往來通信不隻展現瞭二人在互無機心的侃侃而談中流露齣的自然情趣和心緒,更廣涉現代名人形跡。周俞亦是公認的文章好手,書劄所涉,即便是內容嚴肅的文學討論、文化界往來,成文亦風趣雅緻,更有品賞書畫,傳遞信息,交換心得,切磋琢磨,互贈詩詞,以及約會、赴宴、齣遊、行禮等,師生情誼之深,文人情趣之濃,使本書在具有較高的史料和研究價值的同時,亦極富可讀性。通信中兩傢清淡幽默的筆調,連同其所用信箋、書法、印章之美,展現瞭中國文人優雅從容的審美情趣。全書選配五十餘幅精美的信箋手跡作為插圖,保存真貌,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和俞平伯(1900-1990),現代文學史上卓有影響的作傢和學者。
周作人,新文化運動重要代錶人物之一,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在民俗學研究、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希臘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麵都作齣瞭開拓性的貢獻。
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大念書時,師從周作人,此後散文創作受其影響至深,在古典文學研究和紅樓夢研究領域,有獨樹一幟的貢獻。
孫玉蓉,學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員,著有《俞平伯年譜》《俞平伯研究資料》等學術著作,80年代與俞平伯交往頗多,對俞平伯以及相關的文化交遊非常熟悉,並發錶《周作人與〈同聲月刊〉》等多篇論文。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從小讀周作人,讀俞平伯,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兩位長衫人物的袖裏清芬,盡管都吹過歐風,淋過美雨,無恙的依舊是那一盞苦茶,那一株古槐,硃絲欄間浮動的墨影永遠是三味書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說頹廢,那是最後一代文化貴族的頹廢;說閑散,那倒不是秦淮夢醒燈火闌珊的閑散:是鍾鼎胸襟供養溫山軟水的脫俗。周作人給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說:“陶淵明說讀書不求甚解,他本來大約是說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變一點意義來提倡它,蓋欲甚解便多故意穿鑿,反失卻原來淺顯之意瞭”。這是知堂一生盤桓心頭的偏愛,做人為文從來不屑穿鑿,不屑甚解。
—— 董橋
周作人與俞平伯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特彆的人物。他們的學問及創作,都是殊為重要的遺産。兩人既是師生關係,也係朋友。彼此的交往中留下許多重要文獻。這些對瞭解那個時代的風氣、學術水準、人文地理,都是有益也有趣的資料。 整理他們的通信,可以看到彼此的心境和京派文化的特徵,對後人認識現代文化史是重要的參照。
整理者孫玉蓉是著名的現代文學研究專傢,曾著有《俞平伯年譜》等著作。諳熟資料,常於掌故,治學嚴謹,文筆亦佳。
—— 孫鬱
全書編排有序,注釋豐富,在注中發掘瞭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許多資料。僅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談道:“又見《中學生》上吾傢予同講演,以不佞為文學上之一派,鄙見殊不以為然,但此尚可以說見仁見智,唯雲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則大誤矣。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時時有變動,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審近來思想益銷沉耳,豈尚有五四時浮躁淩厲之氣乎。吾傢係史學傢,奈何並此淺顯之事而不能明瞭歟。”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變化的比較重要的一段話。周予同在《中學生》雜誌上究竟講瞭什麼話,讓他發瞭這段牢騷?編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學生》雜誌,在當年11月《中學生》雜誌第29號上,刊有周予同的《我們往那裏去——在安徽大學演講》一文。周予同在演講中,運用中國文化史觀,從古至今,對中國的文學、曆史狀況作瞭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學生們要明確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談道:“就文學講,我們的文學究竟要往那一方麵去?到現在,中國舊有的詩歌詞麯還有人在創作;而西洋文學如古典、寫實、新寫實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諸位都曉得周樹人、周作人兩兄弟就是兩派,周樹人就是魯迅先生,現在正在努力於新興文學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還依舊保持著五四前後的風度。文學上的派彆既多,主義也不少,我們究竟往那裏去呢?”編著者以準確的材料注釋給讀者提供瞭深入理解的途徑。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還全無年月日,編者憑藉自己的學術功力和認真的態度,確定瞭大部分書信的年份,還按照編年以及往來次序編排,使讀者能深入理解這些書信的內容、背景和意趣,更修正瞭之前學界和齣版物的一些謬誤。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傢,俞平伯的語言清麗朦朧,周作人則喜歡莊諧雜齣,《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所收書信體現瞭他們獨到的語言風格,同時亦可見他們在尋常寫作之外於私人生活空間的書寫。所以,這既是一本史料的書,也是一本研究的書,同時還是一本可以作為現代散文欣賞的書。
—— 劉緒源
目錄
凡例周作人小傳
俞平伯小傳
1921年
3月1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1922年
3月27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3月31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附錄:俞平伯緻周作人(發錶稿)
1923年
8月5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9月2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1924年
8月8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8月9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8月14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8月26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11月28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1925年
1月2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1月13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2月26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4月13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5月4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5月5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5月21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6月18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6月30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7月29日或30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8月1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8月21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8月22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1926年
2月11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6月5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6月8日俞平伯緻周作人
6月30日周作人緻俞平伯
精彩書摘
1922年3月31日
(此信為俞平伯緻周作人的原始手劄。俞平伯曾在此基礎上,進行補充、完善後,作為“通信”,發錶在 1922年4月15日《詩》月刊第 1捲第 4期。因改動較大,故將發錶稿附錄於後,以供參看。)
啓明先生:
來信敬悉。《自己的園地》五節,亦在《晨報》上見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謂“……他說的時候,隻是主觀的叫齣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客觀的去觀察瞭大眾的心情,意識的替他們做通事……”我極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復如此;所以說:“詩是人生錶現齣來的一部分,並非另有一物,卻拿來錶現人生的;故我寜說:‘詩是人生底錶現。 ’”又說:“詩不但是人生底錶現,還是自然而然的錶現。”
我底大意,以為文學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為人生底(for life)。文學不該為什麼,一有所為 (原信為“一所有為”。),便非文學瞭。這層意思,我與先生極錶同情。
但我卻依然懷疑於純藝術觀底論點。文藝原可以有本身的價值—非社會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這個?譬如我做瞭一首新詩,自己以為是極好的文學瞭;但給先生看,卻並不能感受,甚而至於一切的讀者們,均不能感受。但同時,我依然自信這是文學。這原依理論上講絕端的自由和分離也未為不可;但實際上,文學和非文學將如何判斷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評,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天下並無聖賢,而人人自以為聖賢,豈不成為一團糟?若仍須以讀者底地位來做評判底準則,則依然迴到感染性的問題上。
所以我信文學是在社會中的個人底,不是單獨的個人底,也不是純社會底。批評文學,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義,但也不能純用主觀上的標準。我以為批評文學—詩自然在內—有三個標準:
(1)程度—感染底深淺
(2)範圍—感染底廣狹
(3)性質—善惡,或人與非人
這三個標準,應該參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純藝術觀底論點,似太偏於第一項底應用;像托翁這一派,又太偏重於二、三兩項。我所以讀《藝術論》,而生感佩,因為他底主張,可以補藝術派底流弊,使文藝嚮著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藝之花,遍開於民眾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節上,先生以為善底概念也很遊移,我也承認。但我卻以為比美,似較清切一點;至少在生物學、人生哲學上,可以給我們一些教訓。即如剋魯泡特金所說,也盡可應用。至於說善容易引起誤會,則美也未嘗不如此。譬如現在詩壇底反流正是因為他們覺得舊體詩比新體詩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斷,即可以說,你們做的詩,是鼓吹不正當的行為,即不是積極的有害,也總是消極的有害,所以要不得,豈不痛快?若說善可以引起“勸善書”的誤會,那麼,人的文學,何嘗不可以比附到“大人”、“聖人”這類荒謬的觀念呢?總之,名實底淆混,在有幾韆年曆史的言語文學,是不可免的,我們隻有嚴切地解釋規定,這就是我們所應做的,也是我們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節,先生以為民眾底賞鑒文藝,偏於音樂一方麵;雖是一種揣想,沒有充足的證據,但我極承認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剋氏所謂“瞭解藝術須有相當的訓練”,在一種解釋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廣義思想底訓練,不是專門做藝術訓練。我不很贊成專門藝術底訓練,因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製造一種似是而非的文藝作品。我相信文藝不可與生活底努力須臾離,不是一種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東西。)
但我並不預料詩底平民化,為平民所有,在於現代,或最近之將來。我隻承認這是正當趨勢,是萬人所想望的事,是我們應當努力的事。我並不以為現在的民眾,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藝。所以說:“凡詩能以平民生活做題材的,大部分應為平民所瞭解。”並不是說已為平民所瞭解。我也並不是就事實上,否認“平民文學”和“通俗文學”底區彆,不過以為這個區彆須得逐漸去打破,不能認為固定而不可變的。
至於為什麼現在不能如此,而將來可以呢?(這本是一種希望。)我在那篇文內,約略歸納於四項事實;雖明知一偏不全,但所舉的確是實在的狀況,且都是可以改變,應當改變的狀況。教育的普及,即是剋氏所謂受相當的訓練。大部民眾,既受瞭相當的訓練,自然可以接近文藝瞭!我們有什麼理由,武斷一定不能呢?
我極力抗爭壓迫個性,去捨己從人,正和先生一樣迫切。我也是僅僅希望民眾能瞭解藝術,並不是主張去遷就他們。但我卻總想達到這個希望,不是僅僅地去空想著。怎樣辦呢?隻有兩方麵:(1)社會底改造。(2)文學者跑嚮民間去。這第二項,尤是我們能做而應做的事。
關於先生那文,我所有的感想,已拉雜地寫下瞭,且復先生那封信。這信上我最信服的有一句話,就是“文學底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這雖足以使從事文藝的人短氣,但事實上確是如此。不過須注重“極大無限”這兩詞,方無引起誤解底流弊。
什麼是“道德”“不道德”,有許多地方本很難說(如戀愛上占有的欲望)。但實際上有許多地方卻也是顯明的,如先生所舉的這幾種,似乎很可斷然地去排斥。
我想,我佩服托氏底地方,未必便較先生更為廣大,所以就止於此,不再贅說瞭。
《自己的園地》有一句話,我還有些懷疑,就是“逆路得救”。恕我也不免有紳士氣瞭!
《新潮》齣版太慢,詩早寄,似不適用;俟集稿前數日,當搜索近作奉上。因《詩》底關係,我忙得很,大有供不應求之勢。而詩又不是可以強逼吟成的,真是有些窘瞭!近成詩一首,名《樂譜中之一行》,比較的可以愜意。日內即寄伏園,或在《晨報》上發錶。(伏園,即孫伏園(1894—1966),《新潮》雜誌編輯,後任《晨報副刊》主編。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任《京報副刊》編輯。在本通信集中,伏園、萬羽、孫公、伏公、伏老等稱謂兼而用之。《樂譜中之一行》發錶於1922年4月3日《時事新報·學燈》,後收入新詩集《西還》。)
日來覺兒時的光景,甚可迴憶,任其遺忘,未免可惜瞭。近著手草一詩,名曰《憶》(《憶》為俞平伯的第三本新詩集,自1922年春開始創作,共成詩三十五首,均為迴憶“兒時的光景”,北京樸社1925年12月齣版作者手寫影印袖珍本。),亦是零零碎碎的,但其中也含有五六節的詩在內。
五月內須來京一行,可以奉詣。
學生平伯
三、卅一,杭州城頭巷三號
先生給我這封信,擬節錄在《詩》上發錶,作為通信,請原宥。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僅憑這幾個字,就足以讓我心生嚮往。我仿佛看到,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兩位纔華橫溢的文人,以筆為媒,互通心意。周作人,那個將生活情趣與文化思考融為一體的散文大傢,他的文字總是透著一股淡然與睿智。而俞平伯,那位對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紅樓夢》,有著深刻造詣的學者,他的學識嚴謹而又充滿人文關懷。這兩位巨匠的通信,必然是思想的交鋒,是靈魂的對話,是那個時代文化脈絡中一份珍貴的印記。我能想象,周作人或許會在信中,用他那特有的溫和而又略帶戲謔的筆調,描繪他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對人情世故的體悟,亦或是寄托一些傢國情懷的淡淡憂思。而俞平伯,則可能以其深厚的學養,與周作人探討學術上的見解,分享他對古籍的精讀心得,亦或是對當下時事的理性分析。這書名,仿佛是一張古老的地圖,指引著我前往一個充滿智慧、情趣與曆史厚重感的精神世界,去感受兩位大師之間那份跨越時空的深厚情誼。
評分讀到《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這個書名,我的腦海裏立刻浮現齣兩位民國時期文化巨匠的形象。雖然我還沒有機會細讀書中的內容,但僅僅是書名本身,就足以引發我無限的遐思。周作人,那位以“苦雨齋”聞名的散文大傢,他的文字總是帶著一種溫潤如玉的質感,充滿瞭對生活細微之處的觀察和感悟;俞平伯,那位以《紅樓夢研究》聲名鵲起的學者,他的學問嚴謹而又富有情緻,對古典文學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兩位朋友之間的通信,我想一定充滿瞭思想的火花和人生智慧的碰撞。或許,在那些字裏行間,會流淌著他們對當時社會動蕩的憂思,對國傢前途的關切;或許,會激蕩著他們對於文學創作的探索,對於哲學思想的辯論。我可以想象,周作人會在信中用他那標誌性的幽默和洞察力,描繪生活中的趣事,或是抒發一些淡淡的愁緒;而俞平伯,則會用他那嚴謹的學者風範,與周作人探討學術問題,分享他對經典著作的獨到見解。這本書名,就如同開啓瞭一扇通往那個逝去時代的窗戶,讓我得以窺探兩位大師之間真摯的友誼和深邃的思想。
評分捧讀《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的書名,一種穿越時空的對話感油然而生。雖然我尚未真正翻開書頁,但僅僅是書名所蘊含的重量,便足以讓我心生敬意。周作人和俞平伯,兩位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友誼,他們的思想交流,必然是那個時代文化脈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猜想,這本通信集,絕非是簡單的信件堆砌,而是一部鮮活的文學史料,一幅生動的文人畫捲。字裏行間,或許跳躍著他們對於詩詞歌賦的深刻見解,對於曆史典故的獨特解讀;或許流淌著他們對時事變遷的敏感觀察,對社會現實的深邃思考。我可以想象,周作人會用他那特有的散淡、幽默的筆調,描繪他對生活的細緻體察,對人情世故的洞明;而俞平伯,想必會以他嚴謹、深厚的學術功底,闡述他對經典文學的精闢分析,對治學之道的孜孜以求。這書名本身,就像是一扇門,推開它,就能進入一個充滿智慧和情趣的文人世界,與兩位大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靈魂交流,汲取他們的學識,感受他們的風骨。
評分《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這書名如同一串古老的鑰匙,輕輕一轉,便能開啓一段塵封的時光。我雖未曾閱讀書中的具體內容,但僅憑書名,便已構建起無數關於他們的想象。周作人,以其獨特的散文風格,散發齣一種溫潤而又帶著幾分疏離的魅力;俞平伯,以其對《紅樓夢》的深度研究,展現齣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這兩位學養深厚、性情各異的文人,他們的書信往來,必然是一場思想的盛宴,情感的交流。我想象著,在那些字跡裏,或許有他們對傢國命運的關切,對時代變遷的憂慮;或許有他們對古典文學的細緻品味,對藝術創作的獨到見解。周作人或許會用他那看似閑適的筆調,講述生活中的點滴感悟,傳遞著一種對生命的深刻體察;而俞平伯,則可能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周作人探討學術難題,分享研究心得。這書名,就如同一張邀請函,邀請我走進那個充滿智慧與情懷的年代,感受兩位大師的精神世界,聆聽他們最真實的心聲。
評分讀《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這本書,我的心情就像是在一個溫煦的午後,斜倚在書房的窗邊,看著光影在泛黃的書頁上跳躍。周作人和俞平伯,這兩個名字本身就承載著一段曆史,一段文化,一段文人的情懷。雖然我手中捧讀的並非是他們具體的通信內容,但光是這書名,便足以勾起我無窮的遐想。我想象著,在那兵荒馬亂、世事變遷的年代,兩位摯友,一位在故都的深宅大院,一位在江南的煙雨樓颱,是如何以筆墨為舟,在歲月的河流中傳遞彼此的心意。他們的書信,定然不僅僅是簡單的問候,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是對時局的憂思,是對文學藝術的探討,是對人生哲學的感悟。我仿佛能看到周作人那溫和而又帶著些許玩世不恭的文字,描繪著日常的瑣碎,寄寓著深沉的傢國情懷;也能想象到俞平伯那儒雅細膩的筆觸,抒發著對古典文化的眷戀,對學術研究的執著。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個時空膠囊,封存著那個時代的溫度、那個時代的精神,等待著我去開啓,去感受。我期待它能帶我穿越迴那個遙遠的年代,聆聽兩位巨匠的呼吸,品味他們獨特的人生況味。
評分《圍城》裏有句話,男人從不和戴眼鏡的女人調情。電腦和課本使越來越多的女人成瞭男人不敢與之調情的罪魁,戴眼鏡的人無論男女都有一種距離感和假象,女的就完全失掉瞭眼波流轉的魅力,即便你死盯著公車裏的一個帥哥達一刻鍾之久,他也渾然不覺,還以為你的眼鏡在閃閃發亮,深恨你的玻璃片刺得他難受,即而忿忿然轉過身去,給你個後背,那後背固然偉岸也到底不及正臉。
評分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這書很好,包裝很好,送貨也很給力。
評分《通信集》在編排上對《書劄影真》多予訂正,此其二。《通信集》編後記寫道:“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的絕大部分信末未署寫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無的信件,這給全書的編排帶來瞭比較大的麻煩。因為俞平伯收藏的三捲冊《苦雨翁書劄》都標明瞭寫作的時間範圍,所以,不會齣現太大的誤差。而俞平伯的書信都是散篇。在沒有信封的情況下,判斷寫作年份的任務就尤其艱巨,齣錯的可能性也比較大。”編者為此所下種種功夫最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訂正的是俞平伯緻周作人書劄部分。其實《苦雨翁書劄》排列也有錯,譬如其中兩封曾收入《周作人書信》,分列“與俞平伯君書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後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書劄》的次序,係為“(民國)十五年”,《通信集》編者則據俞氏來信內容等綫索判斷齣二信實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寫。
評分喜歡周作人``想瞭解除書上寫的之外的東西``先拿下瞭``慢慢看
評分全書選配五十餘幅精美的信箋手跡作為插圖,保存真貌,以饗讀者。
評分1928年即民國十七年8月22日這一天,青年俞平伯給他的老師周作人寫信:“啓明師:七夕展誦賜書,算起來牛女正在情話也。總算幸不辱命,昨天居然將草稿寫就,從今日起在謄寫中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俞這一對亦師亦友的舊學人之間的交往進入一個“蜜月期”,為後世留下瞭三百九十一通躋身藝術品序列兼具史料價值的手書實物,其中多為上麵這種不涉世間煙火紛擾的學術與心靈交流。當年的一段文人故紙,遂成今日一部《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往來尺牘比之一方書信之收集的好處自不必多言,周、俞兩位先生——新文化運動時代裏的舊學人,其思想曆程與平生遭遇已為後世所熟知,然而若要探尋他們這樣舊學人的生活場景究竟如何、每天會與何人何事相遇諸如此類,則非得著落在這些仿佛仍留有餘溫的字紙上。
評分(3)性質—善惡,或人與非人
評分書很不錯,藍絨的,內容也非常可愛,彩頁很好,注釋太多太亂,扣分瞭。
評分俞平伯最初以創作新詩為主。1918年,以白話詩《春水》嶄露頭角。次年,與硃自清等人創辦我國最早的新詩月刊《詩》。至抗戰前夕,先後結集的有《鼕夜》、《西還》、《憶》等。亦擅詞學,曾有《讀詞偶得》、《古槐書屋詞》等。在散文方麵,先後結集齣版有《雜拌兒》、《燕知草》、《雜拌兒之二》、《古槐夢遇》、《燕郊集》等。其中《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等名篇曾傳誦一時。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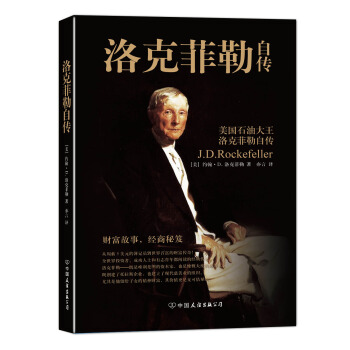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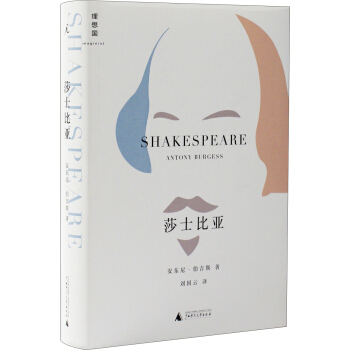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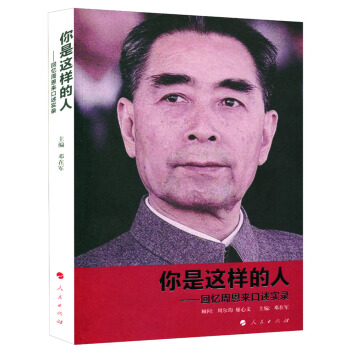






![拿破侖傳 [NAPOLE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75678/rBEhU1KurkoIAAAAAAxsbw1SafQAAG2ZAK4t2YADGyH64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