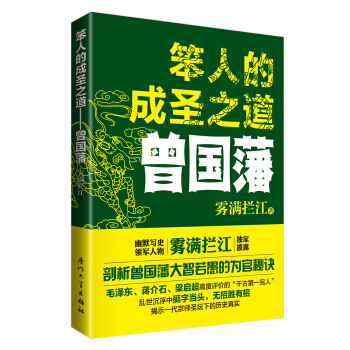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
内容简介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和俞平伯(1900-1990),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
周作人,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大念书时,师从周作人,此后散文创作受其影响至深,在古典文学研究和红楼梦研究领域,有独树一帜的贡献。
孙玉蓉,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等学术著作,80年代与俞平伯交往颇多,对俞平伯以及相关的文化交游非常熟悉,并发表《周作人与〈同声月刊〉》等多篇论文。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为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
—— 董桥
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他们的学问及创作,都是殊为重要的遗产。两人既是师生关系,也系朋友。彼此的交往中留下许多重要文献。这些对了解那个时代的风气、学术水准、人文地理,都是有益也有趣的资料。 整理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彼此的心境和京派文化的特征,对后人认识现代文化史是重要的参照。
整理者孙玉蓉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著有《俞平伯年谱》等著作。谙熟资料,常于掌故,治学严谨,文笔亦佳。
—— 孙郁
全书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在注中发掘了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编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一文。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那一方面去?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歌词曲还有人在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那里去呢?”编著者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的途径。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还全无年月日,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和认真的态度,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年份,还按照编年以及往来次序编排,使读者能深入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背景和意趣,更修正了之前学界和出版物的一些谬误。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书写。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
—— 刘绪源
目录
凡例周作人小传
俞平伯小传
1921年
3月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922年
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3月3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附录:俞平伯致周作人(发表稿)
1923年
8月5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9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924年
8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9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8月1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6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5年
1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2月26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4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5月2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1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7月29日或30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8月2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2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6年
2月1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精彩书摘
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 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 1卷第 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 ’”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 (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
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
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
(1)程度—感染底深浅
(2)范围—感染底广狭
(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
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节上,先生以为善底概念也很游移,我也承认。但我却以为比美,似较清切一点;至少在生物学、人生哲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也尽可应用。至于说善容易引起误会,则美也未尝不如此。譬如现在诗坛底反流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旧体诗比新体诗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断,即可以说,你们做的诗,是鼓吹不正当的行为,即不是积极的有害,也总是消极的有害,所以要不得,岂不痛快?若说善可以引起“劝善书”的误会,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以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总之,名实底淆混,在有几千年历史的言语文学,是不可免的,我们只有严切地解释规定,这就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节,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文艺,偏于音乐一方面;虽是一种揣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极承认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克氏所谓“了解艺术须有相当的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广义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做艺术训练。我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文艺作品。我相信文艺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不是一种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东西。)
但我并不预料诗底平民化,为平民所有,在于现代,或最近之将来。我只承认这是正当趋势,是万人所想望的事,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事。我并不以为现在的民众,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艺。所以说:“凡诗能以平民生活做题材的,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并不是说已为平民所了解。我也并不是就事实上,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不过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去打破,不能认为固定而不可变的。
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能如此,而将来可以呢?(这本是一种希望。)我在那篇文内,约略归纳于四项事实;虽明知一偏不全,但所举的确是实在的状况,且都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的状况。教育的普及,即是克氏所谓受相当的训练。大部民众,既受了相当的训练,自然可以接近文艺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武断一定不能呢?
我极力抗争压迫个性,去舍己从人,正和先生一样迫切。我也是仅仅希望民众能了解艺术,并不是主张去迁就他们。但我却总想达到这个希望,不是仅仅地去空想着。怎样办呢?只有两方面:(1)社会底改造。(2)文学者跑向民间去。这第二项,尤是我们能做而应做的事。
关于先生那文,我所有的感想,已拉杂地写下了,且复先生那封信。这信上我最信服的有一句话,就是“文学底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这虽足以使从事文艺的人短气,但事实上确是如此。不过须注重“极大无限”这两词,方无引起误解底流弊。
什么是“道德”“不道德”,有许多地方本很难说(如恋爱上占有的欲望)。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却也是显明的,如先生所举的这几种,似乎很可断然地去排斥。
我想,我佩服托氏底地方,未必便较先生更为广大,所以就止于此,不再赘说了。
《自己的园地》有一句话,我还有些怀疑,就是“逆路得救”。恕我也不免有绅士气了!
《新潮》出版太慢,诗早寄,似不适用;俟集稿前数日,当搜索近作奉上。因《诗》底关系,我忙得很,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而诗又不是可以强逼吟成的,真是有些窘了!近成诗一首,名《乐谱中之一行》,比较的可以惬意。日内即寄伏园,或在《晨报》上发表。(伏园,即孙伏园(1894—1966),《新潮》杂志编辑,后任《晨报副刊》主编。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任《京报副刊》编辑。在本通信集中,伏园、万羽、孙公、伏公、伏老等称谓兼而用之。《乐谱中之一行》发表于1922年4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新诗集《西还》。)
日来觉儿时的光景,甚可回忆,任其遗忘,未免可惜了。近着手草一诗,名曰《忆》(《忆》为俞平伯的第三本新诗集,自1922年春开始创作,共成诗三十五首,均为回忆“儿时的光景”,北京朴社1925年12月出版作者手写影印袖珍本。),亦是零零碎碎的,但其中也含有五六节的诗在内。
五月内须来京一行,可以奉诣。
学生平伯
三、卅一,杭州城头巷三号
先生给我这封信,拟节录在《诗》上发表,作为通信,请原宥。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仅凭这几个字,就足以让我心生向往。我仿佛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两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以笔为媒,互通心意。周作人,那个将生活情趣与文化思考融为一体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总是透着一股淡然与睿智。而俞平伯,那位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有着深刻造诣的学者,他的学识严谨而又充满人文关怀。这两位巨匠的通信,必然是思想的交锋,是灵魂的对话,是那个时代文化脉络中一份珍贵的印记。我能想象,周作人或许会在信中,用他那特有的温和而又略带戏谑的笔调,描绘他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对人情世故的体悟,亦或是寄托一些家国情怀的淡淡忧思。而俞平伯,则可能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周作人探讨学术上的见解,分享他对古籍的精读心得,亦或是对当下时事的理性分析。这书名,仿佛是一张古老的地图,指引着我前往一个充满智慧、情趣与历史厚重感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两位大师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
评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书名如同一串古老的钥匙,轻轻一转,便能开启一段尘封的时光。我虽未曾阅读书中的具体内容,但仅凭书名,便已构建起无数关于他们的想象。周作人,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散发出一种温润而又带着几分疏离的魅力;俞平伯,以其对《红楼梦》的深度研究,展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两位学养深厚、性情各异的文人,他们的书信往来,必然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情感的交流。我想象着,在那些字迹里,或许有他们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对时代变迁的忧虑;或许有他们对古典文学的细致品味,对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周作人或许会用他那看似闲适的笔调,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传递着一种对生命的深刻体察;而俞平伯,则可能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周作人探讨学术难题,分享研究心得。这书名,就如同一张邀请函,邀请我走进那个充满智慧与情怀的年代,感受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聆听他们最真实的心声。
评分捧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的书名,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尚未真正翻开书页,但仅仅是书名所蕴含的重量,便足以让我心生敬意。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思想交流,必然是那个时代文化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猜想,这本通信集,绝非是简单的信件堆砌,而是一部鲜活的文学史料,一幅生动的文人画卷。字里行间,或许跳跃着他们对于诗词歌赋的深刻见解,对于历史典故的独特解读;或许流淌着他们对时事变迁的敏感观察,对社会现实的深邃思考。我可以想象,周作人会用他那特有的散淡、幽默的笔调,描绘他对生活的细致体察,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而俞平伯,想必会以他严谨、深厚的学术功底,阐述他对经典文学的精辟分析,对治学之道的孜孜以求。这书名本身,就像是一扇门,推开它,就能进入一个充满智慧和情趣的文人世界,与两位大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交流,汲取他们的学识,感受他们的风骨。
评分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本书,我的心情就像是在一个温煦的午后,斜倚在书房的窗边,看着光影在泛黄的书页上跳跃。周作人和俞平伯,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承载着一段历史,一段文化,一段文人的情怀。虽然我手中捧读的并非是他们具体的通信内容,但光是这书名,便足以勾起我无穷的遐想。我想象着,在那兵荒马乱、世事变迁的年代,两位挚友,一位在故都的深宅大院,一位在江南的烟雨楼台,是如何以笔墨为舟,在岁月的河流中传递彼此的心意。他们的书信,定然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是对时局的忧思,是对文学艺术的探讨,是对人生哲学的感悟。我仿佛能看到周作人那温和而又带着些许玩世不恭的文字,描绘着日常的琐碎,寄寓着深沉的家国情怀;也能想象到俞平伯那儒雅细腻的笔触,抒发着对古典文化的眷恋,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这本书,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个时空胶囊,封存着那个时代的温度、那个时代的精神,等待着我去开启,去感受。我期待它能带我穿越回那个遥远的年代,聆听两位巨匠的呼吸,品味他们独特的人生况味。
评分读到《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个书名,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两位民国时期文化巨匠的形象。虽然我还没有机会细读书中的内容,但仅仅是书名本身,就足以引发我无限的遐思。周作人,那位以“苦雨斋”闻名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种温润如玉的质感,充满了对生活细微之处的观察和感悟;俞平伯,那位以《红楼梦研究》声名鹊起的学者,他的学问严谨而又富有情致,对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两位朋友之间的通信,我想一定充满了思想的火花和人生智慧的碰撞。或许,在那些字里行间,会流淌着他们对当时社会动荡的忧思,对国家前途的关切;或许,会激荡着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探索,对于哲学思想的辩论。我可以想象,周作人会在信中用他那标志性的幽默和洞察力,描绘生活中的趣事,或是抒发一些淡淡的愁绪;而俞平伯,则会用他那严谨的学者风范,与周作人探讨学术问题,分享他对经典著作的独到见解。这本书名,就如同开启了一扇通往那个逝去时代的窗户,让我得以窥探两位大师之间真挚的友谊和深邃的思想。
评分俞平伯与叶圣陶、顾颉刚在一起
评分当然,要给两位先生的书信集加以妄论谬品,恐怕会令当时同时欣赏过他们文字的很多名士从坟墓里笑出声来,当世之时,能写到如此境地,彼此能交流到如此知音的层次,恐怕再无第二对了。
评分 人们喜欢收藏尺牍,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牍,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牍集,是一种美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评分47、又
评分书是我们的知心好友。当淋浴在灿烂的阳光中,膝上摊开一本书,闻着纸上散发着的油墨清香,旁边放上一杯水,听顽皮的风娃娃吹开书页的美妙声音,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在我孤独的时候,书陪伴着我,使我感到温暖;在我伤心时,书使我感到快乐,让我感觉世界是多么有趣。
评分首先在这里要感谢爸妈,感谢社,感谢:..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感谢让我们有了阅读的机会,拿到快递过来的书,心情很是激动,估计爱书之人心情都跟我一样。回到家,妞妞看到我拿的书,高兴极了。这次拿到两本书,这本是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大开本的书,纸质很好,色泽饱满,排版也很舒畅。每本故事的寓意都很好,自己拿到书先看也爱不释手。:..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的故事,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配上肆意奔放的绘图风格和极具教育意义的情节植入,在打开想象的翅膀同时,还能学会一些道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魔法师,韵文式的行文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强烈的节奏感更能帮助记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经典书。故事叙述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我就是我。也许我并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喜欢这样做。高呼三声吧,我就是我!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
评分 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够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
评分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牍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牍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评分泰山不辞抔土泥瓦而能巍峨屹立,长江不弃涓涓细流才成浩瀚汪洋。广泛读书,我方吸收,同现实生活结合,方能臻于博大精深。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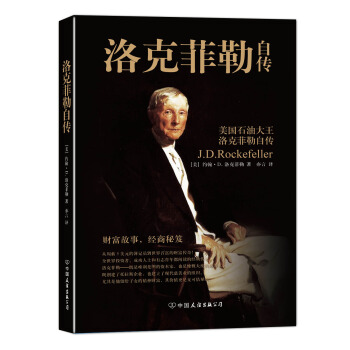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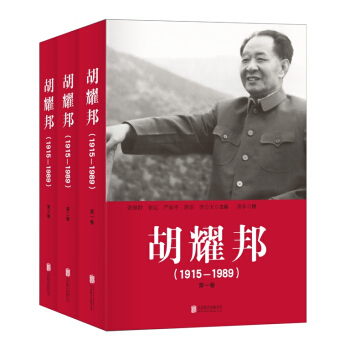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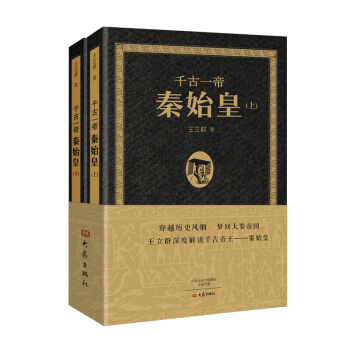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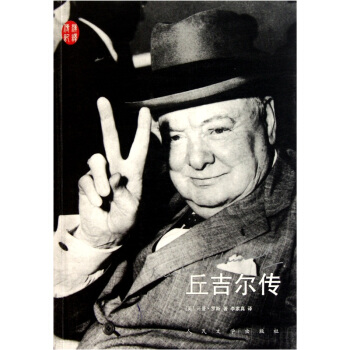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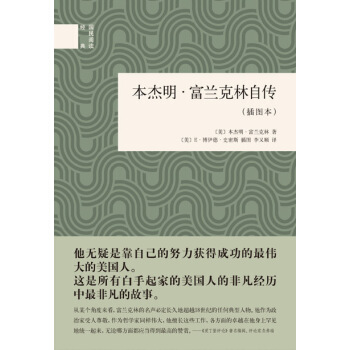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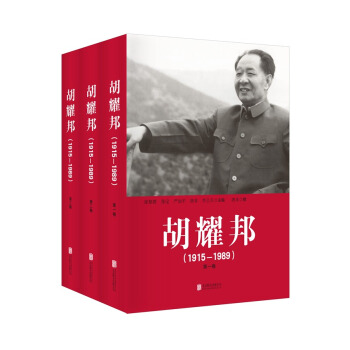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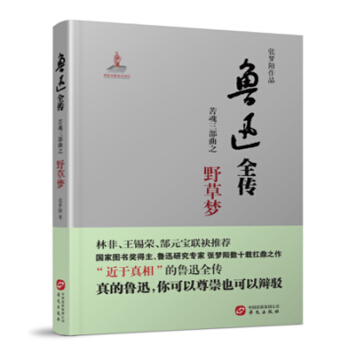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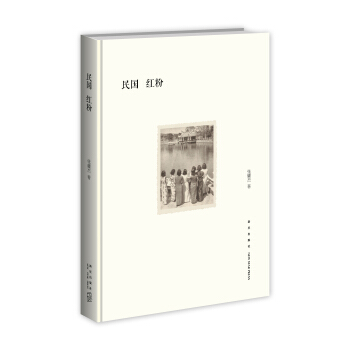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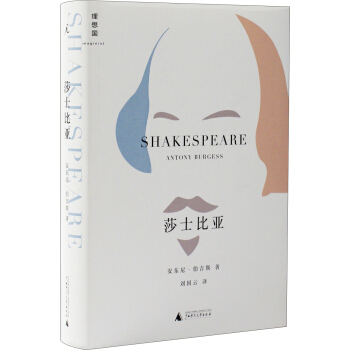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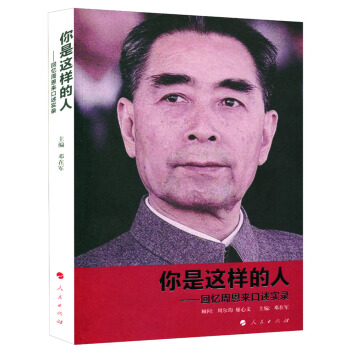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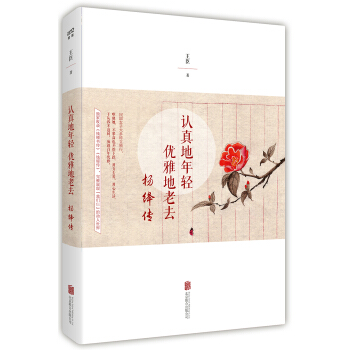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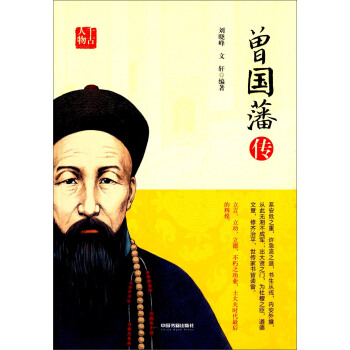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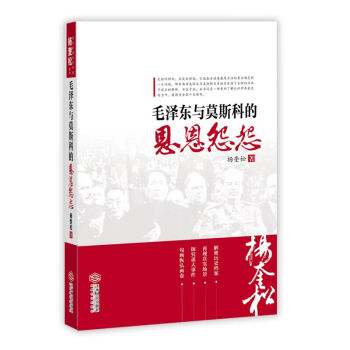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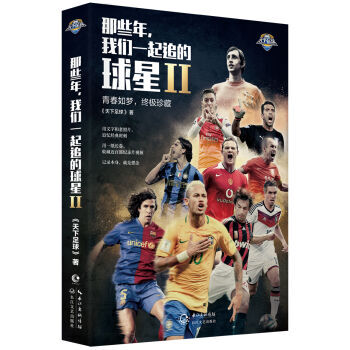

![拿破仑传 [NAPOLE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75678/rBEhU1KurkoIAAAAAAxsbw1SafQAAG2ZAK4t2YADGyH6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