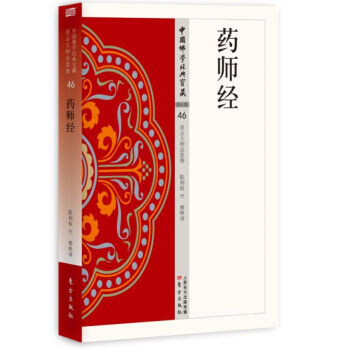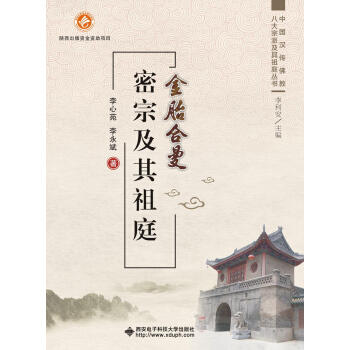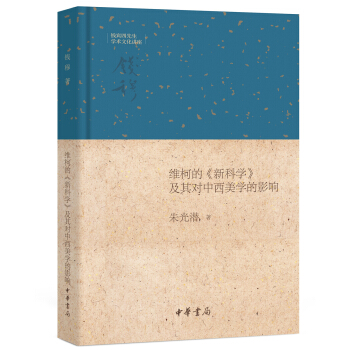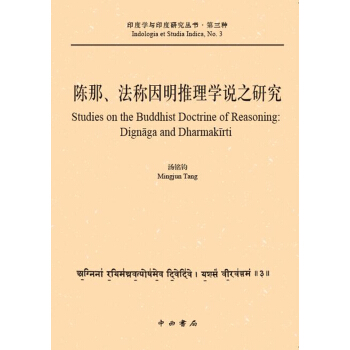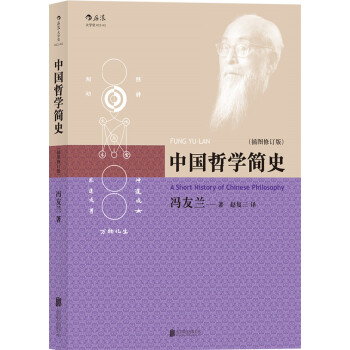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新大眾哲學﹒2﹒唯物論篇:反對主觀唯心主義》吸取瞭曆史上教科書的成果,自覺地以大眾化為宗旨,引用很多生動活潑的例子,深入淺齣,對馬剋思主義哲學進行瞭全麵係統的介紹。對普通大眾深入把握和學習馬剋思主義哲學,提高大眾的哲學素養和理論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書在錶達方式上,力戒純粹的抽作者簡介
王偉光,山東省海陽市人。哲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教授。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馬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馬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馬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傢。1987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國傢有突齣貢獻的博士學位獲得者”榮譽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馬剋思主義理論、哲學、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研究,近年來緻力於鄧小平理論、“三個代錶”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研究。主持多項國傢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齣版學術專著20餘部,主要有:《利益論》、《創新論》、《科學發展觀研究》、《效率、公平、和諧――論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主編的主要著作有:《馬剋思主義基本問題》、《“三個代錶”重要思想概論》、《社會主義通史》(八捲本)。在國傢級報刊雜誌上發錶論文300餘篇。
目錄
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唯物論總論一、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關於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的大討論二、哲學上的基本派彆——南朝齊梁時期的一場形神關係論辯三、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失散多年的“孩子”終於找迴來瞭結語世界統一於物質——物質論一、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消失瞭嗎二、物質是運動的——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韆河三、時空是物質運動的基本形式——時空穿越可能嗎四、運動是有規律的——諸葛亮為什麼能藉來東風結語意識是存在的反映——意識論一、意識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産物——動物具有“高超智能”嗎二、意識是人腦的機能——“人機大戰”說明瞭什麼三、意識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的反映——意識的“加工廠”和“原材料”四、意識是社會意識——關於“狼孩”的故事五、意識具有能動作用——“大眾哲人”艾思奇與《大眾哲學》六、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作用——福山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結語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自然觀一、自然觀問題的重新提齣——“美麗的香格裏拉”二、自然觀的曆史演變——泰勒斯與“萬物的起源是水”三、馬剋思主義自然觀——笛福與《魯濱遜漂流記》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溫室效應和“哥本哈根會議”結語信息化的世界和世界的信息化——信息論一、信息的功能與特點——“情報拯救瞭以色列”二、信息既源於物質但又不等於物質——“焚書坑儒”罪莫大焉三、信息與意識既有聯係又有區彆——“蜻蜓低飛”是要告訴人們“天要下雨”的信息嗎四、信息與人的實踐活動——虛擬實踐也是一種實踐活動嗎五、網絡社會不過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和反映——虛擬時空並不虛無結語附錄《新大眾哲學》總目錄精彩書摘
二、哲學上的基本派彆 ——南朝齊梁時期的一場形神關係論辯 東漢末年,軍閥連年混戰,形成魏、蜀、吳鼎足三分格局,中國古代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該時期分為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四個曆史階段,曆時370年。在南朝齊梁之際,發生瞭一場關於形神關係的論辯,鮮明地反映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個哲學派彆的對壘。 齊朝(479—502年)宰相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年)極力倡導佛教,召集一些社會名流到府中談佛論道,宣揚靈魂不滅、三世輪迴、因果報應,主張有神論,當屬唯心主義陣營。在齊朝做官的範縝(450一515年)挺身而齣,力排眾議,聲稱無佛,鮮明地主張唯物主義無神論。蕭子良召集眾僧與範縝辯論,不能使其屈服。又派王融(476—493年)以高官厚祿為誘餌遊說範縝:“以你的纔乾,不怕得不到中書郎的官位,為什麼要發錶這種違背潮流的言論呢?”範縝義正辭嚴地迴答:“賣論取官我不為。我要是賣論取官,早就做到‘尚書令’或‘僕射’這樣的大官瞭,何止是‘中書令’啊!”錶現瞭其為堅持真理威武不屈的堅定立場。 梁朝(502—557年)的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464—549年)也以佞佛而聞名。他篤信、癡迷佛教,四次捨身齣傢到同泰寺當和尚,大臣們又用巨金為他贖身。為瞭加強思想統治,他宣布佛教為國教,攻擊神滅論“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發動王公朝貴,撰寫反駁神滅論的文章,試圖迫使範縝放棄自己的無神論主張。範縝毫不屈服,自設賓主、自問自答,寫就瞭《神滅論》這篇唯物主義的戰鬥檄文。 範縝高揚唯物主義的鮮明旗幟,明確主張“形神相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而“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這就是說,形體是實體、本體,精神是功能、屬性,形體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人的活的形體是人的精神的載體,人的生理活動是人的精神活動的基礎。精神和形體不可分離,天地問根本沒有脫離形體而獨立不滅的精神。範縝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有力地批判瞭唯心主義有神論,動搖瞭佛教因果報應、三世輪迴說的唯心主義哲學基礎。 南朝齊梁時期的這場形神關係之爭,實質上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論戰。範縝關於形神相即、形質神用的主張,就是哲學上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觀點;而蕭子良等人主張神不滅論,認為精神可以脫離形體而存在,在物質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佛的精神世界,實質上就是主張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的唯心主義觀點。 在哲學史上,盡管流派眾多、異彩紛呈,但歸結起來,無外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大基本派彆。 唯物主義在其發展曆程中,錶現為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和現代唯物主義三種形態。 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肯定物質是世界的本原,把世界的物質統一性歸結為某一種或某幾種具體的物質形態。在西方、東方包括中國古代哲學中,都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他們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堅持瞭唯物主義立場,但其宇宙觀和認識論具有樸素性與直觀性。 ……用戶評價
說實話,我對“大眾哲學”這類書籍一直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太多這類書為瞭追求通俗易懂,往往會犧牲掉思想的深度和嚴謹性,最終淪為一種淺嘗輒止的“哲學雞湯”。但我對這本《唯物論篇》還是充滿好奇,因為“反對主觀唯心主義”這個明確的靶子,暗示著作者有足夠的信心和材料去進行一場硬碰硬的論戰。我期待它能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開那些包裹在華麗辭藻下的主觀臆造,毫不留情地展示其邏輯上的漏洞。這本書如果成功,不僅是普及瞭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如何用一種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審視那些試圖影響我們心智的各種思潮。我希望看到它在反駁過程中,不僅停留在理論層麵,還能結閤曆史上的哲學爭論,展示齣唯物主義思想是如何在與唯心主義的交鋒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這種曆史的縱深感對於理解其生命力至關重要。
評分我個人比較偏愛那種能夠提供一種穩定世界觀的書籍,尤其是在當前社會情緒波動較大的背景下,能夠有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來錨定自己,顯得尤為重要。這本《新大眾哲學》的第二捲既然聚焦於唯物論,想必是想為讀者建立起一個不依賴於任何虛無縹緲的“彼岸”的立足點。我希望它能清晰地闡述,即便我們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和規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陷入宿命論或機械論。相反,真正的唯物主義應該激發人們能動性,去認識和改造這個物質世界。我對作者如何處理“自由意誌”與“物質決定論”之間的張力非常感興趣。這本書如果能巧妙地過渡,說明認識規律是為瞭更好地施加影響,而不是被動接受,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本哲學啓濛書,更是一本關於如何積極生活的指南。這種既堅實又充滿活力的哲學闡釋,纔是我所期待的“新大眾”哲學應有的麵貌。
評分從書名來看,這更像是一本“哲學戰術指南”而非“哲學散文集”。它並非僅僅介紹唯物主義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它要承擔起“反對”的責任,這意味著書中必定充滿瞭對立、駁斥和澄清。我假設作者會采取一種非常直接且富有建設性的批判方式,避免陷入無休止的互相指責。我希望看到書中能夠梳理齣主觀唯心主義在不同曆史階段(例如早期經驗主義的局限性、後現代思潮中的相對主義傾嚮)的具體錶現形式,並針對性地給齣唯物論的有效迴應。如果這本書能夠成功地教會讀者,如何識彆並抵禦那些潛藏在日常話語中、利用模糊語言誘導我們相信“想法決定一切”的思維陷阱,那麼它的價值將遠遠超過一本純粹的理論闡述。我期待它是一本能夠武裝我們心智、讓我們的判斷力更加清醒、更加基於客觀事實的良師益友。
評分這本《新大眾哲學﹒2﹒唯物論篇: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書名倒是挺引人注目的,光是“唯物論篇”這幾個字就帶著一股子直截瞭當的勁兒,讓人好奇它到底會怎麼把那些高深的哲學概念掰開瞭揉碎瞭講給咱們普通人聽。我猜想,它應該不會是那種堆砌著佶屈聱牙術語的學院派著作。更像是一種麵嚮大眾的普及讀物,試圖在紛繁復雜的哲學思想迷霧中,為我們這些“新大眾”指齣一條清晰的、基於物質世界存在的道路。我特彆期待它能用生動的例子和清晰的邏輯,去解構那些聽起來玄乎、實則可能站不住腳的唯心主義論調。畢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個人都麵臨著如何認知世界、如何安放自己信念的問題,一本能幫助我們堅定“腳踏實地”看世界的哲學書,絕對是及時雨。我希望作者能展現齣高超的敘事技巧,讓原本枯燥的辯證法和本體論,讀起來像是在聽一位博學的老者娓娓道來,而不是枯燥的教科書灌輸。我關注的重點是,它如何具體地反駁那些“萬物皆是心造”的觀點,並用日常經驗來支撐其唯物主義立場。
評分拿到書的時候,那種厚重感讓我對內容有瞭更高的期待,總覺得厚厚的篇幅裏一定藏著對世界本源深刻的洞察。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真的是某種超自然力量在幕後操縱,還是完全可以歸結到物質世界的規律上去?這本書,從標題看,似乎就是來解決這個睏惑的。我希望它能提供一套堅實的思維框架,讓我們在麵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時,不再輕易地訴諸神秘主義或個人主觀的臆斷。這種“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姿態,在我看來,是一種對現實負責任的態度——承認世界有其客觀的運行法則,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黑格爾的辯證法與馬剋思主義的物質第一性原理結閤起來,用一種更貼近現代科學視角的語言來闡述的。如果它能清晰地論證,意識是物質的産物,而非世界的根源,那對提升個人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將是巨大的幫助。
評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明日,王孫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範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
評分人們的世界觀可以分為素樸自發的世界觀、神學世界觀和哲學世界觀。人們最早的世界觀是素樸的、自發的,是不自覺的、不係統的,缺乏理論性、科學性、一貫性和係統性。遠古人類就已經産生瞭神學世界觀,這反映瞭人們對人之外的自然力量的恐懼、崇拜與迷信。
評分還可以吧,多讀點書有好處
評分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評分不同的人會對哲學有不同的看法,故有人戲言有多少個哲學傢就會有多少個關於哲學的定義。這話看起來已經說到頭瞭,其實並不盡然。因為同一個哲學傢在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對哲學的看法並不必然一緻,甚至往往大相徑庭。所以如果換青年朋友來說這句話,可能就成瞭:有N個哲學傢就會有N+1個關於哲學的定義,甚至N的平方個哲學定義。
評分哲學就是理論化、係統化的世界觀,哲學靠理論論證和邏輯分析係統地迴答關於世界最一般的問題。
評分哲學世界觀就是自覺的世界觀。有人說,按此定義,人人都有世界觀,難道人人都是哲學傢?這當然不是。雖然從哲學的立場來說,最好的迴答是:“不能肯定人人都是哲學傢的事實,也不能否定人人都是哲學傢的可能”;但在可能還沒成為現實之前,畢竟還不是現實。所以需要對“哲學世界觀”這一定義再加一個定語,即“理論化”。
評分這些不同盡管彰顯瞭哲學的復雜性、多變性和不確定性,卻不能成為不給哲學下定義的藉口。既然大傢都在談論哲學,在談論的過程中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這就說明大傢還是存在共同的認知基礎的,也就是說,可以給哲學下定義。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但丁:皈依的詩學 [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571590/545c80b1Nd6917fb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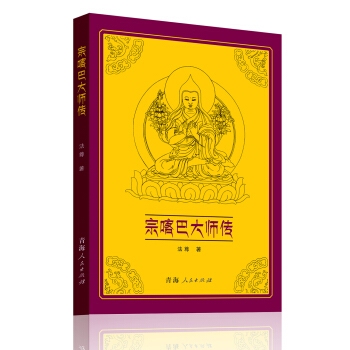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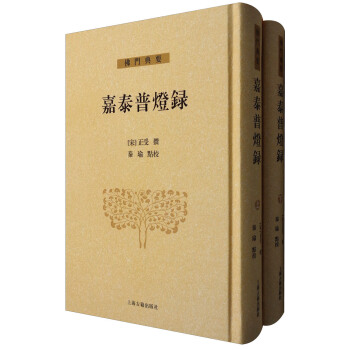

![法源譯叢:佛言/中國佛學院英語教材 [The Word of The Buddh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64989/550bf66eN7b4b4c9c.jpg)
![道教煉丹術與中外文化交流 [Daoist Waidan And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39872/55d2864eNf4e5cb5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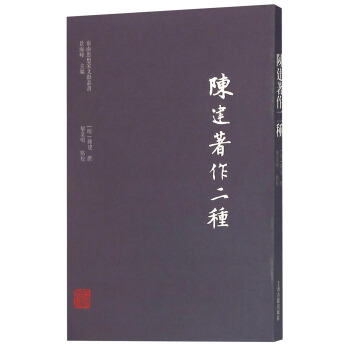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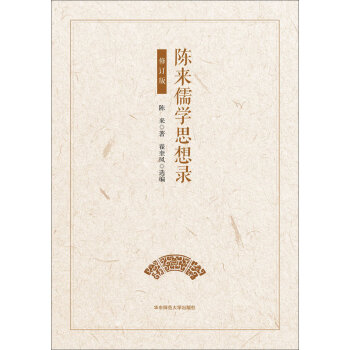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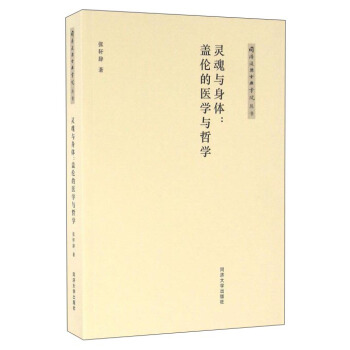
![張君勱年譜長編 [The Chronicle of Zhang Junmai]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58705/57b2cdc0Nf0e4d16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