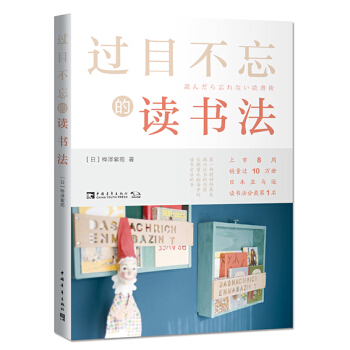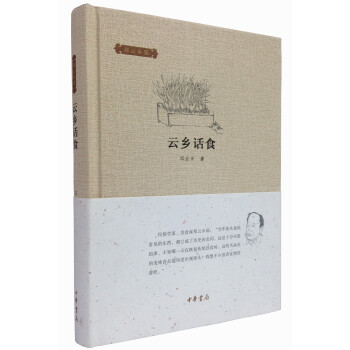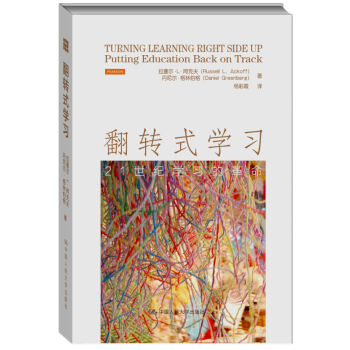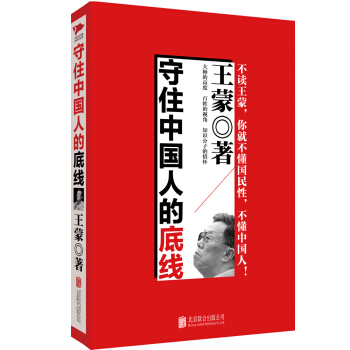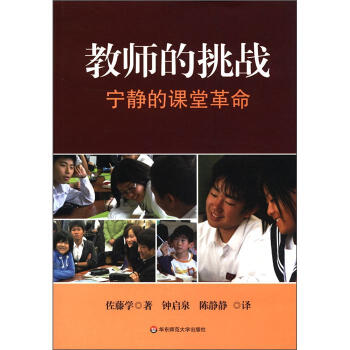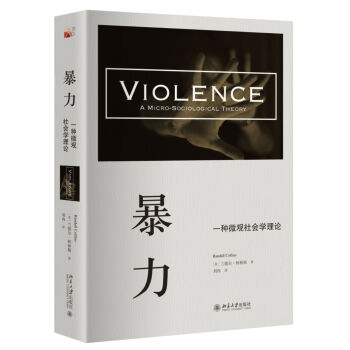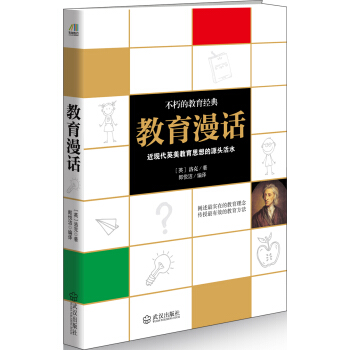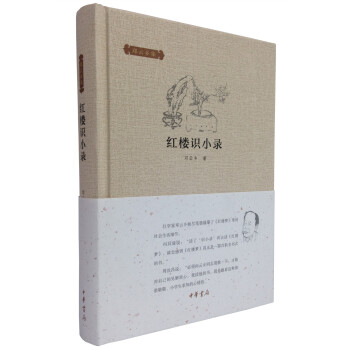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红学家邓云乡极尽笔墨描摹了《红楼梦》里的社会生活细节。读过邓云乡先生的“红学四书”(《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忆》),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这部古典中国的百科全书。
内容简介
《邓云乡集》十七种之一。邓云乡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红学家邓云乡先生从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小物说起,将因年深岁改,今人已难考实的许多事物加以描述,仿若一座别致的博物馆。作者以小识大,汇释难懂之物、费解之事,包含经济、交通、民俗、工艺、营造、园艺、饮馔等方面,将《红楼梦》细展于读者面前。
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目录
银锭与夹剪银块种种
制钱
黄金·金价
金饰·虾须镯
黄金器皿
当头·当铺
当票
死号
大廊
大庙
大庙风貌
凤姐放账
高利盘剥
抄家
抄家清单
清代各种查抄
黛玉进京
释轿之一
释轿之二
驮轿
骡车
车和骡
车围·车垫·挽具
演变和乘客
薛蟠旅行
大车·长行骡子
走骡
拜影
祭祖
搭棚
“纸札”
纸扎
“杠”与“请杠”
骑射
打围
兔鹘
射鹄子
大毛儿皮货
挂钟和打罗
帘子
扇子
“怡红夜宴图”辩
怡红院的炕
释炕
裱糊房屋
花儿匠
海棠
梅花
芍药·蔷薇
竹·笋·菱
吃螃蟹
螃蟹账
乌庄头账单
酒令
吃茶
高鹗的汤
腊八粥
风筝
鸟儿
游戏
烟火
天齐庙
薛蟠小像
宝琴诗谜
后记
附录
原版序一………………………………………… 端木蕻良
原版序二…………………………………………… 周汝昌
原版序三…………………………………………… 冯其庸
精彩书摘
凤姐放账《红楼梦》中写凤姐放高利贷,是暗写,是侧面写,常常是从对话中用几句话轻轻地点出来,一带而过,但份量却不轻,关系十分重要。这事始见于第十一回和第十六回,在十六回中写正遇贾琏回来在房中与凤姐说话时,旺儿媳妇来送私房利钱,被平儿拦住,事后对凤姐说:
那项利银早不送来……知道奶奶有了体己,他还不大着胆子花吗?
说明这利钱是凤姐私房,是体己银子放账所得利钱,是通过旺儿媳妇经手的,是平儿管理的,是瞒着贾琏的,当然更瞒着其他有关人了。
再见于第三十九回,出园途中,袭人让平儿到屋里坐,并问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平儿悄声告诉袭人:“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又告诉袭人道:
他这几年,只拿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又见于本回书后文,平儿对二门上该班的小厮道:
你这一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罢。
这里面进一步写清凤姐放账的资本,一是利用月初向账房支领大观园众人的月钱,到月底再凑别的钱来发月钱;这样每月翻滚,就等于常年这笔月钱都在为凤姐赚利钱,因此只这一笔就翻出几百两利钱。二是自己每月的月钱十两、八两攒起来,越攒越多。三是什么?平儿未说。此处平儿对袭人所说的话还是有保留的。即其他非法的资本,如馒头庵所得三千两就未说。
也写清凤姐每年的体己利钱收入,“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如果一年到了呢?最少该有一千五或者两千吧。这当然还是平儿有保留的说法,实际上仍是要超过此数的。
更写清了外面替她放账的经手人和经手人的手段。经手人旺儿也是拖拉日期,暗示也是靠这个办法来捞好处。
当时社会上面的各种债务,从地区上分,一种是北京,一种是外地,在外地还分城市和农村。这中间北京利钱最重,谓之“京债”。梁玉绳《清白士集》中曾说过:“俗间以放债为业者,京债最重,人每为所累。”而在北京的债务关系中,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一是各种商店以及银钱行业炉房、票号间的正常债务;二是私人亲朋间的友谊债务;三是前面引文中所说的“以放债为业者”的债务。这三者中,利率并不一样。第一种是正常的较低的利率,第二种更是无息或者低息的,如第二十四回中所写倪二借给贾芸钱,说明“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但第三种“以放债为业者”的债务则是重利的,倪二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对贾芸虽然说是“好街坊”,不要利钱,但对别人则不然。《红楼梦》原文说得清楚:“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这就说明“放重利债”是他的职业,赌博场是他的业务场所,喝酒打架是他这行职业的看家本领。没有这点“本领”,在当时的都城中就不能以放债为业,放出去也讨不回来。
凤姐放账,不是第一、第二种,而是第三种,即“以放债为业”式的放账。放这种账,她不可能自己出面,必须有人替她办理,替她办这种事的人,必须像倪二那样的,也就是泼皮式的人物才行。这种人就是要有本事找得到借高利贷的人,到时又要有本事把放出去的账收回来。找得到借高利贷的人也不是件容易事,都城中不比乡下的贫苦农民多,而既因生活所迫要借高利贷,又因土地关系牵连着,不怕借债人逃走,漂了账。都城大官、富商都是大笔债务来往,不会借小额高利贷,而真正贫苦、不遭遇特殊意外的人,也尽可能不沾染这些放高利贷的泼皮。因而他们要找那些最理想的借债人是不怕任何大利钱,恨不得油锅里的钱都想捞来用,而又在压力之下能够有办法还钱的人。如家里管得很严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浪荡子弟;薄有家产,突然吃了官司、锒铛入狱,急于打点花销而又缺少现钱的人家;外地晋京的土财主,被作好圈兜迷恋于嫖、赌的嫖客、赌客,类似这一些人,既敢图一时痛快,借各种阎王账,又不怕他还不起钱。但是这种“秧子”,不是到处都有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赌场等下级社会。一边摆赌台开赌,一边给赌输了、已经红了眼、急于借钱翻本的赌客放账。讨账的时候,该动软的动软的,该动硬的动硬的,可以逼债客卖房、卖地、卖妻、卖儿,甚至偷抢来还账。所以能够办这个的人,一是倪二般的地痞、泼皮,二是旺儿般的豪门恶奴。在社会势力上,旺儿这类的豪门恶奴,又比倪二这类的地痞、泼皮厉害得多。所以凤姐利用旺儿做她的爪牙,在外面放高利贷。在《红楼梦》的文字描绘中虽只聊聊数语,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不知有多少奸诈、阴险的骗局。像第十二回中贾蓉、贾蔷逼贾瑞写借据,第二十五回中马道婆骗赵姨娘写借据,类似这种骗局借约,在旺儿手下也是不会少的。
……
前言/序言
原版序一端木蕻良
《稗雅》、《释小》这一类书,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类书”,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这些作者写的,多是由于亲身体会得来的,因此,都有独到的特点。大概由于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干么不读读诗,可以多知道一些草木鸟兽鱼虫的名儿!”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陆玑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后来,又有解释得更加详细些的《广要》。不难看出,孔老夫子大概是说过这种话的。
楚辞,也是诗。因此,有关楚辞,草木鱼虫这方面的疏证,同样也是接连着出现。我们现在阅读《诗经》、《楚辞》,对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单就草木一种,就不大知道它指的是今天哪些植物了。但在屈原时代,这些植物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东西。正像《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宝玉说的那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藿姜荨的,也有叫作什么丹椒、蘪芜、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像形夺名,渐渐地唤差了,也是有的。”脂砚在这句话下批道:“自实注一笔,妙!”可见“实注”两字,也就点出是曹雪芹的行文中自释自注了。
时间不停地流去,二百年后的《红楼梦》,在我们面前,有许多事物,也可以说“年深岁改,人不能识”了。继续加以“实注”,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我国的疏证谱录这门学问,与时俱增,范围越来越广。分类成集的,篇什浩繁姑且不去说它了。但在学术界,就个人经验所及,或亲闻亲见,写出一些释文笺注的,就这个传统来说,一直没有间断过。
近年《红楼梦辞典》,以及《红楼梦注释》,也都有人努力在做。这对《红楼梦》阅读和传播,是会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这种辞典和注释,限于体例,不可能对某事某条作更多的解释。那么,《红楼识小录》,刚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些补充。
就拿“当票”这种东西为例来说罢,湘云不认识它,宝钗不但认识,而且懂行。这在当时,既反映出来两个人的家庭不一样,又反映出来两人接触事物方面也不一样。在二百年以后的今天,一些读者,不要说宝钗那样年纪的,就是三四十岁以下的,便几乎没有人认得当票是何物了。至于当号、查号、下号、死号……这些名堂,就更无从知道了。查书是查不到的,问人也很难问得着。
又比如,毛皮的分类分等,以及大毛、二毛、小毛等说法,也因时迁事异,很多人弄不清了。关东的“三宗宝”,本是家喻户晓的,单拿貂皮一项来说吧,除了邓云乡同志列举的之外,还有貂爪仁、貂翎眼等等的区别,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人能明白了。
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尚。再以服色为例。比如“福色”,是因为福康安当年喜欢穿这种颜色衣服,于是贵族世家争相模仿,使它流行一时。福康安逝世后,这种风尚自然也就随着逐渐衰落了。又比如,皮、豹皮因为海禁大开,它被西洋贵妇看中,价钱也就越抬越高。而在中国貂翎眼的皮褂子,早已不闻不见,也可以说接近绝迹了。
所以《识小录》这一类著作,不但使人能在疏证说明中,得到具体的知识,并且,还看出很多与它相联系着的社会因素来。是值得提倡的。
在这里,还须提到的,是邓云乡同志曾写过《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一文,可见他已经注意到清代的流通手段问题。这在《红楼识小录》中也有所反映。这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清代的生活提供了一些可资运用的资料。
中国的飞票单据开始虽早,但是,在清代还是以金、银、铜钱等作为日常流通手段。由于金、银的纯度不同,又有官铸、私铸的区分,再加上年代、地区的区分以及度量衡的不统一,金、银的比价就越来越不一致。钱号兑换业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兑换业也就是小型金融交易所和后代银行的雏形,利用金银的成色的差别,来划分兑换率的差别,从中谋利……这种金融业,表面上是使交换率得到平衡,实质上是有意把差别日益扩大,成色愈是千差万别,愈便于行庄谋利。
《红楼梦》对当时高利贷资本,写得比较多,对当时的重利盘剥揭露得比较透彻。在清代有的贵族,也由管家出面,开设典当,或者发放贷款。更多的,是不必开立账房铺面,就由经纪人、牵手、“跑合的”来作成,像王熙凤就是以“体己钱”来放债的。另外,她又要把“宫中钱”(府库中的钱),转化为“体己钱”,也叫小份子钱,所以,她就趁在庵堂时,把事情办妥。牵手就是老尼,在封建社会出现的三姑六婆,她们在经济方面,多半是在放高利贷撮合过程中,取得佣金或物质回报的。而她们过手作成的几乎都是宅门子里的私房钱。
又如“拜影”条,这在曹雪芹时代,是很流行的,这和“烧包袱”(烧冥钱)一样,都是当时流行的岁时风俗。与曹雪芹同时的敦诚,在《四松堂集》卷四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曾妣卧疾帏榻者三年,母日侍汤药未尝暂离,及属纩日,顾先祖曰:“妇善事我十年,无怠容,汝好遇之。”公泣受命,故终身对之如宾。每岁暮祠祭,悬曾妣影像,母对之未尝不欷歔流涕,礼数如生时,至老不衰。
这和《红楼梦》正好互为补充。
这种例证还很多,希望邓云乡同志等诸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能够继续写下去,对一般读者或者研究者,除了加深欣赏和研讨的兴趣以外,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探讨的线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北京
原版序二
周汝昌
我与云乡同志相识不算早,识荆之后,才发现他有多方面的才艺,并皆造诣高深。一九八○年春末,行将远游,出席国际红学研讨会议之时,蒙他特赋新词,为壮行色,这也许是我们一起谈“红”的开始。这是一首《水龙吟》,其词云:
世间艳说红楼,于今又入瀛寰志。衣冠异国,新朋旧雨,一堂多士。脂砚平章,楝亭器度,白头谈艺。念秋云黄叶,孤村流水,繁华记,蓬窗底。
欲识情为何物,问茫茫,古今谁会?画蔷钗断,扫花歌冷,并成旖旎。岂独长沙,还怜屈子,离忧而已。爱西昆格调,郑笺共析,掬天涯泪。
不但才华文采,即其书法,也很见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击节而赏。
从那以后,他每诣京华,必来见访,相与谈“红”。而在我的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谈“红”朋友之中,他是别具风格,独树一帜的一位。
现在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即将付梓,前来索序。我虽末学无文,却不避痴之诮,欣然为之走笔。翰墨因缘,大约就是这个意趣吧。
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原本就是一位“杂学旁收”的特殊人物。杂学的本义是“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所谓“正经”、“不正经”,也就是差不多的语意,——那是很轻蔑的语气呢!说也奇怪,至今还有以正统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杂学,这些大学问者不愿承认它是学问。正因为“正经”是大学问者之所事所为,剩下来的杂学,当然只是小焉者了——《红楼识小录》之命名,取义其在于斯乎?这只是我的揣测,云乡同志的本意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的“不贤识小”的谦语,也确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杂学其实很难,也很可宝贵,我是不敢存有一丝一毫小看它的意思在的。杂学又不仅仅指“博览群(杂)书”,它不只是“本本”上、“书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见闻多、阅历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砚,乃至书中人物凤哥儿,都是明白讲究“经过见过”的。《红楼梦》理无别解地原就是一部“经过见过”的书。这么一来,一般读者,特别是今天年轻一代的人,要读《红楼梦》,想理解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时时陷于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结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关注的却是“谁解其中味”。这问题就不“小”了呀。
我一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琐”之名,不辞“不贤”之号,肯出来为一般读者讲讲这部小说里面的那些事物。据说西方有一种别致的博物馆,专门贮藏百样千般的古代生活细琐用品。我国的博物馆,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尽管极为有趣,却不见保存,大都将历史物品毁掉,令无孑遗,以便后代子孙去做千难万难(也会千差万错)的“考证”工夫。由此想来,如云乡同志肯来讲讲这些内容,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为一个《红楼梦》的读者,我对书中许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错了而自以为懂了,比根本不懂还可怕。云乡同志的这种书,我是欢迎的,而且还觉得内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知识。这其实也不能不是红学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举一个例:南方人没见过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轿,见书中写及宝玉坐轿,便断言雪芹写的都是南方的习俗。又认为手炉、脚炉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这个北方人却都见过的、用过的。最近看与《红楼梦》同时而作的《歧路灯》,其写乾隆时开封人就坐二人小轿,乃益信雪芹所写原是北京的风俗——至少是以北京为主,其真正写南方的,委实是有限得很。像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向云乡同志来请教一下,才敢对自己的见解放心,——我读他的书,就是抱着这种恭恭敬敬、小学生求知的心情的,岂敢向人家冒充内行里手哉。
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壬戌三月初一日
原版序三
冯其庸
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已经脱稿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识云乡同志已经多年,每与他相对,其诚朴有如乡人,而言谈皆务实际,博学多识,纵贯旁通,所以我每次与他晤谈,都不觉日西,可见我们共同的癖好。
我幼年读《红楼梦》,开始毫无兴趣,简直不可终卷,是什么原因呢?一是书中描写的生活、情节、感情、思想,我无法理解;二是书中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着,种种名称实在太繁复了,我简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读起来不免有点昏昏然,可见我当时欣赏能力之低。那时我最欣赏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水浒英雄那种豪气干云,裂石惊天的气概,常常令我神往。读《三国演义》,卧龙的深谋远虑,雅量高致;刘备的知人善任,信托不疑;关、张的豪气千秋;赵云的死生可寄,都让我感到古人往矣,令人低徊。但是一拿到《红楼梦》,就多次让我废卷不可卒读,实际上那时我的知识太贫乏,阅历太浅薄,对于这样蕴藏着深刻思想和广阔内容的巨著,我一时怎么能读懂它呢?后来,我渐渐感到《红楼梦》这部书,需要疏解,需要对它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着,以及各类典故语词,进行解释。最好是能编成一部书,类似大辞典一样,凡与红学有关的词目,一并收入,进行疏注,人手一卷,读《红楼梦》就可以减去许多障碍。这样的设想多年来只是我的愿望而已。现在读了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我感到我的上述愿望已经部分实现了。
我得幸先读了《识小录》,深深感到云乡同志所写的每一事、每一物,都是切切实实的学问,而不是空论。例如关于“怡红夜宴图”,几十年来说法不一,但云乡同志却别具只眼,自出新意,指出了翠墨并未参加夜宴,掷骰子数点数时,自己包括在内。这足见云乡同志读书深细,辨事明晰。又如他在疏释“虾须镯”时,不仅对“虾须镯”的形状、制法、价值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而且连乾隆时流行金镯的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再如在说到《红楼梦》里描写的轿子时,列举了当时轿子的许多种类和等级,令人有如置身于荣、宁二府之中。至于谈到金饰、金价、黄金器皿,以及芍药、蔷薇、花木果蔬之类,亦皆言之凿凿,娓娓动听。所以读了《识小录》再去读《红楼梦》,就会感到《红楼梦》真正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它满身是学问,往往在只言片语里,就包涵着当时的许多社会现实和风习,一经解释,就会感到它的浓烈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这对于我们全面的研究《红楼梦》是大有好处的。云乡同志做了一件有补于《红楼梦》研究的非常切实的好事,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
当然,我不是说“红学”研究,可以不要理论,如果这样理解我的意思,那就完全搞错了。理论研究,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只有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和深入阐述,才能使我们对这部书的理解达到全面而深入,才能真正明了它之所以产生的时代社会条件和它的丰富内容和思想意义,才能弄清楚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它的创新的实质。总之,对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不用马列主义对它作认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把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红学”研究的主要方面,那末,“红学”研究就会失去它的重点。
但是,我们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排斥“红学”研究中的考证、注释和许多专门性的专题研究。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而后者恰好是前者的基础,离开了这些具体的研究,离开了对《红楼梦》本身的切实的理解,那末理论研究就会流于空泛;反之,“红学”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某些考证、疏解方面,那末“红学”研究就会流于琐屑而无法提高,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综合。由此可见这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而且是相互可以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因而我们不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对立起来。
还有一点,这两者的研究,无论是哪一方面,各自都会有错误和正确两种情况出现,决不会是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正确,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错误。具体来说,我们重视、提倡“红学”研究中的理论研究,但决不能认为只要是“理论”研究,这个研究就一定是可取的、正确的、无可评议的了;相反,只要不是理论研究,一涉及到考证、疏解之类的问题,就一定不可取,就一定是错误的了。我认为理论研究中,也要区分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理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都是理论,但却不能说都好;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是理论,同样也不能说都好。反之,在考证、疏解之类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不能认为凡此就一概错误,一概不要。在“红学”研究中,不应该简单地形而上学地来判断哪一种研究是正确或不正确。离开了研究的成果,离开了研究的内容和结论是很难判断这种研究的正确与否的,何况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究竟是对是错,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历史考验,才能论定其是非功过,所以匆忙地对一种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作出结论,往往不一定正确。五十年代对于马寅初的人口论的否定,就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所以学术研究中真正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红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只有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学术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就会走向某一片面或极端,就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在“双百方针”中,“齐放”和“争鸣”应该是并重的,只有“齐放”没有“争鸣”,那也是片面的,“争鸣”可以使“齐放”中的各种问题得到深化,得到全面的认识,对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可以得到纠正,而且“争鸣”本身也就是“齐放”的一种形式,所以在“红学”研究的领域里,必须正确地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那种不适当的干涉,划定某些范围,认为某些问题不能研究之类的看法和议论,并不有利于“红学”的发展。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当然首先要认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完美的科学的理论,是没有偏颇的理论。但是,关键是在真正正确地理解它和运用它,并不是一用上几句马列主义的词句,自己研究的结论就一定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比较符合马列主义的比较科学的结论,并不能保证你在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上都能如此。马列主义是一门严肃的谨严缜密的学问,没有半点侥幸的余地。然而,当你在研究中确实是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确实是努力实事求是地认真地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了深入的缜密的研究以后得出了你的结论,那么也不必害怕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讥评。要坚信在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特权,任何权威都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长期的历史实践,会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结论作出公正的评价。那些“指责”和“讥评”,它也躲不过历史检验这一关。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理论的论争,我们更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检验,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性。
最近在《水浒》的研究中,江苏大丰、兴化的同志作出了贡献,发掘出了有关施耐庵的家谱、地券、墓志等历史文献,这是极为可喜的大事,随之而来的,当然就会对这些发掘出来的东西进行研究。前些时候学术界有些同志对家谱的研究提出了种种责难,认为对作家的老祖宗,尤其是据说十七八代的老祖宗没有必要研究。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活生生的实际是不久之前诗人白居易的家谱被发现并出版和研究了,词人辛弃疾的家谱也被发现了,现在又发现了关于施耐庵的家谱,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不应该把它们抛弃而应该认真的研究。本来“谱牒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什么时候冷落下来的我不大清楚。但记得“十年浩劫”时期和稍前,是批判过一阵子农村中的“续家谱”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的。封建迷信活动当然应该反对,但学术领域里对古代作家的家谱的研究,当然不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当然是正当的史学研究。至于说十七八代的祖宗不应当研究之类的规定,我看也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不必作为定论的。
归根结蒂,在学术研究上,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信心首先是对马列主义的信心,其次是对自己刻苦研究的成果的信心。一项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多年的苦心钻研,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需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分析和综合,需要自己在公布自己的结论之前多方面进行检验。凡是下了这样的功夫的研究,凡是确实是遵循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理论的信心,不必因为有些不同的意见而感到惶然。当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决不能因此而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前后两种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淆,这是不用多说的。
我有感于当前“红学”界的某些现状,因而提出这些问题来,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要坚持实学而不尚空谈。马列主义本身就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根据事实说话,而决不提倡无补实际的“放空炮”。因为这种“放空炮”,除了表明它徒具虚声而外,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而理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解决实际问题。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陈子昂的一首诗。陈子昂处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初唐时代。现在我们正是处在“红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学”的开始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不过,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相反倒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过去的“红学”研究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著述,足可供我们研讨;新一代的“红学”研究者不断发表新著,大大开拓了“红学”研究的园地,“红学”研究的队伍空前扩大,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果真正能做到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和充分地掌握作品本身,掌握与作品和作家有关的一切历史资料,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那末,我们的“红学”研究必将会有更新的发展。
云乡同志笃实的治学态度和诚朴的文风,使我受到很大的启示,上面这些话,都是读了云乡同志的《识小录》后有感而发的,也许说的不对,希望云乡同志和读者们有以教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夜于京华瓜饭楼
用户评价
我买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但这个书名,却意外地引起了我的好奇。《红楼识小录》,听起来就像是一本带着点儿“闲情逸致”的书。我平常阅读,并不追求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大叙事,我更喜欢那种能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然后从中体会出无穷意趣的解读方式。我一直觉得,《红楼梦》最精彩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那些“小”地方。比如,某个丫鬟手里拿的物件,某个小厮跑腿时说了句什么话,或者,某位小姐在花园里不经意间的一瞥,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能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世界,塑造出立体的人物。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位细心的观察者,能注意到这些常人容易忽略的“小”事,并且能从这些“小”事中,解读出大道理。我不想被那些宏观的文学史意义,或者复杂的红学理论所束缚,我只想从一个个具体的小细节出发,去感受《红楼梦》的魅力。我期待这本书能像一位老友,娓娓道来,让我能在一杯清茶中,体会到《红楼梦》的精妙之处。
评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对于《红楼梦》更是如此。每次读完,总会留下一些疑问,总觉得有些地方,作者的笔触虽然精妙,但总有些言外之意,我未能完全领会。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泛泛而谈的解读,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这本书的题目《红楼识小录》,恰恰点中了我的“痒处”。“识小”,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深入细节的解读方式。我希望这本书能专注于那些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小”问题,那些我总是在阅读过程中被忽略,但却又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比如,为什么某个角色在某个时刻会做出某种异常的举动?为什么某个场景的描写会如此冗长?这些“小”的细节,往往能折射出作者的深意,或者人物隐藏的内心世界。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位侦探,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相,能帮我解开那些我一直无法理解的“谜团”。我期待这本书的解读,能给我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以及作者曹雪芹在字里行间隐藏的深邃思想。
评分我一直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很感兴趣,但每次读原著,总觉得有些地方剪不断理还乱,好像有很多潜藏的情感线索,我却抓不住。尤其是那些丫鬟、仆妇,她们看似地位低下,但却也是构成大观园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她们的言行举止,往往能折射出主子们的喜怒哀乐,以及那个时代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现实。所以,《红楼识小录》这个书名,立刻吸引了我。我希望这本书能专注于挖掘那些“小人物”的视角,或者说,从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入手,来解读《红楼梦》。我不想看那些枯燥的学术考证,也不想看那种过于抒情的散文式评论,我更喜欢那种有理有据,又充满了洞察力的解读。比如,书中对于某一个物件的描写,或者某一个场景的布置,它们可能在情节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却能暗示人物的性格,或者预示着某种命运的走向。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把钥匙,帮我打开那些尘封的细节,让我能更深刻地理解《红楼梦》的人物群像,以及作者曹雪芹的良苦用心。我期待它能给我带来一种“原来是这样!”的顿悟感。
评分最近翻开《红楼梦》的各种解读,总感觉很多都绕来绕去,要么就是大段引用原文,要么就是堆砌各种理论,看得人头昏脑涨。我真心希望找到一本能真正“接地气”的解读。我一直觉得,《红楼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些生活化的细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却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也透露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本书的题目《红楼识小录》,就给了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似乎暗示着,这本书不会去谈论那些宏大的主题,或者去争论什么“红学”的流派,而是会聚焦在那些“小”地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识小”,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解读方式。因为很多时候,伟大的事物都是由无数细小的部分构成的。如果能把这些“小”东西都看透了,那对整个作品的理解,自然就更深入了。我期待这本书能像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发现那些隐藏在文字间的“秘密”,并且把它们用一种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希望它能帮助我理解,为什么宝钗的“冷香丸”会那样炼制,为什么黛玉的眼泪会滴在花上,为什么袭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感到不安。这些“小”事,往往是理解人物内心世界和作品主旨的关键。
评分这本书啊,光看书名《红楼识小录》就觉得有意思。说实话,我对《红楼梦》一直是一种又爱又怕的状态。爱它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情节跌宕起伏,简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但同时,它庞大的体系、繁复的人物关系、以及那些细微之处的暗示,总让我觉得像是在迷宫里打转,总也抓不住精髓。所以,当看到“识小录”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动,这会不会是某种“入门指南”?或者说,它能帮我解开那些我一直困惑的小细节?我对那种宏大的学术研究不太感冒,更喜欢那些能让我对原著有更深理解,并且能引发我思考的解读。比如,为什么某个丫鬟的某句话会成为后来的伏笔?为什么某个场景的描写如此细腻,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深意?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一步步走进《红楼梦》的世界,而不是丢给我一堆复杂的理论。当然,我也不希望它过于浅薄,流于表面。我期待的是一种既有深度,又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的解读。这本书的作者,我虽然不熟悉,但从书名就能感受到他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细致观察。这种带着个人情感的解读,往往比那些干巴巴的学术论证更有温度,也更容易打动我。希望这本书能带给我惊喜,让我重新认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红楼梦》。
评分书已经收到,很好,京东物流,飞速发展了!
评分书内容好,包装不错,价格不优惠。
评分趁着双十一京东促销力度大,买了不少好书!
评分这是因为北京四合院的型制规整,十分具有典型性,在各种各样的四合院当中,北京四合院可以代表其主要特点。
评分书已经收到,很好,京东物流,飞速发展了!
评分我怎么就是买的电子书了?怎么就是赠品了?竟然不让发图片。
评分不知为什么邓先生没有周先生名气大呢。邓云乡这个名字应当被更多人知道才对。
评分非常好,很快就读完了。
评分邓老的作品,您值得拥有,真的,邓老的作品,您值得拥有,真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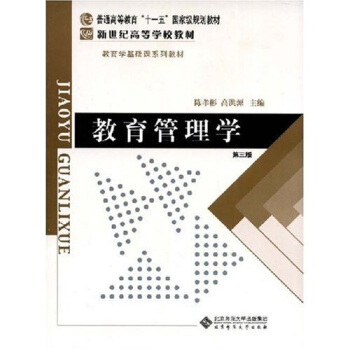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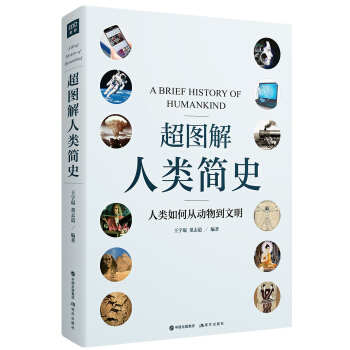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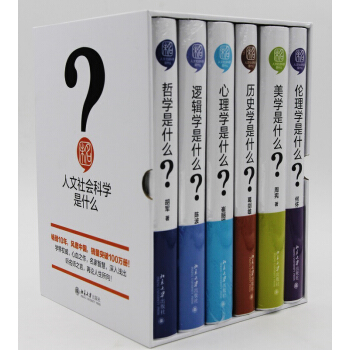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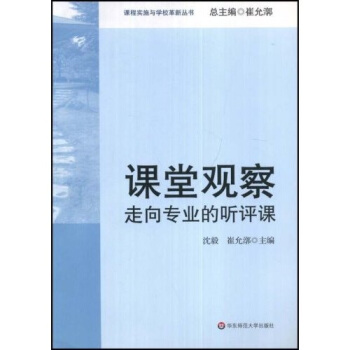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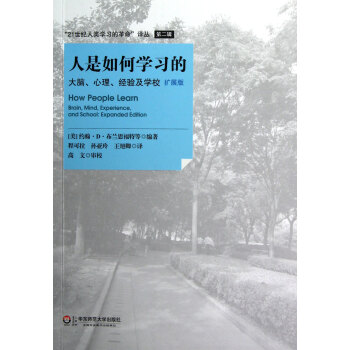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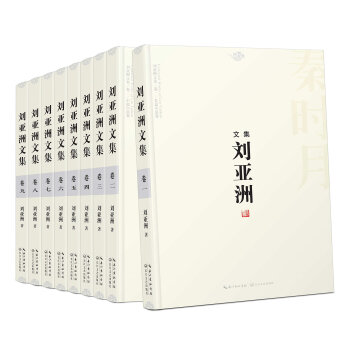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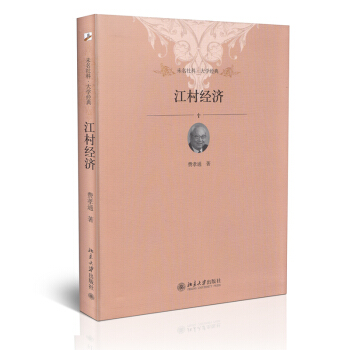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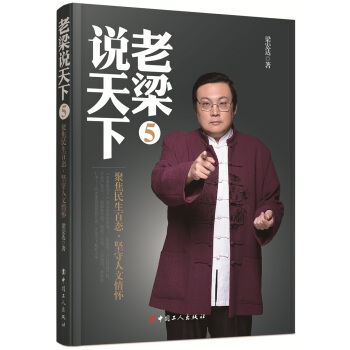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3205/5538b7e0N95c746a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