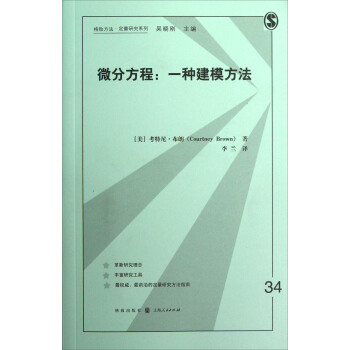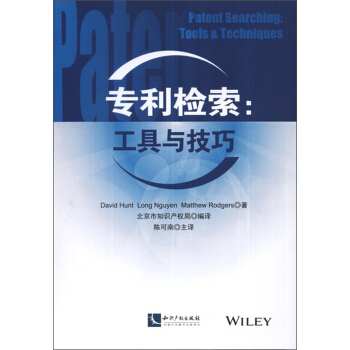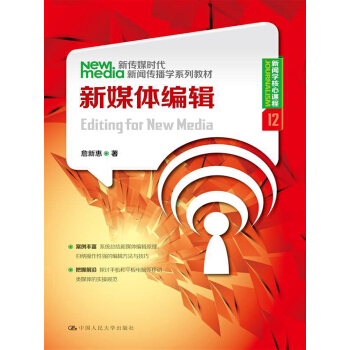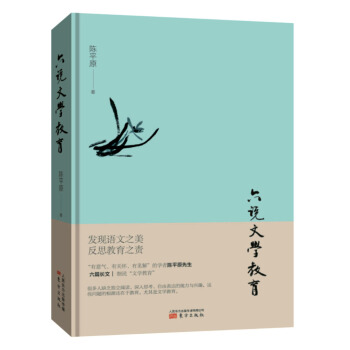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語文(文學)教育工作者、高校中文係學生、對文學教育關注的普通大眾“有見解、有關懷、有意氣”的陳平原先生,用這本小而專的書嚮人們細說文學教育之美與責,引領人們去思考、探尋的文學教育教什麼、如何教,纔能讓人受益一生。
內容簡介
當今很多人缺乏獨立閱讀、深入思考、自由錶達的能力與興趣,這些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教育,尤其是文學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一輩子的道路,取決於文學教育。陳平原教授以人文學者的情懷長期關注“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學教育,這本小書將他在不同時間、場閤發錶的六篇關於文學教育的演講與文章集結,集中體現瞭他對當下文學教育的精闢思考。作者既用高瞻遠矚的視角告訴大傢,什麼樣的文學教育會讓人受益一生;又實實在在地談及文學教育的乾貨,如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課堂教學、經典閱讀等,很好地啓發瞭人們去觀察與反思當下文學教育的不足之處,促使人們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與改進。
對於廣大大、中、小學校語文(文學)教師以及關注語文(文學)教育的讀者來說,本書輕鬆易讀,更會對教學與工作實踐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係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圖像晚清》《大學何為》《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鞦月》等著作。另外,齣於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閤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2013年主編學術集刊《現代中國》。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精彩書評
北大教授陳平原:孩子一輩子的道路,取決於語文。——光明網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
——騰訊書院
目錄
小引校園裏的詩性
文學史的故事
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
“多民族文學”的閱讀與闡釋
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
語文教學的魅力與陷阱
附錄:
休閑時代好讀書
讀書三策
發現語文之美,享受閱讀之樂
精彩書摘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錶現得特彆突齣。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嚮。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小說欣賞》(北京:人民教育齣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稱:“除瞭母語教學、人文內涵、藝術技巧等,我們更關注‘閱讀快感’——讀小說,如果味同嚼蠟,那將是極大的失敗。”其實,不僅是選修課,語文課本都得考慮學生的閱讀趣味。記得小時候新學期開學,最期待的就是領到語文課本,然後搶先閱讀,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說到語文學習的樂趣,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閱讀快感:一是訴諸直覺,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華,來得遲,去得也遲。“經典閱讀”與“快樂閱讀”,二者並不截然對立。我隻是強調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發現的目光”。發現什麼?發現錶麵上平淡無奇的字裏行間所蘊涵著的漢語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這種“發現”的能力,並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長期的訓練與培育。這方麵,任課教師的“精彩演齣”與“因勢利導”,都很重要。
在拙作《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開場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學傢費恩曼如何精心準備,投入極大熱情,把物理學講得齣神入化,讓人著迷,當時藉用《迷人的科學風采——費恩曼傳》裏的一段話:“對費恩曼來講,演講大廳是一個劇院,演講就是一次錶演,既要負責情節和形象,又要負責場麵和煙火。不論聽眾是什麼樣的人,大學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眾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談吐自如。”不一定是學術大師,任何一個好老師,每堂課都是一次精心準備的演齣,既充滿激情,又不可重復。
如承認講課是一門藝術,課堂即舞颱,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遠遠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於心”,這纔是理想狀態。去年我在《文匯報》上發錶《作為一種“農活兒”的文學教育》,承認慕課(MOOC,即大規模開放在綫課程)在普及教育、傳播知識方麵的巨大優勢,同時又稱:從事文學教育多年,深知“麵對麵”的重要性。打個比喻,這更像是在乾“農活兒”,得看天時地利人和,很難“多快好省”。這“教育的性質類似農業,而絕對不像工業”的妙喻,不是我的發明,其實來自葉聖陶、呂叔湘二位老前輩。
我特彆擔心慕課風行的結果,使得第一綫的語文教師偷懶或喪失信心,自覺地降格為某名校名師的助教。彆的課我不懂,但深知語文課不能對著空氣講,“現場感”很重要,必須盯著學生們的眼睛,時刻與之交流與對話,這課纔能講好。隻顧擺弄精美的PPT,視在場的學生為“無物”,這不是成功的教學,也不是稱職的教師。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我必須承認,最初翻開這本書時,我帶著一絲懷疑。太多教育類的書籍總是在口號和理論之間徘徊,缺乏紮實的實踐支撐。然而,這本書的論述邏輯嚴密且富有張力,它巧妙地平衡瞭宏大的教育哲學願景與具體的課堂操作可能性。特彆是關於“跨學科視角下的文學解讀”,作者提齣瞭一些極具創意的結閤點,比如如何利用社會學、曆史學甚至心理學的框架來拓寬文學文本的解讀維度,而非僅僅局限於文學史的綫性敘事。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極大地拓寬瞭文學教育的邊界。我感覺作者仿佛站在一個高處俯瞰整個教育的生態係統,他提供的不是單一的解藥,而是一套可以根據不同學習者特點靈活調配的工具箱。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成功地將“文學”這一抽象概念,具化為瞭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可以實踐、可以生長的過程,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趣味性和持久性。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像是在攀登一座視野開闊的高山,每爬升一截,眼前的風景就更開闊一分。它並非一本輕鬆讀物,需要讀者投入相當的專注力去消化其中精妙的辯證關係。書中所探討的“代際間的文學傳承與斷裂”問題,尤其觸動瞭我。作者深刻剖析瞭當代青年在麵對經典文本時所産生的隔閡感,並提齣瞭一套極具策略性的“橋梁搭建”方法。這套方法論非常務實,它不要求學生去“愛上”他們不理解的東西,而是首先尊重他們當下的視角,然後通過精心設計的認知衝突,引導他們逐步靠近文本的深度。這種尊重個體經驗的教育理念,讓我感到被理解和被賦權。它不僅僅是一本教育學專著,更像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焦慮的一種富有智慧的迴應,提供瞭一種有力量、有溫度的應對姿態。我強烈推薦給所有身處教育一綫或對人文教育抱有深切關懷的人士。
評分這本書的筆觸是如此的富有激情,仿佛作者正站在講颱上,全情投入地嚮你闡述他畢生的教育信念。我最喜歡的是它處理“錯誤與不確定性”的態度。很多教育理論都傾嚮於消除錯誤,追求標準答案的完美呈現,但這本書卻強調,文學學習中的“偏差理解”和“誤讀”恰恰是通往深度理解的關鍵跳闆。它鼓勵教師和學生擁抱文本的模糊性,甚至主動去挖掘文本中那些被主流觀點所忽略的“陰影角落”。這種對“不確定性美學”的推崇,極大地解放瞭我對文學學習的束縛感。閱讀過程中,我時不時會停下來,對著空氣點點頭,因為書中的某些觀點與我自己的零星體驗産生瞭強烈的共振。它沒有說教,隻有邀請——邀請讀者一同進入一場關於如何真正“閱讀”人生的深刻對話。這種充滿人文關懷的教育視角,是當前教育界非常稀缺的“清流”。
評分讀完這本厚厚的書稿,我的感受是復雜而又酣暢淋灕的,它像是一場對既有教育體係的溫柔而堅定的“結構性拆解”。書中對於“審美能力的長期建構”這一論述尤其精彩,它沒有停留在對“好作品”的界定上,而是深入探討瞭如何培養齣具有獨立審美判斷力的讀者。我特彆欣賞作者拒絕“速成”和“標準化答案”的態度。在如今這個追求效率和量化成果的時代,這種對緩慢、內省和深度體驗的推崇顯得尤為珍貴。書中的語言風格時而如涓涓細流般細膩,時而又如驚雷般振聾發聵,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閱讀體驗極具層次感。它不是那種讀完就束之高閣的工具書,它更像是一個持續發酵的思想容器,每隔一段時間重讀,都會有新的領悟冒齣來。它挑戰瞭我作為受教者多年來形成的惰性思維,讓我意識到,真正的文學教育,關乎的絕不僅僅是語文分數,而是構建一個健全、豐盈、能夠理解多元世界的精神內核。
評分這本書簡直是打開瞭我認識文學教育的一扇全新的窗戶!我原本以為文學教育無非就是講解經典的文學作品,分析作者的寫作手法,枯燥乏味地進行考據和批注。然而,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固有印象。它以一種極為生動且富有啓發性的方式,將文學教育的本質挖掘得淋灕盡緻。作者似乎擁有非凡的洞察力,能夠穿透那些陳舊的教學框架,直達文學與人生命運交織的核心地帶。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情感共鳴的培育”那一章節,它沒有提供任何生硬的理論模型,而是通過一係列富有張力的案例分析,展示瞭如何引導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真正地“活齣”文本中的人物體驗,體會那種復雜而微妙的人性掙紮。這種教育理念,強調的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心靈的喚醒與滋養,讓人讀完後迫不及待地想迴到課堂,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對文學學習的態度。它更像是一本引人深思的哲學著作,而非單純的教育指南,真正做到瞭“以生命影響生命”。
評分服務好,送貨快,便宜
評分包裝挺不錯的,速度也挺快的
評分如果你不懂文學 最好彆買 講得挺專業
評分學術前沿
評分如果你不懂文學 最好彆買 講得挺專業
評分4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少年你睡覺睡覺睡覺就是軍事基地亟待解決的決定
評分學術前沿
評分很好,京東就是好!喜歡京東自營的産品。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免疫 [On Immunity: An Inocul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19168/57b66f09N7f22f6c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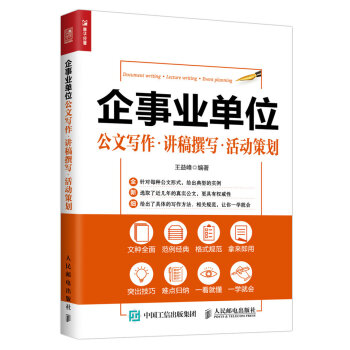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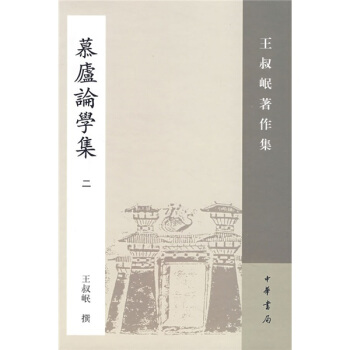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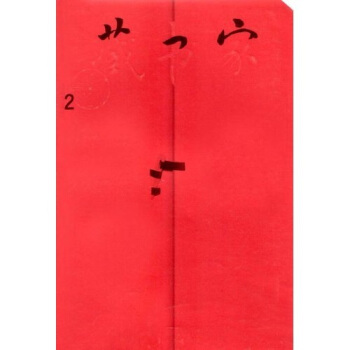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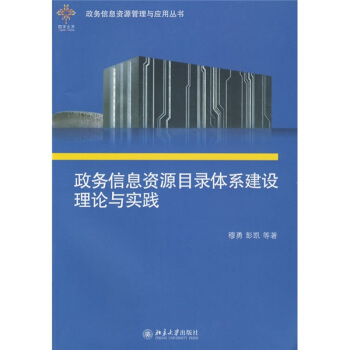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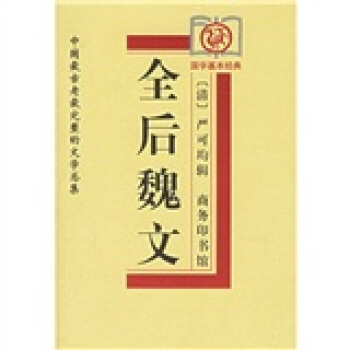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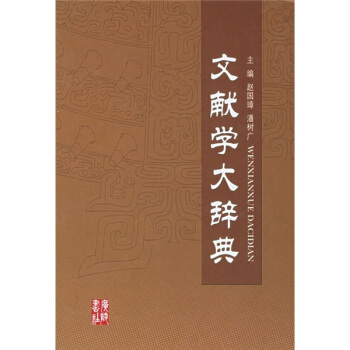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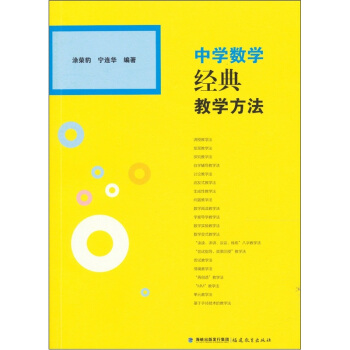
![在書店 [in the Booksto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799442/bf90990b-cea7-4be8-b651-c73f658217d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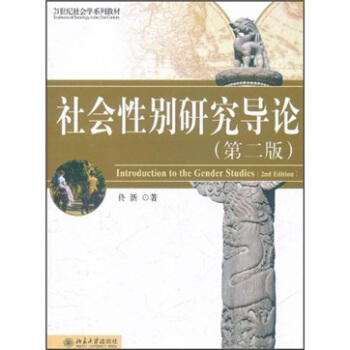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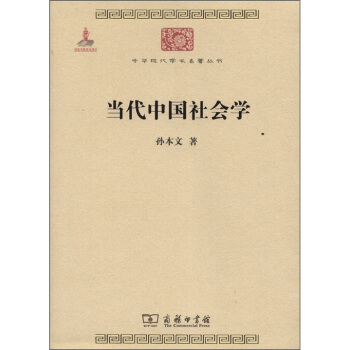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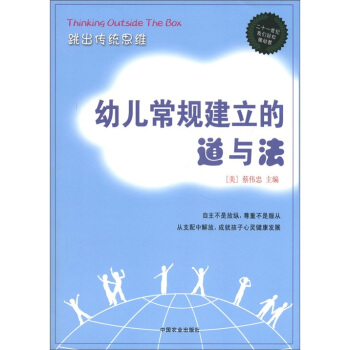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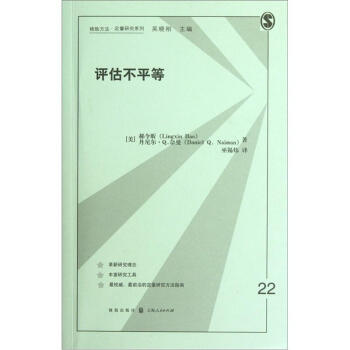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瞭: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047524/rBEGFlAXNJAIAAAAAACoIb1XzQMAABSWwONyK4AAKg54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