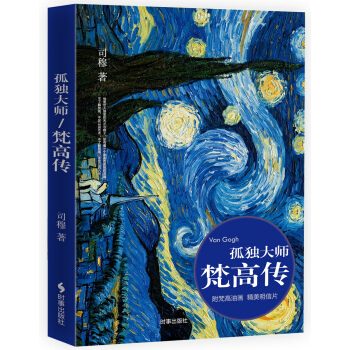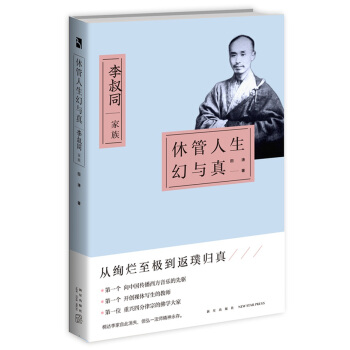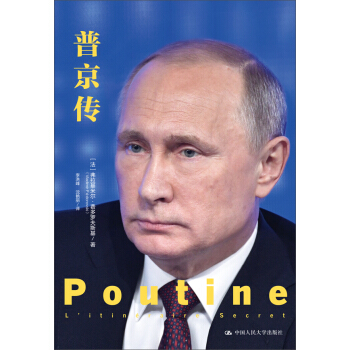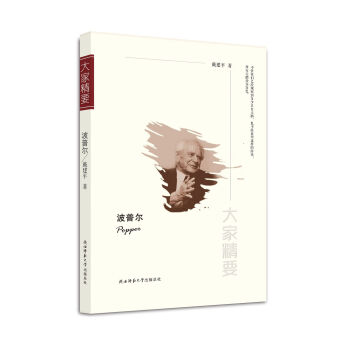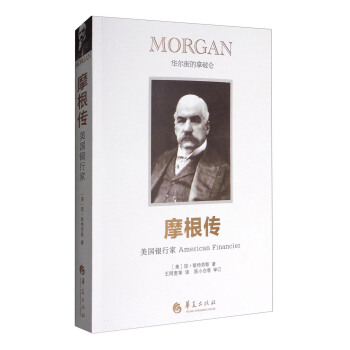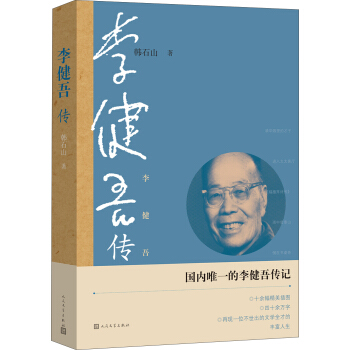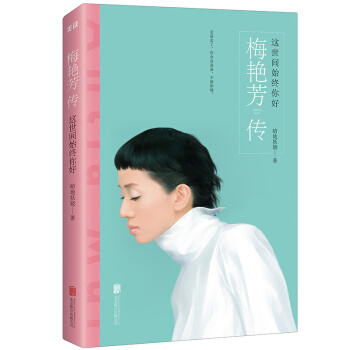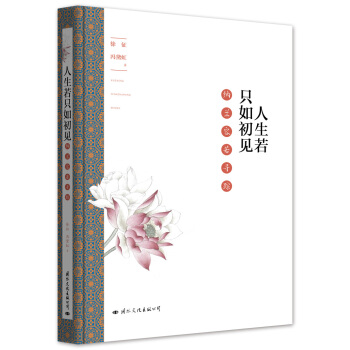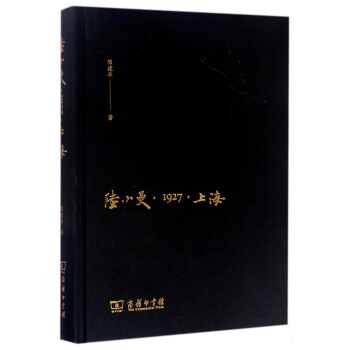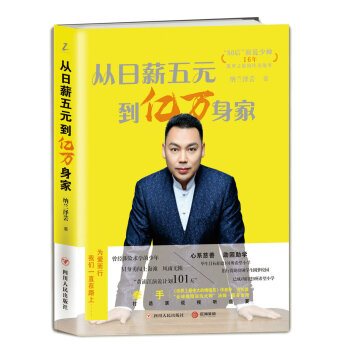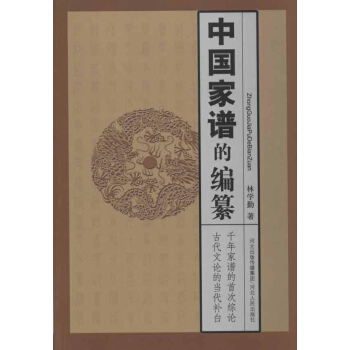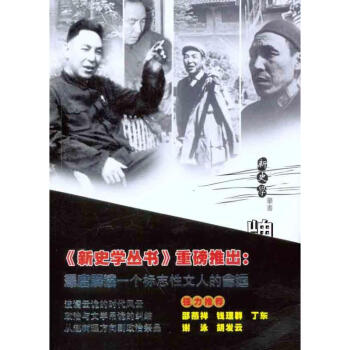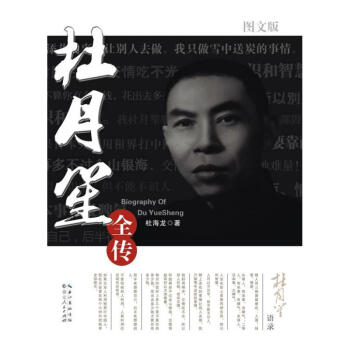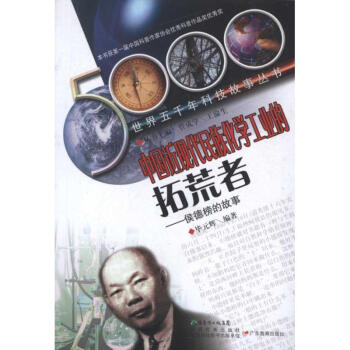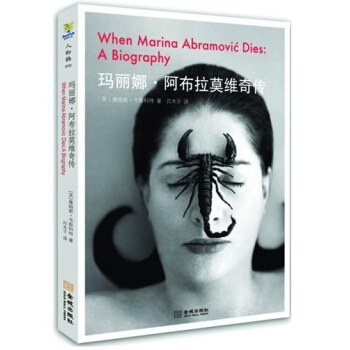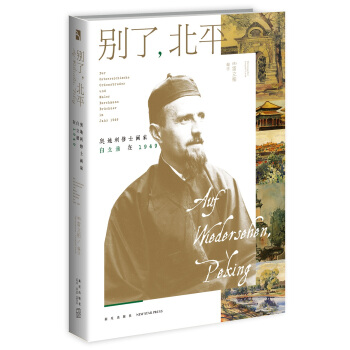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17幅尘封在奥地利圣佳伯尔的画作,重现40年代老北京的景与静,人和情。
奥地利大使亲自作序,盛赞“他把自己生命的26载献给了中国”。
首次披露私人日记,侧写辅仁大学的1948—1949。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三部分,以中德对照形式,介绍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试图阐明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第一部分介绍白立鼐的生平。白立鼐在中国生活了26年,曾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16年。他是中国知名画家陈缘督、陆鸿年、王肃达等人的导师和朋友,在很多方面帮助或影响了这些中国的年轻画家。他甚至还在北京沦陷期间,机智地营救被日军抓捕的中国教授。
第二部分是白立鼐1948年底至1949年离开北京前后的日记。日记忠实记录了白立鼐的当时的处境和复杂心情。
第三部分是白立鼐的画。书中收录了117幅原本封存在奥地利圣佳伯尔的白立鼐画作,其中,素描画37幅,水彩画27幅,人像22幅,静物17幅,其他无归类14幅。这些画作表现出了画家很明显的个人气质:宁静、平和和朴素的美。
书中还收录了8幅高清珍贵历史照片,如白立鼐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的合影等。
作者简介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语文学家。1967年生于奥地利,1985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及基督教神学。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1995年在奥地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2004年2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拉丁语文学史”“古希腊语文学史”“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古希伯来语”等课程。他已出版40多部涉及语言教学和中国历史的汉语著作。
精彩书评
NULL目录
序/奥地利大使艾琳娜 1
Vorwort
序/雷立柏 4
Vorwort
白立鼐修士 001
Br. Berchmans Brückner
白立鼐修士的一生 003
Br. Berchmans Brückner: Ein Lebensbild
白立鼐修士在中国西画史上的地位 009
Br. Berchmans und die Geschichte der westlichen
Malerei in China
白立鼐的告别回忆录:从北京到罗马 027
Erinnerungen an den Abschied: Von Beijing nach Rom
白立鼐的画 091
Die Bilder von Br. Berchmans Brückner
1素描画 Zeichnungen und Skizzen 093
2水彩画 Aquarelle 131
3人像 Portraits 165
4 动物和静物 Tiere und Stilleben 188
5告别北京Abschied von Beijing 206
精彩书摘
1948年12月12日
阳光普照,万物安宁!一种告别的气氛笼罩我们所有人。无论你遇到什么人,他都问:“您也离开吗?什么时候走?”在我住的楼对面有一座新建设的小教堂,快要竣工。周围的地方都已经清理好,现在还需要刷漆,风格是经常见到的“宫廷风格”。
我已经装好了我的箱子和手提包,并写上了地址。蔡修女①来看我,她说学生们计划举办一次画展,并且要自己给自己打分数。陆鸿年和王肃达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天没见面了。
Hell, sonnig und lind! Und sehr still! Auf uns allen liegt Abschiedsstimmung! Wer immer einem begegnet, fragt: ?Gehen Sie auch weg? Wann gehen Sie weg?“ Die Pfarrkirche hier, mir gegenüber, geht der Vollendung entgegen. Der Platz ringsherum ist schon sauber, nur mit den Anstreicherarbeiten ist man noch nicht fertig. Die Ausmalung geschieht im üblichen Palaststil.
Sr. Bernwardine [Tschöpe] war hier und sagt, die Schüler planten eine Ausstellung, bei der sie, die Schüler, sich selbst klassifizieren würden. Lu Hongnian und Wang Suda lassen sich schon viele Sonntage nicht mehr sehen.
1949年1月3日
昨天,星期日下午,我和陆鸿年和郑志(郑宗鋆)一起去崔兴廉的家。他和他的父母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崔给我们看他画的画和素描作品。我们可以以他为荣!他盛情邀请我们在他那里吃晚饭。天黑了我才骑自行车回家:外面很冷,风很大,而且我车上没有灯。回家后我感觉到很快乐,也感到身体很好。也许我经常患头痛是因为我们烧的煤气有问题,或因为我读的书太多?因为一旦我去外面,就不头痛!但是左边的耳鸣看来没有希望,一直不好。
徐思本神父①要我给他两张护照照片,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准备去山东的。”陶百龄修士从上海写信说:“在这里不如北京,各方面都不如北京。”北京非常安静。战争结束了吗?学校的寒假班开始。我获得了批准,校方允许我在工作日开两个教室,并在两个教室里生炉子,这样学生们可以在那里画画。
战争?一些人说很快要签和平条约,另一些人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又有人说外面准备一次“决定性的交战”,第四种人说,北京面临绝粮迫使投降,等等。但是围困我们的人仍然提供水和电!这是什么意思?英语的《北京日报》②停刊。
Gestern, Sonntag Nachmittag, war ich mit Lu Hongnian und Zheng Zhi (Cheng Dj) bei Cui Xinglian. Dieser und seine Eltern bewirteten uns sehr freundlich. Cui zeigte seine Bilder und Zeichnungen. Wir können uns mit ihm sehen lassen! Gegen Verabredung nötigte er uns dann zum Abendessen. Schon war es dunkle Nacht, da fuhr ich bei grosser Kälte und mit Gegenwind und ohne Licht beim – fror tüchtig! Doch daheim angekommen war ich fröhlich und gesund wie selten. Ob nicht der häufige Kopfschmerz vom Kohlengas und vielen Lesen herkommt? Denn sobald ich ins Freie komm sind die Schmerzen geringer! Das linke Ohr freilich scheint rettungslos krank zu sein.
P. Hüngsberg wollte heute zwei Passfotos von mir – für eine ?Shandongreise“, wie er blinzelnd – lächelnd sagte. Br. Severin schreibt aus Shanghai: ?Hier ist es in jeder Beziehung schlechter als in Peking.“ Es ist merkwürdig still. Ist der Krieg eingeschlafen? Die Schule beginnt mit Ferienkursen. Ich habe die Bewilligung eingeholt, an Wochentagen 2 Klassenzimmer offen zu lassen und für beide ein Ofenfeuer zu unterhalten, damit die Schüler dort arbeiten können.
Krieg? Die einen sprechen vom baldigen Friedensschluss, die anderen von ?unversöhnbaren Gegensätzen“, wieder andere sagen, ein ?Hauptschlag“ werde vorbereitet; die vierten sagen, man wolle Beijing aushungern, u.s.f. Dabei versorgen die Belagerer die Belagerten mit elektrischem Strom und mit Wasser! Wer soll sich da auskennen? – Die ?Peking Chronicle“ erscheint nicht mehr!
①蔡修女(Sr. Bernwardine Tschöpe,1905—1957年),波兰人,圣神会修女,1932年到甘肃传教,1947年到辅仁大学,在辅大和辅仁女中任绘画导师。她也于1949年回欧洲,1957年在德国去世。
①徐思本神父(P. Peter Huengsberg,1909—1976年),德国人,圣言会会士,1940 —1949年任北京辅仁大学德语教师和副总务长,1951年入狱,1972年到澳大利亚,1976年在澳大利亚去世。
②英语的《北京日报》(The Peking Chronicle)是外国人在北京办的报纸,和一切其他的外国期刊一样被关闭。
前言/序言
序
人们通常说,音乐可以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可以感动不同历史背景的人,也可以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当然,在美术方面也一直有这种交流,人们会欣赏来自其他地区的美术作品,会得到新的灵感,会接受新的因素。在我们眼前的这本书特别清楚表达了艺术的桥梁作用:本书介绍白立鼐修士的人生、艺术作品和他的美术教学工作。这位修士曾扮演了特殊的中介角色,虽然他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太大。雷立柏以同情而又客观的文笔描述了白立鼐的一生和他在华的工作与使命。
白立鼐曾在北京辅仁大学教学16年之久(1933—1948年),他教导中国学生更好地认识现代艺术,即透视、美术理论和欧洲美术史,他是一位认真的老师,有时候一周上26小时的课。他所支持和培养的年轻中国基督徒画家在1934年秋天的圣诞节画展上展现了自己的作品,并博得了观众的赞赏。
白立鼐自己也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艺术家:在他的素描和水彩画中我们见到了“老北京”,比如北京的城门和北京的郊区,而其中很多景色早已经消失了。
根据他的日记可以意识到,白修士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他把自己生命的26载献给了中国。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北京,虽然1948年和1949年的北京处于很微妙的处境,而他很担心将来的发展。他当时很忧虑在华的外国人和中国的基督徒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白立鼐离开了北京,他经过上海而到达香港。在香港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自传并且说他能很好地理解他,因为世界上的人都是人,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最后,白立鼐飞到罗马,而从那里他向北京的艺术界友人寄了一些明信片——这也记载在他的日记中。
白立鼐的一幅水彩画是从景山上画的故宫。当我下次爬上景山并眺望紫禁城时,我就要找白立鼐当年站的位置,用他的视角看故宫……
艾琳娜(奥地利大使)
Vorwort
Es ist fast ein Gemeinplatz, dass Musik die Grenzen überwindet, Menschen mit verschiedener Geschichte rühren und eine Brücke zwischen Kontinenten bauen kann. Natürlich gab und gibt es auch in den bildenden Künsten immer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Kunst, die andernorts und zu anderer Zeit geschaffen wurde, Befruchtungen und Einkreuzungen. Aber selten kann die Vermittlerrolle – und sei es auch eine bescheidene, was ihre Reichweite angeht - so klar dargestellt werden, wie es hier in diesem Band zur Kunst und Kunstvermittlung von Br. Berchmans Brückner geschieht. Liebevoll und unsentimental, wie Berchmans Brückner wohl selbst auch war, skizziert Leo Leeb sein Leben und Schaffen in China.
16 Jahre lang (1933-1948) war Berchmans Brückner Lehrer an der katholischen Fu Ren Universität in Beijing, wo er 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moderne Malerei, Perspektivik, Kunsttheorie und Kunstgeschichte des Westens eingeführt hat, oft 26 Wochenstunden lang. Die christliche Malschule, die er förderte, präsentierte sich erfolgreich in einer Weihnachtsbilder-Ausstellung im Herbst 1934, bei der junge chinesische Künstler erste Verkaufserfolge erzielen konnten.
Berchmans Brückner war aber auch selbst ein produktiver Künstler: aus seinen Gemälden und Aquarellen tritt uns das ?alte“ Beijing entgegen, mit seinen Stadttoren und Vororten, die es längst nicht mehr gibt.
Aus seinen Tagebüchern spricht die tiefe Verbundenheit mit China, dem Land, dem er 26 Jahre seines Lebens schenkte. Der Abschied fiel ihm schwer, wiewohl Peking 1948 und 1949 umkämpft war und die Unsicherheit der weiteren Entwicklung im Lande mit ihren möglichen Auswirkungen auf Ausländer im Allgemeinen und Christen im Besonderen ihn bedrückte.
In Hongkong, einer wichtigen Etappe seiner Ausreise aus China, liest er eine kurze Autobiographie von Mao Ze Dong und notiert, dass er ihn gut versteht, weil Menschen eben Menschen seien. Von Rom aus noch hielt er – mit bescheidenen Postkarten, wie er in seinem Tagebuch notiert – Kontakt zu seinen alten Künstlerfreunden in China.
Wenn ich das nächste Mal vom Kohlehügel auf die verbotene Stadt blicke, vorausgesetzt das Wetter ist klar, werde ich Berchman Brückners Perspektive suchen, wie sie uns aus einem seiner Aquarelle überliefert ist.
Irene Giner-Reichl
用户评价
手捧《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我仿佛走进了一个被时间定格的下午。白立鼐,这位奥地利修士画家,用他非凡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1949年北平那个特别时刻的独特印记。这本书并非仅仅记录历史的转折,它更像是白立鼐内心的一场深刻告白。他笔下的北平,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充满了人间的烟火。他观察着街边小贩的吆喝,捕捉着孩童纯真的笑容,感受着黄昏时分古老城墙的沉寂。这些画面,在他眼中,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一种对过往的深深眷恋。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淌,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他离开北平,带着的不仅仅是他的画作,还有他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爱,以及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告别”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离开,更是精神上的铭记与传承。
评分读完《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我的脑海中始终回荡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寂静。白立鼐这位奥地利修士画家,在1949年离开北平前的日子,被他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笔触描绘出来。我仿佛能听到他内心的低语,看到他眼中闪烁着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不舍。书中所呈现的,不是宏大的政治变革,而是日常生活琐碎中的不凡。他观察着街头卖艺人的落寞,记录着孩童嬉戏的纯真,描绘着夕阳下古老城墙的静默。这些场景,在常人眼中或许平淡无奇,但在白立鼐的笔下,却充满了生命力与情感的张力。他的观察,超越了国界和文化,直抵人性的共通之处。他笔下的北平,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故事、充满温度的精神家园。他即将告别的一切,在他心中都化作了永恒的画面,值得细细品味。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留白”,在于它引人遐想的空间。白立鼐的离开,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思索,关于故土,关于归属,关于那些我们曾经珍视却又不得不放手的东西。
评分这本《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带给我的,远不止是一段历史的追溯,更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当我翻开书页,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空气中弥漫着告别的气息,却又夹杂着坚守的微光。白立鼐,一个来自遥远奥地利的灵魂,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画笔,记录下了他眼中那个即将告别的北平。从他的文字中,我能感受到他对这座古都深沉的爱恋,以及面对时代洪流时,内心涌起的复杂情感。他并非简单地描绘风景,而是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那些日常生活中蕴含的诗意与忧伤。街头巷尾的吆喝声,老宅院里的斑驳光影,甚至是一位普通百姓脸上的一丝愁绪,都被他细腻地刻画出来。这让我不禁思考,在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有多少个像白立鼐这样的个体,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印记。他的离开,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也是对一段青春的铭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的温度,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也让我对“别了”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是冷冰冰的史料堆砌,而是饱含情感的生命记录,是一次对过去的回望,也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评分《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它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细腻而动人。白立鼐,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画家,他的目光并非聚焦于时代洪流中的波澜壮阔,而是沉浸在1949年北平这座城市里,那些被忽略的、寻常的瞬间。他用文字,勾勒出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午后的阳光洒在古老的屋檐上,老人们在庭院里悠闲地品茶,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这些场景,在他的笔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人情的温暖。他捕捉到的,是这座城市即将告别的“过去”,是他眼中那些值得留存的“现在”。他离开北平,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溯,也是对个人情感的梳理。我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他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眷恋,以及面对时代变迁时的无奈与不舍。这本书让我明白,宏大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的瞬间组成的,而这些微小的瞬间,往往更能触动人心,唤起共鸣。
评分《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这本书,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沉思。白立鼐,一位来自遥远的奥地利修士画家,他在1949年离开北平之前,留下的文字,像一束柔和的光,照亮了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这本书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没有激昂的宣言,而是以一种极其个人化、极其细腻的视角,描绘了北平这座城市在那个特定时期的生活片段。他关注的是街头巷尾的细微之处,是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是古老建筑在时光流转中的静默。他用他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那些即将消失的景象,那些充满温情却又带着一丝伤感的瞬间。他离开,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承的告别。这本书让我感受到,即使在历史的巨变面前,个体的情感依然是如此宝贵,如此值得被记录和珍藏。白立鼐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去窥视那个时代的另一面,去感受历史的温度与人性的光辉。
评分商品很不错,已多次购买了,京东商城送货很快!
评分哎哟,不错,哎呦,不用Q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评分商品很不错,已多次购买了,京东商城送货很快!
评分很满意的一次购物,下次还来买。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尚可。。。。。。。。。。
评分一起回忆
评分哎哟,不错,哎呦,不用Q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评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旧中国,苦难深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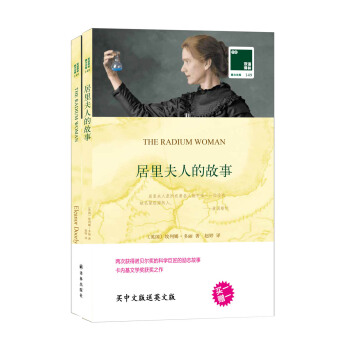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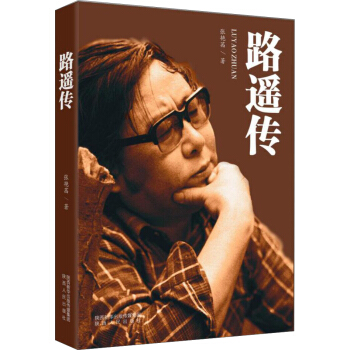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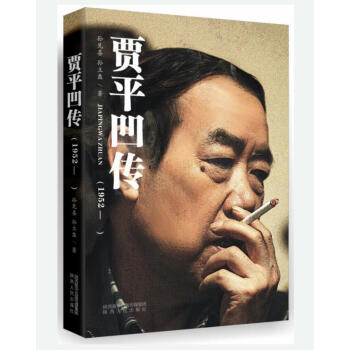
![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 [Machiavelli:A Man Misunderstoo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1580/59ae3c18N718f7b3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