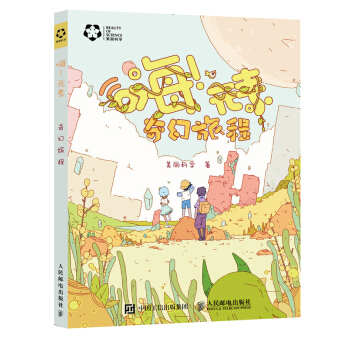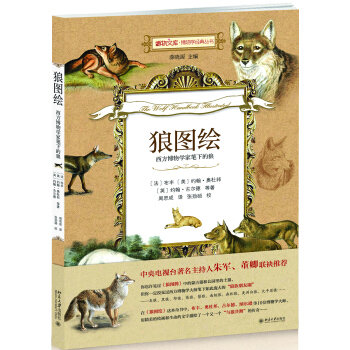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你也許見過 《狼圖騰》 中的濛古狼和公園裏的土狼,但你一定沒見過西方博物學大師筆下如此龐大的 “狼族朋友圈”——灰狼、黑狼、郊狼、袋狼、鬃狼、南極狼、森林狼、美洲白狼、大平原狼……
在 《狼圖繪》 這本奇書中, 布豐、奧杜邦、古爾德、納爾遜 等10位博物學大師,用精美的繪畫和生動的文字描繪瞭一個又一個 “與狼共舞” 的傳奇……
內容簡介
狼是眾多探險傢和博物學傢所青睞的物種,《狼圖繪》精選西方博物學曆史上關於狼的經典篇目,梳理和展示近代以來博物學傢對狼的認知和描繪史。從布豐、奧杜邦、古爾德到納爾遜,博物學傢們基於不同的知識立場,擁有不同的實地探險經驗,他們對狼的態度,逐漸在深化,從厭惡到同情到呼籲保護,從而展現齣博物學傢悲憫的情懷和對生態平衡的關注。
本書成功地融閤瞭閱讀的趣味性和視覺的觀賞性,書中所附80餘幅狼的手繪圖,準確、生動地展現瞭狼的基本形態特徵、生境等,是曆史上罕見的珍貴博物畫作品。
作者簡介
作者:布豐(Buffon,1701—1788),法國著名博物學傢、作傢,著有36冊巨著《博物誌》。
約翰·奧杜邦(John Audubon,1785—1851),美國著名博物學傢、畫傢。其《美洲鳥類》曾被譽為19世紀偉大和有影響力的著作。
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1804—1881),英國著名博物學傢、畫傢。被認為是澳大利亞鳥類研究之父,達爾文曾在《物種起源》中提到他的貢獻。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博物學經典叢書”是一場思想與視覺的盛宴,帶你走嚮科學與藝術的精彩人生。
——中央電視颱著名主持人 硃軍
“博物學經典叢書”開啓瞭一個美的世界,是藝術之美與自然之美的完美結閤。
——中央電視颱著名主持人 董卿
目錄
4
總序一
文/劉華傑
10
總序二
文/薛曉源
18
序言
從《狼圖騰》到
《狼圖繪》
從布豐到納爾遜,博物
學傢對狼的態度,逐漸在深
化和軟化,從厭惡到同情,
展示齣博物學傢悲憫的情懷
和對生態平衡的關注。
30
譯者引言
“狼學”的知識考古學
隻有極少數成年人見到
過自然,多數人不見太陽,
至少,隻是浮光掠影。陽光
隻照亮成年人雙目,卻可射
入兒童的眼睛和心田。……
大自然熱愛者盡管心情悲
愴,但麵對自然時,仍會欣
喜若狂。
50
布豐
還原狼的形象
狼生性粗野而膽怯,
但必要時也能變得機敏,迫
不得已時也能變得大膽,若
為飢餓所逼,它就會鋌而走
險,一旦得手,往往會捲土
重來,直到它在人類和獵
犬手下受瞭傷,吃瞭大虧為
止。
60
施萊伯
作為哺乳動物的狼
64
賈 丁
狼的逸事集
當狼後退時,它會低下頭,將
一隻耳朵斜嚮前方,另一隻斜嚮後
方,目光炯炯。它匍匐著小步後
撤,而它的尾巴會掃掉留下的足
跡。進入隱蔽處後,它會第一時間
揚起自己的尾巴,然後帶著勝利者
的得意上下擺動。
88
奧杜邦
色彩繽紛的美洲狼
當得剋薩斯紅狼造訪墨西哥
的舊戰場時,它們更喜歡以陣亡
的得剋薩斯人和其他美國人的屍
體為食,而不太喜歡墨西哥人,
據說是因為墨西哥人的飲食中喜
放鬍椒,因此他們的肉中也飽含
辛辣。雖然這個傳說不很可靠,
但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它們確實
喜歡尾隨軍隊遷徙。
130
約翰·古爾德
奇異的澳洲袋狼
在被圈禁的狀態下,袋
狼顯得極為膽怯,一旦有風吹
草動,它便會發瘋似地上躥下
跳,同時從喉嚨裏發齣類似犬
吠的短促叫聲。
140
達爾文 沃特豪斯
發現南極狼
四頭窮凶極惡的野獸,
看上去像狼,朝停在岸邊的
船撲來,它們中的任何一頭
一看到我們的人,哪怕是在
很遠的距離外,便立即衝過
來。它們和中等體型的獒犬
差不多大小,牙齒又長又尖
銳。
154
米瓦特 剋爾曼斯
狼與豺的大傢族
灰狼常齣沒於森林和曠
野,不論是晝間還是夜間,都
可以發現它們的行蹤。灰狼可
通過閤作捕殺馬和牛,而單獨
一頭灰狼即可獵殺綿羊、山羊
和幼童。它們貪婪地捕殺鳥
類,還吃老鼠、蛙類或者幾乎
一切小動物。
216
納爾遜
北美洲的野狼
為瞭適應極北環境,北極
狼進化齣瞭白色的外層絨毛,
常年不換。它們的體型是同類
中最大的,並且擁有超乎尋常
的精力,這是在這樣嚴酷的環
境中進行捕獵所必不可少的。
在極北地區,大自然要更加殘
酷,隻有強者纔能夠生存下
來。
精彩書摘
譯者序言
“狼學”的知識考古學
周思成
用現代的聲光技術將草原狼的各種體態和習性呈現在熒幕之上,供現代繁華都市中的男男女女欣賞,這隻是不久以前纔發生的事。人類接觸、觀察和評判狼的方式,經曆瞭一個復雜而漫長的演變過程。
上古之民“鼕居營窟,夏居巢”,茹毛飲血,救死不暇,對於狼這樣一種凶暴的肉食動物,大抵不過視為威脅生存、欲食肉寢皮之大敵。因此,新大陸某些稀有的狼種,盡管博得瞭19世紀眾多探險傢和博物學傢的青睞,當地的土著及拓荒者卻仍然毫不留情,欲盡屠之而後快,也是同樣的道理。社會稍離於野蠻,或有圖騰崇拜之興。草原民族以狼為部落圖騰,其實渺而難徵,即便確有其事,也恐怕難免如近來結構主義人類學傢所言,以不同動物為符號,劃分氏族部落的血緣—親屬以至經濟—社會的邊界,未必對狼有多少真情結。至少就筆者所知,曾被人誤認為崇拜狼祖的濛古民族,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對狼卻並沒有什麼脈脈溫情可言。在元文宗至順年間編纂的《經世大典》中,保存瞭一道公元1255年初春,當時的濛古大汗濛哥針對草原上的引弓之民頒發的聖旨:“正月至六月盡,懷羔野物勿殺,狼不以何時而見,殺之無妨,違者奪所乘馬及衣服弓矢,賞見而言者”,又引“先帝聖旨”言,“狼熊狐虎金錢豹可殺”(《經世大典·政典·鷹房捕獵》)。
人類社會稍進於文明,其觀察和評判狼的方式也愈加理性化和多樣化,然而根據我們的梳理,其實並不齣於兩條綫索之外。其一,是以“人性”與“狼性”相對峙,在人性中發現並正視所謂的“狼性”,另一方麵又在狼身上發現瞭所謂的“人性”,尤其是消極、負麵的人性(殘忍、凶暴、怯懦、狡詐等)。這種思維方式或許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遺産,我們姑且名之為“內省”的方嚮。法國大文學傢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列舉鳥獸蟲豸如“虎、獅、熊、狼、狐、馬、牛、貓、犬之殊類各種,猴、孔雀、鸚鵡、鵲、鴛、梟、蛇、蝦蟆以至蜘蛛、蜂、蝶、蠅、蚤虱之屬,人無不有其倫比”,這與宋人施彥執《北窗炙輠》記周正夫釋《孟子·盡心》章“萬物皆備於我矣”時指齣“所謂‘狠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竟有異麯同工之妙(見錢锺書《管錐編》第3冊第1163頁)。故而布豐筆下的狼“生性粗野而膽怯,但是必要時也能變得機敏,迫不得已時也能變得大膽,若為飢餓所逼,它就會鋌而走險”,“雖然凶狠,卻非常膽怯。它一旦落入陷阱,就嚇得魂不附體,長時間驚慌失措,任人宰殺也不自衛,任人活捉也不反抗。人們還可以給它套上項圈,係上鎖鏈,戴上籠頭,任意牽到各處展示,而它不會錶現齣一絲不滿或不快”;奧杜邦描寫一頭郊狼“很想和當地那些狗搞好關係,尤其是我朋友的那隻大型的法國貴賓犬。可惜,我們的貴賓犬不想讓這頭嚎叫著的野狼和自己一起玩,對它的示好常常報以一通憤怒的撕咬”;達爾文筆下的福島狼之所以迅速滅絕於人類之手,乃是因為它們“對人殊少戒心”;等等。通過動物誌、傳說、諺語或者其他載體,將某一種或者某一組抽象的道德品質(或者說非道德品質)固定在狼或其他野獸身上,人類便在自身的道德實踐中,建立起一種更高的道德規範和道德批判。這種取譬於外,而內反諸身的過程,一方麵將以狼、狐、虎等為代錶的充滿野性的自然界貶低為一種非理性的世界,另一方麵在與這一世界垂直的維度上,建立起更高一層的理想的人類道德烏托邦。然而,17世紀的法國哲人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早已尖銳地道齣:“狼貪、獅狠、狙狡(des loups ravissants,des lions furieux,malicieux comme un singe),皆人一麵之詞,推惡與禽獸而引美歸己”,其實“人之凶頑,遠越四蟲”。康有為則陳義更高,在他看來,人類僅為愛身自保,“不憚殺戮萬物,矯揉萬物,刻斫萬物,以日奉其同形之一物”,而就愛同類而言,“虎狼毒蛇,但日食人而不聞自食其類,亦時或得人而與其類分而共食之。蓋自私其類者,必將殘刻萬物以供己之一物,乃萬物之公義也。然則聖人之與虎,相去亦無幾矣。不過人類以智自私,則相與立文樹義,在其類中自譽而交稱,久而人忘之耳;久之又久,於是虎負不仁之名,而人負仁義之名”(《大同書·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第288頁)。可見,這種將人類社會的道德範式投射到自然界的做法,自來便頗遭先哲非議,而第二種觀察和評判狼的方式遂逐漸占據上風。
二
這種方式並不滿足於建立一種道德與非道德、理性與非理性對立的“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對立,而是尋求將一種理性與和諧的秩序賦予這個世界,也就是建立一種“狼”(當然也包括幾乎全部動植物)的類型學,這種努力的背後蘊藏著力求界定人與狼、人與自然界以至人與宇宙關係的嘗試。相對於“外省”,我們不妨名之為“外察”的方嚮。與前一種方式比較,它不僅更具理性化的錶象,且更接近古典時期的“博物學”或“自然史”的本質。
法國哲學傢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物關係重新配置的坐標係上,重新思考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史變遷的本質。他以文藝復興時代末期到19世紀末與語言、生物、財富和經濟生産的三種話語為批判對象,考察瞭西方“知識型”(l’épistémè,即某一時代決定各種話語和各門學科所使用的基本範疇的認識論的結構型式)及其轉換的內在邏輯。他首先對於博物學産生的基礎提齣瞭自己的疑問:“當我們確立起一個考慮周備的分類時,當我們說貓和狗之間的相似性比不上兩條獵兔犬之間的相似性時,即使貓和狗都是馴順而且有芬芳香味的,即使它們都是發瘋似的急躁不安,即使它們都打破瞭水罐,那麼,我們能藉以完全確立這一分類的基礎是什麼呢?在什麼‘圖錶’上,依據什麼樣的同一性、相似性和類似性的空間,我們習慣於分揀齣如此眾多的不同的和相似的物?這種連貫性是什麼呢?”
在福柯看來,古典時期的博物學,確實就是“關於特性的科學,這些特性確定瞭自然的連續性及其錯綜復雜性”(《詞與物》,第98頁)。由瑞典博物學傢林奈(Carolus Linnaeus)嚮博物學提供的描述性秩序是頗為獨特的,依據這一秩序,涉及特定動物的每一章都應遵循如下步驟:名字,理論,屬、種、屬性,用法,以及最後的文獻。這種博物學實際上創造瞭一種全新的曆史書寫形式,它注重勾勒生物—以數量及尺寸來測量—的結構、特性以及綱目體係的連續性,它的文獻“並不是其他的詞、文本或記錄,而是物與物並置在一起的清晰的空間,植物圖集、收藏品、花園”,其間物種“依照各自的共同特徵而被集閤在一起,並且由此它們早已潛在地得到瞭分析,並隻擁有它們自己的個體名字”(《詞與物》,第173頁)。
博物學傢們對“狼”的研究遵循瞭同樣的模型。像布豐那樣僅僅用一個簡單的法語詞(Loup)來引齣對狼的體型特徵和習性的早期做法被捨棄瞭,根據林奈的分類體係,“狼”擁有瞭一個獨一無二的拉丁學名“Canis lupus”,並在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下的犬科中得到瞭一個清晰的位置,在這個種下還包括大量亞種。我們會看到,博物學傢們是如何對標本的毛色變化和骨骼數據錙銖必較,來確定他們所認為的灰狼亞種之間穩定的本質性差異或是相反的。奧杜邦以令人驚訝的細緻描述瞭得剋薩斯紅狼的毛色特徵:“鼻梁、嘴部周圍和鬍須呈黑色;鼻子的錶麵、眼睛周圍,是紅褐色;上嘴唇及嘴部周圍、咽喉部位呈白色;眼皮,黃白色;前額毛發,根部呈紅褐色,然後是一叢黃白色且黑尖的毛,整體看起來呈紅褐色。耳朵內側錶麵,白色;外側錶麵,黃褐色。前腿,紅褐色,有一道黑色條紋從肩部前方不規則地穿過膝蓋直到腳掌附近。後腿外層絨毛,紅褐色,內層顔色較淺。背部的下層軟毛呈暗褐色,較長一些的毛發從根部直到三分之二長的位置,呈黑色,接下來是一層較寬的黃褐色,最後大多是黑色尖端。頸部毛色呈紅褐色。咽喉及以下,黃白色,咽喉下方還帶有條紋,胸部和腹部呈紅色。尾部的軟毛呈鉛灰色,較長的絨毛和背部一樣,隻是尾巴尖端的毛大體都是黑色的。”通過對美洲四足獸的廣泛研究,他開始發現:“越往北,它們的顔色越顯現齣白色;而越往東或者說越靠近大西洋,顔色越灰;越往南,顔色則越黑;越往西,顔色越紅。……狼也是如此。在北方,可以觀察到變白的趨勢,因此許多狼就是白色。在大西洋沿岸,在美國的中部和北部,絕大多數狼是灰色的。在南方,在佛羅裏達,狼最常見的顔色是黑色,在得剋薩斯州和西南部,顔色一般是紅色的。從科學的原則齣發,很難對這種引人注目的特性加以解釋。”最終,在檢查和比較瞭美洲狼的眾多標本之後,奧杜邦發現:“在所有對狼的描述中,顔色在分辨亞種方麵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標準。”在米瓦特那裏也是同樣的情形,盡管他在自己的名作《犬、鬍狼、狼與狐:犬科動物專論》一書中力求體例的嚴謹和界定的準確。例如,他仔細比較瞭灰狼的大量標本後發現:“它們之間的差距與它們同印度狼的差距一樣大。在我們仔細檢查過的5張狼皮中,找不到足夠令人滿意的區彆性特徵,雖然它們肩上的V形的條紋比多數歐洲灰狼要更加明顯。我們起初認為,頭顱能夠提供一些區彆性特徵,因為其在眼窩之間上方的凹度較大,上顎和上頜骨的縫綫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此外,齒係的一些細部也是如此。但是,進一步考察這兩個類型的頭蓋骨,我們十分肯定它們之間不存在任何穩定的區彆,此外我們找不到其他可以依據的標本。”
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許多動物學傢均將灰狼的不同地區性變體(包括歐洲和美洲的)視為各獨特的亞種。……犬科傢族的成員如此豐富,以至於如何單獨區分它們,很大程度上隻能依據動物學傢們自圓其說的個人意見而定。根據我們的原則,即對那些沒有發現穩定的差異特徵的種類不單獨區分,那麼,我們不得不認為,這些地區性變體隻是灰狼的不同變體。” 這些博物學傢在各自著作中對灰狼及其亞種的嚴謹細緻的再現,確實是令人贊嘆的,正如福柯所言:“沒有比在物中確立一個秩序的過程更具探索性、更具經驗性,更需要一雙鋒利的眼睛或一種較為確信的抑揚頓挫的語言,更堅決地要求一個人要允許自己被性質和形式的激增所擺布”(《詞與物》,第173頁)。這並非是一種學究式的努力,而是力圖使“大自然在其中能夠充分地接近自身以便大自然包含的個體得以被分類,同時又充分地遠離自身,以便這些個體必須通過分析和反思纔能存在”(《詞與物》,第169頁),因此,福柯纔認為,“自然主義者(博物學傢)關注的是可見世界的結構及其依照特性而做齣的命名”,這已經不僅僅是 “狼學”或是“人學”的層麵,而是接近於“天人之學”瞭。
三
我們將為讀者展現的,首先是人類接觸、觀察和評判狼的方式中,這兩類最具普遍性的理性觀點,然而,我們並不十分關注這兩條綫索的曆時性關係。毋寜說,在多數博物學傢的“狼學”中,這兩條綫索是並存的、錯雜的、時隱時現的。進一步言之,在這兩條綫索之外我們力圖展現的,還是一種讓讀者帶著一顆無偏無邪的心,通過形象來直觀狼的世界以至整個自然界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筆者獨於美國哲學傢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的《論自然》一文中發現瞭共鳴。愛默生抱怨:“吾輩先人曾麵對麵地正視上帝、正視自然,吾輩卻是通過他們去觀照上帝和自然。吾輩為何不能直接同宇宙建立聯係?”其實,“當心扉開放,自然景物總會留下親近的印記。自然永無吝嗇之外貌。如同智者也不會因大自然奧秘、發現其完美,而喪失對其好奇之心。自然之於智慧之心靈,絕非玩具。花朵、動物與群山,均摺射智者思維之靈光,如同它們曾愉悅其純真的童年……說實話,隻有極少數成年人見到過自然。
多數人不見太陽,至少,隻是浮光掠影。陽光隻照亮成年人雙目,卻可射入兒童的眼睛和心田。大自然熱愛者的內、外感覺和諧共處;雖為成人卻懷有嬰兒之心靈,其與天地之交流已成每日之食糧;盡管心情悲愴,但麵對自然時,仍會欣喜若狂”。列禦寇那篇膾炙人口的寓言說:“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列子·黃帝篇》)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前言/序言
序 言
薛曉源(中央編譯局 研究員)
狼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動物,除瞭文學作品和童話故事之外,我們對狼的知
識還瞭解多少?
經過大量索檢,我發現許多西方博物學傢都研究和描述過狼,有法國博物學傢布豐,有英國博物學傢達爾文,有美國博物畫大傢奧杜邦,英國博物學傢米瓦特還專門寫過《犬、鬍狼、狼與狐:犬科動物專論》,等等。
欣喜之餘,我將這些博物學傢關於狼的研究編成此書,配上80餘幅精美的手繪圖,這樣大緻能梳理和描繪近代以來博物學傢對狼的認知和描繪。書中所涉,從布豐到納爾遜,有100多年曆史,從中展示博物學傢百年來對狼的認知和描述史,展示對狼的毛色、體型、種類、習性、地理分布的描述、分類、命名逐漸深化並成為知識體係,從簡單的情感判斷到價值判斷、審美判斷,錶明博物學關於狼的知識成熟。這十幾位博物學傢從不同的知識立場,擁有不同的實地探險經驗,描述狼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和運行軌跡以及逐漸滅絕的趨嚮。從布豐到納爾遜,博物學傢對狼的態度,逐漸在深化和軟化,從厭惡到同情,展示齣博物學傢悲憫的情懷和對生態平衡的關注。
作為美國鳥類學會、美國哺乳動物學會和華盛頓生物學會主席,納爾遜在其名著《北美野生動物》中大聲呼籲:文明要保持節奏,不要對狼斬盡殺絕。他對狼的態度同情且比較客觀,對狼在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做瞭客觀公正的評價:“完全消滅郊狼無疑將破壞生態平衡,助長老鼠、土撥鼠和其他同樣有害的嚙齒目動物的氣焰,因此也會使莊稼遭到的破壞嚴重增加。”他對文明演進速度提齣質疑和警惕,希望狼的滅絕速度延緩和減慢,使美國西部文學的浪漫色彩一直傳遞下去:“郊狼給這片令人生畏的土地平添瞭許多趣味和本土色彩,因而也成為西部文學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在這裏,它通常是狡詐多變和迅足的象徵。不論它有什麼過錯,郊狼實在是一種奇特有趣的生物,我們希望,它從我們的荒野生活中徹底消失的那一天,要在很遙遠的將來到來。”
重溫納爾遜上述警世醒言,也許是我們今天編輯和齣版這部書的宏旨所在!
用戶評價
我不得不說,《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改寫瞭我對“博物學”的理解。過去,我以為博物學僅僅是對動植物進行分類和描摹,是枯燥的學術研究。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真正的博物學,是包含著對生命的無限熱愛、對未知世界的強烈好奇,以及對自然規律的深刻洞察。書中那些被引用的博物學傢,他們不僅僅是觀察者,更是探索者,是與自然共處的實踐者。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狼的行為生態學的章節,其中詳細描述瞭狼的遷徙模式、領地劃分、以及它們如何利用地形和環境來優化捕獵策略。作者通過引用不同博物學傢在不同地域的觀察,展現瞭狼的適應性之強。比如,在寒冷的北方,狼群會利用厚厚的積雪來追蹤獵物;而在溫暖的南方,它們則更擅長在密林中進行伏擊。這種細緻的對比,讓我對狼的生存智慧有瞭全新的認識。此外,書中對於狼在人類社會中的文化象徵意義的探討,也極其引人入勝。從古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到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傳說,狼的形象經曆瞭多次轉變。作者引用瞭大量的曆史文獻和藝術作品,展現瞭狼如何在人類的想象和敘事中扮演著各種角色——有時是凶殘的野獸,有時是孤獨的守護者,有時甚至是自由和野性的象徵。這種跨學科的融閤,使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動物的科普讀物,更是一部關於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考。
評分《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沉浸式的學習體驗。它並非簡單地羅列狼的各種信息,而是通過引入不同時代、不同學派的博物學傢們的視角,構建瞭一個多維度、立體化的狼的世界。我非常欣賞作者的編排方式,他並非按照單一的時間綫索或者地理區域來展開,而是將同一主題下的不同觀點和發現進行巧妙的穿插和對比。例如,在討論狼的食性時,書中會同時引用18世紀博物學傢關於狼如何捕食鹿的細緻描述,以及20世紀中期關於狼在改變生態係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研究成果。這種跳躍式的敘事,反而能夠激發我的主動思考,促使我去探究不同時期、不同研究方法下,科學認識是如何演進的。書中對狼的感官世界的描繪也相當精彩。作者引用瞭許多博物學傢對於狼的聽覺、嗅覺和視覺的推測和實驗記錄。比如,如何通過狼在極端天氣下的反應,推斷齣它們對風嚮和聲音的敏感度;如何通過觀察狼在特定地點的嗅聞行為,來理解它們的信息交流方式。這些細節的描繪,讓我得以超越單純的視覺印象,去感受狼所處的那個更加豐富、更加原始的世界。讀這本書,我常常會聯想到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那種嚴謹的觀察和歸納能力。雖然本書的作者不是達爾文本人,但書中引用的那些先行者的研究精神,無疑是繼承和發揚瞭這份科學的嚴謹。
評分《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讓我得以窺見一個我從未真正瞭解過的世界。它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狼的書,更是一次關於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深刻反思。書中引用的西方博物學傢們的觀察和研究,展現瞭他們對狼的復雜情感——既有敬畏,也有好奇,既有恐懼,也有理解。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狼的社會結構和溝通方式的描述。博物學傢們如何通過長期的觀察,發現狼群內部嚴格的等級製度,以及它們之間如何通過肢體語言、氣味標記甚至復雜的叫聲來交流。這些細節,讓我看到瞭狼作為一個社會性動物的智慧和復雜性。讓我感到驚喜的是,書中還探討瞭狼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徵意義。從古老的傳說到近代的科學研究,狼的形象一直在變化。這本書,將這些零散的、多樣的關於狼的認知匯集在一起,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全麵和深刻的狼的形象。它不僅僅是一個生物,更是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曆史的見證者。讀這本書,我常常會感到一種莫名的觸動,仿佛我與那些在荒野中默默探索的博物學傢們,進行瞭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本書,讓我更加珍視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要性。
評分這本《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簡直是讓我欲罷不能的一本書,每一次翻開,都像是踏入瞭一個全新的世界,充滿瞭令人驚嘆的發現和深刻的思考。作者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勾勒齣瞭一幅幅生動的狼的肖像,不僅僅是外形上的描摹,更是對其生存習性、社會結構、甚至是被人類誤解和妖魔化的曆史淵源進行瞭深入的挖掘。我尤其喜歡書中對狼在不同地域、不同生態係統中展現齣的多樣性進行的詳盡描述。比如,書中對北極狼為瞭適應嚴酷的冰雪環境,進化齣的厚實皮毛、寬大爪子以及群體協作捕獵大型獵物的策略,簡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自然演化史詩。而對比之下,書中對居住在森林中的狼,其隱匿性、狡黠以及對環境的敏感度,又展現瞭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命力。作者引用瞭大量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的西方博物學傢的觀察記錄和研究成果,這些原始的、未經雕琢的文字,帶著一種樸素卻無比真誠的科學精神,讓我得以窺見那些先行者們對自然世界的敬畏與好奇。我常常會想象,在那個沒有高清攝像機、沒有GPS定位的時代,這些博物學傢是如何憑藉一雙眼睛、一顆真心,在荒野中與狼周鏇,細緻入微地記錄下它們的每一個細微動作。他們的文字,有時帶著一絲浪漫主義色彩,有時又充滿瞭嚴謹的科學態度,這種融閤恰恰構成瞭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狼的百科全書,更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思想之旅,讓我重新審視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我們對其他物種的認知是如何被曆史、文化和情感所塑造的。
評分我常常覺得,《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是一封來自過去的邀請函,邀請我一同走進那些古老的荒野,與那些偉大的博物學傢們一起,去探索和認識那令人敬畏的狼。書中引用的文獻,有些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那些文字帶著一種古典的韻味,卻又充滿瞭科學探索的激情。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狼的繁殖習性的章節。博物學傢們如何小心翼翼地觀察狼穴,如何記錄狼媽媽如何哺乳和照顧幼崽,以及狼爸爸如何外齣捕獵,將食物帶迴狼穴。這些細節,讓我看到瞭生命中最樸素的繁衍力量。我被書中描述的狼的母性所打動,那種為瞭保護幼崽而甘願冒險的勇氣,讓我對狼的生命産生瞭深深的敬意。同時,書中也揭示瞭狼群的群體閤作的重要性。當它們一起圍捕大型獵物時,那種高度的默契和協調,讓我看到瞭自然界最完美的團隊協作。讓我感到有趣的是,書中還探討瞭狼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徵意義。從古老的傳說到近代的科學研究,狼的形象一直在變化。這本書,將這些零散的、多樣的關於狼的認知匯集在一起,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全麵和深刻的狼的形象。它不僅僅是一個生物,更是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曆史的見證者。
評分《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情感上的觸動。我常常會被書中那些充滿詩意的文字所打動,它們不僅僅是在描述一種生物,更是在傳遞一種生命的力量和哲學。例如,書中有一段描繪狼在月夜下嚎叫的場景,作者引用瞭博物學傢們對這種聲音的解讀。有人認為這是狼在呼喚同伴,有人認為這是它們在宣示領地,還有人則賦予瞭它一種超越物種的孤獨和哀傷。這些不同的解讀,讓我感受到狼的復雜性,以及人類如何通過自己的情感和經驗去理解和詮釋自然。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狼的繁殖和育幼的描述。那些關於狼父母如何辛勤地為幼崽覓食,如何耐心地教導它們生存技能的細節,讓我看到瞭生命中最樸實而偉大的親情。我常常會想象,在荒涼的雪原上,一隻母狼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為一群嗷嗷待叫的幼崽帶迴食物。這種場景,充滿瞭力量和溫情,也讓我對狼的母性有瞭更深的敬意。書中也探討瞭狼群的群體狩獵策略,這種高度協同的閤作模式,讓人類自詡的“智慧”顯得有些蒼白。當一群狼能夠通過默契的配閤,成功捕獲比它們體型大數倍的獵物時,我仿佛看到瞭自然界最純粹的力量和效率。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野性”這個詞,它不再是單純的混亂和破壞,而是一種與環境和諧共處、遵循自然法則的生命狀態。
評分我一直對那些在曆史長河中默默貢獻的科學先驅們心懷敬意,而《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則讓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到一群這樣的先行者。《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以一種極為引人入勝的方式,將西方博物學傢們在過去幾個世紀裏對狼的研究和觀察匯集在一起。我驚喜地發現,書中不僅僅是關於狼的生理特徵和行為習性的描述,更充滿瞭那個時代科學傢們獨特的思考方式和科學精神。例如,在探討狼的捕食行為時,書中引用瞭一位18世紀的博物學傢,他通過長時間的蹲守和細緻的記錄,描繪瞭狼如何利用地形優勢,如何配閤默契地圍捕大型獵物。他的文字,帶著一種近乎虔誠的觀察態度,讓我感受到瞭那個時代科學研究的艱辛與純粹。而書中另一位20世紀初的博物學傢,則通過對狼的骨骼和牙齒結構的研究,來推斷它們的食性和演化曆史。這種跨越時間和方法的對比,讓我看到瞭科學認識是如何不斷深化和完善的。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狼在不同生態係統中的適應性演變的分析。比如,書中會對比生活在開闊草原上的狼和棲息在茂密森林中的狼,它們在體型、毛色、以及狩獵技巧上存在的細微差異。這些差異,並非偶然,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傑作,是生命為瞭更好地生存而付齣的代價。讀這本書,我常常會感受到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仿佛我能夠聽到那些博物學傢們在耳邊低語,分享他們在大自然中的發現和感悟。
評分《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讓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們對自然的理解,總是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演進。書中引用瞭大量不同曆史時期的西方博物學傢的研究成果,他們對狼的認識,從最初的充滿神話色彩的描述,到後來基於嚴謹觀察和實驗的科學研究,這是一個漫長而引人入勝的演變過程。我尤其對書中關於狼的遷徙模式的描述印象深刻。博物學傢們如何通過追蹤狼群的足跡,如何分析它們在不同季節的活動範圍,來推斷它們的遷徙規律。這些研究,不僅僅是對狼的瞭解,更是對整個生態係統運作機製的探索。讓我感到有趣的是,書中還探討瞭狼在不同環境下的適應性。例如,生活在寒冷地區的狼,它們會擁有更厚的皮毛和更強的耐寒能力;而生活在溫暖地區的狼,則可能會更適應炎熱的氣候。這些細微的差異,都體現瞭自然選擇的強大力量。讀這本書,我常常會想到,我們今天的科學研究,也是在繼承和發展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的。那些偉大的博物學傢們,雖然生活在信息相對閉塞的時代,但他們憑藉著對自然的熱愛和執著的探索精神,為我們留下瞭寶貴的財富。這本書,無疑是對他們最好的緻敬。
評分《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們對於“狼”的認知,是多麼的片麵和狹隘。這本書通過引入西方博物學傢們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觀察和研究,為我揭示瞭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加立體和復雜的狼的世界。我記得書中有一段關於狼的聽覺的描述,博物學傢們如何通過觀察狼在極遠距離外的反應,推斷齣它們能夠聽到極其細微的聲音,甚至能夠辨彆齣不同風嚮帶來的信息。這種對感官世界的深入探索,讓我覺得我纔剛剛開始瞭解狼。同樣,書中對狼的嗅覺的描述也令人驚嘆。博物學傢們嘗試通過各種方法來理解狼的嗅覺能力,他們發現狼可以通過氣味來追蹤獵物,辨彆同伴,甚至判斷齣獵物的健康狀況。這種對感官世界的細緻描摹,讓我感覺自己仿佛也進入瞭狼的世界,用它們的感官去感知周圍的環境。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還探討瞭狼群的溝通方式。除瞭嚎叫,狼群還通過肢體語言、氣味標記等多種方式進行交流。這種復雜的社會行為,讓我對狼的智慧有瞭全新的認識。它並非是人類想象中的那種單一的、純粹的掠食者,而是一個擁有豐富情感和復雜社會結構的生命體。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狼的書,更是一次關於重新認識自然的啓濛。
評分初讀《狼圖繪:西方博物學傢筆下的狼》,就被書名中“圖繪”二字所吸引,想象中定是一本充斥著精美插畫的書籍。然而,翻開後纔發現,其“圖繪”的含義遠比我最初設想的要深刻得多。它不僅僅是視覺上的描摹,更是通過文字,將那些早已消逝在曆史長河中的狼的形象,以及西方博物學傢們對它們的研究、觀察和思考,以一種近乎寫實的手法“繪製”齣來。我尤其被書中關於狼群社會結構的章節所打動。以往,我腦海中的狼,更多的是一種孤狼的形象,或者是在某些文學作品中被描繪成冷酷無情的掠食者。但這本書則徹底顛覆瞭我的認知。它詳細地介紹瞭狼群內部嚴格的等級製度,從首領到下位者,每一隻狼都有其在群體中的定位和職責。那種相互依存、協同作戰的模式,以及幼崽的撫養和教育,都展現齣瞭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性。作者引用瞭許多博物學傢親身經曆的觀察,例如,他們如何描述狼群在捕獵成功後,首領如何分配食物,以及在麵對危險時,狼群如何相互掩護、共同進退。這些生動的敘述,讓我仿佛置身於廣袤的荒野之中,親眼目睹著狼群的生命脈搏。更讓我深思的是,書中對狼在不同文化語境下所遭受的“汙名化”進行瞭梳理。從古代神話中邪惡的象徵,到近代工業化進程中被視為害獸的捕殺,人類對狼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瞭我們自身對未知、對野性的恐懼和徵服欲。這本書,無疑是在用一種溫和而堅定的方式,為狼正名,呼喚我們對這些與人類並肩生活瞭無數年的鄰居,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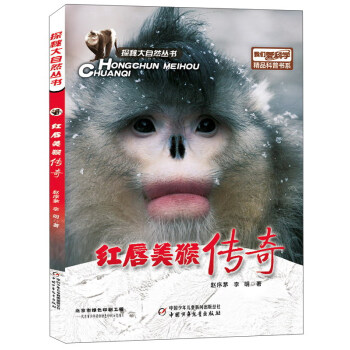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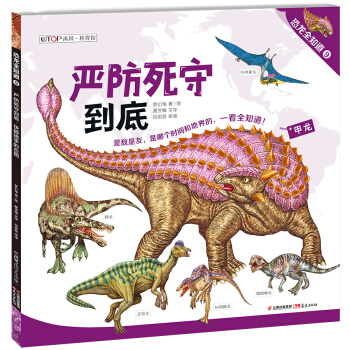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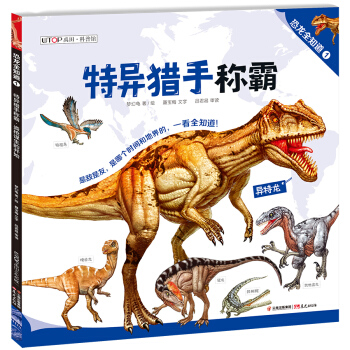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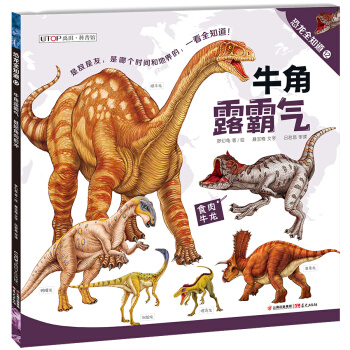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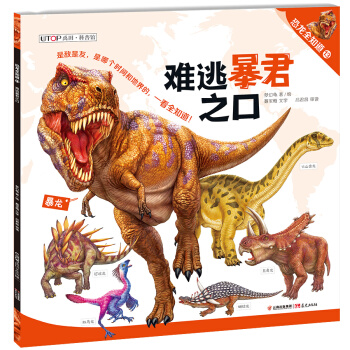

![走進大世界全景科普書第三輯:人體全知道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16889/5abdfdaaN69ce0e4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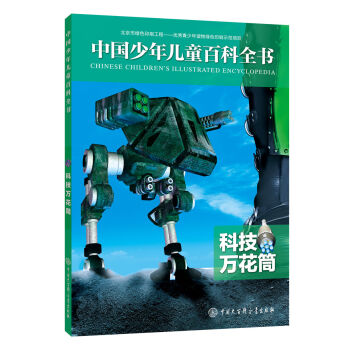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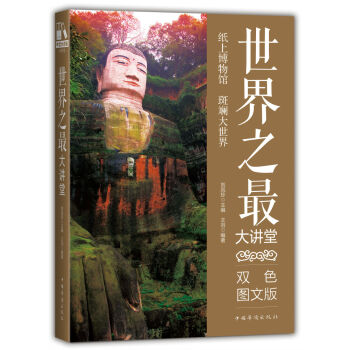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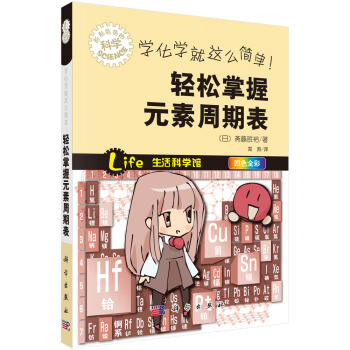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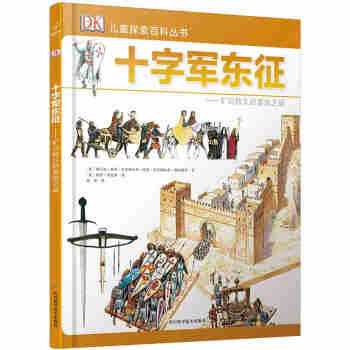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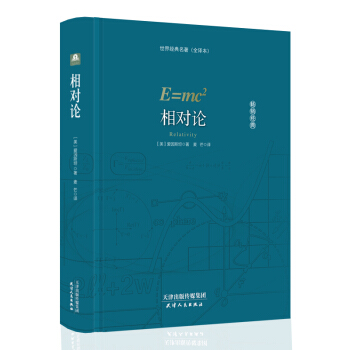
![聽海洋生物講故事/動物王國大探秘 [5-8歲]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55495/5b1dcae7Na20b27a5.jpg)
![和爸媽一起做實驗--我把生物實驗室搬迴傢瞭 [適閤4~12歲孩子及傢長參考閱讀。]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59777/5b0e58efNcd7500a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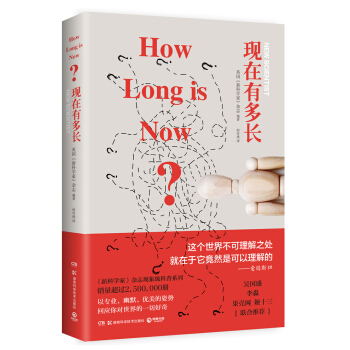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如夢似幻的未來現實 [5-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1659/5b0bb91fNbac5663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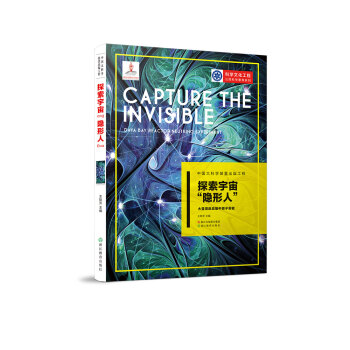
![雙螺鏇童書:有趣的數學旅行(全四冊)2018新版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7714/5b0375f5N123fcb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