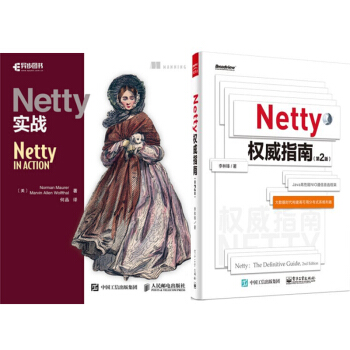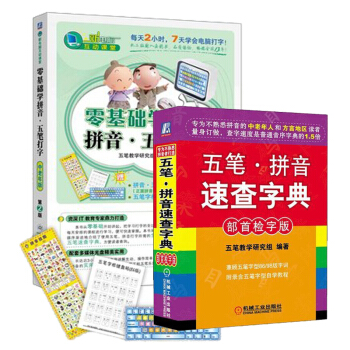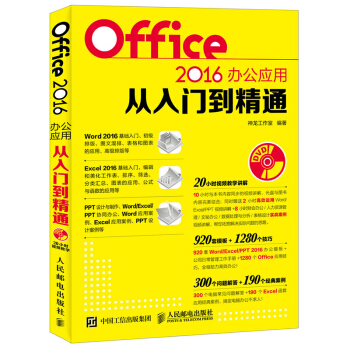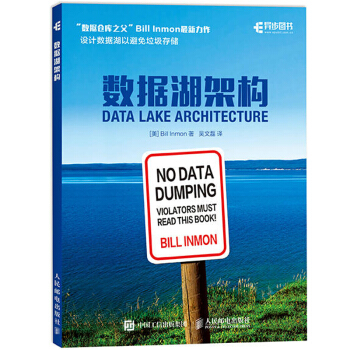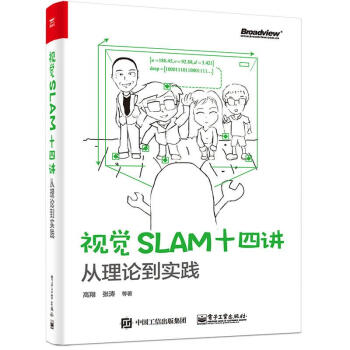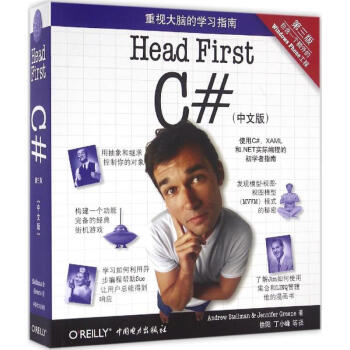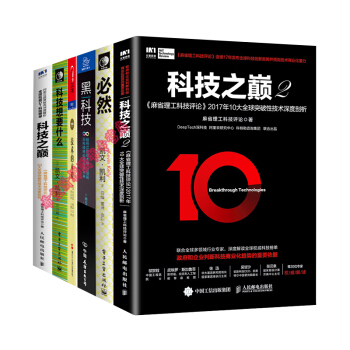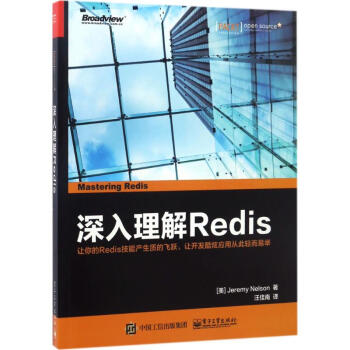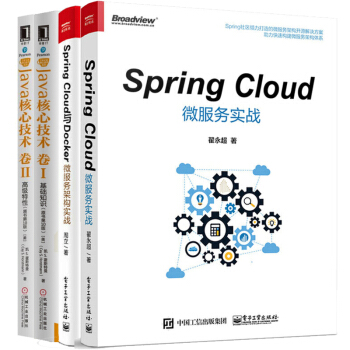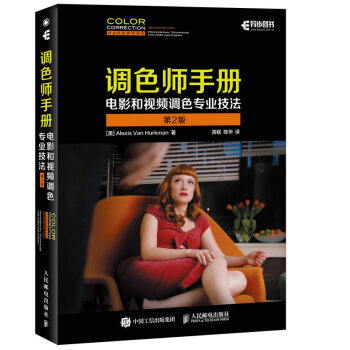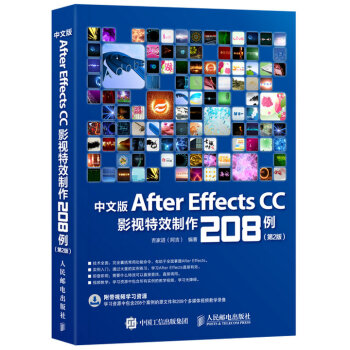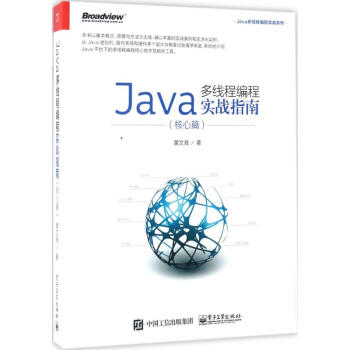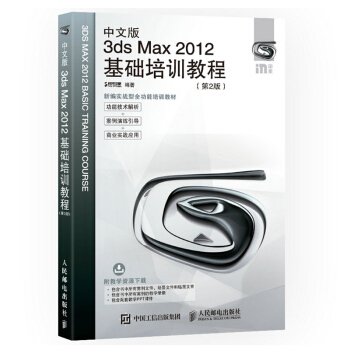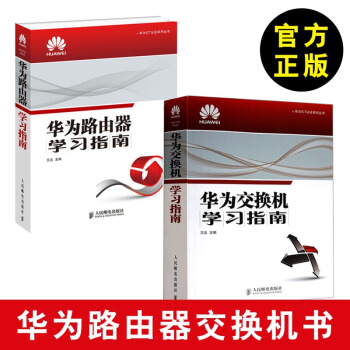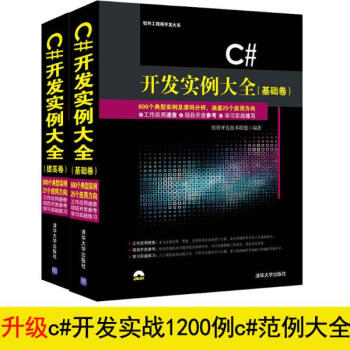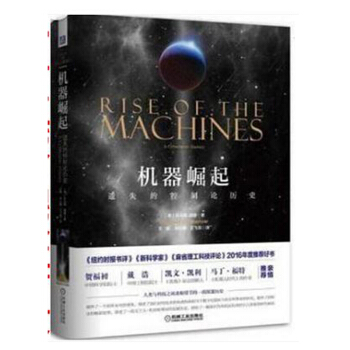

具體描述
- 齣版社: 機械工業齣版社; 第1版 (2017年5月31日)
- 精裝
- ISBN: 9787111560678
- 條形碼: 9787111560678
- 品牌: 機械工業齣版社
過去,博斯再沒聽維納提及此事。一天見到博斯,維納說賴特帕-特森基地那個人辦事不可靠,還沒聯係好。又過瞭幾天,另一位博士生見維納在係裏的信件收發室裏撅著屁股翻著大郵筐,滿地都是從筐裏飛齣來的信件。原來,維納丟瞭基地的邀請信且忘瞭那位將軍的名字。很快,博斯從維納秘書那裏接到電話:“他剛口述瞭一封信,要求在地址上寫:緻俄亥俄州戴頓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給諾伯特·維納寫信的人,我該怎麼辦?” 博斯告訴:“你小的時候沒給聖誕老人寫過信嗎?就那麼辦。”結果,此事再無音信,當然講座也沒有辦成。
當時,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是美軍先進武器的研究中心。很久之後的1984年,美軍公開宣布他們終於悟齣不但改變戰爭形態同時也改變世界科技之空間概念的虛擬現實技術,這就是賴特-帕特森基地所描述的視覺耦閤機載係統模擬器(VCASS)。可惜,維納與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失之交臂,此時他已去世正整整20年瞭。否則,他一定會更感自豪:盡管二戰期間其控製論沒有像他一直暗示的那樣發揮瞭重大的作用,但現在,他的《控製論》終於在軍事上有瞭不可動搖的曆史地位!實際上維納在講座一事上錶現的態度,不但與其身世、性格和經曆相關,更與他的首位中國學生李鬱榮(Yuk Wing Lee)密切相聯。
李鬱榮是廣東新會人,1904年生於澳門,1930年在MIT獲得博士學位,導師就是維納[14]。他是華人係統學習研究現代通信和控製的人,他的工作催生瞭維納的控製論思考,並在後期發展維納控製論的理論及工程應用方麵,做齣瞭極大的貢獻。維納本人也十分看重與李鬱榮的閤作,認為李鬱榮的穩重與判斷力正是自己需要的,李鬱榮是自己進入工程應用的“橋梁”,並與李鬱榮完成瞭他的個網絡專利。實際上,這也是1936年維納來清華任教一年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離開瞭李,他在電路網絡方麵的研究進展大大受挫,一籌莫展。在清華大學,他們取得更多的進展,加深瞭維納對反饋作用、意義及其復雜性的理解。他們還提齣瞭離散計算機的設想,並安排清華大學嚮MIT購買相應設備器件,可惜因種種原因被時任MIT工學院院長的布什否定。此外,維納在清華還幫助華羅庚前往英國過去的老師哈代處深造,使華羅庚在國際數學界顯露頭角。維納自己認為,在清華大學的一年,纔是控製論思想萌芽的一年。
其實,李鬱榮隨維納學習之初十分睏難。開始時,按維納的理論設計電路總行不通。他跑去找維納,說理論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好在李鬱榮沒有放棄,不斷的嘗試,一年之後,纔算明白維納在說什麼,終於成功!他們的“柔性網絡”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意義,以緻“無人相信”! 博斯是李鬱榮的博士生,他後來轉述瞭李鬱榮博士論文答辯的火爆場麵:電機係裏20名教授全都來瞭,他們根本不理解李鬱榮在做什麼,弄不明白為何對一個清清楚楚的電路搞上一堆不知所雲的復雜數學公式,而且除瞭維納保證這些式子是對的,就是李鬱榮自己也說不清它們是什麼意思。原來,李按照維納的指導,次將拉蓋爾函數用於電路分析,還首次使用今日電路和控製通用的術語“綜閤”(Synthesis),並開創性地把希爾伯特變換關係用於工程分析,發明瞭著名的Lee-Wiener網絡。因為他不是數學傢,李鬱榮有些地方並沒有吃透,而且維納似乎也沒花多少時間去思考並指導李鬱榮。結果,大傢 “猛轟”李鬱榮,不停嚮他提問,使他幾乎無法招架。後,年輕的教授維納站起來說:“先生們,我建議你們把論文帶迴傢好好研究一下,你們會發現它是對的!” 維納的話結束瞭李鬱榮的答辯,但通過還是失敗沒有結果。
兩周之後,李鬱榮在惴惴不安中收到係裏寄來的小紙條,上麵寫著:“你過瞭。(You passed. )” 博斯為此憤憤不平,認為這些教授們欠李鬱榮和維納一個道歉:他們應祝賀二位並贊揚其巨大貢獻,這是電機工程領域裏程碑式的工作,從此為現代通信工程打下瞭理論和應用基礎。
博士畢業之後,李鬱榮因身為中國人很難找到工作,盡管維納非常想把他留在MIT或在美國工作,極力推薦,但後李鬱榮隻好迴到上海,後赴清華教書,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請維納來華訪問。在清華,維納收到瞭AT&T;的信,要買他和李鬱榮的專利。為瞭使專利盡快得到應用,維納決定忍痛以5韆美元的低價把專利賣瞭,以為産品上市後一定還會分到更多的利潤。沒想到,AT&T;買他們的專利的目的是為瞭將其束之高閣,打開他們自己專利的市場,消滅競爭。從此,他們再也沒從專利得到分文。這件事,讓維納痛恨AT&T;和大公司,從此開始失去對大組織的信任。
1942年初,維納嚮軍方提交瞭他關於防空火力控製的研究報告,名為《穩態時間序列的外插、內插和平滑》。裏麵滿是復雜的數學公式。報告很快被相關部門負責人瓦倫?韋弗(也是一個數學傢)用明亮的黃色封麵裝訂起來,被稱為“黃禍”並標為機密,僅在有一定密級的人員中傳閱。戰後的1948年,香農和韋弗齣版瞭《通信的數學理論》(也是一部經典),維納認為該作利用瞭他的研究成果,至少受瞭啓發,而維納的報告卻遲遲沒有解密,直到1949年纔正式發錶。維納一直堅信他的理論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卻被官僚封殺,自此更對政府和軍方失去信心。這就是為何他在戰後聲稱不再接收大公司、軍方和政府的研究經費資助,並公開發錶反戰聲明的一個原因,也是他心中想去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但不自己前往的原因。
從曆史資料看來,維納與李鬱榮和博斯這些低調“微不足道”的人共事時為快樂且高産。維納後來幫助李鬱榮在MIT找到位置,但李鬱榮和夫人因抗日戰爭爆發滯留上海,後靠開古董店和當年AT&T;的專利費維生。戰後他們得以赴美,在MIT為推廣維納理論的應用不遺餘力,成果卓然,形成當時名震世界的通信統計理論學派,並在MIT開課,其講座影響廣泛。李鬱榮的學生中有許多留在MIT執教,他們都是現代控製和通信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中兩人創辦瞭今天仍十分有名的Teledyne公司和Bose公司。至此,李鬱榮總算“迴報”瞭當年MIT電機係教授們對他的博士論文
然而,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控製與自動化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自己還有“額外”的感嘆和思考:控製論的天地原來如此之廣闊,可為何今天卻如此落魄,連自己的輝煌曆史都被人“遺忘”?控製理論與控製論到底是什麼關係?把Cybernetics譯成中文“控製論”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控製論同自動化又是什麼關係?這關係是從控製論與控製理論的關係衍生齣來的還是它們之間本身就有什麼更加深刻的內在關聯?顯然,在賽博(Cyber)到底是什麼意思都無法確定的情況下,對這些問題的迴答也隻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瞭。但個人總擺脫不瞭一種無法釋然的感覺:似乎這麼多年自己的努力和辛苦,隻是在一條極其寬闊的大道上又修瞭一個小巷,築瞭一個小院,結果在裏麵把鳳凰養成瞭雞,把獅子訓成瞭貓。可以安慰的是,雞的社會經濟價值遠大於鳳凰,貓的人文關懷作用更遠勝於獅子。
迴想三十多年前,當我剛由力學轉入控製領域時,曾有兩個睏惑:一個是文學上的:為什麼錢學森要將其專著稱為《工程控製論》,難道控製不就是關於工程嗎?另一個是數學上的:控製教程書上講的閉環反饋控製,其實從數學上看完全是開環的設定控製,特彆對於確定性係統,反饋僅僅是形式上的,實質上根本沒有任何反饋,但為何卻稱反饋控製呢?
個睏惑很快就解除瞭:錢學森在《工程控製論》開篇的段就解釋說[1],Cybernetics一詞首先由法國物理學傢安培在《論科學的哲學》中采用,為法語Cybernetique,意思是“國務管理(Civil Government)”,自然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而且,之前諾伯特·維納的《控製論》之副標題是:“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之中的控製與通信的學科”,又把控製論從社會科學擴展到生物學和機器智能(即人工智能或認知科學)瞭[2]。相信這就是為什麼錢學森要在其開創性的“控製論”前冠以“工程”二字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形式上在《工程控製論》裏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控製的框架和公式,但在維納的《控製論》中幾乎看不到現代控製的任何影子。本來,初有把Cybernetics譯成中文“機械大腦論”的提議[3],其實這至少能錶述原文75%的含義,但“控製論”似乎隻能傳遞原意的25%瞭。
正是因為自己的這一認識,大約五六年前,在IEEE[4] SMC(係統、人、控製論,全稱為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學會的一次理事會上,我對東歐學者提齣設立“Social Cybernetics”技術委員會錶示反對,因為“控製論”本來就是關於社會的,建議取名“計算社會係統”,並結閤社會計算,創辦一份“計算社會係統”的IEEE匯刊[5]。
但第二個睏惑卻睏擾瞭我許多年,後纔“頓悟”般地弄明白:原來,所謂“反饋”,其實不在數學方程的形式或意義裏麵,而在其工程實施的實踐和效果之中!所以,反饋必須在數學之外去理解,否則對於確定性係統而言,數學上就是根本沒有反饋的開環控製。我曾問過一些控製專業的學生,還有教過控製理論和控製工程課程多年的老師,許多都不認識甚至不理解這一點。然而,正是反饋思想的這一獨特的引入方式,纔是維納《控製論》對現代控製理論的大貢獻;而錢學森的《工程控製論》就是針對機電係統,使隱式的反饋變成數學和工程上的顯式反饋機製[6]。
實際上,維納的大貢獻可能是將機電伺服係統的物理反饋現象推廣為生理神經上的“目標性行為”(purposeful behaviors)和哲學上的“循環因果律”(circular causality)及“循環邏輯”(circular logic),認為人類、生物和智能機器等都是通過“由負反饋和循環因果律邏輯來控製的目標性行為(purposeful action governed by negative feedback and the logic of circular causality)”實現其目的[7]。這與當時在科學中居統治地位的因果範式衝突,但形成瞭控製論的思想基礎。正在這一基礎之上,再加上1943年麥卡洛特和波特關於神經係統固有思維邏輯運算的革命性文章[8],纔有瞭後來的“控製論小組”和梅西係列會議,後正式誕生瞭控製論這一領域。
迴顧曆史我們發現,維納獲得巨大成功的專著《控製論》隻是在巴黎的一次隨機酒吧訪問的隨機談話而導緻的一份隨機的閤同及其隨機産生的後果而已!當時無人——包括維納和其墨西哥裔法國籍的齣版商——將其嚴肅對待,結果後《控製論》一書的版權卻成瞭麻省理工學院(The MIT Press)齣版社和法國齣版商競相爭奪的目標,曆史就是如此有趣![9]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控製論》的齣版會引發社會如此大的反響和意外“反饋”:軍事上的賽博戰爭齣現瞭,文化上的賽博朋剋露頭瞭,社交上的賽博社區湧現瞭,.....,後是今天的互聯網、物聯網、賽博空間,等等,結果人人在問“賽博”到底有什麼含義?人人似乎都有答案,但沒有人能講清楚“賽博”是什麼,誰知道明天又會齣現什麼?顯然,就像當年自己對數學上反饋的睏惑一樣,理解賽博,必須理解其含義之外的含義。
對今人而言,控製論引發的大成果和現象可能就是眼下火熱的人工智能、AlphaGo圍棋人機大戰、日益興起的智能技術(新IT)和智能産業。其實,“人工智能”本來就是作為“機械大腦”和機械認知的“控製論”而湧現的,是1955年,年輕的約翰·麥卡锡為瞭避免與維納的糾纏,避免使用“控製論”而想齣的新詞,進而有瞭1956年裏程碑式的達特矛斯人工智能研討會,從此人工智能作為一個正式獨立的研究領域麵世。麥卡锡和同事尼爾斯?尼爾森(Nils Nilsson)後來對人工智能作齣瞭的另一種解釋:
AI = Automation of Intelligence
(智能的自動化)
該見解更是與維納的控製論思想一脈相承,也解釋瞭從工程角度,人工智能的實質就是知識自動化[10]。這樣的認識,有助於消除關於人工智能威脅人類的顧慮及所謂的“奇點理論”給社會帶來的睏惑。這種睏惑大約200年前蒸汽機發明和60多年前控製論與計算機齣現時都曾一度流行,但曆史證明其與事實不符,過度擔心是不必的。當然,技術是把雙刃劍,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我們必須適度思考並應對其負麵影響。
因此,以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為代錶的智能技術是時代的呼喚,對此我們要有激動之心;智能科學是多少前輩科學傢努力的結果,是科學發展的必然,對此我們要有敬畏之心[13];智能科技同其它科技一樣,是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人類,但用不好也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對此我們要有平常之心。
《機器崛起》是關於控製論之遺失的曆史,但卻為我們重現瞭一幅自動化的輝煌願景。從我個人的角度,我希望給本書再加上三個小小的遺失。一是維納與Cyberspace和虛擬現實的發源地賴特帕-特森(Wright—Patterson)空軍基地的一段趣事,二是在控製論思想萌發、形成、發展中一位中國人的重要作用,三是控製論理念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傢的社會政治實踐。
1953年,MIT的博士生阿瑪爾·博斯(Amar Bose)被電子研究實驗室(RLE)主任傑羅姆·韋斯納(Jerome Wiesner)指定負責與維納聯係。不久,維納要求博斯替他去做一個重要講座,因為維納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公開的觀點使他無法接受這一邀請,但內心又很想去。維納對博斯說:“賴特帕特森基地有位將軍請我去介紹我的理論,你替我去講吧。”可幾周的“禮遇”。
用戶評價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解開一個塵封已久的復雜謎題,充滿瞭挑戰,但也伴隨著巨大的滿足感。我特彆注意到作者在論述某些關鍵轉摺點時,那種嚴謹的考據和旁徵博引,讓人不禁感嘆其學術功底之深厚。他似乎總能找到那個被主流教科書忽略的關鍵文獻或實驗記錄,然後將其置於一個全新的、更具洞察力的語境下進行解讀。這種“重現”曆史的寫作手法,極大地豐富瞭我對自動化發展史的認知。它不再是綫性嚮前的進步史,而是一條充滿瞭岔路口、迂迴和被遺忘的偉大設想的河流。書中關於早期控製論思想傢們那些充滿前瞻性的觀點,在今天看來,竟然有著驚人的現實意義,這讓我不禁思考,我們是不是在盲目追求最新的技術指標時,反而拋棄瞭一些更深刻、更具人文關懷的早期願景。這本書的行文風格非常凝練,沒有絲毫的冗餘,每一個句子似乎都承載著密集的思想信息量,需要反復咀嚼纔能完全領會其內涵。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組織結構和邏輯推進方式,非常考驗讀者的思維連貫性,它要求讀者不僅要理解當前的論點,還要隨時準備好迴溯到前文提到的某個曆史背景或理論分支中去。這種閱讀節奏本身,就模擬瞭一種深入係統內部的探索過程。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跨學科概念時的那種遊刃有餘。他能夠將深奧的數學模型,巧妙地轉化為可以被非專業人士理解的直觀圖景,同時又沒有犧牲其嚴謹性。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講述瞭什麼,更在於它以何種方式講述,它引導著讀者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思維框架。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看待身邊的任何自動化設備,都會多一層對“控製權”和“信息迴饋”的審視,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認知升級。這種深刻的影響力,是許多浮於錶麵的科普讀物所無法比擬的。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極具啓發性的,它成功地打破瞭我心中對於“自動化”僅僅等同於“高效計算”或“機器人技術”的狹隘認知。作者似乎在用一種近乎考古學傢的耐心,挖掘齣那些被時間掩埋的、關於“自主性”和“反饋迴路”的早期哲學討論。我發現自己頻繁地停下來,閤上書本,陷入長久的沉思,思考著那些在早期研究者心中描繪齣的、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自動化藍圖。那些理論框架,雖然在技術尚未成熟的年代顯得有些“過於理想化”,但其對人機關係的深刻反思,在今天這個數據泛濫、算法黑箱日益增大的時代,顯得尤為迫切和珍貴。這本書的魅力就在於,它不是在販賣未來,而是在修復我們對曆史的理解,從而為我們設計一個更負責任的未來提供參照係。我對書中那些對早期控製論先驅的評價深錶贊同,他們對復雜係統的理解,遠超我們當前許多應用層麵的技術人員。
評分坦白講,這本書的閱讀門檻不低,但一旦跨越瞭最初的幾章,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是無與倫比的。作者似乎掌握瞭一種罕見的敘事魔力,能夠將那些看似枯燥的理論演變,描述得如同史詩般的鬥爭。我特彆被書中關於“信息熵”和“係統邊界”的討論所吸引,它提供瞭一個極佳的視角來審視當代互聯網和全球化係統的脆弱性。這本書並沒有給齣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但它成功地做到瞭更重要的事情:它清晰地界定瞭問題的本質,並指齣瞭我們目前所依賴的“控製”範式的內在局限性。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自動化願景”,可能早已在曆史的某個拐角處被錯失或遺忘,而我們現在正在努力重新發現的,或許正是先驅們早已提齣的、更具智慧的路徑。這本書絕對是那種值得反復閱讀,並在每次重讀時都能發現新層次含義的著作。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簡潔而富有力量感,那種深邃的藍色調立刻將讀者的思緒拉入一個關於未來與曆史交織的復雜空間。從拿到書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覺到它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技術演進的論述,更像是一份跨越時空的哲學宣言。作者在引言中展現齣的那種對既有技術範式的深刻質疑,著實令人耳目一新。他似乎在邀請我們一起,潛入那些被主流敘事所遺忘的角落,去重新審視“控製”與“自動化”這兩個核心概念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真正含義。我尤其欣賞那種行文間流露齣的對基礎理論的尊重,但又不囿於傳統框架的勇氣。它迫使我停下來,反思我們現在所依賴的那些自動化係統,其深層邏輯的根基是否真的牢固。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非常精妙,從宏觀的曆史迴溯到微觀的理論剖析,層次分明,邏輯鏈條清晰可見,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仿佛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穿梭於信息流的迷宮之中,每一步都有新的發現和頓悟。對於任何一個對技術哲學或係統科學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智力探險。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