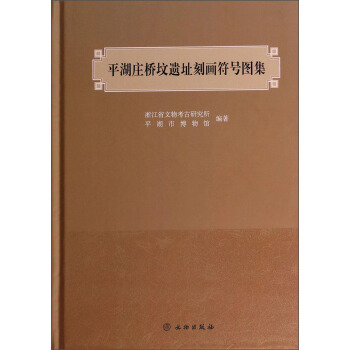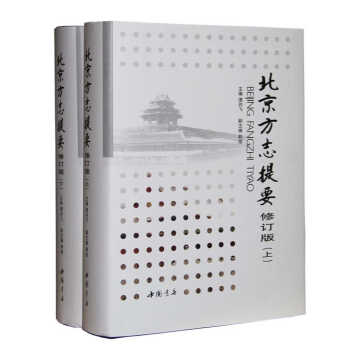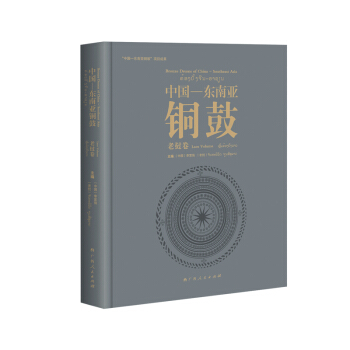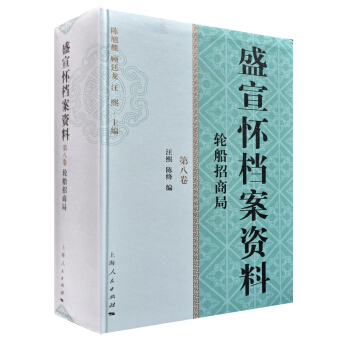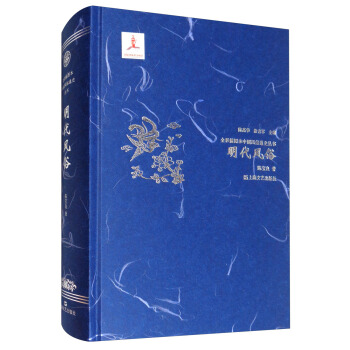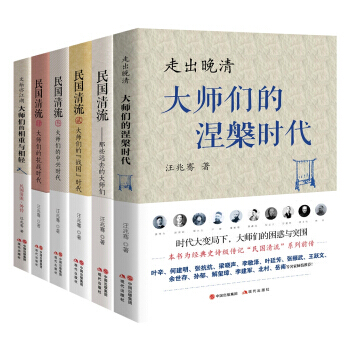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代民国清流,一代民族脊梁,在糜烂的时局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中国近现代史上具盛名的文化大师们的群体雕像,生动,鲜活,立体!
著名编辑家、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老先生呕心沥血之作!
内容简介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活跃、文化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作者简介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精彩书摘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1
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无心计、坦诚却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高上的艺术”。他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的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啊,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李大钊、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代理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人物。李大钊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用户评价
在阅读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之前,我对民国历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充满了各种新闻报道和影视剧的剪影。然而,这本书将那些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和深刻的图景。汪兆骞先生的写作,有一种强大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他能够清晰地梳理出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尤其喜欢他对于“清流”群体的挖掘,他展现了这些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是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的。这些人物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发现,在那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正是这些“清流”的存在,才使得社会不至于完全失去方向。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个精心打磨的短篇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感染力。读起来,我常常会被那些荡气回肠的情节所吸引,也会为那些令人唏嘘的命运而感叹。总而言之,这套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民国历史的新窗口,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也对那些为理想奋斗的先贤们有了更深的敬意。
评分我对民国史的兴趣,更多的是源于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无疑满足了我对这一块的求知欲。汪兆骞先生的文字,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他将那些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尤其喜欢他对“清流”的界定和描绘,他不仅关注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坚持原则的官员,更将目光延伸到教育、文化、学术等领域,发掘那些默默奉献、坚守理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的故事,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挣扎,也看到了他们的傲骨与担当。书中穿插的许多史料和轶事,都极具史料价值,让我对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我常常会为那些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人物而感动,他们的故事,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解。总的来说,这套书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更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意。
评分对于民国这段历史,我一直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对其开放与进步的赞赏,又有对其动荡与破碎的惋惜。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恰好捕捉到了这种复杂性,并且以一种更加立体和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汪兆骞先生的文字,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他能将那些沉重而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他对“清流”人物的挖掘,他展现了这些人在乱世中的坚守与担当,他们可能没有改变历史的洪流,但他们的存在,却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书中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物都有涉及,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全景图。我尤其被其中对一些知识分子在困境中依然坚持学术探索的故事所打动,他们的执着,是对时代最好的回应。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十分巧妙,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篇,但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画卷。总的来说,这套书让我对民国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也让我对“清流”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
评分我常常觉得,历史的解读,就如同剥洋葱,层层深入,才能触碰到最核心的真切。而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无疑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剥洋葱的工具。汪兆骞先生的叙事,不仅仅是事件的堆砌,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他对于“清流”群体的关注,让我看到了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仍然有那么一群人,用他们的智慧、良知和坚持,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我尤其欣赏他对这些人物的描绘,没有简单的批判或赞美,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选择,理解他们的局限,也理解他们的伟大。书中那些生动而充满细节的描写,让我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之中,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我尤其被其中一些关于文化、教育领域“清流”的故事所吸引,他们的坚持,对后世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读来令人感慨万千。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独特,既有史书的厚重感,又不乏散文的灵动性,读起来丝毫不枯燥,反而有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评分作为一名对民国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尝试过不少相关的书籍,但真正能让我眼前一亮,并且愿意反复阅读的,屈指可数。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汪兆骞先生的叙事风格,有一种温润而坚韧的力量。他笔下的民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标签可以概括的,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没有回避那个时代的光辉,也没有掩盖其阴暗的一面。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清流”的定义和解读,他不仅仅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更深入到文化、教育、学术等各个领域,发掘那些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的经历,往往更能触动人心,因为他们的斗争更具普遍性,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更具代表性。书中对于时代背景的铺陈也做得相当到位,读起来丝毫不会感到生涩,反而能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的脉搏。我个人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民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多元而丰富的面向,不仅仅是政治的动荡,更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
评分我一直对那种能够拨开历史迷雾,还原真实面貌的著作情有独钟。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无疑满足了我对这一点的所有期待。汪兆骞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乏文学的温度。我最欣赏的是他对“清流”精神的解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清流”代表了一种独立、正直、不随波逐流的精神风貌。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描绘,没有过度拔高,也没有刻意贬低,而是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思想、言行以及所处的环境。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一些名不见经传但同样具有风骨的人物事迹的挖掘,这让历史的画卷更加丰富和立体。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在那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是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他们的坚持,又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启示?这本书的叙事节奏也把握得非常好,既有宏大的历史背景铺陈,也有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读起来引人入胜,不会感到枯燥。总的来说,这套书不仅仅是一次对民国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那个时代精神的致敬,让我深受启发。
评分我一直相信,历史的温度,就藏在那些被忽略的人物和细节之中。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恰恰让我感受到了这份温度。汪兆骞先生的笔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他将目光投向了民国时期那些“清流”人物,这些人可能没有掌握大权,但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时代的风气,传承着民族的精神。我尤其欣赏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没有将他们神化,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做的努力和选择。书中的许多细节,都让我深受触动,比如一位学者在贫困中坚持办学的决心,一位文人在动荡中依然守护文化遗产的执着。这些故事,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性之光,也让我对“清流”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的叙事方式也十分独特,既有宏观的历史背景介绍,又有微观的人物故事讲述,读起来既有知识性,又有感染力。
评分我一直认为,历史的魅力在于细节,而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恰恰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它不像一些流水账式的史书,只是简单地记录“谁在何时做了什么”,而是深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人物动机、社会背景以及潜在的影响。汪兆骞先生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他能够将复杂的政治斗争、社会思潮娓娓道来,又不失可读性。我特别欣赏他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摹,比如某位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某位学者在困境中的坚持不懈,这些细节都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有血有肉。书中穿插的许多史料和逸闻趣事,也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惊喜。我常常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所打动,比如某个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小故事,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和事件的堆砌,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我尤其喜欢书中对“清流”群体的关注,他们或许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对那个时代的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阅读这套书,就像是在与那些历史人物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的选择和无奈。
评分一直以来,我对民国时期那种既有新思想的涌现,又有传统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充满了好奇。这套《民国清流经典套装》就如同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那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年代。汪兆骞先生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他不仅仅是讲述历史事件,更是深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人物命运和社会思潮。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清流”群体的描写,他们身上那种不为强权所屈服、坚持真理的风骨,在那个时代尤为可贵。我看到了他们在政治风暴中的挣扎,在学术殿堂里的坚守,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思考。书中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没有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我尤其被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所打动,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们的坚持和选择,却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光辉。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很吸引人,流畅而不失典雅,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乏文学的趣味。它让我对民国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评分这套书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一直以来,我对民国时期那种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年代都充满了浓厚的好奇。然而,市面上很多关于民国的书要么过于学术化,要么流于八卦轶事,很难找到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的读物。看到“民国清流经典套装”这个名字,我就心头一动,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翻开第一页,就被汪兆骞先生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笔触所吸引。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将那些鲜活的人物、跌宕起伏的事件娓娓道来。我尤其喜欢他对于那些“清流”人物的刻画,他们身上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那种在乱世中坚守理想的执着,读来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书中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描绘也十分生动,从政客的尔虞我诈,到文人的风雅集会,再到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都勾勒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忽略的小人物的关注,更是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立体和真实。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那个年代,亲眼见证着历史的 unfolding。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是我在其他书籍中鲜有获得的。总而言之,这套书不仅是历史知识的宝库,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让我对民国那个时代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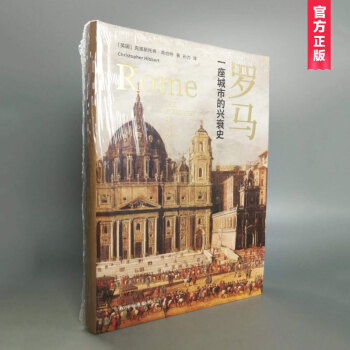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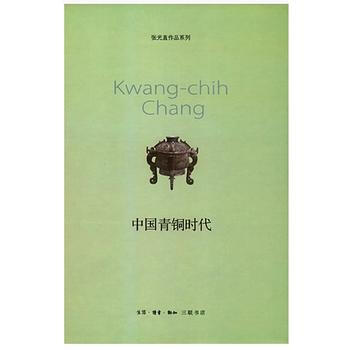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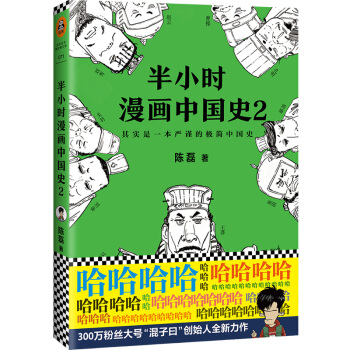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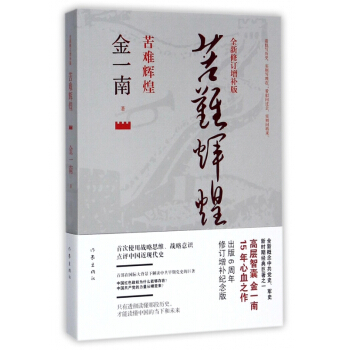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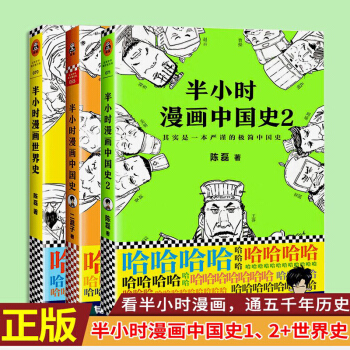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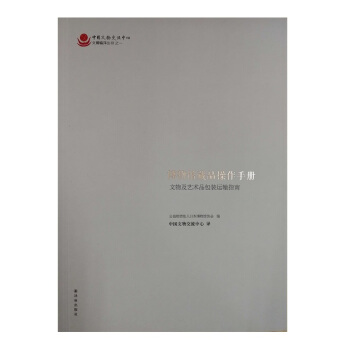
![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10卷) [Complete Works of Statues in Lingmen Grotto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683858/6b2e1511-c988-44b9-8c23-ebf26159b1f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