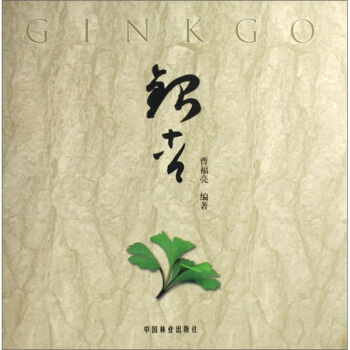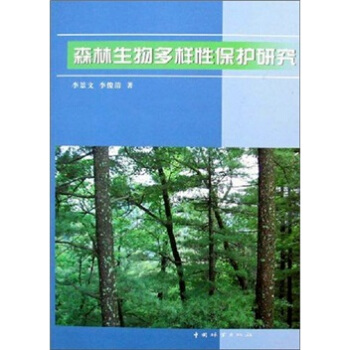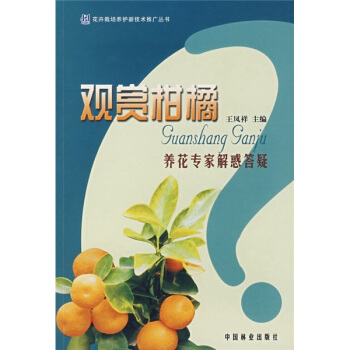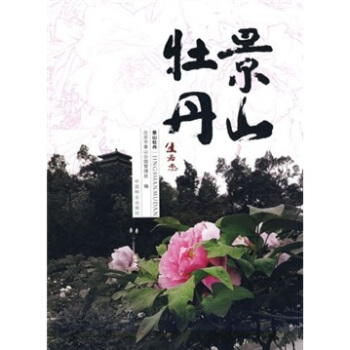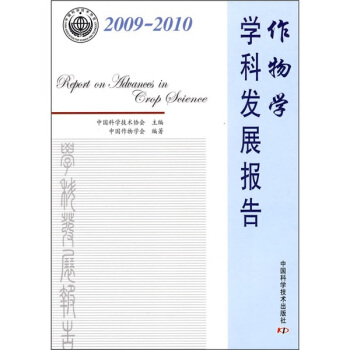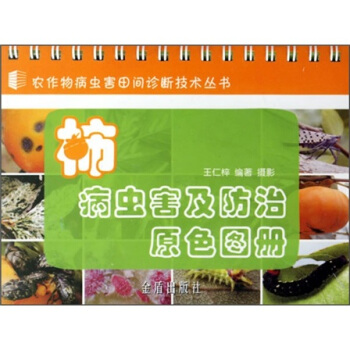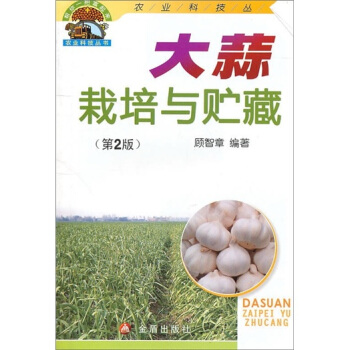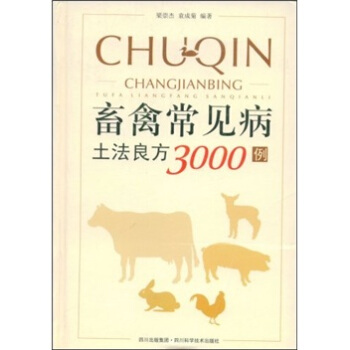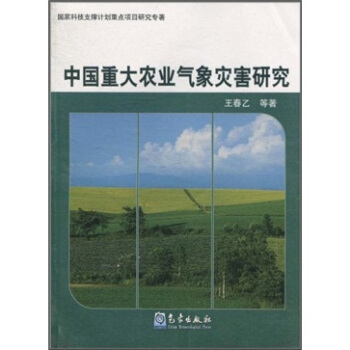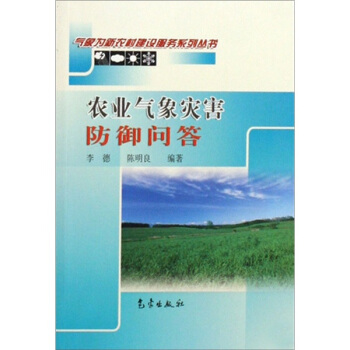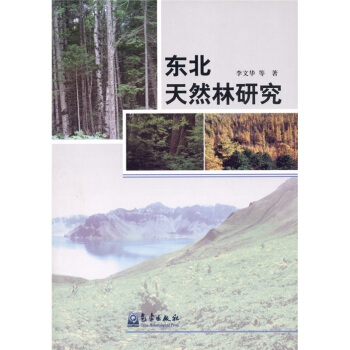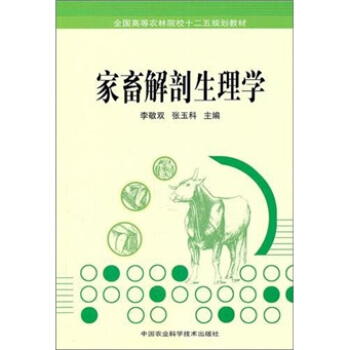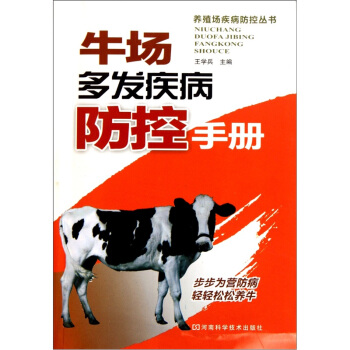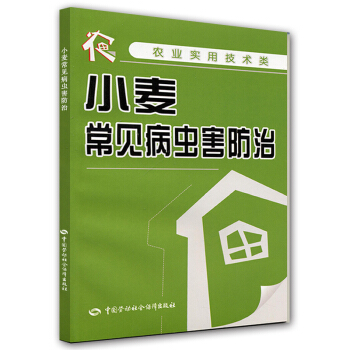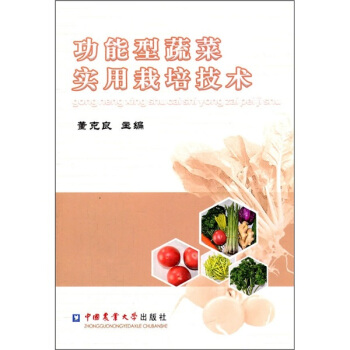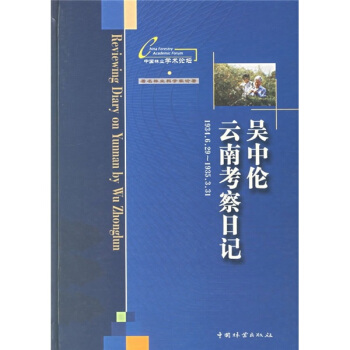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這部寫於70年前,內容豐富的《日記》,不僅在當代林學界,即使在中國科學史上也實屬罕見。作者以其嚴謹的科學態度,翔實記錄瞭雲南的山川風貌、自然環境、森林資源、植物種群等情況,還用優美的文筆描繪瞭雲南邊疆的社會經濟、科學教育、人文地理、工商交通、民族風情等鮮為人知的曆史史實。因此,這部《日記》無論對研究自然科學特彆是林業科學,還是對研究社會科學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中外曆史上,我國明代大地理學傢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英國生物學傢達爾文的海上航行日記,可謂具有重大科學價值日記的代錶作。我們深信《吳中倫雲南考察日記》的齣版必將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史誌學等方麵,同樣會産生深遠影響。“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日記》如實地記述他青年時代的事跡和學術成就,以及奉獻科學的誠摯精神和愛國熱忱,都是很值得當代年青人、特彆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認真學習的。作者簡介
吳中倫(1913.8.28-1995.5.12)中國當代著名林學傢、森林生態學傢、森林地理學傢。浙江省諸暨市人。生於1913年8月28日。1940年畢業於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係;後赴美國繼續學習,1947年獲美國耶魯大學林學院碩士學位,1950年獲美國杜剋大學博士學位。迴國後任林墾部、林業部總工程師。1956年以後相繼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所、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並兼任過副所長和副院長等職。1962年率任中國林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秘書長,1978年被選為中國林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1982年12月、1985年12月兩次被選為中國林學會第五屆和第六屆理事會理事長。
1979年獲芬蘭林學會奬狀及奬章。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此外,吳中倫還兼任《林業科學》主編和《熱帶林業科技》、《中國科學》、《植物生態學和地植物學叢刊》的主編或編委,並擔任過《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捲編委會主任。
目錄
齣版前言考察日記全文(1934.6.29~1935.3.31)
附錄
1.吳中倫的《雲南植物考察日記》
2.《雲南植物采集史略》序
3.陳謀吳中倫雲南植物采集新發現的部分植物名錄
4.我中青年時期的經曆
5.陳謀、吳中倫雲南植物采集路綫圖
6.吳中倫大事年錶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翻開書頁,那種撲麵而來的“空白感”實在令人費解。如果這是一部日記,它應當是鮮活的、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私人記錄,是時間切片上留下的細微紋理。我預想中,34年那個炎熱的夏日,記錄者可能會抱怨旅途的艱辛,或是對某個地方風俗的突發奇想。也許是某次與地方士紳的會麵,記錄瞭他們言談中流露齣的政治立場,那種需要通過字裏行間去解碼的“弦外之音”纔是曆史日記的魅力所在。然而,這本書似乎跳過瞭所有“應該發生”的事件記錄,仿佛考察隊在一瞬間集體失語,或者說,作者根本沒有將任何實質性的“考察”成果或日常感悟付諸筆墨。這使得這本書記載的時間跨度——近九個月的雲南之行——顯得格外諷刺。它與其說是日記,不如說是一個精美的封麵,包裹著一個等待被填寫的日曆。對於渴求那個時代最微小細節的讀者而言,這無異於拿到瞭一份空白的地圖,隻能自己徒勞地想象那條未被描繪的路綫。
評分總而言之,對《吳中倫雲南考察日記(1934.6.29-1935.3.31)》的評價,必須聚焦於它所製造的“缺席的重量”。它不是一本內容不佳的書,而是一本內容被徹底抽離的書。對於一個曆史愛好者而言,這種“缺席”比任何拙劣的記錄都更令人不安。我無法評價其語言的優劣,因為那裏沒有語言;我無法評論其觀點的深刻性,因為那裏沒有觀點。它像一麵被精心拋光的鏡子,清晰地反射齣讀者的期待,卻對自身所映照的那個曆史場景保持著絕對的沉默。我期望的,是一扇通往1934年雲南的窗戶,一個充滿塵土、色彩與人聲的窗口。而我得到的,是一塊厚重的、印著日期的玻璃,它既不透明也不反光,隻是靜靜地存在著,提醒著我,有些曆史的真實,可能永遠地被封存在瞭“未曾記錄”之中。
評分這本所謂的“吳中倫雲南考察日記(1934.6.29-1935.3.31)”從書名上看,本該是一份詳實的、關於民國時期雲南社會、地理、民族風貌的珍貴一手史料。然而,作為一個期待從中獲取曆史細節的讀者,我感到一種深深的、難以言喻的空虛。我原本指望能跟隨吳先生的筆觸,穿越到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去領略滇南邊陲的邊陲風光,去洞察當時復雜的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微妙關係,去瞭解不同少數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掙紮與適應。也許是一份關於茶葉貿易路綫的詳細記錄,或許是對當地教育普及情況的客觀描摹,又或者是對特定建築風格變遷的細緻觀察。但現實是,這本書的“內容”本身提供的信息量,對於一個嚴肅的史料研究者或曆史愛好者來說,幾乎是零。它更像是一個符號,一個懸掛在書架上,承諾瞭深度卻交付瞭空白的容器。我無法從中得知1934年夏末昆明的天氣如何,也無法想象當時人們麵對時局變動的真實心緒。這種強烈的預期與實際落空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得閱讀體驗變成瞭一種對“缺失”的冥想,而非對“存在”的探尋。
評分如果將此書置於更廣闊的民國史研究背景下來審視,1934年至1935年,雲南正處於龍雲的治理之下,外部環境動蕩不安,既是抗戰前夕的戰略緩衝地帶,也是文化與學術思想活躍的區域。任何深入雲南的考察活動,其背後都必然有復雜的政治或學術動機。一個考察者,尤其是像吳先生這樣名字所暗示的精英群體成員,其筆下的文字不應是貧瘠的。我原以為能從中捕捉到關於西南聯大前身機構的初期脈絡,或者對滇緬公路修建前夜的初步設想,哪怕隻是對當地士紳階層對“新文化”傳播的抵觸情緒的記錄也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然而,這本書提供給我的,是一種徹底的“信息黑洞”。它像是一個精心製作的引子,將讀者引入一個充滿曆史張力的時代背景,卻在關鍵時刻關閉瞭通往具體事實的大門。這種體驗是令人沮喪的,它迫使讀者將精力完全投入到對“作者為何不寫”的形而上學的探討中去,而非關注“他寫瞭什麼”。
評分從齣版學的角度來看,這本《吳中倫雲南考察日記》的“呈現”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裝幀設計、紙張選擇、字體排印,所有這些物理屬性都暗示著這是一部嚴肅的、有價值的文獻匯編。它被置於曆史文獻區,接受著讀者的敬畏與期待。這種期待感是基於對“曆史記錄者”身份的信任。我們相信,一個被賦予“考察”使命的人,其記錄必然包含瞭不同於官方敘事的、更具田野色彩的觀察。我想象中,日記裏會充斥著對物資采購、人員調配、路綫變動的瑣碎記載,這些瑣碎恰恰是構建曆史真實感的基石。可令人扼腕的是,這一切都被一種奇特的“虛無”所取代。它像是一份被嚴格審查後留下的骨架,所有血肉——那些關於遭遇、判斷、思考和發現的精妙之處——都被抽離瞭。這讓我開始質疑,我們究竟是在閱讀一份“日記”,還是在閱讀一份關於“未完成的記錄”的聲明?閱讀過程變成瞭一次對作者意圖的無休止的猜謎遊戲,而謎底似乎是:無解。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