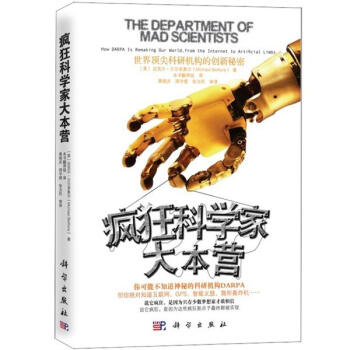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万 钢︱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伯虎︱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毅︱中国工程院院士
怀进鹏︱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晓庆︱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研究院院长
刘云浩、吴建永、杜子德、林润华等著名学者专家
《纽约时报》、《大众科学》、《大众机械》等国际著名媒体——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美国棒的创意工场不是贝尔实验室,不是硅谷,也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而是由五角大楼领导的绝密军事机构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建立的军事部门,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回应苏联的太空计划。虽然DARPA属于政府机构,但是没有冷冰冰的氛围和官僚做派,那里的科学家偏爱牛仔裤和运动鞋。不过他们喜爱的还是在各个领域寻找颠覆性创意。从能源、IT,到航空航天领域,DARPA无时无刻不在为人类制造惊喜。
改革信息是第1次公开DARPA运行模式的著作,从DARPA的创新科技成果——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高超音速飞机、无人驾驶汽车等,到科研项目的管理方法和其历任领导的行事风格,都做了详尽的解读,旨在为读者揭示,为何DARPA可以长期引导科技创新并不断地把二十世纪的科学幻想转变为二十一世纪的技术现实。
如果你致力于创新产业、从事科研管理、关注前沿科技,或者你对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取之不尽的新能源感兴趣,那么请跟随本书立刻穿越到未来50年吧!
作者简介
迈克尔·贝尔菲奥尔,美国著名科技作家、记者、演讲家,主要关注前沿科技领域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技术,为《纽约时报》、《大众科学》、《大众机械》、《新科学家》、《金融时报》、《连线》等世界著名媒体以及新兴高科技公司撰写科技文章。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获得史无前例的采访权,踏进仅有百分之二的美国人熟知的神秘机构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并参观了DARPA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场所,采访了那些与DARPA合作或为DARPA工作的科学家、管理者以及政府要员。
精彩书评
在全球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兼容并蓄,了解世界科技强国科技研发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插上创新的翅膀。——万钢,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希望此书能对探索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有所帮助。
——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
DARPA的经验不光对国防科研有价值,我国民口科研管理部门也应认真学习DARPA的管理方法。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
正如我所料到的,这是一本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和行动的书籍。
——怀进鹏,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的中国如何参与塑造世界的科技图景?我们如何去做出有世界级意义的科技业绩?答案是我们必须突破自我,必须创新。其中,学习与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一个深刻改变世界的科研创新机构。《疯狂科学家大本营》生动地解读了DARPA的创新密码,包括团队、文化、组织、经营管理和技术等方方面面,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思考。
——李伯虎,中国工程院院士
《疯狂科学家大本营》讲述了DARPA引导美国科技发展的故事,在项目管理、科技研发创新、科研成果产业转化这些方面,都能给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思考。
看完这本书,我不禁回顾了我国的军事科技和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从内心讲,我很为中国的军事科技和航天科技研发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作为一支自主研发和创新的科技力量,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军事科技和航天科技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使得我国在军事和航天实力上有着一个和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相称的地位。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DARPA那样,能让自己的研发成果如此巨大地影响人类生活呢?无论是互联网、GPS、合金材料……这些都来自十几年前的DARPA研发计划。我想,这个差距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在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的能力和力度的差别。更进一步说就是科技研发管理体制问题,但是,究其根本,还在于我们是否彻底解放了思想,我们是否在科技管理上有了更加开放的观念和更加前瞻的眼光。
——李德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目录
推荐序一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推荐序四
推荐序五
推荐语
前言
第一章 战争的代价
伊拉克战争的代价
笨重的假胳膊
林上校
肌电手臂
对完美假臂的构想
实现变革的团队
艰难的研发历程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同场竞技
让研发价值最大化的幕后推手
第二章 特别项目管理局
来自宝洁的国防部长
三军之争
发射人造卫星的价值
这根“老黄瓜”成功了
俄国人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总统的漫长噩梦
夹缝中诞生的救世主
借调来的国防部长
国家的科学顾问
DARPA的诞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三章 星际计算机网络
收计算机的垃圾场
星际计算机网络
人机共生的梦想
世界第一次互联网演示
阿帕网--互联网之母
计算机网络变革
反战情绪
斯坦福研究所的诞生
度假村般的研究所
神奇的语音识别项目
人与机器谁翻译得更准确
自学习的个人助手
未来指挥部
只有演示,没有成品
漂亮的世俗品
杀手级应用的会议助手
第四章 机器人医生时代即将来临
等待
曲折的研发过程
转机
黄金一分钟
初尝微创手术
成功
机器人外科医生手术室
外科护理系统
战场上的外科机器人医生
太空站中的外科机器人手术系统
医用机器人的未来
第五章 后座司机
DARPA的守门人
莫哈韦沙漠里的开幕式
沙漠挑战赛的由来
技术需要面向实际
规则的“动态张力”
业余选手的胜利
德国气质
斯汀的失败
“老板”的优异表现
当梦想照进现实
简约与技术
合作无国界
命运坎坷的斯汀车队
场地设计的变化
参赛车队的各自遭遇
关于竞赛的种种
比赛开始
他们撑到了最后
挑战赛带给人们的启示
自主驾驶的过去及未来
第六章 疯狂创意者的故事
坚固的大门
门缝里的一丝曙光
开启DARPA神秘之门
秘密“金矿”
伟大来自创意
美妙的副作用
特瑟与DARPA的第一次邂逅
特瑟时代
第七章 终极先锋
初遇终极先锋
终极先锋的工作原理
国家航天飞机项目为何失败
走出实验室
高超音速飞机
黑燕计划有变
A航天客机的设计
高超音速技术未来
第八章 人类能源
能源不再是战争的根源
新能源研究探索之路
师生联手
分色镜突破与混合材料
生物燃料
挑战航空燃油
北达科他那群干巴巴的家伙
格罗尼沃德发家史
让世界更清洁
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
揭秘能源和环境研究中心
相信我,这真的是JP-
生物燃料抢了我们的粮食
五花八门的发电机
发电站的革命
国家的财富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推荐序一为中国科技发展插上创新的翅膀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
创新是国家强盛的源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坚持依靠创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本由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组织翻译的《疯狂科学家大本营》,就讲述了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知名的美国科普作家。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以往很少为外界知晓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独特的创新模式。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DARPA在科技领域进行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如何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发展。最突出的就是,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用的一些科技成果,如互联网、智能义肢、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远程医疗、即时通信、合金材料等,都是由DARPA率先开发出来的。DARPA不仅在科研方面始终坚持先发先行,而且对科研成果的管理和转化也十分高效,从而成为了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研实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迫切需要改革体制、创新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兼容并蓄,了解世界科技强国科技研发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插上创新的翅膀,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示。
推荐序二
创新营地巡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
2001年2月美国工程院将代表美国工程科技最高荣誉奖励的Draper奖授予劳伦斯·罗伯茨(Lawrence Roberts)、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伦纳德·克莱恩罗克(Leonard Kleinrock)和文顿·瑟夫(Vinton Cerf)四人,表彰他们对互联网所做的贡献,他们都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在1968~1972年先后加入ARPA计划的ARPANET项目,他们的工作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互联网成为20世纪后期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发明之一,至今互联网上的创新仍层出不穷。但互联网仅是ARPA以及其后来的DARPA的重要发明之一,GPS、航天飞机、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医生等也都出自DARPA。
《疯狂的科学家大本营》一书选取了DARPA诸多研究领域中有限的几个,从摘取的几滴浪花中透视大海的内涵,作者用其笔尖将DARPA的神秘面纱掀开一角,让我们跟着作者去探究承担DARPA项目的几个研究团队。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些重大发明的题目出自哪里?是上面主管部门下达的还是仅凭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该书更多介绍的是自下而上提出,奇思妙想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对未来需求的判断。选题不是可行性优先而是重要性优先,立项之初的任务似乎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挑战极限会激起研究人员的兴趣,当然也需要上级主管的魄力来支持,需要具有能够从貌似疯狂的想法中总结出真正可行方法的洞察力。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宁愿采取风险很大的新路也不愿走保守的技术路线,敢于另辟蹊径缘于跨学科的团队,得益于不急于求成和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才能鼓起研究团队攀登的勇气。在用人机制上,慧眼识才至关重要,DARPA的管理者知道难题不仅要用非常规的手段解决,而且要由非常规的人员来实现,前述获得Draper奖的四位互联网科学家当年在刚拿到博士学位或还在攻读研究生阶段就因其研究内容符合需要而被委以重任,牵头ARPANET项目。知人善任还表现在充分发挥老科学家的经验和学识上,一些年过60的科学家仍然活跃在前瞻性的项目中。在考核机制上,该书并未过多着墨,但不以短期成果论英雄,研究人员得以心无旁骛、锲而不舍。另外,四位拔尖的互联网科学家协同创新终成互联网大业的例子,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考核机制有利于凝聚群英。关于研究经费,书中讲到如何游说主管部门争取经费的例子,但项目经费并非都来自政府,也有其他投资者,项目管理者知道如果一开始就有太多钱的话就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节省, 有太多的钱可能比没有钱更会让公司失败。另外,大多数投资者都要求快速回报,而急功近利与潜心研究相矛盾,项目的管理者为解决流动资金短缺,努力寻找需要这些技术的民用客户,吸引客户资助研究,从这一意义上促成成果的商业化。在研究成果的推广上,尽管DARPA计划是国防导向,但研究人员始终没有忘记推动成果的民用,寓军于民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另外,成果不是以报奖作为目的,而是力求精益求精可靠好用低成本服务于大众,正如XCOR航天公司的总工程师所说:“你必须相信这一信仰能够实现,你必须保持乐观,很显然,如果我们单纯想赚钱的话,我们会去做其他更加容易的事情。”
“说它疯狂,是因为只有少数的梦想者才敢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说它疯狂,是因为这些疯狂的创新点子最终都被实现。”当然,DARPA计划运行几十年来肯定也有过一些失败案例,本书鲜有涉及,即便列出也瑕不掩瑜。他山之石尚可攻玉,而他山之玉可以为镜,希望此书能对探索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有所帮助。此书不仅适于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阅读,而且其中所含的创新思维对青年学子也颇有启迪,书中提到的让计算机输入像钢琴“五指和弦键盘”那样可同时按多个键的键集就是一例,而让计算机通过被使用而学习并了解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达到成为人的知心助手的创意也充满挑战和极富想象。
推荐序三
从DARPA的成功中能学习到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国杰
为了学习美国人如何进行科技创新,如何组织、管理科技创新项目,科学出版社引进并出版了《疯狂科学家大本营》。这本书的内容是破解美国国防部领导下的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创新密码。
科学出版社希望我为此书写篇推荐序,我欣然同意。同意的原因一是向广大读者,特别是科研人员和科技官员推荐一本很有价值的好书;二是想借此机会谈几句学习DARPA科技管理的体会,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发表一点意见,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提一点建议。
我国科技界对DARPA并不陌生,我们天天在使用的互联网的前身就是DARPA支持的ARPANET。大到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小到计算机的鼠标都是DARPA支持的科研成果,美国的超级计算机、集成电路、高超音速飞机、手术机器人等尖端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DARPA的支持。光是DARPA支持MOSIS实验室就为美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集成电路设计师。极而言之,没有DARPA,就没有美国今天领先的高技术。
美国是崇尚“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一个政府部门会起到这么大的作用。2008年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在《政治学和社会》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2010年我国刊物《国外理论动态》翻译发表了该论文的中文版,名为《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这篇文章认为:“过去30年来,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一直起主导作用,但是事实上联邦政府在资助和支持私营企业新技术商业化方面依然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干预作用。”文章详细论述了DARP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政府机构如何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巨大干预作用而又在主流的公开辩论中被隐形。
DARPA不是美国创新技术的唯一源泉,更多的原始发明来自大学的基础研究。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模式来自创业的小企业(startups),比如仙童、Apple、微软、Yahoo、Google、Facebook等。从根本上讲,新的市场需求是牵引企业发展的动力。但企业的前瞻研究总是有限的,有些风险较大或者需要多个企业竞争前合作的前瞻研究多半需要政府来组织和引导,政府在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不能忽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都要起作用,而且两手都要硬。
美国共和党右派为了反对克林顿政府对DARPA组织的先进计算计划的支持,曾喊出“政府不是出路,政府是问题”的口号。国际上也有一种看法: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尽人意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外国评论家只说出了我国政府存在科技管理上“越位”的弊端,我国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确实对科技项目管得过细。但很少人认识到,我国缺少DARPA这样的引领高科技发展的管理机构。我们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特别需要像DARPA一样的内行专家去组织与监督,但我们有些重大专项却采取了863计划,甚至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办法。DARPA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由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有预算自主权的小型科研机构,他们能深入扎根于他们所资助的具体科研团队中。1966年,时任ARPA(DARPA的前身)信息处处长的泰勒以其独到的眼力认准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的罗伯茨有能力主持ARPA网的研究,不惜以削减整个林肯实验室经费的“威胁”迫使他上任。这和今天我国众多单位围着科技部申请课题多么不一样。如何培养这种识人的眼力是我国发展科技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这篇简短的推荐序中,我无意为DARPA评功摆好。在小布什当政的几年里,我也曾听到许多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朋友抱怨DARPA减少了对大学科研的支持。我只想鼓励读者认真从这本书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在科技体制改革中,找到适合我国科技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简单地把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办法延伸到所有的科技项目。DARPA的经验不光对国防科研有价值,我国民口科研管理部门也应认真学习DARPA的管理方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与国外最大的差距是缺少自主可控的基础技术平台,发展云计算和移动计算最需要的也是构建与Apple、Google和微软公司的平台类似的产业生态环境。在建立这样的产业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类似DARPA这样的引领者和组织者是不可缺少的,我国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DARPA。
推荐序四
创新从哪里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怀进鹏
近日,科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文戈向我推荐他们即将出版的引进版新书《疯狂科学家大本营》,并邀请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当看到这本书后,我注意到封面书名下方的两行字--“说它疯狂,是因为只有少数的梦想家才敢相信;说它疯狂,是因为这些疯狂新点子最终都被实现”。正如我所料到的,这是一本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和行动的书籍。
《疯狂科学家大本营》的作者贝尔菲奥尔先生通过讲述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故事,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个世界顶级科研机构的创新秘密。作者曾获得史无前例的采访权,近距离接触到了DARPA--在美国也只有2%的国民十分了解这个神秘的科研创新机构;他亦参观访问了DARPA分布于美国各地的研究场所,还采访了与之合作的科研机构及其科研团队的管理者与科学家,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作者通过详实的采访素材、生动的笔法写就的创新故事,读起来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深思。
我想,许多读者阅后会和我一样,掩卷沉思一个问题:创新到底从哪里来?
创新到底从哪来?我们不妨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根据全书内容提炼出DARPA的5个本质优点:大胆、创新、灵敏、务实和迅速。如果把其中的“创新”改为“简约”,再加上“坚韧”,那么这新6点也许就是微观上的创新要素。
如果没有大胆的想象,就称不上“疯狂”,不“疯狂”,也就难以有令人惊奇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创造。
IT领域的各类创新一再证明KISS(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法则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可以说,不论是体系结构还是网络协议的设计,抑或是各类软硬件的优秀设计都是“简约”这个创新要素的明证。我们最为熟知的例证莫过于史蒂夫·乔布斯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的三连胜,他一再用简约的法则去重新定义MP3播放器、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三类产品。早在苹果公司推出自己的产品之前国际市场上就已经有了成熟的产品(MP3播放器和手机)或者失败的商业应用案例(平板电脑)。但简约却像杠杆一样使得苹果公司撬动了硬件生产板块,震动了软件领域,甚至颠覆了内容生产行业,瓦解了运营商在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
灵敏即灵活敏锐,用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潜在的用户需求(包括军事应用需求和民用市场需求),用灵活的方式去跨过或者绕过创新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坚韧,则是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必要的坚持;而务实则是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从众多问题中遴选出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务实也意味着以当下条件为基础去分解目标并攻破子目标,这往往意味着要用高频率迭代的方式去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并最终解决问题,而这样才是迅速的。
显然这6点是紧密结合的。敏锐地发现需求,大胆构想愿景,务实地去选择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简约的原型或试验样品(或初级产品),迅速迭代,不断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务实、敏捷地去想方设法不断逼近总目标,不断逼近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然而,美国国内长期的创新领先优势暗示我们,创新绝非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绝非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范围的团体的事情,它亦有着宏观的一面,正是这宏观的一面使得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影响世界的创新成果。
那么,在宏观层面上创新从哪里来呢?DARPA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创新来自高效的科研创新管理机制。而且,若是结合DARPA的经验与问题来看,宏观层面的创新也依然是那6点。政府需要去引导、促进长远的科技研发,为此政府本身需要大胆去支持有远见的科学家及其团队;政府领导下的科研管理机构需要大胆去挑战高难度的科研项目,但同时也需要敏锐而务实地遴选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务实地去挑选可获得资助的务实的科研团队;整个管理机制必须简约、灵活,抛弃官僚主义和臃肿的组织架构,对资助团队的引导、敦促、支持必须敏捷,双方间的反馈要迅速;政府最好能够在长远项目上有所坚持……
要保证机制的简约、灵活,也许在某些研发领域及其组织机制上,我们也应该大胆考虑借助市场的力量,利用市场分配资源的敏捷性去引导、管理团队进行科研创新--把资金投给有潜力的科研团队,以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操作。这意味着,获得资助的科研团队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校,都应具有小型公司运作的那种高效性与灵活性。若科研团队借鉴现代小微企业的运作模式进行项目运营,那么这种通过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将使科研团队以创业的心态与精神,务实、灵敏、迅速地进行科技研发,并尽可能地释放出科研人员的创新能量。这样的创新成果也往往因为能够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具备很好的商业价值,并能够迅速进行产业转化和商品化。
关于创新,要思考,更要行动!
推荐序五
创新从哪里来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研究院院长 黄晓庆
美国最伟大的科技创新工场在哪里?
贝尔实验室?硅谷的斯坦福、伯克利还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抑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都不是!而是DARPA!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这是一个由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隶属于五角大楼的国家级研发机构。当时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政府和军队以及民众,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DARPA,它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在人造地球卫星和探索太空的研发计划领域对抗苏联,以不再重蹈人造卫星落后于苏联的覆辙,美国人决心要在科技领域取得前瞻性的突破,成为创造游戏规则和改变游戏规则的科技领先者。
DARPA把那些军事长官、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疯狂的科学家集合在一起,在极具前瞻性的科技领域,包括机器人、远程手术医疗、智能义肢、无人驾驶汽车、高速飞行器、航天火箭和新材料及新能源等诸多方面,寻求创新研发突破。
DARPA,以其特立独行的高效方式,天才般地、神奇地发明创造不仅是在军事应用领域,而更多的是在向民用领域进行技术迁移的过程中为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塑造了现代科技的核心。
我阅读了这本书的原文,被极大地震撼,我似乎是真切地感受和理解着一个大国应如何从科研体制创新上走出一条最能激发研发创新潜力,最具前瞻性和战略高度并且最能促进研发成果的生产力转化的科技研发道路。这条道路此前犹如隐没在北京早晨冬日的大雾中,读完此书,似乎阳光照耀穿透浓雾,让这条模糊不清的道路豁然清晰起来,蜿蜒伸展,可以看到它通向的远方。
我想,一如DARPA曾经走过的坎坷和辉煌。对于国家级的研发机构,也包括国家企业的研发机构,我们相信国家唯有给予这些机构其应得的支持,并留出茁壮成长所需的良性空间,这些研发机构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巨大财富!
DARPA从一开始的构想和运作,就是一个以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研发进展并遏制世界其他力量对美国造成威胁为首要使命的机构,多年来一直保持这种定位。其使命是使用让对手望尘莫及的下一代高科技来武装军队,这个使命让DARPA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锋利焦点;而且它强调快速将项目从概念推进至工程原型,且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金,这理应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国家研发创新的典范。
其值得借鉴之处还在于真正的创新不需要依赖大量的资金花费和大群的官僚军团。DARPA仅仅使用美国国防预算资金的0.5%来运转,它的员工在一个普通大小的独栋建筑里办公。但DARPA的确已经促成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创新(例如,互联网和GPS)。它成功的关键,除了将官僚系统压缩到最小之外,就是它的项目经理们只有有限的任职期限。任职期限限制保证了替DARPA做最重要工作的人们更关心如何完成机构的任务,而不是保住他们的工作。DARPA一开始就决定不亲手管理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把项目外包给其他研发机构或团队来做,这个决定让它一直在高效快速开发新的技术,并在需要时任合约研发机构或团队自由发展,从而使得自身一直处于科技的前沿。
DARPA的了不起,其实并不仅仅是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科技创新的成功,更加给力的是它持续为人类奉献着一道道科技盛宴。这本书会为读者展现这些科技创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得以思考和践行他们的成功方法,并由此改善我们的工作和人生。
……
前言/序言
我头一次知道机器人医生是源自一本科幻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艘进行星际旅行的宇宙飞船上,飞船上的机器人医生可以使它的使用者接近永生。对于星际旅行来说,这是一项必备条件,即便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来航行。而现在,我居然亲眼看到了机器人医生的实物,它就蹲在硅谷一个实验室的角落里,像一个巨大的机械昆虫,嘴巴和四肢都栩栩如生,正严阵以待地准备在手术台上展示它高超的技能。
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也是人工制造的。工程师把“病人”放在手术台上,模拟出真人躺下的情景。我的导游是一位47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机械工程师。他指着一只装满手术工具的手术器械柜和一个摇臂式机器人护士,解释说,这种机器人是在工业机器人的基础上发明的,从前这种机器人的工作对象绝大多数是汽车,而不是人体。他还跟我解释了机器人医生系统的工作原理。不用怎么费劲去想象,我就仿佛身临其境了。
鲜血正喷涌而出,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病人被猛地抬到手术台上,考虑到此时情形紧急,必须立即止住大出血。受伤的病人绑着绷带,气息微弱,任由机器人医生调遣着机器抓钳抓紧他的受伤部位。手术台上的微型CT扫描器沿着病人身体向下滑动扫描,将信息及时地反馈给机器人医生的计算机大脑。之后,机器人医生便开始手术。首先,它用针刺进病人的身体,然后敏捷地把一根输血导管穿过病人的血管系统,从而丝毫不误地找到了微弱搏动的动脉,血正通过动脉的破裂缺口汩汩流到手术台和地板上。
机器人医生停下,不再移动,在病人身体内部进行着外界看不见的手术。然后,当机器人医生堵住血管的破裂缺口时,就像开着的水龙头被拧上那样,血流戛然而止。随着一阵“嗡嗡”声和“咔哒”声,机器人医生满意地收回了它的抓手,抽出了输血导管,代之以简易静脉注射。无需任何语言的命令,一旁的机器人护士移向手术器械柜,从中取出一些缝合线,再移回机器人医生身旁,把医生的一只手臂拔掉,接上另外一只全新的手臂。机器人医生就用这支新手臂接过缝线,开始灵活迅速地给病人缝合伤口。从诊断伤口到手术完成,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两分钟。瞬间又一个战士被救活了,相信在今后的某一天他又能生龙活虎地重回战场。
“想试试吗?”工程师问我。
“当然。”我回答说。
他让我在另外一个机器人医生面前坐下,这个机器人医生是最新版本的医生模型,然后他指导我把双手放在一副金属把手上,他让我身体前倾,这样我可以透过控制台上的双目显微镜看清整个操作过程。之后,我立刻被传送到了屋里另外一张手术台前,台上有模拟的身体正等待着我做缝合手术。我清楚地看到手术台和模拟身体的3D效果,在我不专业地操纵着机器人的抓手并尝试缝合时,我的双手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病人因为我手艺不精、操作不当而引发的每一次痛苦搐动。这一次亲身经历让我不仅眼瞅着科幻小说中的情景变为现实,还让我身临其境。
在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个奇怪的政府机构里,我度过了非比寻常的一段漫长旅程,而我对机器人医生的拜访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篇章。我认识的人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政府机构,但是这个神奇的机构却以不计其数的创新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用过互联网吗?电脑鼠标呢?卫星导航系统呢?这些都是DARPA昔日的杰作!非常感谢DARPA对我撰写本书的支持,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探讨一下这个机构目前发展的项目计划中,有哪些足以媲美昔日那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同时也为了与实现这些项目的人进行交流,以了解他们疯狂创新的故事。
我第一次了解到DARPA是源自世界第一次私人太空旅行的报道。那是2004年6月22日,在加利福尼亚莫哈韦小镇上,电视转播工作人员已经收起了卫星天线和帐篷,准备驱车回洛杉矶,他们的背后跟着成千上万驱车前来围观的群众。这个在洛杉矶以东大约100英里①的莫哈韦沙漠中的小镇,在一天之内又归于往日的空寂,只有旗杆被风鞭打的声音,偶尔还会传来飞机在机场起飞和降落时喷气发动机和活塞发动机的咆哮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座航天港。
2004年的6月21日,太空1号(SpaceShipOne)第一次把63岁的迈克·墨尔维尔送到外太空。太空1号是由一位疯狂的、敢于创新的著名飞机设计师设计的,飞船的建造也是由他经营的一家小型公司完成。这家公司的名字叫缩尺复合材料公司(Scaled Composites),总部设在莫哈韦小镇机场的保养场上。飞船的造价仅用了2500万美元,只是波音737-600客机售价的一半。这架小型的太空飞船由纯手工制作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三倍,比任何一架现役的民用飞机都要快,不过还是远远小于到达太空轨道所必需的时速25马赫②。尽管如此,太空1号还是突破了大气层,使得墨尔维尔在失重状态下漂浮了4分钟。当年,这条消息登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不过,似乎在报道墨尔维尔太空之旅的记者中,我是唯一会在第二天回到莫哈韦小镇来看看这个商业太空港平日情形的记者。整个小镇的室外几乎没人,像一个鬼镇。所有人都在室内,躲过沙漠里的炎炎烈日,在他们的机库和办公室里工作,度过平常的日子。
我的发现之旅始于调查一家名叫XCOR航天的火箭研发和制造公司。就像事后所证明的那样,那天我的发现也只有这么多。虽然XCOR航天公司看上去没什么,但它确实和航天界其他特立独行的公司(如缩尺复合材料公司)齐名,它代表了私人太空之旅的希望、梦想和潜力。XCOR航天公司占用了一座平凡无奇的蓝色机库,这座机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大门上一个非写实的火箭推进式飞机图像就是把此处和其他寻常机库区别开来的唯一标志。我走进一间破旧不堪的休息室,看得出公司想把这间屋子作为接待厅来使用,只是很明显他们的这一想法不太成功。四周墙上挂着装裱过的介绍公司的杂志和文章复印本。其中有些文章介绍了一架自制飞机,它是公司的工程师用一辆汽车改装的,他们给汽车装上了一对火箭引擎,给它起了个绰号叫“EZ-Rocket”。
公司的心脏位于一个敞开的机库,作业区和作业台沿着四周排开。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友好的中年工程师,名叫阿莱塔·杰克逊。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她极其聪明,拥有将自己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普通人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中所需要的幽默感。她全然不像那些开创了首次太空旅行纪元的前辈们,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和传说中的攻坚克难人物的固定印象。虽然负责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政府计划,但杰克逊对太空旅行梦想的投入程度丝毫不亚于她的前辈。“如果不能例行、定期、可靠地接触太空,那我认为我们这个星球就有麻烦了。”她简单地跟我解释说,“我们必须利用太空,利用得越早,地球上的每个人也就能过得越好。”
每个人?
“如果人类能够例行访问太空的话,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她具体解释道,“比如我们可以带回我们没有的资源。”
比如说?
“一个直径3千米的碳质球粒陨石小行星产生的副产品中的黄金可能会比迄今为止地球上所有开采到的黄金总量还要多。”
XCOR的总工程师丹·德朗同样由衷地相信,开发出人类可以承受得起的太空旅行的方法将具有变革世界的力量。“这几乎是一种宗教信仰。”他在XCOR的工作间加入了我和杰克逊的谈话:“你必须相信这个信仰能够实现,你必须保持乐观。很显然,如果我们单纯想赚钱的话,我们会去做其他更加容易的事情。”
尽管梦想看起来有点崇高而遥不可及,但是这些科学家却采用非常实际的方法,实现对太空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开发。他们需要投资者,所以他们建造了那辆火箭推进式汽车来作为技术展示,以表明他们的梦想不仅是建立在可靠的工程技术原则之上,并且他们的火箭还可以安全地飞行,并通过普通可靠的商业模式来运转。为了进一步展示他们火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他们建造了一个很小的“茶车”火箭,只有15磅③推力,以乙烷和一氧化氢为燃料驱动,装置在一个可运动的推车上,样子有点像酒店里客房服务用的餐车。实际上,他们的确曾在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发动这台设备。“我们得到了消防部门的安全认证,”德朗对此很骄傲,“消防部门的安全认证给我们的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发现非常宏伟的目标与基本的、常识性的商业原则,以及寻常的问题求解之道组合在一起时极具启发性。不同于缩尺复合材料公司,XCOR没有一个手握大量闲置资金的天使投资人,它的投资者们都期待着投资回报,而且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这也并没有让杰克逊和德朗感到困惑。由于先前在旋转火箭公司(Rotary Rocket)的失败经历--那家公司在花掉了3000万美元之后,连一架可以飞的太空飞船都没造出来,所以杰克逊和德朗的团队开始提倡“少而美”的哲学。“有太多钱可能比没有钱更会让公司失败,”德朗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有太多钱的话,你永远也不知道节省。”
为解决流动资金短缺这一问题,XCOR的经营者的解决方法是寻找需要技术的个人客户,而这些技术也是XCOR所希望开发的技术。他们的第一个太空里程碑是一架凭火箭推力即可从飞机跑道上起飞的双人座火箭推进式飞机。不同于“喷气飞机+火箭飞机”的太空1号系统,它不需要喷气式母机的帮助就能达到与太空1号同样的高度和速度。杰克逊和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希望火箭飞机能够在那些有太空旅行梦想的人群和科学家中找到市场,有些科学家希望微重力飞行试验可以比以前更加便宜。在走到那一步之前,XCOR的工程师们希望能够在太空飞船的一些技术上挖掘出足够多的利润,以支持他们开发另一些无法找到客户、没有市场需求的太空飞船组件和技术。
在我访问XCOR的时候,他们的工程师们正顺利地进行太空旅行的商业运作。他们当时刚刚开发完成了活塞驱动的液体氧气泵。这项技术显然不像太空1号那样有轰动性,但是只要是懂火箭的人都知道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技术。DARPA的项目经理显然是行家,他们对XCOR的新泵技术投资了75万美元,现在他们正在期待着投资得到回报。
当时,我对DARPA了解不多,只知道它是XCOR的主要客户以及它是一家政府机构。那时,我刚开始写一本有关小型商业太空公司(如缩尺复合材料公司和XCOR)的书,在我的印象中,太空项目的私人应用研发领域比庞大的政府领域更有活力。
在安萨里X奖对人类第一次太空私人旅行的资助下,商业太空飞行领域开始起飞。此奖项要求获奖者不能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奖项的设立者彼得·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先生认为,太空旅行太贵是因为政府太空项目扼杀了这个行业的创新精神。X奖的竞争者们倾向于认同他的观点,我当时也深信彼得·迪亚曼迪斯的这一观点,从而专心致志地撰写着关于X奖的争夺及其余波的故事。
可是,我越是对DARPA不屑一顾,它越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书中--《火箭人:一群有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工程师和飞行员们如何大胆地将太空私有化》。那时这个机构在资助“太空探险科技公司”--或称为“SpaceX”,由伊伦·马斯克(Elon Musk)创立并领导,公司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旁。马斯克曾经是贝宝公司(PayPal)的联合创始人,由于这家公司在2002年被卖给易趣,马斯克从中大赚了一笔。如今,马斯克把太空旅行视为人类躲避造成恐龙灭绝之类环境大灾难的最大希望。马斯克不仅把希望放在月球上,他的目标一直延伸到火星,并且希望能提供科技基础设施,使人们永久性地定居在那里。这并不是所谓的白日做梦和天方夜谭,单是SpaceX的创始人就注资了1亿美元,他们的研发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包括建造和测试了猎隼1号(Falcon 1)。马斯克团队的工程师都很优秀,有一些是从SpaceX主要的竞争对手公司挖过来的,他们也相信整个计划能够获得成功。DARPA对猎隼1号的首次演示发射也很有信心,这也正是它成为SpaceX的第一位顾客的原因。
DARPA也资助了另外一家在太空科技研发领域的创业公司,名叫高空发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旋转火箭公司的前CEO加里·哈德森(Gary Hudson)创立。公司的目标是降低卫星发射成本,方法是把火箭从C-17运输机的尾部投下去。这颇有点像太空1号摒弃不用其竞争对手使用的昂贵的一次性第一阶段助推器,而是在发射第一阶段用一架飞机助推。为了载人发射,高空发射有限公司不是把这个大块头火箭踢出C-17运输机的尾部,而是选择把它从一架由缩尺复合材料公司定做的飞机的腹部抛下,或者在必要时,这架飞机可以由一架经过特别改装的波音747代替。通过一家名为太空变革公司(也叫t/Space)的衍生公司,哈德森试图让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资助他与合作伙伴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在支付太空变革公司600万美元用于研究此计划之后,NASA便放弃了。哈德森对NASA拒绝跟进支持把人类送入太空轨道的全新理念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他觉得NASA过于官僚化,太倾向于冷战时代的运作模式(NASA更希望拿下金额大的合同,而并不是很关注新鲜的想法,即使后者价格更加低廉,甚至也更加安全),这和许多后来被称为新太空领域企业家的人想法并无二致。哈德森只是摇了摇头,便又投入到高空发射有限公司的工作中去。高空发射有限公司之后在莫哈韦航天港测试启动了火箭发动机,并把虚拟火箭从C-17运输机的尾部投下。正如我所发现的,高空发射有限公司是一个空军项目,正是由DARPA而非他人所负责。
DARPA究竟如何与这些在理念上最“前卫”的太空企业建立深厚的工作关系?这些企业都以攻克传说中无法逾越的难关而著称,传统的“智慧”认为除非有重大政府项目的预算,否则无法解决这些难题。我认为这种工作关系和DARPA的两项过人之处有关:(1)灵活看待问题,知道难题不仅要用非常规的手段解决,而且要由非常规的人员来实现;(2)能够从貌似疯狂的想法中总结出真正可行方法的洞察力。我不由地想知道,DARPA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和这群沙漠流浪者一样,如此急切地想要用更低廉的成本访问太空?
最终,在兜了一大圈之后,我又回到了DARPA这里。我的所见所得让我大吃一惊。原来DARPA是美国第一家太空机构。没错,不是NASA,也不是美国民用太空机构,是DARPA--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国防部研发中心的机构,最初是为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号召而创立,目的是追赶并超越俄国人④的太空成就。
艾森豪威尔建立了NASA和DARPA--那时候的DARPA叫做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高级研究计划局),没有D(国防)的意思。二者的设立是对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回应。当时NASA的成立章程的直接目的是在太空打败俄国人,而ARPA的任务更加宽广,包括了研发所有先进的科技,以保卫美国并抵御来自世界上任何角落的科技冲击。ARPA在NASA之前就大力推动了美国的火箭项目,而NASA就像恒星吸聚周围的物质最后形成一个太阳系那样,吸收了这些项目,最终击败俄国人,登上了月球。同时,ARPA也悄悄地进入信息科技领域的研究。在1969年,NASA成功地使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而ARPA也开创了当时不为人知的阿帕网(ARPANET),它作为互联网的主干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21世纪初期,NASA完成自己的初始使命30年后依然迷失于寻找下一个清晰的目标,而此时DARPA却华丽地转身回到了太空领域。它的项目经理们琢磨着要是访问太空能够变得更加“快速反应”(用军事术语来说),那他们在这方面表现自己的机会又有多少。为了应对特定的冲突,在执行特殊的侦察和通信任务时发射弹出式卫星,这个想法如何?或者是别的想法:空军或者陆军有没有可能在几个钟头的响应时间之内就把特种部队派遣到地球的另一端执行一次攻击任务呢?
我挖掘得越多,我越是被这个行事低调,却影响巨大的国防科研部门所吸引。这个政府机构,预算不少于30亿美元⑤,运营模式却像一家小型公司。它十分迅速地资助着各式创新科技项目,却有着最少的官僚主义烦扰。它是如何成功地完成这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伟绩的呢?我一直在思考,其他的公司和组织机构可以向它学习些什么呢?更让人兴致勃勃的是,DARPA还会酝酿出哪些将像互联网那样影响巨大,却又不为我们所知的令人惊奇的项目呢?
我之所以对DARPA这么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09年美国在国防相关活动上的开支达到了6510亿美元之巨。这个数额占了政府弹性预算的一半多,超过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的国防预算的总和。这样的一个数字正表明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位亲手建立NASA和DARPA的总统--曾警告过的过度的国防开支对国民造成的直接损害。“每生产一支步枪,每下水一艘战舰,每发射一枚火箭,所有这些军事开支最终都意味着偷窃,都是从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百姓手中偷窃而来。”这是他在1953年4月对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话,这次演讲通过电视和无线电向全国广播。“制造一颗现代重型炸弹的花费等于在30个城市分别建立一所砖房小学的支出,等于建造两座分别能为6万人口城镇供电的发电站的支出,等于建造两家设备齐全的医院的支出,等于建造50英里的水泥高速公路的支出。我们对每一架战斗机都付出了50万蒲式耳⑥的小麦,对每一架歼击机我们都支付了为8000人构建新房的价钱……从任何真正意义上来说,军事开支都不是经济之道。那是以战争威胁之名,把人类吊在钢铁十字架之上。”
后来这位总统在他1961年的离职演讲时,说出了那番著名的言论,对军工企业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斥之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尤其让人感到惊异的是,此话出自一位比任何人都要更为懂得一个强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重要价值的将军之口。毕竟,二战时期艾森豪威尔曾在欧洲统帅过盟军部队。
艾森豪威尔本人看不到任何其他出路,唯有接受庞大的军队及其威胁国家健康的事实。“直到我们这个世界最近的一次冲突之前,”他在离职演讲中解释,“美国还没有军火工业。美国制造的犁头,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也可以化为刀剑来用。但是如今我们无法承担遇到紧急情况时临时拼凑一股国防力量的风险;我们被迫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大比重的军火工业。”
但是他也找到一个减轻巨额国防支出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方法。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全国州际和国防公路法案”,国家高速公路网便开始修建,后来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州际公路网”。表面上看,这个网络是在战争的情况下用于军队的快速行军和民众从城市快速撤离的公路,整个网络可以说是总统在两届任期内最有价值的工程,它同样也是五角大楼在斥资用于军事之外,释放一部分资金作为民用的一种途径。ARPA被证明是艾森豪威尔所斥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一线曙光。
阿帕网自创立后,发展成为了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前身起初用于为战舰、战机和地面军车导航,如今却为数不尽的徒步旅行者、抢险人员,还有手机用户指路。在激动人心的广阔领域里数不清的工程中,DARPA促成并带来了一些过去50年间最为有用的科技成果。与此同时,其运作费用却只占每年国防预算中的很小一部分--只有一架B-2轰炸机费用的1.5倍,只有NASA预算的1/6。DARPA向我们证明了,美国军队有能力在不拖垮美国经济的情况下,保持其科技实力领先世界的地位。
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对这一主题略作探讨,我会把笔墨集中在这个机构对我们社会具有巨大潜在影响力的工程上,集中在那些可以媲美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的项目上。与此同时,我也会讲讲DARPA非同寻常的历史。跟我一起进行一次顶尖科学和技术的神奇之旅。DARPA的故事是疯狂科学最好的例子。说它疯狂,是因为只有少数的梦想者才敢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说它疯狂,是因为这些疯狂的创新点子最终都被实现。
用户评价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在探讨未来趋势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的、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它没有沉溺于对技术乌托邦的盲目乐观,反而深入剖析了科研机构在面对地缘政治、伦理困境以及商业化压力时的复杂博弈。例如,在讨论基因编辑技术的前沿应用时,作者并未止步于其医学上的突破潜力,而是细致地梳理了围绕知识产权、社会公平以及监管真空所产生的激烈冲突。这种将科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去审视的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认知边界。它提醒我,任何一项伟大的科学突破,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它们无不与人类社会最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纠缠在一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更是一部关于现代知识生产体系运作机制的深度剖析报告。
评分这部书的开篇简直就是一剂强心剂,把我直接拉进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殿堂。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对于那种老派的、略带灰尘感的实验室场景的描绘,简直让人身临其境。我仿佛能闻到福尔马林和臭氧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看到那些摆满了玻璃器皿和错综复杂的线路板的工作台。他没有直接去介绍什么高深的技术,而是通过讲述那些“怪咖”研究人员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如何与周围环境互动,来构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研究氛围。特别是有一段描写,关于一位研究员为了解决一个微观粒子的偏振问题,连续三天只靠速溶咖啡和某种冷冻食品维生,那种近乎偏执的投入感,真是让人动容。这本书成功地避开了枯燥的学术报告堆砌,而是聚焦于“人”本身——那些被好奇心驱动,愿意为了一丁点突破而燃烧生命的个体。这种对科研生态的微观观察,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来得震撼人心。它让我们看到,伟大的发现往往诞生于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近乎疯狂的坚持。
评分本书的结构处理非常精妙,它不像传统科普那样线性推进,而是采用了类似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顶尖机构之间进行着快速而流畅的跳转。这种跳跃感非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营造出一种全球智慧网络同步运作的宏大画面。读到关于深海生物发光机制的探讨时,我仿佛置身于漆黑的海底洞穴;下一章,视角立刻切换到了赤道附近的高空,讨论着新型大气污染物的数据建模。这种场景的快速更迭,让读者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的待命状态,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巧妙地在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研究之间,搭建了看不见的逻辑桥梁,揭示出底层科学规律的共通性。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无论研究对象是细胞核还是星系,驱动科学进步的底层逻辑思维模式是何其相似。
评分读完这部分内容,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识渴求症”。作者在阐述某些前沿概念时,展现出了一种罕见的叙事天赋,他能把极其复杂、需要多年专业训练才能理解的理论,用一种近乎诗意的比喻轻松地包裹起来,让人在理解的瞬间感到一阵酣畅淋漓的愉悦。举例来说,对于量子纠缠现象的解释,他没有使用传统的薛定谔方程或者贝尔不等式,而是用了一个关于“遥远双胞胎心灵感应”的故事框架来展开,这使得即便是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读者,也能抓住其核心的荒谬与美感。这种由浅入深的引导技巧,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但绝不意味着内容的肤浅。相反,我感觉自己仿佛接受了一次高级别的私人辅导,每一个概念都像被精心打磨过的宝石,闪烁着清晰的光芒。这种将“艰深”转化为“易懂”的能力,是这部作品最值得称赞的艺术成就之一。
评分我对书中对“失败的艺术”的探讨印象极为深刻。在主流叙事中,科学成果总是被塑造成一条笔直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但这部作品却大胆地将聚光灯打在了那些被掩盖的、耗资巨大的、最终证明是死胡同的实验上。作者用近乎田野调查的口吻,记录了那些“昂贵的错误”,包括一些接近成功却功亏一篑的重大项目。他没有将这些失败简单地归咎于偶然或资金短缺,而是深入剖析了当时认知框架的局限性,以及研究团队在压力下做出的决策失误。这种坦诚和批判性的反思,让整个叙事充满了人性的重量。它告诉我们,科学进步的真实成本,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昂,而这些被浪费掉的资源和时间,其实是为后来的成功铺设的不可或缺的台阶。这种对真相的直面,令人肃然起敬。
评分老板推荐的书,对这方面也感兴趣
评分③我们的教师为了控制课堂,总担心秩序失控而严格纪律,导致紧张有余而轻松不足。轻松的氛围,使学生没有思想顾忌,没有思想负担,提问可以自由发言,讨论可以畅所欲言,回答不用担心受怕,辩论不用针锋相对。同学们的任何猜想、幻想、设想都受到尊重、都尽可能让他们自己做解释,在聆听中交流想法、
评分--李伯虎,中国工程院院士
评分很快!!!!!!!!!!!!!!!!!
评分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获得史无前例的采访权,踏进仅有百分之二的美国人熟知的神秘机构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并参观了DARPA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场所,采访了那些与DARPA合作或为DARPA工作的科学家、管理者以及政府要员。
评分作者简介
评分第二次买了,这次还有小赠品
评分还好,多以前不了解的一些东西多增强了解
评分挺好的省事,方便。米也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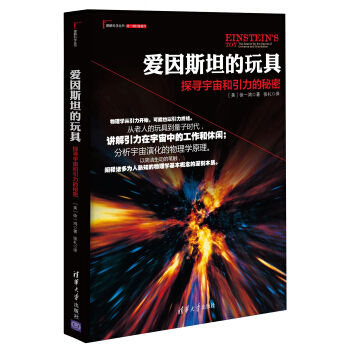
![小错误,大发明:40个发明的小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72437/rBEGD0-w3rgIAAAAAABwQ2JvXWUAAA7iwDrJhMAAHBb218.jpg)
![森林报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22760/9385b7cf-d931-40ff-b431-eac0aab45488.jpg)
![美国国家地理青少系列:怪异恐龙总动员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75445/89dd9f94-f914-4934-8285-ef26a7105587.jpg)
![幼儿安全常识 学前儿童安全常识必备绘本(全5册)真果果出品 [3-6岁] [Children's Safety Educ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62578/54642139Nc3905464.jpg)
![DK趣味立体百科:动物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40930/59bb2cafNb75e4212.jpg)
![杨红樱科学童话(彩图注音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538423/9e3c53ae-45e4-4096-a835-8928716780ba.jpg)
![美国国家地理:非洲动物跳出来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71418/rBEHaVC22JkIAAAAAAEjS8OwJ7kAADEIgEIDegAASNj798.jpg)
![学习改变未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79778/58ae8decN40f37aad.jpg)
![我的第一本美国国家地理:动物百科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93234/rBEhU1MKm_gIAAAAAAJuHCEybQIAAI9IwGbg-cAAm40161.jpg)
![花朵的秘密生命 [ANATOMY OF A RO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97322/591975eaN568a3bb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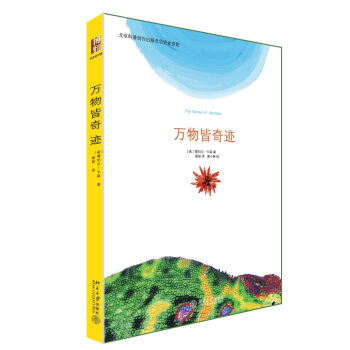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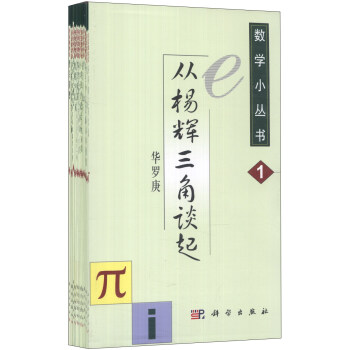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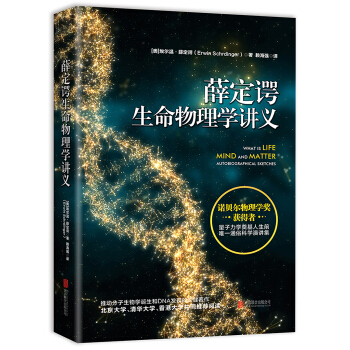

![我的第一本搞笑科普漫画书:不可思议的现象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2453/55a755c1N0edffe57.jpg)
![森林报冬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22761/59a1d952-46c2-4731-aa76-70ed6b76bc87.jpg)
![DK我画的第一套知识百科:我笔下的奇妙世界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27885/55547f7eNfb9c2f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