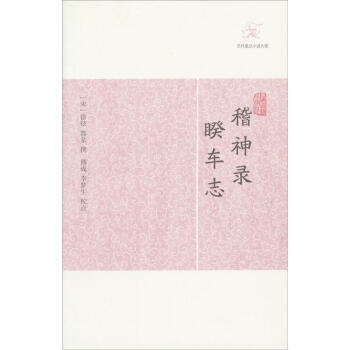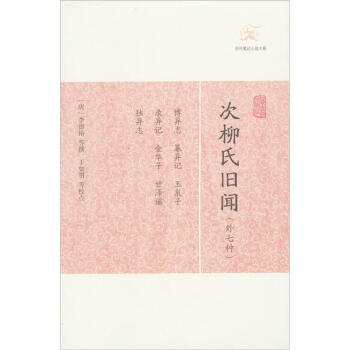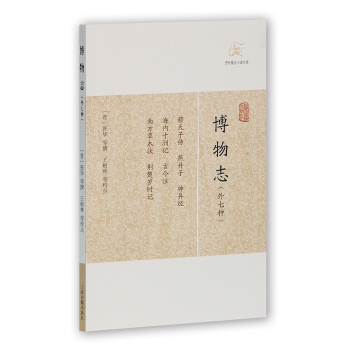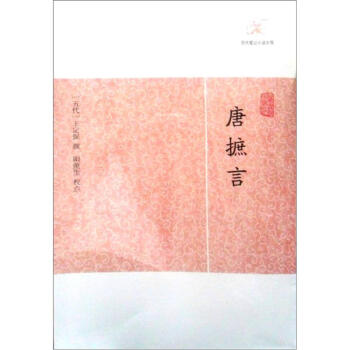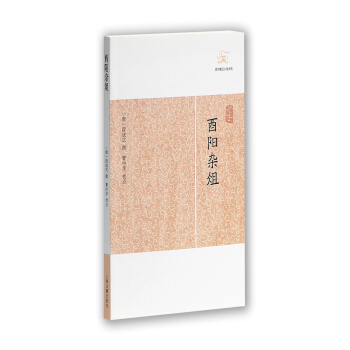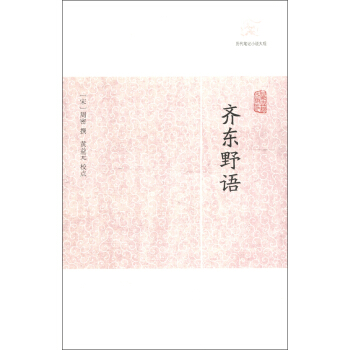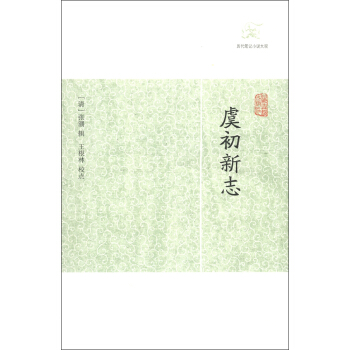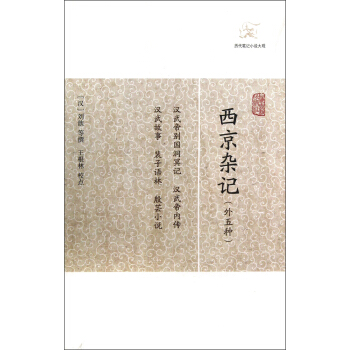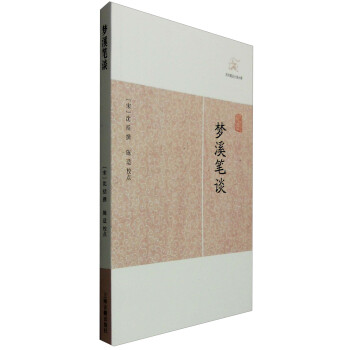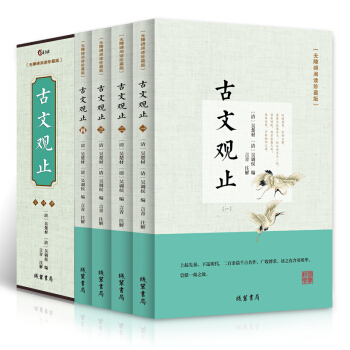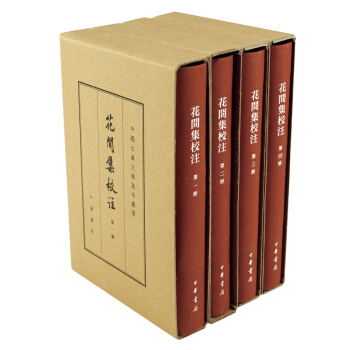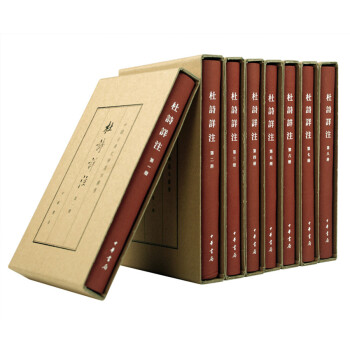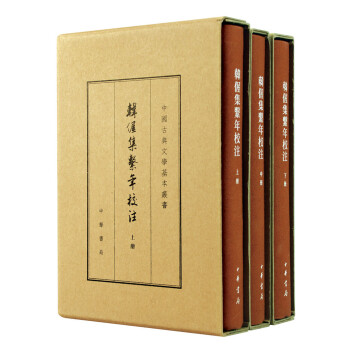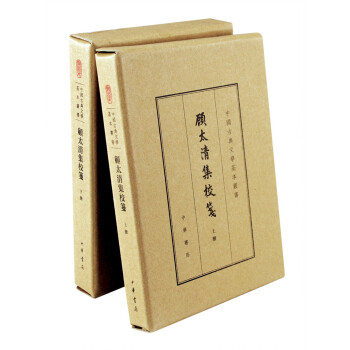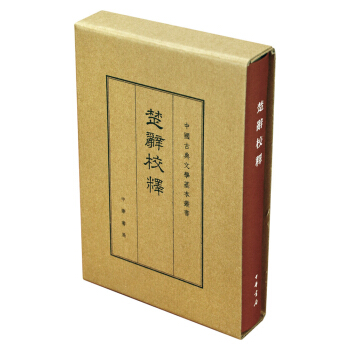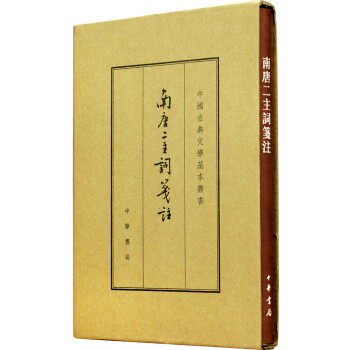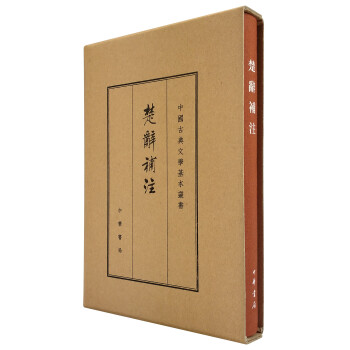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收录《开元天宝遗事》、《明皇杂录》、《松窗杂录》、《开天传信记》、《本事诗》、《杜阳杂编》、《剧谈录》、《桂苑丛谈》共八种。目录
开元天宝遗事明皇杂录
松窗杂录
开天传信记
本事诗
杜阳杂编
剧谈录
桂苑丛谈
精彩书摘
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壞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壞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壞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颞才能言,有京兆尹过壞,命颞咏“尹”宇,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壞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瓖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壞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壞子颞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殉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官,殉子抚为会昌尉,殉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殉曰:“国忠持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殉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殉迁改疾速。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萧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则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这本书,着实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尤其是它在文笔上的独到之处。不像许多古籍那样晦涩难懂,此书的语言风格更偏向于一种雅致的叙述,既有古韵,又不失流畅。读起来,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当时遣词造句时的那种匠心独运。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它没有刻意去渲染悲壮或激昂,而是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将事实呈现出来,但恰恰是这种“不动声色”,更显其背后蕴含的深意。特别是其中一些对话的描写,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人物的神态、语气,甚至隐藏的心理活动,功力可见一斑。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反而让读者有更多的空间去想象和体悟,也更显其高明。书中的许多比喻和形容,也十分贴切生动,让那些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读来不觉枯燥,反而引人入胜。
评分这本《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人情味”。正史往往聚焦于权力斗争和政治格局,但这本书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细节,都得到了细致的描绘。读到书中对某些宫廷人物私下里的言谈举止的记载,你会发现,即使身处尊贵之地,他们也同样会有普通人的烦恼和乐趣。比如,某个平日里威严的官员,私下里竟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与人争执,这种反差极具戏剧性,也让人觉得格外真实。这些“遗事”,就像一块块拼图,虽然零散,却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更加丰满、更加人性化的历史群像。它让我看到了,历史并非只有冰冷的事件,更有鲜活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联系。
评分《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这本书,虽然名为“遗事”,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在补充和印证正史方面。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某些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与我之前阅读过的史书进行比对,发现了不少有趣的异同之处。有些在正史中被一笔带过的细节,在这里被详细展开,为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有些记载,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够印证或反驳正史中的某些说法,其价值不言而喻。书中的“外7种”更是拓展了史料的广度,涉及到了更多层面的人物和事件,使得我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更加全面。当然,对于这些“遗事”,阅读时也需要保持一份审慎的态度,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辨析,但其作为一种补充和参考,无疑是极具价值的。
评分偶然翻到这本《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原本只是被书名吸引,以为是史书或野史,没想到读来别有一番趣味。它不像那些正襟危坐的史书,上来就是家国大事,权臣更迭,而是像一位老友在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琐碎细节。那些关于宫廷生活的描绘,无论是妃嫔的打扮,还是宴饮的排场,都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见。其中对大臣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描绘,更是出人意料,让人忍不住莞尔。比如,某位以严谨著称的官员,在书中竟有如此童趣的一面,让人对其有了更立体、更鲜活的认知。这种“遗事”的视角,恰恰弥补了宏大叙事中往往缺失的温情与烟火气,让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触手可及。它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并非冷冰冰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个体。读罢掩卷,心中不免对那个时代的风物人情,生出几分怅惘与向往。
评分初拿到《开元天宝遗事(外7种)》,以为是一本纯粹的史料汇编,细读之下,才发现其内容之驳杂,远超想象。除了开篇引人入胜的“开元天宝”时期的逸闻趣事,后续收录的几种“外”篇,更是如同打开了一扇扇不同的窗户。有的篇章专注于描述某个特定人物的生平轶事,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该人物的细致观察与深刻理解;有的则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饰、饮食到民俗、宗教,无不涉及,堪称一部鲜活的社会风情画卷。尤其令我惊喜的是,其中有几篇对当时文学艺术的探讨,虽不甚宏大,却独具慧眼,点出了许多常人不易察觉的艺术精妙之处。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呈现方式,使得全书内容丰富而立体,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每一篇都像一个独立的小品,却又在整体上勾勒出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生动的历史图景。
评分《两般秋雨盦随笔》是一部著名的丛著杂纂类笔记,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四类:稽古考辨、诗文评述、文坛逸事、风土名物。由于作者性贯灵犀,博设经典,因而该书中提供的许多资料很有价值,对古代名物佚事的考证论述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评分书已收到,活动价买的,性价比高,快递给力,包装也好。
评分这个系列的书非常喜欢,《清异录》采摭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若干条,每条下各出事实缘起,以类编排为三十七门,天文地理、人事官志、草木花果、虫鱼鸟兽、居室器用乃至仙神鬼妖,无所不备,当时社会方方面面,广为包罗。《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清异录·江淮异人录》有关内容为后世频频引用,颇具影响。惟其条目总数,实为六百五十七,与俞允文序所言六百四十八不符;而目录各门下所载条目数,百花、兽名、鱼、居室、陈设、馔羞诸门亦有一条多寡之出入。大约统计疏漏之外,流传版本的差异也是该书条目数不一的原因。
评分《博物志》由西晋张华编撰。为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实为继《山海经》后,我国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这本书不错,内容不隆冬,实在可以令人在春天里消遣时间,不错,快哉快哉
评分这个版本印刷字体纸张都很满意。没有现代的注解,更干净。
评分不错!不错!支持京东正品!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