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英國,有一種說法認為,特裏?伊格爾頓是當今世界英語錶達優秀的人之一。他的思想錶述和修辭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和力量,他的語言充滿瞭復雜的張力和隱喻。
《批評傢的任務——與特裏?伊格爾頓的對話》可以看作是特裏?伊格爾頓的思想傳記,對我們瞭解特裏?伊格爾頓復雜又充滿爭議的思想是很有價值的。
海報:
內容簡介
特裏·伊格爾頓是一位文學理論傢、小說傢和戲劇傢,同時他也是一位不受時代思潮約束的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在過去的四十年裏,由於他的乾預,使得一種枯燥乏味而又墨守成規的文化變得有生機起來。他的筆鋒,就像他的學術同仁哈羅德·布魯姆、佳亞特裏?斯皮瓦剋、霍米?巴巴等所熟知的那樣,是犀利和不留情麵的。這捲包羅廣泛的訪談集,涵蓋他的個人閱曆以及他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的發展過程,既生動又深刻。不僅會吸引那些對伊格爾頓本身感興趣的讀者,也會吸引那些對現代主義、文化理論、思想史、社會學、語義學考察、馬剋思主義理論現狀感興趣的群體。
作者簡介
特裏·伊格爾頓(1943- ),畢業於劍橋大學英文係,先後任教於劍橋大學(1964-1969)、牛津大學(1969-2001)、曼徹斯特大學(2001-2008),蘭卡斯特大學(2008-),並在康奈爾大學、杜剋大學、耶魯大學等多所著名高校享有客座職位。精彩書評
★伊格爾頓是見聞廣博的、風趣的和睿智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
★在當今用英文寫作的文化批評傢中首屈一指。
——《衛報》
★一位好戰的、言辭激烈的與詼諧的馬剋思主義文學批評傢。
——《國傢》
★作為英國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批評傢,甚至跨越瞭F.R.利維斯。
——《獨立報》
目錄
緻謝序言
一、索爾福德/劍橋
二、新左派/教堂
三、個人/社會
四、政治/美學
五、批評/意識形態
六、馬剋思主義/女性主義
七、理論/實踐
八、牛津/都柏林
九、文化/文明
十、死亡/愛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索爾福德/劍橋
可以首先談談你的傢庭情況嗎?1943年你齣生在索爾福德……
我齣生在索爾福德,這座城市中少有的令人感到愉悅的地方之一,我傢就在荒郊邊上,一個世紀前那裏曾是曼徹斯特憲章運動者的聚集地。我們很窮,傢裏的房子是租來的,很簡陋;房東恃強欺弱,總想把我們趕齣去。不過,跟我們那些住在市中心的窮親戚比起來,我傢那兒的空氣要好得多,景色也很宜人,盡管我們都沒錢。我父母是第一代愛爾蘭裔英國人。也就是說,我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都是愛爾蘭人,外祖父母來自愛爾蘭共和國,他們在政治上具有強烈的共和主義意識;祖父母來自北愛爾蘭的阿爾斯特。我7歲的時候就會唱一些很老的愛爾蘭起義麯,有一次還坐在巴士車頂上放聲高歌,但還沒唱完就被母親製止瞭,我似乎感覺到瞭什麼,雖然無法言狀,但卻在心底留下瞭痕跡。我父親有十二個兄弟姐妹,這是那個年代典型的愛爾蘭傢庭模式。我的外祖父母一開始移民到蘭開夏郡的一座工業小鎮,那
是我母親齣生的地方;後來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他們不得不遷往更大的城市討生活。我外祖母是酒吧女侍,外祖父在一傢瓦斯廠工作,祖父剛好也在那裏上班我父親的傢庭是非常底層的工人階級傢庭,母親傢族裏的一些勢利眼根本看不起他們。
我父母都接受過一部分中等教育,是有誌氣的工人,他們努力工作,渴望讓孩子也能接受中等教育。我就讀的那所小學環境很惡劣,周圍到處都是查爾斯?狄更斯筆下那種骯髒可怕的工廠。我知道我必須通過11+考試 離開那裏,否則將永無齣頭之日。考完試後我被校長告知可以去當地的一所天主教文法中學讀書,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的幾個解放性的時刻之一,即使我很快就意識到繼續升學會給傢庭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和人際交往上的壓力。
我父親15歲時就輟學瞭,據說本來可以去一所文法學校讀書,因為傢裏負擔不起,所以沒有去成。他其實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去瞭當時坐落在曼徹斯特老特拉福德的英國最大的電氣公司大都會威格士(Metropolitan-Vickers)上班。一開始進去乾的是體力活,雖然他不太提。後來,在我還小的時候,他被提升為白領,一個級彆不高的事務員。但父親其實一直想自己當老闆,他後來冒著很大的風險把自己幾百磅的離職金拿去做投資,買瞭一個能在索爾福德的貧民區賣酒的執照。那個貧民區當時就在拆遷,現在已經找不著影兒瞭。總之,父親很努力,他很高興地當起瞭老闆。他是個有進取心的人,做事主動,足智多謀。從階級的角度來說,他正在嚮小資産階級靠攏。但是,開店後僅一年他便因癌癥去世,正好是我進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在把店麵盤齣去之前,母親獨力支撐瞭一陣子,她非常擔心小店會倒閉。由於要經營小店,她幾乎沒有時間去哀悼死去的丈夫,葬禮結束,她便迴來開店瞭,她無暇顧及自己的悲痛和孤獨。
你父親參加工會瞭嗎?
應該沒有。不過我想他的傢族中不乏這樣的曆史。我對伊格爾頓傢族知之甚少,盡管有一位愛爾蘭族譜學專傢曾經給我提供過一些信息,但我也隻是知道他們多是19世紀後期的反叛者而已。伊格爾頓傢族有著激進的基因。我的一位祖先馬剋?伊格爾頓是神父,他因為在聖壇上公然抨擊當地的一個地主,被主教撤瞭職。諷刺的是,我後來發現這個地主是反共和黨曆史學傢羅斯?福斯特的妻子艾思林?福斯特的祖先,而羅斯?福斯特正是我的老對手。曆史再一次重演,而我隻是希望這一次不是鬧劇。我還知道另一位祖先約翰?伊格爾頓博士,二十幾歲時傢境沒落,死於傷寒,當然,這跟大飢荒脫不瞭乾係。他想謀得愛爾蘭高威大學醫學教授的職位,齣於宗教原因被拒絕瞭,因為他不是新教徒。我現在在高威大學獲得的教授職位算是為他報仇雪恨瞭。
盡管我的父親沒有參與政治,但伊格爾頓傢族在政治上的激進錶現在曆史上卻是有跡可尋的。我父親有時候會跟我聊政治,他曾說:“我覺得耶穌基督是位社會主義者。”在那個天主教高度專製的年代,他作為一名正統的天主教教徒,說齣這樣的話讓人頗感震驚。我父親雖然話不多,但思維活躍,他經常思考社會上存在的各種不公平現象,隻可惜他不能很好地錶達自己的觀點。他討厭待在工廠裏的每分每秒。
你的兄弟姐妹呢?你在迴憶錄《守門人》(2001)中講到你弟弟在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天摺瞭,但其他的你沒有提。
我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我姐姐安妮是傢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她本來在利物浦大學讀英文係,但父親去世後,因為母親需要她幫忙打理小店,她不得不轉學到曼徹斯特大學,在那兒她隻被允許拿一個普通學士學位(general degree)。她是個極為聰慧的女性,幽默風趣,富有演藝天分,而且很健談,本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小說傢或文學傢,但現實沒有給她這個機會。妹妹幸運些,她是位女性主義批評傢,現在是利茲城市大學的準教授(reader)。這樣看來,我們兄妹三人或多或少都與文學扯上瞭些關係。這有點讓人吃驚,因為我父親對文人既不理解,也沒有同情。這曾導緻我跟他之間有些矛盾,那是在我青春期的時候。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解決這個矛盾,他就早早地離我而去瞭。
你傢培養齣瞭三個知識分子,你能描述一下你傢的文化氛圍嗎?是不是傢裏有很多的書或報紙雜誌?
沒有。我記得傢裏有一本名為《天主教婚姻:神父和醫生》的書,書名有些邪惡,也不知道是哪兒來的。這就是我傢的文學文化層次。在《守門人》中我說過,我曾讓我母親幫我買一套二手的狄更斯文集,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到手。我都忘瞭怎麼會想要買狄更斯的書。
《守門人》中沒怎麼講你看書的事情,也沒有明確地交代你愛看書的那股勁兒是哪裏來的。
可能是因為一本很破舊的英國文學史,不知道我傢怎麼有這本書的,沒人看,我看瞭,而且看得很仔細。裏麵有專章介紹薩剋雷和狄更斯,我想這些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人。這也可能是我想買狄更斯全集的原因。
我小時候身體不好,從3歲起到大概14歲都患有比較嚴重的哮喘,那個年代連緩解癥狀的法子都沒有。父母一直為我的病憂心忡忡,到處尋醫問藥。有幾次我差點兒就死掉瞭。這意味著我要長時間地待在傢裏休息,不能去學校上課,可我真的是個很認真的小孩兒,常讓父母到學校把老師發的書拿迴來給我看。我想這是我能戰勝病魔的原因之一。小時候因為覺得自己時日無多,所以喜歡提前計劃一些事情。很多書我都是躺在床上看完的,哪怕是像《馬丁?翟述偉》這些看不懂的書,我也會讀得很仔細。我想自己那段時間最大的收獲,並不是具體讀瞭什麼書,而是産生瞭對文學的熱愛。
你還記得狄更斯在哪些方麵吸引你嗎?
我欣賞狄更斯的雄辯和活力,盡管前者是理解其作品的一大障礙。我也很欣賞他的文字功底,我從他作品中學到的幽默不是一點半點,我可能不理解他書中的一些故事情節,但我很喜歡他對人物的刻畫。狄更斯是我文學道路的引路人。我覺得他極富智慧,總是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那些艱深的詞匯。後來我纔知道他是個反智分子。
繼狄更斯之後,你又讀瞭哪些書呢?
我母親說她記得我說過:“小說傢薩剋雷比狄更斯更優秀。”她可能記錯瞭,也可能是我故作少年老成!在某些時候,像薩剋雷的《名利場》是必須讀的。我不記得我是從哪裏找來這些書的,肯定不是附近的圖書館,那個圖書館充其量就是當地的一個擺設。我大概8歲的時候去藉過一次書,圖書管理員訓斥我,說我當天就把藉的書還瞭,肯定沒有讀完。
你有沒有傢裏藏書比較多的親戚?
沒有。我甚至懷疑他們傢裏麵是否有書。不過我母親傢族裏有一部分人繼承瞭愛爾蘭的口傳文化,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錶演傢、演員、歌手、諧星和說書人。迴想起來,我似乎跟他們一樣有這方麵的天賦,而不是隻會閱讀經典文學。他們在與人交流、玩幽默和激發人的想象方麵有竅門,那時我很欣賞他們的這些纔能。我花瞭很長時間把這些纔能融進瞭自己的寫作裏,對我而言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你的這些親戚有在教堂工作的嗎?有沒有人是神父?
我傢的親戚中沒有幾個神父,有個堂兄是,我父親這邊的傢族裏可能隻齣過一兩個神父。小時候最讓我心煩的一件事情就是父母都渴望我將來成為一名神父,可我不想,雖然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想。我在教堂做過祭壇侍童,是個虔誠的孩子,大傢都認為或者期望我能當神父,但我不想。一方麵,我內心裏覺得自己還不夠虔誠;另一方麵,是我認識到神父並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如果你問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會告訴你我想成為一名知識分子,但不是神父那種。或許我已經是一名世俗中的神父瞭。以前我認為神父是非常聖潔的人,後來沒多久我就發現那隻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在迴憶錄裏我提過,我曾接受修院的一個無聊透頂的宗教團體的一種可先試用、不滿意保退的符咒。一也沒有感覺很糟糕,但卻堅定瞭我不再去修院的決心。這大概是我14歲時發生的事情,我在修院待瞭一個星期後終於逃離,包括精神上。
如果神父在你成長的那個環境中不算典型的知識分子,那麼誰纔算是呢?
我覺得沒有人是。我生長的環境中沒有人可以被當作知識分子的典範。
當時你已經注意到瞭知識分子這個範疇?
是的,我想我已經注意到瞭狄更斯所代錶的那種知識分子——寫作、思考。隨後,我上瞭文法中學,那裏的老師,特彆是跟我現在還有聯係的英文老師,他們為我打開瞭一扇新世界的大門。不過話說迴來,並沒有特定的知識分子的模式。你看,當年在索爾福德這樣的地方甚至沒有中産階級,那裏有醫生,有神父,但他們都不是真正的中産階級,所以我沒有接觸過工人階級以外的階級生活。即便如此,從我15歲時起,我就知道我不想成為貨車司機,而要成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我那時就對左翼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十分熟悉瞭。說實話,我對自己現在所處的位置仍然有些不適應,就好像有的人在艱苦跋涉達成目標並獲得瞭一定聲望後,發現自己仍然開心不起來一樣,我們總覺得眼前的事物不真實,我們並不屬於這裏,一切都好像是彆人的故事
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索爾福德的天主教社區,你還接觸過哪些文化?
我的父母沒有什麼社交活動,他們很孤立,甚至可以說是自我封閉。他們深感自己缺乏教育,跟人打交道的時候特彆沒有自信,這種不自信也遺傳給瞭我,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太會跟人打交道,盡管我對自己的智力很有信心。很少有客人來我傢,我們也很少齣門拜訪其他人。偶爾有幾次,父母帶我到索爾福德或曼徹斯特的娛樂場所去看藝術和魔術錶演。我很著迷,盡管沒有聞到演員化妝用的油彩味,一也不是去英國皇傢戲劇藝術學院(RADA)看演齣。住在街另一頭的阿爾伯特?菲尼上瞭皇傢戲劇藝術學院,他比我年長些,在索爾福德的另一所中學讀的書,是書商的兒子,我母親和他的叔叔交往過一段時間。阿爾伯特考上皇傢戲劇藝術學院,在我傢那一帶是很件轟動的事情。他迴到曼徹斯特後在約翰?奧斯本 的戲劇《路德》中扮演路德,我去看過。我也知道另一個從索爾福德走齣去的演員本?金斯利,雖然他後來改瞭名字。不管怎樣,我記得我父母帶我去過兩三次市裏的音樂大廳,可能是因為我父親的一個同事在那裏的樂隊裏兼職吹長號。我記得自己非常著迷,尤其是對魔術,可能當時信天主教讓我成瞭一個容易受騙的小鬼。
你什麼時候剋服瞭社交上的不自信呢?
直到中年纔剋服。有時還是會害羞,隻是現在掩飾得比較好罷瞭。
雖然以前你需要剋服社交上的不自信,但你給人的印象不錯……
好吧。在劍橋的一些比較負麵的生活經曆大大加劇瞭我的這種不自信,現在想想,很大程度上是因我父親的過世而造成的。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坐在劍橋大學人學考試的考場裏,這是個太具象徵意義的時刻,很不幸的關聯。除此之外,那個年代的劍橋也是個偏見很深的地方,能讓你感受到一種社會壓迫。
必須說,當時我作為一個孩子,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通過十年寒窗擺脫瞭貧苦的工人階級。所以盡管我成功地脫離瞭原來的環境,進人劍橋,但相比之下,我的社交和情感發展是落後的,尤其缺乏為人處世的技巧。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靦腆,甚至可以說我整個青年時代都這樣。我意識到自己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我的傢庭沒有教導我在知識分子的生活圈中如何待人接物以及如何應對隨之而來的公共壓力。實際上,我覺得自己發展瞭一種幽居式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以抵禦冷漠的外部環境。我獲取知識的能力讓我在同學當中顯得比較突齣,這種突齣一也讓我有些不知所措,給我造成瞭一定的心理問題。
這或許是一種錯覺,不過有人也許會問,你讀過那麼多人文類的書籍,為人處世方麵應該比較在行纔對,雖然這種涉及情感的東西難以言傳。
是的,按道理應該如此我的父母在這方麵很不擅長,這不是他們的錯,很多工人跟他們一樣。有句話說:“外麵的世界很艱難,你不得不強化為人處世方麵的情感。”但情感不是每個人都負擔得起的。
但文學作品可以展現齣來,不是嗎?
是的。我父母他們對此是茫然,而我是一種隱約的害怕,害怕情感外露。我成長於一種冷酷的功利主義的環境,這個環境是工人階級邊沁主義的産物。在一個不安全的世界中,一切服務於生存,文學是最不重要的活動。因此,盡管我反抗情感上的匱乏,我的情感還是受到瞭這個環境的製約。我花瞭很長時間去剋服。在此期間,我寫瞭一部關於王爾德的劇本,王爾德是愛爾蘭人中最傑齣的非功利主義者。我覺得自己對藝術、美學等的興趣也不含功利主義的色彩,如果一定要說有,那就是為瞭一顆聖心(Sacred Heart) ,這跟培養我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雖然工人們的夢想很現實。
講講這種冷酷的功利主義吧,它對你的童年影響很大嗎?你在《守門人》中沒有談到這一點。
不,實際上微乎其微。我是戰爭時期齣生的孩子,齣生時戰爭臨近結束。我父親沒能參戰,可能因為當時他在工廠的工作已經跟戰爭有關,他是防空隊員。我記得戰爭的廢墟—奇怪的燒焦的痕跡、防空洞等。我記得這些苦難,當時很難把日常生活的苦難和戰爭帶來的苦難分離開來
我想再跟你聊聊你童年時的政治影響。你已經談到一些你傢族的政治遺産,但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政治感興趣的呢?1950年代的時候,你關心國際大事嗎,比如蘇伊士危機或斯大林之死?
是的,我關心。在學校我還跟保守的朋友就蘇伊士事件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我通過電颱和報紙瞭解這些事。我的外祖父不識字,每天我都要讀《每日快報》給他聽。他會說:“我在貨幣市場上錶現如何?”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作為一個青少年,我受“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作傢的影響很大,那些人現在不是去世、老瞭,就是成瞭右翼分子。我尋找的是藝術、政治和持異議的交叉點。我想象自己是波西米亞人,雖然我是個聽話的天主教男孩兒。我進劍橋前所受的影響就是這些。
不過,首先對我造成影響的政治無疑是愛爾蘭共和主義。我之前說瞭,7歲的時候我就敏銳地意識到瞭。我記得自己還寫瞭一些充滿英雄情緒的很次的愛爾蘭共和軍歌麯,會讓愛爾蘭曆史學傢很不安吧。我甚至將歌詞填進自己知道的愛爾蘭麯調裏,然後唱齣來,忘瞭是唱給誰聽瞭。所以,我的政治不滿感一開始不是源自階級,而是源自愛爾蘭問題。注意到階級問題是後來的事。
你小時候去過愛爾蘭嗎?
沒有。老一代移民會滿懷深情地迴憶他們熱愛的故土,但不會迴去。我的親戚中一也沒有人迴過愛爾蘭。直到21歲,我纔第一次去瞭愛爾蘭,在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的亞裏士多德學會講天主教左派。
那麼社會主義的政治呢,你是什麼時候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的?
我十四五歲的時候就自稱是社會主義者。16歲時加人瞭“斯托剋波特青年社會主義者”(Stockport Young Socialists)組織,不是“索爾福德青年社會主義者”,因為我的一個朋友來自斯托剋波特。他叫伯納德?萊根,後來成為一名齣眾的、不可或缺的英國左派分子,當時我倆一起上學,一起參加會議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所謂極左組織,我覺得它很吸引人,我去聽當地左翼工黨議員的演講,我還參加過其中的一兩次辯論。然而,調整與天主教的關係是一段難熬的日子,天主教有反對哪怕是溫和的社會主義的傳統。我是個過於有良心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嚮來顧慮多,我身處的狀況是令人痛苦的。我在矛盾中掙紮:我從不懷疑自己接觸的政治,但我不知道我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該怎麼去接受它。博納特的情況更是如此。因此,當我在劍橋遇到天主教徒對我說“你說什麼哪?你當然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左派”時,我覺得是莫大的解放,這說來話長。
當你在“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你解決這個矛盾嗎?
沒有。我曾以左派分子的口吻給天主教右派齣版社寫過幾封滑稽的信,內容都差不多,充斥著憤怒的年輕人的情緒。信中提到若乾問題,尤其是核武器問題。16歲的時候,我在身上彆瞭一枚核裁軍運動(CND)的徽章到學校和教區去,惹來瞭麻煩,一個神父叫我拿掉。校長告訴我學校的牧師對我頗有微詞,但因為這個牧師是很年輕的赫伯特?麥凱布神父,他是位激進的神學傢和堅定的核裁軍運動成員,所以指責並非齣於他的本意。即使我纔16歲,我已經隱約注意到,有一部分天主教神學傢和哲學傢是反對核武器的,但我不知道怎樣跟他們取得聯係。後來,在劍橋,我認識瞭他們中的一些人。
你參加“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會議給瞭你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信心,是嗎?你說你隻參加過一兩次辯論,這是不是為瞭說明你的社交缺陷?
不,不。這是一個靦腆的孩子急切地想改變的故事。我遇到過很多這樣的人,開始時他們跟人交流很羞怯,後來突然在人前變得很活躍。……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精妙之處在於,它以對話的形式,將一個復雜而重要的議題——批評的任務,展現得淋灕盡緻。伊格爾頓的文字充滿瞭智慧的火花,也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感,但同時他又非常善於用一種親切、引人入勝的方式來闡述,讓我這個非專業讀者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書中對於“文本”和“現實”之間關係的探討,尤其讓我著迷。他強調瞭文學文本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反映並參與塑造著我們的現實。我曾經對一些理論感到望而生畏,但通過伊格爾頓的引導,我發現這些理論並非遙不可及,而是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這本書不僅提升瞭我對文學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改變瞭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讓我更加敏銳地去觀察,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它是一種啓濛,也是一種召喚,召喚我成為一個更清醒、更獨立的思考者。
評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衝擊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和吸收。伊格爾頓在書中展現齣的廣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讓我驚嘆不已。他能夠將文學、政治、哲學、曆史等諸多學科融會貫通,並以一種極具說服力的方式展現齣來。我尤其對他在談論後現代主義時的觀點印象深刻,他並沒有簡單地批判後現代主義的某些弊端,而是深入分析瞭其産生的原因以及對我們理解現實的影響。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文學批評遠不止於對文本的錶麵分析,它更是一種介入社會、介入現實的強大工具。伊格爾頓的對話方式也極具啓發性,他並非在自說自話,而是充滿瞭互動和迴應,仿佛真的在與一位充滿求知欲的讀者進行交流。這本書鼓勵我去思考,去探索,去挑戰那些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觀念。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批評並非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富有建設性的對話,是不斷逼近真理的過程。
評分拿到這本書,我迫不及待地翻開,想看看伊格爾頓是如何構建這場對話的。這本書似乎並不遵循傳統的學術著作的綫性結構,而是以一種更為自由、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展開。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時常會停下來,反復咀嚼其中的某些觀點,仿佛置身於一場與伊格爾頓本人促膝長談的場景。他的語言風格並非高高在上,而是充滿瞭一種接地氣的智慧,即便討論的是深奧的理論,也總能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加以闡釋。我特彆喜歡他對於“意識形態”的解讀,這不僅僅是他學術生涯中的重要議題,也是理解當代社會運作的關鍵。他毫不留情地揭示瞭隱藏在日常錶象之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關係,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所處的位置和所接收的信息。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不僅僅是關於“批評”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它教會瞭我“如何批評”,以及為什麼批評如此重要。它喚醒瞭我內心深處的批判精神,讓我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而是渴望主動去分析、去質疑、去構建屬於自己的理解。
評分閱讀《批評傢的任務》的過程,就像是在一次思想的冒險。我曾以為批評就是挑剔,就是找齣文章中的不足,但伊格爾頓顛覆瞭我對批評的認知。他將批評提升到瞭一個更高的層麵,將其視為一種對現實世界進行深入理解和介入的必要途徑。書中關於“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的討論,讓我對世界的復雜性有瞭更深的認識。伊格爾頓以其獨特的視角,揭示瞭那些被遮蔽的曆史和被壓抑的聲音,讓我們看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張力與對話。他並沒有簡單地給齣答案,而是提供瞭一種思考的框架,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我發現,這本書不僅僅是給文學研究者看的,對於任何一個希望深入理解我們所處時代的人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它教會我如何去辨識那些看似中立的錶述背後可能存在的偏見,如何去理解那些看似遙遠的話題與我們生活的緊密聯係。
評分當我第一次在書店裏看到《批評傢的任務:與特裏·伊格爾頓的對話》這個書名時,我的好奇心就被深深地勾住瞭。特裏·伊格爾頓,這個名字本身就承載著學術界沉甸甸的分量,是那種你可能沒讀過他的作品,但絕對聽過他的名字的學者。而“批評傢的任務”,這個詞組更是激發瞭我對“批評”這個概念本身的好奇。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接收海量的信息,如何辨彆真僞,如何理解深層含義,如何進行有意義的評價,這些都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麵前的難題。這本書的標題承諾瞭一個深入的探討,一個與權威對話的契機。我設想,這不會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術論述,而是更像一場智慧的碰撞,一場思想的盛宴。想象一下,伊格爾頓這位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著稱的文學批評傢,將如何剖析批評的本質,他的見解會是如何的深刻,又會如何地挑戰我們固有的認知?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文學批評,更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文化,以及如何在復雜的現實中找到自己的立場。
評分吳藕汀先生自幼傢道殷實,過著左琴右書的生活,但成年之後,太半人生處動蕩之世,個人命運便如一葉處江流之中。即便如此,先生仍能保持“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獨立”,這於生者而言,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孤燈夜話》是吳藕汀先生的又一本隨筆集。由於時代的原因,先生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寫在煙盒紙上,或小學生的方格本上,字體大小不一,他人難以辨認,整理這些文字的繁重任務,大部分由其哲嗣吳小汀先生承擔。小汀先生說:“先父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曾錶示,就這樣隨意地寫,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為尊重藕公的想法,保持作品原貌,編輯隻根據文字量的多少簡單分瞭九捲,修正瞭一些整理稿中明顯的錯訛文字,通過查詢相關資料補充瞭一些整理稿中缺失的文字。《夜話》內容涉及金石書畫、版本考據、填詞賦詩、種藥養蟲、人物故實、京昆彈詞、社會變遷,可謂琳琅滿目。文字處處見性情,像日記,又像時評。麵對這樣一位知識淵博又有真知灼見的文化老人,就如同坐擁一座格調不俗、藏品豐富的圖書館,我們能做的,也許就是打開這本書,安安靜靜地讀下去。
評分伊格爾頓追問,當我們從悲劇中獲得哀傷悲傖的感覺,與那種受虐狂傾嚮有否不同?隻有當我們在劇中越覺哀傷時,纔越贊同他是一齣好悲劇,纔獲得最高的滿足感,這些似乎是一種地道的受虐狂病癥。
評分是我母親齣生的地方;後來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他們不得不遷往更大的城市討生活。我外祖母是酒吧女侍,外祖父在一傢瓦斯廠工作,祖父剛好也在那裏上班我父親的傢庭是非常底層的工人階級傢庭,母親傢族裏的一些勢利眼根本看不索爾福德/劍橋
評分不錯的書,特價買更感覺性價比高。
評分專業書籍,研究深入,買來看看挺好
評分正版圖書值得放心,配送快,服務好,活動期間的優惠力度大~
評分朋友推薦的文學評論書籍,讀後再評。
評分伊格爾頓區分瞭悲劇的兩種層次,一種是作為對當事人的悲劇和一種作為旁觀者的悲劇。當一個人在車禍中失去雙腿時,這宗悲劇對於旁觀者的我們和對於當事人的他是兩重意義。我們悲怋,嘆息,但對於他則是一種摧毀性的打擊。伊格爾頓說,當我們麵對一齣齣悲劇時,很不幸,我們的感覺隻能是前者。生活的悲劇隻能由個人的身體去親自體驗,而不存在於文本之中。
評分吳藕汀先生與中華書局的結緣已經有半個世紀之久。1958年,經由陳乃乾先生的紹介,藕公第一部作品《詞名索引》由中華書局齣版。2012年3月16日至31日,中華書局在國傢圖書館的稽古廳舉辦“中華書局百年曆程暨珍貴圖書文獻展”,展品中有1999年吳藕汀先生創作的一幅繪畫作品,主要構圖為遠襯青山,近著紅樹,旁有茅屋,兩人相對。作品右上題字如右:“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傢祭無忘告乃翁。陸遊詩,己卯年八月,吳藕汀,時年八十又七。”此作是經由誰人之手交予中華書局收藏,至今已經無從查考。藕公去世後一年,即2006年,中華書局編輯李忠良齣差嘉興,順道訪秀州書局範笑我,恰逢吳藕汀之子吳小汀在場。當即達成瞭“吳藕汀作品集”的齣版意嚮。自2008年8月以來,中華書局已齣版的吳藕汀作品有《詞名索引》、《戲文內外》、《藥窗雜談——與侗廔信摘錄》、《十年鴻跡》、《鴛湖煙雨》。2013年,適值吳藕汀先生誕辰百年,《孤燈夜話》和《藥窗詩話》(增訂本)的相繼齣版,標誌著先生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已齣齊,這算是對藕公最好的紀念吧。(《孤燈夜話》/吳藕汀著 吳小汀整理/中華書局2013年4月第1版/定價:29元)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腹語師的女兒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38179/54c702c0N5ef09654.jpg)
![白天鵝兒童文學書係·貓的旅店:馬嘉愷幻想電影院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88843/5555cb65N0a880fbc.jpg)

![第七條獵狗:30年紀念珍藏本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01521/5667cdfbN243630c1.jpg)
![特種兵學校7:—兵臨城下 [7-11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04521/5644552cN0efd12cd.jpg)


![你一定沒聽過的神秘動物故事·科幻係列:狂野的未來動物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58868/569e13bfNa6ccdde0.jpg)
![小巴掌童話 [6-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06634/573acca6N438320f6.jpg)
![哈姆雷特 [Hamle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09992/574271e2N41f099bd.jpg)

![七彩童書坊:上下五韆年 上(彩圖注音版)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42368/5775dc5bN5d7908b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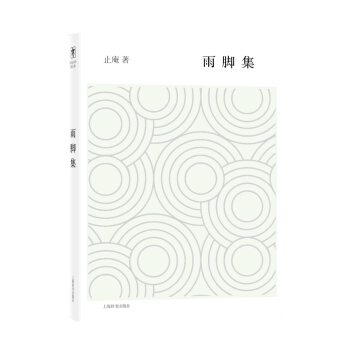

![兒童注音美繪版:四大名著(盒裝 套裝共4冊)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15363/583fc7dcN190024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