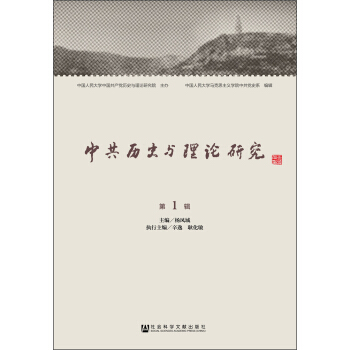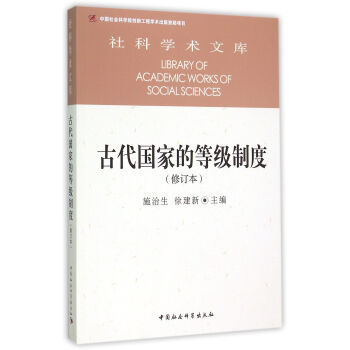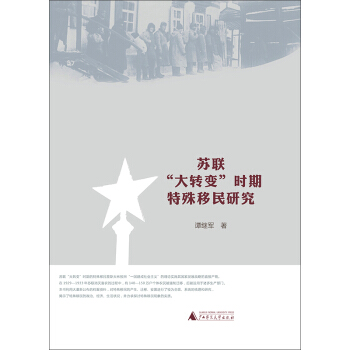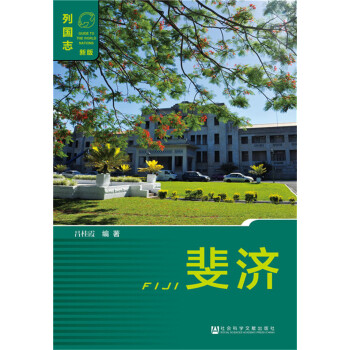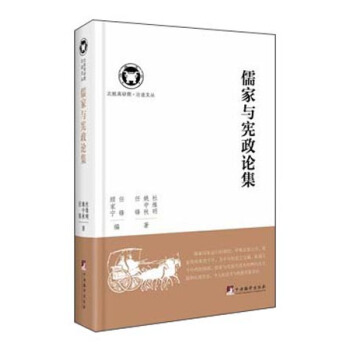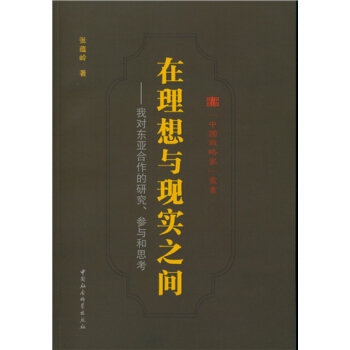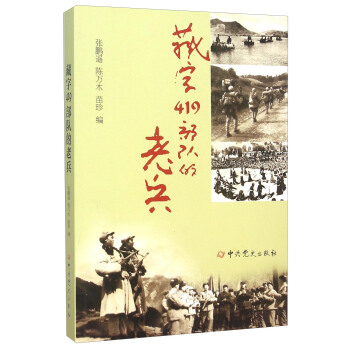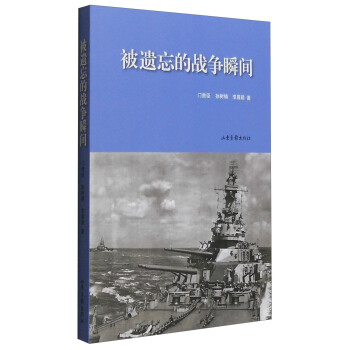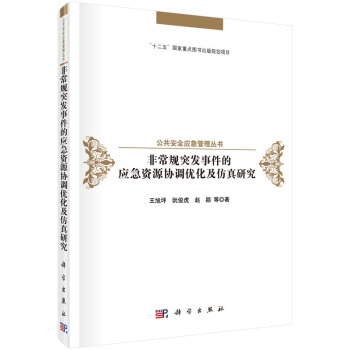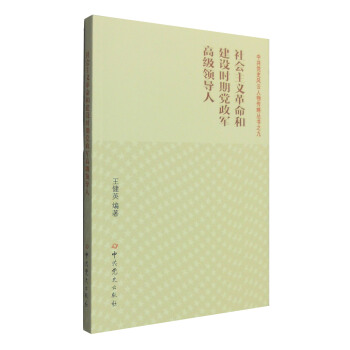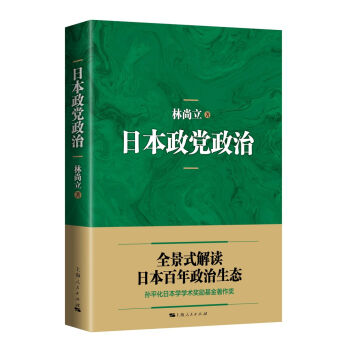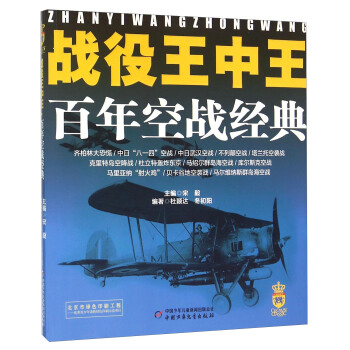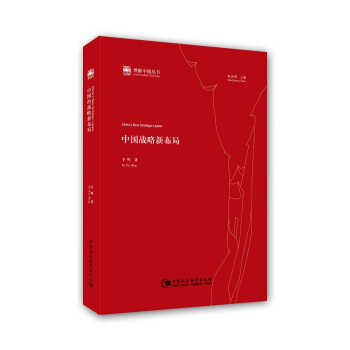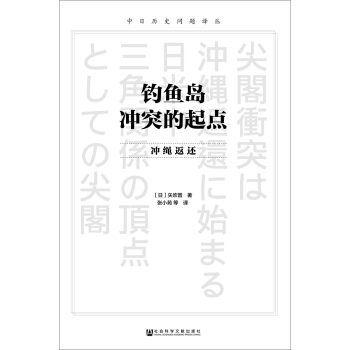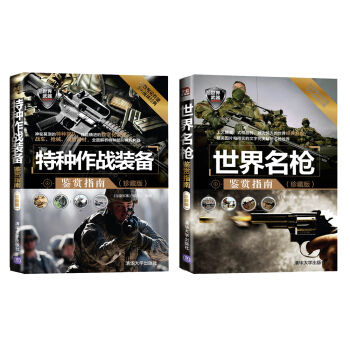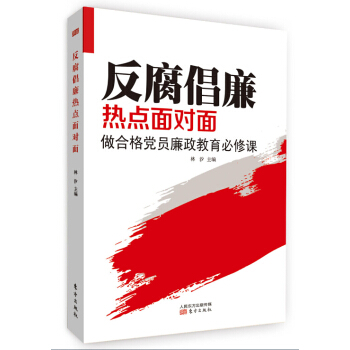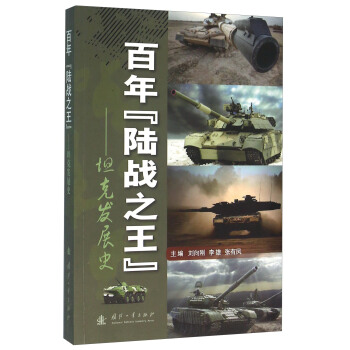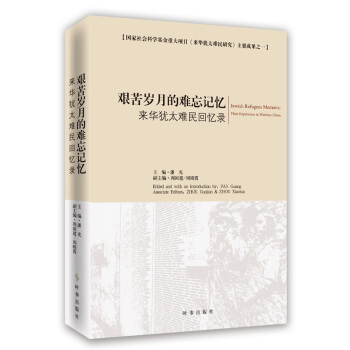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内容简介
时事出版社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此书,本着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在数次艰苦细致的采访中,去粗存精,为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贡献了充满华彩的一笔;与世界正义的人民一道口述历史分享光荣!作者简介
潘光,1947年生于上海,在海南省长大,后来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取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和历史,其中包括犹太以色列研究、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危机和反恐怖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他为国际文明对话联盟高级委员会成员。目录
本书采访或引用其回忆录的犹太难民简介第一章 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
第二章 抵达上海,走进中国
第三章 在中国的土地上闯荡和拼搏
第四章 最艰难的时刻——虹口隔离区
第五章 患难中同甘共苦——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
第六章 战争结束的前前后后
第七章 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
目前掌握的来沪犹太难民姓名录(英文)
犹太难民来华大事记(1933—194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简介
后记
精彩书摘
谨以本书纪念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幸存70周年前言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
主编的话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随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1933年4月,纳粹德国颁布了第一个反犹法令“恢复公职人员法”,规定“非雅利安祖先的文官必须退职”。根据这一法令,犹太人被赶出了政府机关。同月,制定了“大学生十二守则”,其中一条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是犹太人。”此后犹太裔大学生在校园内处境日趋困难。同年10月,“国家报刊法”出台,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连配偶都不能是犹太人,于是犹太人又不得不离开新闻和出版部门。1935年秋,纳粹德国公布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及一切相关的政治权利,并且不准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源血统的公民”结婚。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和纳粹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抵制和冲击犹太人经营的企业、商店和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如共产主义书籍)均付之一炬。许多世界文化名人如海涅、毕加索、门德尔松、塞尚等人的作品均被查禁,连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泰斗和文化巨匠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 1936年反犹行动稍有收敛,因为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奥运会一过,反犹行动立即再次升级。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一秘赖特,纳粹当局立刻借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犹狂潮。11月9日这一天,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2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由于当日成千上万块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称为“玻璃破碎之夜”(Kristallnacht)在犹太难民的回忆中,也有称其为“碎玻璃之夜”和“水晶之夜”的,本书均根据采访时原话记录,不加以硬性统一。。在史书中,这个词后来就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代名词。此后,纳粹当局又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犹太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带黄星,犹太人的护照均要加盖“J”字,犹太医生的许可证也被吊销。至此,德国犹太人已丧失了生存的权利。 第一章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随着德国吞并和占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令被照搬到德占地区,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针。1938年3月—1941年5月,纳粹德国先后吞并、侵占和“进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于是纳粹的反犹运动也扩展到了上述地区,一些傀儡当局与纳粹狼狈为奸,在其中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在这一时期开始对犹太人实行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方针。波兰的几百万犹太人全部被集中到特定的隔离区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华沙的50万犹太人被赶入仅271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成千上万的人不堪饥寒交迫而死去。在维也纳,纳粹建立了“犹太移民总处”,专门负责将奥地利犹太人驱赶出境,并在这些犹太人离去之前榨尽他们的钱财。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有近10万奥地利犹太人倾家荡产才换来了出境许可。在柏林,承担同样使命的机构名叫“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从1933年到1939年,超过28万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本土,占1933年德国境内525万犹太人的533%,对那些缴不起费用的犹太人,纳粹当局千方百计逼犹太富豪和慈善组织为他们掏腰包。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英文缩写为JDC)犹太慈善组织,1914年建立,旨在援助和支持全球各地处于困境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难民。为此就付出了数百万美元。 1843年,上海向外国人敞开了大门,此后欧美列强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英、美两国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法租界。在近一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移民和难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尤其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区,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一个“孤岛”,只能通过海路与外部世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而且不需要经济担保等其他文件,这对于许多被关过集中营,而又身无分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尤为重要。不过,许多犹太难民仍千方百计地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因为只有获得某国发放的签证,他们才被允许离开纳粹占领地区。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拒绝向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通过发放签证拯救了数千犹太人,他发的签证被称为“救命签证”。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欧洲的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英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法西斯向中东的进逼,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的进入作出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德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号轮船拒之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实际上,当时只有极少数有钱的犹太人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纳粹是杀人犯,但美国也成了“被动的帮凶”。同时,不少中立国怕招惹是非而拒绝接收犹太难民,而许多亚洲、非洲、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困难而无力安置犹太难民。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多少犹太难民。就是在这样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面临死亡威胁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逃往上海——当时世界上唯一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东方大都市,也有少数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哈尔滨、重庆等中国城市。 犹太难民回忆〖1〗1欧内斯特·科尔曼(Ernest Culman)1935年《纽伦堡法案》开始实施后,事态变得严峻起来。1935年还是1936年,我记不清了,我父母想去一个紧挨着湖边的度假胜地打发暑假。于是我们向当地一个犹太人开的旅店寄出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执,度假的地方离柏林不远。我记得父亲有一次还专门询问店老板,我们是否可以到湖里游泳,因为在许多有湖的景点都写有“禁止犹太人进入”的标语。“没问题,当然可以。”店老板如是回答。可我们到了湖边却发现湖边的许多地方都有写着“禁止犹太人入内”的字眼的标识。 1938年的时候,我父亲的工作权利也被剥夺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患者来找他看病,政府不允许他给非犹太病人看病,当然也不能给雅利安人看病。 1938年11月10日,我回到了学校。我不仅是我们全班,而且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名犹太学生。大家对“水晶之夜”所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到家后,母亲问我:“你在学校听说了什么吗?”“是的,犹太会堂被烧了,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母亲哭了,她告诉我说一位虔诚的老人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样去犹太会堂,可却发现会堂被烧毁了,老人立刻返回通知了母亲,他说起话来还有点儿结巴。母亲最初的反应是灯或是燃烧的蜡烛被打翻了,造成了教堂失火,她从没想到过会是人为故意烧毁的。 有一天,我父亲去看望一位被秘密警察带走遭受毒打的病人。警察来到我们家搜寻我父亲和我哥哥,我哥哥当时快有13岁了,他说:“你们要找的科尔曼医生不在这里。”“那他去哪里了?”警察问道。“他出诊去了。”“上哪里出诊?”警察依然穷追不舍。后来警察在一位病人的家里找到了父亲,我父亲就这样被带走了,被关进了监狱。 监狱里的大部分人都住在一个类似于宿舍的大房间里,唯独我父亲自己一人住一间房。他在格里尼茨住了有三十年之久,几乎那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我母亲问监狱的管理人员为何我父亲单独住一间房,监狱管理者说:“科尔曼女士,这不是什么单独监禁,我们不能把科尔曼医生和其他人关在一起。”其他人都认为我父亲有特殊权利,实际上他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房里非常可怕,没有人可以说话,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我回到学校之后,蒂尓老师每天都找我坐在长椅上交谈,“你父亲还在家吗?你父亲还在家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问我。格里尼茨的警察长曾经是德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官,由于是他负责被临时关押在监狱里的人,他没有把任何人送去集中营,所以五六天之后我父亲回到了家。父亲被释放后回到家里就哭了,我印象中几乎没看到他哭过,父亲哭的时候很可怕,我试着去理解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 父亲回到家不久,我们就从广播中得知犹太孩子不允许去公立学校读书了,所以第二天我也没去学校上学。我的老师人很好,把我在学校所有的课本和其他物品都送回了家。他说他很感激那天我没去上学,因为校长派人给他捎话说:“你的班上有全校唯一的一名犹太学生,请务必把他从学校清除出去。”由于那天我没去上学,我的老师可以告诉校长说我那天没在学校出现。 从我能记事起就觉得似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想着移民到其他地方生活。甚至在“水晶之夜”前,我父母就着手计划去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开始重新定做一些家具,大而沉重的书架上被按上了腿,零碎物件变少了,我们还买了许多衣服,连鞋底都是双层的,一旦鞋底磨损坏了,就可以直接撕下而用新的鞋底。 为了去巴勒斯坦定居,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水晶之夜”把巴勒斯坦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办公室烧毁了,相关的移民文件也被付之一炬。父亲那时恰巧被投进了监狱,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显得极为渺茫。后来,母亲联系上了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亲戚,计划去美国定居,我知道我们又要学习英语了。我的家庭教师每天都来我家教我英语,包括一些最简单的英语。她大约只有二十岁,也没什么经验。虽然不能去学校上学,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学校。 我们和辛辛那提的亲戚取得联系后,他们寄给我们一封担保书。但是,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不得不等待。有一天,我们家举办晚餐派对,其中一个人突然说:“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要去上海。”紧接着另一个人说:“我和你一起去。”我父亲说:“我也加入你们,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共有三个犹太家庭要前往上海,我哥哥和我是其中仅有的两个孩子。 离开欧洲整理物品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箱子里,它的尺寸大概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秘密警察会监督我们整理东西,金银物品早已根据其重量兑换成了现金,每个人只被允许携带两件银器,我们的箱子里装了八件银器。我还有一些铝制的玩具银币,这些“钱”当然都是一文不值的,我母亲准备将其整理打包,但是警察制止了她。母亲说:“你们看,这不过是些玩具钱罢了。”她最终说服了警察允许我们携带这些玩意儿。事后我对母亲说:“为什么你不索性让警察拿走这些东西?”事实上,我并不太在乎我自己的东西。警察们仔细地检查着我们放入箱子里的每一件物品。我父亲有一些有趣儿的玻璃杯,从外面看那杯子好像盛满了酒,可当你试图举杯一饮而尽时却发现什么也倒不出来,监督我们的警察对这些杯子很是着迷,我母亲便把杯子送给了他们。此后的监管也轻松了许多,我们打包整理物品的速度也快了许多,然而我父亲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他不肯乘此机会逃脱检查。 我们携带的衣服都是单独定制的,我叔叔经营着一家服装商店可以下单定做衣服,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穿着同一种材质的衣服。为了携带这么多衣服,我们还特意定制了一些箱子,母亲带了一件皮毛大衣,父亲带了显微镜和别的什么东西,遗憾的是许多物品都在上海卖掉了。 作为一个小孩,我对此次航行激动不已,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次大冒险。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要离开德国前往上海,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上海在哪儿,也不理解当时父母所承受的恐惧和压力,对他们即将面对的事情我都无从知晓,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父亲好好聊一聊,他离开我们实在太早了。 当我们最终要离开德国前往上海时,我父亲的一些非犹太好友也赶到我家向他道别,“老年犹太人之家”的楼上也挂出了欢送的横幅。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对父亲说:“在某些方面你比我们轻松多了,你至少可以在孩子们面前说出你想说的话。而我们却要在孩子们面前管好自己的嘴,小心谨慎地说话,因为孩子们可能会把我们送进监狱。”我被这番话惊呆了,当时我只有9岁。 亲朋好友向我们道别之后,我们乘坐火车离开了德国。到达意大利境内的勃伦纳山口时正值午夜时分。我睡得正香,但是火车上的每个人都必须下车接受海关的检查。我母亲对其中一位负责人说:“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留在车上?他睡着了。”“当然可以,但是我不敢保证你能在火车出发前回到车上。”负责人回答道。很显然,我不得不被从睡梦中叫醒。 德国人只允许我们携带少量的现金,当我们到达勃伦纳山口时才发现父亲所携带的现金远远超过了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只好赶忙给我叔叔打电报。车行至意大利热那亚港口时,我的姨妈早就到了热那亚为我们送行,当我们登上远赴上海的游轮时,大家都显得格外激动。 和那些乘坐意大利航船的难民们不一样,我们乘坐的是一艘荷兰轮船,在船上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在船上的膳宿花费了我们不少钱,船上的人还要记录下我们的每一笔开支,但他们好像胡乱写一通,诸如昨晚赌博输掉一百元,买香烟花掉一笔钱等等。荷兰船上有个规定,10岁以下的小孩不得和成年人一起用餐,所以我不得不和船上其他小孩一起吃饭,对此我十分忐忑,站在甲板上还能看见陆地时我就晕船了。 我父母觉得在我们前往上海的航行中或许能在新加坡、马尼拉,或是香港停留一会儿,但不幸的是我们下不了船,我们还得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换船才能最终抵达上海(那时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雅加达还叫巴达维亚)。我们在雅加达停留了一周左右,那里的荷兰犹太社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很不错的旅店,一位在军队工作的犹太医生款待了我们,他是一位陆军少校。我们简直享受到国王般的礼遇,就像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人一样。我们可以自己随意支配一辆汽车,当然还配有司机,那感觉真的棒极了。一周过后,我们踏上了驶往上海的航船。 ……
用户评价
‘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这个书名就如同一声来自遥远过去的呼唤,带着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重量,直接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历史和人性的好奇。 ‘艰苦岁月’,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个动荡的世界,那段充满离乱与苦难的时光,而 ‘难忘记忆’ 则像是黑夜中的星光,预示着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总有那些令人铭记的片段,它们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伤痛的,但都构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华犹太难民’,这个关键的定语,将我引向了一个相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历史角落,它激发了我对这段独特经历的探索欲望。 我好奇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中国的土地成为了犹太难民的庇护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些流亡的犹太人在中国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是充满了挑战,还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温情?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用最真实、最朴实的语言,为我展现那些被遗忘的细节,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个体故事,那些在异国他乡坚韧生存、努力生活的回忆,它们必将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理解人性的复杂与伟大,提供一份宝贵的资料。
评分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幅幅画面。 ‘艰苦岁月’ 像是沉甸甸的铅块,压在我心头,让我预感到其中充斥着泪水与汗水,充满了失去与不舍。 然而,紧随其后的 ‘难忘记忆’ 又像是一束微光,穿透阴霾,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这个副标题则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得以窥探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特定族群的生存轨迹。 我不由自主地去想象,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在战乱年代,怀揣着怎样的心情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他们是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的? 是孤立无援,还是得到了当地人的接纳与援助? 我尤其对 ‘难忘’ 这个词感到好奇,它意味着什么? 是那些刻骨铭心的苦难,还是那些超越苦难的温情? 是绝望中的一丝慰藉,还是黑暗中的一点星光? 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穿越时空的阻隔,去感受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生命故事,去体会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悲欢离合,去理解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守,又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留下属于他们的独特印记。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深深地吸引了我。 ‘艰苦岁月’ 几个字便勾勒出一段充满挑战的历史时期,而 ‘难忘记忆’ 又预示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珍贵的个人经历。 ‘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则清晰地指明了叙述的主体和背景。 我立刻联想到那个动荡的年代,二战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无数生命在战火中颠沛流离。 犹太民族作为备受迫害的群体,他们的逃亡之路充满了艰辛与不确定。而选择中国作为避难所,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选择。 我好奇他们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是得到了友善的帮助,还是面临了新的困境? 书名中所提到的 ‘难忘记忆’,想必记录的不仅是生存的挣扎,更是人性中的光辉,或是那些让他们铭心刻骨的瞬间。 我期待着能够通过这些回忆,深入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感受那些在绝境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光芒。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可能是一部关于勇气、韧性和希望的史诗,它将带领我走进一群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去倾听他们不曾被遗忘的故事。
评分书名 ‘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仿佛是一首低沉而悠扬的旋律,瞬间将我拉入了一个充满故事感的历史画卷。 ‘艰苦岁月’,无需赘言,便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重苦难,那是时代的烙印,是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 ‘难忘记忆’,则在苦难中注入了情感的温度,它暗示着这些记忆之所以被铭记,必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原因,或许是那些在绝境中闪烁的人性光辉,或许是那些难以磨灭的创伤,又或许是对生命顽强不息的赞歌。 ‘来华犹太难民’,这一信息瞬间提升了历史的维度,将故事的背景聚焦在中国,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想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是如何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风港的? 他们是如何抵达中国的? 在中国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是否有感人的故事,关于接纳与帮助,关于跨越国界的友谊? 这本书名所传递的信息,让我感觉它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客观陈述,更是一种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挖掘,是对那些被时间冲刷却依然鲜活的记忆的珍视。 我渴望通过这本书,去感受那些在极端困境下,人类所展现出的惊人韧性与生存智慧。
评分‘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这个书名本身就散发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 ‘艰苦岁月’ 几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尤其是对于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而言,那无疑是一段充满磨难与考验的时期。 ‘难忘记忆’ 则透露出本书的主旨,它不是简单地记录历史事件,而是侧重于个人的感受、情感和经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回顾。 ‘来华犹太难民’ 这个定语,更是将故事的发生地锁定在中国,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的偶然性。 我好奇的是,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中国的土地成为了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又是如何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避难者的? 书中收录的回忆,想必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有对过往苦难的追忆,有对失去家园的痛楚,或许还有在异国他乡遇到的陌生人的善意,以及重获新生的喜悦。 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这些第一手的回忆,去感受那段被历史洪流裹挟下的个人命运,去了解他们在中国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以及那些让他们至今难以忘怀的瞬间,这些瞬间或许平凡,却蕴含着不平凡的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