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汪曾祺,在自创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大师级作家。其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基础上修订,注重系统性及版本价值。
★由连续两届获得“中国*美的书”设计师张胜先生精心设计,典雅大气,装帧雅致温润,布面精装,尽显纯正文学趣味。
★编校者精益求精,耗费十年心血,参校作者手稿、手校本及各种文集,力求当代文学新善本。
内容简介
汪曾祺和沈从文一样,是那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他对白话文的贡献是****的,文字干净而传神。他的小说作品“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邂逅集》是汪曾祺的头本小说集,70年后首次重现。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成熟、*具代表性的作品。
《鸡鸭名家》《戴车匠》《落魄》这三篇都是取材于作者对故乡往事的回忆,其所写的人物,其叙事的方式,就连其用词造句,与作者几十年后所写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都是一脉相承。汪曾祺为什么写这些?他发表在《猎猎——寄珠湖》的散文道出了其中奥秘:“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所以他不睡觉,且不惜自己的言语,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话着故乡风物……”
汪曾祺后来把《邂逅集》中的《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作了一些修改”,《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现,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
本书编者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的基础上编选修订,尽可能保留了各种文集本身的趣味;每部文集各自独立,又具一定的系统性;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汪曾祺先生的读者,也具有相当大的版本价值。
作者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一九二〇年生。-九三九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为沈从文先生的及门弟子。约-九四〇年开始发表散文及小说。大学时期受阿索林及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影响,文字飘逸。以后备尝艰难辛苦,作品现实感渐强,也更致力于吸收中国文学的传统。毕业后曾做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的职员。一九四九年以后,做了多年文学期刊编辑。曾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京剧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蒲桥集》《晚翠文谈》《塔上随笔》《独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精彩书评
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境界。
——黄裳(著名散文,家藏书家)
汪曾祺的小说,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已。
——李陀(著名作家,理论家,评论家)
汪先生的好,是如今大多数中国作家身上没有的好。他那种夫子气,文士气,率性而真切,冲淡而平和,有大学而平易,阅人阅世深厚而待人待物随意。
——何立伟(著名作家)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
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
——孙郁(著名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
目录
复仇………………………………………………………………一老鲁……………………………………………………………一九
艺术家…………………………………………………………四八
戴车匠…………………………………………………………六五
落魄……………………………………………………………八四
囚犯…………………………………………………………一○六
鸡鸭名家……………………………………………………一二○
邂逅…………………………………………………………一六三
关于《邂逅集》
精彩书摘
大淖记事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见之于诗,这大概是第一次。他很能写出节令风物之美。,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垅,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直达邻县兴化。
大淖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往里去,临水,就是码头。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和兴化,隔日一班,单日开走,双日返回。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就卖船停业了。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
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二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的(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外皮染成深蓝紫色,极甜脆),卖风菱的(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壳极硬),卖山里红的,卖熟藕(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的。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他们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来时,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住上一阵,有的住得长一些,有的短一些,到生意做完,就走了。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了。到太阳落山,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
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这地方兴用锡器,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香炉、蜡台、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酒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嫁闺女时都要赔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因此,二十来个锡匠并不显多。
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一副锡匠担子,一头是风箱,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锡器是打出来的,不是铸出来的。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一般都是自己备料,——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拉动风箱,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就化了;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裱纸的一面朝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绳头留在砖外,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锡是软的,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也不那样吵人。粗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
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是个老锡匠,他说话没有人不听。老锡匠人很耿直,对其余的锡匠(不是他的晚辈就是他的徒弟)管教得很紧。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他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除了上市应活,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
老锡匠会打拳,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他屋里有好些白蜡杆,三节棍,没事便搬到外面场地上打对儿。老锡匠说:这是消遣,也可以防身,出门在外,会几手拳脚不吃亏。除此之外,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
老锡匠有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儿,在家大排行第十一,小名就叫个十一子,外人都只叫他小锡匠。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四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锡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
老锡匠经常告诫十一子,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有什么勾搭:“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三
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
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东乡、北乡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进哪家大户的廒仓,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沿运河外运。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逻、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单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担稻子一百五十斤,中途不歇肩。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一齐换肩。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每挑一担,领一根“筹子”,——尺半长,一寸宽的竹牌,上涂白漆,一头是红的。到傍晚凭筹领钱。
稻谷之外,什么都挑。砖瓦、石灰、竹子(挑竹子一头拖在地上,在砖铺的街面上擦得刷刷地响)、桐油(桐油很重,使扁担不行,得用木杠,两人抬一桶)……因此,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
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起初挑半担,用两个柳条笆斗。练上一二年,人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像大人一样的挣钱了。
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因此,这些顽童得到一个稍带侮辱性的称呼,叫做“筢草鬼子”。有时懒得费事,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时,他们早就没影儿了。锅腔子无处出烟,烟子就横溢出来,飘到大淖水面上,平铺开来,停留不散。这些人家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吃的都是脱粟的糙米。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采,为他们助兴。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
没出门子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年轻时也是挑夫,后来腿脚有了点毛病,就在码头上看看稻船,收收筹子。这老头儿老没正经,一把胡子了,还喜欢在媳妇们的胸前屁股上摸一把,拧一下。按辈份,他应当被这些媳妇称呼一声叔公,可是谁都管他叫“老骚胡子”。有一天,他又动手动脚的,几个媳妇一咬耳朵,一二三,一齐上手,眨眼之间叔公的裤子就挂在大树顶上了。有一回,叔公听见卖饺面一半馄饨一半面下在一起,当地叫做饺面。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梆走来,他又来劲了:“你们敢不敢到淖里洗个澡?——敢,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饺面!”——“真的?”——“真的!”——“好!”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喊叫:
“下面!”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四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父亲名叫黄海蛟,是黄海龙的堂弟(挑夫里姓黄的多)。原来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上高跳要提着气一口气窜上去,中途不能停留。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胡,他就走过去接过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两手一提,把两箩稻子倒在“窝积”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因为为人忠诚老实,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成亲。那年在车逻挑粮食,遇到一个姑娘向他问路。这姑娘留着长长的刘海,梳了一个“苏州俏”的发髻,还抹了一点胭脂,眼色张皇,神情焦急,她问路,可是连一个准地名都说不清,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黄海蛟和她攀谈了一会,这姑娘就表示愿意跟着他过。她叫莲子。——这地方丫头、使女多叫莲子。
莲子和黄海蛟过了一年,给他生了个女儿。七月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就取名叫做巧云。
莲子的手很巧,也勤快,只是爱穿件华丝葛的裤子,爱吃点瓜子零食,还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这和大淖的乡风不大一样。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焖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
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只是她留下的这块肉,黄海蛟实在是疼得不行。他不愿巧云在后娘的眼皮底下委委屈屈地生活,因此发心不再续娶。他就又当爹又当妈,和女儿巧云在一起过了十几年。他不愿巧云去挑扁担,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鱼网和打芦席。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睎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巧云十六了,该张罗着自己的事了。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他们都有这意思。这点意思黄海蛟知道了,巧云也知道。不然他们老到淖东头来回晃摇是干什么呢?但是巧云没怎么往心里去。
巧云十七岁,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她的父亲黄海蛟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起初以为不要紧,养养就好了。不想喝了好多药酒,贴了好多膏药,还不见效。她爹半瘫了,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有时下床,扶着一个剃头担子上用的高板凳,格登格登地走一截,平常就只好半躺下靠在一摞被窝上。他不能用自己的肩膀为女儿挣几件新衣裳,买两枝花,却只能由女儿用一双手养活自己了。还不到五十岁的男子汉,只能做一点老太婆做的事:绩了一捆又一捆的供女儿结网用的麻线。事情很清楚:巧云不会撇下她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一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谁愿意呢?这家的全部家产只有三间草屋(巧云和爹各住一间,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堂屋)。老大、老二、老三时不时走来走去,拿眼睛瞟着隔着一层鱼网或者坐在雪白的芦席上的一个苗条的身子。他们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
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老往淖东头跑,但是小锡匠还短不了要来。大娘、大婶、姑娘、媳妇有旧壶翻新,总喜欢叫小锡匠来;从大淖过深巷上大街也要经过这里,巧云家门前的柳阴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巧云要回家看看她的残废爹,问他想不想吃烟喝水,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织席很容易划破手,压扁的芦苇薄片,刀一样地锋快),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巧云从十一子口里知道他家里的事:他是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有一个老娘,守寡多年了。他娘在家给人家做针线,眼睛越来越不好,他很担心她有一天会瞎……
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精装书的装帧设计简直让人爱不释手,翻开扉页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那种老派匠人对细节的执着。布面材质的触感温润而有质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覆膜精装,它散发出一种沉静的书卷气,让人忍不住想多摩挲几下。书脊处的烫金字体虽不张扬,却在光线下熠熠生辉,透露出一种低调的奢华。装帧的厚重感也恰到好处,捧在手里有分量,但阅读时又不会感到负担。尤其是内页的纸张选择,那种略带米黄色的纯木浆纸,墨色印染得非常均匀清晰,字迹边缘锐利,读起来眼睛非常舒服,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也不会有视觉疲劳。装帧的用心程度,完全是对文字本身的尊重,它不仅仅是一个容器,更像是一件经过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让人在每一次翻阅时,都能体验到阅读实体书的纯粹乐趣。
评分我最近迷上了一种阅读体验,就是那种能让人瞬间穿越时空的文字。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尤其是在描摹那些旧日场景时,有着一种不动声色的魔力。它没有那种刻意煽情的笔触,却能在不经意间勾勒出生活的原色——那种烟火气十足、带着时间沉淀的味道。比如对一个寻常市井小店的描述,你能清晰地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油盐酱醋的味道,仿佛身临其境地坐在那张有些年头的木桌旁,听着周围人带着地方口音的闲谈。这种文字的“在场感”非常强,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审视,而是融入其中的温情。读完一段,常常会陷入长久的沉思,感叹生活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叙事,而作者恰恰是那个善于捕捉这些瞬间的洞察者。它让我想起了很多已经消逝的场景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温柔的回溯,而非僵硬的怀旧。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叙事节奏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从容。在这个信息爆炸、追求效率的时代,阅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恨不得每一页都有惊人的转折或爆炸性的信息。但这部作品却像是在缓缓行走,它不急于推进情节,而是把大量的篇幅用来精雕细琢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初读时可能会觉得有些缓慢,但一旦适应了这种韵律,就会发现这种“慢”恰恰是它最宝贵的地方。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匿于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碎片之中:一杯茶的温度,窗外光线的变化,一次不经意的眼神交汇。它需要读者投入足够的心神,像品尝一道需要细细咀嚼的佳肴,才能品出其中层次丰富的滋味。这种对时间的尊重,也是对文字本身的尊重,非常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里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疏离感”,但这种疏离并非冷漠,而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美学。作者仿佛站在一个既熟悉又略微抽离的角度,审视着周遭的人与事,使得情感的表达非常克制和内敛。你很难找到大段的、直白的情感宣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包裹在精炼的、近乎散文诗的句式之中。这种表达方式,反而让情感更有穿透力,因为它把解释和解读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读者需要自己去填补那些没有明说出来的情绪张力,这种“参与感”让阅读体验变得极其个人化和深刻。它不直接喂给你答案,而是引导你去探索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些情感主题的共鸣,非常考验读者的悟性和细心。
评分我特别欣赏这本书在描绘人物时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精准”。书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不是通过复杂的心理独白来塑造的,而是通过他们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被定格下来。比如,一个人如何对待他的旧物,他走路时的步伐,他在等待时的眼神,这些微小的侧面描写,却构建出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人格侧影。这些人物,即便在很短的篇幅内出现,也仿佛在我们身边真实存在过,有着自己的呼吸和轨迹,绝非脸谱化的符号。这种捕捉生活本质的能力,需要极高的观察力和艺术提炼力,让读者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那些人物的面孔和他们的生命痕迹,这种鲜活感是许多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
评分好书好书买了好多好多
评分《邂逅集》是汪曾祺的头本小说集,70年后首次重现。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中*成熟、*具代表性的作品。
评分★在汪曾祺先生自编文集基础上修订,注重系统性及版本价值。
评分印刷精美,校对仔细,值得收藏。
评分★由连续两届获得“中国*美的书”设计师张胜先生精心设计,典雅大气,装帧雅致温润,布面精装,尽显纯正文学趣味。
评分非常好的汪曾祺集子!
评分管家琪奇幻童话系列:思考的小鱼+莲雾国的小女巫+小豆芽的生命宝盒+骨头博士找骨头(套装共4册) [7-10岁]
评分汪曾祺的十本,印刷纸质装帧什么的都不错,做活动买下来也很划算,推荐。
评分河南文艺出的汪曾祺集是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集子了,封面典雅朴素,文章也耐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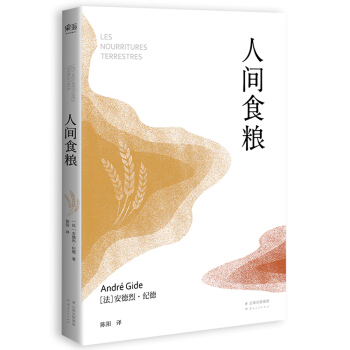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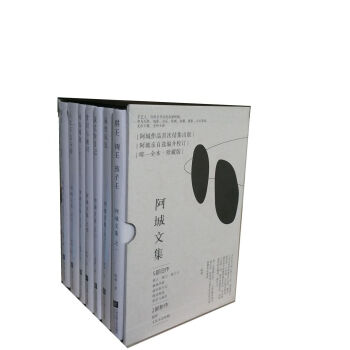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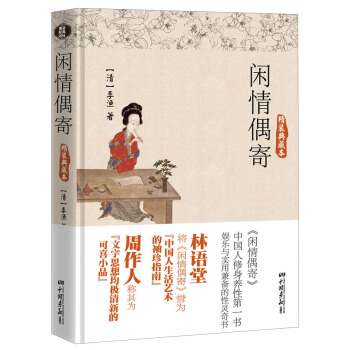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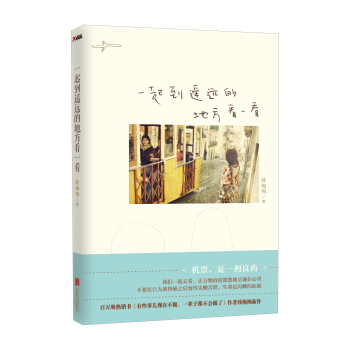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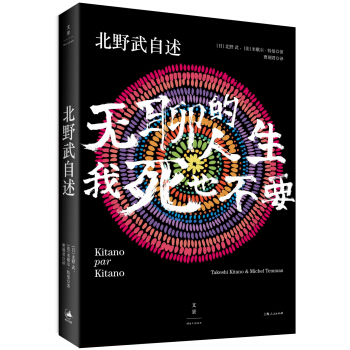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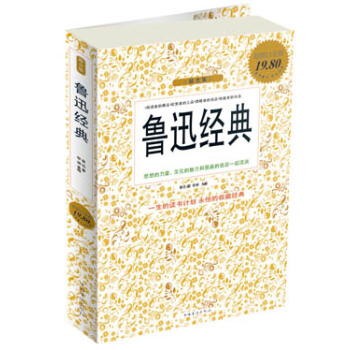
![毛姆文集:观点 [Points of Vie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6418/554ab85cN959691d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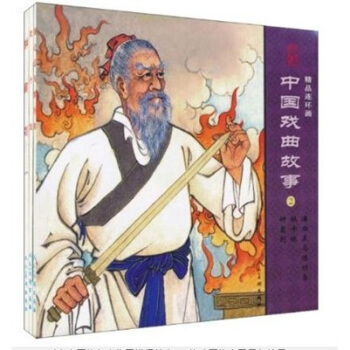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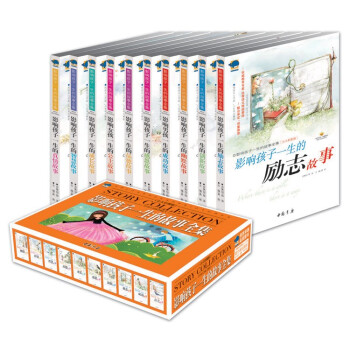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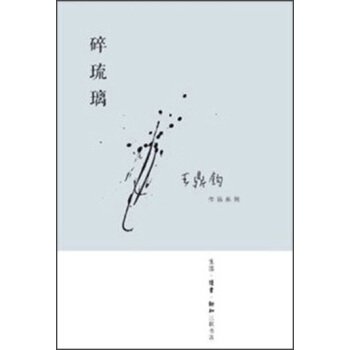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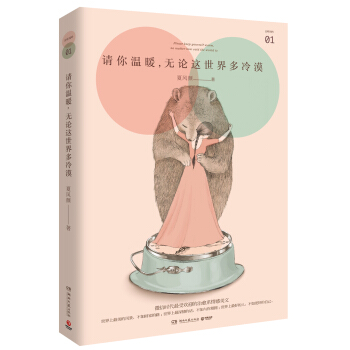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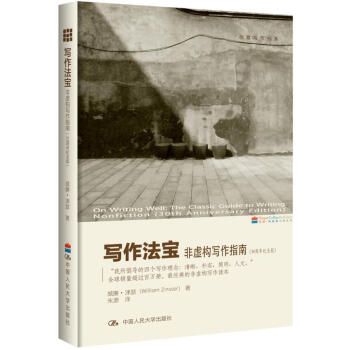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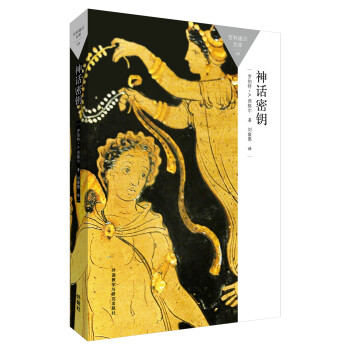
![年糕的故事(中英对照)/中国民俗故事 [3-6岁] [The Story of New Year Cak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59335/5518ab15Ncc8ed06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