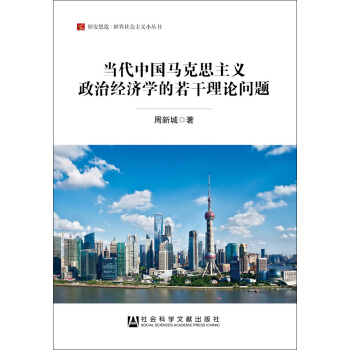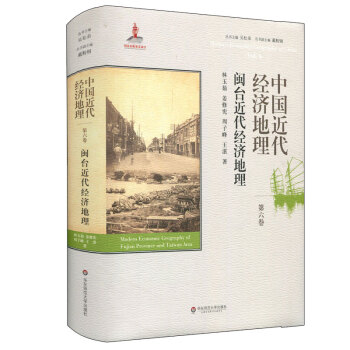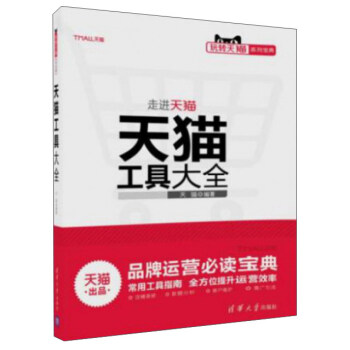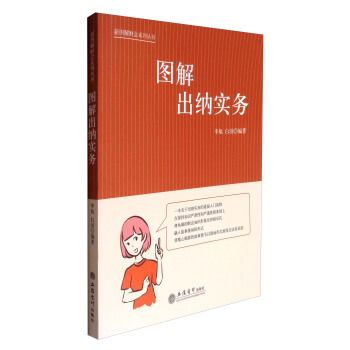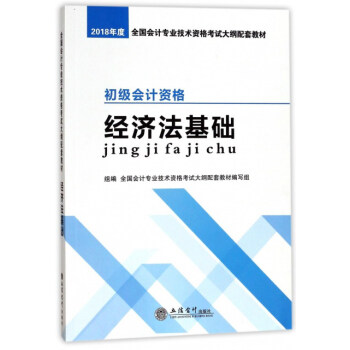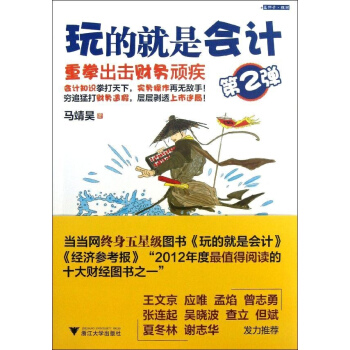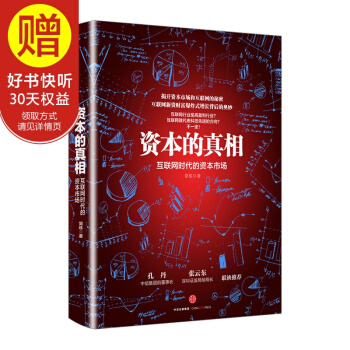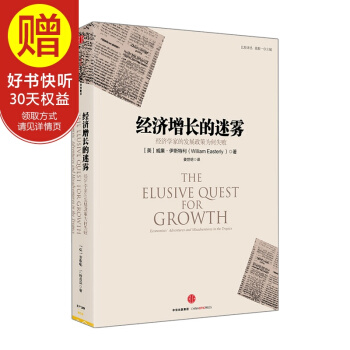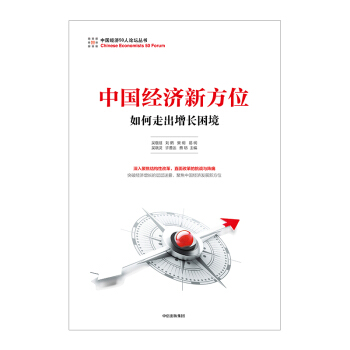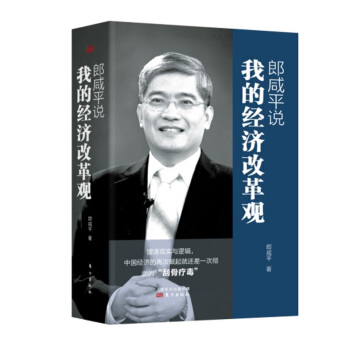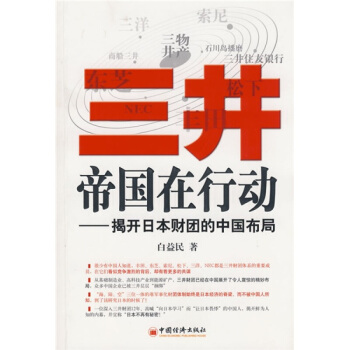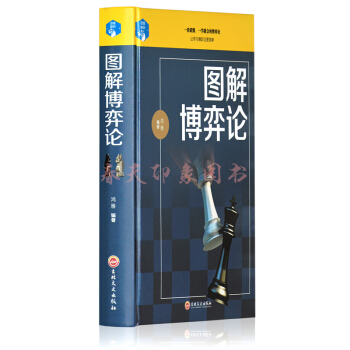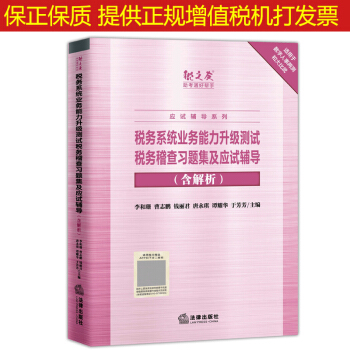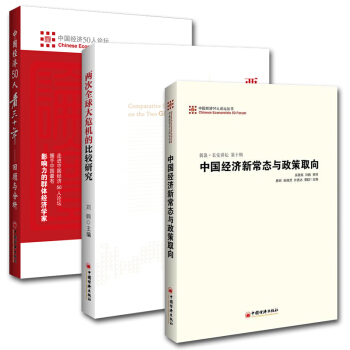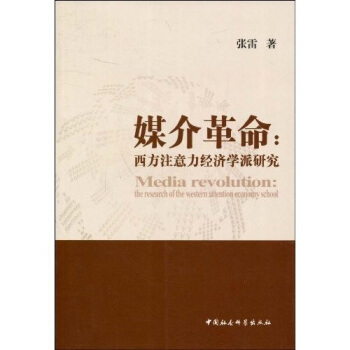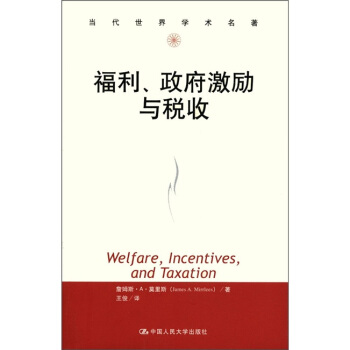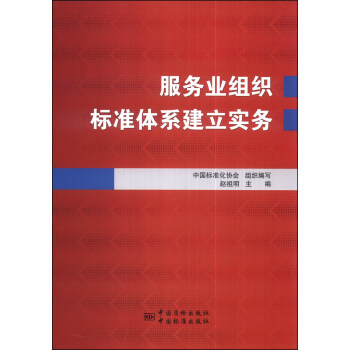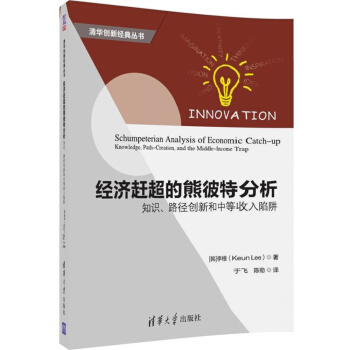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当前,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各国纷纷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并将其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于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的伟大战略,由此掀起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热潮。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继续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创新的理论工作者,应积极贡献对创新的理论洞察与政策建议。
国际上,创新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之后逐步为各国经济、管理和政策研究者所重视。北美和欧洲国家拥有一批杰出的创新理论研究者,形成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美国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及工学院为代表,在创新管理学、创新经济学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欧洲以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等为代表,在创新经济学理论和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亚洲,韩国学者率先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追赶方面取得了研究优势,日本学者则在知识创新、精益创新等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印度学者在创新方面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他们先后提出了原生态创新、朴素式创新、反向创新等新的创新理念,在创新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目录
第一部分概述与展望
第1章引言
1.1驱动本研究的问题: 如何维持赶超势头
1.2中等收入陷阱和持续赶超
1.3本书的论点: 专注于短周期技术
第2章知识是经济赶超的关键力量
2.1新熊彼特主义中有关经济赶超的观点
2.2知识和经济赶超: 概述关键因素
2.3测量赶超和数据
第二部分知识与经济赶超: 三个层面的实证研究
第3章知识与国家层面的赶超
3.1引言
3.2从国家创新体系到经济增长
3.3测量国家创新体系和特定的假设
3.4赶超型经济增长和未赶超型经济增长: 回归结果
3.5小结
第4章知识与行业层面的赶超: 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比较
ⅩⅧ
4.1引言
4.2理论框架和假设
4.3技术赶超的差异: 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
4.4模型的结构和结果
4.5总结
第5章知识与企业层面的赶超: 韩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比较
5.1简介
5.2理论框架和假设
5.3测量和数据
5.4知识和企业层面的绩效
5.5总结
第三部分理论构建: 如何逃脱增长的陷阱
第6章构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实现经济赶超的理论
6.1简介
6.2总结本书第二部分的发现
6.3专注于短周期技术以实现持续赶超
6.4技术转折点以及高端、中端、低端的发展道路
6.5从以贸易为主的专业化到技术专业化
6.6迂回、模仿和直接复制
第7章如何建立技术能力以进入短周期的技术领域
7.1简介
ⅩⅨ
7.2学习过程和阶段的概述
7.3基于许可/转让/ FDI的学习以建立吸收能力
7.4多样化的学习设计能力
7.5通过跨越学习: 韩国的移动电话和数字电视
7.6如何迁移到短周期技术领域: 一个总结
第8章中国和印度的赶超
8.1简介
8.2印度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制造业的赶超
8.3作为短周期技术的印度IT服务产业
8.4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短周期技术上的努力
8.5中国和印度的技术拐点
第四部分技术拐点理论和结论
第9章技术拐点理论的提出
9.1简介
9.2一个单变量理论?
9.3其他经济体的拐点
9.4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和其他替代模型
9.5遗留的问题
第10章总结和结束语
10.1总结
10.2本书的贡献和局限
附录表格
注释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对于韩国企业,资本一劳动比率是由总有形资产减去那些在建投资后与雇员人数的比值来衡量的,而对于美国企业,资本-劳动比率是物业、厂房、设备的价值除以员工人数。对于韩国企业,投资比例或增长潜力是当期(1年)增加的总有形资产的价值除以当年年初或者前1年年末总有形资产值。对于美国公司,投资比例是在某一年的物业、厂房和设备的价值变化除以该年年初的物业、厂房和设备的总价值。对于产业部门的虚拟变量,韩国企业用3位数KSIC(韩国标准产业分类)代码,美国公司使用两位数的SIC代码。
接下来,我们最感兴趣的变量包括技术的周期时间、原创性、知识库的多元化(即每个企业在多少个不同技术类别中拥有专利)和自引率。除了这些主要变量,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基本的变量,如各公司持有的专利数量(即每个企业i在第t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及通过平均影响因子测量的专利质量(即先计算某专利被引用的次数,然后将该次数与同一专利类别的其他专利被引用的次数做对比,并且用该公司在不同专利类别的专利分布来加权计算)。
……
前言/序言
这本书的写作起源于我受到的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这项教育部的资助仅限于“明星”学者,要求受资助的学者作为独立作者在为期五年内撰写一本专著。在我得到这项任务之前,我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主要是集中精力写期刊论文。虽然我之前出版过我的博士论文,但我一直觉得写好期刊论文比写书更重要。所以不用说,如果没有这项资助,我不会想到写一本书,这本书也就不会存在了。
不过,开始写书后我很快意识到了我之前想法的错误。编写这本个人专著,使我有机会将我分散在期刊上的想法综合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韩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产业政策”的结果。在经济赶超阶段,韩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而现在韩国政府的重心放在了促进学术发展上。
虽然本书有以上的写作背景,以及其重点是关于经济赶超的讨论,但颇具讽刺的是,书中却很少讨论产业政策本身。我在书中避开产业政策的原因是,不少学者如Ha�睯oon Chang(1994)和Alice Amsden(1989)已经讨论过东亚的产业政策。通过采用熊彼特的创新方法体系,本书侧重于从不同国家或世界部分地区的不同赶超经验中总结出一个更一般化的理论。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更成功这个重要的问题时,这本书提出了几种关键的创新体系。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技术的周期时间。技术的周期时间是指一项技术出现改变或被淘汰的速度,以及替代的新技术出现的速度和频率。本书表明,成功的经济体和企业往往专注于(或逐步迁入)基于短周期技术的行业。
技术后来者之所以能够进入这类技术领域并成为专家,是因为在短周期技术的行业现存的技术领先者的统治地位很可能被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所打乱,而且在短周期技术行业后来者也不必过于依赖那些受领先者控制的已有的技术。新的机遇带来了新的发展前景,而对现有技术更低的依赖可能会加快定位知识创造机制。这个特性也意味着更低的进入门槛、更大的利润可能性,而且因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冲突会较少,这也意味着需要较少的特许权使用费,甚至有可能产生先发/快发优势和产品差异化效应。作为一个类比,Jones和Weinberg (2001)对自然科学中“年龄—成就”关系的研究表明,青年科学家(类似于试图实行赶超的技术后来者)在他们年轻时往往容易在抽象/演绎性知识创造上取得更大的贡献,而在需要以积累知识为基础的归纳性知识创造上,则不容易实现对年长科学家的“赶超”,这是因为归纳性知识过时的速度相对缓慢得多。
本书主要使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和产业作为成功实现赶超的实例,这也留给我们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是否已经在有意识地专注于短周期技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政策制定者实际上经常会问自己,“下一步是什么?”他们会敏锐地观察并推测哪些行业和商业机会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潜力,并仔细考虑如何才能进入这些新兴行业。因此可以说,虽然政策制定者没有特别计划按照短周期技术理论来实践,但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总是在追求短周期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技术往往是对现有技术的依赖程度最低。
本书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学者们传统推荐的策略并不一样。我们认同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应该专注于以贸易为主的专业化这一传统提法,然后,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中等收入国家如何实现赶超的专业化条件。我们建议中等收入国家专注于最少依赖现有技术的技术领域,以及那些能提供最大发展机会的新技术领域。如此一来,我们的发现便补充了林毅夫的经济发展理论。林毅夫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引进那些对技术领先者而言已经成熟、而在本国尚未发展的产业。而本书推荐技术后发国选择优先进入那些更短技术周期的领域。我们认为,当技术后发国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后,它便可以进入一个对后来者和领先者都算是新兴技术的领域。中国已经在若干个行业中开始了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因此,这本书独特的政策建议是,持续的工业赶超不仅需要进入成熟的产业,同时也应该努力进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新兴产业的领域。
这本书也可以和Acemoglu和Robinson (2012)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做一个对比。首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没有解释一个国家如何走向更加包容性的制度,这也是比尔·盖茨在该书的书评中所指出的。此外,我观察到,包容性制度、限制攫取的制度可能对低收入国家和全球化之前的前现代化经济体很重要,而当代中等收入国家的失败并不主要由于攫取性制度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由于其较弱的创新体系造成的,因为这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本书还提供了一个评估方法,以判断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正在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我们将这个拐点称为技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专利组合来测量,以判断该国的技术周期时间是否达到峰值,并转向更短的周期时间的技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了这个转折点,中国大陆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印度看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高峰,但其下降趋势尚不十分明显,所以我们还不能判定印度是否已经通过了它的技术转折点。
本书将经济赶超定义为一个企业或国家缩短与领先的企业或国家的技术距离的过程。经济赶超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Gerschenkron (1962),以及Abramowitz(1986)的著名的文章“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这些前人的研究普及了赶超的概念,并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标准词汇之一。不过,上述文章分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表现,而本书则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后来者。本书基于在创新体系上的单一的统一框架,并在三个层面(即企业、产业和国家)对赶超进行了跨国的定量分析。在这一多层次分析中,我们确定了一组实现赶超的决定因素,并使用专利数据来衡量这些因素,同时将技术的周期(短周期)作为转换变量,以及将知识的本地化创造和技术的多样化作为终点变量。
本书提供了量化创新系统和熊彼特经济学的一套全新而精致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用于对国家、产业、企业进行计量分析。这些方法除了对研究人员有帮助,还对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用的见解。特别是,第7章指出了如何可以建立经济赶超所需的技术能力,并强调了政府角色、公共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技术能力建设是实现追赶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
本书的写作离不开新熊彼特主义或演化经济学领域中前人的奠基性研究,尤其是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与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共同撰写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在这一研究领域,我其实是一个“后来者”。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研读这本书——在它首次发表整整10年之后。我的知性之旅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进化”到研究后发经济体的创新。有趣的是,这两个领域都可以被归入“赶超经济”这一主题之下。虽然前者强调对经济体制的追赶,但两者都缩小技术后进者和技术领先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本书认为,后进者无法通过直接效仿或复制领先经济体的经济行为而迎头赶上,要实现赶超,后进者需要走一条与领先者完全不同的路。
在读过尼尔森的著作之后又过了10年,我们才在北京举行的2004年Globelics会议上相遇。会议结束后,我成了尼尔森发起的研究赶超问题的团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成为我的另一位领路人本特�舶⒖恕ぢ椎峦叨�(Bengt�睞ke Lundvall)创立的Globelics会议的经常参与者。研究赶超问题的团队于2005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第一次会议,这一会议启发了多部研究赶超的书的写作,例如产业部门创新体系与赶超(Malerba和Nelson,2012),知识产权(IPR)与赶超(Odagiri等,2010),以及创新型企业与赶超(Amann和Cantwell,2012)。这个会议也催生了研究大学—产业的联系与赶超的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在上述4本书中,我都贡献了其中一章。另外,我也从Globelics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的年会中受益匪浅。本书的很多章节曾经在这些会议中陈述过,并汲取了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的很多建议与意见,如约翰·坎特维尔(John Cantwell),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和弗兰科·麦乐博(Franco Malerba)。我的研究能
得到这些学者直接和间接的反馈,使我感觉十分荣幸。
其他一些学者也热心地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很多建议。具体而言,尼尔森介绍给我大量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文献,并帮助我修订了关于企业层面分析的那一章。他也将图什曼(Tushman)的作品介绍给我,图什曼的研究也表明能力—摧毁的非连续性也可能导致新进入者的崛起。另外,作为技术赶超主题的开拓者之一,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也读过本书的好几次修订稿,并对本书的整体结构修订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使我重新评估这本书的主要概念,我在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中从他的鼓励和反馈中受益良多。
亚当·泽麦(Adam Szirmai)建议我将技术转折点理论进行一般化推广,基于这一建议,我将其扩充为单独的一章(第9章)。最近我发现,战后的日本相比很多欧洲国家而言更加关注于短周期技术,但那时将此内容添加到书中已经为时过晚。Kangkook Lee和Kyooho Park也对本书的早期版本补充了很多意见。我尤其要感谢Kyooho Park,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合作时发现了技术周期时间的重要性。
本书进行的计量分析是基于美国的专利数据库。这个专利数据库是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课题组编制的,特别是Bronwyn Hall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在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的一次会议中,Bronwyn Hall也对本书第4章提出了她的意见。书中使用的一些变量是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的,当然我的研究团队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也在调用时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我想感谢我的学生所做的管理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的工作,特别是Junki Park、Buru Im、Raeyoon Kang和Hochul Shin。
这本书不少章节的早期版本曾提交各种学术会议,所以其最终成型也离不开当时会议参与者的反馈。我要感谢Eduardo Albuquerque、Hyunbai Chun、Susan Cozzens、John Foster、Xudong Gao、Shulin Gu、Mei�睠hih Hu、K. J. Joseph、Taehyun Jung、Byung�瞃eon Kim、Chulhee Lee、Xibao Li、Maureen McKelvey、Justin Lin、Xielin Liu、Mehdi Majidpour、Mammo Muchi、Rajeshwari S. Raina、Sadao Nagaoka、Barry Naughton、Hiro Odagiri、Walter Park、Rajah Rasiah、Bhaven Samphat、Elias Sanidas、Daniel Schiller、Jung C. Shin、Lakhwinder Singh、Joseph Stiglitz、Bart Verspagen、Yi Wang、Brian Wright、Guisheng Wu、Xiaobo Wu、Yao Yang、Gabriel Yoguel以及Jiang Yu。特别值得感谢的会议包括在布里斯班举行的2012熊彼特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会议,多次Globelics会议(北京、吉隆坡、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及达喀尔),国际能源署(IEA)和世界银行的New Thinking in Industrial Policy会议,在东京举办的EPIP会议,Conference on Science、Technology、and Innovation Policy(亚特兰大)、Cicalics Workshops(杭州和北京)、Africalics Academy(肯尼亚的内罗毕)、亚太地区创新研讨会(Asia�睵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s)(新加坡和首尔)、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新罕布什尔州)和EBES Conference(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也受惠于在下列学校(机构)进行的研讨会: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哥德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UNU�睲ERIT、美利坚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the Amirkabi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黑兰)、旁遮普大学(Punjabi University)、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北京大学CCER和经济学院、UFMG(贝洛奥里藏特)、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汉诺威大学(Hanover University)、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NISTADS(新德里)。
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Chris Harrison、Claire Poole和 Tom O’Reilly,他们付出的宝贵工作才使本书能够面世。几位编辑也对本书的英文做了很多润色,其中我特别感谢阿姆里特·考尔(Amrit Kaur)的服务。
最后我要感谢我可爱的妻子素妍(So�瞴eon),她总在为我的工作不断祈祷。
李根(Keun Lee)
写于首尔冠岳山
2013年春
用户评价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令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忧虑的议题。这本书将熊彼特的分析与这个现实困境联系起来,无疑增加了其现实价值。我非常想了解,熊彼特式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他对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以及制度变革的强调,能否为我们提供理解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全新视角。书中是否会分析,为什么一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而另一些国家则能够成功跨越这一阶段? 我特别关注书中对于“陷阱”的成因的剖析,是结构性问题,还是创新活力不足,抑或是制度性障碍?熊彼特理论中的哪些要素,例如企业家创新动力减弱、新技术的应用受阻、或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可能导致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也希望书中能提供一些克服这一挑战的可能路径,例如通过深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并基于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来评估这些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评分这本书名着实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尤其是在当下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新兴经济体纷纷寻求突破的背景下。一直以来,我对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论述,在理解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洞察力印象深刻。而这本书将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与“经济赶超”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相结合,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切入点。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运用熊彼特的经济学思想来解释不同国家在追赶发达经济体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和机遇的。 “知识”作为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期待书中能深入探讨知识在经济赶超中的动态作用,例如,知识的获取、吸收、创新以及传播是如何驱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的。是技术模仿和引进占主导地位,还是自主研发和原创性知识的创造更为关键?书中是否会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并分析它们在赶超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我很想看看作者如何将熊彼特的“知识”概念与当今全球知识经济的现实联系起来,是否会涉及到教育体系、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评分“路径创新”这个词组非常引人注目,它似乎暗示了一种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思路。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往往侧重于路径依赖,而“路径创新”则意味着要打破既有的束缚,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界定和阐述“路径创新”在经济赶超中的具体含义。它是否指的是在产业选择、技术路径、制度设计等方面寻找全新的解决方案?书中是否会举例说明,有哪些国家或地区通过成功的路径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克服了发展中的瓶颈?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让我能更直观地理解“路径创新”的实践意义,以及它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更深一层,我想知道“路径创新”是否与“颠覆性创新”有所关联,熊彼特本人就强调了后者对经济格局的重塑作用。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新兴经济体如何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下,通过“路径创新”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实现从追赶者向引领者的转变。我对作者如何构建这种“创新”的分析框架,以及它如何能够指导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营者,感到十分期待。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弧线:从“经济赶超”的宏大目标,到熊彼特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再到“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关键议题的聚焦。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几个看似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概念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 coherent 的分析框架。 我期待看到书中能够提供严谨的理论论证,同时也包含丰富的事实和数据支持。比如,是否会选取一些典型的国家案例,通过熊彼特式的分析来解读它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它们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以及在知识创新和路径选择方面是如何实践的。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熊彼特宏观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微观的企业行为和宏观的产业演变,最终来解释“经济赶超”这一复杂现象的。这本书是否会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或者更侧重于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
评分读到这个书名,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核心论点。我非常好奇,这本书如何将熊彼特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创造性破坏者”角色的理解,应用于解释“经济赶超”的动态过程。是不是书中会强调,企业家在发现新机遇、引入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和新市场方面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一个国家努力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 我期待书中能深入探讨,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制度能够激发和培育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经济赶超。比如,是否会涉及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健全等方面?熊彼特理论中关于“创新”的五种类型(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是否会在书中得到具体的应用和阐释,用来分析不同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创新策略?我想看到的是,作者如何通过熊彼特的理论,为理解和促进经济赶超提供深刻的洞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在世纪之交的发展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30790/57e1efffN6d224ac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