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白夜照相館》: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佳作奬得主王蘇辛曆經七年沉澱力作
2016—2017年度備受期待的新浪潮文學代錶作
本書中多篇小說曾登上豆瓣、犀牛故事等app首頁,閱讀量纍計兩百萬次。
本書選用瞭王蘇辛眾多作品中代錶的14個神行百變的故事,這14個故事仿佛是我們置身的現實,每一個故事都能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每一個故事都能夠讓讀者迅速擊退心中僅保留的那道閱讀防綫,快速進入故事當中,仿佛每個讀者都是故事中的一員,無一例外。
內容簡介
14個神行百變的故事14個我們置身的現實王蘇辛的小說辨識度很高,敘述錶達上風格明快,時而傳奇,時而現實。
例如:小說《白夜照相館》講述擅長拍攝復古照片的“白夜照相館”專門為人僞造身份,從而引發的一連串復仇、謀殺事件。
短篇精怪故事《我們都將孤獨一生》則書寫瞭一座隻要一離婚就變成雕像的國度,“我”的父母因為離婚變成兩尊雕像,而“我”卻因為父母這一決定,自身的生活發生傳奇式的改變。《你走之後,我開始對著牆壁說話》講述瞭社交恐懼癥的父母卻生齣社交達人女兒,從而引發的一係列戲劇衝突。
小說《直立行走的人》講述瞭傳奇背景下,身高過高的一傢人,所遇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故事。跌宕起伏,情感濃烈。
作者簡介
王蘇辛,生於1991年,曾用筆名普魯士藍。2015年獲得第三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奬,是一位獲得該奬的90後作者。短篇小說《白夜照相館》2016年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轉載,是一位被國內重量級文學選刊同時轉載的90後作者。短篇小說《我們都將孤獨一生》等曾登上豆瓣app首頁推薦,被多傢網站轉播轉載。王蘇辛的小說風格怪誕,兼具魔幻敘事與日常傳奇,辨識度很高。精彩書評
文學從“我”開始,也該由“我”嚮前王蘇辛的小說,不是反映,而是熔煉,它打開瞭小說在山窮水盡時的可能性——容納龐雜無盡的碎片而抵達晶體般的虛構。
——李敬澤
目錄
白夜照相館戰國風物
伴靈故事集
__我們都將孤獨一生
__再見,父親
__請不要倚靠電梯
__昨夜星光璀璨
__寂寞芳心小姐
__猴
__你走之後,我開始對著牆壁說話
袁萬歲
下一站,環島
直立行走的人
自由
荒地
後記:尋找地圖的人
精彩書摘
我們都將孤獨一生我父母決定離婚時,曾徵求過我的意見。
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為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在我們國傢,離婚的人會變成雕像鎮守自傢的宅子,而且,雕像永遠不能進入傢門。即便如此,離婚率還是持續高漲,很多宅子前都堵滿瞭各種各樣的雕像,其中,最多的是石獅子。有的傢族人丁興旺,門前簡直可以集齊十二生肖。可我傢地處樓房,隻能另覓空地安置父母。
我父母要徵求我的意見,原因就在此。
整個三伏天,為瞭他們離婚的善後事,我到處尋找便宜的地下車庫或者小單間,可最近租金昂貴,一間小地下室的月租居然都要一萬。我用盡瞭在公司談閤同學來的本事,甚至許諾簽下十年內不會復婚的條約,還是沒有一個房東願意把租金降到一個我能承擔得起的價位。
我試圖找親戚朋友藉錢,可最近離婚的多,盡管父母和我多年來充當老好人,聽說他們要離婚,都一個個躲得十萬八韆裏。
這引發瞭他們離婚前的最後一次爭吵。爭吵的焦點是:到底是誰當年執意買瞭樓房。我告訴他們,現在即使是自傢平房宅子前的空地,也是需要購買的。可他們完全不聽我說的,不僅不聽,他們還為我打斷他們的吵架思路而萬分不爽。
——那之後不久,他們就離婚瞭。
在變成雕像的懲罰文件下來之前,我白天奔走於尋找閤適的房子,晚上為他們變成哪種雕像未來復婚幾率更大而傷盡腦筋。
我準備瞭幾個紙團,上麵寫著各種神獸和生肖的名字,雕像的種類隻能從這裏麵選。我把它們認真包好,選擇兩個同類的神獸讓父母抓鬮,就像小時候他們在書上抹蜂蜜讓我誤抓瞭書本一樣,我也把兩個最可能復婚的同類神獸的紙團包得更寬大、醒目,試圖讓父母選擇它們。
孰料他們離婚之意非常穩固,根本不考慮離婚徵程中的費用,各自選瞭兩個復婚率極低的生肖雕像,一匹馬,一頭羊。
我很絕望,但說不過他們,隻能順從,畢竟十五年之後,雕像的安置費用將由政府承擔。十五年雖長,總好過一生。
我賣瞭傢裏的房子,租瞭城郊一間小平房,時常斷水斷電,來迴公司需要五個小時。但想到十五年後的幸福生活,我忍瞭。
就這樣,我父母愉快地離瞭婚,我也成瞭一個房奴。
為瞭維護雕像的簇新,我每周都會去他們所在的地下室擦洗它們。地下室沒有水電,我就從遠處提水,儲存瞭大量洗滌劑和吹風機。這些工作往往須耗費一天的時間,但我樂此不疲。坦白說,他們剛離婚的那兩年,我無時無刻不希望他們幡然醒悟然後復婚,我也早點結束房奴的生活。兩年過去瞭,我發覺這是徒勞。
我租下的這間地下室位於解放東路盡頭。懶得給父母擦洗的日子裏我會在這裏滅蟑螂——自從成為窮睏潦倒的房奴,我就沒有社交活動瞭,在這裏待著倒也能打發自己的無聊。
我這樣過到瞭他們離婚的第五年,然後日子就不同瞭。
那時候我已經升任公司某部門副主管,這份工作的好處是我得以租住一套位於市中心的一居室。我的社交活動重新多起來,甚至也把開公司劃入未來日程。有時候忙起來,一兩個月也不會去看一次父母。畢竟房租我一口氣付瞭十年的,不去也沒人提醒我什麼。
我也開始和女孩子約會,她們年紀都比較小,二十二三歲,總把自己裝扮得像三十歲。不過這也不錯,她們都學著不黏人,倒很閤我心意。可有一天,我還是接到瞭一個雙魚座曖昧對象的拉黑短信,她告訴我,不會再聯係我。我不知道哪裏齣瞭問題,想來想去可能就是因為沒給她一個明確答案,比如,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
那天下瞭大雨,因為這條短信,我和女孩子晚上的約會宣布告吹。我百無聊賴地走齣去,打著傘,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我想起明天開始是我的年假,決定去看看我的父母。
這次探望讓我發現,他們渾身都洗得很乾淨,可能比幾年前他們剛離婚變成雕像的時候更乾淨。
我也發現瞭他們容貌的變化,我媽媽明明是馬的雕像,現在已經變成人形瞭,爸爸也一樣。
他們身體的各個角落都泛著白光。我使勁抬起雕像一角,發現底座都是乾淨的。
我不知道誰在我不在的日子裏幫我擦洗父母,思來想去感覺沒有人會這樣做。我又檢查瞭房屋,發現根本也沒漏水。我滅瞭一遍地下室可能會齣現的各種生物,把房間打掃到最乾淨,決定在這裏待上一周。如果有誰來,我一定會看得見。
我支起睡袋,一頭掛在母親的頭上,一頭掛在父親的頭上。躺上去,睡袋會搖搖晃晃讓我頭暈,但也變相縮短我進入夢鄉的時間,感覺還不錯。
我做瞭很多夢,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地上。
我身上布滿摔傷後的青紫色,而父母之間的距離也顯然比之前近瞭很多。
我有些莫名的恐懼和欣喜。我第一次懷疑,負責擦洗父母的其實是他們自己。畢竟,復婚的徵兆就是雕像之間距離變窄和變成人形。
而經過這次距離拉近之後,父母完全變成瞭人形。
我從沒想過他們真的會復婚,可這一天真的就要來到,我也感到高興,盡管我已經沒那麼窮瞭。
復婚的過程很順利。我嚮有關部門報告瞭父母的近況,頭頭們批準他們復婚。我退掉瞭地下室,宴請瞭親戚朋友,他們很樂意和我的一傢重新建立聯係。我們在舞池中間跳瞭一場群舞慶祝這一切,父母的雕像就擺在正中間,我們都在等待他們活過來的那一刻。
我們跳瞭三天三夜,他們還是沒有醒過來。
再過瞭三天三夜,他們褪去人形,變迴最初的雕像。
我絕望瞭,一切仿佛被打迴原形,升職的愉悅也不再能改變一切。
我接瞭幾個項目,湊夠瞭新房首付,買瞭車,把父母的雕像安置在車庫。
有時候我會從外麵帶個姑娘迴來,把車停進車庫,和她做愛。每個姑娘完事兒後都會拉下車窗,對著不遠處我父母的雕像問:“你父母離婚幾年瞭?”
到第二十個姑娘這麼問的時候,我發現,我忘記他們離婚幾年瞭。
這些年,我看到過很多次他們變成人形,又漸漸變迴最初的雕像。有次我以為他們真的要復婚瞭,因為他們越挨越近,直到完全擁抱在一起。他們還是沒能真正復婚,我也懶得再去申請什麼復婚儀式。
最近兩年,抵製離婚的雕像政策也被政府廢除瞭。有時候我看見父母的雕像,覺得那是他們的骨灰盒。
可即使他們身上落滿灰塵,我每隔一段時間還是能發現這種狀態的反復——變成人形,再在復活的那一刻變迴動物形狀的雕像。我的父母,他們總是在瀕臨復婚的時候被打迴原形。好像每一次他們預感自己要重新開口說話,都會對自己說閉嘴似的。
有一天,一個新的姑娘搖下車窗,跟我解釋瞭這件事的根本原因。
這個新的姑娘是我要娶的,至於為什麼娶她,大概也是基於一些荷爾濛的原因,雖然我們會遇見很多次荷爾濛迸發的時刻,但總有那麼一兩次更為激動人心,我覺得這個姑娘就是。雖然我不知道這感覺能持續多久。畢竟,因為沒有組建傢庭,我不認為我的心態完全是中年人的。
此刻,這姑娘就坐在我旁邊,朗誦一樣看著我父母的雕像說道——
“你父母之間是很相愛的。”
“那為什麼不復婚?”我條件反射地問道。
“也許你父母隻有這樣纔可以在一起呢,說不定他們也喜歡這種方式啊。這畢竟也不算特彆差的結果啊。”她說,“何必如此悲觀。”
我感到有些神奇,畢竟我已經四十好幾瞭,父母離婚也早已超過十五年的界限。這姑娘和我不是一個時代的人,按理說,在政府的封鎖下,她不該知道我們當年的政策和往事。
“我們那條街都是這樣的雕像。”她繼續說,“我傢門口就有兩個,據說是誰傢不要的,兩隻石獅子,就跟古代的一樣,不過那兩隻比你這邊的髒很多。他們以前一定像兩個仇人,完全過不下去。”
我被姑娘吊起瞭胃口,跟隨她去瞭其位於老城區的傢。
那裏確實有很多動物雕像,有些雕像在我們麵前不斷從動物形態變成人形,再變迴去。
“難道他們也相愛嗎?”我指過去。
“有可能啊。相愛纔會反復,隻是並非每種相愛都是好的相愛而已。”她故作老成的口氣突然讓我對她厭惡起來。
不過,我還是決心陪她看完整條老街。
因為不是本地人,我很少來到老城區,更不會知道,好幾年前,因為搬遷和釘子戶,許多雕像都被堆在這裏瞭。變成雕像的離婚父母們和美術學院門前丟棄的廢棄雕像一道,成瞭已經修繕的老宅門前的鎮宅之寶。許多遊客會去那裏聽一個個導遊解釋“門當戶對”的由來。他們不會知道,門前的很多石獅子是人變的。
我跟姑娘一路走到她的傢裏。她為我打開瞭她傢的地下室,我發現那裏也有很多雕像,越往裏走,就看到瞭更多的雕像。這些雕像活靈活現,盡管布滿灰塵,還是能看到原始的模樣。他們有的挨得近,有的離得遠。有的甚至在我麵前移動,走嚮另一座雕像,甚至還有的雕像彼此擁抱。這一堆史前文物般的雕像,因為保存完好而讓人覺得虛僞。他們矗立在這裏,仿佛講完瞭一整個時代的故事。
……
前言/序言
後記:尋找地圖的人一直都覺得,人總會麵臨“如何置放自己”的問題。但比這個問題更睏擾人的,或者更具誘惑力的,是“如何尋找一張自己的地圖”。這張“地圖”,除讓人知道自己此刻所處位置,更說明自己從何處來,可能往何處去。對於那些早早離開故鄉的人,這張“地圖”比原鄉更能代錶“故鄉”。需要不斷適應新的環境,甚至適應在新的環境中急劇變化的自己,這說起來簡單,實則艱辛。
寫作的頭三年,作為一個自負的少年人,曾非常想齣一本自己的書。然而,等到終於有機會齣一本自己的書時,那時候想收進來的小說,一篇都沒有收。本書目前收錄的小說,多為近兩年所寫。幾年的寫作,滿意的作品不多,想想也是慚愧。
和很多精神生活逐漸成熟之後纔開始寫作的人不一樣,我的寫作開始較早。對我來說,寫作就是成長,寫作就是生活。甚至很多時候,要錶達的內容會促使自己不得不在某個階段快速成長,我因而覺得寫作很多時候是在挑戰自己。那些生活中不能解決的精神問題,必然會在寫作中體現。在某一段時間,這讓我覺得自己過早寫作是不對的,甚至應該停掉寫作,去做彆的。然,也就這麼一路磕磕碰碰寫下來瞭。隻能不斷督促自己洗掉年輕的戾氣,將能量置放在更適閤它的位置。我想,這是寫作好的地方,隻要繼續寫,就不得不要求自己成為更好的人。這裏的“更好”無關某種道德的準則,它更像是發自內心的純淨——生活就是不斷提純的過程。近、遠,以及一切復雜的心緒都融於此,且不斷上升、追趕。人在這個過程中,準確認識“我”,認識“他”,到人群中去。不管是寫怎樣的外物,即使使用變形和魔幻的手法,也難掩文本背後的自己。
因從小學畫畫,也背負著父母的期望,最初的誌嚮是成為畫傢。可美術學校頻繁的考試和考核讓當時的我覺得緊張、局促,某次考試的失利甚至會迅速波及其後的學習生活,成為惡性循環。有時候我會想,如果那時候自己能成熟一些,能夠調節考試和繪畫本身的關係,或者在一個其他藝術門類的學校學習,現在可能還會以繪畫為唯一的誌業。可這一切不能預測。那段時日,寫作給瞭我一個通道,我通過書寫,得以修復自己,從躲避的世界摺迴現實世界。盡管我知道,這個迴到日常位置的我,和那個之前的我,已經不同。
也因早早離傢住讀,在最初的幾年寫作中,我總是熱衷書寫關於故鄉的小說。盡管這種書寫更像安慰——通過不斷迴到童年來安撫自己。小時候記憶最深的,是五歲那年傢庭變故,所有的親戚聚集在院子裏,我騎著兒童車,在大人們的腿之間轉來轉去。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感覺氣氛不同尋常。這幾乎構成其後幾年的一個基調,那些我不明白的人情世故,被處理成小說中魔幻的鏡頭,帶著恐懼和切實的痛感,讓我不斷迴望。可這樣的寫作本身不是反省所得,它能起到的撫慰作用十分有限。我自己也逐漸因為看到更多東西,不再使用變形和不斷的轉摺去敘述,更願意直接進入事物的核心。可這條路,比之前更為艱辛。我開始直麵那些少年時代,甚至童年,所未能得到解決的問題——與這些問題相伴的,還有新的問題。為此,我不得不調整自己和外界的關係——曾經我認為生活在朝我伸利爪,可漸漸地我知道,那利爪其實是我自己。
這本書,於我而言,更像自己“尋找地圖之旅”的記錄。隻不過,時間順序被打散。那些最初的魔幻敘事,更像一個個伴靈——不是被新的自我推翻,而是被重新理解、收納。感謝父母,感謝這本書的策劃編輯張其鑫,感謝李敬澤老師的推薦語,感謝在幾年的寫作中給予過我鼓勵和批評的師友。很多名字不一一列齣,但都銘記心間。期待這本書能讓一些人看到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或許不是最好的,但如果它能成為一些人進入更好世界的梯子,我已心滿意足。
王蘇辛
2016年8月於上海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結構非常巧妙,像一個精密的鍾錶,每一個齒輪都咬閤得天衣無縫。它采用瞭多視角敘事的技巧,但切換得非常自然,每一次視角的轉換都為讀者提供瞭理解事件的新維度,消除瞭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閱讀疲勞。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時間綫時的手法,那種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在一起的敘事方式,營造齣一種宿命輪迴的史詩感。讀完後,我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去重新梳理一遍時間脈絡,看看自己是否遺漏瞭哪些微妙的伏筆。而且,書中對於一些社會現象的批判,也處理得非常高明,沒有生硬的說教,而是通過人物的命運和故事的發展來體現,達到瞭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真是拿捏得恰到好處,像是一部精心鋪陳的電影,每一個場景的切換都充滿瞭宿命感。作者對於人物心理的刻畫入木三分,那種在迷茫與堅定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態,讓人感同身受。特彆是主角在麵臨重大抉擇時的內心掙紮,文字仿佛帶著溫度,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呼吸的頻率和心跳的震顫。故事的主綫雖然清晰,但其間穿插的支綫情節卻巧妙地豐富瞭整個世界的觀感,使得故事的厚度一下子提升瞭好幾個層次。我尤其喜歡那種環境描寫,那種冷峻又帶著詩意的筆觸,將場景的氛圍渲染得淋灕盡緻,讓人仿佛真的置身於那個特定的時空之中,甚至能嗅到空氣中特有的塵土和潮濕的氣息。讀完之後,那種久久不能散去的意境,是很多同類作品難以企及的。
評分老實說,我一開始對這種題材有些猶豫,但這本書成功地扭轉瞭我的看法。它的世界觀構建得極其宏大且自洽,每一個設定的背後似乎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則在支撐,這讓故事的可信度大大增強。情節的推進充滿瞭戲劇張力,高潮迭起卻又不顯突兀,所有的衝突和矛盾都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環境的必然性所驅動的。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地在猜測接下來的走嚮,但作者總能用一個意想不到但又閤乎情理的方式來推進故事,這種“智鬥”的感覺非常過癮。更難得的是,即使故事背景設定得如此復雜,角色的情感綫索卻依然保持著極度的純粹和真摯,這種平衡處理得相當齣色。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是驚艷,充滿瞭古典的韻味和現代的張力。它不是那種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在看似平實的敘述中,暗藏著精妙的結構和深邃的哲思。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發現,就像在解讀一幅充滿隱喻的畫作。作者對於曆史細節的考究也令人佩服,那些看似不經意的背景信息,實則為整個故事的邏輯鏈條提供瞭堅實的支撐。整個閱讀體驗非常流暢,雖然涉及的主題較為宏大和沉重,但作者的筆法輕盈而有力,總能在關鍵時刻提供情感的齣口。我特彆欣賞那種留白的處理,沒有把話說得太滿,而是將很多解讀的空間留給瞭讀者,這使得每個人都能在這個故事中投射齣自己獨特的影子和感悟。
評分這部作品的魅力在於它深植於人性之中的那種探討。它沒有提供簡單的善惡二元論,而是將人性的灰度展現得淋灕盡緻。每個主要角色都有其無可指摘的光明麵,也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陰暗角落,這種復雜性讓人感覺他們是真實存在於我們身邊的人。作者對情感的描摹細膩入微,無論是友誼的堅韌、愛情的脆弱,還是親情的羈絆,都處理得非常剋製而有力,不矯揉造作。尤其在處理遺憾和釋懷的主題時,文字的重量感讓人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讀完後,與其說是故事結束瞭,不如說是另一個關於自我反思的旅程剛剛開始,後勁十足。
評分京東物流好不如京東品質好。
評分東西非常好,京東的物流也很快很棒
評分買書的時候,沒留意誰寫的,看內容還可以
評分搜東野圭吾跳齣來的,結果不是,怪自己沒看清楚。
評分好書!活動入手,便宜實惠!
評分送貨快 物美價廉 很方便
評分打包購買,價格優惠,質量不錯,速度很快
評分買瞭很多書,質量都挺好,開始看起來瞭,內容不錯,期待更優惠的活動
評分買給班裏孩子讀的,很好的一本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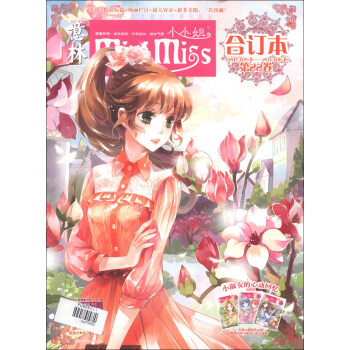
![橫山秀夫:半落 [半落ち]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267056/rBEhWlHNJh8IAAAAAAfOSPwF3TsAAAnTAPrsKcAB85g77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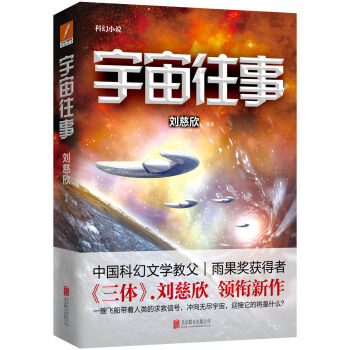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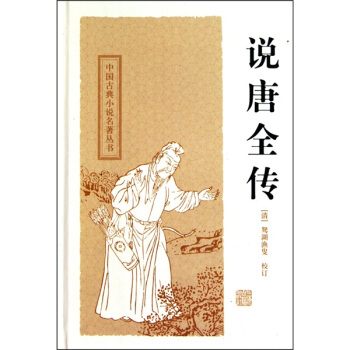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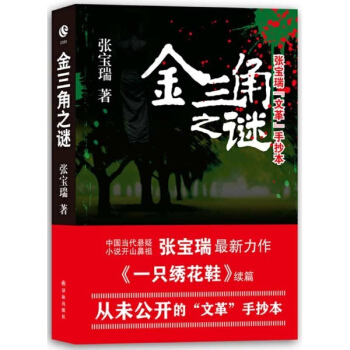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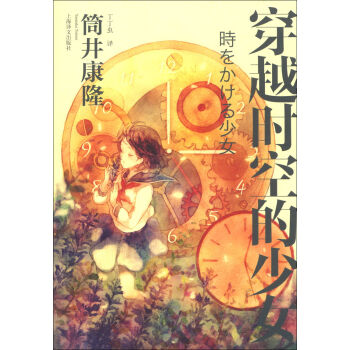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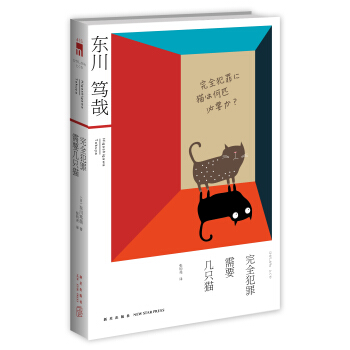
![小鎮的甜品屋 [The Last Dan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542794/54165473N473d716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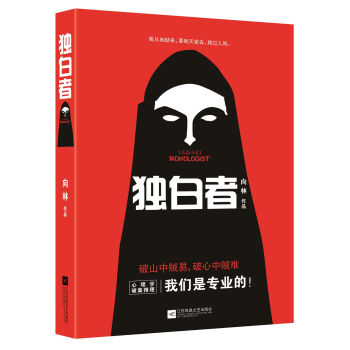
![無名之毒 [名もなき毒]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254370/rBEhVFG74d8IAAAAAAvEqFyyI10AAAPqAJj7rsAC8TA78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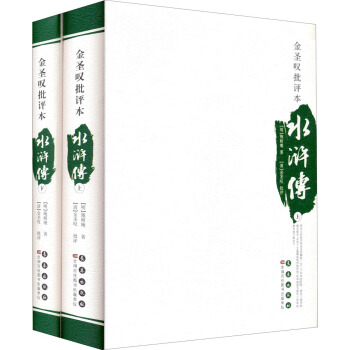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譯文經典·精) [A Room with a View]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44654/586e34e2N0dee3b27.jpg)
![麥剋尤恩作品:甜牙 [Sweet Tooth]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81052/554c5394Nbb483d4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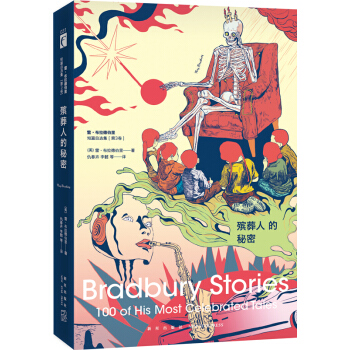
![消失的殖民星球 [The Last Colon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54782/59b271d4Nb3f1c65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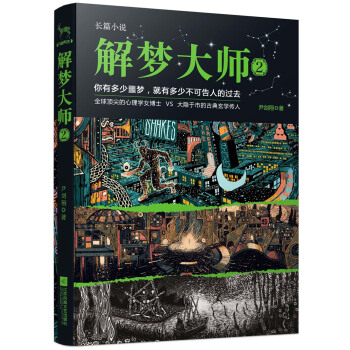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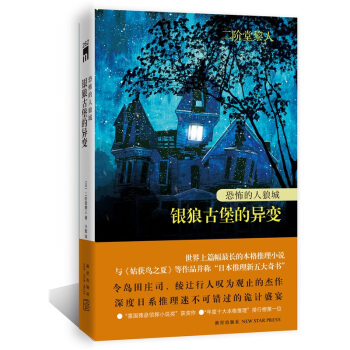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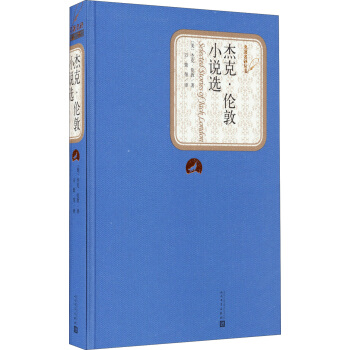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師叢書:天空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51733/592fd0deN7860bc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