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白夜照相馆》: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佳作奖得主王苏辛历经七年沉淀力作
2016—2017年度备受期待的新浪潮文学代表作
本书中多篇小说曾登上豆瓣、犀牛故事等app首页,阅读量累计两百万次。
本书选用了王苏辛众多作品中代表的14个神行百变的故事,这14个故事仿佛是我们置身的现实,每一个故事都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每一个故事都能够让读者迅速击退心中仅保留的那道阅读防线,快速进入故事当中,仿佛每个读者都是故事中的一员,无一例外。
内容简介
14个神行百变的故事14个我们置身的现实王苏辛的小说辨识度很高,叙述表达上风格明快,时而传奇,时而现实。
例如:小说《白夜照相馆》讲述擅长拍摄复古照片的“白夜照相馆”专门为人伪造身份,从而引发的一连串复仇、谋杀事件。
短篇精怪故事《我们都将孤独一生》则书写了一座只要一离婚就变成雕像的国度,“我”的父母因为离婚变成两尊雕像,而“我”却因为父母这一决定,自身的生活发生传奇式的改变。《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讲述了社交恐惧症的父母却生出社交达人女儿,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戏剧冲突。
小说《直立行走的人》讲述了传奇背景下,身高过高的一家人,所遇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跌宕起伏,情感浓烈。
作者简介
王苏辛,生于1991年,曾用笔名普鲁士蓝。2015年获得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是一位获得该奖的90后作者。短篇小说《白夜照相馆》2016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是一位被国内重量级文学选刊同时转载的90后作者。短篇小说《我们都将孤独一生》等曾登上豆瓣app首页推荐,被多家网站转播转载。王苏辛的小说风格怪诞,兼具魔幻叙事与日常传奇,辨识度很高。精彩书评
文学从“我”开始,也该由“我”向前王苏辛的小说,不是反映,而是熔炼,它打开了小说在山穷水尽时的可能性——容纳庞杂无尽的碎片而抵达晶体般的虚构。
——李敬泽
目录
白夜照相馆战国风物
伴灵故事集
__我们都将孤独一生
__再见,父亲
__请不要倚靠电梯
__昨夜星光璀璨
__寂寞芳心小姐
__猴
__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
袁万岁
下一站,环岛
直立行走的人
自由
荒地
后记:寻找地图的人
精彩书摘
我们都将孤独一生我父母决定离婚时,曾征求过我的意见。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在我们国家,离婚的人会变成雕像镇守自家的宅子,而且,雕像永远不能进入家门。即便如此,离婚率还是持续高涨,很多宅子前都堵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像,其中,最多的是石狮子。有的家族人丁兴旺,门前简直可以集齐十二生肖。可我家地处楼房,只能另觅空地安置父母。
我父母要征求我的意见,原因就在此。
整个三伏天,为了他们离婚的善后事,我到处寻找便宜的地下车库或者小单间,可最近租金昂贵,一间小地下室的月租居然都要一万。我用尽了在公司谈合同学来的本事,甚至许诺签下十年内不会复婚的条约,还是没有一个房东愿意把租金降到一个我能承担得起的价位。
我试图找亲戚朋友借钱,可最近离婚的多,尽管父母和我多年来充当老好人,听说他们要离婚,都一个个躲得十万八千里。
这引发了他们离婚前的最后一次争吵。争吵的焦点是:到底是谁当年执意买了楼房。我告诉他们,现在即使是自家平房宅子前的空地,也是需要购买的。可他们完全不听我说的,不仅不听,他们还为我打断他们的吵架思路而万分不爽。
——那之后不久,他们就离婚了。
在变成雕像的惩罚文件下来之前,我白天奔走于寻找合适的房子,晚上为他们变成哪种雕像未来复婚几率更大而伤尽脑筋。
我准备了几个纸团,上面写着各种神兽和生肖的名字,雕像的种类只能从这里面选。我把它们认真包好,选择两个同类的神兽让父母抓阄,就像小时候他们在书上抹蜂蜜让我误抓了书本一样,我也把两个最可能复婚的同类神兽的纸团包得更宽大、醒目,试图让父母选择它们。
孰料他们离婚之意非常稳固,根本不考虑离婚征程中的费用,各自选了两个复婚率极低的生肖雕像,一匹马,一头羊。
我很绝望,但说不过他们,只能顺从,毕竟十五年之后,雕像的安置费用将由政府承担。十五年虽长,总好过一生。
我卖了家里的房子,租了城郊一间小平房,时常断水断电,来回公司需要五个小时。但想到十五年后的幸福生活,我忍了。
就这样,我父母愉快地离了婚,我也成了一个房奴。
为了维护雕像的簇新,我每周都会去他们所在的地下室擦洗它们。地下室没有水电,我就从远处提水,储存了大量洗涤剂和吹风机。这些工作往往须耗费一天的时间,但我乐此不疲。坦白说,他们刚离婚的那两年,我无时无刻不希望他们幡然醒悟然后复婚,我也早点结束房奴的生活。两年过去了,我发觉这是徒劳。
我租下的这间地下室位于解放东路尽头。懒得给父母擦洗的日子里我会在这里灭蟑螂——自从成为穷困潦倒的房奴,我就没有社交活动了,在这里待着倒也能打发自己的无聊。
我这样过到了他们离婚的第五年,然后日子就不同了。
那时候我已经升任公司某部门副主管,这份工作的好处是我得以租住一套位于市中心的一居室。我的社交活动重新多起来,甚至也把开公司划入未来日程。有时候忙起来,一两个月也不会去看一次父母。毕竟房租我一口气付了十年的,不去也没人提醒我什么。
我也开始和女孩子约会,她们年纪都比较小,二十二三岁,总把自己装扮得像三十岁。不过这也不错,她们都学着不黏人,倒很合我心意。可有一天,我还是接到了一个双鱼座暧昧对象的拉黑短信,她告诉我,不会再联系我。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可能就是因为没给她一个明确答案,比如,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那天下了大雨,因为这条短信,我和女孩子晚上的约会宣布告吹。我百无聊赖地走出去,打着伞,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我想起明天开始是我的年假,决定去看看我的父母。
这次探望让我发现,他们浑身都洗得很干净,可能比几年前他们刚离婚变成雕像的时候更干净。
我也发现了他们容貌的变化,我妈妈明明是马的雕像,现在已经变成人形了,爸爸也一样。
他们身体的各个角落都泛着白光。我使劲抬起雕像一角,发现底座都是干净的。
我不知道谁在我不在的日子里帮我擦洗父母,思来想去感觉没有人会这样做。我又检查了房屋,发现根本也没漏水。我灭了一遍地下室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生物,把房间打扫到最干净,决定在这里待上一周。如果有谁来,我一定会看得见。
我支起睡袋,一头挂在母亲的头上,一头挂在父亲的头上。躺上去,睡袋会摇摇晃晃让我头晕,但也变相缩短我进入梦乡的时间,感觉还不错。
我做了很多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我身上布满摔伤后的青紫色,而父母之间的距离也显然比之前近了很多。
我有些莫名的恐惧和欣喜。我第一次怀疑,负责擦洗父母的其实是他们自己。毕竟,复婚的征兆就是雕像之间距离变窄和变成人形。
而经过这次距离拉近之后,父母完全变成了人形。
我从没想过他们真的会复婚,可这一天真的就要来到,我也感到高兴,尽管我已经没那么穷了。
复婚的过程很顺利。我向有关部门报告了父母的近况,头头们批准他们复婚。我退掉了地下室,宴请了亲戚朋友,他们很乐意和我的一家重新建立联系。我们在舞池中间跳了一场群舞庆祝这一切,父母的雕像就摆在正中间,我们都在等待他们活过来的那一刻。
我们跳了三天三夜,他们还是没有醒过来。
再过了三天三夜,他们褪去人形,变回最初的雕像。
我绝望了,一切仿佛被打回原形,升职的愉悦也不再能改变一切。
我接了几个项目,凑够了新房首付,买了车,把父母的雕像安置在车库。
有时候我会从外面带个姑娘回来,把车停进车库,和她做爱。每个姑娘完事儿后都会拉下车窗,对着不远处我父母的雕像问:“你父母离婚几年了?”
到第二十个姑娘这么问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他们离婚几年了。
这些年,我看到过很多次他们变成人形,又渐渐变回最初的雕像。有次我以为他们真的要复婚了,因为他们越挨越近,直到完全拥抱在一起。他们还是没能真正复婚,我也懒得再去申请什么复婚仪式。
最近两年,抵制离婚的雕像政策也被政府废除了。有时候我看见父母的雕像,觉得那是他们的骨灰盒。
可即使他们身上落满灰尘,我每隔一段时间还是能发现这种状态的反复——变成人形,再在复活的那一刻变回动物形状的雕像。我的父母,他们总是在濒临复婚的时候被打回原形。好像每一次他们预感自己要重新开口说话,都会对自己说闭嘴似的。
有一天,一个新的姑娘摇下车窗,跟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根本原因。
这个新的姑娘是我要娶的,至于为什么娶她,大概也是基于一些荷尔蒙的原因,虽然我们会遇见很多次荷尔蒙迸发的时刻,但总有那么一两次更为激动人心,我觉得这个姑娘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感觉能持续多久。毕竟,因为没有组建家庭,我不认为我的心态完全是中年人的。
此刻,这姑娘就坐在我旁边,朗诵一样看着我父母的雕像说道——
“你父母之间是很相爱的。”
“那为什么不复婚?”我条件反射地问道。
“也许你父母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一起呢,说不定他们也喜欢这种方式啊。这毕竟也不算特别差的结果啊。”她说,“何必如此悲观。”
我感到有些神奇,毕竟我已经四十好几了,父母离婚也早已超过十五年的界限。这姑娘和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按理说,在政府的封锁下,她不该知道我们当年的政策和往事。
“我们那条街都是这样的雕像。”她继续说,“我家门口就有两个,据说是谁家不要的,两只石狮子,就跟古代的一样,不过那两只比你这边的脏很多。他们以前一定像两个仇人,完全过不下去。”
我被姑娘吊起了胃口,跟随她去了其位于老城区的家。
那里确实有很多动物雕像,有些雕像在我们面前不断从动物形态变成人形,再变回去。
“难道他们也相爱吗?”我指过去。
“有可能啊。相爱才会反复,只是并非每种相爱都是好的相爱而已。”她故作老成的口气突然让我对她厌恶起来。
不过,我还是决心陪她看完整条老街。
因为不是本地人,我很少来到老城区,更不会知道,好几年前,因为搬迁和钉子户,许多雕像都被堆在这里了。变成雕像的离婚父母们和美术学院门前丢弃的废弃雕像一道,成了已经修缮的老宅门前的镇宅之宝。许多游客会去那里听一个个导游解释“门当户对”的由来。他们不会知道,门前的很多石狮子是人变的。
我跟姑娘一路走到她的家里。她为我打开了她家的地下室,我发现那里也有很多雕像,越往里走,就看到了更多的雕像。这些雕像活灵活现,尽管布满灰尘,还是能看到原始的模样。他们有的挨得近,有的离得远。有的甚至在我面前移动,走向另一座雕像,甚至还有的雕像彼此拥抱。这一堆史前文物般的雕像,因为保存完好而让人觉得虚伪。他们矗立在这里,仿佛讲完了一整个时代的故事。
……
前言/序言
后记:寻找地图的人一直都觉得,人总会面临“如何置放自己”的问题。但比这个问题更困扰人的,或者更具诱惑力的,是“如何寻找一张自己的地图”。这张“地图”,除让人知道自己此刻所处位置,更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可能往何处去。对于那些早早离开故乡的人,这张“地图”比原乡更能代表“故乡”。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甚至适应在新的环境中急剧变化的自己,这说起来简单,实则艰辛。
写作的头三年,作为一个自负的少年人,曾非常想出一本自己的书。然而,等到终于有机会出一本自己的书时,那时候想收进来的小说,一篇都没有收。本书目前收录的小说,多为近两年所写。几年的写作,满意的作品不多,想想也是惭愧。
和很多精神生活逐渐成熟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人不一样,我的写作开始较早。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成长,写作就是生活。甚至很多时候,要表达的内容会促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个阶段快速成长,我因而觉得写作很多时候是在挑战自己。那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精神问题,必然会在写作中体现。在某一段时间,这让我觉得自己过早写作是不对的,甚至应该停掉写作,去做别的。然,也就这么一路磕磕碰碰写下来了。只能不断督促自己洗掉年轻的戾气,将能量置放在更适合它的位置。我想,这是写作好的地方,只要继续写,就不得不要求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里的“更好”无关某种道德的准则,它更像是发自内心的纯净——生活就是不断提纯的过程。近、远,以及一切复杂的心绪都融于此,且不断上升、追赶。人在这个过程中,准确认识“我”,认识“他”,到人群中去。不管是写怎样的外物,即使使用变形和魔幻的手法,也难掩文本背后的自己。
因从小学画画,也背负着父母的期望,最初的志向是成为画家。可美术学校频繁的考试和考核让当时的我觉得紧张、局促,某次考试的失利甚至会迅速波及其后的学习生活,成为恶性循环。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时候自己能成熟一些,能够调节考试和绘画本身的关系,或者在一个其他艺术门类的学校学习,现在可能还会以绘画为唯一的志业。可这一切不能预测。那段时日,写作给了我一个通道,我通过书写,得以修复自己,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尽管我知道,这个回到日常位置的我,和那个之前的我,已经不同。
也因早早离家住读,在最初的几年写作中,我总是热衷书写关于故乡的小说。尽管这种书写更像安慰——通过不断回到童年来安抚自己。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五岁那年家庭变故,所有的亲戚聚集在院子里,我骑着儿童车,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感觉气氛不同寻常。这几乎构成其后几年的一个基调,那些我不明白的人情世故,被处理成小说中魔幻的镜头,带着恐惧和切实的痛感,让我不断回望。可这样的写作本身不是反省所得,它能起到的抚慰作用十分有限。我自己也逐渐因为看到更多东西,不再使用变形和不断的转折去叙述,更愿意直接进入事物的核心。可这条路,比之前更为艰辛。我开始直面那些少年时代,甚至童年,所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新的问题。为此,我不得不调整自己和外界的关系——曾经我认为生活在朝我伸利爪,可渐渐地我知道,那利爪其实是我自己。
这本书,于我而言,更像自己“寻找地图之旅”的记录。只不过,时间顺序被打散。那些最初的魔幻叙事,更像一个个伴灵——不是被新的自我推翻,而是被重新理解、收纳。感谢父母,感谢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其鑫,感谢李敬泽老师的推荐语,感谢在几年的写作中给予过我鼓励和批评的师友。很多名字不一一列出,但都铭记心间。期待这本书能让一些人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如果它能成为一些人进入更好世界的梯子,我已心满意足。
王苏辛
2016年8月于上海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深植于人性之中的那种探讨。它没有提供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而是将人性的灰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个主要角色都有其无可指摘的光明面,也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这种复杂性让人感觉他们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作者对情感的描摹细腻入微,无论是友谊的坚韧、爱情的脆弱,还是亲情的羁绊,都处理得非常克制而有力,不矫揉造作。尤其在处理遗憾和释怀的主题时,文字的重量感让人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读完后,与其说是故事结束了,不如说是另一个关于自我反思的旅程刚刚开始,后劲十足。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惊艳,充满了古典的韵味和现代的张力。它不是那种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看似平实的叙述中,暗藏着精妙的结构和深邃的哲思。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就像在解读一幅充满隐喻的画作。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考究也令人佩服,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背景信息,实则为整个故事的逻辑链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整个阅读体验非常流畅,虽然涉及的主题较为宏大和沉重,但作者的笔法轻盈而有力,总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情感的出口。我特别欣赏那种留白的处理,没有把话说得太满,而是将很多解读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这使得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故事中投射出自己独特的影子和感悟。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非常巧妙,像一个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天衣无缝。它采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技巧,但切换得非常自然,每一次视角的转换都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事件的新维度,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阅读疲劳。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时间线时的手法,那种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宿命轮回的史诗感。读完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重新梳理一遍时间脉络,看看自己是否遗漏了哪些微妙的伏笔。而且,书中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也处理得非常高明,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来体现,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真是拿捏得恰到好处,像是一部精心铺陈的电影,每一个场景的切换都充满了宿命感。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那种在迷茫与坚定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特别是主角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内心挣扎,文字仿佛带着温度,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呼吸的频率和心跳的震颤。故事的主线虽然清晰,但其间穿插的支线情节却巧妙地丰富了整个世界的观感,使得故事的厚度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层次。我尤其喜欢那种环境描写,那种冷峻又带着诗意的笔触,将场景的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时空之中,甚至能嗅到空气中特有的尘土和潮湿的气息。读完之后,那种久久不能散去的意境,是很多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
评分老实说,我一开始对这种题材有些犹豫,但这本书成功地扭转了我的看法。它的世界观构建得极其宏大且自洽,每一个设定的背后似乎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则在支撑,这让故事的可信度大大增强。情节的推进充满了戏剧张力,高潮迭起却又不显突兀,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环境的必然性所驱动的。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猜测接下来的走向,但作者总能用一个意想不到但又合乎情理的方式来推进故事,这种“智斗”的感觉非常过瘾。更难得的是,即使故事背景设定得如此复杂,角色的情感线索却依然保持着极度的纯粹和真挚,这种平衡处理得相当出色。
评分超级好!!!!超级给力!!!!!
评分东西不错,物流很快,包装完好无损
评分怪诞的故事却又照见了人性,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评分书很不错的,年末了配送还是很快的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书不错,纸质也挺好的,,正好搞活动买本看看
评分还看,屯着先。但是京东活动买书还是很优惠的!
评分书挺好,派送的包裹也结实。
评分图书质量不错,价廉物美,值得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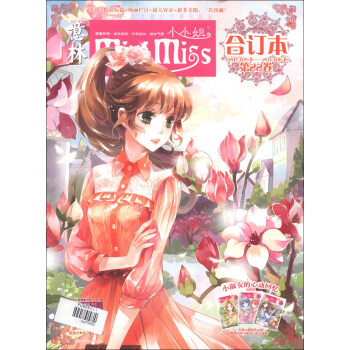
![横山秀夫:半落 [半落ち]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67056/rBEhWlHNJh8IAAAAAAfOSPwF3TsAAAnTAPrsKcAB85g77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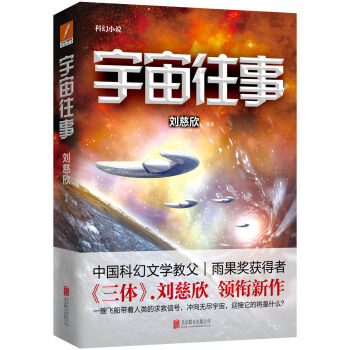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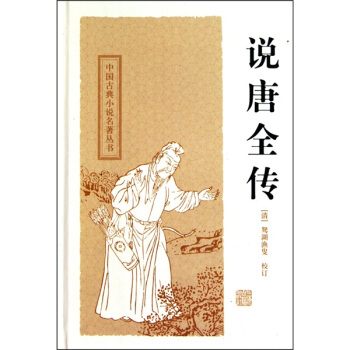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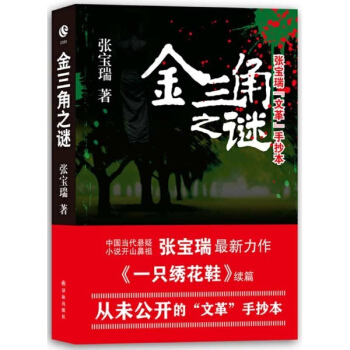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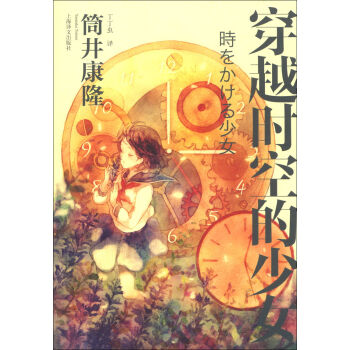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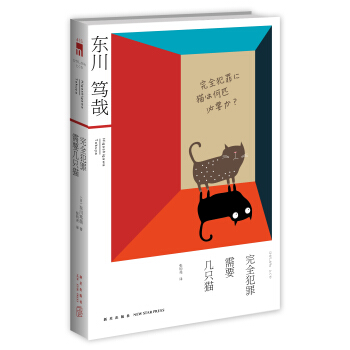
![小镇的甜品屋 [The Last Da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42794/54165473N473d716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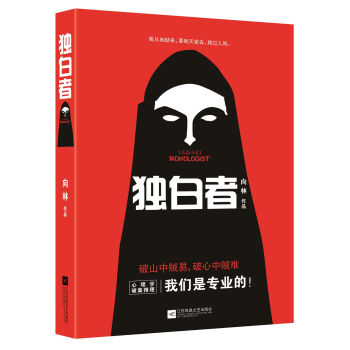
![无名之毒 [名もなき毒]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54370/rBEhVFG74d8IAAAAAAvEqFyyI10AAAPqAJj7rsAC8TA78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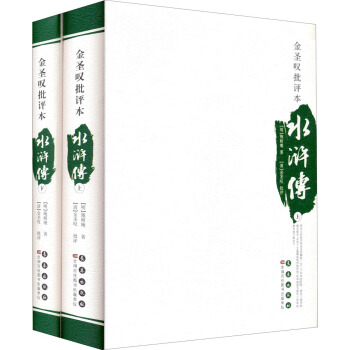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译文经典·精) [A Room with a Vie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44654/586e34e2N0dee3b27.jpg)
![麦克尤恩作品:甜牙 [Sweet Too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81052/554c5394Nbb483d4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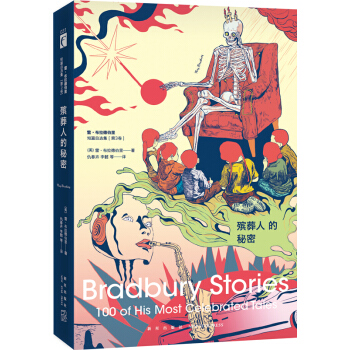
![消失的殖民星球 [The Last Colon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54782/59b271d4Nb3f1c65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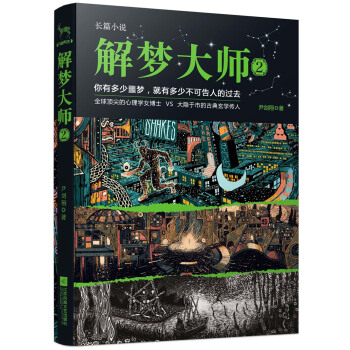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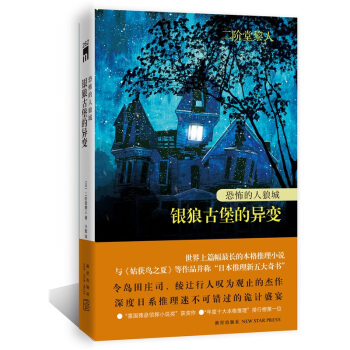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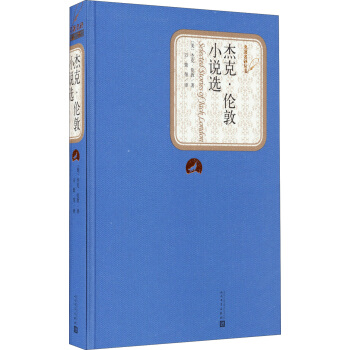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天空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51733/592fd0deN7860bc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