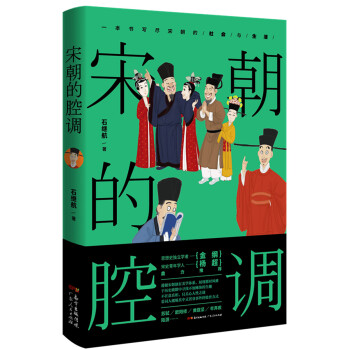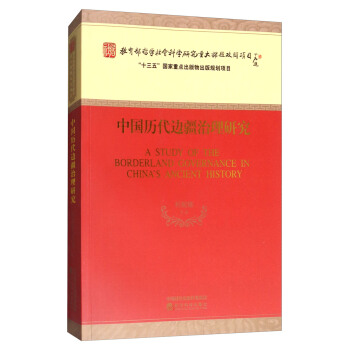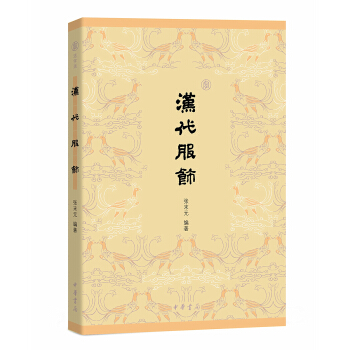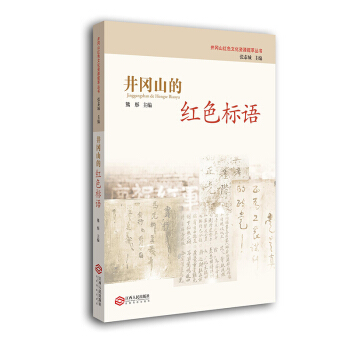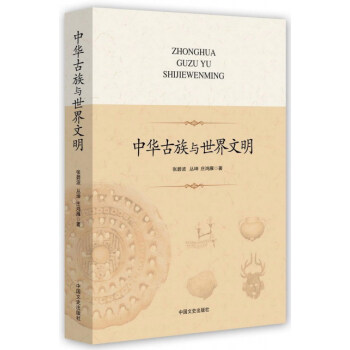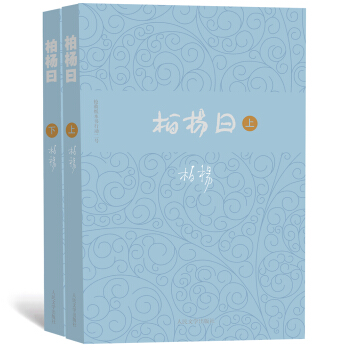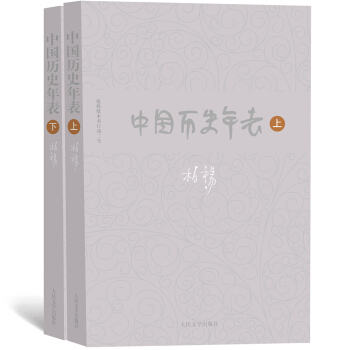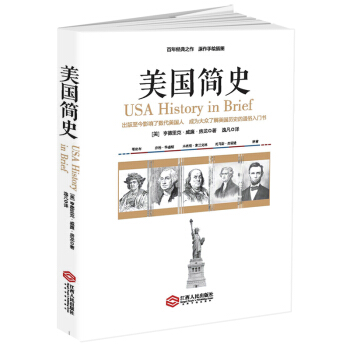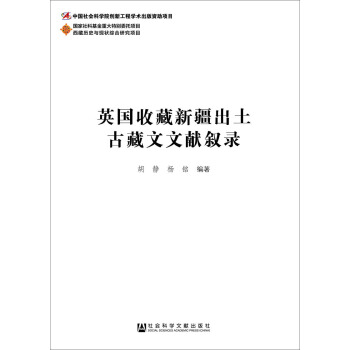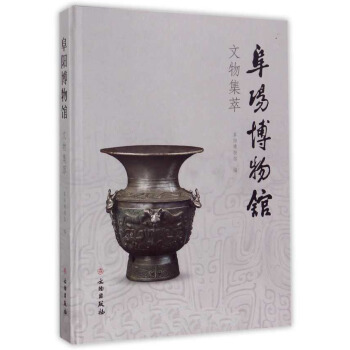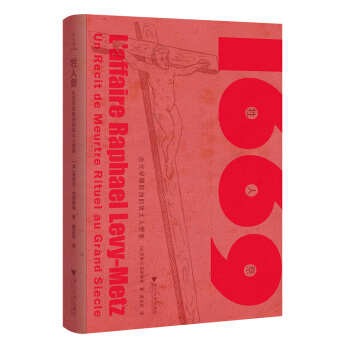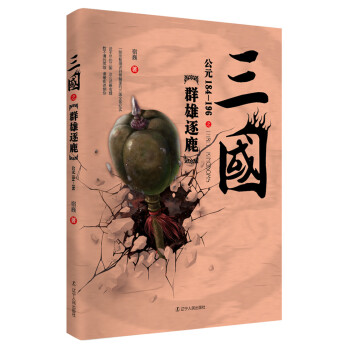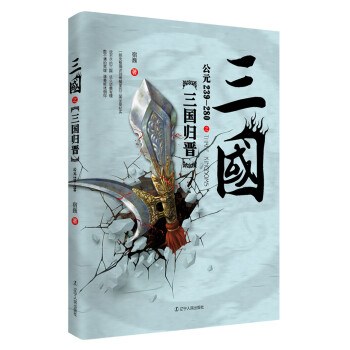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近年来随着满族史研究和清史研究深入拓展,开展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专家学者将目光从正史资料转向注重满族家谱研究。满族家谱研究除各图书馆外,在民间有大量收藏。二十几年来,满族家谱整理出版数量较大,但大多为将原本点校后重新排版印刷,尽管再现了原本文字内容,但却没有保留家谱原貌,使其史料信息及价值丢失很大,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多学科交叉研究满族历史及原生态文化的需要。《佛满洲家谱精选(三卷本 套装共3卷)》对珍贵的陈满洲家谱进行了全部收编;并尽可能的收录了《八旗满洲世族通谱》、《清史稿》等有载录的佛满洲家谱,或地方满洲名人家谱;还收录了高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满洲家谱。本《集成》主要收录家谱有:福陵觉尔察氏家谱、马佳氏家谱、牛钴禄氏家谱、萨克达氏家谱、哈达那拉氏家谱、富察氏家谱、瓜尔佳氏家谱等约70部。
作者简介
吕萍,女,吉林长春人,现任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长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东北史、东北边疆与民族特别是满族历史与文化、东北地域民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吉林省哲学规划办、教育厅等社科项目10余项,在研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民委、吉林省教育厅等社科基金项目5项。出版专、编著《满族文化论集》、《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褂和她的弟子们》《中国满学》等8部。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内页插图
目录
吉林卷沙济富察氏宗谱(道光丁亥年本)
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厢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民国十九年本)
辉发沙克达氏家谱(清末本)
马希哈拉宗谱(民国初年本)
打焦楼屯谱书(民国五年本)
赫舍里氏康族世谱——民国十年本
后记
黑龙江卷
讷音富察氏增修支谱(光绪十五年本)
富察氏增修支谱溯源纪(光绪十六年本)
瓜尔佳纳音关氏谱书(1937年本)
关氏宗谱(1941年本)
后记
辽宁卷
那氏宗谱(光绪年间本)
索绰罗氏谱书(光绪十五年本)
永陵喜塔腊氏谱书(光绪二十三年本)
洪氏谱书(民国二年本)
白氏源流族谱(民国十(年续修本)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民国十三年抄本)
萨嘛喇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年续修本)
富察氏谱书(民国三十七年刻本)
后记
前言/序言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人口占全国满族人口的半数,在满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和地位。辽宁满族人口中,清代八旗满洲后裔至少占全省满族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满族人口主要来源有五种情况:
一是清初留守驻防的八旗官兵。二是从康熙到乾隆时期,清朝曾多次从京畿派回辽宁八旗驻防,其中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数量最多。清初,朝廷派内大臣何洛会为总管,统领八旗官兵800余名驻防盛京,另在兴京(新宾)、东京(辽阳)、广宁(北镇)、熊岳、宁远(兴城)、凤凰城(凤城)、牛庄、岫岩、义州(义县)、盖州、海州(海城)、耀州(营口)、锦州等城共设35个佐领,驻防八旗兵约达2000员,每兵按6口家计,仅清初留驻防的满洲人口即约达18000人。康熙时,清廷数次增派八旗官兵回盛京等地驻防,以加强军事防御。同时,清代东北三陵,在清初时就留有守陵的官兵。
二是清代派回驻防的八旗官兵。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为增强“龙兴重地”的军事防御实力,又派遣大批八旗满洲、汉军、蒙古官兵回防辽宁,尤其盛京、兴京、凤凰城等军事要地,皆派有驻防官兵,从而使辽宁满洲人口急剧猛增。清初在辽宁建有封禁“发祥重地”的柳条边,设有21个边门(后来减为20个),每个边门驻有四五十人的官兵,每个墩台都设有巡逻兵和台丁。同时,清廷又在辽宁各军事要地设置城守尉,各交通要道还设有驿站,自然派有八旗官兵。上述种种官兵连其家属,世代繁衍于辽宁。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从京师调拨辽宁岫岩城守尉的赫舍里氏,到光绪己卯年(1879)氏族人口仅阿尔密一支即达3590人。
三是王庄皇庄官庄旗田的满洲庄丁。天启元年116211,后金政权进占辽沈后,在辽阳建立东京城,统治中心迁至辽沈大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将辽东、辽北、辽南大片土地山林分封给满洲贵族,作为私有财产,设立王府庄园、官兵旗田,而耕耘这些王庄旗田的包衣阿哈(奴仆),主要由被征服的女真人阿哈和原居汉人组成。清入关后,盛京设内务府三旗,旗下设有许多的皇庄,又设盛京六部,其中户、礼、工三部都设有许许多多的官庄。这些皇庄、官庄、王庄以及八旗官兵的旗田遍布辽东各地,汉人耕种的上好田地几乎全部占为旗田‘辽东各地几乎遍布王庄、官庄、旗田、果园、木园、炭林、渔场,耕地与山林都由满洲阿哈耕种与经营管理。如太子河中上游的本溪耕地山林’大部分都被努尔哈赤分配给他的次子礼亲王代善,还有敬谨亲王、安平贝勒等人。镶红旗邓氏三世兄弟五人在敬谨亲王府的王庄任庄丁,至十世的咸丰年间,邓氏人口已达2500余人,成为本溪满族大户。
四是清人关后收编的新满洲八旗兵。这主要是指将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收编入旗,是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如康熙七年(1668)收编赫哲人、库雅喇人等,共编为78个佐领。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等叛乱后,其兵及家属一半人迁入内地盛京、锦州、广宁、义州4城31个佐领,共1131户,11180人。三十一年116921,编海拉尔蒙古巴尔虎旗26个佐领,迁10佐领500户2273人隶人盛京将军。第三年又再迁4佐领203户320人归隶盛京将军。康熙三十一年同时还编伯都纳锡伯人74个佐领,与达斡尔、卦尔察人共14458丁归隶盛京上三旗。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从齐齐哈尔调2000多旗兵隶入盛京,分驻24城。三次新编隶盛京的新满洲、巴尔虎、锡伯官兵共6500名,再加上其家属,总人数达40000人。至乾隆时,辽宁驻防八旗官兵共达18625人,计其家属在内约达134000人。
五是关内汉人移民入旗。顺治十年(1653)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垦荒则例》,自关内招来大批汉人,分派辽东各地垦荒种地。据诸多满族家谱记载,在顺治八年(1651)时就应诏移民辽东。《则例》中有招民授官的规定,凡此之汉人,大多被编入汉军旗下,分配在王庄或官庄中为庄丁,少数被派往边台驿站做台丁驿丁。康熙七年(1668)诏令封禁,此后,“闯关东”移民而来的汉人多以三种形式投入旗籍:一是投旗占山垦荒,二是投充王庄官庄为庄丁(又称壮丁),三是投充盛京内务府皇庄和盛京官庄为庄丁,这些汉人加入旗人籍。
辽宁满族多为上述五种来源’少数由于特殊原因迁回辽东,如本溪的吴俄尔格氏冤案平反后自京城迁回辽东,落居本溪,赫舍里王氏一支为避诛连迁回抚顺,赫舍里金氏为避罪迁来本溪,伊尔根觉罗氏随清兵抗击沙俄,与部伍走失,为避惩罚而南逃,潜居本溪等。
用户评价
这套《红楼梦》,哎呀,真真是读进去了,里头的人物关系复杂得像一张巨大的网,贾府的兴衰荣辱,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尤其是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情愫,每一次读到她们的互动,都忍不住替她们揪心。曹雪芹的文笔细腻入微,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简直是神来之笔。你看那王熙凤的泼辣精明,机关算尽,最后落得个凄凉的下场,真是让人感慨世事无常。书里描述的那些大家族的繁华景象,服饰饮食,一砖一瓦都写得栩栩如生,仿佛能闻到那个时代的香气。每次翻开这本书,都能发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某个不起眼的丫鬟,可能在后文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本书不仅仅是讲爱情悲剧,它更像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和人情冷暖。读完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和书里的人物一起经历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评分对于一个热爱自然和生态的读者来说,这本关于野生动物摄影和保护的画册兼散文集,简直是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它记录了作者常年在非洲大草原和南极冰原上,用镜头捕捉到的那些生灵的瞬间。书中的文字部分,并不只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关于生存、关于繁衍、关于抗争的故事。我尤其被那组关于雪豹母子在雪山之巅相依为命的系列照片所震撼,那种极寒环境下的温情,对比得极其强烈,让人瞬间理解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作者的文字非常富有诗意,他没有用过于学术的语言,而是用最真挚的情感去描绘这些野性之美。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只是一个微小的存在,我们有责任去守护这些与我们共享家园的生命,那种宁静而磅礴的力量感,是任何都市喧嚣都无法比拟的。
评分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探险和神秘学领域的著作,暂且叫它《失落的文明密码》吧。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死板地罗列史实,而是将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和现代科学理论大胆地结合在一起。作者似乎真的深入了那些人迹罕至的古迹,描述的场景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和未知的恐惧。比如,书中对一个沉没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玛雅遗址的描绘,那种湿热、幽暗、充满毒虫的环境,读起来简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腐朽气息。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些颠覆传统认知的假说,关于那些史前文明是如何消失的,他们掌握了怎样的技术,虽然很多内容听起来天方夜谭,但作者引用了大量看似严谨的“证据”,让人不得不去深思。这本书激发了我对未知世界强烈的探索欲,读完后,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完整。它更像是一场思想的冒险,非常过瘾。
评分我最近沉迷于一本探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入门读物,书名大概是《符号的迷宫》。坦白说,哲学书通常让人望而却步,但这本书的作者真是个高手,他用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比如流行文化、网络语言、广告营销等等,来剖析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比如解构主义、拟像理论。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戴上了一副全新的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突然间,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都变得可疑起来。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所谓的“真实”,在作者的分析下,都成了被精心构建的符号系统。比如,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其实是被社会媒体不断强化的一种“拟像”。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比较跳跃,充满了反问和逻辑思辨,需要读者时刻保持警惕,跟上作者的思路。它没有给我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教会了我如何去提问,如何质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真理”,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
评分最近迷上了一本讲古代官场斗争的小说,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大明风云录》这类书,最吸引我的就是那种步步为营的权谋较量。主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如何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一步步爬到权力的高层,中间遇到的阻碍和暗算,真是让人看得手心冒汗。书里对官场的腐败和人性的复杂描写得太到位了,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不得已。那种朝堂上的唇枪舌剑,表面和气,实则暗藏杀机,作者对权力的游戏把握得炉火纯青。我特别喜欢看主角设计陷阱,看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官一个个落马时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当然,光有权谋还不够,书里还穿插了一些主角的个人情感线,让这个铁血的官场故事有了一丝人性的温度,不至于太过冰冷。读完后,感觉自己都变得更精明了一些,对人际交往中的潜规则都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实是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