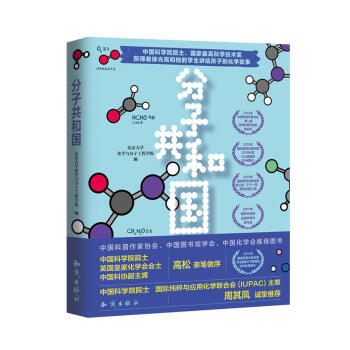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可怕的事并不存在于知识中……而存在于由对知识的渴望产生的冲动所带来的惊人的力量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通过创造自己的生物来理解自己,以揭开他身上的秘密。
内容简介
1816年6月,莱芒湖畔:一群年轻人——拜伦、雪莱和他未来的妻子玛丽,决定写一些关于鬼怪的故事。《弗兰肯斯坦》就这样在玛丽?雪莱的笔下诞生了。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成为一部现代神话。
更加神奇的是,这个拥有特殊使命的启蒙时代女性,在书里预言了两个世纪之后发生的事:人工生殖、基因工程、优生学、超人类主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生产”人类,已经变成了现实。
莫奈特?瓦克安基于玛丽?雪莱的生活和作品,在本书中揭露了现代科学的危险性。正如生物学家雅克?泰斯达在序言中所写的,“疯狂的科学家慢慢变成了疯狂的科学”。
作者简介
莫奈特?瓦克安(Monette Vacquin),精神分析学家和随笔作家,出版的著作主要关于生物学的“进步”给人类所带来的变化,包括:《弗兰肯斯坦:理性的疯狂》(Frankenstein ou les délires de la raison,1989)、《儿童仓库》(Le Magasin des enfants,1990),《占据生物》(Main basse sur les vivants,1999)、《但不至于太严重》(Grave ma non troppo,2015)。
译者:
周欣宇,1993年出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目录
前 言
玛丽所知道的
玛丽与她的同伴
小说《弗兰肯斯坦》
俄狄浦斯与普罗米修斯
《最后的人》
隐喻的废除
预言家玛丽
从幻想到现实
灾 难
传承中的旋涡
有关于女性的知识
说给玛丽的话
去除人类起源的特性:人工生殖的另外一面
对亲缘关系的思辨
克隆:从相似到相同
子宫机器
关于小种子的几个故事……
反动者、蒙昧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
沉默,我们在变化
无意识科学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致 谢
译后记
精彩书摘
【试读】
序言:回响
1982年,在法国的第一个体外人工授精婴儿阿芒迪娜出生后不久,也就是“当试管婴儿将一切都变得不真切”,让莫奈特·瓦克安“疲倦于如此多的空想”的时候,她开始探索“一些关于无性繁殖生物的真实故事”。在《弗兰肯斯坦》中,最让这个精神分析学家感兴趣的莫过于作者的故事:玛丽·雪莱是如何在“有着古老悲剧色彩的、厄运代代相传的生活中”,写出这样一本“在现代生活中仍引起巨大反响”的书?而且在写《弗兰肯斯坦》之前的两年,这位年轻的女子曾在自己的日记里描述了自己接触到的无比粗俗的人,并写道:“上帝创造一个全新的人远比净化这些怪物来得容易”……
不过,莫奈特·瓦克安早在开始写作本书的第一版之前就决定了要分享和深入她对人工繁殖意义的研究。她在《占据生物》(Main basse sur les vivants,1999)一书中提到过一个非正式的团队:“我们是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或者法学家。不用多说也知道,这种不同领域之间的碰撞,加上我们这种非正式的组合给出的完美的自由空间,定是非常耀眼的。”我作为“仓库管理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1990年出版的合集命名为《儿童仓库》)中的生物学家,造出了第一个孩子!实验室中枯燥而简陋的一连串生物密码让我发现了新的思考模式,同时还发现了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智慧。如果没有我曾经作为技术人员与团队的默契,或者我的“仓库管理员”同事做的胚胎培养,我想我都没有这个勇气去想到我现在做的试管婴儿,或是去说出这一过程中的局限,然后以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去证实它的可行性,直到人们最终赋予它一个政治含义。从这种无法从冰冷的试验台产生的觉醒,到热烈的想法,我尤其要将这种转变归功于精神分析学家莫奈特·瓦克安、法学家玛丽- 昂热尔·埃尔米特(Marie-Angèle Hermitte)、伯纳德·阿德尔曼(Bernard Edelman)和社会学家路易斯·万德拉克(LouiseVandelac)。我还记得当时在社会党执政的政府中做司法助理工作的一位教研员,他对我们很失望,并且向我们要一个解释。他似乎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奇怪和隐秘的力量在支持我们这群人。因为我们的思想经常在科学界中被指责为“蒙昧主义”,受到强烈的批判,被认为影响“进步”。在这场对我们“侵犯科学”的控诉中,每一位“仓库管理员”都勇敢地站出来发声,这位社会党的教研员在那天见证了一场智慧的盛宴,只能哑口无言,但似乎依然没有被说服。不久后,女性主义杂志《支持选择》的创始人卡洛琳·弗里斯特(Caroline Fourest)严正指控我向教会妥协,忽视了自己是彻底的无神论主义者。我的同伴们则因为很多是犹太人的原因免遭责备,指控犹太人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却没有符合既定的规则时,连思考都变得那么难,更别说被理解了。
作为对这些不理解的简短回应,几年前我就该效仿莫奈特·瓦克安写的玛丽·雪莱,“在她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呼喊……她相比透明,更偏爱阴影;相比无懈可击的理论,更偏爱不完美的存在”。玛丽·雪莱在她的作品《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问世后的十年出版了《最后的人》。莫奈特·瓦克安也是在她的《弗兰肯斯坦:理性的疯狂》这本书出版的十年后,出版了《占据生物》。这两部作品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玛丽·雪莱要写这两本书,并了解这两位女性。她们讲述的故事虽然不同,却拥有类似的敏锐的直觉。
在《占据生物》中,莫奈特·瓦克安有史以来第一次书写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并且表明:“在要求唯一理智来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同时,法国大革命标志了一种传播链中前所未有的决裂。科学堕入了这个巨大的裂缝中。”她再次提到了她早在十年前就在她的《弗兰肯斯坦》中所提到的人工受孕的制造者们,“那些在战时或战后不久出生的研究者,往往是激进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试想他们怎么可能研究出一种最疯狂的优生学工具?这与他们最珍贵的理想相悖,岂不是一种对他们命运的重复的嘲笑?”她还在书中回答道,“与这项技术一起出现的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是关乎整个西方世界的事件……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家,还有参与的个体,这场‘危机’让他们完全不知所措”。这样的分析并没有赦免研究者的科学义务,正如公民科学基金会所写的:“每个人的责任与他的财富、权力和知识成正比。不花任何力气与他人交往,却以自己无能为名;不努力地去获得知识,却以无知为名,都无法免除自己的责任。”然而,这并没有让我们这代人不去创新,人民就如同决策者,只要研究者能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们一定也能达成共识。《占据生物》带来了一种迷人的光芒,不仅仅解释了“最尖端科学中出现的最古老的迷惑”这种现象,同时也揭示了玛丽·雪莱写这部小说的原因,还有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及其所造生物行为的意义:“可怕的事并不存在于知识中……而存在于由对知识的渴望产生的冲动所带来的惊人的力量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通过创造自己的生物来理解自己,揭开他自己身上的秘密。”
我必须承认,在阅读和重读莫奈特·瓦克安的作品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在书写事实,并且比那些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专业性所做出的数据、曲线和图表更加具有说服力。首先,我和她在一些概念上达成了共识,例如关于“理性的疯狂”,而这些概念被我的同事们所唾弃。还有“本质的研究”,它通常是控制欲的“遮羞布”,还有“生育计划”,不过是对代加工婴儿的过度辩白,为了实现一切可能性而拒绝限制,以治疗为借口来担保人类实验的继续,还有为了让人类继续存在,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的相异性……
但是,如果这些观察可以体现生物医学的方向,仅仅做出这些方向的解释是不够的,也因为如此,“仓库管理员们”,尤其是莫奈特·瓦克安的培育幸运地使这些简单的证明变得复杂并且符合医学的进步,正如解开了“暗中连接着命运和无意识的纽带。在这个角度下,弗兰肯斯坦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一个有先兆的梦”。然后,在一场世界级的人工助孕医学会议上,作者看到走廊上豪华的展台,便写下了这样的话:“突然间,注射器似乎太靠近脆弱的黏膜,工业似乎太靠近科学,而无意识则太靠近市场”……我非常理解她!
在《最后的人》中,玛丽·雪莱提到了12世纪初的一场大瘟疫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对此,莫奈特·瓦克安评价道:“这象征着玛丽的孤独,同时也是一部治愈她的小说,使她变得不那么难受。”她认为,玛丽应该是在自问:“罪恶到底是人性之外的东西还是人生来就有的?”她还说,事实上这是一种“看不见听不着的、深藏在内心的罪恶”。瘟疫是《最后的人》的主角,是在写《弗兰肯斯坦》后(1816)不久,对一场在19世纪上半叶横扫欧洲的霍乱的模糊记忆。彼时,玛丽的心理处于一种更加戏剧化的状态,更甚于她的灵感喷发。书写《弗兰肯斯坦》时:在经历了她身边发生的如此多的死亡、流产之后,她又因为丈夫疾病性的幻想症焦虑不已。有一次,雪莱在梦中要掐死她,瓦克安评价道,这恰似书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与伊莎贝尔度蜜月时,“那个怪物要杀死伊莎贝尔的那一幕”。然后就有了雪莱在暴风雨中悲剧性的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孤独,于是她开始狂热地书写《最后的人》。瓦克安写道,“自索福克勒斯以来,鼠疫是所有诅咒的范式:那是对人类的欲望和暴政,还有无法超越的矛盾的诅咒。”而玛丽在《最后的人》里的游荡,“是人类性欲最基本的缺陷,这种无法避免的不协调由爱和创造的力量造成,但同时,也有重复和毁灭的因素在里面”。这种重复和毁灭已经在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周围的人中实现(他的弟弟、朋友、密友,接着是他的妻子都被他创造的怪物所杀害),在《最后的人》里,则毁灭了整个人类。从《最后的人》中,瓦克安得出了玛丽在《弗兰肯斯坦》中所暗示的内容,这“是对一个问题不懈的追问,是对一种可能未来的预兆……在现代的曙光中,她写给我们,她写的也是我们”。
甚至在开始提笔写《弗兰肯斯坦》之前,雪莱长久以来的脾气暴烈的女伴和拜伦就让玛丽听到他们充满激情的对话,来让她感到确信。瓦克安想象到了玛丽的担忧:“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理性将会变成一种合理化,这个对欲望高超的掩饰,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无论是父亲们,还是产生的威胁,或者国家体制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急不可待,而且有着强大的力量和对寻找证明强烈的渴望。”然而,玛丽并不是今天那些科学主义者给她冠名的那种“反科学的蒙昧主义者”,“在她眼中,知识没有任何应该受指摘的行为。但是她赶走了那种想要以知识为借口来操控的冲动和执念……她认为最可怕的事,是在无法控制的冲动驱使下,将别人作为一种工具”。而且,这个造物的丑陋“是隐喻的,它没有展现出其与控制的关系,那是产生它的地方”。在维克多向那个怪兽妥协、应他的要求给他制造一个女伴之后,他改变了主意,毁掉了这个才刚开始做不久的作品,玛丽写道,因为他害怕两个怪兽会诞下“丑陋的后代,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莫奈特写道,因为“她知道那个怪兽是在履行欲望带来的强大力量,她在书写《弗兰肯斯坦》时就如同在写一封请求信……在将这个怪物描写成一个强迫的、被爱所困的杀人犯时,玛丽发出了抵抗象征崩塌的呐喊,这种崩塌是将他人工具化和取消相异性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莫奈特所知道的,也就是玛丽所知道的。而她们的直觉又与科学哲学家皮埃尔·图意埃(Pierre Thuillier)的所见略同。他的渊博巨著《大爆炸,西方崩塌报告,1999—2002》(La Grande Implosion, Rapport sur l’effondrement de l’Occident, 1999-2002,Fayard,1995)于莫奈特·瓦克安的《弗兰肯斯坦》出版后的几年问世,他在书中预感到这个疯狂世界的终结,并且将这个时间点预言在他早逝的1998年后不久。他在书中设想了成立于2077年的“一个研究西方文化终结的小组”,这个小组里有历史学家、人文学者和诗人,在分析这个“大爆炸”的队伍里,科学家似乎是最不够格参与的,因为他们可能是始作俑者。而这场“大爆炸”由“2002年前最终动荡前一连串的骚乱、袭击、爆破和绝望的场景”构成。在这部博学的专著中,皮埃尔·图意埃借助大量引言来表明,尽管因为我们伟大科学家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这场灾难是可预见的,但每个时期发出的警告也没有办法制止灾难的发生。“早在《大爆炸》之前,所有他想说的都已经被说了”,但是那些紧紧抓住进步主义信仰的人,“已经不再知道什么是‘文化’,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即使丢掉了灵魂,一个社会几乎可以照常运作”。而且,“一项提议,如果要被定性为是理性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命令),必须被剥夺所有的魔力、所有情感的动荡和所有幻想的力量”,这些描述与莫奈特·瓦克安在同一时期所表达的观点惊人地相似。图意埃还引用了安德烈·马尔罗的话:“尽管欧洲清晰地展现出力量,但它的夜晚既贫乏又空洞,空洞得就像一个征服者的灵魂”。在这场对西方世界衰落的审判中,皮埃尔·图意埃当然没有忘记提起玛丽·雪莱和她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她曾经试图警示西方人。他在书中写道:“当西方人自认为是造物主的时候,他们让一种新的人性出现,这种人性必定会使灵魂和心灵感到巨大的沮丧”,他还写道:“其实,他(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不过是制造出了一个低于人类的生物,这个生物在情感和精神上都是残缺的……通过这个生物工程师的失败经历,玛丽·雪莱揭示了所有社会工程项目的徒劳。她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去选择另一条路。”玛丽·雪莱在《最后的人》中的诅咒正是描写了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你们没有听到暴风雨来临时的咆哮声吗?你们没有看到云层散开,苍白、不可抗拒的毁灭正在袭击这片废土吗?…… 你们没有看见这些揭示着人类末日的征兆吗?……我们的敌人,就如同荷马笔下的灾难,悄无声息地践踏着我们的心灵。”皮埃尔·图意埃让人们注意到,玛丽·雪莱所要传达的思想得到了一些伟大人物的反馈,但并没有效果,其中有赫尔曼·梅尔维尔(他的作品《白鲸记》)还有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他谈论了“西方世界的机械性畸变”,并且将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成为“最值得敬佩的小机器人……”。图意埃把他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比较,他解释道:“就好像是那个怪物,他是通过理性被创造出来的,但却有着无法挽回的不完整,并且与真实的生活割裂。”皮埃尔·图意埃总结道,这种想要制造一个人工世界的执念会产生“最高级的怪物,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灵魂,他被控制,被这个消费社会的小小乐子所奴役”,当一个新出现的进步的怪兽以超人类主义的名义发展壮大,图意埃的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在提到纳粹为了不让怀孕的女人生产而夹紧她们的大腿时,莫奈特·瓦克安质询道:“出生不就是产生区别的初体验吗?极权主义不就是禁止区别的产生吗?”在这里,我们怎么可能不联想到体外受精?这种受孕的方式在孩子出生前,刚受孕时就“揭秘”,这是通过胚胎植入前诊断来判断身份和作选择的有利时机。还有“社会克隆”的来临,这是两种事物结合的产物:父母通过胚胎植入前诊断带来的基因选择前集中的幻景,以及文化全球化带来统一化的压力。克隆,在莫奈特·瓦克安眼中,具有“重复性完成的特征”。克隆人类技术已经可以在避免至今仍颇有争议的多莉实验的基础上随时出现,至少直到人类创造出一些我们认为是“杰出”的人类。因为,如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发明了人类试管受精的罗伯特·爱德华兹所言:“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值得被克隆的人”……
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出版之际,科学的危害还未被认真地解析,然而在人工受孕所带来的影响之后,科学的危害开始被重视。因为和现实相比,玛丽的书更多的还是被认为是一部小说,而且,在人们的想象中,创造怪兽的欲望是缺失的。也就是说,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拿去构建一个幻想中的生物,然后把每个人的“自我”掩藏在一具具陌生的肉体之下。与人工助孕法并行的,当然还有医学上的辩护,更具体的是人工助孕法可以安抚由无法生育引起的内在的焦虑。那么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与那些学习体外受孕术的“巫师”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是在他们病态的世界中,相比控制自己的故事,他们更有一种想要控制一切的欲望。
…………
雅克·泰斯达
“孕育”出法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生物学家
用户评价
“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像是一次对人类智力和创造力边界的深度探险。它并没有回避那些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的科学前沿,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剖析了其中潜藏的风险。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合成生命”和“人工生物”的讨论感到着迷。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我们正越来越有能力在实验室中“创造”生命,或者至少是模拟生命的某些基本特征。书中是否探讨了当科学家能够设计和构建具有特定功能的“人工生物”时,可能带来的伦理和社会影响?这些人工生物,它们是否拥有某种形式的“权利”?我们是否有权利用它们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比如制造生物燃料,或者清除环境污染物?又或者,当这些人工生物在设计上出现失误,或者被滥用时,它们是否会成为新的“生物武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我设想,书中会引用一些生物伦理学家的观点,以及一些涉及基因工程事故的案例,来佐证这些担忧。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对创造生命的挑战,而本书则将这种挑战延伸到了“设计”和“构建”生命。它提醒我们,在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能力时,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我们正在创造什么,以及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创造物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当这些创造物本身就具有生命的可能性。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在第一眼看到时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个标题本身就带着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和深刻的反思,让我立刻联想到玛丽·雪莱那部经典的哥特小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创造生命的恐怖故事,更是对科学伦理、造物主的责任以及人类傲慢的深刻寓言。而“当代”这个词,则预示着本书将把这种古老的警示带入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科技爆炸的时代。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将如何剖析那些在实验室里、在基因编辑台前、在人工智能算法的深邃代码中,与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野心和疏忽惊人相似的现代科学“造物”?那些被我们赋予了生命、智能,抑或是改变我们生存形态的科学成果,是否也同样潜藏着失控的风险?书中是否会涉及基因工程中可能引发的伦理争议,例如设计婴儿、克隆技术,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可能造成的颠覆性影响?又或者,它会聚焦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探讨机器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的掌控,以及在追求效率和智能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会不经意间创造出一种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驾驭的存在?我想象着作者会引用大量的案例研究、科学理论,甚至哲学的思辨,来构建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不失可读性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科学的科普读物,更可能是一部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路径进行审视和质询的深刻论述,它迫使我们停下脚步,思考“我们正在创造什么?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创造物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题目,本身就承载着一种责任感,提醒着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光明的探索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幽暗的深渊,需要我们以审慎和智慧去导航。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就像是一次深度潜水,将我带入了现代科学探索中最令人不安的深海区域。它并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提出了更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对书中关于“数字生命”和“虚拟存在”的讨论尤其感兴趣。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正越来越模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界限。书中是否探讨了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否会产生自我意识?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数字空间中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立思考和情感反应的“生命”?这种“数字生命”的伦理地位是什么?我们是否有权利去“创造”或“删除”它们?又或者,当人类意识可以被数字化并上传到虚拟空间时,这是否会颠覆我们对“生命”和“死亡”的定义?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作者的论述,可能使其变得触手可及,甚至迫在眉睫。我猜测,书中会引用哲学家的观点,以及科幻作品的启示,来探讨这些前沿问题。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究,而本书则将这种探究延伸到了数字时代。它提醒我们,在创造更高级的智能和更逼真的虚拟世界时,我们是否也在重新定义“存在”本身,以及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跨越科学、哲学和伦理边界的深刻思考,让我对这本书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用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将我拉入了一场关于人类创造力与责任的深刻反思之中。它并没有回避那些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的科学前沿,反而以一种近乎解剖般的冷静,剖析了其中隐藏的风险。我特别着迷于书中关于“人机协作”的边界与潜在冲突的论述。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与机器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书中是否详细阐述了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医疗诊断、法律判决、甚至是军事决策中,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当机器的判断与人类的直觉、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如果人工智能的算法中潜藏着偏见,而我们却对此浑然不觉,那么这种偏见又会如何被放大并固化到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我设想,书中会引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展示人机协作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从令人惊叹的效率提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误判,再到令人担忧的失控。作者可能将这种人机关系的演变,与弗兰肯斯坦博士与他创造物的关系进行对比,指出人类在追求效率和智能的同时,是否正在逐渐丧失对自己创造物的掌控力,甚至被它们所“异化”。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审视这种日益紧密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保持人类的主体性,避免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以一种令人警醒的方式,揭示了科学探索中那些不为人知的风险。它并没有回避那些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的科技前沿,而是以一种近乎剖析般的冷静,深入探讨了其中隐藏的潜在危险。我特别对书中关于“环境改造”和“地球工程”的论述感到着迷。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大胆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来反射阳光,或者通过生物工程改造植物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些“地球工程”的设想,听起来像是解决全球性危机的救星,但作者是否深入分析了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比如,平流层气溶胶可能对臭氧层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或者大规模的基因改造植物可能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我设想,书中会引用一些环境科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这些技术的发展方向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是积极拥抱,有些则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作者可能将这些大规模的环境改造计划,与弗兰肯斯坦博士试图控制自然、创造生命的野心进行类比,指出人类在试图“修复”或“控制”自然时,是否正在扮演着一个傲慢而危险的角色,最终可能导致比原先更严重的灾难。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审视人类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种种尝试,思考我们在试图“改造”地球时,是否也应该怀揣着敬畏之心,审慎地考量每一步行动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免重蹈覆辙,创造出我们无法挽回的生态“怪物”。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在我阅读过程中,不断地挑战着我对科学的既有认知。它并非是一本简单地歌颂科学成就的读物,而是以一种更为审慎和批判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科学发展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阴影。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基因编辑技术和生命改造方面的论述。CRISPR-Cas9技术的出现,无疑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修改生物体的基因组。然而,这种能力也伴随着巨大的伦理困境。书中是否详细阐述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风险,例如可能造成的永久性遗传改变,对未来世代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公,比如“基因富豪”和“基因贫民”的分化?作者是否深入探讨了“设计婴儿”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行为对人类多样性和自然进化进程的潜在威胁?我猜测,书中可能引用了一些科学家的观点,他们对此技术的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意见,有些是积极拥抱,有些则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种多角度的呈现,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复杂的问题。弗兰肯斯坦创造生命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对自然的僭越,而现代基因编辑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在拥有改变生命蓝图的能力时,更需要怀揣着敬畏之心,审慎地考量每一步行动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免重蹈弗兰肯斯坦的覆辙,创造出我们无法控制的“怪物”,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社会形态上的。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如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迪,将我引入了对现代科学发展方向的严肃反思。它并未止步于对技术成就的赞颂,而是以一种近乎批判性的视角,揭示了科学探索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阴影。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数据独裁”和“算法霸权”的论述感到着迷。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我们正在生活在一个被算法深刻塑造的世界。书中是否详细阐述了当算法成为信息筛选、内容推荐、甚至社会决策的主要驱动力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当算法的背后潜藏着设计者的偏见,或者仅仅是追求效率而牺牲了公平性,那么这种“数据独裁”的模式,是否会悄然侵蚀我们的自由意志,甚至改变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我设想,书中会引用一些社会学家、传播学者的观点,以及一些关于社交媒体算法操纵的真实案例,来佐证这些担忧。作者可能将这种对数据的过度依赖和算法的无处不在,与弗兰肯斯坦博士试图通过科学掌控一切的野心进行类比,指出我们在追求智能化和便捷化的同时,是否正在无意识地将我们的生活交给一套我们不完全理解、甚至无法质疑的“系统”掌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审视我们与数据和算法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拥抱科技便利的同时,保持人类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避免成为被算法所“异化”的个体。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的光怪陆离。它没有停留在技术本身的介绍,而是深入探究了科学背后潜藏的伦理困境和哲学思辨。我对书中关于“人类增强”和“后人类主义”的讨论尤为着迷。随着生物技术、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于“改造”人类自身,使其拥有超越自然极限的能力。书中是否探讨了诸如通过基因编辑、脑机接口、或者生物制药来提升人类的智力、体能、甚至是寿命的各种可能性?这些“人类增强”技术,在带来巨大希望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担忧。它们是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创造出“超级人类”和“普通人类”之间的鸿沟?“后人类主义”的思潮,是否正在挑战我们对“人”的传统定义,甚至预示着人类本身的消亡?我设想,作者会引用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例如尼采、哈贝马斯等,来探讨这些前沿理论。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对创造生命的挑战,而本书则将这种挑战延伸到了改变人类自身的边界。它提醒我们,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时,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我们正在追求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不再完全是“人类”的未来,以及这个未来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存在的挑战。
评分“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仿佛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现代科技发展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光影。它并未止步于对单一技术的介绍,而是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揭示了人类在追求科学进步过程中可能走向的歧途。我特别对书中关于“不可预测性”与“科学失控”之间的辩证关系感到着迷。作者很可能深入探讨了许多前沿科学领域,例如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甚至量子计算,这些技术在带来巨大潜力的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书中是否分析了这些技术在研发初期,科学家们可能并未完全预见到其长远的应用后果,例如纳米技术可能对环境和生物体的潜在危害,合成生物学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或者量子计算的出现将颠覆现有的信息安全体系。这种“未知”的风险,正是弗兰肯斯坦故事中,主角对自身造物的无知和疏忽的现代翻版。我设想,书中会引用大量的科学界内部的争论和反思,以及一些历史上的案例,来佐证科学发展并非一条坦途,而是充满着诱惑与危险的迷宫。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关于科学本身,更是关于我们如何与科学共存,如何去驾驭那些我们创造出来的强大力量。它迫使我们思考,在拥抱科学带来的便利与进步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建立起更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确保科学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福祉,而非成为我们自身的掘墓人。
评分读完“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这本书,我脑海里萦绕着一股复杂的情绪,像是被一种既敬畏又担忧的思潮所裹挟。作者并没有回避科学探索中最令人不安的那些角落,他以一种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了那些在追求突破和进步的过程中,可能偏离了人类福祉轨道的科学项目。我特别被书中对于“智能”定义以及人造智能潜在威胁的探讨所吸引。我们孜孜不倦地试图模拟、甚至超越人类的智慧,但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意识”的本质?在构建越来越复杂的算法和神经网络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我们无法预测的力量?书中可能对那些被过度依赖、甚至被赋予决策权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在金融市场、军事防御、医疗诊断等领域,一旦出现算法的错误或偏见,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作者巧妙地将这些现代科学的困境与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悲剧进行了类比,提醒我们,即使是最纯粹的科学动机,也可能因为缺乏对后果的深思熟虑而导向毁灭。书中关于“意图”与“结果”之间鸿沟的论述,让我印象深刻。科学家们可能怀揣着拯救世界、改善人类生活的初衷,但他们的发明在实际应用中,却可能被滥用,或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正如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在被抛弃后才走向了复仇。这种对科学的双刃剑效应的深刻洞察,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敬意,它不仅仅是在描述科学,更是在警示我们,在科学的狂飙突进中,人文关怀和伦理审视是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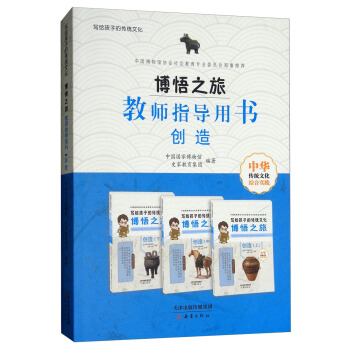
![我们的世界(套装共2册)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49575/5af5555aNec4b4e4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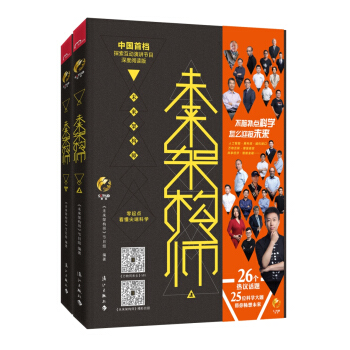
![揭秘草原动物 [La savan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55211/5b0275e6N0b0bde3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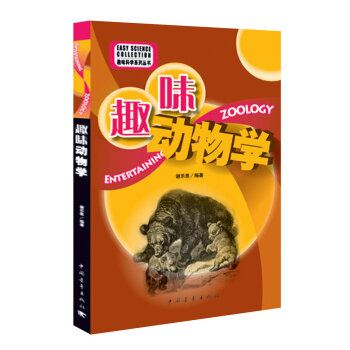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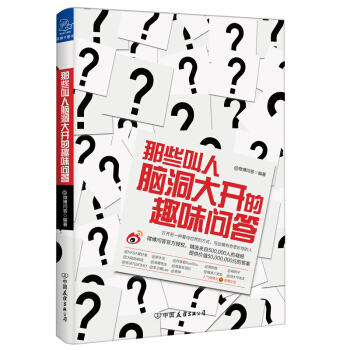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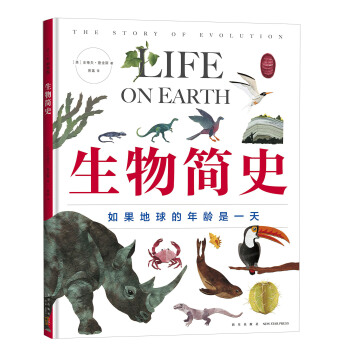
![听昆虫讲故事/动物王国大探秘 [5-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65918/5b07a837N2e5ce6b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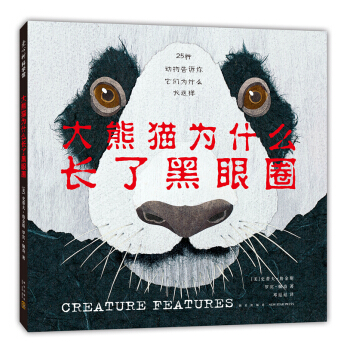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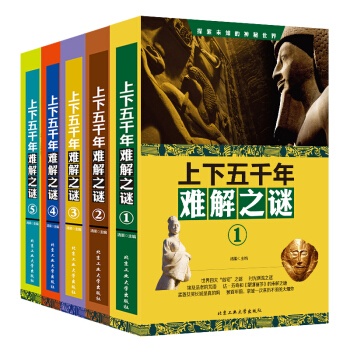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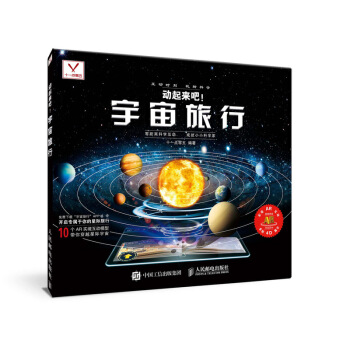
![DK有趣的科学系列:有趣的化学-这就是元素(精)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74006/5b149eccN6d6173b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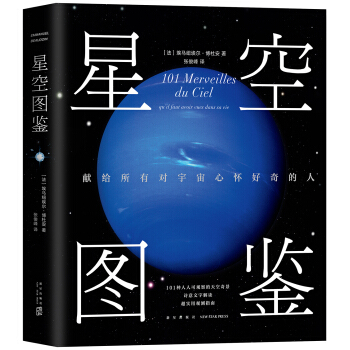
![地球简史(绘本版):地球46亿年的起源和演化 [3岁以上]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77592/5b18db5dNc892b141.jpg)
![中国历史地图 [3-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77634/5b1f2b2eN3817f8c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