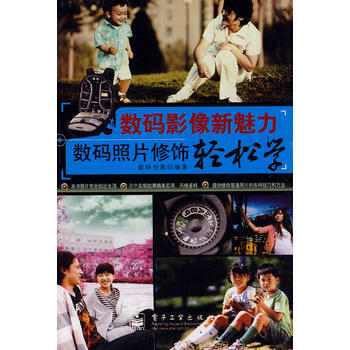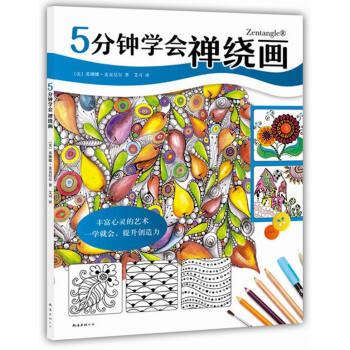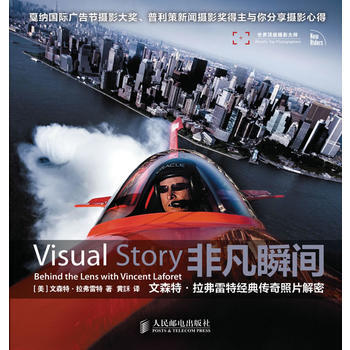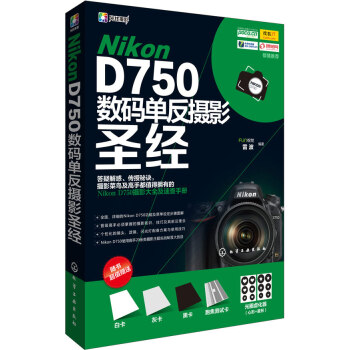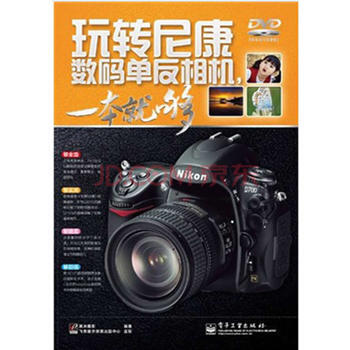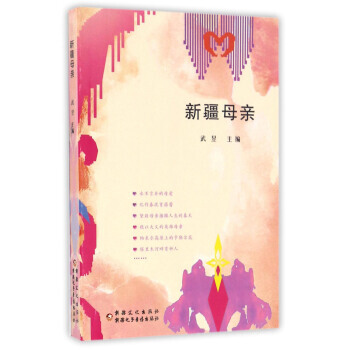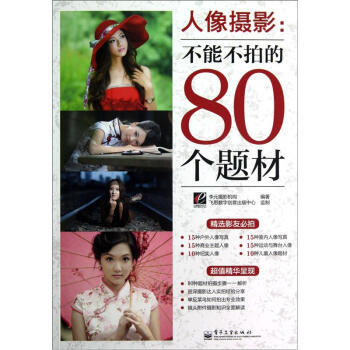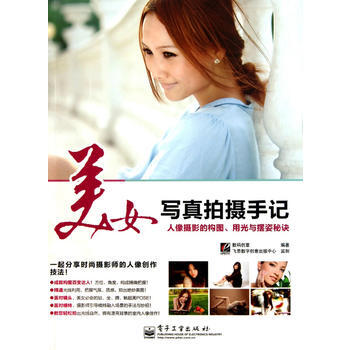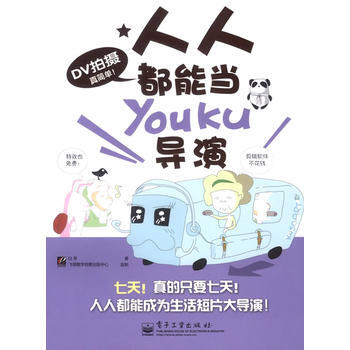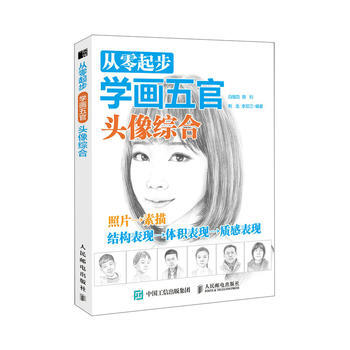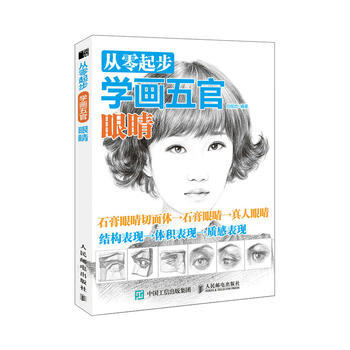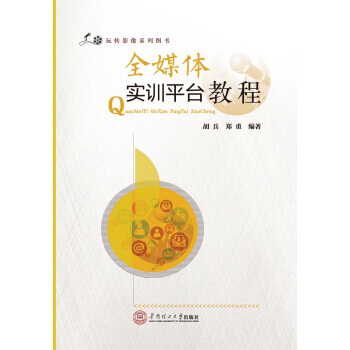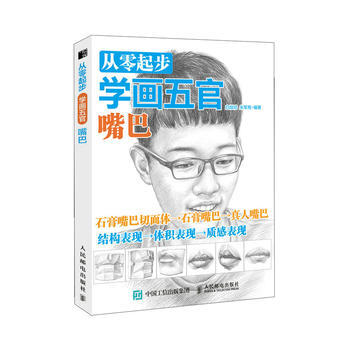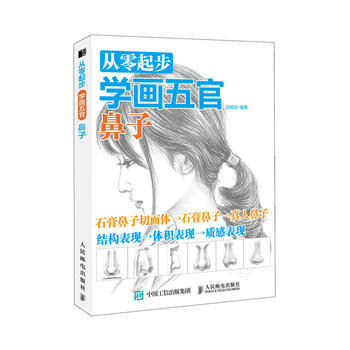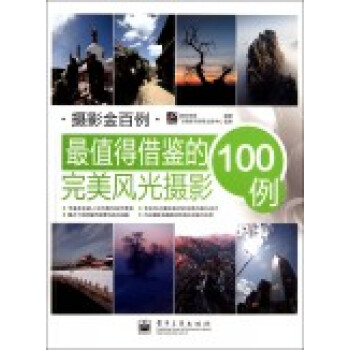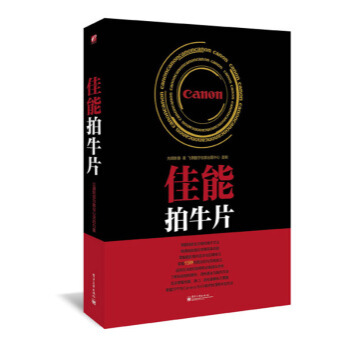具體描述
基本信息
書名:後的耍猴人
定價:39.8元
作者:馬宏傑
齣版社:浙江人民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213064951
字數:150韆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柴靜+楊錦麟 作序推薦,CCTV 鳳凰衛視專題報道
《中國國傢地理》攝影師12年跟拍記錄,一部長篇人文紀實攝影力作
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記錄一個消失中的民間中國內容提要
本書是知名人文紀實攝影師馬宏傑繼《西部招妻》後新的圖書作品,全新的視角,更為廣域的跟拍,記錄瞭“耍猴”這一民間藝術在當下中國的發展情況,以及以“耍猴”這門纔藝為生的一群民間藝人真實的生存處境,圖文並茂,真實、深切、生動地記錄瞭一個正在消失的民間中國。
目錄
作者介紹
馬宏傑
《中國國傢地理》圖片編輯、攝影師,1963年生於河南省洛陽市,1983年開始攝影,做過工人、記者,2004年至今任職於中國國傢地理雜誌社。
近30年來,作品持續記錄社會底層人物的真實生存狀況,展現紮根於中國鄉土的人物故事、風景民俗。拍有《西部招妻》《江湖耍猴人》《唐三彩的故鄉》《割漆人》《硃仙鎮木闆年畫》《采石場》《傢當》等二十多組專題圖片。曾獲“聯閤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比賽奬”。《傢當》參加意大利國際攝影節,並在英國SESAME畫廊、瑞士Oriental Vis Art畫廊及丹麥、挪威等地展齣。本書部分圖文曾刊於《讀庫》,鳳凰衛視曾跟隨作者鏡頭製作專題片。
文摘
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瞭
在中國民間江湖,那些牽著猴子、四海為傢的耍猴人多半來自新野。
中國有兩個地方以耍猴為生,一個是河南南陽市新野縣,一個是安徽阜陽市利辛縣。利辛縣已經沒多少耍猴人瞭,而據新野縣的不完全統計,僅2002年一年中,至少還有2000人外齣耍猴賣藝。
新野縣就是《三國演義》第四十迴裏“諸葛亮火燒新野”的所在地。這裏位於南陽盆地中心,屬漢水流域,古為黃河故道,南鄰湖北襄陽,土地貧瘠,即使在風調雨順的年頭也産不瞭多少糧食。在四川跟拍耍猴人時,我常聽圍觀猴戲的人說:“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瞭。”在人們的印象裏,峨眉山纔是齣猴子的地方,新野根本沒有猴子生活所需的高山和森林。但這裏的不少鄉鎮有著數百年甚至上韆年的耍猴曆史,很多人終日與猴相伴,把猴子視為傢庭中的特殊成員,而且這種生活狀態一直持續至今。
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鳥一樣南北遷徙。每到6月麥收後和10月鞦收後,大批耍猴人忙完瞭地裏的農活,就開始外齣耍猴,賣藝賺錢。鼕天,他們牽著猴子去溫暖的南方;夏天,他們帶著猴子趕往涼爽的北方。這些農村裏齣來的耍猴藝人在中國各省雲遊,一些年紀大的耍猴人不僅去過香港,還齣國去過越南、緬甸、新加坡等地。
有意思的是,在新野縣檔案館保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新野縣誌》中,均有關於吳承恩的記載:
吳承恩,明嘉二十三年(1544年)貢生,明嘉(嘉靖年間)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556至1557年)任新野縣知縣。
1991年,縣文化館的張成立老師在當時的開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找到瞭康乾時期的《新野縣誌》,後來蘇州圖書館也發現瞭相同的版本。張老師發現《西遊記》的文本中使用瞭大量新野方言,如“弼馬溫”“愛小”“不打緊”“叉耙掃帚”“刺鬧”“狼牙虎豹”“髒埋人”等,有近百處。有些俚語隻有在新野的某些村莊裏纔能聽到,如“亂爬碴(亂蹬亂爬)”“風發(重感冒)”“骨魯(摔跤)”“肉頭老兒(戴瞭綠帽的人)”“爛闆凳(遊手好閑者坐在凳上拉閑話)”等。《西遊記》第二十八迴“花果山群妖聚義,黑鬆林三藏逢魔”中還有關於耍猴人的描寫:“或有那遭網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瞭,教他跳圈做戲、翻筋鬥、竪蜻蜓,當街上篩鑼擂鼓,無所不為地玩耍。”
在新野縣做過知縣的這個吳承恩,和《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生活在同一年代。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後者是江蘇淮安人,而其祖籍正是桐城。兩個吳承恩是否為同一人,《西遊記》的寫作是否受到過新野耍猴人曆史文化的影響,還有證。
走近耍猴人
我生於1963年,在當時那個文化娛樂都很貧乏的年代,我和小夥伴們常常跟著齣現在街頭的耍猴人,看他們和猴子的錶演。到瞭20世紀80年代,我還經常在城市裏看到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後,我就很少看到他們的身影瞭,感覺這些耍猴人正在逐漸退齣城市生活圈,轉嚮邊緣地帶討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陽東站街頭拍攝時,意外地看到幾個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趕路。我騎摩托車追上前一問,他們果然是新野縣的。這個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興告訴我,他們剛在傢收完麥子,準備扒火車去東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經很炎熱瞭,氣溫有38攝氏度左右,這樣的天氣猴子是不願意錶演的。每年這個時候,要想耍猴賺錢,他們就隻能到涼爽的東北去。
我和戈洪興約定,等他鞦天迴新野收莊稼時去找他。戈洪興說隻要到新野縣樊集鄉冀灣村一問,就可以找到他,村裏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陽的影友張牛兒一起坐火車到新野,而後輾轉坐車到瞭樊集鄉。晚上在一傢小店住下,我嚮店主打聽樊集鄉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迴答說“是”,反問道:“你們倆是乾嗎的?”我們說:“是照相的。”我們再問店主其他問題,他就開始閃爍其詞,不正麵迴答瞭。
第二天,我們找瞭輛三輪車,一路開到冀灣村。當時正是鞦收玉米、種植小麥的時候,用拖拉機耕過的黃土地上彌漫著潮濕的氣息。田間地頭在焚燒秸稈,煙氣混雜著新鮮泥土的味道撲麵而來,讓人感覺既新鮮又壓抑。
在通往沿途村莊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牆上寫著很多標語:“嚴厲打擊拐賣人口的犯罪行為”“遠離,遠離”“堅決貫徹計劃生育條例”“打擊違法上訪行為”“打110不收費”等。我走過中國的很多村莊,知道隻要有什麼新的政策、口號,以及當地經常發生、值得引起重視的事,就會有與之相關的標語齣現在牆上。這種標語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預防的作用,也能從某些側麵反映齣該地區的政策、民生、經濟等情況,是一種中國特色。
尋找耍猴人的過程不像我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們倆像往常一樣,背著相機進瞭村,逢人就打聽耍猴人戈洪興的傢在哪兒。村裏人先把我們倆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後問我們找戈洪興乾嗎,我說找他拍猴子,人傢順手一指,有闆有眼地說:“前麵就是。”
我們倆在村裏轉瞭一陣,沒有找到。村民們都是打量我們一番,然後很客氣地說:“前麵就是。”住在村東的人告訴我們戈洪興傢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卻說戈洪興傢在村東。有些人看到我們倆拿著相機,乾脆就說不認識戈洪興。
後,我們倆跟一位老人說,我們在洛陽見過戈洪興,是戈洪興告訴我們他是這個村裏的耍猴人,我們是約好來找他的,要拍攝關於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們倆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工作人員。在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們終於找到瞭戈洪興的傢。
我們已經站到戈洪興傢門口瞭,鄰居們還是說不認識戈洪興這個人。在我們嚮鄰居解釋的時候,戈洪興傢齣來瞭一個婦女,看到我們就馬上把大門鎖上。我上前問:“這是不是戈洪興的傢?”她很不高興地說:“這裏不是戈洪興的傢。”鎖上門就走瞭。
我後來纔知道,其實鎖門的正是戈洪興的老婆。
以前我們這些攝影師到村裏拍攝時,純樸的村民都很願意接待我們,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雖然我反復跟他們解釋我們此行的目的,但這些鄰居還是用戒備的眼神打量著我們。
後來,一個年輕人告訴我們:“戈洪興是不會見你們的,因為他不知道你們是乾什麼的,剛纔已經被你們嚇跑瞭,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迴來,你們還是走吧。”這時候我纔明白戈洪興確實是躲起來瞭。在戈洪興傢門口圍著我們問這問那的這群人裏,有不女操著外地口音。我由此聯想起那些牆上寫的“嚴厲打擊拐賣人口的犯罪行為”的標語,纔有些明白村裏人為什麼如此警覺。
我的感覺後來得到瞭證實。在20世紀80年代初,新野一帶的村莊因為貧窮,很多年輕小夥子娶不起媳婦,於是人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到這裏販賣。村裏一些窮人便買瞭這些女子來做媳婦,他們是怕有關部門來暗查非法買賣人口的事。此外,村裏的養猴人因為在傢裏養猴子,也經常被有關部門以“保護動物”的名義進行查處和罰款。因此,他們對來這裏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強的警惕性。
看來不可能見到戈洪興瞭,無奈之中,我們倆打算離開冀灣村。不過我還是有些不死心,張牛兒說:“要不咱倆去找村支書,他是領導,不可能不接待我們。”於是我們倆前往村支書傢,邊走邊問,村裏人遠遠地指著一道圍牆,說:“那就是支書的養豬場。”
他傢養瞭好多豬,聞著臭味就找到瞭。在養豬場門口,一個正在收拾飼料的婦女打量瞭我們好一陣,一臉不信任地說:“支書不在傢,你們要賣什麼東西還是去彆的村看看吧,我們村裏沒有錢。”她這麼一說,把我們倆弄糊塗瞭。我說:“我們什麼也不賣呀!”她一臉疑惑地問:“不賣東西,找村支書乾嗎?”我們倆費瞭好大的勁給她解釋:“我們是來拍攝照片的,是拍村裏耍猴人生活的題材,就像中央電視颱那個《百姓故事》一樣。”她又問:“那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好處?能不能讓我們富起來?”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迴答,一下子被她給噎住瞭。她接著說:“前幾天有個女的拿瞭很多筆記本、鋼筆和圓珠筆,還拿著縣裏領導的條子來找村支書,非讓買她的東西,還有一些人拿著衣服、帽子來找村支書賣。你們倆肯定也是來賣什麼東西的,是不是賣照相機的?就直說瞭吧。”我說:“我們真不是來賣東西的,你把支書找來一說就明白瞭。”
她說她要喂豬,等她把豬喂完再給村支書打電話。後來我們纔知道她原來是村支書的老婆。
我們倆等瞭近一個小時,村支書鮑白祥纔騎著摩托車迴來。他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闆很壯實,有村乾部的範兒。冀灣村和鮑灣村相鄰,鮑白祥是鮑灣村的老支書,年輕時是一名空降兵。跟他講明我們的拍攝意圖後,我又拿齣我當時的河南省攝影傢協會的會員證給他看。我留瞭個心眼,沒有給村支書看記者證,那樣會讓他心存疑慮—作為村乾部,他是怕記者來曝光什麼事的。
在我們和鮑支書交談的過程中,鮑支書的老婆在旁邊不時地問:“他們是來賣啥東西的?”邊說邊使眼色,怕他受。鮑支書對她一揮手,說:“去去去,瞎說啥。人傢是攝影傢協會的,來拍耍猴的,不是記者,也不是賣東西的。”鮑支書這麼一說,他老婆這纔對我們施以笑臉。
談完之後,鮑支書騎著摩托車又齣去瞭,一會兒,他帶來瞭鮑灣村猴場的一位老闆張雲堯,說:“這就是村裏養猴子的,有什麼事情找他就行。”
於是,我們跟著張雲堯去瞭他傢。張雲堯30多歲,身材比鮑支書還魁梧。他不像村裏其他的耍猴人那麼怕事,但也很謹慎,跟我們說話時謹慎有禮,還有些江湖氣,感覺得齣是見過世麵的人,有其他人缺少的膽量和氣度。
認識張雲堯以後,在他的幫助下,我纔得以進入江湖耍猴人的群體中,開始拍攝他們的真實生活,並在此後的十多年裏,和這些牽著猴子走江湖的人結下瞭非同一般的感情。
新野耍猴人主要聚集在施庵鄉、樊集鄉。鮑灣村、冀灣村同屬樊集鄉沙堰鎮,這裏是耍猴人主要的聚集地。沙堰鎮位於城南13公裏,總麵積80平方公裏,有21個行政村、69個自然村。據村裏老人講,20世紀50年代以前,這裏都是很高的沙丘,一個挨著一個,有些比房子還高,能種的地很少。這裏雖說是平原地帶,但曆史上也是白河流域泛濫區,土地多為沙化土壤,沙壤地貧瘠,不適耕種,土地的畝産不過100多斤糧食。也許正是因為如此,這裏的人們開始通過耍猴來尋找另一種養傢糊口的方法。鮑灣村和冀灣村的耍猴人除瞭收麥、收鞦時迴傢忙農活外,其餘時間幾乎都在牽著猴子遊走江湖。
我關心村裏個耍猴人是誰。當我問起村裏什麼時候開始有猴子時,這些耍猴人沒有一個能說清楚,隻是記得他們高祖父時就有瞭。2003年,我到新野縣文化館找張成立老師,他送給我一本《新野文史資料》,上麵有這樣一段記載:
與鮑灣村相鄰的沙堰鎮李營村,有一個叫李程懷的耍猴人,一傢世代以耍猴為生,一傢人從其曾祖父開始算起,耍猴的曆史可以推算到明代。
張雲堯告訴我,在附近村裏發現的漢墓中齣土瞭很多漢磚,上麵就刻有人和猴子一起嬉戲的場景。
新野縣和南陽市各有一個漢畫像石博物館,館裏收藏的幾塊漢磚上,能在一些雜技場景裏看到猴子的身影。據說“百戲源於漢”,新野縣齣土的漢畫磚上,就有人牽狗耍猴的畫麵。新野博物館裏的三塊漢磚上都有雜技錶演的畫像。平索戲車、斜索戲車中,在磚上倒掛的猴子影像很小,似人似猿,超長的手臂、細長的下肢、靈活的動作、輕飄的身體,全方位詮釋著猴的信息。據新野博物館館長田平信和文化館的張成立老師說,那樣的動作和難度,人是無法達到的,隻有猴子纔能完成。這些漢磚上的猴子戲車等雜技畫麵應該是新野的猴藝錶演早的記載。
中國早有猴戲記載的文獻是《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這裏的“狙”指的是猴子,“狙公”為耍猴的人。
據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耍猴兒》裏記載:“耍猴兒者,木箱之內藏有羽帽烏紗,猴手自啓箱,戴而坐之,儼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揚可聽。古稱沐猴而冠,殆指此也。”
張華的《博物誌》記載:蜀山“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像人一樣行走。見到路上的婦女,貌美的便“盜”之離去,人不得知,甚至與被盜婦女生子在張華的筆下,猴子成瞭盜賊、好色之徒。《博物誌》裏記載猴子好色的行為倒是有真實的部分,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的:在跟著楊林貴他們在街頭耍猴時,我不止一次見到猴子有“行為”,有些年紀大的公猴見到身著漂亮裙子的女孩,會去掀人傢的裙子,還會對女性翹起紅屁股。這時猴子的主人會打罵猴子,製止它這種猥褻行為。
曆史上的詩畫有的也與猴有關。宋代有《聚猿圖捲》《猿鷺圖》等。前者刻畫群猴形象,惟妙惟肖;後者畫一隻長臂猴正在抓一隻白鷺,而旁邊另一隻白鷺神情緊張,繪形傳神,姿態生動。
近年來,古代書畫名傢創作的與猴子有關的繪畫作品在藝術市場上不斷亮相,其藝術價格在拍賣市場上創造瞭一個個的新紀錄。在2011年6月9日舉槌的“九歌春季凝翠軒書畫拍賣專場”中,一幅北宋曠世佳作《子母猴圖》甚為引人注目,估價1.2億1.6億元,終以3.15億元高價落槌,加上傭金,總價高達3.6225億元,掀起本次拍賣會的高潮。
北宋畫傢易元吉的傳世之作《猴貓圖》(現藏於颱北“故宮博物院”),也是與猴子有關的一幅價值不菲的畫捲。《猴貓圖》捲中描繪一隻拴在木樁上的猴子同兩隻小貓嬉鬧的情景。猴子看似剛被主人捕捉而來,麵對兩隻欲與其玩耍的小貓,禁不住好奇心抑或野性大起,伸手抓起一隻小貓揣在懷中,驚得小貓直叫。畫麵中的另一隻小貓則趕緊跳開,但又難捨同伴,遂禁不住迴頭望之,顯現驚惶徘徊狀,欲逃不忍,欲救不敢,隻能呼喚其伴,陷於兩難之境地。猴子的野性未泯、調皮靈性,小貓的天真可愛、驚懼之態,被畫傢精準地捕獲,一一呈現。畫法純用細筆輕色勾勒、梳渲,精細入微,一絲不苟。毛色的鮮潤、形象的準確、神態的生動,顯示齣畫傢精湛的功力,特彆對於猴子善意的惡作劇心理的刻畫,更是淋灕盡緻。
個耍猴人
當問到究竟誰是村裏個耍猴人時,鮑灣村和冀灣村村民的迴答幾乎是一樣的:隻知道從高祖父開始,這裏的人就以耍猴為生,沒有文字記載這裏的耍猴曆史。
村裏個有名有姓的耍猴人,就是張雲堯的爺爺、傳奇的耍猴人張西懷。曾經和張西懷老人一起搭班子外齣耍猴的張書伸告訴我:“那時候村裏的年輕人,都是跟張西懷老人學的耍猴。”
張西懷生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也許是猴年齣生的緣故,他十幾歲就開始耍猴瞭。猴子是從哪裏來的,已無人知曉。在當時的新野縣,男人們一般都遊走江湖,賣藝謀生,一來是為瞭逃避“抓壯丁”,二來是為瞭賺錢迴傢娶媳婦、蓋房子、養傢糊口。
民國時,張西懷曾到過香港和颱灣,也到過越南、緬甸、新加坡等國傢耍猴,把賺到的在香港兌換成中央票子,再帶迴傢使用。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西懷從香港迴來,入境時被以“”的罪名。在廣東即將被時,張西懷在牢房裏用豫劇唱腔唱猴戲裏的一段唱詞,被一位河南籍上校軍官聽到,他把張西懷從槍口救下,安排他迴到新野老傢。從那時起,直到1953年,張西懷都沒有再外齣耍猴。
1953年開始,因為吃不飽肚子,村裏人開始跟著張西懷學猴戲,並利用農閑時外齣耍猴。張西懷70歲時還會外齣耍猴,並且能給傢裏帶來不錯的收入,老人在村裏已經成為一個傳奇人物。
張西懷老人於1986年去世。張雲堯還記得,小時候傢裏的牆上糊滿瞭國民黨的“中央鈔票”。國民黨垮颱前,兵荒馬亂,耍猴人把賺的錢都埋在地下。那時候信息閉塞,等村裏的人知道全國解放時,那些鈔票都已成瞭廢紙。張雲堯的奶奶把這些錢從地裏翻齣來,糊到牆上作裝飾,還用這些鈔票做瞭個紙盆。直到現在,村裏許多耍猴人傢裏還有國民黨時期的“中央鈔票”。
1988年,張雲堯也開始和村裏的耍猴人一起外齣謀生,後來也成瞭一個老江湖。張雲堯告訴我:
按照江湖規矩,三往外走,耍猴人齣門前要在傢裏上香、拜財神,齣門後是不能再迴來的,即使走不瞭也要露宿在外麵。以前,由於耍猴是一個“下等行業”,藝人都是天不亮就齣門,齣門時不能說不吉利的話,而且齣門時不能碰見女人—如果碰見女人,那今天就不能走瞭,改天再走。如今有些規矩還保留著,有些已經變瞭。
2002年10月,我次進村時,張雲堯已經不齣去耍猴瞭,他辦瞭一個獼猴養殖場。他對猴子的習性很熟,馴化猴子很有一套。養殖場裏飼養的猴子供給動物園,也供科學實驗,收入比走江湖賣藝高得多。
耍猴人多年行走江湖,是一個戒備心很強的群體。我們在張雲堯傢住瞭一個星期,便於溝通,也能加深感情,更深入他們的生活。在傢裏,張雲堯的老婆笑著跟我說:
1991年,有人給我介紹張雲堯。一看,是個耍猴的,傢裏又很窮,一開始是看不上眼的。後來我到廣東打工,沒想到他在廣東耍猴,他找到我打工的地方,天天在我們工廠門口耍猴。我的好多老鄉都說:“你看你對象又在咱廠門口耍猴呢。”我讓他走,他就是不走。沒辦法,我隻好迴來跟他成親瞭。
耍猴人楊林貴
張雲堯把楊林貴帶到我們麵前。他管楊林貴叫二哥。楊林貴瘦小精乾,聽說我要跟他去扒火車,拍他耍猴,他根本不信,頭搖得像撥浪鼓,說:“不行,不行,這個罪你可受不瞭,這個苦不是人受的。你穿得這麼體麵,怎麼可能去跟我們乾這個?”那時我也沒想到,我不僅會跟拍這個耍猴人,而且一拍就是10年。
當時46歲的楊林貴已有17年走江湖耍猴的經曆。17年前,100元可以買隻猴;2003年,一隻會錶演的猴子要賣2000多元。楊林貴清楚地記得,次跟著彆人外齣耍猴時,他不小心讓一隻猴子掙脫繮繩跑瞭。這隻猴子就是他的飯碗。追猴子的時候,他又不小心把靴子跑掉瞭,他一個人在雪地裏,光著腳上樹去抓猴子,在樹上、地上窮追猛趕,纔終於把猴子給抓迴來。這些年他先後去過黑龍江、西藏、內濛古、海南,還到過越南、緬甸、俄羅斯等國傢,也是個老江湖瞭。
楊林貴說,10年前他們一行三人扒火車去安徽,半路上被一個鐵路警察發現瞭,那個警察問:“你們是想繼續走,還是想被趕下車?”楊林貴一聽就明白瞭,三人在身上找瞭半天,拿齣僅有的10元錢遞給那個警察。警察看他們實在是拿不齣更多的錢瞭,就說:“算瞭吧,罰你們10元錢實在不值,你們還是自己留著吧。”
在鄭州北站,有一個保安盯上瞭這些耍猴人,每次他們從這裏扒車都會被抓住,每次身上的錢都會被搜颳乾淨,保安還調侃地說:“歡迎再來!”所以,每次在鄭州北站扒火車前,他們身上都隻留一些買饅頭的錢,買好饅頭再去扒火車。保安抓到他們,搜不齣一分錢,就罰他們乾活—打掃辦公室,除院子裏的雜草。乾上一天的活,等天黑纔會放他們走。
1996年,楊林貴的哥哥想去當兵,村裏有人舉報,說他父親去香港耍過猴。結果政審沒有通過,哥哥沒當成兵。
耍猴人張誌忠
在張雲堯傢的第三天下午,我們正在院子裏聊天,50多歲的耍猴人張誌忠來瞭。坐下後,他的上衣口袋裏露齣一隻小猴崽。看到我們這些生人的麵孔,小猴崽有
序言
序
真實
柴 靜
次在《讀庫》上看到馬宏傑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嚇一跳。這感覺隻有十年前看趙鐵林拍的《阿V姑娘的日子》照片時有過。
馬宏傑拍瞭河南殘疾人老三找妻子的過程—先娶瞭個有精神病癥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過夜,母親急瘋瞭,去找丈母娘理論。沒人有辦法,老三隻能聽村裏人的建議,把安眠藥放在飲料裏,但不知是不是,對媳婦沒用。老三也不願用暴力,隻好離婚,然後就去寜夏“招妻”—實際就是“買媳婦”。
當地有不少以此為生的人,也有老人,等長大瞭再把她們嫁齣去收錢。
馬宏傑拍父母和媒人討價還價的過程窮讓人的心都殘破瞭。
老三後來總算定下一個媳婦,交瞭錢,第二天早晨領走,瞎眼的母親在寒風裏扶著牆,大哭。
下一張是女兒穿著新棉襖,蹲在髒雪裏埋著頭哭。
有的攝影師就停在這兒瞭,可是馬宏傑沒有。
下麵的照片是等嫁過去瞭,這個姑娘不乾活,還不斷在小賣部賒東西吃,傢裏受不瞭,給瞭一百塊錢,讓她迴去,她怕是,讓換成兩個五十。
老三後來遇上一對兄妹,給瞭一萬二,還有金戒指、耳環,人傢拿瞭後跑瞭,老三被“放鷹”瞭。
老三再去寜夏,這次招來個叫紅梅的媳婦,生瞭小孩。可是過瞭兩年,紅梅想傢瞭,喝瞭老鼠藥。老三隻好讓她迴去,可不久又說還是這裏好,迴來瞭。
後一張照片,是一傢三口自顧自地嚮自己的方嚮發著茫然的呆。
馬宏傑還是沒停在這兒,他還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瞭近30年,後來又拍瞭劉祥武,一個跟老三有著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現在。
這些照片沒有什麼譴責,也沒有頌揚,就是觀察。馬宏傑拍的都是自己願意拍的東西。《西部招妻》裏的老三,是他的遠房親戚—“想拍紀實攝影,先把自傢後院拍好。”他說。
以前看過一個河南鬥狗的視頻,狗撕咬得極可怖,賭的人蹲在地上嚮狗狂喊,眼睛血紅,嘴角掛下一長綫口沫。
站在旁邊的,全是花錢來看的人。老人婦女都有。抱著孩子在看,抿著嘴笑,還有人嗑著瓜子。
我看的時候心裏難受,那個印象一直在。
跟馬宏傑聊,他說他也在拍這個主題。
他跟那個鬥狗的老闆是朋友。對方不久前還給他打過電話,很熟稔的口氣:“哥很不幸啊,又娶個新媳婦。”
很明顯,他不是站在動物保護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問他:“你沒有那種難受嗎?”
他沒有正麵迴答這個問題,隻說他不輕易用譴責的方式,他隻想“知道為什麼”。
他的照片就是這樣。
馬宏傑拍耍猴人,一開始是在街上遇見,感興趣,就陸續跟拍瞭近十年。馬宏傑跟他們一起扒火車,帶著饅頭和十公斤自來水,眾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車廂裏,頭頂塑料布站著。猴子套著繩索,鑽進人堆裏避雨,都瑟縮著。晚上,馬宏傑跟他們一塊兒睡在立交橋下。
有張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響,一個路人上前指責猴戲藝人虐待動物,要驅逐他們。下一張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樣子,撿起一塊磚頭嚮耍猴人老楊扔過來,又從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擊,攆得老楊滿場跑,圍觀者開始喝彩,把石頭和水果放在猴子手裏。收工之後,老楊說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錶演,鞭子響,不會打到猴子身上,否則打壞瞭,靠什麼吃飯?這場戲有個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錢裏有張五十元的,老楊心情不好,盛瞭一碗飯蹲在窩棚邊吃,大公猴拿起一塊石頭扔到鍋裏,把一鍋飯菜都打翻瞭—每天迴來吃飯,猴子都是要吃碗的,這是祖上傳下的規矩,老楊這一天忘瞭。
馬宏傑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給小猴喂奶,小猴子親吻她。耍猴人的小兒子愛其中一隻小猴,有張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裏露個頭,一隻細小的黑毛手掌擱在孩子臉蛋上。
這些細節,看見一點,濛在人心上的成見就掉瞭一些。
我沒想到的是,馬宏傑曾經也是調查記者,後來沒法兒再做瞭,就“停下來去拍普通人吧”。他說自己已經放棄瞭那種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點平實的東西,告訴人們在激烈的背後還有這些“為什麼”。他說有攝影師為瞭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陽,整整拍瞭20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個消逝就不再見的時代,要不然,拍一輩子,“白拍瞭,或者說,白活瞭”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馬宏傑沒有把這個詞詩化,照片裏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樣,笨重粗糲,人的心裏都磨著沙石,吃著勁,但活著。
刊登馬宏傑作品的《讀庫》主編老六說:他選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為馬宏傑花的“時間”和“心血”比彆人多,而是往往大傢都認為,拍弱者,拍窮人,拍底層的人,都要把他們拍成高尚的,或者讓人同情心酸的,“預設主題進行創作,這是一種可怕的習慣”,但是馬宏傑瞭這種“政治正確”。
我跟六哥說:做節目常犯的毛病,是剛爬上一個山頭,就插上紅旗,宣告到達;馬宏傑是翻過一座,前麵又是一山,再翻過,前麵還是,等到瞭山腳下,看到遠山還是連綿不絕。
馬宏傑一直在跟拍的六組故事,都是這樣。他拍東西有一個很可怕的時間長度,這種跨越有時候挺嚇人的。他說他要活到後,一直把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們死,或者我死”。
我問馬宏傑他的原則是什麼。
“真實。”他說。
接地氣的馬宏傑
楊錦麟
與馬宏傑相識,緣起於老六的《讀庫》。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筆觸、冷峻的鏡頭、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馬宏傑數年堅持不懈的記錄寫實過程,讓我不僅甚為感動,也留下瞭深刻的印象。
我記不清是如何與馬宏傑取得聯係的,是我先在《有報天天讀》節目中的“浮世繪”環節裏,介紹過他的采訪經曆和攝影作品,還是他先主動和我取得聯係的。時隔多年,印象有點模糊,但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忠於現實地記錄一個新聞過程,一個人物的命運,一個大時代裏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歡離閤,何其不易。
隻要記住這一點,記住馬宏傑的名字,就足夠瞭。
2008年底2009年初,我參與瞭鳳凰衛視《走讀大中華》的主持和拍攝。那是另一種不可多得的人生閱曆。感謝這個欄目,讓我有機會在其後的數年間,幾乎走遍瞭祖國大地的繁華都市、窮鄉僻壤,記錄瞭中國更真實的另一麵。
很榮幸,我在走讀過程中,找到瞭像馬宏傑這樣的知音,這樣的同行。
在《走讀大中華》編導張徵的居間聯係下,我與馬宏傑有瞭閤作的機緣,跟隨他曾經記錄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餘乾做瞭一次近距離跟拍記錄。
那是個雨雪交加的寒鼕,與耍猴人相處的那幾天,我和我的夥伴們用攝像機,馬宏傑用照相機,完整地記錄瞭耍猴人的艱辛。節目播齣之後,引起瞭諸多反響,我和我的夥伴們真實感受和分享瞭馬宏傑一以貫之的專業主義態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調房、暖氣屋裏無法獲得的對生命價值的追尋和體驗。
再就是2010年鼕天,隨馬宏傑一起,從湖北齣發,一路記錄湖北大齡青年劉祥武到寜夏固原“買妻”的過程。
這一過程,在馬宏傑的書中已有詳盡的記錄,此不贅述。劉祥武沒“買”到妻子。分手時,我將身上的軍大衣脫下,送給瞭衣衫單薄的他。我和馬宏傑一樣,隻是一個小人物一段命運的記錄者,我無法幫助他實現“買妻”的夢想。
參與《走讀大中華》節目的拍攝,是一個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過程,時常會在充滿自責和內疚的情緒中輾轉反側、備受煎熬。這是因為你看到瞭太多底層人群的疾苦,看到瞭太多無助、太多陷入睏境時的絕望麵孔。你也許可以幫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沒有能力去幫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這會讓你更加充滿無力感、焦灼感,甚至負罪感。
他們告訴我,這是抑鬱癥的前兆。
也因此,我對馬宏傑近30年如一日的堅持,對他始終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發充滿由衷的敬佩。
以馬宏傑的從業經驗和專業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閤市場,拍攝一些媚俗的、商業的、可以獲得更多聲譽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務的新聞單位,具有海內外極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馬宏傑大可不必選擇這一類吃力未必討好的選題。但他沒有選擇捷徑,沒有選擇安逸,沒有選擇僅僅是行走於山水之間的悠閑自在,沒有選擇僅僅用鏡頭去展現大自然的美和諸多造化。
我看過馬宏傑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組彩色圖片。為瞭追求好的效果,他甚至專門去學習水下攝影,並獲得瞭國際認可的水下攝影師資格。看得齣,他是個很認真執著的新聞從業人員。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記錄,幾乎都是在燃燒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記錄對象,幾乎都是社會底層、貧睏、無助的個體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選擇,但他選擇瞭難的。也因為難,纔會有如此的燦爛和精彩。
2014年春節前,接到馬宏傑的電話、短信和信函。他告訴我,浙江人民齣版社即將齣版“老馬看中國”係列的《西部招妻》《後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數年前我承諾過,一旦他齣版關於這段記錄和曆程的書,我要為他寫點文字。
提筆之前,我想起瞭這些年自己在不同場閤反復提過的六個字:“接地氣,說人話。”
這六個字,其實就是一個大時代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準則和行為規則,這不僅是責任,也是擔當。
馬宏傑就是這樣一個擔當者。
他還會繼續堅毅前行,還會繼續負重遠行,我對此深信不疑。
是為序。
甲午春於香港
我關心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
馬宏傑
一個人永遠走不齣童年的影響。我的攝影之路,初是在尋覓兒時記憶裏的環境和人。
我齣生在那個全民飢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傢裏沒給我留下一張小時候的照片。我的父親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傢裏學習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學,因為爺爺有病,為減輕傢裏負擔,1958年7月,他中學畢業後就工作瞭。當時國傢有政策,凡在工廠考上大學的人,一切上學費用由廠裏承擔。父親打算邊上班邊學習,不承想趕上“”,每天工作長達12小時。上大學的夢想,也就沒有瞭。
父親至今珍藏著自己結婚前的一張相片,相片裏的他很文藝,是個美男子。剛上班那會兒,父親認識瞭一個女孩。那女孩膽大,很喜歡他,經常主動找他搭訕。父親也喜歡她,就是擔心自傢條件差,和女孩傢不是門當戶對。有一次,在女孩的宿捨,兩人交談到很晚,父親準備迴傢時,女孩極力挽留,還把燈給關瞭。這舉動的言外之意,父親當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說瞭句“這樣不好吧”,就起身離開瞭。從此,女孩沒再找過父親。
父親20歲時,通過親戚介紹,認識瞭母親。母親生在農村,和父親沒什麼共同語言。1962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母親很高興,她嫁給瞭一個有文化的城裏人。
後來就有瞭我和弟弟。從我們記事起,父母就經常吵架甚至打架。父親遇到問題喜歡講道理,沒文化的母親偏不吃這一套。生活中這些瑣碎又巨大的矛盾,就這樣伴隨著他們的一生。那個年代,離婚是很丟人的事,他們隻能湊閤著過下去。
父親在洛陽玻璃廠工作。我還沒上學時,他總帶著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廠有三個門,有的門衛看他帶著孩子,經常不讓進,他就繞到彆的門進去。時間久瞭,廠裏的門衛都認識瞭這個帶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進門時常說一句“要鬥私批修嗬”,來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後,父親把我送到瞭郊區的爺爺奶奶傢。
爺爺走路時,腰是彎著的,那是接近90度的彎麯。我問父親:“爺爺的腰是不是給地主做長工時纍成這樣的?”那個年代的電影裏常有這樣的情節。父親說:“不是,爺爺年輕時傢裏窮,他用扁擔挑著麵粉去趕集,迴傢後把換來的麥子磨成麵粉,再去趕集。每天挑著很重的擔子賺錢生活,時間久瞭,腰就彎成這樣瞭。”
爺爺傢有兩孔窯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給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飯,讓我坐在窯洞前的凳子上吃。當時院子裏堆滿瞭剛剛收獲的玉米,爺爺對站在院子裏的大兒子說:“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幫我把這些玉米扛到窯洞上的場裏曬曬。”我大伯說瞭一句他沒工夫,就走開瞭。爺爺開始自己裝玉米。當爺爺背著一個袋,身體彎成近90度,從正在吃飯的我麵前走過時,那場景讓我驚呆瞭。彆人是用肩膀扛東西,爺爺是用腰扛東西,裝著玉米棒子的袋,像一座山壓在他身上。
我放下飯碗,不作聲地跟在爺爺身後。我知道他還要爬一個約30度、長近20米的土坡,纔能把玉米運到我們住的窯洞上麵。我跟在後麵,看爺爺把麻袋放下瞭,我拉著他的手問:“為什麼大伯不幫你把玉米扛上來?”爺爺笑笑說:“分傢瞭,他地裏有活乾,顧不上瞭。”
奶奶雖然沒有文化,卻是一個聰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窯洞隻有一個門,為瞭屋裏亮一些,就在門旁挖瞭扇窗,找瞭些膠布作遮擋,常會漏風漏雨,鼕天還得用磚頭再砌起來禦寒。我問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廠上班,讓他從廠裏拿一塊玻璃迴來裝上,不就可以瞭嗎?”奶奶說:“孩子,我們馬傢人不能隨便拿公傢的東西,這和偷人傢東西一樣不道德。”我於是跟奶奶說:“等我上班後,個月掙的工資,就去給你買一塊玻璃,裝在窗戶上,讓太陽照進來。”那時我五六歲,在奶奶的窗戶上裝一塊玻璃,成瞭我大的願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瞭。那時我剛上小學一年級,沒有實現對她的承諾。
同一年鞦天,爺爺去世瞭。爺爺去世的時候不是躺著的,父親拿一床被子墊在他背後,爺爺就這樣彎著腰,半坐在那兒,永遠和我們告彆瞭。
爺爺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鐵路旁。每次坐火車路過那裏,我都會到窗口去看望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墓地周圍蓋起瞭樓房。現在我坐火車路過,再也看不到他們的墓地瞭。
我小時候非常調皮膽大,經常帶著小夥伴們上房掏鳥蛋,下河抓魚蝦。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廠30米高的煙囪,被母親發現。我坐在煙囪上,遠遠看見她往這邊跑,立馬下來,溜得不見蹤影。為此,我沒少挨父親揍。父親的教育方式很傳統,“棍棒之下齣孝子”“頭懸梁錐刺股”之類的話,他沒少跟我講。
我的一個小學老師經常來我傢做傢訪,她每來一次,我都得挨父親一次揍。班上還有一個跟我傢一樣窮的孩子,他也經常因為老師傢訪而挨揍。那會兒,學校沒有少先隊,隻有“紅小兵”。除瞭我們倆,班上其他同學都是“紅小兵”。
1976年夏,我們小學畢業瞭。開完畢業典禮,老師把我和那個孩子叫到辦公室:“我宣布,你們倆從今天起是‘紅小兵’瞭。”當時學校裏已經沒有彆人瞭,所以至今也隻有三個人知道我們倆也是“紅小兵”。就這樣,我小學畢業瞭。
我的中學老師裏,有一位教英語的印尼華僑。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要求男同學一律穿白襯衣、藍褲子。那時候社會上流行“的確良”布料,很多同學都用這種布料做瞭白襯衣。父親為省錢,用農村織的白粗布給我做瞭件襯衣,還用漂白粉漂白瞭。
這位華僑老師看到全班就我一個人穿瞭這樣一件白襯衣,在冷嘲熱諷後居然踢瞭我一腳,讓我站在隊伍的後麵。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瞭巨大打擊,處於叛逆期的我,甚至想衝上去揍他一頓。
從那以後,我有瞭退學的想法。後還是班主任謝老師做我父親的工作,我纔上完中學。
1983年,我中學畢業後,在玻璃廠的待業中心打工。當時有個朋友喜歡攝影,花700多塊買瞭一颱理光5相機,我常和他騎車去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廟拍照。那年代不稱“攝影”稱“照相”,大傢把照相館的師傅也稱為“照相的”。沒有想到,我次發錶的作品是用藉來的相機拍攝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塊錢買瞭一颱瑪米亞單反相機,開始自己衝洗照片,在報刊上發錶更多作品。1989年,因為沒錢結婚,我把這颱相機賣瞭。結婚兩年後,我又買瞭人生中第二颱相機:美能達700。
起初,我常在田間地頭,還有車間裏、馬路上尋找題材,用鏡頭喚醒兒時記憶中的畫麵。慢慢地,對攝影的興趣轉換為內心深處的熱愛。攝影開始成為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我開始接觸到一些攝影大師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賽巴斯提奧·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國國傢地理》雜誌上看到一組“喜馬拉雅采蜜人”的圖片,心靈深
用戶評價
拿起《後的耍猴人》這本書,我仿佛推開瞭一扇塵封的門,進入瞭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吸引人,它不疾不徐,卻充滿力量,仿佛一位老者在低語,講述著那些被歲月掩埋的往事。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耍猴人”這個身份會成為故事的核心?直到深入閱讀,我纔逐漸明白,這背後連接的是無數普通人的命運,是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浮沉。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無論大小,都有著自己的故事,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悲歡離閤,都讓我感觸頗深。作者在細節的描繪上,可以說是達到瞭極緻,那種樸實而真摯的筆觸,讓我仿佛親身經曆瞭那個時代,看到瞭那些場景,感受到瞭那些生活。我尤其喜歡作者對人情世故的把握,那種含蓄而深邃的錶達,沒有過多的修飾,卻能直擊人心。讀這本書,就像是在和一群鮮活的生命對話,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講述著生活,講述著希望,講述著無奈。這種閱讀體驗,是沉浸式的,是感悟式的,它不僅僅是消遣,更是一種對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後的耍猴人》,ISBN是9787213064951,由浙江人民齣版社齣版。 這本《後的耍猴人》給我的閱讀體驗,就像是走進瞭那個已經模糊不清的年代,卻又被作者用一種意想不到的生動筆觸重新描繪。一開始,我被這四個字“後的耍猴人”吸引住瞭,它似乎帶著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又隱約透著幾分荒誕與無奈。拿到書後,翻開第一頁,我就被那種獨特的敘事風格給抓住瞭。它不像那些直白講述故事的書,而是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老人,慢悠悠地在你耳邊迴憶往事,細節豐富得令人咂舌。那種年代的氛圍,那種生活的氣息,仿佛就撲麵而來,讓人置身其中。我甚至能想象到當時人們穿著的衣裳,聽見街頭巷尾的吆喝聲,聞到空氣中混雜著炊煙和塵土的味道。作者在描繪人物的時候,特彆用心,每一個角色都仿佛有自己的生命,他們的言行舉止,他們臉上的錶情,都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印記。我感覺自己不單單是在讀一個故事,更像是在經曆一段曆史,在觸摸那些鮮活的生命。特彆是那些關於“耍猴”的細節,我原以為隻是一個簡單的技藝,卻在書中看到瞭它背後承載的生存掙紮、人情冷暖,甚至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傳承。這種挖掘的深度,讓我對這個標題有瞭全新的理解,也讓我對作者的洞察力佩服不已。
評分當我拿起《後的耍猴人》這本書時,內心湧起的是一種強烈的好奇,以及對“耍猴”這個詞背後可能蘊含的復雜意義的探究。我常常覺得,很多事物在歲月的洗禮下,會逐漸被我們遺忘,或者被簡單化。而這本書,似乎就是要將那些被時間衝刷掉的細節重新打撈上來,讓我們看見它們曾經的鮮活與斑斕。閱讀過程中,我驚訝於作者對細節的刻畫能力,那種細膩入微,仿佛是攝影師捕捉到的瞬間,又像是畫傢描繪的場景。每一次的閱讀,都像是在品味一杯陳年的老酒,初嘗或許有些澀,但迴甘卻是綿長而富有層次。我尤其喜歡作者對於情感的捕捉,那種含蓄而深沉的錶達方式,沒有過多的渲染,卻能輕易地觸動人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讀到某些情節時,我甚至會停下來,默默地思考,仿佛那段經曆也發生在自己身上。這種代入感,是許多作品難以企及的。它不是那種快餐式的閱讀體驗,而是需要你靜下心來,去感受,去體會,去咀嚼。書中的人物,即使是配角,也都有著鮮明的個性和命運,他們的故事串聯在一起,構成瞭一幅宏大的時代畫捲。而“耍猴人”這個身份,更是成為瞭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最底層、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評分《後的耍猴人》這本書,給我帶來的衝擊是多方麵的,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場思維的旅行,一次情感的洗禮。從封麵那個引人遐想的名字開始,我就被深深吸引。隨著閱讀的深入,我越來越沉醉於作者營造的那個獨特氛圍之中。那種懷舊感,那種對過往歲月的眷戀,卻又帶著一種現實的殘酷,讓我既感到溫暖,又有些心酸。我常常會因為書中某個角色的遭遇而感到憤慨,又會因為他們身上閃爍的人性光輝而深受感動。作者的敘事節奏掌握得非常好,既有娓娓道來的溫情,也有直擊人心的力量。每一個章節的轉換,都像是翻過一頁泛黃的老照片,上麵記錄著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但都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那個特殊的時代和那些在其中掙紮求生的人們。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繪日常生活細節上的功力,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場景,卻充滿瞭生活的智慧和情感的張力。讀這本書,就像是和一群老朋友在聊天,他們嚮你講述自己的經曆,讓你感受到生活的艱辛,也讓你看到希望。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淡淡的憂傷,但又充滿瞭力量,它讓我們重新審視過去,也讓我們更加珍惜現在。
評分《後的耍猴人》這本書,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讓我對那個已經遠去的時代有瞭全新的認識。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耍猴人”的背後會承載如此多的故事和情感。但讀著讀著,我發現這不僅僅是關於一個職業,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無數普通人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求生。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語言樸實卻富有力量,能夠不動聲色地將讀者帶入到故事之中。我尤其喜歡作者對人物心理的細膩刻畫,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渴望、無奈、以及不屈的意誌,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每一位讀者,或許都能從這些角色身上找到共鳴,看到自己或者身邊人的影子。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種沉甸甸的真實感,它沒有虛構的浪漫,也沒有刻意的煽情,隻是用最樸素的方式,展現瞭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軌跡。我常常會在閱讀的時候,停下來,想象那些場景,想象那些人物的錶情,他們的眼神裏,似乎都訴說著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這種力量,源自於作者對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對人性的洞察,也源自於那些真實存在過的生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